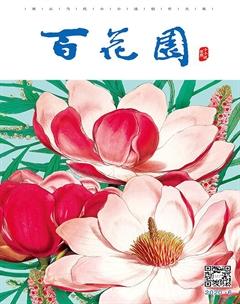李新貌
七戒

李新貌是瓦城机务段的火车司机,人称“李大车”。20世纪80年代,瓦城习武风挺盛,在机务段,李大车也是一个练家子。他练大成拳,也练螳螂拳。他还带了俩徒弟,一个叫万三,一个叫姜四,经常到东山花园树林里的空地上练功。俩徒弟比较“作”,但也没大恶,后来都在严打期间被枪毙了。
机务段还有一个叫石老五的练家子,是修理火车头的,不玩传统武术,玩散打和拳击。他瞧不起练“传武”的,说都是些花拳绣腿,中看不中用。李大车闻听石老五对“传武”不敬,就气不打一处来,找人带话过去,定个时间地点,比画比画。
石老五正想印证一下自己的实战能力,就一口答應,比画就比画。比画的结果是,石老五一顿组合拳把李大车打倒在地。
事后,有人问李大车:“怎么搞的,输得那么惨?”李大车说:“我的‘杀人技没用,用必当场死人。我师父对我说过,术高莫用。你们外行看不出来,石老五打我,已经被我内力所伤。过个十年八年的,你再看他。”
十年后,石老五死于癌症,才五十出头的年纪。有人对李大车说:“还是你内力厉害,石老五不知天高地厚。”李大车连忙解释说:“和我无关,和我无关。”
20世纪90年代,李大车不练“传武”改练气功,有空就盘膝打坐。时间久了,他说自己开了“天眼”。一次,他去运用工程师的办公室闲扯,对工程师老白说:“白工,我可以看见你的脑浆子,你信不?”老白说:“去去去,出去,我还有活儿呢,你能看见我脑浆子,我看你是脑子进水了。”
半年后的一天晚上,下大雨,李大车操纵一列重载货物列车爬万家岭车站南的大坡。由于下雨,车轮空转,车速越来越慢。副司机有点儿慌了,说:“师傅,这个位置要是停车了,再起车就困难了。”李大车说:“慌啥?你过来开车,待我发功,我一发功,就能爬上去。”他把副司机拽到自己的位置上,让他开车,自己则在副司机座位上盘膝打坐,口中念念有词……
列车最终没有爬坡成功,停车了,只能请求救援。调度员又派了一个火车头过去,两个火车头一个拉一个推,才爬上坡顶。这一耽误,后面的几列旅客列车全部晚点一个多小时,后果严重。
车队决定让李大车暂时不要开车了,下来干点儿杂活儿,扫扫地,收拾收拾卫生间。一个多月后,李大车找车队长,要求上车。车队长说:“你去精神病医院看看病,如果精神没问题,马上叫你上车。”看病的结果是,李大车精神方面确实有问题。后来经权威人士鉴定,发给李大车一个证,俗称“彪子证”。
只有火车司机才有资格叫“大车”,李大车开火车是不可能了,所以逐渐地就没人叫他“李大车”了,直接就叫他真名“李新貌”,背后则称之为“李彪子”。
李新貌有“彪子证”,上不上班也没人管,工资还得照开,就是奖金少点儿。一次我看见他坐在一段平时基本不用的钢轨上,蓬头垢面,脑袋缠着几圈铁丝,做成一个天线状指着天空,手里拿着一个铁锤,咣咣砸钢轨。我喊他:“李师傅,你这是在干吗?”他答:“给外星人发射信号啊!”我忍住乐,说:“快走吧,一会儿火车过来了。”他看我一眼说:“你说你彪不彪?你看这轨道,都生锈了,能有火车过来?再说了,我就是开火车的,火车敢撞我?你知不知道铁锈是啥化学成分?三氧化二铁……”
李新貌有“彪子证”,领导们都怵他,看见他老远就躲了。机务段有个小百货商店,李新貌没事儿就往那儿出溜,买东西不给钱,拿起来就走。售货员给主管领导打电话,领导说:“记账,算公家的。”
有一次机务段开职工代表大会,某领导正在台上讲话。李新貌冲上台去,一把将领导的麦克风夺下,说:“你瞎白话什么?你会说什么东西?你们领导班子的腐败问题怎么不说说?”领导急忙去夺麦克风,李新貌就拿着麦克风围着桌子转圈……台下的人都笑得前仰后合。
李新貌被火车撞死后,机务段工会组织一些人去送他最后一程。殡仪馆工作人员很敬业,给李新貌的遗体整容化妆。我发现长年不修边幅脏兮兮的李新貌,经一番捯饬,不但好看、精神多了,嘴角好像还挂着一抹神秘的微笑。有人调侃说:“李新貌,李新貌,旧貌换新颜……”有人喊:“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我们鞠躬后出来,当时,很多人的眼圈都是红的。
[责任编辑 王彦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