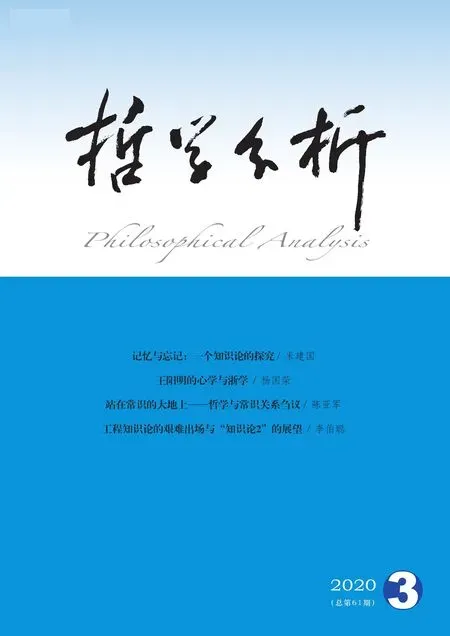“忘”有三种定义吗?①
——关于“忘”的哲学反思
邓文韬
引 言
哲学家贝内克(Sven Bernecker)指出:“如同记忆,忘不是单一的现象。”②Sven Bernecker,Memory:A Philosophical Stud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0,p.98.关于记忆或回忆的哲学讨论宛如恒河沙数。在史丹福哲学百科全书(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线上哲学百科全书(Internet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和劳特里奇哲学百科全书(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中都可见讨论记忆或回忆的条目。奇怪的是,相比之下,哲学讨论忘的定义彷似牛山濯濯。而且,在上述的哲学百科全书中都没有讨论“忘”的条目。反而,其他学科如心理学、脑神经科学、人类学等领域都纷纷提出“忘”的概念。很多哲学家都理所当然地运用了这些“忘”的概念,而未加以反 思。
本文旨在批判地分析“忘”的三种定义。本文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说明“忘”作为“提取失败”定义的困难及其解决方法。第二部分阐释“忘”作为“信息缺失”定义的困难及其解决方法。心理学、脑神经科学,甚至哲学领域都习以为常地接受两种忘的定义。然而,学界一直忽略的是在上述定义外,忘的第三种可能定义:忘”作为“缺乏注意”的一个层面。这可追溯到柏拉图对“无感知” (ἀναισθησίαν)与“忘”的严格区分。前者意指从来没有形成记忆的状态;后者意指记忆从有到无的状态。由于注意不足,故欠缺编码。由于欠缺编码,故未烙印在脑海而成为记忆。虽然学界长久以来都忽略“忘”作为“缺乏注意”的定义,但笔者在第三部分论证,我们可以合理、合乎经验地支持第三种“忘”的定义。在文章结尾,笔者提出,三种忘”的定义是兼容的,因为它们分别意指记忆过程三阶段的否定。忘记作为“提取失败”“信息缺失”“缺乏注意”三种定义,分别对应“提取”“储存”“编码”记忆过程三阶段的框架。由此观之,最能概括忘的定义的就是“记忆的否定” (the negation of memory)。
一、忘作为“提取失败”
部分心理学家和脑神经科学家认为,“忘”就是记忆提取的失败(retrieval ailure)。①心理学家图威(Endel Tulving)和路夫特夫妇(Geoffrey R. Loftus and Elizabeth F. Loftus) 都是这一观点的重要支持者。其中,图威特别强调提取失败的“忘”有别于信息缺失的“忘”,详细讨论可参见Endel Tulving,“Cue-dependent Forgetting:When We Forget Something We Once Knew,It Does Not Necessarily Mean that the Memory Trace Has Been Lost;It May Only Be Inaccessible”,American Scientist,Vol.62,No.1,1974,pp.74—82;Geoffrey R. Loftus,et al.,Human Memory:The Processing of Information,East Sussex:Psychology Press,1976,pp.78—82。我观察一件事物,并将所观察的事物保存在记忆中。在此理解下,记忆并非意指特别的记忆内容,反而意指记录和保存过去观察而获取的信息之系统。而记忆的“痕迹” (trace) 意指记忆系统内被记录和被保存的信息。换言之,记忆指保存信息的系统,而记忆的“痕迹”指保存在系统内的信息。由于“痕迹”的特性是原原本本地保留过去的信息,所以记忆的“痕迹”都是原原本本地保留过去观察而获取的信息。值得注意的是,“记忆”有别于“回忆”。回忆是回溯和提取记忆的能力,借此再现保存在记忆中的信息。如果没有回忆,则保存在记忆中的信息无从再现。故此,假如一个人不能提取记忆,我们会认为他忘记了某些过去曾获取的信息。假如一个人长期不能或难以提取记忆,我们会形容他是一个健忘的人。例如,有人问我,我在哪里见过iħ=Hψ?我依稀回忆到,这是我曾经在维也纳大学名人长廊里看到的一个刻在雕像上的方程式,但无论如何反复思量我都回忆不起这个方程式刻在哪一个维也纳大学名人雕像的人名下。显然我既忘了这是物理学家薛定谔(Erwin Schrödinger)的方程式,也忘了过去因观察而获取的关于维也纳大学名人雕像的信息。在此情况下,“忘”意指无法提取保存在记忆中的信息。又例如,我经常难以回忆起早前定好的计划,明明已经计划好并记入脑中了,但总在准备行动时难以提取相关信息,反倒需要依靠太太或友人的提醒。因为我时常未能提取保存在系统内的信息,所以他们都认定我很健忘。这种对“忘”的定义,我们可以视之为“提取失败”,即,
如果S不能提取早前获取的信息X,则S忘记了X。
提取失败仅关联于记忆过程的三阶段[“编码” (encoding)、“储存” (storage)和“提取” (retrieval)]中“提取”的问题,而无关“储存”的问题。因为信息并没有缺失。当一个人处于忘了某事物的状态时,他就是处于不能提取已编码和已储存的信息。然而,这定义似乎太宽广,不够严格,以致许多直觉上不是“忘”的经验但却落入“忘”的定义。例如,我在专注地计划未来参与国际会议交流。事实上,在专注于计划的时刻,我却不能提取早前获取的信息。因为我仅仅运用了想象的能力,而没有运用提取记忆的能力。更重要的是,因为我没有任何意图提取早前获取的信息,所以这情况不涉及任何早前获取的信息。上述例子符合“忘”作为“纯粹提取失败”的定义中的前件:不能提取早前获取的信息X。“不能提取”既可以指“提取记忆的能力不足”,又可以指“没有运用提取记忆的能力”。在专注地计划参与国际会议交流时,我没有运用提取记忆的能力,故不能提取早前获取的任何信息。根据肯定前件(Modus ponens) 的推论蕴含规则,我们可以有效地宣称上述例子是“忘”的例子。
1. 如果S不能提取早前获取的信息X,则S忘记了X。(忘作为“提取失败”的定义)
2. 在专注于计划的时刻,我不能提取早前获取的信息X。
3. 故此,在专注于计划的时刻,我忘记了X。(1,3 MP)
一个人进食、行走、睡觉、看电影、即兴弹奏音乐,这些情况下人都没有运用提取记忆的能力,故都不能提取早前获取的特定信息。如果我们接受“纯粹提取失败”的定义,姑勿论我们当时是否意图提取早前获取的信息,只要我们没有运用提取记忆的能力,我们就是处于“忘”的状态。这显然有违我们运用“忘”这一词汇的直觉。
那么,我们可以收窄忘的定义,多加入一个条件:意图提取早前获取的某信息。这保留了忘作为“提取失败”的基本定义。此时,“忘”的定义可微调为:
如果S意图提取早前获取的信息X,但不能提取早前获取的信息X,则S忘记了X。
这个微调可以排除无意图提取早前获取某信息的情况,遂可以排除无关回忆的情况落入“忘”的定义。例如,一个人意图提取早前获取的关于哲学家康德出生年份的信息,但不能提取早前获取的信息1724年,则那个人显然忘记了康德出生年份是1724年的信息。相反,一个人没有意图提取早前获取的关于哲学家康德出生年份的信息,即使他不能提取早前获取的康德出生年份的信息,那么,他仍不算忘记了康德出生年份是1724年的信息。然而,部分学者如弗里斯(Matthew Frise)仍然认为,经过微调后的定义不够严格。他提出被称为LEAD的忘记理论(定义)。LE指学习learning);A指读取或提取失败(access failure);D指意向或意图(dispositional)。这三点都是忘的必要条件。结合上述三个必要条件,他明确指出忘的定义是:
忘可以被视为:未能读取或提取某人曾经习得并当下意图读取或提取的信息
(Forgetting can be failing to access something that was learned and is intended to be acc essed)。①Matthew Frise,“Forgetting”,in Michaelian,Kourken,Dorothea Debus and Denis Perrin(eds.),New Directions in the Philosophy of Memory,New York and London:Routledge,2018,p.233.
相较之下,弗里斯的定义补充了关于信息的性质。弗里斯的定义和微调定义都同样包含:(1)信息是当下被意图读取或提取的;(2)信息是当下未能被读取或提取的。但弗里斯的定义和微调定义的不同之处在于,费斯强调信息是“曾经习得” (was learned)的,“你不能忘了你从未习得的信息……在忘的时候,忘要求学习(learning)”②Matthew Frise,“Forgetting”,p.32.。字面上,“曾经习得”和“早前获取”似乎分别不大。但其实个中涉及更精细的理论预设。虽然弗里斯没有说明,但我们可以借用心理学对学习learning)和加固(consolidation)的关系说明其中的关键。③Endel Tulving and Martin Lepage,“Where in the Brain is the Awareness of one’s Past?”in Daniel Schacter and Elaine Sacrry(eds.),Memory,Brain,Belief,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1,p.218;Alan Gauld,“Memory”,in Edward Kelley and Emily Kelley(eds.),Irreducible mind:Toward a psychology for the 21st century,Maryland:Rowman & Littlefield,2007,p.278.早前获取的信息不会自然储存成为记忆,从观察而获取的信息必要通过学习过程中的加固才会形成长期记忆(long-term memory),储存在记忆系统中。否则,仅仅从观察而获取的信息没有经过加固,只能形成短期记忆,暂存在记忆系统中。我们可以设想两个懂得中文字的人,他们分别进入一个教室,并坐在一张书桌前。书桌上有一张同样写满中文字的纸张。两个人都有两分钟时间观察阅读纸张上的中文字。其中一人观察阅读纸张上的中文字后马上到另一间房接受提问,而另一人则可以继续留在教室,虽然写满中文字的纸张被回收,但留在教室的人可以继续在脑海中回忆加固。经验显示,经过加固的人比未经过加固的人有更牢固的记忆。①一些类似的实验亦印证了这一设想。详情可参见Hilde A. Lechner,Larry R. Squire,and John H. Byrne.“100 years of Consolidation—Remembering Müller and Pilzecker”,Learning & Memory,Vol.6,No.2,1999,pp.77—87;Michael C. Anderson,“Rethinking Interference Theory:Executive Control and the Mechanisms of Forgetting”,Journal of Memory and Language,Vol.49,No.4,2003,pp.415—445。由此观之,“曾经习得”的信息经过加固较“早前获取”而未经过加固的信息更牢固地储存在记忆系统中。弗里斯的LEAD定义能够更精确地指出,忘是“曾经习得”的信息(长期记忆)的提取失败,而非任何信息(短期记忆和长期记忆)的提取失败。
二、忘作为“信息缺失”
弗里斯的定义或许更精密,可避免过宽的外延。但他的定义仍然以“提取失败”为核心,却未包含“忘”作为“信息缺失”的情况。在日常理解中,人们不会仔细区分记忆过程三阶段。更多人认为,“忘”相对的概念不是提取(回忆),反而是储存(记忆)。“忘”更普遍地被理解成储存困难和由限制所导致的“信息缺失” (loss of information)。②讨论信息缺失的学者都默认了忘作为“信息缺失”的定义。他们旨在讨论“忘”的重要性及其积极作用。其中,麦尔—荀伯格和米克艾力安特别指出,忘作为“信息缺失”的美德(virtue)。如果信息过多,甚至泛滥的话,则会影响认知系统和记忆系统的功能,轻则减慢提取信息的速度及可靠性;重则瘫痪整 个 系 统 的 运 作。详情可参 见 Viktor Mayer-Schönberger,Delete:The Virtue of Forgetting in the Digital Age,Cambridge: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1;Sven Bernecker and Thomas Grundmann,“Knowledge from Forgetting”,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Vol.98,No.3,2019,pp.525—540;Kourken Michaelian,“The Epistemology of Forgetting”,Erkenntnis,Vol.774,No.3,2011,pp.399—424。
忘作为“信息缺失”的定义:仅若S缺失原本储存在记忆系统中的信息X,则S忘记了X。
我们可以模拟计算机的信息缺失来理解“忘”作为“信息缺失”的定义。假如计算机储存信息的硬盘(hard-disk)受损或信息从硬盘中被删除,则原本储存在硬盘中的信息便缺失了。计算机亦因此不再可能提取相关信息。在此模拟中,计算机被模拟为人脑;硬盘被模拟为记忆系统。原本储存在记忆系统的信息一旦永久或暂时地缺失,人们都不能提取相关信息。这一定义不仅兼容于“忘”作为“提取失败”的定义(不能提取早前获取的信息X),而且更进一步解释了“提取失败”的原因。因为信息缺失,自然无所提取,所以未能提取相关信息。
可是,“忘”作为“信息缺失”的定义绝非无懈可击。在忘作为“信息缺失”的定义中,“缺失”有歧义。“缺失”可以表示两种程度的缺失:永久丧失和短暂隐藏。从量而言,顾名思义,“永久”丧失的缺失是“永久”的,而“短暂”隐藏的缺失是“短暂”的。从质而言,永久“丧失”的缺失是“消失殆灭”的,而短暂“隐藏”的缺失是“隐藏不显”的。将两种不同程度的缺失放到“忘”作为“信息缺失”的定义中,我们可以进一步区分“永久忘记” (permanent forgetting)和“短暂忘记”temporal forgetting)。①Sven Bernecker,Memory:A Philosophical Stud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0,pp.198—201. 贝内克在第7.4节特别讨论到这两种类型的“忘”。永久忘记的情况下,原本储存在记忆系统中的信息永远地完全消失,不再存在于记忆系统中;相反,短暂忘记的情况下,原本储存在记忆系统中的信息仍然存在于记忆系统中,只不过暂时隐藏于当下。前者不再可能重现(unavailable),而后者可能再现,但现时不能进入(inaccessible)。那么,“忘”作为“信息缺失”的定义必须再细分为“永久丧失信息”的“忘”和“短暂隐藏信息”的“忘”:
(1)永久忘记(忘作为“永久丧失信息”)的定义:仅若S永久丧失原本储存在记忆系统中的信息X,则S忘记了X。
(2)短暂忘记(忘作为“短暂隐藏信息”)的定义:仅若S短暂隐藏原本储存在记忆系统中的信息X,则S忘记了X。
这两个定义是互不兼容,甚至矛盾的。在这两个条件句中,“仅若”所关联的内容是条件句的后件,而“则”所关联的内容是条件句的前件。换言之,(1)可以翻译成若S忘记了X,则S永久丧失原本储存在记忆系统中的信息X”;(2)可以翻译成若S忘记了X,则S短暂隐藏原本储存在记忆系统中的信息X”。如果S永久丧失短暂隐藏原本储存在记忆系统中的信息X,则S不可能短暂隐藏原本储存在记忆系统中的信息X,反之亦然。从时间而言,S不可能既永久又短暂地失去信息X。这在概念上是不兼容的。从性质而言,信息X不可能既存在又不存在于记忆系统中。这在逻辑上是矛盾的。由此观之,“缺失”的歧义显示出,“忘”被定义为“信息缺失”的内部矛盾。
要么,我们否定“忘”的歧义及其不兼容和矛盾;要么,我们接受“忘”的歧义及其不兼容和矛盾。贝内克否定上述歧义。他断言,“我们从不会永久地忘”,而且“人类忘的所有例子都是短暂忘记的情况”。①Sven Bernecker,The Metaphysics of Memory,Dordrecht:Spring Science & Business Media,2008,pp.25—26.他通过否定“永久忘记”,消解了“缺失”的歧义及其引发的不兼容和矛盾。然而,他后来修正了这一观点,并与米克艾力安等学者的观点一致:永久忘记和短暂忘记是有效且符合事实的区分,不过,永久忘记的实例却很罕见。②Sven Bernecker,“On the Blameworthiness of Forgetting”,in Michaelian,Kourken,Dorothea Debus and Denis Perrin(eds.),New Directions in the Philosophy of Memory,New York and London:Routledge,2018,p.244.Kourken Michaelian,“The Epistemology of Forgetting”,p.400.
相比之下,永久忘记的实例的确远较短暂忘记的实例少。大部分例子出现的情况是:人的大脑颞叶、海马回、杏仁核与视丘等部位严重损伤下,或因年龄引发的退化下,造成记忆能力失常,则有可能导致记忆力衰退甚至是完全丧失。例如,一位23岁的俄罗斯士兵萨硕斯基(Zasetsky)因为在“二战”中脑部左枕顶区域(left occipito-parietal region)严重损伤,导致他患上了失忆症(amnesia)和失语症(aphasia)。在受伤后的早期生活中,他完全想不起身边各种事物的名称,甚至在想要表达的时候都想不起一些单词。③Alexander R. Luria,The Man with a Shattered World,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2,p.19.在他躺在病床上时,他需要一个储尿桶,无论他多么努力意图提取相关事物名称的信息,他就是想不起来。根据他自己后来的形容,“我就像生活在一片迷雾当中,仿佛一直都在半梦半醒的状态中,我的记忆一片空白。”他似乎完全丧失了原本储存在记忆系统中的方向、事物名称等信息。④Ibid.,pp.88—89.或许,有人会质疑萨硕斯基能否作为永久忘记的例子。因为当护士走过去问萨硕斯基是否需要储尿桶并用手指指向储尿桶时,萨硕斯基却意外地可以理解护士所说的名称,并回答护士。而且,萨硕斯基经过训练后,在他后期生活中,能重新运用很多字词,写了超过3000页的日记。由此看来,即使脑部受到严重损伤,通过适当训练,他仍然能够再重新学习丧失了的信息。然而,如果我们仔细留意,萨硕斯基的确是永久丧失了原本储存在记忆系统中的信息。他能够理解护士所说的名称和写超过3000页的日记的原因是,他“重新”获取了相关信息。在他脑部严重损伤后,原本储存在记忆系统中的信息X已经永久丧失。他重新学习并储存在记忆系统中的信息是Y。虽然X和Y都是意指“储尿桶”,但萨硕斯基获取此信息的方式和背景都大相径庭。X是童年时在家中从父母处习得,但Y却是受伤后在医院从护士处习得。可见,上述质疑不能否定萨硕斯基作为永久忘记的例子。又例如,脑神经科学家戴维斯(Michael Davis)的母亲患上脑退化症或失智症dementia),神经细胞逐渐地死亡。在母亲患病早期时,戴维斯询问她自己在哪里出生。即使她母亲不再知道戴维斯是谁,她仍然能够回答戴维斯,她在密歇根州的迪尔伯恩出生。当母亲患病晚期时,她不再记得她在哪里出生,而且从磁力共振成像所见,她的大脑已没再剩下任何神经细胞。由于戴维斯母亲的所有脑神经细胞不再复原,故不仅失去所有记忆力,而且永久丧失了原本储存在记忆系统中的信息。贝内克和米克艾力安进行关于“忘”的哲学讨论时,都强调关注“正常”的“忘”:短暂忘记。他们显然接受,甚至暗地肯定“忘”的歧义:永久忘记和短暂忘记。基于这一区分,他进而提出“正常”和“不正常”的区分,短暂忘记是正常,因为它常见,而永久忘记是不正常,因为它罕见。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必须接受“忘”的歧义及其不兼容和矛盾呢?
永久忘记的定义有一个困难。从方法论上,我们难以确定原本储存在记忆系统中的某项信息是否为永久丧失。人们可以通过其他人的说话或其他的记忆提示memory cue)去回忆暂忘的信息。在回忆成功后,他们可以确认刚刚真的暂忘了的某项信息。我们可以设想一个思想实验,有一天,陈太太突然问陈先生记得求婚纪念日是哪一天吗?陈先生思前想后都想不起来。陈太太指向拍拖纪念日的照片,但陈先生都不以为然。她按捺不住,直接跟陈先生说,求婚纪念日和拍拖纪念日是同一天。此时,陈先生恍然大悟,求婚纪念日是2月23日。在这一例子中,陈先生忘记了两项信息:(1) 求婚纪念日和拍拖纪念日是同一天;(2)求婚纪念日是2月23日。陈先生如何发现他自己忘记了这两项信息?当他发现自己忘记了(2)时,他才发现自己同时忘记了(1)。一方面,陈先生通过陈太太的第三段明言求婚纪念日是2月23日的说话去回忆起(2)。另一方面,陈先生通过反思陈太太的第二段暗示求婚纪念日和拍拖纪念日都是2月23日的记忆提示去回忆起(1)。在成功回忆起(2)和(1)后,陈先生才能确认刚刚真的暂忘了信息(1)和(2)。由此观之,确认短暂忘记现象是一个后设认知,通过后设反思,我们可以第一身确认刚刚短暂忘记及被暂忘的信息。相反,我们不可以第一身确认永久忘记及被忘的信息。原本储存在记忆系统中的信息永久消失殆尽意味着,忘记者不可能通过他人的说话或其他的记忆提示(memory cue)去回忆被忘记的信息。那么,有其他方法确认永久忘记及被忘的信息吗?在当下的脑神经科学和认知心理学中都没有任何方法确认永久忘记。即使被视为永久忘记的例子,如萨硕斯基和戴维斯母亲,研究人员都是借其脑伤或脑退化和其异常的记忆力去“推论”他们受永久忘记所影响。我们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永久忘记。正如戴维斯坦言,“这个定义(‘忘’作为‘永久丧失信息’的定义)的明显问题是在现阶段不可能在任何生物上作相关的测量,遂因此建基这些因素,我们仍然不能确认这种‘忘’(永久忘记)事实上发生。”①Michael Davis,“Forgetting:Once Again,It’s All About Representations”,in Henry L. Roediger III(eds.),Science of memory:Concept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p.318.即使我们仍然不能在第一身观察的方法上确认这种忘记(永久忘记)事实上发生,但我们可以有两种方式回应这方法论上的困难。第一,我们可以提出,忘的歧义——短暂忘记和永久忘记——只是概念的设想。假如它只是概念的设想,那么,“永久忘记”这一设想而生的概念可以免去第一身观察的方法论要求。正如,我们方法论上要求“圆方”(round square)第一身观察,是多么荒谬的事呢?第二,我们可以通过第二身或第三身推断确认这种忘记(永久忘记)事实上发生了。医生或研究人员可以查问永久忘记者的家人,甚至追查永久忘记者的日记、图像文件资料等数据,借此判断永久忘记者是否事实上永久忘记某事物。故此,上述方法论的困难不足以推翻“忘” (永久忘记) 的定义。
三、忘作为“缺乏注意”
当代西方学界对“忘”的讨论主要集中在“提取失败”和“信息缺失”的定义,却鲜有讨论“忘”作为“缺乏注意”的定义。这一忽略可追溯至柏拉图的论述。一方面,他断言,记忆就是“感知的保留” (preservation of perception)。②Plato,Philebus,Oxford:Clarendon Press,1975,p.27. 34a10.另一方面,他用书写的比喻说明感知信息与记忆的关系。③Ibid.,pp.34—36. 38e—39a.柏拉图强调,当感受(affection)穿透身体,又穿透灵魂,这样才可以被称为感知。感知必定伴随感受。灵魂彷如一本书。从感知的信息伴随感受渗入(penetrate)我们的身体,感知的信息才可以刻印在我们的灵魂。刻印在灵魂的过程彷如书写在书本的过程。大力书写,能深刻在书本;但轻柔书写,只能浅印在书本。如果没有用力书写,就不能在灵魂中有任何印象。同样,越强烈的感受,越能深刻在灵魂;越薄弱的感受,越能轻描淡写在灵魂。如果没有伴随任何感受,就不能在灵魂中有任何印象。如果不能在灵魂中有任何印象,则没有感知信息。没有感知信息,则没有感知的保留;没有感知的保留,则没有记忆。那么,信息没有伴随任何感受而被接收是如何一回事?
在柏拉图的《斐莱布篇》 (Philebus)中,苏格拉底提及一种现象:信息仅渗入我们的身体但未渗入我们的灵魂。④Ibid.,p.27. 33d8.如果信息仅渗入我们的身体但未渗入我们的灵魂,则不能视之为感知。他把上述状态命名为 lack of sensation(ἀναισθησίαν)。Ἀναισθησίαν可字面上分为ἀν和αισθησίαν两部分。ἀν意指“潜在、非实在”的“无”或“缺乏”,αισθησίαν意指“感知”。①关 于 这 部 分 的仔细 讨 论,可 参 见 Tang Man-to,“ἐπιλήθομαι(epilelesthai) and λήθη(lethe):On Plato’s Philosophy of Forgetting”,SOCRATES,Vol.5,No.3—4,2018,pp.51—53。Plato,Philebus,p.27. 34a5.Ἀναισθησίαν可被翻译成“无感知”。②Ibid.,p.27. 34a5.根据柏拉图的观点,“无感知”就是“信息仅渗入我们的身体但未渗入我们的灵魂”的现象。当代的记忆研究或许可以进一步解释柏拉图的观点,而且说明“无感知”与缺乏注意”有何关系。
外来的信息不会自然成为记忆。外来的信息要首先经过编码的过程,才能转换成符合内在的心理表征(mental representation)。转换成符合内在的心理表征,才能进一步储存为记忆。相反,没有编码的过程,则不可能转换成符合内在的心理表征。编码的过程是记忆形成的必要条件。“信息仅渗入我们的身体但未渗入我们的灵魂”意味着,外来的信息仅被感知器官接收,但尚未经过编码过程。在此情况下,外来的信息没有转换成符合内在的心理表征,自然不能进一步储存为记忆。“无感知”可以被理解成“信息未经过编码过程”的现象。那么,为何信息未经过编码过程?如果在编码过程,有充分注意力(attention),就易于产生“准确编码”,外来的信息就能够转换成“符合内在”的心理表征。这有助于线索依赖性提取(cuedependent retrieval)的速度和可靠性。但如果在编码过程,缺乏注意力,就易于产生编码失误”,甚至“编码失败”,导致提取时造成失误或失败(忘)。③相关讨论,可参见 Geoffrey Underwood,“Attention and the Perception of Duration during Encoding and Retrieval”,Perception,Vol 4,No.3,1975,pp.291—296;Daryl Fougnie,“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ttention and Working Memory”,New Research on Short-term Memory(Vol.1),2008,p.45;Marvin M. Chun,et al.,“Interactions between Attention and Memory”,Current Opinion in Neurobiology,Vol.17,No.2,2007,pp.177—184。安德伍德(Underwood)和覃(Chun)的团队研究都兼论注意力和提取的关系,并提供了一些认字或人脸辨识的实验佐证。有注意力,就有编码过程;缺乏注意力,就没有编码过程。没有编码过程,就衍生出“无感知”现象。所以,缺乏注意,就衍生出“无感知”现象。
在提及“无感知”时,苏格拉底特意跟他的对话者普罗塔库(Protarchus)说明,无感知”不等同于“忘”。一方面,“忘”是“记忆缺失” (loss of memory)的状态;另一方面,根据柏拉图感知和记忆关系的观点,记忆就是“感知的保留”。这表示,无感知,则无感知的保留;无感知的保留,则无记忆。“无感知”都是“记忆缺失”的状态。④Plato,Philebus,p.27. 33e5.虽然两者性质一样,但苏格拉底强调两者的差异。“忘”是一种记忆从有到无的记忆缺失,但“无感知”从来都“无”感知,不可能有“感知的保留”,所以“无感知”不等同“忘” (记忆从有到无的记忆缺失)。
然而,“忘”必定是一种记忆从有到无的缺失吗?我们可以从两方面论证“忘”作为“缺乏注意”的定义。首先,我们可以从推论上支持“忘”作为“缺乏注意”的定义。
1. 如果我们没有忘X,则我们有关于X的记忆。(直觉)
2. 我们没有关于X的记忆。(缺乏注意导致“无感知”现象)
3. 故此,我们忘 X。(1,2 MT,DN)
这是一个有效的推论。我们可以有理由地支持一种“忘”作为“缺乏注意”的定义。其次,在日常生活中不难理解,这种忘记作为“缺乏注意”的定义。如果我们有一个特定的目标时,即使身旁出现不同的事物,我们都可以视若无睹。“视若无睹”的说法近似柏拉图在《斐莱布篇》中所讨论的没有经过编码过程的“无感知”。虽然我视觉上感知某物,但被感知的事物没有刻印在我脑海之中,仿佛过眼烟云。如果我对身旁出现的不同事物视若无睹,甚至连自己的生活都不顾,仅仅专注于特定的目标,则可能出现“废寝忘食”现象。“废寝忘食”现象中的“忘”同样既无关提取,亦无关储存。反而,这种“忘”是缺乏注意的意思。我们可以设想,专注于温习而“废寝忘食”者或许有饿和累的感受,或许望到身旁的床和食物,但他不注意这些东西,只专注于温习,遂其他事物都被忘掉。有别于“提取失败”和“储存失败”的忘记的定义,这种“忘”相对的概念是注意地关顾、理会。由于我们不注意地关顾、理会,故感知物跃入眼帘后并未进行编码,遂没有记忆。故此,我们显然有“忘”作为“缺乏注意”的日常语用经验。
忘作为“缺乏注意”的定义:如果S接收某信息X时缺乏注意力,X不加以经过编码的过程,则S没有关于X的记忆(S忘X)。
脑神经科学家弗里德曼(Michael C. Friedman)和卡斯蒂尔(Alan D. Castel)亦认为,“缺乏注意”所导致的记忆缺失亦可被视为“忘”的一种。他们举出一个日常例子。如果我们记着停车场内所有不同的泊位,则我们难以找出自己车辆今天所停泊的正确位置。所以当我们有目标地关注我所停泊的正确位置时,我们必须“忘掉”不相干的信息。“这因时制宜性质的忘记能让我们保持最新、最相干的信息,同时也能让我们忘记在未来会变得无关系的信息。”①Michael C. Friedman and Alan D. Castel,“Are We Aware of Our Ability to Forget?Metacognitive Predictions of Directed Forgetting”,Memory & Cognition,June 2011,p.448.他们所论及的这种忘记既无关提取,亦无关储存。早在储存之前,信息已经被“抛诸脑后”,借此能让我们专注于关顾和理会与特定目标最相干的信 息。
结 论
总之,“忘”作为“提取失败”“信息缺失”和“缺乏注意”这三种定义各自有其内部困难。在“忘”作为“提取失败”的定义中,争议点在于不能提取的信息有什么性质。如果“不能提取”意味着无需运用提取的能力,则不能提取的信息可以泛指任何无需运用提取的能力而生的信息,如想象的信息、感知的信息。故此,不能提取的信息必须加上曾经在早前习得的性质。在“忘”作为“信息缺失”的定义中,争议点在于缺失的意思。缺失可以有永久丧失和短暂隐藏两种意思。但缺失的歧义既不能同真亦不能同假,这导致两种“忘”在作为“信息缺失”的定义中互相矛盾、不兼容。故此,从普遍性和缺失的程度作区分有助于消弭其中的矛盾和不兼容。“忘”作为“缺乏注意”的定义最大的困难在于,早在柏拉图的哲学中已经否认这一种定义的忘。故此,提供有效的论证和“忘”的日常经验有助于支持这一定义的合法性。
无可否认,各种忘的定义都能够把握忘记的某些性质。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忘忘”有三种性质迥异的定义?从狭义的“忘”而言,答案是肯定的。三种“忘”的定义显示三种迥异的性质,而且不能互相化约。这三种迥异的性质对应记忆过程的提取”“储存”和“编码”三个阶段。“忘”作为“提取失败”的定义意指“提取”的否定;“忘”作为“信息缺失”的定义意指“储存”的否定;而“忘”作为“缺乏注意”的定义意指“编码”的否定。我们可以用下列的表格理解它们的关 系:

记忆的过程 忘的定义提取提取失败储存信息缺失编码缺乏注意
由此观之,每一种“忘”的定义都是对记忆过程各阶段的否定。然而,从广义的“忘”而言,“忘”没有三种性质迥异的定义,反而三种定义都指向一个更根本的定义:“记忆的否定” (the negation of memory)。因为三种定义——“提取失败”“信息缺失”“缺乏注意”——都不外乎记忆三阶段的否定。①“提取失败”“信息缺失”和“缺乏注意”是忘的定义,但碍于篇幅所限,这些定义之间有何关系、是否与“提取”“储存”和“编码”记忆三阶段一样有“阶段”的关系未能在本文展开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