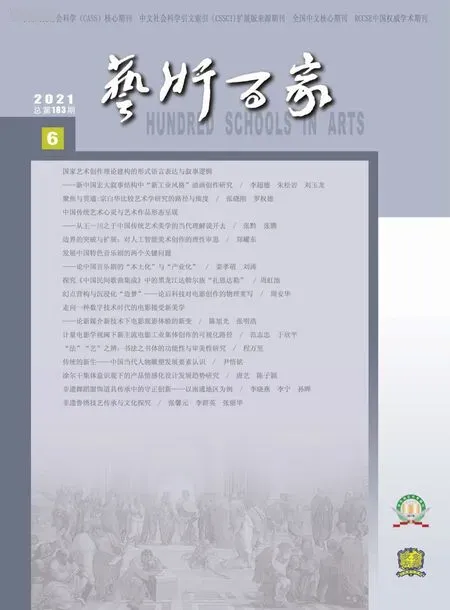从主体迁变到话语重塑∗
——中国电影批评话语的“同时代性”思考
周 旭
(四川外国语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重庆 400031)
在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中,话语不仅体现着对应的权力,还建构着主体并支配其进行话语实践。就电影批评而言,由于批评主体的话语实践有其相应的物化形态,并且与批评相关的一切都会以或显或隐的方式投射到批评家的话语实践中去,这就为我们窥探批评家“身体”上的权力印痕,及其应对权力的曲折心境提供了言说的证据。数字媒介建构的赛博空间,不仅催动着中国电影批评主体的迁变与话语重塑,也为批评主体带来了新的境遇与写作焦虑。这种批评主体身份的迁变,至少可以引发三个层面的思考:第一,对于专家批评而言,相对封闭的纸质媒介从传播模式和传播渠道上维护着专家批评的话语霸权,但进入赛博空间以后,不管专家们是否愿意,他们都将与各种未知的人群相遇,人人都成了发言的主体;第二,对于大众批评而言,匿名书写是他们活动的资本,他们像游民一样在比特之城里游荡,聚集在各种话语广场,以肆意狂欢、反抗和个性化的姿态颠覆着原有的话语秩序;第三,从批评话语实践层面看,电影批评话语的生成受制于社会文化、媒介环境、批评主体身份等多种因素,所以电影批评话语研究不能摈弃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而是要把批评主体的身份特征、话语焦点、话语策略等与社会文化联系起来,考查电影批评话语的“同时代性”特质。
一、批评的力量:左翼影评小组与革命话语实践
李道新教授在《中国电影批评史(1897—2000)》一书中,把中国电影批评划分为社会学批评、本体批评和文化批评三大阶段,并将社会学批评又细化为电影的伦理批评、新文化批评、救亡批评、社会批判、政治批评、大批判、社会功利批评七个时期。这种划分标准虽然显得比较宏观,却道出了中国电影批评发展的文化脉络。与之同时,社会学批评、本体批评和文化批评这三种批评还暗藏着另一个划分标准,那就是不同时期的电影批评有着不同的话语焦点。的确,电影批评作为一种话语现象,不仅要受制于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还要受到更深层次的社会关系,如社会机构、媒介环境、批评主体的身份等因素的制约。因此,任何时期的电影批评不可能只是一种简单的电影文化现象,它必然与特定的社会关系勾连在一起,呈现为独属于某一历史时期的话语实践活动。譬如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电影批评,并不是偶然的迸发式的激情产物,而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更是现代知识分子、爱国进步人士实现救国救民思想启蒙的自觉选择。左翼电影批评作为一种革命话语的实践,其发生背景、批评主体构成以及批评话语焦点都显现出强烈的时代烙印。
首先,从社会背景层面看,左翼电影批评的发生既是特定历史时期社会文化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中国共产党进行文化宣传的政治需要,更是左翼知识分子为了宣扬反帝反封建革命思想而进行的话语实践。左翼电影批评作为左翼电影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发生自然与当时左翼电影运动爆发之时代背景密不可分。1930年代的中国,内忧外患,灾难重重。特别是在“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救亡运动席卷而来,抗日救国成为各种文艺创作的重要表现题材。但就电影发展而言,一方面,当时的电影市场基本上被外国影片所垄断,影片内容大多是关于“帝国主义侵略弱小民族的”,或者是表现“美国人生活方式的影片,不少是色情的东西,不堪入目”;[1]1另一方面,中国自己的电影创作仍被“一片乌烟瘴气的武侠神怪电影所笼罩”[2]74,“据不十分精确的统计,1928年至1931年间,上海大大小小的约有五十家电影公司,共拍摄了近四百部影片,其中武侠神怪片竟有二百五十部左右,约占全部出品的百分之六十,由此可见当时武侠神怪片泛滥的程度”[3]133。直到20世纪30年代初,随着全国抗日救国热情的持续高涨,“武侠神怪影片在革命舆论的抨击和广大观众的唾弃下,才逐步地没落了”[3]136。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左翼电影人为了响应风起云涌的社会革命思潮,积极投身到文艺革命斗争中,具体做法包括:一是通过译介苏联社会主义电影理论,尤其是爱森斯坦和普多夫金等蒙太奇学派代表的电影理论,为电影“武器论”“工具论”寻求思想根源,如1932年夏衍、郑伯奇联合翻译了普多夫金的《电影导演论》《电影脚本论》等著作,并在《晨报》副刊《每日电影》上连载;还有陈鲤庭也翻译了普多夫金的《电影演员论》《苏联电影十五年》等重要文献。二是在电影创作和批评实践中自觉贯彻电影“武器论”“工具论”的文艺思想,强调“电影是阶级斗争最犀利的思想武器”[4]43,是组织群众、教育群众的良好工具。所以,左翼电影人非常注重电影剧本的创作,他们通常利用电影编剧的身份,创作一些能够唤醒民众、激发抗日热情的作品。如夏衍创作的《狂流》、《春蚕》(改编)、《上海二十四小时》,以及郑伯奇和阿英改编的《盐潮》、阿英和郑伯奇等人合作的《时代的儿女》、沈西苓的《女性的呐喊》、田汉的《三个摩登女性》《黄金时代》《民族生存》、阳翰笙的《铁板红泪录》《中国海的怒潮》《逃亡》等剧本,均比较尖锐地反映了当时的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具有很强的革命性和进步性。
其次,从批评主体的构成看,左翼电影批评的主体是“影评小组”,而“影评小组”的核心成员基本上都是共产党员,这无疑引领着左翼电影批评话语的革命性方向。1932年至1937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电影批评组织相继成立,其中“电影小组”“中国电影文化协会”“影评小组”“艺社”等都是从事电影批评的中坚力量。据夏衍回忆,中共电影小组在1933年3月成立,主要成员有夏衍、钱杏邨、王尘无、石凌鹤、司徒慧敏五人,夏衍为电影小组组长。[5]246较之“左联”“剧联”“社联”等其他左翼文化组织,早期“电影小组”的构成人员比较单一,大多是共产党员,且他们都有过革命斗争的经验。1932年7月,为了争夺电影文化领导权,左翼“影评小组”在“剧联”的领导下成立,最初由田汉负责,成员仅有黄子布(夏衍)、王尘无、石凌鹤、鲁思、徐怀沙等少数几人。此后,“影评小组”逐渐扩大,陆续有席耐芳(郑伯奇)、张凤吾(钱杏邨)、沈西苓、施谊(孙师毅)、聂耳、柯灵、陈鲤庭、唐纳、毛羽、李之华等人参加。1933年后又有尤兢(于伶)、怀昭(宋之的)、穆桂芳(赵铭彝)、张庚等人加入。[6]501933年2月,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电影文化协会”在上海成立,黄子布(夏衍)、郑正秋、张石川、陈瑜(田汉)、洪深、聂耳、蔡楚生、史东山、孙瑜、黎民伟、卜万苍、任光、金焰、唐槐秋、胡蝶、应云卫、沈西苓、姚苏凤、程步高、周剑云、李萍倩、周克、查瑞龙等31人当选为执行委员和候补执行委员。“中国电影文化协会”的宣言是号召“电影工作者亲切地组织起来,认清过去的错误、探讨未来的光明,开展电影文化向前运动,建设新的银色世界”[7]。1936年6月成立的“艺社”,虽然仍以“剧联”和“影评小组”为核心,但由于左翼电影文化运动处于低潮,革命文艺活动转入地下,仅吸纳了一些积极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影评工作者和编导等参与,并联名发表了“《反对工部局禁止演剧通启》、《争取演剧自由宣言》、《为反对异国水兵暴行宣言》、《反对日本〈新地〉辱华片宣言》等具有很强革命性的文章”[8]163。自此,左翼影评人队伍不断壮大,形成了以负责领导左翼电影理论评论工作的共产党员、进步电影工作者和一些政治方向游移不定的“同路人”等为主体的文化宣传和抗争组织。他们在电影批评实践活动中,不但要反抗国民党的文化围剿,还要同电影界的各种反动势力、电影商人斗智斗勇,以保障左翼电影创作与批评的有效开展。
最后,从批评话语的焦点看,左翼电影批评的实质是“以影评为抓手来揭露和批判社会中的不平等,揭示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态势,进而达到宣扬马列主义,唤醒民众革命意识之目的”[9]90。具体言之,左翼电影批评不但在批评实践中自觉运用社会历史的批评方法,而且还把抗战主题、爱国主义、反帝反封建、启蒙民众等革命话语与电影批评的性质和功能、电影批评的标准和方法,以及电影批评主体的自我修养等问题对接起来,体现出强烈的时代使命感和主体意识。关于电影批评的性质、任务、方法和电影批评者的自我修养等,左翼电影批评家曾展开激烈的讨论,如公吕在《批评的任务》一文中提出“电影批评卫生不卫生的问题,比好吃不好吃的问题重要得多了”[10]。同样,夏衍也认为,过去那种将影评当作“私人感情酬赠”的批评方式,只是“一种宣传和广告的延长”,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电影批评,真正的电影批评“一方面应该以启蒙者的姿态来帮助电影作家创造能够理解艺术的观众,另一方面还应该以一个进步的世界观的所有者和一个实际制作过程的理解者的姿态来成为电影制作者的有益的诤友和向导”。[11]所以,在具体的电影批评实践中,“电影批评者要把握大众的意识,一定要在实际生活和正确的理论中克服自己,一定要在实际中学习,一定要实际转变那才有办法,只靠浮薄的知识是不行的”[12]。此外,亦如王尘无所言,“在阶级社会里,一切都是阶级的。同时在阶级斗争的过程中,一切都是阶级斗争的武器。因为‘某一阶级所制造的艺术是意识地或非意识地拥护着自己的阶级’。电影当然不能例外”[13]。如是,在20世纪30年代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加剧的时代语境里,左翼电影批评人的时代责任便是把电影批评作为阶级斗争的“武器”“工具”,用以揭露和批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电影的阶级本质,激发广大民众的革命斗志。
二、批评的返魅:知识分子一代与电影本体批评
20世纪30年代,由于民族危亡、社会动荡,左翼电影批评已超越电影批评的传统功能,主动承担起了社会批评的革命责任。左翼电影批评促使电影与社会进一步发生关联,引导观众把电影虚构的影像世界与社会现实相对照。如是,电影影像因得到“电影批评的社会性阐释,最终以社会形象的方式进入民众的社会生活,并影响着民众的社会观念和思想情感”[9]138。而左翼影评人作为中国进步电影创作的思想引领者,在电影批评实践中自觉运用马列主义阶级观来分析电影、认识电影本质,较为深刻地揭示了电影艺术在阶级社会的阶级属性和重要作用。与此同时,他们不再空谈社会责任和时代使命,而是用实际行动来启迪民众觉悟,为民众代言。左翼电影批评始终坚持革命现实主义的批评原则,运用电影这一大众化的艺术形式和话语方式,介入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为1930年代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以及中国电影第一次历史性的转型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左翼电影批评这种过于强调电影艺术的意识形态性、忽视电影艺术本性的批评方法,同样给中国电影发展带来了诸多负面影响。特别是在“十七年”和“文革”时期,“中国电影批评基本上是以评判影片的政治功过是非为主要目的,以政治标准为主要或唯一的影片批评标准,以政治索隐、主题和典型形象分析等为批评方式”[14]164。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随着十年浩劫的结束,各项社会生活秩序得以开始重建,作为社会文化生活之重要部分的电影才回归到相对正常的生产、流通和消费的发展轨道上。在此种社会文化背景下,中国电影批评逐渐走出“十七年”和“文革”时期政治索隐式电影批评的阴霾,转向一种更贴近时代发展、更为自律的电影本体批评,具体表征如下:
第一,电影批评范式的全面转型,包括电影批评观念、批评方式、批评对象等都产生了非常明显的变化。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电影批评逐渐转向对电影本体相关问题的争鸣与探讨,如钟惦棐所言,“近数十年,中国电影理论方面发展的比较充分的是电影社会学,或者说电影政治学。直到今天,还很难说我们在思考电影问题时,不是首先从政治出发”[15]3。同样,陈荒煤也指出:“由于片面地强调政治标准第一,只强调文艺的政治教育作用,否认文艺的娱乐作用、审美作用等等原因,使得文艺创作的题材狭窄、形式单调,既缺乏生动鲜明的艺术形式和艺术感染力量,也缺乏深刻的思想性,把文艺创作变成了枯燥的政治说教。”[16]91而姚晓濛则认为:“‘文革’结束以后,中国的文艺批评力图摆脱纯政治的主题分析和人物性格分析的批评模式,进而加强艺术化的形式的分析,解决一个如何将作品放到理想的艺术和美学的高度来理解的问题。”[17]4故而,中国电影批评的转型首先应该纠正过去那种“政治标准第一”的错误观念,为电影创作发展做好理论层面的正确指向。电影批评者在具体的电影批评实践中,要竭力摆脱“政治标准第一”的意识形态镣铐,从艺术性和审美特性的角度,对影片的艺术形式、艺术风格、艺术成就、艺术价值等进行全方位分析。20世纪80年代,当《一个和八个》《黄土地》《红高粱》《黑炮事件》《猎场扎撒》等一批具有艺术探索和创新精神的作品出现之时,不少电影批评工作者便自觉摈弃了政治批评的方法,从电影本体的角度对这些作品的影像语言、摄影造型、叙事技巧、声画关系等给予高度评价。例如陈凯歌的《黄土地》被很多业内人士和评论家赞誉为一部有点“陌生”的佳作,“与《裸岛》相比,《黄土地》这首诗,气势更加磅礴”[18]64。甚至,有评论者直接指出:“在构图、色彩、光线、摄影机运动以及声画结合等电影造型手段的运用上,影片《黄土地》不拘泥于生活的真实,而力求充分揭示被拍摄对象的内涵,赋予它们某种诗意,以达到最大的表现效果。”[19]16总之,电影本体批评就应该侧重对电影作品镜头语言、镜头运用、画面构图、景别、影调、色调、布光技巧、场面调度、场景设计等进行分析,给予观众艺术层面的文化启迪和审美教益。此外,电影本体批评与政治批评在批评方式上也存在着较大差异。具体而言,政治批评“往往将电影作品在政治思想方面的某些缺点或错误(有些方面甚至还不能说是‘缺点’或‘错误’)无限放大、上纲上线,并结合简单、粗暴的叙述语体,对电影作品的创作者进行人身攻击”[14]168。这种居高临下、先入为主、简单粗暴地判定影片思想政治是非得失的批评方式,不仅挫伤了电影创作者的工作积极性,也阻碍了电影批评以及电影理论的发展步伐。而电影本体批评则主张在自由争鸣与探讨的基础上,从具体影片文本出发,对作品的艺术价值进行意义阐释和审美判断。以《电影评论选(故事片1981)》《电影评论选(故事片1982)》《当代中国电影评论选(下)》三部影评集为例,这三部影评集共计收录134篇文章(其中重复的6篇文章已合并计算),都属于电影批评方面较具代表性的文章。首先,从文章来源看,它们基本上都选自《电影艺术》《当代电影》《文艺研究》《文学评论》《电影文学》《电影新作》《电影评介》《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文艺报》《文学报》等比较有影响力的报刊,并且都经过编审人员的重重筛选,有较强的专业性和质量保证;其次,从涉及的影片来看,基本上囊括了1979年至1985年的重要作品,如《苦恼人的笑》《生活的颤音》《小花》《啊!摇篮》《归心似箭》《庐山恋》《巴山夜雨》《喜盈门》《天云山传奇》《沙鸥》《知音》《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小街》《邻居》《牧马人》《都市里的村庄》《逆光》《人到中年》《城南旧事》《青春万岁》《武林志》《咱们的牛百岁》《红衣少女》《高山下的花环》等;最后,从批评的方式看,这一时期关涉电影本体批评的文章可以说是主流,政治批评的文章虽然没有销声匿迹,但数量上比较少,且大部分政治批评都已泛化为社会历史批评或社会思想、社会伦理批评。对此,完全可以从一些代表性的评论文章得到印证,譬如翁睦瑞的《评〈巴山夜雨〉的艺术魅力》、张明堂的《用镜头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天云山传奇〉的导演艺术特色》、韩小磊的《新一代的闪光——漫谈影片〈沙鸥〉的导演艺术》、张仲年的《试论〈小街〉的艺术探索》、婴子的《评〈城南旧事〉的导演风格》、澍笙《缓流的河 时而扬波——影片〈没有航标的河流〉的叙事特色》、蔡师勇的《朴素就是美——影片〈青春万岁〉导演艺术漫谈》、成谷的《赵焕章的艺术追求——兼评影片〈咱们的牛百岁〉》、梅朵的《她像一只白鹤飞向天空——评影片〈红衣少女〉》、刘白羽的《巨大心灵震动的艺术——评电影〈高山下的花环〉》等,基本上都是围绕影片的艺术特色、艺术风格、导演技巧、叙事特点等本体问题展开评价和分析的。
第二,电影批评转向电影本体批评主要是通过电影批评话语焦点的转移来彰显的。电影这一舶来品,在历经左翼电影、国防电影、十七年的“人民电影”、“文革”电影的“洗礼”后,电影的社会属性和政治功能曾经一度成为电影管理者、电影批评家,甚至电影创作者讨论得最多的问题,而电影本体的问题却少有提及。进入新时期后,随着一大批娱乐片的出现,电影创作、电影理论界不得不开始正视和讨论电影的艺术特性问题。于是,钟惦棐、张骏祥、郑雪来、罗艺军、邵牧君、谭霈生、罗慧生、白景晟、张暖忻、李陀、李少白等,以及一批更为年轻的电影理论批评工作者纷纷撰文,对电影的文学性、电影与戏剧的关系、电影语言现代化、电影观念、电影创新等问题展开激辩,奏响了中国电影批评由政治话语向电影本体话语转向的序曲。1979年初,白景晟的《丢掉戏剧的拐杖》一文,从戏剧冲突、时间与空间形式、对话与声音的结合等角度分析了电影与戏剧的内在关系,并提出“是到了丢掉多年来依靠‘戏剧’的拐杖的时候了。让我们放开脚步,在电影创造的道路上大踏步地行走吧”[20]8。该文以极为决绝的态度向传统戏剧电影观念发出了挑战,其基本观点被赞誉为“新时期探讨电影艺术特性的先声”[21]267,“标志着新时期电影意识最初的觉醒”。[22]3接着,张暖忻、李陀发表了《谈电影语言的现代化》,该文在梳理电影语言的历史发展脉络之基础上,指出中国电影形态落后的症结在于电影语言太陈旧,所以必须跟上世界电影艺术的发展步伐,推进电影语言现代化,即“要摆脱戏剧化的影响,从各种途径走向更加电影化”,“在镜头运用的理论和实践上要有新的突破”,“努力探索新的电影造型手段”,以及“不断探索新的表现领域,如对人的心理、情绪的直接表现等”。[23]44—47之后,作为对白景晟观点的一种呼应,钟惦棐在《一张病假条儿》中提出了“电影与戏剧离婚”的主张,呼吁“要打破场面调度和表演上的舞台积习,取消镜头作为前排观众在一个固定席位上看戏的资格,并以两年三年为期,使摄制组全体心怀银幕”[24]35。这一观点将电影与戏剧关系的讨论引向了高潮,赞同者认为,电影的形成和发展虽然从戏剧艺术中吸收了诸多养料,甚至可以说中国电影是依靠戏剧才迈出自己的第一步的,但是长期沿用传统的戏剧观念来进行电影创作,势必阻碍中国电影的进一步发展。而反对者则认为电影不能也无须摆脱戏剧的影响,因为与戏剧舞台相比,电影虽然能够自由设计时间和空间,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完全摒除戏剧矛盾与情节冲突。所以,只要电影还是一种叙事的艺术,那么戏剧矛盾和戏剧情节就不是违反了电影的本性,而是电影本性之所在。同样,对“电影与戏剧离婚”持商榷观点的还有陈玉通的《论电影艺术的“非戏剧化”》、谭霈生的《舞台化与戏剧性——探讨电影与戏剧的同异性》、钟大丰的《现代电影中的戏剧性》等文章,这些文章共同谱成了新时期以来中国电影理论界关于电影本体问题的一次激烈的话语交锋。此外,20世纪80年代中国电影理论批评的另一话语焦点便是有关电影文学性的论争,这次论争涉及电影的文学性、电影文学以及电影的文学价值等多个层面。如张骏祥在《用电影表现手段完成的文学》一文中直言,导演的终极任务就是要用电影艺术语言把作品的文学特性充分表现出来,因为电影的文学特性可以包括作品的思想内容、典型形象的塑造、文学表现手段等几个方面,许多影片质量不高的原因就在于缺乏文学性,所以,“电影不能排斥叙事文学的长处,不能排斥戏剧文学的长处,也不能排斥抒情文学的长处,而是要兼收并蓄”[25]7。但是,张骏祥的观点很快遭到了郑雪来、张卫等人的质疑,郑雪来强调:“把电影视作一种文学,表面上似乎抬高了电影的地位,实际上否定了它作为独立艺术的存在,这种观点是与包括我国电影在内的世界电影发展总趋向相悖的。”[26]81而张卫坚持认为无论是从编剧思维,还是从时空结构和物质表现手段等层面看,电影都与文学具有不一样的美学特质。由此,如果只是片面强调电影的文学价值,而不引导电影创作遵循电影艺术的特殊规律,那么今后的电影创作仍旧会处于“无米下锅的畸形局面”[27]87。在张骏祥同郑雪来、张卫等几次交锋之影响下,钟惦棐、邵牧君、袁文殊、余倩、李少白、马德波、鲁勒等一大批电影理论家也陆续加入到这场关于电影的文学性的论争当中,较具代表性的文章有钟惦棐的《电影文学要改弦更张》、邵牧君的《电影、文学和电影文学》、袁文殊的《电影文学之我见》、余倩的《电影的文学性和文学的电影性》、李少白的《辩证地历史地看待电影和电影文学》、马德波的《在探索中演变的我国电影观——从关于“文学价值”的讨论说起》等,这些文章共同把电影与文学的相关讨论推向了高潮。对于中国电影界而言,此次论争无疑比“电影语言现代化”“电影民族化”的讨论,更带有根本性的意义。[28]90如是观之,无论是电影与戏剧关系的讨论,还是电影语言现代化、电影文学性的争辩,都是中国电影批评话语发生转变的具体表现。自此,中国电影批评逐渐摆脱了传统的政治批评模式,电影本体批评迅速发展成为电影批评场域的主流话语,进而“直接促成了以‘第五代’为代表的新电影运动的发生”[29]43。
三、批评的泛化:迷影一代登场与民间话语狂欢
随着数字媒介时代的来临,电影批评场域里的批评主体发生了较大迁变。毫不夸张地说,数字媒介赋予每一个电影爱好者发声的权利,促使电影批评真正进入到众声喧哗的时代。在数字媒介所建构的赛博空间里,越来越多的电影爱好者找到了自己发声的位置,并迅速成长为中国电影批评的重要力量。对此,有研究者认为:“一方面,观影渠道的多元化,为迷影者们大量观赏优秀电影提供了便利;另一方面,网络空间成为孕育、繁殖迷影话语的温床。”[30]145的确,数字媒介不仅改变了电影的创作、传播和观赏方式,还为电影批评提供了新的话语空间和书写模式。与20世纪30年代左翼影评小组的意识形态批评和80年代的电影本体批评相比,大众影评很大程度上不再受体制化、学术化规范的限制,迷影者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运用不同的话语表达方式进行电影批评,这在某种程度上既拓展了中国电影批评的话语空间,又丰富了中国电影批评的话语内涵。
首先,迷影话语的生产、传播和流行均离不开数字媒介这一基础条件。电影批评作为一种话语实践活动,其生成和传播均离不开相应的媒介形态。反之,媒介形态的发展也会影响电影批评话语的生产方式和传播效力。在比特化的数字媒介传播系统中,所有的信息资源都可以通过互联网共享,“这些信息在网上的传播多采用多媒体、超文本式传播,其信息的丰富和多样同样是任何传统大众传媒所无法相比的”[31]36。数字媒介不仅可以传播和容纳海量的信息,还具有迅捷性、开放性、交互性和多媒体性等传播特性。较之纸质媒介,数字媒介的首要特性便是迅捷性,因为数字媒介传播不受印刷、运输、发行等环节的限制,可以瞬时传递到用户眼前,进而形成一种信息海洋,让人自由遨游其中。这种传播上的迅捷性,不但提高了文化传播效率,拓展了人们的日常生活空间,还为电影批评提供了快捷的传播渠道和信息存储方式,使得电影放映、电影观赏与电影批评几乎能够同步进行,大大提升了电影批评的实用价值和社会影响力。再有,数字媒介为电影批评建构了一个开放的话语空间,这种开放性集中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电影批评生产的开放性。主要指数字媒介在信息传播与意见发布上打破了传统媒介的垄断地位,任何人在任何时间和地点都可以在公共论坛、社区网站、个人博客、个人微博、微信公众号等平台上,对任何一部作品或任何一种电影现象发表自己的意见和评论。二是电影批评扩散的开放性。传统电影批评由于受传播媒介时空的限制,其传播的受众面比较狭窄,传播速度滞后,且不易储存和查阅。而数字媒介具有存储海量信息的能力,可以把电影批评以及电影相关的信息都存储于数据库之中,供广大读者随时随地查阅自己感兴趣的影评文章。此外,数字媒介传播系统还增强了电影批评的互动性,这种互动不像传统纸质媒介需要依靠信件、电话等辅助手段,而是直接通过公共论坛、社区网站、博客、微博、微信公众号等,即时、自由地进行互动。众所周知,在传统媒介语境中,电影批评者和受众双方的地位、职能是泾渭分明的,加之影评传播时间上的滞后性,这就容易导致“影评人批评的侧重面和观点与大众欣赏口味的脱节”[32]45的不良后果。当然,有少量报刊开设了影评人与读者沟通的专栏,但囿于版面和审稿机制等因素,亦无法从根本上改变这种单向传播所带来的种种弊端。而数字媒介灵活、便捷的互动传播模式,则很好地解决了电影批评信息互通和互动的矛盾。任何人在互联网上阅读影评时,都可以通过跟帖、留言,甚至是转发、点赞等形式及时反馈意见,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态度。同时,数字媒介还可以通过超文本技术使得文字与声音、图像同时出现,对电影批评进行多媒体形态传播,让受众觉得新颖而奇特。
其次,从受众群体的年龄看,迷影话语受众呈现出低龄化的发展趋向。据统计,近年来影迷人数不断增加,且呈现出低龄化特征,年龄段主要集中在19岁至35岁,平均年龄为23.6岁。[33]202如是观之,在数字媒介时代,青少年不仅是观影的主体,也成了电影批评话语生产的主力军。特别是在赛博空间,迷影一代的声音几乎已成为电影批评话语的主流,他们的某些观点和观影偏爱亦成了影响中国电影发展的重要力量。例如,我们从近年来学界热议的“粉丝电影”“互联网+”“网生代”“工业电影美学”等电影现象中,亦可窥视出中国电影受众低龄化的发展态势。尤其是“网生代”,它存在两个层面的意义指向:“一是指创作者依赖互联网而获得影响力、知名度后,转过来去做电影的一代人;另一个则是指由网络生产出来的一代观众。”[34]6相较于第五代、第六代导演代际转换的时间继承关系,“网生代”导演更多体现为一种空间上的独立性,而“网生代”电影作品在整体气质上不仅呈现出“情感的草根化倾向、审美的粗鄙化倾向和文化的虚无主义倾向,且在叙事方式上集中体现为文化消费式自恋、碎片化表达、虚拟与现实互动三方面的特质”[35]191。“网生代”电影之所以能受到年轻观众的追捧,主要是因为它降低了电影制作的门槛,使得电影内容和表达方式变得更加“亲民”,更能满足年轻观众娱乐体验和情感宣泄的需求。总之,作为“网生代”的迷影群体虽然在年龄上表现出低龄化的倾向,但其观影偏好与娱乐诉求却成了影响当前电影创作的重要因素。
最后,从话语风格层面看,大众影评具有民间化、狂欢化的话语特质。毋庸置疑,迷影一代的崛起与数字媒介提供的自由、开放式的传播平台紧密相关。与纸媒时代严格的审稿机制相比,赛博空间所营构的是一种相对匿名性、开放性的文化生态,评论者不必在意种种约束,可以按照自己所想所思,发表自己的感受和意见。这种匿名性的书写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电影批评的门槛,使得不同身份的影迷涌入电影批评场域,形成一种众声喧哗的泛批评格局,且在批评话语风格上也呈现出渐趋民间化的特质。究其缘由,赛博空间的匿名性写作让专家影评与大众影评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专家影评开始陷入失语的尴尬处境。为了重新建构自己在新媒体场域中的位置,他们不得不以“迷影者”的身份和姿态进入赛博空间,尝试适应这种“数字化”的媒介环境。例如早在2007年,尹鸿、章柏青、张颐武、郝建、崔卫平、张卫、王志敏、周星、饶曙光、陈犀禾、陆弘石等30多位专家学者、知名媒体影评人纷纷开通博客,并联合新浪网组建了“中国影评家官网”,特别强调:“影评写作在内容上要兼顾专业性和娱乐性,既有学术气息,也有对当下上映的商业片、娱乐片的及时评价;在功能上要形成专家与观众的在线交流和互动,从创作意图、影片细节、电影行业、评价体系等多个角度共享电影文化和理解感受,促进中国电影良性发展。”同样,在其他一些专业网站或论坛上,如世纪在线、中文电影资料库、后窗看电影、银海网、环球电影论坛、时光网、豆瓣网、电影评论网、影评网等,都可以寻觅到专家学者进行博客写作的活动踪迹。与此同时,赛博空间的匿名性书写亦为大众影评人提供了相对自由的发声平台,他们不再受书写身份、书写门槛、书写范式的限制,可以随意通过个人博客、微博、微信等平台发布自己的评论。与专家影评相比,他们大多属于网生一代,他们深谙网民的娱乐心理和审美趣味,在批评话语风格上放弃了专家影评那种孤芳自赏的清高和故弄玄虚的文字游戏,取而代之的是更大的自由度和民间性,其追求娱乐性、趣味性、个性化的写作方式和批评姿态,更能博得大众影迷的认同。可以说,大众影评的勃兴使得中国电影批评真正进入众声喧哗的时代,把批评话语权归还给了大众。
统而言之,电影批评话语的生成具有明显的“同时代性”特质。从20世纪30年代左翼电影批评的革命话语、80年代知识分子一代的电影本体批评话语到90年代中期以来迷影一代的大众影评话语,中国电影批评主体身份的迁变与批评话语的重塑,既是社会文化发展使然,也与数字媒介所提供的开放、自由的媒介传播环境密不可分。纵观中国电影批评发展史,电影批评主体在较长一段时间内都被电影“武器论”“工具”等文艺思想所禁锢,电影批评也常常围绕一些宏大的社会主题,以政治意识和“完美道德”的标准来审视作品,以达到引领和教化观众之目的。但进入20世纪90年中期后,随着数字媒介的发展,大众影迷们不仅获得了自由发声的平台,而且以其极为个性化、民间化的话语风格,联动商业资本在电影批评场域内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高位。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不少大众影评文章仍停留在情绪宣泄、娱乐逗趣的层面,缺乏立体、有深度的文化反思。所以,大众影评要获得相应的学理性和社会公众认同,就必须建构良好的批评话语秩序,避免纯粹的情绪宣泄和私语化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