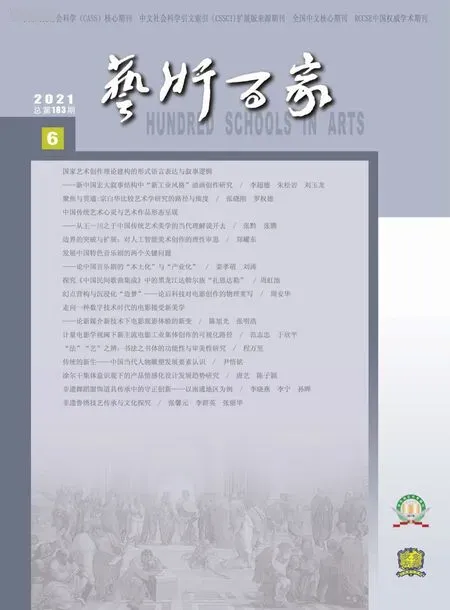他者印象:广州外销画对中国形象的建构∗
殷 洁
(南京大学 考古文物系,江苏 南京 210023)
一、外销画出现前中国形象的历史变迁
中外交流古已有之。远在秦汉之前,中国的丝绸已传到波斯和希腊,正是由于丝绸的输入,在古希腊时期,对中国的称谓由原有的Sinae变为Seres①。彼时西方人②心中,遥远的东方中国是一个盛产丝绸的国度,这一时期西方人对中国形象的认识,自然而然的是借由贸易商口耳相传,这说明在中外文化交流过程中,商品本身的特性会影响国家形象的建构。然而关山万里,交通不便,这些辗转相传的口述及文字形式建构起来的中国形象本身存在主观性的偏差。“由于文字与图像草稿本身不能为视觉想象提供准确的对象,那些几乎根据想象而来的描绘更多地接近西方经验。”[1]IX例如对中国的地理位置认识不清,认为赛里斯人居住在靠东方、印度和大夏一侧;或错将中亚一带“身材超过了一般常人,长着红头发、蓝眼睛,声音粗犷”[2]12的丝绸商人当作中国人。金尼阁也评论说:“有两类写中国的著者:一类想象得太多;另一类听到很多,不加思索就照样出版……他们不知道商人们的普遍习惯是夸大一切事情,把莫须有的事情也说成是真的。”[3]41
早期零星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精巧古玩或优雅艺术品曾借助丝绸、茶叶等大宗商品一起辗转海外。[4]104尤其是瓷器,借由其“柔美典雅的色泽、温润细腻的质地、优雅别致的造型和富有异国情调的纹饰图案激起欧洲极大的兴趣和好奇,成为人们踊跃购置和收藏的对象。”[5]108新航路开辟后,中西文化在印度洋得以正式接触,[6]1因此,当1513年葡萄牙商船首次出现在中国海面时,神秘的东方成为充满机遇的苍茫世界。随着中国与海外诸国通商规模的逐步扩大,运往欧洲的瓷器、漆器、壁纸等各类物品随着中外贸易所搭建的交流渠道,进一步演变成中国文化西传的载体。异国器物相较于传统的文字描摹而言更加直观,在增进西人对中国兴趣的同时,进一步刺激了西方世界对东方中国社会场景的好奇:这些精巧的器物是如何制造出来的,又是在何种社会环境中达成原初的和谐?填补这个想象空间的,便是在中西交通更加快捷、便利的情况下,越来越多的外交使节、商人、探险家亲自踏上中国大地,而大范围、成体系的关注更离不开宗教势力的穿针引线。
1540年,教皇保罗三世批准耶稣会士来华传教,[7]165教会作为殖民势力的引导者先行进入东土世界。耶稣会尤其重视用神学和科学知识培养人才,其修士须在15年的修行时间内接受神学、哲学、文学等各种学科的教育,语言、艺术、天文和医学特长成为海外传教的法宝。[1]30不像以往局外人不求甚解的观察,传教士群体本身文化素养较高,当他们逐步深入中国内陆后,或是取得帝王赏识得以在宫廷谋官就职,可以站在靠近权力巅峰的位置来观察中国,或是结交社会名流增加影响力,广收教徒传播教义。在此过程中,教士群体得以接触到中国社会各个阶层,因而对中国有了更为全面的理解。他们将自己的观察评断以文集书信的形式带回母国,这一时期由这个特殊群体所编织出来的中国形象,包括了对自然资源的夸赞、对不熟悉风俗的讶异、对中国人道德感的推崇还有对某些愚昧习俗的贬损,深刻影响了西方主流社会对中国形象的认知,一定程度上引发了18世纪的“中国风物热”。
“中国风物热”可以说是西方在资本主义扩张潮流下亟需理解东方的时代产物,这不仅符合文艺复兴以来对外部世界探索和求知的理念,也是资本主义发展时代,欧洲将自己的憧憬和幻想映射在中国这个古老文明的国度。[4]105在长达百年的时间里,中国文化在欧洲的传播可谓广泛,既有通过贸易交往输入的各类商品、艺术品,也有通过来华人士,特别是传教士著述和译著所带去的思想文化。前者直接影响了欧洲迷恋和仰慕的中国风物,并赋予当时盛行的洛可可风格以艺术灵感;后者则为启蒙运动提供了一个能够不借助宗教而成功建立起道德文明的社会典范,将世俗的理想和人文精神注入到社会思潮和改革中。[8]190
然而自18世纪60年代开始,“中国热”从最初的仰慕到排斥,直到向完全相反的方向发展。甚至连“中国迷”伏尔泰的观点都发生了极大转变:“人们因教士及哲学家的宣扬,只看到中国美妙的一面,若仔细查明真相,就会大打折扣,人们应该结束对这个民族智慧及贤明的过分偏爱。”[9]190到了外销画兴起的前夜,对完美华夏幻想的破灭和洛可可艺术风格的隐退就像它们来时一样迅速。
二、外销画的图像特征
乾隆二十二年(1757),清政府独留广州一处作为对外贸易的唯一口岸,即“一口通商”。[4]21鸦片战争之前,国内货物的出口、海外商品的输入都须经广州港中转,广州由此成为南中国最重要的经济、政治之地。商品贸易的繁荣不仅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也推动了中西文化的交流。随着贸易市场开拓、收集政治讯息等方面的需求,西方对中国的印象从神秘浪漫的最初向往转向对东方印象真实社会场景的深入探究。本文的研究对象便是在18世纪中叶③,广州口岸经济与文化交流独领风骚的背景之下,由广州本土画家通过临摹和学习西洋绘画技艺,绘制出被时人称为“洋画”的画作。[10]2由于画作本身具备的明亮色彩、华美装饰、西式画技等特色弱化了原始素材的说教性,受到当时来到广州口岸西人的喜爱,这种畅销一时的艺术品被后人称为“中国外销画”④。
西方世界了解中国的渴望与需求造就了以图像介绍中国社会风貌的外销画之兴盛,但中国历史上并不乏写实、纪实类型的绘画作品。上溯至北宋启始,以写实风格见长的风俗图、戏剧年画和小说杂书插图已初具规模,并出现过以反映市井民众生活面貌的传世名作《清明上河图》。入清之后,王致诚、艾启蒙、贺清泰、郎世宁多位欧洲传教士曾供奉于康乾之际的宫廷画院。尤其是郎世宁,历仕康、雍、乾三朝,曾对中西两种截然不同的画法结合进行过长期的探索和尝试,成功将西洋画写实技巧与中国传统画技相糅和,创造出内廷线画法和融合中西画法的“泰西”技法。“泰西”技法在描绘重大历史事件的画作中,更善于表达构图开阔、场面雄伟的场景。[11]在西洋画师的影响下,《耕织图》《雍正祭先农坛图》《紫光阁赐宴图》等描绘清代宫廷祭祀、筵宴、典礼场景的画作,以示《康熙南巡图》《乾隆平定西域战图》等“实录”图先后被创作出来。同样具有纪实功能的画作,为何外销画更能起到全面建构中国形象的作用?
首先,不同于以上层建筑为主要题材的宫廷画作,外销画的题材全面地呈现出中国社会的多元面貌,内容涵盖了风土人情、自然生物、山川地理、街市百业、建筑宅地、港口风貌等。如英国维多利亚和阿伯特博物馆馆藏的一组街市百业画,既有叫卖的商贩(卖莲藕、卖麻脐)、沿街摆摊的艺人(戏法、舞猴),还有各种手工艺人(补鞋、做烟)等,就像百科全书中的插图一般,起到“场景说明”的作用和“宣物”的功能。丰富的题材携带着浓郁的时代气息,劳作场景中的人物精气、街肆繁华从中可窥一般,让人如同置身于真实场景之中。外销画受到西方社会的欢迎,正是因为“借此(外销画)他们得以熟悉中国风土人情以及生活状态”[12]15。在摄影发明和普及之前,恰是这种全景式的图像资料作为理解中国的一种有效的视觉蓝本,成为当时尚未能与中国全面接触的西人“对天朝上国赖以形成概念的依托”[13],是西方世界对认识中国的重要媒介。
其次,陈寅恪在《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中称:“盖两种不同民族之接触……其关于文化方面者,则多在交通便利之点,即海滨湾港之地。”[14]45这肯定了滨海地域在中外文化交流上所起到的先锋作用。作为清代闭关锁国下唯一的通商口岸,国内货物的出口、海外商品的输入都须经广州口岸,不同文化的相互碰撞塑造出广州口岸文化的多样性,也多出几分世俗化与平民化特有的灵活性。[4]22这种多样性、世俗化、灵活性孕育出一种市井烟火风貌,作为口岸文化创作者的艺术家运用直白明了的图像视觉来描绘场景、塑造印象,向域外世界呈现出鲜活而繁盛的中国景象。单纯的纪实摒弃了情感上的依归,借助能够被西方世界理解和接纳的西画技法来描绘中国的生活场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跨文化语境的共鸣。
外销画通过描摹来华洋人涉足的广州港口面貌、绘制中国园林的景致、记录中国市井百业,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充当了中西交流之间的重要桥梁,使得西方人对那个已经产生兴趣却依然倍感神秘的东方世界,有了更为直观和深入的了解。不同于以往借助口耳相传的道听途说,或者单纯文字描绘造成的模糊理解,外销画借由中国画工之手通过直白明了的画面向西方人介绍了一个更为真实的中国。如今回看历史,外销画所折射出来的历史文化,使得我们不仅能够将它作为一种图像史料来研究当时的社会场景,还能够通过它来审视和明晰西方世界对中国的认知,实现“让往昔复活”。
三、外销画对中国形象的建构
1.有限的偏差
外销画在一定程度上如实记录了清代社会的风貌,然而,即便是如实拍摄的照片也会因为观看视角的不同而造成对社会环境的不同理解。因此,在讨论外销画文物对中国形象的建构之前,需首先理清其对清代南中国社会风物的描摹在多大程度上是准确的。
孔佩特在《广州十三行》一书中提到外销画上存在某些值得推敲的细节,比如十三行商馆画中外商旗帜的描绘“有时已经过时或画错了部分重要的旗帜样式”[15]9;再比如由于内港的含沙量高,实际上只适合停泊小型帆船,而有些画面中描绘的大型船只显然不符合实际情况[15]16;还有的画作对实际场景表现手法过度艺术化处理,比如描绘虎门炮台时“总是缩小虎门海峡的宽度并增加两边山上炮台的高度,以取得惊人的视觉效果”[15]20。
外销画对现实场景的背离与失真的确存在,这首先源于创作过程中的程式化与流水式作业,克罗斯曼称之为“一套程式(a set formula)”[16]74,其目的是提高绘制效率、增加创作数量。对于很多外销画家而言,他们在创作过程中无法轻易摆脱对模版的依赖,哪怕是非常成熟的外销画家,其作品也显现出程式化的痕迹。[16]70许多画作中的装饰性细节普遍遵循着一套固定模式,比如18世纪早期销往英国的悬挂纸画背景多为“固定配置的山、石、水”,“类似的锯齿形山峰、带波纹的水”[12]28;某些特有的构图与内容被画家持续沿用,“1772年的悬挂纸画中出现的蓝色背景上的白色花鸟,罕见且新颖,但是这种画法一直沿用到了十九世纪”[12]30。对于市场上需求量较大的画作,更是采用流水线方式成批量绘制。[10]151“画人头的专门画头,画衣服的专画衣服。风景画、风俗画也是各有分工,画树者、画水者专择其一,制作很快。”[17]54这种程式化和流水线创作形式使得画家无法根据社会风貌的变迁,及时记录变化中的社会场景,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外销画准确性不够的问题。
其次,对西方画作的临摹与学习过程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外销画家的创作自主性。虽然早期外销画的出现离不开中国传统绘画的哺育,但由于外销画所使用的技法、材质不同于国画,外销画家通过出国留学、跟随来华的西方画家直接或间接学习等途径来学习西洋画技,因此临摹西方画作在当时的外销画行业中较为普遍。克罗斯曼对不同时期画技的研究指出,很多中国外销画家直接沿袭西方画家的构图或用色,如最著名的外销画家之一林呱对人物眼睛、嘴巴的处理方式同他的老师如出一辙。[16]19—20,30该学者还依据1805—1825年间40多张风格与外销画奠基人史贝霖画风相似的肖像画、港口船舶画进行了细致的研究,认为这段时间有一批外销画家明显继承了他的风格,只是“水平没有史贝霖的画作那么生动”[16]109—110。虽然对西方画作的借鉴是绘画技法的问题,但是长久以来,对西方画作亦步亦趋地跟随与依赖限制了中国本土外销画家的视角,导致其笔下中国场景的真实性与准确性发生偏差。
除此之外,外销画的买方市场具有较大话语权,西人的订制需求是造成准确度降低的第三个原因。传统上,中国文人认为对商业利益的追求会使得创作者丧失相对的艺术独立性,故而对创作过程中的商业性往往避而不谈。与文人画相比,外销画是艺术品,但也是商业交往中的商品,所体现出来的艺术品特质是附着在商品特质之上的。因此,以追求商业价值为目的之一的外销画在创作过程中并非完全随画家所欲,更可能出现的情况是绘画的题材内容和创作方式是被明确要求的。即便西人要求单幅画作在细节上做到尽量准确,也会由于关注视角与侧重点的不同而与整体环境形成一定的偏移。更确切地说,西人的订制需求对外销画的影响并非体现在单幅画作是否准确,而是使外销画形成了某些特定的视角,这种西方式的视角本身就具有偏颇性。造成西式视角偏颇的主要原因是清政府对通商口岸的严格管控,对来华经商的外国人也采取苛细的限制和防范政策,比如他们每个月仅可在行商的陪同下离开十三行馆区,去海幢寺和花地游玩两次等规定。由于西洋人的活动范围受到限制,只能在夷馆附近的新中国街和老中国街活动,而这些区域实际上“不是典型的中国或者广州街道,这里的商店特定为西方人而不是为中国人提供商品”[15]75,因而无法全面了解中国更广阔地区的真实风貌。
2.对中国形象的建构
前文分析了外销画家在创作过程中,鉴于创作与流程的程式化、艺术表现手法以及绘画订制人的特殊要求,使得外销画在一定程度上偏离原貌。那么,既然外销画存在着偏差,它对建构中国形象有何作用?这种作用又体现在什么地方?
让我们把研究视角拉回画作的创作者身上。中国传统绘画的创作者多为文人士大夫阶层,而外销画创作者是身处中西贸易汇集之地的民间职业画家。相较于前者而言,为何偏偏是广州口岸的职业画师更容易接纳西画并以此为生?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国传统文人画内含借物比兴的寓意,画家们在留白中抒情、在题诗中咏志,将中国文人独有的高情意趣、家国情怀隐匿在画作中。只有经过深厚文化熏陶的人才能熟悉这种精神特性的表达,不缚于技、不流于常。因而,单从画家群体的主动性来看,文人画家群体因为情怀的束缚难以涉足为洋人、为海外市场作画。即便开始已有西画传入中国,中国的文人画家们依旧固执地坚守着水墨中的孤舟蓑笠,对于外面变化着的“外夷”世界采取了一种视而不见的态度。但是,身处中华帝国阶层序列末端的外销画师们既不如宫廷画师那样受制于帝王意志,也不像文人士大夫那样以追求艺术造诣、抒发个人情感为创作主旨,将画作本身与精神蕴含相分离是外销画家和文人画家最显著的差别。恰因脱离了情怀的束缚,他们更像是一个客观的记录人,分离了精神蕴含之后的外销画作更加直白易懂,才能够被那些对东方世界只有管窥蠡测、一鳞半爪印象,难以深入品味中国深厚文化积淀的西人所理解。
第二,针对外销画因受绘画技术的影响而在风格上呈现出“西方化”色彩的问题,这种呈现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复制,广州画工笔下的外销画仍具备自身独有的特色。这种特色随着本土画家画技及创作的日益成熟,他们在中国文化场景中习得的自主性与创作性也会渗透进外销画的风格中,这使得外销画作并非是对西式画技的单一临摹或复制。创作自主性赋予艺术品超越市场特性的空间,使得艺术品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摆脱商品特性所赋予的呆板、固化,在沿袭传统、迎合市场的过程中具备内在的艺术生命力,并对西方市场产生了反馈作用。这种反馈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西方对东方的理解,这也是外销画庋藏于大英博物馆、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皮埃博迪博物馆等世界知名博物馆的一个主要原因。
第三,当艺术创作受到经济利益牵扯时,就难以保持艺术创作的独立性,因而在商业特性浓郁的外销画创作氛围中,画家们迎合市场以求顺利销售的行为就易于理解。但外销画仍是艺术品,商业特性之外仍然为艺术特性保留了发挥空间。为了满足西方市场的定制需求而造成的片面视角,事实上反而在某种程度上赋予外销画另一种价值,即外销画中所体现出来的场景,不管是中国真实的生活空间还是附加了想象和艺术创作的空间,又微妙地符合了西人对当时中国社会的关注点。在孔佩特等西方学者看来,订制反而是维持外销画准确度的保障,“西方商人或者船长在委托画家制作或购买外销画作品时,至少都会要求画家尽可能严谨地描绘旗帜、船只和建筑物。西方人对于外销画的喜爱,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外销画家对于细节描绘的严谨”[15]10。这意味着外销画并非呆板固化地遵循西方市场的要求,画工们要做的是以一种能够被接受的方式,将定制人或者市场偏好恰当地表现出来。参与构建中国文化的他们最初因生计靠近西人世界,却在寻求经济利益的过程中完成了身份的转型,深谙西式绘画技术及表达方式的画家们以一种更积极的态度展开面向世界的对话和交流。[18]
尽管外销画存在细节描绘和视角上的偏差,造成无法及时反映时代发展进程的缺憾,但是时代发展本身就很缓慢,百年间的模板即便陈旧不堪,仍能呈现出较为完整的社会面貌,有限的偏差并不足以影响外销画的整体写实特性。相较于外销画出现之前的图像,或是由西方人根据文字材料绘制而成的插图,或是丝绸、瓷器等自身带有纹饰图像的商品承载了一定的形象塑造功能。西方人根据这些图像资料来了解中国,不仅不能修正文字记录本身所存在的臆想成分,还可能因为图像的零散性而导致印象混乱。外销画作为一种兼备景象记录及传播特质的图像出现之后,西人得以对中国的社会生活、风土人情有了更全面、真实、具体的认识。其沿袭的纪实特性使我们可以通过对外销画的进一步解读来了解西方是如何借助这些图像来管窥中国社会变迁,以及这些图像又是如何塑造中国在西人心目中的形象,从而建构起对中国社会的“他者印象”。
四、结语
通过对西人视角下中国形象形成、发展过程的梳理,不难发现,外销画出现之前,西人主要通过丝路商人的口耳相传或者探险家的游记来认识中国。然而这些辗转相传的口述及文字材料或多或少存在臆想、附会的成分,容易造成对中国认知的偏颇和片面。17世纪之后,大批受到高等教育的传教士进入中国,长期笼罩在神话和传说的迷雾逐渐散去,西方对中国的认识变得更加深刻和准确、立体和真实。18世纪开始,清朝广州口岸贸易兴盛,西方借助经济交往、文化交流等途径,逐步摆脱对中国的单方面幻想。外销画作为一种文物图像应时而生,中国形象得以真实的呈现,不仅满足了西人对中国文物艺术和审美的需求,还有助于深化对中国社会场景的理解。加之外销画家身处于中国场域之中,使得外销画比以往的文字著述要更加真实,也更加可靠。外销画作为时代的经历者与见证者,通过生动、真实、直白的文物图像,记录了清代广州地区乃至整个古老中国的生活场景,建构了西方对中国形象的认知。
① 赛里斯究竟是否指代中国,中外学界仍有争议。中国学者对于赛里斯称谓的研究,张星烺、梁家农等人有详细论述,严建强、袁宣萍在研究中西文化与艺术交流的论著中也有论及。
② 按照地理学的解释,“西方”概念的界定泛指位于西半、北半球国家,主要包括欧洲、美国、加拿大等现代国家,此处仅指古代以波斯帝国和希腊罗马帝国为主的西亚和西欧。而就本文的主要研究对象外销画而言,尽管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比英国、美国更早来到广州开展贸易,却没有出现大规模购买、收藏外销画的情况,那么泛指的西方国家的概念将远超外销画的传播范围。因此,为了使本文的论述更具典型性,“西方”的概念在一定程度上是象征性含义,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国别界定。这样的侧重可能会显得地理概念上的模糊,然而这样的划分和集中,可以使得我们在观点的讨论上,不至于因地理学概念的理解而使得研究对象复杂化。
③ 对于清代外销画历史源流的认识,以往国内外研究者普遍认为,外销画最早出现于18世纪中期,兴盛于19世纪中期,消逝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然而《大英图书馆特藏中国清代外销画精华》一书所取得的研究成果表明,最早在1700年的厦门就已经出现了外销画,至18世纪末已有大批外销画的发展态势蔚为可观,19世纪则是外销画的鼎盛时期。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广州地区的外销画逐渐衰落乃至消失时,北京却出现了布列斯奈德(Emil Vasilyevich Bretschneider)(1833—1901)在京期间(1866—1884)聘请北京画家绘制的北京风俗画,以及稍后以周培春为翘楚的画家所创作的数以千幅以北京社会生活和风俗为题材的外销画,是外销画完全退出历史舞台前的最后一次繁荣。宋家钰、卢庆滨、王次澄、吴芳思编著《大英图书馆特藏中国清代外销画精华》,广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④ “外销画”一词的名称是1949年之后艺术史家们出于方便而发明的术语,它来源于“外销瓷”的表述,然而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这样一个过于简单的词汇有些不太准确,因为中国画工所创作出来的作品虽主要是卖给西方人,但是买家并没有将中国画分为“外销”或“内销”的习惯。参考龚之允《图像与范式:早期中西绘画交流史(1514—1885)》,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