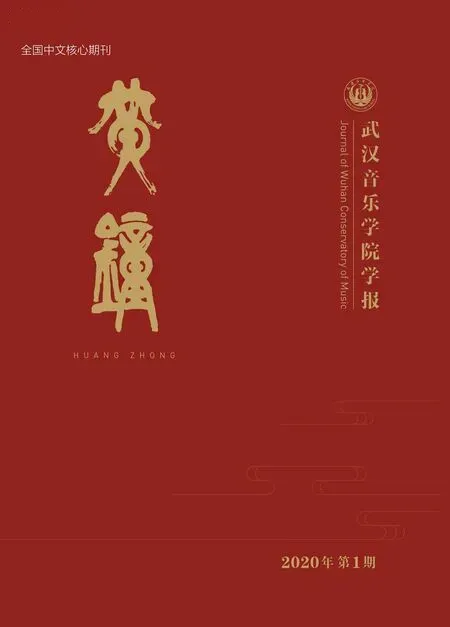是革新,还是复兴?
——勋伯格“无调性”音乐中的复调-音程式创作思维探究
袁利军
与前些年相比,近几年国内学界有关阿诺德·勋伯格(Arnold Schoenberg,1874-1951)“无调性”音乐创作的研究,已不再专注于“无调性”音乐作品中是否有调性因素的出现,而是越来越注重去挖掘“无调性”音乐作品本身的形式建构原则,或与调性音乐的组织逻辑进行比较。①如杨玉婵:《勋伯格<钢琴组曲>Op.25的艺术特征和技法研究》(山东大学2016年硕士学位论文);赵倩:《勋伯格钢琴作品23中第五首的创作技法及演奏分析》(《音乐创作》2018年第1期,第149-151页);孙宇:《勋伯格<五首管弦乐小品>(Op.16 No.2)结构思维研究》(《音乐探索》2018年第2期,第101-107页);师占成:《勋伯格音乐的音高组织与结构思维——以<勋伯格三首钢琴小品>(Op.11)第一首为例》(《内蒙古艺术学院学报》2018年第3期,第101-112页)等。在这一悄然转变的背后,有一个观点实际上已得到越来越多的默认,那就是“无调性”音乐其实并非调性音乐的完全对立面,而是与调性音乐创作思维并列存在的另一种创作逻辑和思维方式。在这一基础之上,本文则进一步认为,勋伯格“无调性”音乐中的创作思维方式实际上也并非完全革新的产物,其中主要依赖核心音程动机进行复调立体化贯穿的组织手段,与调性产生之前早期音乐的构建方式存在着一定的共通之处。
一、音乐历史中的复调-音程思维与主调-和弦思维
依据不同的音高组织逻辑原则,学界有将西方音乐历史划分为前调性时期(大约17世纪之前)、调性时期(大约18、19世纪)和后调性时期(20世纪以来)三大阶段之说。②可参见[美]Joseph N.Straus:Introduction to Post-Tonal Theory(Upper Saddle River:Prentice Hall,1990);陶辛:《西方音乐前调性时期音高组织思维研究——序论》(《音乐艺术》2003年第3期,第50-54页)。前调性时期的音高组织主要依靠音与音之间的对位化关联来完成,调性时期则依靠和弦与和弦之间的等级化关联体系进行建构,而后调性时期(包括“无调性”创作)则表现为将调性时期的等级化体系放弃之后所进行的一系列个性化探索。
事实上,在调性产生之前,西方音乐在组织逻辑上便存在着类似“无调性”音乐中运用音程动机贯穿进行组织的例证。谱1是奥地利音乐理论家鲁道夫·雷蒂(Rudolph Réti,1885-1957)在其名著《调性·无调性·泛调性》中所例举的一首对中世纪格里高利圣咏有重要影响的犹太圣咏旋律。
谱1 雷蒂著作中例举的犹太圣咏旋律③ 谱例引自[奥]鲁道夫·雷蒂:《调性·无调性·泛调性》,郑英烈译,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2年版,第146页。

他认为,在这首圣咏中,“所有的音都被一种十分类似调性的力量吸引在一起。E音代表中心旋律点,即一种主音,而整条旋律线可以看成是一个主要通过与这个基础音的关系而建立起来的音乐单位。”④[奥]鲁道夫·雷蒂:《调性·无调性·泛调性》,郑英烈译,第16-17页。他将这种现象称为“旋律调性”。他认为,这种在古老的圣咏和一些民间音乐中常见的现象,显然与西方古典音乐中所谓“和声调性”的概念是不尽相同的。不仅如此,在整个西方音乐的历史进程中,这两种调性类型还呈现出了一种此起彼伏的发展态势:当“和声调性”成为音乐中的统治概念时,正是“旋律调性”从这种局面中弱化甚至消失的时候,而在20世纪现代音乐中,“和声调性”在一定程度上被摒弃,而“旋律调性”则有可能得到合情合理的复兴。⑤[奥]鲁道夫·雷蒂:《调性·无调性·泛调性》,郑英烈译,第19页。在这一观察视角之下,西方音乐历史实际上也被大体分成了三个阶段,并且这三个阶段大致与之前提出的前调性、调性和后调性时期的划分基本一致。只不过,这样的划分方式似乎能够更好地将每个时期的创作思维本质揭示出来,尤其在第三个阶段,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对第一个阶段创作思维进行复兴的做法。
实际上,在雷蒂的这一“旋律调性”概念中,主音的调性中心地位是依赖其他各音与其之间所构成的音程关系而得以确立的。并且,前调性时期复调音乐的组织建构也都是以音程的对位化建构为主的。鉴于此,我们不妨将这种组织思维称为复调-音程思维,以此与调性时期具有严格等级化的主调-和弦思维形成对照。在复调-音程思维模式下,各音、各音程之间不存在等级上的差别,彼此平等、独立,并通过一种音对音的组织思维进行音乐的建构;而在主调-和弦思维模式下,各音则与其较近的泛音组成纵向排列的和弦,并依据共同音的多少判别诸和弦之间的远近关系,还根据各和弦构成之间的等级差别来建构具备强大向心力的调性组织体系。也就是说,在调性和声体系出现之前,西方音乐主要靠的是音程以及结合体的组合形式进行复调化构建,而当和弦连接的形式出现之后,其从不协和向协和的“解决”进行更加能够产生出某种从不稳定到稳定的满足感。但凡事均有极致,当调性体系及其中的主调-和弦连接原则在19世纪末的一代作曲家那里行将就木时,以音程以及结合体为核心的复调组织形态便有可能再次浮出水面,成为西方音乐建构的根本基础。
实际上,掀起“无调性革命”的作曲家阿诺德·勋伯格本人也曾明确地阐述过这两种创作思维之间的差异:“虽然古典音乐文献中的许多乐章都是把主调音乐的和对位的技巧兼收并蓄,但它们之间却有着根本的区别。主调音乐式旋律的处理基本上决定于用变奏手法的动机发展。对位的处理则相反,它不是把动机加以变化,而是展示基本主题(一个或几个)所固有的各种可能的结合。”⑥[奥]阿诺德·勋伯格:《作曲基本原理》,吴佩华译,顾连理校,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5年版,第186页。也许,勋伯格正是认识到了这一点,才敢于大胆抛弃调性,迈向“无调性”的不归路,因为他在潜意识中明白,就算音乐中没有了功能调性体系的组织,却仍有另一种用来组织音乐作品的手段,那就是早在调性体系产生之前就已在历史中出现的复调-音程结合贯穿的形式构建手法。
这样的观察视角,有利于我们更加清醒地看待“调性”这一西方音乐历史中最为重要和核心的组织手段。尽管西方音乐在几百年的发展中逐步孕育出了“调性”这一典型的充满西方文化精神的高级音乐语言体系,并依照自身的发展逻辑推动了数代音乐家的创作,但理论研究者却必须要清醒地认识到,这一音乐语言并非西方音乐的唯一建构方式,也并非从一开始就存在。就其本身作为一种语言体系而言,它注定会在历史中走向衰竭和自我否定的境地。
二、“无调性”音乐创作与复调-音程思维
为了论证“无调性”音乐与复调-音程思维之间的关联,我们来看一下勋伯格“无调性”作品组织逻辑的实质。笼统地说,这类作品中包含着一种“音程动机纵横立体贯穿”的核心组织手段:每部作品都建立在所谓“核心音程细胞动机”的基础之上。这个“核心音程细胞动机”由3至12个音级按照特定的意图自由排列而构成,在音乐的发展与构建过程中,其可以横向、纵向或横纵结合等多种陈述方式出现,也可以用它的倒影、逆行和倒影逆行以及各种转位和移位的形式出现,从而在乐曲中起到对比与统一的逻辑作用。
以勋伯格《空中花园篇》(Op.15)中的第7首(1908)为例(见谱2)。这首歌曲共19小节,是勋伯格较早显露出“无调性”创作思维的系列作品之一。尽管这是一首声乐作品,但其中却充满着器乐化的创作思维。如谱2所示,在第1小节中出现的两个不协和和弦显然并不构成某种传统功能性的和声进行,而是充当了全曲的核心音程动机。第一个和弦由两个大三度音程叠加而成,第二个和弦则由增四度和纯四度叠加而成。其中所包含的大三度、纯四度和增四度音程在乐曲后面的主要骨干处进行了变化性贯穿。如第3、4小节强拍上的变化形式:第一个和弦向上大二度移位加转位,第二个和弦将其中的增四度和纯四度音程上下倒置并向下小六度移位,同时两个和弦的时值缩减1/2。再比如第7、8小节的扩展性变化:第一个和弦向上大六度移位加转位,并扩展出过渡音;第二个和弦将其中的增四度和纯四度音程上下倒置并移位(其中的以等音形式出现),并扩展出过渡音;第三个和弦与第一个和弦一样,经由过渡音后,第四个和弦则扩展成了由大三度和纯五度叠加的形态。第9-11小节,对核心音程动机中的第二个和弦进行了展开:其中主要的纵向和弦是由纯四度和增四度叠置而成的,而中间的“分解和弦”也以纯四度和增四度音程为主。终于,在第13-17小节,核心音程动机的终极扩展变化形式出现,半音阶中的十二个音级出全,意味着发展过程的终结。最后两小节,核心音程动机以增值的形式“原样”再现,增加了结束时的稳定感。除了以上提到的这些地方之外,其他小节处则大都以过渡句的样貌出现。要注意的是,在这一过程中,不管核心音程动机在这些地方的外形作出如何变化,其中的“音程内容”是保持不变的。
谱2 《空中花园篇》(Op.15,no.7)⑦ Arnold Schoenberg:Das Buch der hängenden Gärten,Op.15,Vienna:Universal Edition,1914.


1909年,《空中花园篇》(Op.15)还未完成,勋伯格便以很快的速度完成了《钢琴曲三首》(Op.11),其中的三首乐曲所采用的主要创作手段仍然是核心音程动机的贯穿。但具有突破性意义的是,这部作品中所有的不协和音得以全面解放,音高之间没有任何的等级性差别,所以这一核心音程动机在进行贯穿时,已经完全实现了纵、横贯通的立体化组织关系。如其中的第1首(见谱3),由b、g组成的三音核心音程动机(包含小二度、小三度、大三度)在前几小节中以纵、横的形态贯穿出现。尤其是第4-5小节,这一动机以四声部对位的方式出现,其中包括高声部出现的小三度音程、中声部出现的加了经过音的小二度音程,以及次中音声部出现的对核心音程动机的横向变形展开。在这期间,低音声部的、中音声部的b以及高音声部的g又以纵向排列的形式构成了对核心音程动机的变化形态。
在5:00~15:00之间,站内出现由负荷和光伏发电引起的不平衡功率,电动汽车辅助储能电池进行充放电,SOC在充电时上升,在放电时下降,电动汽车的调制功率在-1 500~1 500 kW之间。
谱3 《钢琴曲三首》(Op.11,no.1)第1-5小节⑧ 谱3、谱4的版本均为Arnold Schoenberg:3 Pieces,Op.11,Vienna:Universal Edition,1910(1925).

再比如其中的第2首(见谱4),第2小节出现的核心音程动机Ⅰ(由三音构成的增五度、增四度和大二度音程)在第3小节通过“发展性变奏”⑨这一概念为勋伯格在分析勃拉姆斯的作品时提出,其主旨在于对音程动机进行的各种“在变奏中展开”的技术手段,如改变顺序、裁减、增值、移位等。一个动机经过发展性变奏之后,其形态可有较大改变,但其实质却与原动机保持一致。的手段扩展为了音程动机Ⅱ(即在原有的音程之外,又增加了大、小三度和小二度音程)。在该乐曲的第1-13小节(第一部分)中,这两个音程动机在主要的骨干处得到了各种变形、扩展和模进的再现。如第4小节的高声部c实际上是音程动机ⅠⅠ的逆行变化形态(核心音程为大二度、小三度和小二度);中声部的所包含的核心音程则为小三度、小二度和增五度,低声部的两个纵向音程分别是和(大三度的转位形式),均为核心音程动机所包含的音程。第4-5小节低声部出现的三音虽然似乎是作为过渡音出现的,但其中所包含的音程也在核心音程动机当中(增四度的转位形式和大三度)。从第5小节到第9小节,高声部的音型似乎形成了一个推进高潮的段落——在第9小节的强拍和弦上到达高潮,其中所构建的音型也为两个音程动机采用相同的方法所进行的综合变形形态。之后,在第9-11小节出现的两次推进,也是音程动机Ⅰ、ⅠⅠ的变形模进再现(核心音程为小三度和大、小二度),低声部则为动机ⅠⅠ的纵向排列形式(核心音程为增四度、大二度和大三度)。终于,在第11-12小节处将十二个音级全部出齐,代表着音程动机发展的终极形式。而后,在第13小节以纵向和弦的形式回顾了核心音程动机中的音程内容,其中所包含的音程除了核心音程减四度(增五度的转位)、大二度之外,还出现了相对协和的纯五度音程,由此产生出相对终止的效果。另外,为了保证作品的统一感,作曲家在低声部设计了持续不断的三度音程背景,为高声部对核心音程动机的各种扩展和变化提供了空间。
谱4 《钢琴曲三首》(Op.11,no.2)第1-13小节

不仅如此,时隔十几年后,当勋伯格于1923年宣称自己创立了“十二音作曲法”时,其作品中也是类似的做法。只不过,这一时期的作品在对音程动机进行贯穿发展时,又兼顾到了其中的有序化排列,以及十二个音级的不可重复性——这也正是“十二音作曲法”的本质。以他完成于那一年的作品《五首钢琴小品》(Op.23)中的第1首为例(见谱5)。
谱5 《五首钢琴小品》(Op.23,no.1)第1-4小节⑩ Arnold Schoenberg:5 Pieces,Op.23,Copenhagen:Wilhelm Hansen,No.2326,1923.
首先,在前三小节中,十二个音级就全部出齐了(见谱例中标注的数字0-11);其次,通过对这几小节音高组织逻辑的分析,可看出这类作品的组织依然是依靠核心音程动机的多样化贯穿来完成的:高音声部的三音动机所包含的音程是增二度和小二度,中音声部的三音动机和低音声部的(a-c-b)则主要包含小二度和小三度。由于增二度和小三度的音响效果是一样的,在“无调性”音乐中,也可以将这几个三音动机看作是同一动机的变化形式。如谱5所示,在短短几小节中,对这一核心音程动机通过倒影、逆行倒影和移位的变化形式就多达十个。这些形式以纵横交错的方式排列在一起,共同构成了这类音乐中的音高组织建构逻辑。
而在勋伯格之后创作的完全十二音作品中,“核心音程动机”由之前的三音或五音动机彻底转变成了由全部的十二个音级所构成的有序化“序列”。并且,由于十二音序列内部的音程内容是“恒等”的,因此这类作品的创作重心便转向了对序列进行多样化处理的方式上去了。比如美国作曲家乔治·佩尔(George Perle,1915-2009)对勋伯格1944年完成的十二音作品《钢琴和乐队协奏曲》(Op.42)前几小节的分析(见谱6)。
可看出,高声部是对十二音序列的原型展现,其中每个音都没有重复(持续音除外)——第5-6小节中对编号8、9、10三音的音型反复在作曲家看来并不算是重复,而低声部则以片段化的自由组合形式填充在高声部的长音空隙当中,由此形成连绵不断的音响效果(见谱6中的数字标注)。

通过以上对勋伯格在不同阶段创作的“无调性”音乐作品的分析可以看出,核心音程动机的多样化贯穿是其中的根本性思维方式。这些音程动机通过转位、移位、纵横变化、逆行、倒影、倒影逆行等方式进行的外在性变化,使音乐的音响不断地得到更新,但并不会影响其中的本质性“音程内容”——这才是我们对这类作品进行考量时的主要“凭据”。而这种做法,正是本文第一部分所述复调-音程创作思维的体现,或者说是对这种思维方式的延续与发展。
在勋伯格的作曲观念中,“无调性”音乐中的核心音程动机被称为“基本型”(Grundgestalt)。为了更清晰地表达这类作品中的组织思维,他也曾在自己的著述中明确表示,“基本型”这个概念的内涵在英语中应该被称为“基本集合”(basingset),或“十二音集合”(12-tones set),或者简单地称为“集合”(set)。⑫[奥]Arnold Schoenberg:“Problems of Harmony”(1934),The Musical Idea and the Logic,Technique,and Art of Its Presentation,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5,p.279.美国音乐理论家阿伦·福特(Allen Forte,1926-2014)将“无调性”音乐中不能称为和弦的这些音程动机也称为“集合”,并总结出一套音级集合的分析理论,无疑是音乐分析学一次革命性的发展。可见,运用“集合”这一数学概念来指称“无调性”音乐中的组织逻辑似乎是比较合适的,它能将“无调性”音乐依靠音程组合的复调式构建来组织乐曲的逻辑加以暗示出来。正如乔治·佩尔所言:“在无调性音乐中,音乐的线条方面不再受标志调性音乐的和声和旋律的严格标准所支配,这已大致暗示出把对位化写作的方法用来作为组织整个音乐总体的方法。”⑬[美]乔治·佩尔:《序列音乐写作与无调性——勋伯格、贝尔格与韦伯恩音乐介绍》,罗忠镕译,第25页。
武汉音乐学院郑英烈先生早在1989年的论文《从调性到无调性——兼论勋伯格的集合意识与集合思维》中就提到,勋伯格在1905年的作品《歌曲八首》(Op.6)中已用到了自己的“署名集合”(EsCHBEG,即由六音构成的集合形式),从而展现出基于“集合思维”之上的作曲法。比如,其中第二首歌曲的歌唱声部第一乐句采用了“署名集合”,并且这个集合所采用的是“无序”和“移位”的形式;而其中第六首歌曲的钢琴引子右手声部采用的是“署名集合”补集的逆行移位形式。不仅如此,1909年,由这一集合作成的旋律又被勋伯格用在了“无调性”作品《期待》(Op.17)当中。郑先生认为,“这就从本质上有别于以往一些应用某大师的名字作为动机的做法,它意味着勋伯格基于集合思维的新的作曲法的潜意识已反映到他的作品中来了”。⑭郑英烈:《从调性到无调性——兼论勋伯格的集合意识与集合思维》,《音乐研究》1989年第3期,第86页。
笔者认为,在这种以音程内容为主要考量标准的“集合思维”模式之下,所有的和弦都失去了以往在功能调性体系中的“功能性”,而仅以其中所包含音程内容的异同和相似度来判断彼此的关系。比如大三度和减四度并没有功能上的区别,大三和弦和小三和弦所包含的音程内容也是相同的,而属七和弦和半减七和弦也是相同的。通过这一角度的思考可推出,勋伯格的“无调性”和十二音作品中所展现出的,已并非是传统调性思维所引致的中心感和动力向前的组织体系,而是以音程的“并置”化为逻辑,采用许多灵活的方式造成音乐构造上变化的另外一种结构方式。如此,既保证了作品的有机统一,同时又与传统的调性结构方式完全不同。
另外,“集合思维”的概念中其实也暗含了音高组织在纵横层面贯通的立体化创作思路,⑮这是勋伯格提出的“音乐空间”(musical space)概念的实质。而这是一种复调化的思维方式。美国学者默里·迪宁(P.Murray Dineen)曾在他的文章中提到一个勋伯格在教学中的故事:“勋伯格捡起一顶帽子,拿到他的学生面前,解释道:‘你们看,这是一顶帽子,不管我从上、从下、从前、从后、从左、从右去看它,它一直都是帽子,尽管从上和从下看到的不一样。’”⑯引自[美]P.Murray Dineen:“The Contrapuntal Combination:Schoenberg’s Old Hat”,Music Theory and the Exploration of the Past,edited by Christopher Hatch and David W.Bernstein,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3,p.435.他认为,对勋伯格而言,“无调性”创作中的集合思维就是这顶“帽子”,它是一个多面的“音乐空间”。对于复调对位式作品而言,一个基本结合就是中心,每一个新的对位结合就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这个中心,虽然表面形状不同,但听上去依然可辨。而在“无调性”音乐的“集合思维”下,各音高之间的组合以及变化形式似乎也是这样得以完成的。因此,默里·迪宁在文章中生动地将此方法称为勋伯格的“旧帽子”。⑰参见[美]P.Murray Dineen:“The Contrapuntal Combination:Schoenberg’s Old Hat”,Music Theory and the Exploration of the Past,edited by Christopher Hatch and David W.Bernstein,p.435.与之对应的是勋伯格的“新帽子”——发展性变奏的技术。而勋伯格本人则也曾在1950年的文章《巴赫》中写道:“巴赫是第一位十二音作曲家”⑱[奥]Arnold Schoenberg:“Bach”(1950).Style and Idea:Selected writings of Arnold Schoenberg,edited by Leonard Stein,with translated by Leo Black,London:Faber&Faber,1975,p.393.。
这种依据复调式对位结合进行建构的方式,实际上有利于在音乐作品中构建出更加立体的、多维空间式的音乐样貌。而勋伯格本人的确十分重视复调对位技术在创作训练中的地位,正如他在《对位法初步训练》一书中所言:“须以一种十分不同的方式去看待对位理论。它不只是纯粹的理论,而更是一种训练方法。更重要的是,这种方法意在教会学生在日后作曲时学会如何运用知识和思想。因此,不但要发展学生在声部写作方面的能力,而且还要向他们介绍非常艺术化的作曲原理,从而引导他们认识到这些原则能在多大程度上作为艺术中的通用原则”⑲[奥]阿诺德·勋伯格:《勋伯格对位法:对位艺术的探秘之钥》,[美]伦纳德·施泰因编,周强译,孙红杰校,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257页。。可见,对于勋伯格而言,学习复调对位法不仅仅是为了效仿前调性时期作曲家的写作手法,而是将其作为一种更为通用的音乐创作思维,运用在具体的创作实践中去。很显然,我们在他的作品中也的确发现了这一点。
可见,“无调性”音乐中的组织逻辑确非凭空出世的全新手法,而是来自勋伯格对历史中两种音高组织思维(尤其是前调性时期)的深入理解。
三、“无调性”音乐复兴复调-音程思维的多重缘由
上文已证实“无调性”音乐与复调-音程思维之间的关联,而如果从历史、美学与哲学的视角去反思这一现象产生的缘由,则也有一番意味。
从音乐创作的原初层面来看,作曲家在面临音乐创作时,他首先面对的是每个独立的音高本身,而作曲家的创作任务就是将这些音高进行彼此之间特定的组织和构建。当两个音出现之后,音程的意义便显露出来。而就音程概念中的两个音高本身而言,它们之间本来并不存在着优劣高低的等级差别。反倒是在历史的长河中出现的功能调性和弦体系,赋予了这些音高以特定的等级功能性。从“和弦”本身的构成上来看,它在纵向构成上的几个音之间便已达成某种等级性的关系,比如根音实际上产生出了将其他各音聚合起来的一种中心力量,其他几个音都因为与根音之间的某种功能性关系而产生出特定的功能属性。同时,这几个音又以纵向的形式融为一体。由此,“音程”与“和弦”之间的属性区别便一览无余:“音程”一词不包含某种功能性,而“和弦”一词则为其中的音高添加上了更多的功能性内涵。由此可见,“调性”才是西方音乐特定历史下出现的一个特殊文化产物,而前调性时期和后调性时期无非是没有采用这一对象进行创作而已,同时其更多地依赖于无等级差别的单个音和音程作为基本单位,似乎反倒能够显示出更具原初意味的作曲内涵。
正是由于音程思维下对单个音高所附属的功能性进行的撇除,便让“无调性”音乐和十二音序列音乐在音高组织和建构方面与之达成了某种共通。也正是基于音程和和弦之间原本就存在的这一差异,复调-音程思维和主调-和弦思维所构成的音乐样貌也形成了差别。在主调-和弦思维下,和弦是音乐建构的最小单位,因此作曲家的音乐创作所关注的主要是其中和声衔接的横向功能逻辑,由此形成了具有明确方向感和动力性的音乐;而在复调-音程思维模式下,由于音程或单个音成为音乐建构的最小单位,因此作曲家在创作中则不仅要关注横向上的音高序进,同时也需要兼顾各音高在纵向上的结合方式,由此形成了更具空间化和立体化的音乐形态。
从另一角度来看,历史之所以形成这样的音乐发展样貌,实际上与每个阶段主导性的美学思潮也有着神秘性的关联。前调性时期,西方世界受到基督教文明的垄断性统治,其在美学观念上追求的是同一性和相似性,而对对立、差异和变化则持排斥态度,因此那一时期的音乐中在音高组织上也体现出平等、无等级差别的状态。而在调性时期,启蒙理性哲学占领着观念上的主导地位,其讲求理性以及对立统一的规则和规范,因而音乐中的各要素便也相应地具有了严格意义上的等级划分,并形成了一套严格的规范体系。在后调性时期,随着非理性主义哲学的崛起,对理性、中心和规范的打破,以及对规则和权威的排斥成为主导理念,在音乐创作中寻求去除中心性和等级性等美学观念,都恰恰成为复调思维与音程思维得以复兴的乐土。
从哲学角度而言,前调性时期流行的经院哲学强调对基督教教义的专权维护,因此其音乐中追求相对平稳、协和和无差异性的音高组织倾向,而调性时期以哲学家黑格尔(Friedrich Hegel,1770-1831)的“肯定辩证法”为主导的德国古典哲学强调矛盾对立双方在更高层面上的和解,推崇所谓“同一性原则”,因此那一时期的音乐中遵循着唯一的调性体系原则,几乎所有作曲家的创作都是在这一体系原则之下进行发挥。在后调性时期,以哲学家阿多诺(Theodor Adorno,1903-1969)的“否定辩证法”为代表的现代哲学的核心则是对“同一性原则”的批判,强调对个体性和差异性的正视和保留。因此这一时期的音乐中充满着对立的各方,它们不寻求解决和化解,而是赤裸裸地以对立的姿态展现在作品当中,呈现出平行化和并置化的特征。比如在勋伯格的十二音序列作品中,不仅十二个半音的地位均等,包含十二个半音的序列之间也构成平等、无等级性的伙伴关系,而非依附和主次的关系。事实上,阿多诺也认为,勋伯格的十二音音乐本质上就是一种对位法性质的技法,复调风格和对位法在这里实现了真正的复兴和再生:“对位法毫无疑问地是十二音技法的实际受益者,它在作曲中获得了首要地位。在十二音音乐中对位法的逻辑优越于和声-主音音乐的逻辑,这是因为这种逻辑将纵向结构从和声的约定俗成的力量中解放了出来。……依靠序列关系的力量的普遍性,十二音技法从本源上讲就是对位性质的技法,因为所有共时的声音都是独立的,一切都是序列的整体组成部分……”⑳转引自于润洋:《现代西方音乐哲学导论》,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419页。
综上所述,勋伯格“无调性”作品中以单个音为个体彼此组合而成的纵横贯通式的空间化音乐,是由复调-音程式创作思维所构建出来的结果,是在某种程度上对前调性时期音高组织思维的复兴和拓展。而无论从音乐创作的原初层面,还是从历史、美学和哲学的视角来看,这样的结果都有一定的必然性。
——评《勋伯格与救赎》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