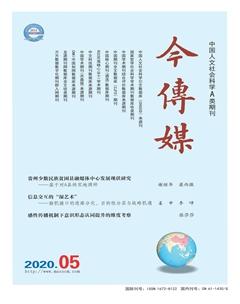新《广告法》视阈下网红广告规制研究
蒋孝舒
摘 要:网红广告以其互动性强、用户定位精准、价格低、流量变现率高等优势备受广告主青睐,但其在法律层面存在诸多问题,挑战了新《广告法》的广告合法性底线。本文针对以上问题,从立法、行政、广告行业和网络平台四方面提出网红广告规制的具体建议。
关键词:网红广告;新《广告法》;广告规制
中图分类号:F71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20)05-0057-02
一、 概念厘清
(一) 网 红
“网红”指在网络空间因某一事件或行为引发网友关注的红人,较传统意义上的明星、名人不同,他们的走红渠道由传统媒体转向网络。社交媒体时代的“网红”在娱乐、美妆、美食等领域具备专业知识或才华,拥有具有相关兴趣的粉丝群体。由艾瑞咨询和新浪微博联合发布的《2018年中国网红经济发展研究报告》显示,2018年粉丝规模在10万人以上的网络红人数量较去年增长51%,截至2018年4月,中国网红粉丝总人数达5.88亿人[1]。
(二) 网红广告
目前学界对网红广告没有统一概念,有学者认为网红广告本质上是网红自带团队、明星效应、渠道推广三者结合的产物[2]。结合前文所述“网红”的概念,可以将网红广告理解为网络红人依靠所处的媒介平台,将自己(或团队)策划并参与制作的广告产品面向网民推广,从而促进该产品销售的活动。
(三) 新《广告法》
1994年10月2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以下简称“旧《广告法》”),2015年4月24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以下简称“新《广告法》”),自2015年9月1日起开始实施[3]。较之旧《广告法》,新《广告法》将互联网广告写进法条规范内容,使网络广告总体上有法可依。
二、 网红广告优势与现存问题
(一) 网红广告优势
网红广告具有互动性强、娱乐性强、用户定位精准、价格较低、广告呈现方式隐匿、形式多样、流量变现率高的特点,是其受到广告主青睐的优势所在。数据显示,2017年与广告主签约的网红人数占比达57.53%。
(二) 网红广告现存问题
1.模糊广告的可见性。网红广告多采取网络直播、短视频的形式发布,不少广告伴随“好物推荐”“产品实测”等标题进入网民视野,其广告标识被隐匿,公众在完整了解直播、短视频完整内容之前并不知晓这是一条广告。这就违反了新《广告法》第十四条规定的:“广告应当具有可识别性,能够使消费者明辨其为广告”。
2.虚假广告丛生。消费者在听取美妆网红建议购买并使用产品后并未获得网红所述的效果,这符合新《广告法》第二十八条所述虚假广告情形:“商品的性能、功能与实际情况不符”。网红直播过程中“翻车”现象也时有发生,头部网红李佳琦的“大闸蟹”、“不粘锅直播”事件都曾被指涉嫌售假。
3.不良广告信息传播。根据新《广告法》第十九条规定“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不得以介绍健康、养生知识等形式变相发布医疗、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广告”,可纵观小红书、新浪微博等平台的“大V”广告内容,不乏对“酵素”“鱼油”等保健食品的过度宣传包装,严重影响观众形成正确的健康观念。
4.广告版权归属不明。类似于微博短视频这种网红广告由网红及背后团队进行创作,广告主对广告视频提出修改意见,广告版权由网红自身所有。广告主投入了一定数额广告费用,却不拥有广告脚本版权,也无法在未经网红团队同意的情况下进行二次修改和跨平台传播,广告主的利益受到损害。
三、 我国网红广告规制现存问题
(一) 政府规制现存问题
1.法律制定滞后网络。2015年新修订的《广告法》并没有专门针对互联网广告的规范条款,2016年出台的《互联网广告暂行管理办法》的部门规章仍缺乏对各类网红软性广告的具体处罚条款。因此我国亟需出台《互联网广告法》对种类繁多、数量庞大的互联网广告进行法律规范。
2.惩罚力度较轻。从惩罚主体来看,新《广告法》规定“广告主应当对广告内容的真实性负责”,而实际广告主很难对网红团队的广告制作细节进行真实性把控。因此一旦出现违法网红广告,将广告主、网红及发布平台都应视情况纳入处罚范圍,从惩罚金额来看,新《广告法》的行政处罚数额与广告费用挂钩,但200万的最高行政处罚标准与网红所获收益相比不值一提,处罚力度太轻使法律法规形同虚设。
3.监管主体单一。我国《广告法》采用传统“政府主导模式”,各级监管部门可对本地的报社、电台、电视台逐级监控有效打击。社会化媒体兴起后,广告发布者数量及传播速率快速增长、软性广告中的违法广告信息难以界定,“政府主导模式”体现出监管主体单一弊端[4]。
4.监管部门协作缺乏。我国互联网广告规制权属各级工商管理部门,广告违法信息识别则须依靠工业和信息化部门。部门之间缺乏有效协作,工商管理部门的监管亦难达到理想效果。
(二) 行业规制现存问题
1.广告行业自律薄弱。受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影响,我国广告行业自律组织先天发育不足,后天职能模糊。由政府主管部门授权和委托行使监管职能,过多受到政府行政管理影响,中国广告协会等主要自律组织官方色彩浓厚,民间性行业组织的固有属性淡化。
2.网络平台监管主体缺位。网络平台监管部门人力和技术资源有限,无法对海量网红广告一一进行审核。网红广告博主于平台而言,具有用户、签约客户、监管对象、网红的多重身份,使平台监管主体陷入两难,众多网络平台的监管流于形式。
四、 我国网红广告规制路径
(一) 出台《互联网广告法》,改善违法广告惩处依据
目前我国互联网广告规制总体上有法可依,但在具体法条上仍缺乏具体依据。出台《互聯网广告法》作为新《广告法》的补充法律,对软性广告的内容和边界做出具体界定,可解决许多违法广告问题。
现行以广告费数额为主惩处依据的模式无法避免互联网节点传播中污染某一节点造成对整体网络环境的影响,传播次数更难估量违法广告不良影响的深度、广度,应将违法广告信息传播次数作为惩罚依据,规范力度也得以加强。
(二) 向“社会监管模式”转型,加强跨部门合作
“社会监管模式”并不意味着政府机构减弱其作用,而是呼吁消费者参与监管,鼓励消费者进行举报和纠偏,遇到违法广告信息侵害自身权益时勇敢拿起法律武器。发挥消费者协会、新闻媒体等社会组织作用,强化舆论监督效应。各级工商管理部门和信息化部门实现信息互通,建立网红广告信息大数据库,全国联网协调配合打击违法广告。
(三) 形成政府引导下的行业自律
美国政府引导下的广告主、广告公司、媒体行业规范组合大大提高了行业自律对互联网广告的约束能力,我国可参考美国商业优化局(BBB)建立第三方网络广告自律审查机构,提高我国广告行业自律意识。
(四) 网络平台建设网红信用机制
新浪微博等网络平台已建立起信用积分机制,但评价标准模糊,对规范网红广告的实际作用不大。尝试对具有平台认证的网络红人进行信用评级机制能逐步提高网红广告准入门槛,发布、传播违法广告、被其他用户举报并验证确实违反《广告法》等行为均会降低其信用评级,对信用评级较低的网红可采取平台限流等惩罚性措施。
网红广告的迅速兴起对网民日常生活产生巨大影响,对其进行规范势在必行。2015年始行的新《广告法》将互联网广告纳入了法律管理的范围,但违法网红广告的泛滥从侧面反映出目前立法仍存在不足之处。以立法为基础,政府监管配合行业自律、社会监督才是规制网红广告的可行路径。
参考文献:
[1] 中国网红经济发展洞察报告 2018年[A].艾瑞咨询系列研究报告(2018年第6期)[C].上海艾瑞市场咨询有限公司,2018:36.
[2] 徐斌,葛涛.网红经济下网红广告的传播策略分析[J].新闻研究导刊,2018,9(19):32-33.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N].人民日报,2015-04-28(023).
[4] 徐爱玲.网络广告的法律规制问题研究[D].沈阳工业大学,2018.
[责任编辑:杨楚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