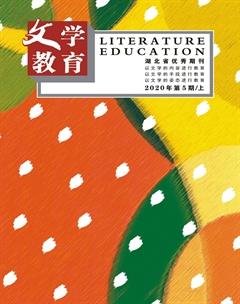“存在仿佛是为了对应”
“诗是人性在语言艺术中的隐喻,是美在现实生活中的文字呈现。”汪剑钊对于诗歌持这样一种认知。为此也就不难理解其所说的,“诗歌的意义就蕴藏于人性,我们则可以通过诗歌看到最美好的人性。”(《诗刊》2019年第9期)从某种意义上说,汪剑钊是在坚守一种理念,一种——“诗歌最根本的品质”仍在于抒情和审美功能——的理念,而这一理念无他,即是几千年来中国诗歌一以贯之的抒情言志传统。加以“言之无文,行之不远”的告诫,审美的功能也在其中了。他似乎有些反对“载道”所带来的负重感,不乐于见到政治学、宗教学、伦理学等应该承担的责任被强行地加诸于诗,主张要打破这些外来的枷锁,不希望诗歌成为它们的“奴役”。因此透过其作品,我们总是可以见到其中张扬着传统诗歌本体论的影子,也就不足为怪了。
诗歌的确可以明心见性。不过,不同的诗人由于性情和识见的缘故,在某些情境中对于这一征验的表现并不明显。汪剑钊是易于表现性情的人,故而其诗歌中对于这一点的呈示相对比较显著。如其《桃花一把将我扯进春天》,在诗中他沉醉于桃花,沉醉于那“在历史的诋毁中”所闪烁的“香艳到朴素的美”,个人的喜乐立马便“现形”了。即使在看起来可能有哲学诱导的诗篇中,我们也常常能够见证这一点。如其《一只鸟如何领悟世界》即是如此,诗歌先是对鸟进行赋写,然后逐渐渗入人为意识,由“人的梦想”做一过渡,最后落实于一种带有空灵想象的浪漫之思:“空中,那只鸟/俯视着熙熙攘攘的人群,/它将产生怎样的想法?/是的,有什么鸟的想法?/如果有一个鸟国,/它的边境线在哪里出现?”从某种程度上说,作者最后的“领悟”动摇了鸟的世界,“完善”了诗人自己。很显然,这是诗人在对鸟的赋格中,打开了个体的真性情,从而使得个人与鸟在“领悟”中形成了一种割裂的统一。但亦正是因为有割裂,所以见性情。
汪劍钊说:“置身在一个诗性缺乏的时代,或许最需要的就是诗歌的出现和存在”,“在人们的心灵深处,诗歌仍然是生活的核心内容之一,是他们渴望抵达的一种境界。”对于他自己而言也正是如此。他总是试图从真实的“生活”里吐掉苦果,摒弃孤独,让诗歌的快慰走进烦躁的心灵。他沉浸于这种语言艺术的“嚎叫”与“倾泻”中,仿佛真正抵达了某种镜像。一如他在《生活》一诗中所描述的那样:“语言可以照亮阴郁的内心,/让裸身的对话始终保持愉快的频率。”尽管在诗的结尾他还有“得继续生活”这样显得有些无奈的话语,但是仍然看得出,他并不想打破生活与诗的这种界限。
审美是汪剑钊对诗歌功能的重要认定标准之一。他说,诗是“美在现实生活中的文字呈现”。在诗歌中他也完全实践了这一点。他的诗歌大多都写得极具美感,一方面出于他在文字选择上的考究,另一方面出于他对整首诗歌在情绪和谐上的建构。在汪剑钊的作品中,我们总是能感受到语言文字本身的美感和韵味在其中浮动。像《一只鸟如何领悟世界》的首节,对于鸟的一段唯美的描写,读诗的人很少不拜倒在其语言的裙裾下。又如某诗的题目——“秋日,微醺在成都”,“微醺”的择取,看起来既自然又略具匠意,实在是美感十足。从某种意义上说,汪剑钊的确有借助语言酿诗的情趣在。在此诗的结尾汪剑钊说:“诗,乃语言的醇酒”,这一言语正好可以拿来为他自己的诗歌作注。另外,他的诗歌也很少捕捉冲动的情绪,总是充满了一股宁静的和谐。即使偶尔有冲动出现,他也多将其化作静谧的不安分,颇有些戴望舒为诗所制定的“以文字来表现的情绪的和谐”的味道。
汪剑钊虽然偏重从事物中搜寻情绪的“带来”,然而并不沦为客观主义的爬梳。他一直努力从事物中发现奇特乃至美好的意义,或者从此溯源直达那些灵性的奥秘居住地。我非常欣赏他在《雪地上的乌鸦》中的那一段沉思:“存在仿佛是为了对应,/污秽的雪水流淌,浸泡/一张黑白照的底片,/而我们熟悉的乌鸦即将在寒雾中凝固,/成为夜的某一个器官。”如果一个人一直在以平和的灵敏观察万物的秘境,那么生命与诗最终必然走向一个浑一的存在。就像诗中所说的,“存在仿佛是为了对应”。一个诗人的存在是为了对应他的诗,一首诗的存在是为了对应给予它生命的诗者。这是诗人与诗拥抱的必然结果。当然,也是每一个作诗的人想得到的“结果”。
赵目珍,诗人,批评家。深圳职业技术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访问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