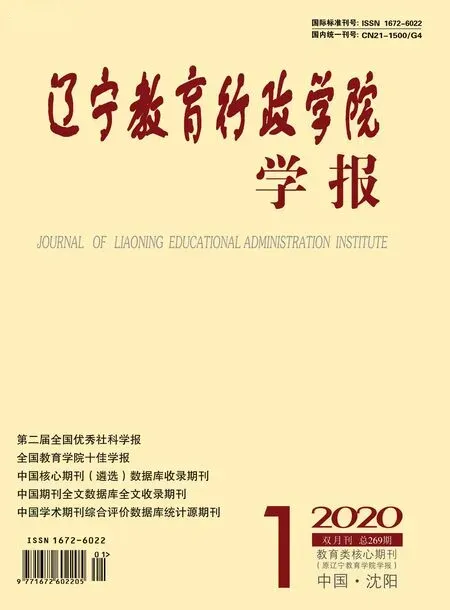顺从与反叛:妻性与女性自我意识的交锋
林静怡
东北大学,辽宁 沈阳110819
“妻”字最早出现于《易·卜辞》:“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1(]P59)这是一句凶卦,大意是困于乱石之中,周围荆棘横生,回到家中见不到妻子。在这一句困卦爻辞中,我们可以探知到,在古代“妻”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在家中,因为归家之后不见妻即被视为不祥之兆。《说文新证》对“妻”有这样的解释:妻,妇与夫齐者也。从女,从屮,从又。又,持事,妻职也。,古文妻,从女。,古文贵字。[2(]P885)从“妻”字的甲骨文字形1 和字形2 来看,[3(]P885)如图1、图2 所示。有学者认为象以手抓取女子头发,强抱为妻;也有学者认为象以手束发,可为人妻。在第一种解释下,相对于夫,妻是处于被胁迫、被控制的弱势地位的;在第二种解释下,人妻则是具有了被规范的意味,身体发肤虽受之父母,但人妻的象征却是以手束发,暗合着端庄、典雅的审美特点。《礼记·曲礼下》中“妻”的说法进一步被规范,“天子之妃曰后,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庶人曰妻”,[3(]P17“)妻”是对平民配偶的称呼。但“妻”这一称呼在古代也有其他的叫法,如“内人”“贱内”等。通过这种称呼我们也可以看出,在我国古代“妻子”于一个家庭当中所处的位置,相对于男人来说,她们是受到限制的,就像聂绀弩回忆萧红时,提到萧红喃喃低语的一句话:“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4](P65)这一句话说出了古代乃至近代女性本身所处的地位和困境——“妻子”作为被压制和隔绝的群体,距离外部世界很远。这种状况,直至现代,渐渐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同时,妻子在社会上与家庭中的地位变化与女性身上的“妻性”变化密不可分。

图1 “妻”字甲骨文字形1

图2 “妻”字甲骨文字形2
妻性,是成熟女性身上带有的明显区别于未成年小女孩儿的一种特性,即能够相夫教子,具有贤良淑德的特点,以家庭与丈夫为生活中心,甚至忽略自我主体性,屈从于男性的意志,把自己看作是男人的一种附属品。戴锦华曾经提到:“一个‘标准女性’,一个‘好女人’,她应是一个无名者,一个贤内助,一个奉献者与牺牲者”。[5](P3)这里对所谓的有妻性的女人进行了很好的解读,即有妻性的女性必须具备无名化、失语性、顺从性、奉献性和牺牲性。事实上,所谓的“妻性”更像是古代的“三从四德”的一个变种。虽然现代人对古代的“三从四德”进行批判,妻性也成为追求两性平等时的一个靶子,但它作为一种男性审美标准,在我们的文化观念中是根深蒂固的。只是在现代社会中这种男性审美标准不再以强势的文化侵略表现出来,而是以一种具有极强隐蔽性的温情文化进行渗透。“妻性”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被鲁迅明确提了出来,他在杂文《鲁迅全集·而已集》的《小杂感》中说道:“女人的天性中有母性,有女儿性,无妻性。妻性是逼成的,只是母性和女儿性的混合。”[6](P555)这里提到的“妻性”在鲁迅看来是不自然的,女人可以自然地有“女儿性”和“母性”,但是“妻性”却是被逼的——实际上是后天规训而成的。
一、“无名者”与“奉献者”的妻性意识来源
闻一多在《真女性应该从母性出发而不是从妻性出发》中提到“真女性”,在这里他认为“真女性”应该追溯到奴隶社会之前的无主奴无阶级的社会关系当中。在这种社会关系背景下,女性是以本来面目示人的——原始社会除了女人可以生育之外,与男子是相同的,可见女性的生育功能促使女性本身就具有母性,这是天性使然。但女子本身是没有“妻性”的,然而在社会的发展进程中“妻性”意识却出现了,这主要源于以下因素。
(一)“菲勒斯中心主义”——男性力量崇拜与女性力量贬抑
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以男权社会为主,男性是正极,是一个家庭的天。女性本身在体能方面要逊于男人,又有孕育和生产的问题,受到的威胁和挑战要多于男性,所以在传统意义上女性容易依附于男性生存,也就建立起了“父权”和“夫权”的合法性。除此之外,在西方,以“菲勒斯中心主义”为核心,一众理论学家建构起了庞大的男权文化体系。菲勒斯源自于希腊语,弗洛伊德将这个词作为“男权”“父权”的代表,对男性本身所具有的“天然性别权力”加以肯定,认为男人不仅是两性关系的一方,更是两性关系中的超越。在这种传统文化与现代理论建立之下,男性建立起了两性之间的统治地位,女性则是处于对男性的崇拜、仰视和屈服之下。
(二)后天的社会力——婚姻与伦理道德的规训作用,异性的暗示与同性的压力
在传统社会,婚姻是对女性的一种变相的统治和约束,“婚姻契约常常被暗示成一种劳动契约,但这又是一种不被法律所认定的劳动契约……妇女被剥夺完美的行使社会要求的权力,她根据‘平等的关系’在家中被承认,在这个家中照管家庭琐事,以换取食物、衣服和住宿,成为‘平等、互惠’的妻子。……婚姻契约也被误解成一份妻子身体与性的购买合同。”[7](P348-350)传统社会当中婚姻成为束缚女性自由与自主性、对女性进行物化的一个工具,女性在婚姻之中沦为奴隶,带上奴性,把自己当作是丈夫的奴仆。女性处于这种情况时是无法觉醒的,因为还有道德伦理对女性行为进行更深的驯化作用,女性应作为家庭中的贤妻良母,做好相夫教子的工作,正所谓“女德无极,妇怨无终”,女性应知女德,守妇道,树立起“贞妇烈女观”。
法国著名女文学家、女性主义者西蒙娜·波伏娃在《第二性》中说过:“在所有地方,在任何时代,男人都炫耀他们感到自己是创造之王的满足心情。犹太男人在他的晨祷中说:‘感谢我主和宇宙之主上帝没有让我变成女人。’而他们的妻子忍气吞声地低语:‘感谢我主按照他的意愿创造了我。’”[8](P61-63)由此可以看出,在进入有阶级、有主奴的社会之后,男性与女性的地位存在巨大差异,女性处于奴隶位置,是男人的附属品。男性不断向女性灌输男性本就应站在支配地位的观点,而女性也会施予同性这种以夫为尊的压力,所以说这种妻性特征的形成是水到渠成的。既由生理性的差别决定,也由社会的、后天的约束规范生成。
二、不同时期女性写作作品中的妻性表现
从古代至近代,中国的女性在历史中“失声”了几千年,中国的女性文化在古代也是长期处于男权文化压抑之下的,因此并未形成完整的女性文化体系。20 世纪初,伴随着“人”的解放,妇女解放运动蓬勃开展,中国女性的女性意识也越发觉醒,中国的女性写作终于浮出了历史地表,成为一道不同于传统男性写作的风景线。20 年代到40 年代,大批女作家突破男权中心藩篱,开始以群体规模出现在文学舞台,书写女性自己的文字。文学步入当代之后,“十七年”文学中的女性作家作品、80 年代和90年代的以及新世纪以来的女性写作作品,以一条纵向轴线表现了女性意识觉醒、湮没、“雄化”、再度崛起、强化高潮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女性文化受到社会各个层面的影响,也被以男性为中心的男权文化所渗透和影响。
(一)20 世纪20 年代到40 年代:新女性登台亮相,妻性逐渐失落
中国现代文学从五四时期开始,高举理性的大旗,强调“德先生”和“赛先生”,与之相对应的是高喊着个性解放的大潮流,女性作为被启蒙的重要对象,觉醒的过程是渐进性的。常彬在她的《女性文学话语流变》中写到:“如果抽去其体现以男性意志为中心的话语烙印,女性,这个在两性社会中与男性的存在一样悠远漫长的性别,就再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谁,怎样成为自己,为自己命名,甚至从来就没有意识到还有‘自己’的存在。”[9](P3)中国的女性经过了一个漫长的混沌时期,在五四时期,女性在启蒙之下加快了觉醒的脚步,并且在三十年代、四十年代都形成了比较独特的女性文化景观。陈衡哲、庐隐、凌叔华、冯沉君(淦女士)、冰心、丁玲、萧红、苏青、张爱玲等诸多女作家,塑造了一系列自我觉醒的新女性形象。这些女性不同于以往的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她们身上多了女性对自身的认识,少了对男人的依附和顺从。与同时期的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人物相比,这些女性形象主要可以分为有妻性与妻性缺失两种类型。
在以上提到的20 年代至40 年代女作家中,冰心塑造出来的女性是有妻性女性的代表。冰心认为女人是这世间不可或缺的元素,正如她所说:“世界上若没有女人,这世界至少要失去十分之五的‘真’,十分之六的‘善’,和十分之七的‘美’。”[10](P124)冰心对女性是有着一种热烈的赞美心理的,她笔下的女性基本都有三种身份:姐姐、妻子、母亲——待字闺中时是好姐姐,出嫁之后是贤妻良母。《两个家庭》中的亚茜就是贤妻良母的典范女性,一方面,她是接受过新式教育的知识女性;另一方面,她能够把家里收拾得干净整洁井井有条,对孩子教育有方,对丈夫照顾周到。这样能够使一个家庭和睦温馨的好妻子形象,在冰心的作品中是很常见的,她们内外兼修、秀外慧中。如果说冰心笔下的女性还存在着妻性,在30 年代的女作家丁玲笔下,这种妻性特征就很难见到了。丁玲本人在《三八节有感》中就指出了女性在社会当中所面临的各种不公和压力,她的作品中也常表达着她对男性的失望。她笔下如《莎菲女士的日记》中莎菲这样的女性形象比比皆是,她们很骄傲,有自己的独立意志。到了40年代,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彻底抛弃了妻性。虽然在《倾城之恋》中白流苏是一个传统的上海女子,但她却不是中国传统的女性。她离了婚,拒绝给死去的前夫戴孝,这说明她没有遵从中国古代从一而终或者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观念。在她与范柳原的爱情角逐之中,她想成为他的妻子,但这种欲望是一种强烈的不安和掌控的欲望,她想要抓住范柳元并且经营起稳定的生活,但她有自己的算计和心思,绝不是“以夫为天”的女性。这种妻性的失落在《金锁记》中达到了巅峰。曹七巧如同一个疯子,如果说她在嫁入姜家之前是一个健康的自然的女人,身上带着“女儿性”,那么嫁到姜家之后她不但没有发展出“妻性”和“母性”,反而连天生的女儿性都失去了。她在自己的爱欲破灭、生活失重之后,逐步沦为金钱的奴隶。如果说传统的具有完整妻性的女人是男权社会的奴隶,那么曹七巧则是资本入侵潮流下金钱社会的奴隶。
从亚茜到莎菲,这是一个妻性失落的过程,女性身上的自我意识逐渐浮出水面得到强化,女性作为一个独立的群体,拥有了大胆追求幸福的自由。从莎菲到曹七巧,却是一个女性丧失了传统美德和健全自我走上了异化道路的表现。从20 世纪20 年代到40 年代,女性从温和的觉醒走向激烈的反抗,最后走上虚无的绝路,这是女作家们对女性所处的一种恶劣生存环境的血泪控诉。
(二)80 年代:在朦胧的女儿性之下反观妻性的缺失
“十七年”时期的文学作品中,关注更多的是社会主义建设浪潮中的女性形象,或呼唤散发着男性特征的泼辣果敢女性,强调“男女平等”,如《李双双小传》中的李双双;或希冀女性复苏革命意志,用同志性代替了妻性,如《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可以说,女性的光彩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遮蔽,女性的自我意识也再度被掩盖。而80 年代的女性写作一方面是要对“十七年文学”与“文革文学”进行矫正;另一方面又要向前再进一步。戴厚英对自己的小说《人啊,人》进行阐释的时候提到:“一个大写的文字迅速的推移到我面前:‘人’!一支久已被唾弃、被遗忘的歌曲冲出了我的喉咙:人性、人情、人道主义!”[5](P136)当“人性、人情、人道主义”再次被推上大讨论的风口浪尖时,关于女性的困境也越来越被关注。作为一个痛苦的理想主义者,张洁在大量作品中宣告了她对男性拯救的绝望。在《祖母绿》中,曾令儿与卢北何身上都是有妻性的,当初的曾令儿愿意为了心爱的男人左葳付出一切,这是一种不求回报、无怨无悔的付出,带有古希腊悲剧式的神圣与崇高,但是当曾令儿度过了她的少女时代,她就超越了左崴也超越了自己,达到了人生的另一个高度。卢北何身上的妻性也是以左崴为中心,她找到曾令儿让曾令儿帮助左崴完成课题也是出于对左崴的保护,但又存在着一种控制欲望。可以说曾令儿身上的妻性是一直都有的,但这种妻性被更高的精神境界所遮蔽,曾令儿不再是那个愿意为了左崴一个人生养孩子的少女,她完成了一个女人心智上的超脱与成熟。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张洁自己也是在寻求一种女性精神上的出路。
80 年代女性写作存在一个共性——女作家们普遍善于塑造“慈父师长”类尊重女人、勇敢正直、品德高尚的男人。与这种理想型男人相对应的是不拒绝男性权威的“小女人”、小妻子或者是少女型女人。在这类女人身上,我们很难看到妻性,往往更能体会到女性内心中的不安与迷茫,她们在探寻着自己的位置。女人要面临着家庭和事业的两大选择,这种情况下很难两全,选择了家庭可能就要成为一个传统的女人,失去自己的独立性;选择成为事业型女人,又在所难免地需要走上女性“雄化”的道路。谌容的《人到中年》也是一部直面现实、探路现代女性心理症结的作品。女性在做好妻子和做好事业之间很难平衡,像“马列主义老太太”这样的人物不会是具有妻性的女人,而像《懒得离婚》中对婚姻失望之后产生“疲软心理”的女性身上的妻性也不复存在,这是80年代女性作家在积极思考女性去路的表现。同为女性写作者,张抗抗是一个固执的理想主义者,她也企图在时代的迷雾中找到女性的出路。她善于塑造迷茫中的“少女型”的女人,这也是她自己的一个写照,张抗抗曾经说过:“我是类似于简爱那种依靠自己的力量与命运搏斗的女性,为了追求平等和自由,可以忍受最大程度的痛苦,做出崇高的牺牲。”[11](P495)作品《隐形伴侣》中的肖潇,她是拒绝成长的,她没有能力去应付一段婚姻。因为她既没有妻性,也不想去成为一个妻子或是一个母亲,这些对于一个执着于少女梦想的女人来说是残酷的。张抗抗通过对精神与意识的分析来说明女性心中的伤痕与期待,这是对于传统女性不自知的一个反拨。
可以说,在80 年代的女性写作之中,传统型的女性形象是比较匮乏的,而铁凝在《麦秸垛》中却刻画出了一位淳朴、丰满的大芝娘,她是具有女性原始力量的人物。但铁凝着重刻画的同样不是她“相夫教子、为媳为妻”的特征,而是一种原始的母性和无尽的地母胸怀。《麦秸垛》中的另外一个女性形象杨青沉稳、端庄,得体内敛而富有心机,能够牢牢地掌控住陆野明,显然这并不是一个具有妻性美德的女子,她甚至是夫妻关系中的引导者与掌控者。《玫瑰门》中的司漪汶作为一个有着过剩精力的女人,她想要摆脱男人对她的束缚,但她却一次次地被打击,愿望也一次次地幻灭。可以说,司漪汶是逃避妻性的,她妄图通过自我实现,寻得女人在历史中的一席之位,但结果注定失败。
整体来说,80 年代的女性写作者在迷雾之中探寻出路,女性形象大多是迷茫的、矛盾的,她们处于传统美德与现代诉求的夹缝之中。女性写作者一开始没有完全放弃对理想男性的渴望与追求,当这一切化为泡影时他们逐渐走向了痛苦的决裂。作为男权社会的被放逐者,女性写作者不再将女性获救的希望寄托在男人身上,她们笔下人物的女儿性既是对妻性的一种逃避,也是对未来的一种宣告——少女总是有更丰富的成长空间,有如一张白纸,这也为90 年代女性写作的反叛姿态奠定了基础。毫无疑问,以陈染、林白等人为代表的90 年代女性写作者完全摒弃妻性,充分张扬了女性的主体意识。
(三)新世纪以来:两性之间对立减弱,单薄妻性下是女性的温和与坚忍
新世纪以来,文学受媒体与市场的影响越来越大,网络写作的潮流风起云涌。90年代进行写作的一批女作家依旧从事创作,她们开始对90年代过于激烈的“性别写作”进行一定程度的修正,并尝试着从这裂隙间挖掘另一些被遮蔽着的女性经验。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时期,还是以一种回避现实生活的小女人的任性态度,但到了90 年代后期的《玻璃瓶》,能够看到一定的转向,即“曾经凄凄艾艾怨尤压抑的小女人呓语在对往事热情洋溢的二度叙事中蜕变为爱生活,爱生命,爱人们的女性生命本体咏赞”。[12](P48)新世纪之后,林白走出了阴郁、封闭、焦虑、孤独的女性心理世界,不再用强烈的女性自我言说意识进行创作,她开始以博爱的胸怀和热爱生命的积极姿态,用心去感受女性身体与意识以外的世界,作为他者去倾听来自大地上的声音。陈染也不再是那个只善于写“私人生活”的女作家了。铁凝的《笨花》与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也都在新世纪的女性写作中展现了新的面貌,女性身上泛着一种超越传统妻性的光芒,这是一种温柔中带着坚忍、黑暗中透着光明的力量。女性意识以一种柔能胜刚的形态呈现出来,如同一条河流,虽然可能要绕石而行,但同样可以入海。
总的来说,新世纪以后女性文学中一贯存在的两性关系的冲突对抗,逐步因生命的本位意识而消除,突显出一种超越性别意识的现实意义和实践价值。这既是对女性写作在精神和实践上的超越,也是女性作家自身的成熟。
三、妻性、女性意识与话语权力之间的关系
纵观中国现当代文学这一百年,女性作家的写作景观与男性作家的写作景观差异很大。男性作家笔下有各式各样温柔、忠贞、坚定的女性,她们具有中国传统女性的包容美与坚忍性。巴金《家》中的瑞珏,端庄大方、知情达理,是中国式的好儿媳、好妻子;曹禺《雷雨》中的梅侍萍,隐忍大度、不计前嫌……男性作家更善于塑造各种符合男权社会标准的女性形象,这种女性形象是传统社会对女性的要求,女性应该有妻性,女性天生就应该成为妻子。在女性意识尚未觉醒,女性又没有话语权的环境中,男性作为主导主宰着社会的发展。当女性从封建礼教的牢笼中脱去镣铐,女性意识逐步崛起的时候,她们不再满足于只作为一个妻子而存在,更渴望拥有一个社会身份。一旦女性的这种期待受到男性的排挤甚至打压时,女性自然要群起而攻之,这也是为什么在中国现代当代女性文学作品中两性之间的对立冲突一直存在。
当女性可以拥有自己的话语权,在表达了自己对这个社会的失望之后,同样会转向对女性自我的内省和质询。这就使女性写作可以由控诉社会、揭露男性发展到解析女性自身。
铁凝的《无雨之城》塑造了三位女性:有妻性的葛佩云、变化中的陶又佳与无妻性的丘晔。葛佩云是普运哲的结发妻子,陶又佳是普运哲的情人,而丘晔则是因为工作原因跟普运哲产生联系。可以说,普运哲是一个中心人物,以普运哲为代表的男权社会关系网就此展开。葛佩云是典型的传统女性,以夫为天,在发现了丈夫的婚外情之后依然逆来顺受,企图保全家庭,让一切都保持不变;丘晔则是与葛佩云相反,她是完全新式的女性,颇有些男子特点,能够建立起自己的事业,虽然需要男人的慰藉,但更多的是她作为一个给予者对这个世界嬉笑怒骂;陶又佳则是葛佩云与丘晔的结合体,她拥有自己的工作,并且得心应手游刃有余,在她坠入对普运哲的情感之河前,她是一个新时代女性,独立优雅、不卑不亢,可当她爱上普运哲之后,便落入了传统女性的窠臼,但最后陶又佳受了普运哲的刺激之后骨折受伤,在乡下养病给了她一个新的开始——陶又佳重新认识了普运哲与她之间的这段感情,终于走向洒脱的境界。可以说,陶又佳是一个女性意识觉醒了的人,她身上具有矛盾性,因为她的自我与本我长期处于僵持状态,无时无刻不在自己的自我意识与传统的伦理道德习惯之间挣扎。当她的自我意识与传统的价值观念的交锋,由于外在因素的刺激而加速对立时,一旦她的理性重新占领阵地,这种矛盾也于顷刻间土崩瓦解。葛佩云作为传统有“妻性”的女性代表,她的形象是寡言少语的。但是陶又佳与葛佩云不同,前期的陶又佳对待爱情与生活都颇有自己的见地,这让普运哲在习惯了葛佩云的笨拙之后有了心动,但当他意识到陶又佳呈现出咄咄逼人的一面之后,普运哲毫不犹豫地推开了自己的情人——“如果占领一个女人这么艰难,那我为什么还要占领你呢?”[13](P269)也就是说,在男权社会之下,男性并不允许女性来挑战他的权威,对于他建立起来的现有制度产生威胁。女性妻性消隐,重获话语权力之后,必定要被男权世界所排斥。
福柯认为:“话语即权力”,这种权力在男性与女性之间的此消彼长的变化也充分显示了妻性、女性意识与话语权力之间的关系。当社会生态得到健康平稳发展,男性不再处于绝对主导地位时,男性与女性之间的话语权力会维持一个平衡,这使得男女之间的矛盾与对立关系得到缓解。
四、妻性发展与女性写作的未来:性别对抗和解、走向包容与尊重
实际上,我们并不一定要把“妻性”打上落后或是狭隘守旧的标签,理想与健康的妻性也是可以存在的。女性与男性在生理上既然有着先天的区别,女性发挥出自己的女性之美也不是说就一定在向男权屈服,臣服于男人。独立自主并不等同于分庭抗礼,但妻性不是女性的天性,男性也应给予女性尊重与理解。在谈到“妻性”的时候,我们并不是要杀死女性的自我意识,以牺牲女性的权利和自我为要求,而是要寻找一种“妻性”与女性自我意识的平衡。但如果说要把“妻性”强加到女性身上,并非是女性自由选择的结果,那“妻性”就会沦为男权文化绑架女性的绳索。女性拥有选择的权利,“妻性”不应是对女性付出与牺牲的要求——这是一个性别对抗和解、走向包容与尊重的时代。由于我们仍旧处于男权社会,女性主义文学作品与女性主义的批判任务很容易引起人们的误读误判,但女性主义并不是要打倒男性群体,建立母系社会,女性主义的终极关怀是要建立一个更为合理的人类生活方式,建构更为合理的人际关系与价值体系。[14](P210)
近些年来,随着网络文学的发展壮大以及新媒体与自媒体的助力,文学呈现着多元化的发展态势。因为传播媒介的多样化,也使思想的交锋更加频繁,“直男癌”“女权婊”等词汇也大量产生。究其根源,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我们还是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挑战,包括价值观方面的挑战,新的时代也在提出新的问题。如今的时代,文化语境空前复杂,女性写作也是人类一次新的精神探索与历险。当女性拥有了话语权,不再被边缘化、被放逐之后,女作家们将以细腻的情感、细致的笔触、敏感的情绪,去触碰更广阔的文学题材。近些年来,女性写作在底层书写方面的深度和力度也是值得肯定的,女性写作的未来不止于女性本身,它将会迎来一个空前繁荣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