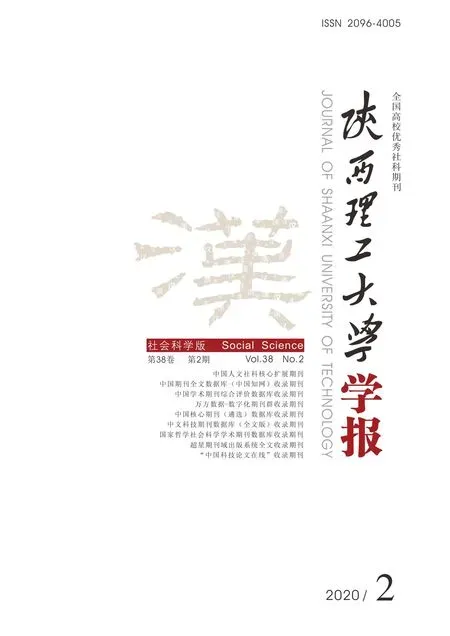论简牍文书的整体设计
曹 骥
(内江师范学院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四川 内江 641100)
依据图书的概念及构成要素,简牍文书被认为是我国最早的正式图书。作为一种图书形态,简牍文书受到许多研究者的关注,不过对于其整体设计还缺乏系统的研究。因此,笔者将此问题摭出,并对其进行考察,以期深化对简牍文书的整体认识。
一、简牍文书的幅面规格
纸书的幅面规格一般用开本来表示,简牍文书并没有开本这一概念,但却有一定的幅面规格。现代书刊开本的选择需要考虑诸多因素,如:书刊的性质、门类和用途;图表、公式的繁简和大小;编排的体裁和文字的结构;版面的字数及篇幅的大小;材料的合理利用;印刷的方便、阅读的便利;读者对象的特点;等等。简牍文书“开本”的选择没有如此复杂,主要考虑的是性质与用途,这尤其体现在文书长度的选择上。
传世文献对简牍的长度多有记载,因简牍文书的性质及记载内容的不同而有等差。记古书类简牍的长度,有二尺四寸、一尺二寸、八寸之分,如贾公彦疏《仪礼·聘礼》“百名以上书于策,不及百名书于方”曰:“郑作《论语序》云:‘易、诗、书、礼、乐、春秋策,皆二尺四寸……《孝经》谦半之,《论语》八寸策者,三分居一又谦也。’”[1]450记律令类简牍的长度,有两种,一种是长三尺,如《史记·酷吏列传》:“客有让周曰:‘君为天子决平,不循三尺法。’”[2]3153一种是长二尺四寸,如《盐铁论·诏圣篇》云:“二尺四寸之律,古今一也。或以治,或以乱。”[3]122记诸子之书类简牍长度为一尺,如《论衡·书解篇》云:“诸子尺书,文书具在。”[4]435记皇帝策书为次第编“二尺”“一尺”简,蔡邕《独断》云:“策者,简也。礼曰:不满百文,不书于策。其制长二尺,短者半之,其次一长一短,两编。”[5]3-4皇帝诏书所用简牍长度为尺一,《后汉书·陈藩传》:“尺一选举,委尚书三公。”注曰:“尺一谓板长尺一,以写诏书也。”[6]2162记文书“籍”为一尺二寸简札,《汉书·元帝纪》:“令从官给事宫司马中者,得为大父母父母兄弟通籍。”颜师古注云:“应劭曰:‘籍者,为尺二竹牒,记其年纪名字物色。’”[7]286
不过,与传世文献记载不同的是,出土实物的简牍长度与传世文献所载多不相合。如文献记载“六经”的长度均为“二尺四寸”,但阜阳双古堆汉墓出土的《诗经》残简,据推测长26厘米,约合汉尺一尺一寸,与二尺四寸相距甚远[8]90-98;律令类简牍的长度文献记载有“三尺”“二尺四寸”两种,出土实物简牍多达不到二尺四寸,如岳麓书院藏秦简中完整的律令简长度为一尺二寸,张家山汉墓出土的《二年律令》简长一尺三寸。此外,随着出土实物的增多,简牍的长度也越来越多样化。之所以造成出土实物与传世文献记载不合的现象,有两种推测:一是因为版本不同的缘故。如律令册,存在不同的版本,一种是中央王朝下达的律令册,即所谓的定制长度,另一种是郡国以下各级官府或个人的抄录本,长度和一般文书简册同[9]36。这一推测在最近新出土的文献中得到证实,2017年12月出版的《岳麓书院藏秦简(伍)》中有关于简牍形制的官方规定,证实官方所用简牍形制与民间有所不同[10]224-225。二是时代不同的缘故。文献关于六经二尺四寸的记载,主要出于汉人的记述,如王充的《论衡》、郑玄注《论语序》以及《后汉书》的相关记载,那这个二尺四寸制度就很有可能是东汉正在实行的制度,有学者认为是汉武帝尊儒后开始实行[11],那么就不能将秦及汉初出土的经书类实物简牍与这个制度相比附,因此,对简牍文书的长度要作辩证的看待。
以上讨论的是简牍文书的长度,对于简牍文书来说,决定其幅面规格的,除长度外,还有宽度。一枚简牍即相当于纸书的一页,那么简牍的宽度具体情况又是如何?不同于简牍长度,传世文献没有简牍宽度的记载,不过,出土实物可以让我们窥其梗概。简和牍在形制上有所差别,牍是方板,能够书写多行字,《仪礼·既夕礼》曰:“书赗于方,若九若七若五。”[1]747出土实物中多见书写两行字以上牍,尹湾汉墓出土的牍中,其中一枚书写行数达26行之多。牍的宽度一般在1厘米之上,1973—1974年破城子遗址出土的完整木牍296枚,宽度在1.3—4厘米;湖北荆州纪南镇松柏村1号墓出土木牍63枚,宽度在2.7—6.5厘米。相比于牍,简比较狭长,一般书写一行或两行,简宽在零点几厘米到几厘米不等。除去一些宽度比较大的异形简外,1厘米左右宽的简最为常见。
与纸书不同的是,简书采取的不是折页装订,而是平面装订。因此,简书的宽度(幅长)不像纸书单页的宽度就是书的宽度那样,而是装订成一册的所有单枚简宽度之和(包括简与简之间的空隙)。简书的宽度(幅长)为多少?有无定式?传世文献中没有记载。出土实物中成册出现的简书很少,目前发现最完整、最长的简册是敦煌出土的永元器物簿。永元器物簿由77枚简组成,全长91厘米,从常人双手持简阅读的可行性上而言,这个长度不会让人感到不适。《岳麓书院藏秦简(伍)》的相关记载也可以为此作注解:“诸上对、请、奏者……其一事而过百牒者,别之,毋过百牒而为一编。”[10]224这是秦代官方对编一册简所用简数的规定,即最多不能超过100枚简。如果按照永元器物簿单简的规格去计算,100枚的简书宽度(幅长)大约在118厘米左右。考虑到阅读的方便性及实用性,幅长在1米内的简书应当是当时的常态。
二、简牍文书的装订样式
书籍装订样式多样,就纸书而言,中国古代的书籍装订样式有卷轴装、旋风装、经折装、蝴蝶装、包背装、线装等多种样式;现代常用书刊的装订样式则有平装(简装)、精装、线装、骑马订装、散页装等样式。书籍的装订样式之所以多样,与书籍的性质、用途、读者对象及可提供的材料、工艺等因素有关。简牍文书载体的材料属性,决定它很难像纸书那样进行折页叠加装订。简牍文书的装订,文献一般称之为编,《汉书·诸葛丰传》:“编书其罪。”颜师古注曰:“编,谓联次简牍也。”[7]3250即将简牍编联成册。不过,在具体的装订方式上,简和牍有所区别。
简的编联基本上采取帘式编缀,即利用编绳将许多枚简通过缠系的方式依次联结成册。编绳的质料据文献及出土实物主要是丝纶和麻绳,间或也会用到其他质料,如:兽皮,《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晚年痴迷读易,以致“韦编三绝”。此处的“韦”,《说文》解释为“兽皮之韦”,因此,一些经过加工处理的兽皮可以作为编绳的材料(1)也有学者将“韦编”之“韦”通“纬”,解释为横线。商承祚:《韦编三绝中的韦字音义必须明确》,《商承祚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62页。。有时编绳的选用还会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如蒲、蔺,睡虎地秦简《秦律十八种》中有关于蒲、蔺等柔韧的草作为编绳的记载[12]83。
编绳所用数量与简册长短有关,一般简册越长,编绳数量越多,出土实物中,一道到五道的编绳都有。一道编绳目前仅见于丧葬文书中,如湖北江陵凤凰山167号汉墓遣册,在距离简首7厘米处有一道编绳。二道编绳比较常见,一般把简划分为三等份,或是第二段稍长,第一、第三段等长,无天头地脚,如郭店《老子》《五行》、银雀山《六韬》《尉缭子》以及居延永元器物簿等。三道编绳也比较常见,分为留天头地脚和不留天头地脚两种形式。留天头地脚的只有中间两段写字,如上博简《周易》《从政》、睡虎地秦简《语书》《编年纪》、张家山《二年律令》《奏谳书》等;不留天头地脚的可以四段均书写文字,一般第一段与第四段等长,第二段与第三段等长,如上博简的《孔子诗论》《彭祖》等。四道编绳比较少见,留有天头地脚,中间三段书写文字,如武威汉简《仪礼》甲本、香港中文大学藏简148号简。五道编绳最为罕见,留有天头地脚,有四段可书写文字,目前仅见于武威汉简《仪礼》丙本。
在编、写的先后顺序上,是先编后写还是先写后编,学界认为二者都有,从出土实物看,诚然如此。如长沙左家公山15号墓出土战国时期编联好的未书写简册证明先编后书的情况是存在的;而居延永元器物簿许多文字被编绳所覆盖,明显属于先写后编。学者们往往依据简册上文字对编绳的避让情况来判断编、写先后,通常认为如果简册上留有编绳的空间或编绳上下二字的距离较一般为大,就是先编后写,反之,为先写后编。如《岳麓书院藏秦简》的整理者即认为岳麓简有部分为先编后写,其理由就是“联系编绳的位置内完全没有文字痕迹”[13]前言。但这种判断稍显武断,因为先写后编同样也能预留编绳空间,其主要方法就是利用契口,契口一般在简的右侧,主要用来固定编绳所用,根据契口的位置,完全能做到对编绳的避让。另外,台湾学者林素清曾发现居延汉简中存在简体三分之一等长处分写“上”“下”的标尺简[14]57-60,标尺简的存在使文字能整齐的做到对编绳的避让,因此,简册上编绳的位置内没有文字痕迹,并不是先编后写的必要条件。
以上为简的编联形式概略,相较于简,牍比较宽厚,一般是单件使用,不需要编册,但当所书写内容较多时,也需要某种方式进行联结。一种方式就是在牍的顶端或下端钻孔,各牍注记序号,用编绳进行串联。如敦煌出土的《急就篇》觚。《史记·滑稽列传》记载东方朔上书汉武帝,用奏牍三千,武帝用两个月才读完,阅读期间需要暂停时,辄“乙其处”[2]3205,做好注记,显然这三千奏牍并不是杂乱的堆放,而是按次序进行串联。另一种方式就是将相关牍进行捆绑,如湖北江陵高台18号汉墓出土了四枚木牍,其中一枚背面有两道编痕,但却不见正面也有编痕,可知当是将木牍叠压捆绑的方式联结。
除上述这两种方式外,还有一种牍的联结方式值得介绍——雯都兰达木牍。雯都兰达是英国哈德良长城边上的一个要塞,在这里发掘有公元85年—200年罗马帝国时期的大量木牍。这批木牍形制比较特殊,通常以两片牍板对折的形式存在,文字横书右行,一般写在对折的两片木牍内侧。对折木牍的一边还留有孔或楔口,将数个这样的对折牍通过边孔相连,其结构特征非常形似纸书的蝴蝶装。因此,这些对折木牍可视为向多页书发展的过渡形式[15]258-271。
三、简牍文书的版式
版式也叫版面格式。现代书籍中的版式具体指的是版心以及周空尺寸,正文的字体、字号、排版形,目录、标题、注释、表格、图名、图注、标点符号、书眉、页码以及版面装饰等项的排法。简牍文书的版式比较疏略,与现代书籍版式大有不同。通观简牍文书的笔墨之迹,约略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文本文字,包括篇题、正文、计字尾题以及书手或校对者署名。第二部分为标号。第三部分为叶数。
1.篇题。篇题一般书于简册的首简背面或末简的背面,根据收卷方式的不同而有所分别。如果以一册简的最后一支简为中轴,字向内,卷起后首简在最外层,篇题就书于首简的背面,如睡虎地秦墓竹简的《效律》,张家山汉墓竹简的《二年律令》;反之,如果以首简为中轴,篇题则书于末简的背面,如睡虎地秦墓竹简的《语书》《封诊视》《日书》,张家山汉墓竹简的《奏谳书》。还有些带有篇次的篇题,会将篇题、篇次分书于两支简上,如武威汉简《士相见之礼》,第一简背面书写“第三”,第二简背面书写“士相见之礼”,按照左行读法,正是“士相见之礼第三”。
2.计字尾题。司马迁《史记·自序》言:“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即是对《史记》一书篇数字数的总计。计字尾题一般书于篇末的下方,如北大汉简《老子·下经》篇末记为“●凡两千三百三”[16]。有些计字尾题在篇末正面写满字时,还会写在最后一简背面的下部,如武威汉简《有司》篇。
3.书手或校对者署名。简牍上文字一般均为手抄,不过出土实物中抄写者姓名并不多见。尹湾汉墓6号墓出土的《神乌傅》中一支简的下部有双行小字,整理者认为乃作者或抄写者姓名。张家山汉墓竹简中则有数处关于书手或校对者署名信息,如张家山汉墓竹简《引书》第76简末书写“●□吴”,张家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认为可能是抄写者姓名。又如张家山汉墓竹简《算数书》的42简、56简的地脚处分书“王已雠”“杨已雠”,则明显属于校对者的署名信息。
4.标号。除去文字外,简牍文书的文本中还会出现许多标号。其常见的主要有圆点号(●),其作用在于分章、分节、用作句读以及作为篇题或尾题的前缀符号;重文号(=),用作所重之文下;钩识号(﹂),用作句读;顿号(、),作用与钩识号相似,也是用于句读。此外,较为常见的标号还有三角形、斜线等。出土的简牍文书中,标号的运用情况不一。如睡虎地11号秦墓所出竹简主要是法律文书,所用符号主要有4种;《居延汉简》标号共有15种,用法近40种[17]。
5.叶数。叶数相当于今天书籍中的页码,出土简牍文书中不乏有叶数者。书写叶数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明确简序,防止编简错、脱。叶数一般写在简的下端,或在简正,或在简背,这和书手的习惯有关。由于书写叶数乃是书手的个人行为,叶数的编序也会出现不同的情况:一是一篇通用一个顺序来编排叶数;二是一篇有两个以上叶数顺序;三是一篇中一部分简有叶数,另一部分简无叶数。第二、三种情况出现的原因是因为一篇文字由不同的书手抄写而致,书手根据自己的习惯,或重编叶数,或不写叶数。
6.正文。笔墨之迹中最重要的是正文。由于是手抄,简牍文书中的文字并无字号的概念,但字体有所体现。就目前所见出土实物简牍文字中,汉代以前的字体有小篆、楚文字、秦隶。郭店楚简及上博简中的一些文字据考证“具有齐系文字特点”,其形体当与楚文字一样,介乎小篆的圆浑与隶书的方折。汉代实物简牍中的文字主要有近于秦隶的早期隶书、汉隶(八分体)、章草、新隶体(罗振玉谓楷七而隶三)。
7.缮写。简牍文书的缮写不同于今天的横书右行,采用的是直书左行,即从上到下、从右向左书写。为何会采用这种书写方式,已不可考,一般认为这与中国文字的构造、生理及心理等因素有关。缮写的格式主要有三种:(1)连写非提行式。就是从头至尾连续书写,不留白提行,出土的简册中这种格式最常见。(2)留白提行式。书写的内容告一段落后,不接写于简的空白处,而是换行另写,多见于遣册及分章类书写简册。(3)分栏式。将简牍从上至下分成若干栏,按照第一栏、第二栏……依次抄写,栏界或以栏与栏之间的空白作界隔,或刻以划痕,或以符号作为标识。出土实物中,简牍文书的分栏,从两栏到八栏都有,如郭店楚简《语丛》(三)第64—72号简分两栏书写;岳麓秦简《为吏治官及黔首》分三栏、四栏书写;睡虎地秦墓竹简《为吏之道》分五栏书写;岳麓秦简《质日》分六栏书写;《居延汉简》甲编1991分七栏书写;睡虎地秦墓竹简《日书》甲种第136—139简分八栏书写。
四、简牍文书的表面整饰
简牍文书的表面整饰工作贯穿于简牍文书制作的整个过程。竹、木是简牍的主要材质,基于防蠹、防霉、便于书写及存放等方面的原因,还需要对砍伐的竹、木进行修治整饰工作。竹、木的构造不同,在具体的修治整饰工作上也会有不同。
竹简的修治工作比较繁杂,首先要对竹筒进行截取和剖解工作,即《论衡·量知篇》所言:“截竹为筒,剖以为牒。”[4]194筒之长短取决于要造竹简的长短,许多时候一些竹节间距较大的竹子就能满足制作一枚竹简的长度,但是当制作的竹简较长或竹节间距较短时,也会在竹节上写字,这就需要对凹凸不平的竹节进行额外的刮削、打磨。截取的竹筒经过剖解后成为长条状,外层皮为竹青,内层皮为竹黄,文字一般写在竹黄上,为了便于书写,一般要对竹黄进行刮削、打磨。不过,在此之前要经过一道极其重要的程序——杀青。所谓杀青也就是对新竹进行脱汁,也叫汗青、汗简。《后汉书·吴祐列传》:“恢欲杀青简以写经书。”李贤注曰:“杀青者,以火炙简令汗,取其青易书,复不蠹,谓之杀青,亦谓汗简。”[6]2099从出土的实物看,杀青的过程并不是用火炙烤竹青面,而是炙烤竹黄面,及至背向火的竹青面被烤出、烤尽汁液。经过杀青的竹简不但能很好地防蠹、防霉,而且能起到定型的作用。

书写并编联好的简册,为美观和收藏的方便,还需要有一次等齐手续。所谓等齐,与后世的裁切书根相似,具体做法是将简册天头一端平抵在平面上,用刀锯切去地脚端不齐处。这种等齐手续往往会破坏简牍上所写内容,如武威汉简《仪礼》甲本《特牲》第十三、十四两简地脚端的叶数明显有被削去的痕迹[19]305。经过等齐手续的简册,经打磨后,其简端是平齐的,不过,也有例外。出土的战国简中有将简端修成梯形者,如郭店楚简的《性命自出》等;也有将简端修成圆形者,如上博简的《孔子诗论》等。相较于平端,梯形端及圆端费时费力,之所以如此修治,应当是出于美观的考虑。
等齐好的简册一般就可收卷存放了,有些简册比较重要,还会被装帧。甘肃天水放马滩一号秦墓出土有460枚竹简,大多保存完好,其中绝大部分简的天头地脚两面粘有深蓝色布片,推测应为装帧所用[20]。不过,在收卷之前,有时可能还会对简牍施加一道涂胶或上油的工序(并不是所有的简牍都有这道工序),但是这道工序是在书写前还是书写后存在争论。尹湾6号汉墓出土的木牍曾涂胶,石雪万认为是在书写前完成的[18]173;湖南长沙走马楼吴简在整理时发现竹简上有层植物油,整理者认为涂油是在书写编联后完成的,据此有学者认为所有的涂胶(油)工序都是在书写后完成的[21]148。笔者以为判断涂胶(油)工序是在书写前还是书写后要看简牍的具体情况。一是要看涂胶(油)的简牍是否存在削改处,削改处的墨迹是否存在渗透晕开现象,如果存在,证明是先涂胶(油),因为先涂胶(油),削改处的胶(油)被破坏,其处的墨迹渗透晕开程度与其他未削改处是不同的。二是要看涂胶(油)简牍的编绳痕迹处是否有胶(油),如果有,就要结合第一种情况判断;如果没有,就证明是先书写,后涂胶(油)。从目前出土的简牍看,武威木简中的《燕礼》若干简明显属于先涂胶后书写,至于尹湾6号汉墓出土的涂胶木牍和湖南长沙走马楼涂油吴简,惜其整理者并未作上述分析,结果正确与否还有待验证。涂胶、涂油不但可以有效地保护简牍及其上面的文字,而且可以使简牍表面光亮而有色泽,增强其美感。
在中国书籍史上,简牍文书占有重要地位,不仅是因为它产生的历史早、使用的时间长,而是它本身形成的各种制度对后世的古籍制度产生了很大影响。如“册”“编”“卷”均源于简牍,后世的“直书左行”“分栏”“页码”“标点符号”亦滥觞于简牍文书格式制度,即使今天的书籍制度中也时常有简牍制度的影子。因此,欲探讨中国古代的书籍制度,就必须研究简牍文书之形式,此所谓“源”明而“流”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