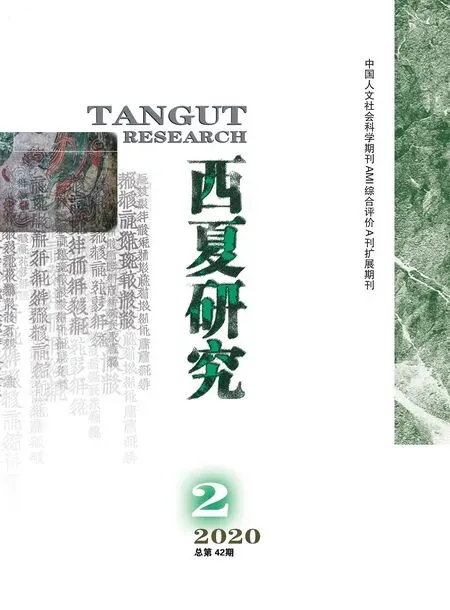武威出土西夏买地券背记符号考论
□张 涛 于光建
1997年在甘肃武威西关武警支队家属院发现一座西夏墓,出土一件西夏乾祐十六年(1185)汉文朱书买地券。1998年在武威西郊响水河煤矿家属院内又发现一座西夏墓,出土了一件西夏乾祐廿三年(1192)汉文朱书买地券。此两方买地券一经出土,学界便从不同角度展开了相关研究。
在买地券的出土情况、券文释录整理方面,朱安、钟亚萍等在考古简报中首次对武威武警支队家属院出土的西夏乾祐十六年(1185)西夏墓墓葬形制、随葬器物进行介绍,对券文内容进行释录[1]。姚永春对武威西郊响水河煤矿家属院内发现的西夏双人合葬墓中出土的西夏乾祐廿三年(1192)买地券进行介绍[2]。除上述两份考古简报初次公布录文外,还有学者在其著述中对券文重新进行释录整理。陈炳应[3]155-156,于光建、徐玉萍[4],高朋[5]280-281,孙继民[6]202-204,鲁西奇[7]307-309,黎大祥[8]314-319,李桥[9],等等将西夏乾祐十六年(1185)买地券与西夏乾祐廿三年(1192)买地券券文重新进行了释录校对,逐步解决了先前录文存在的漏、错、误问题,并对涉及问题进行了考证。
这两方买地券的源流问题也是学者们关注的重点。于光建、徐玉萍[4],高朋[5]42,鲁西奇[7]492,马春香[10],穆旋[11]等学者认为武威所出西夏时期买地券在券文源流与格式上主要以北宋《重校正地理新书》中所载买地券格式为范本,但李桥[9]认为西夏买地券与后蜀买地券有密切联系。
学者还通过买地券分析西夏时期的丧葬习俗。崔红芬认为西夏乾祐十六年(1185)买地券券文内容中所提及的中国本土神灵与党项人的天体信仰有一定联系,反映出西夏巫术的流行,认为可能含有某些道教成分[12]。于光建在论述武威西夏墓特点时,认为买地券反映出道教占卜、巫术信仰对西夏民众丧葬习俗有所影响[13]。
还有学者对此两方买地券中出现的人名、族属等问题进行考论。史金波[14]认为西夏乾祐廿三年(1192)买地券券文中提到的卖地者“咩布勒嵬”为党项人姓氏。在关于两方买地券主人的族属问题上,于光建[4]认为是党项人的买地券、鲁西奇[7]307-310认为是西夏汉人所使用的买地券、李桥[9]则认为是属于来自四川的遗民。另外,还有学者就券文文体中的祝文元素进行了探讨[10]。
综上所述,学术界关于此两方买地券的探讨多集中于买地券券文的释录整理、券文格式、源流、文体及道教、巫术对西夏葬俗影响等方面。值得注意的是,2015年《西夏文物·甘肃编》首次刊布了这两幅买地券多角度的彩版图录[15]1694-1697,使我们更加清晰真实地看到买地券的原貌,极大地帮助了我们对此两方买地券进行再认识。通过《西夏文物·甘肃编》所刊布的彩色图版,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两方买地券背面下部近中间位置都有朱书符号(见图1、图2)。这两个朱书符号看上去并非随意涂画,而是更像两个汉字拆解叠加构成。此两方买地券背后的神秘朱书符号究竟是书写者的随意涂写,还是具有其他特殊含义或功用?目前学界有关该买地券的研究都忽略了这个问题,本文将通过梳理相关丧葬礼仪的传世典籍文献,并结合已刊布的其他地区和朝代的买地券资料,予以解读,不妥之处,请方家斧正。

图1:西夏乾祐廿三年买地券(背面)朱书符记位置(红色方框处)

图2:西夏乾祐十六年买地券(背面)朱书符记位置(红色方框处)
一、买地券是下葬“斩草”环节中的镇墓明器
买地券作为古代民间葬仪中所使用的重要明器,在宋元之际民间墓葬的使用中颇有蔚然成风之势。关于武威西夏墓中所出土的两方买地券,学界均认为其券文内容与格式来源于北宋官修堪舆书《重校正地理新书》中所记载的买地券券文样式,此书所载买地券券文样式为官方标准券文样式。正如鲁西奇所指出:“进入金代以后,仿照《重校正地理新书》式样的买地券,在北方不断普及,并逐渐成为宋夏金元时期,北方买地券样式主流。”[7]488-495
要想解读武威出土两方买地券背后朱书符记,还是要回到买地券本身的用途上,厘清买地券在宋元时期的民间葬仪中究竟是如何使用的。北宋王洙所撰官修《重校正地理新书》详细记载了这一时期买地券在民间丧葬仪式流程中的使用情况,为我们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重要文献依据。
古代民间举行丧葬仪式的流程大致分为卜葬、下葬、谢墓三个主要环节,其中的下葬环节中又可细分为立“明堂”、行“斩草”仪式、营墓、葬埋、镇墓等环节[7]4-20。关于立“明堂”仪式与行“斩草”仪式的具体内容,《重校正地理新书》卷十四有详细记载[16]111。并且根据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所出P.3647号《葬经》文书中关于“推丧庭”之法的记载可知,“斩草”仪式也是在丧庭(明堂)举行[7]10。所以在行“斩草”仪式之前,需要先进行立“明堂”仪式。
据《重校正地理新书》记载,“明堂”是主管丧葬的神灵所居之地,亦是祭拜后土诸神的场所。并且立“明堂”是上自王侯下至庶人在下葬之前所必须遵从的环节,否则便是“大凶”,或称“盗葬”,将会招致灾祸,对生者不利。立“明堂”时,在墓地中心处取土设为祭坛,祭坛为方形,祭坛的周长随着墓主身份等级的不同亦有所不同。先王的祭坛周长为三丈六尺,而公侯及以下级别则为二丈四尺。祭坛的四个方向开有四口,称之为“四门”,分别是“天门、地户、人门、鬼门”。祭坛的上方设金、木、水、火、土五方上帝的祭祀灵位。此外,在祭坛的西南角设阡陌将军神灵位,墓穴口处设立幽堂亭长神灵位[16]111。《重校正地理新书》中附有《祭坛开天门地户人门鬼门主人祭官祝生及执事者位列之图》,对“明堂”祭坛大致形状、陈设、主人、执事、祭官、祝官(祝生)位置进行了绘制[16]112,使我们对宋元时期民间葬仪中所设立的“明堂”有了更加直观的印象。此外,根据书中附图注文可以得知,立“明堂”仪式是在行“斩草”仪式之前,这也正好与敦煌莫高窟出土文书所记载相符。
立“明堂”仪式结束之后,便进行“斩草”仪式。《重校正地理新书》记载下葬举行“斩草”仪式,其目的是为了“断恶鬼,安亡魂”。若不举行“斩草”仪式同样会招致灾祸,对生者不利。在行“斩草”仪式时,便会使用到买地券。公侯身份以下的亡者所用买地券为两方,长方形,长约一尺,宽约一寸。用朱笔书写券文,放置于祭坛上黄帝神位处。“斩草”仪式结束后,一方用于神灵,埋在“明堂”位心;另一方用于亡人,放在墓穴中的灵柩前。2008年山西汾阳东龙观金代明昌六年(1195)王立墓出土两方买地券,印证了《重校正地理新书》的记载。考古发掘报告称:“一方买地券置于墓室砖床正面靠墓室北壁,另一方买地券置于M5墓道东南发现一处活土小坑,买地券与地心砖相对盖压在陶罐上。置于墓室砖床正面靠墓室北壁的买地券可能就是用于亡人,置于灵柩前。墓道东南发现的买地券可能就是用于神灵,埋在‘明堂’位心处。并且两方买地券不仅券文内容一致,而且书体也一致,有可能为同一人书写。”[17]
二、行“斩草”仪式流程
《重校正地理新书》卷十四对行“斩草”仪式的具体内容记载详细[16]112,买地券在行“斩草”仪式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梳理行“斩草”仪式的基本流程,有助于我们对买地券功用的进一步认识,也便于理解武威买地券背后的朱书符号的含义。
首先要求参加“斩草”仪式的各位神职人员均穿着吉服,列于各自相应位置上。仪式所需各类祭祀供品准备齐全并归置于相应位置。准备完毕后,开始行“斩草”仪式。作为神职人员的执事带领祭官先从祭坛的东门引入。祭官上祭坛,到各位神灵位前布置位板与五色彩币。焚香完毕,祭官下祭坛从南门出,面向北方站立。接着,执事洗爵酌酒与祭官一同从南门进入祭坛,对祭坛上的各神灵位开始祭奠。祭奠完毕后,执事与祭官从祭坛南门出,面向北方站立。祝官则位于祭坛西南方向,面向东方开始跪读祝文。祝官读毕祝文,祭官便再一次进入祭坛。之后即将进行使用买地券的“斩草”仪式。
“祭官入,就黄帝位前,跪读两券,背上书合同字,置于旧处,俯伏而起,出南门外,北向再拜,行酒上香。”[16]112祭官在祭坛黄帝神位之前所诵读的券文便是《重校正地理新书》中所载券文,亦应是本文所讨论的武威西夏墓出土买地券正面券文。祭官还需到祭坛西南方的阡陌将军神灵位酌酒并诵读祝词。接着,祭官到黄帝神灵位前,将“斩草”所用的茅草放于幽堂墓穴前,酌酒诵祝词。祭官结束以后,祝生便开始引领诸位孝子跪坐于幽堂墓穴前。祝生手持铁剑并诵读祝词,然后将剑交与孝子,继续诵读祝词,孝子随祝生祝词内容指令“斩草”三次并将铁剑反向掷于五步之外。祭官再次进入祭坛黄帝神灵位前,进行跪拜祝酒诵读祝词。以上祭奠活动结束后,执事便将所斩之草、五彩信币及相应祭品进行祭奠,最后安置买地券。执事带领孝子将买地券一方埋于祭坛地心位置,另一方随后放置于墓穴灵柩前。[16]113
三、买地券背面朱书符号是“合同”二字
通过对《重校正地理新书》中有关“斩草”仪式流程的梳理,我们发现一个关键信息,即祭官在“明堂”黄帝神位前,“跪读两券,背上书合同字,置于旧处”。由此可见武威出土的这两方西夏买地券背面朱书符号可能就是此处祭官所写“合同”二字,并非随意涂画。同时,祭官在书写“合同”二字时,多以骑缝章形式将“合同”二字书于两方券边缘处,故如今保存下来的买地券背面的两枚朱书符记应为“合同”二字的一半。武威西郊西夏墓所出土的两方买地券是放置于墓室用于亡者的买地券,至于明堂中心位置的买地券,只是没有被发现而已。
买地券背后以骑缝章形式在两券边缘处书写“合同”二字的现象并非只存在于甘肃武威出土两方买地券中,已出土的唐宋元明时期买地券也多存在书写“合同”二字现象。如河南嵩县出土金大定二十九年(1189)董承祖买地券,在买地券方砖一侧,也写有朱书“合同”二字的一半[18];河南焦作金代冯汝楫墓所出买地券,背有阴刻骑缝“合同契券”字样[19];托克托县出土金代买地合同分券,在砖背面有半截骑缝字,上书“合同分券”四字[20]。
在买地券上书写“合同”二字,并不限于背面骑缝章形式。综观目前发现的各个时期的买地券资料,书写“合同”二字形式多种多样。有些书写在买地券正面骑缝处,如陕西西安金代李居柔墓所出土李居柔买地券便在正面券文左下角骑缝处书写“合同”二字[21]。有些直接在买地券正面书写完整的“合同”二字,如安徽合肥南唐保大十年(952)墓出土陈氏十一娘买地券,正面中书“合同”二字[22];安徽合肥出土五代汲府君买地券正面书有墨书古文“合同”二字[22]。甚至还有在券砖侧面书写“合同”的,如陕西铜川市阿来村明墓出土买地券,左侧另有楷体朱书“合同分□”四字,四字均为左半边[23]。综上,我们可以得知祭官无论是在买地券正面还是背面都会书写“合同”二字。由于买地券是受到道教因素影响下的产物,因此,祭官在买地券上书写“合同”二字时,有些会发生形变,将“合同”二字叠加书写,类似于道教符箓,以体现其神秘性。又或许与“买地券的券文书写方式会出现不同,目的是为了照顾神明的特殊阅读习惯”[5]22,这也就是为什么武威出土两方西夏买地券背面朱书符号既像叠压的“合同”二字的一半,又像一种符号。此外,1998年甘肃武威永昌镇刘沛村一座元墓出土的至元二十六年(1289)蒲法先买地券,背面也残留有类似朱书的符号,应该也是骑缝章样式的“合同”二字一半[24]。
综上所述,武威西郊西夏墓出土的乾祐十六年(1185)和廿三年(1192)两方买地券是研究西夏的丧葬文化,特别是为研究道教对西夏葬俗影响,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以往的学者多关注于买地券正文及其源流等信息的考论,忽视了背面的朱书“合同”符号。“合同”二字是祭官在立完“明堂”后、“斩草”仪式开始前,诵读祝词和券文内容后现场书写。买地券是古代民间葬仪中所使用的冥契,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人与神灵之间所签订的契约,相当于亡人向神灵购买土地时,亡人与神灵之间所签订的关于土地买卖的文书。买地券一共为两方,一方埋在“明堂”位心,交付给神灵;另一方则埋在墓穴灵柩之前,交付给亡人。祭官代替亡人与神灵在买地券上签字画押,在两券背面骑缝处书写“合同”二字。书写完毕,神明接受亡人祭物,合同生效,亡人所住墓地便为“合法”之所,而非“盗葬”,不会受到魑魅魍魉的侵害,起到镇墓避邪之用。
注释:
①高朋总结出买地券的券文书写方式有三种,分别为从右向左或从左向右、单行正书双行反书、依据地券形状来螺旋书写。高朋认为:“之所以会出现各种不同的书写方式,主要是为了照顾神明的特殊习惯。”并引用韩森的观点:“人们相信是神明发明了汉字,所以,给神明的那份契约可以用汉字书写。神明虽然可以读汉字,但他们会按不同的顺序来读,因为‘阴间诸事,均按另一种方式运行’。受此启发,或许祭官在书写‘合同’二字时发生形变,或许也存在此种功用。”具体参见高朋《人神之契:宋代买地券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