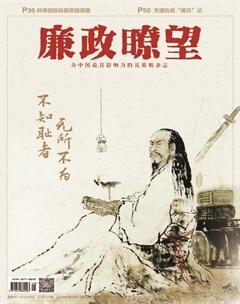“耻”字春秋,淘出国之小节与大义
曾勋
春秋时期思想空前活跃,文学艺术异常繁荣,“春秋笔法”几千年来为士人青睐。无论是苏轼、苏辙两文豪还是胡适、鲁迅,对彼时士人的精神品格都推崇有加。
孔门七十二贤之首的颜渊受鲁定公邀请去看马术表演,看到马跑了很远的路,但训练师仍然不停地鞭打它们,他便借机吐槽鲁国的国策,说百姓就像这些可怜的马,被逼得太紧。鲁定公听了,羞愧难当,赶紧认错改正。
《左传》《吕氏春秋》犹如“吐槽大会”现场,经常出现“寡人闻命矣”“寡人知过矣”等国家一把手检讨忏悔的表述。
那是一个“知耻”的时代,固有群雄并起,也无碍思想的空前活跃和文学艺术的繁荣,“春秋笔法”几千年来为士人青睐。后来的粉丝,无论是苏轼、苏辙两文豪还是胡适、鲁迅,对彼时士人的精神品格都推崇有加。
北宋时《春秋》为显学,据说欧阳修十多岁便可倒背如流,后来他作《廉耻说》,一句“廉耻,士君子之大节”达成了文脉的传承。鲁迅则在微言大义中解构了历史的嬗变——春秋时侠客是以“死”为终极目的,他们的结局大都慷慨赴死,而清代小说中的侠客,少了气节,不知廉耻,个个成了地主官僚和黑白两道通吃的混混。耻感文化在不同时期的强弱,凸显出各个时代精神与文化的荣衰。
耻辱之刑与华夏文明的原始耻感
《水浒传》中,被逼上梁山的好汉大都“有前科”,他们有的被逼杀人犯罪,受到的刑罚都很相似,打一顿脊杖,随后在脸上刺下“金印”,最终发配充军或者囚禁,宋江、武松、林冲等人的脸上刺的是“囚”字。这种刑罚叫墨刑,让犯罪者脸上刻着永远都磨灭不掉的“耻辱”痕迹。追溯其渊源,还要到尧舜时期。
先秦时代,尚处于典范政治的原始社会,对违反道德、习俗行为的惩罚,国家采取激发羞耻感等象征性惩治手段,以达到“刑期于无刑”的社会效应。当时,以德行教化民众的国家还没有形成一套道德体系,因而,用刑法羞辱的方式比较普遍。
《史记》和《尚书》记载,舜帝任命皋陶创造了最古老的法律《刑典》,其中的象刑据说是由舜帝亲自发明的。当时,人们通过罪犯所著之衣而知其罪行,由此激发犯人的羞耻感并引以为戒。
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常使用黥面的囚徒去做苦役。秦国商鞅变法时,有一次太子犯法,商鞅让办案人员找来太子的师傅公孙贾,说他纵容太子犯法,应该治罪,施以黥面,以示惩诫。公元前213年,丞相李斯奏请焚烧《诗》、《书》等书籍,规定说,如果命令下达之后三十天内不烧者,要“黥为城旦”,即刺面后罚作一大早就起来修护城墙的苦役工。
秦末农民大起义的队伍中,有许多是受过黥面之刑的囚徒。汉初被刘邦封为淮南王的英布,年轻时也曾因小罪被黥面。
在《周礼》中还有“耻诸嘉石,役诸司空”的记载,对于恶人,国家官员可以让他们坐在嘉石上去羞辱他。耻诸嘉石在当时作为严厉的精神惩罚,它能够实行的前提条件在于民众心中有耻。到了民国,诸如游街、示众等与现代社会伦理相悖的刑法依旧大量存在。
用诸如象刑的刑法治罪而激发犯罪的羞耻心,在法学家荀子看来,这样的羞耻心是因为被剃发易服或者黥面而异于他人产生的不适感,十分原始,所以耻辱之刑法维系起来的也是原始而廉价的耻辱感。他说:“杀人者不死而伤人者不刑,是谓惠暴而宽贼也。”也就是说,假如只是象征性地惩罚,不是太便宜恶人了吗?如何让世人发自内心地知廉耻,在儒家那里,有一套更为可行的方案。
儒家思想下反求诸己的知耻
殷商时期卓越的政治家傅说,曾辅佐高宗武丁安邦治国,开辟中古时代的盛世画卷。一次,他與君王谈治国理政的经验,引出了古代士人理想主义的滥觞,“予弗克俾厥后惟尧舜,其心愧耻,若挞于市。”也就是说,作为臣子如果不能让君王做尧舜,那这样的辅臣,都该心存惭愧耻辱,就如同在闹市被鞭打一样。
这是《尚书》中关于耻感意识的理性记录,至春秋战国,奴隶主阶级没落,新的社会秩序需要新的意识形态。经过儒家与法家的阐释,耻感演化为类似劝诫的“消极自由”,逐渐成为裁量是非的标准和社会内在的道德意识。
据台湾学者朱岑楼统计,《论语》中有强烈的耻感取向,在全文498章中,竟有58章与耻感有关。其中说的“行己有耻”,为后世士人提供了立身立言的第一行为准则——只要自己认为是可耻的,就不能去做。而“耻”事的界定,在孔子之前,法家的管仲关于“礼、义、廉、耻”国家四维的经典早已有定义。
法家通过刑赏论荣辱的体系,并不被“在野”的传统士人青睐,儒学提倡的通过自省而“知耻”的道德规范,被普遍接受,后世程朱理学、阳明心学,都秉持了这样的耻辱观。
春秋战国,国家对“耻”的敏感空前。知耻的先决条件就是敢于承认错误,当时的国君很少有闭目塞聪的,大夫、官宦,几乎都将个人人格与国格对等,上演了一出出悲壮的耻辱者故事。
据《史记》记载,春秋时期晋国理官李离,因为误听属下的话错杀了人,想以死抵罪。晋文公说:“这是你手下官吏有过失,不是你的罪责。”李离表示:“我听察案情有误而枉杀人命,却要把罪责推诿于下级,说不过去。”并以错杀人就要以死偿命为理由,伏剑自刎而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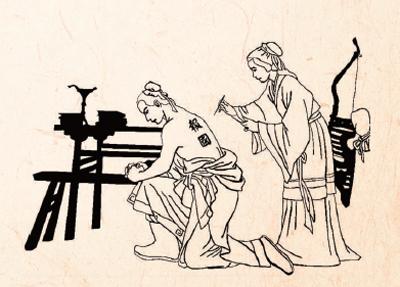
在楚国,国相石奢的父亲杀了人后逃命,石奢追上他之后出于孝道和情感,不忍心把父亲逮回去偿命,便将其放走后自杀谢罪,“坚直廉正,无所阿避”是后人对他的褒奖。
东汉时期,杨震却金的“网红故事”传遍大江南北,多少巨野文人骚客为其立碑扬名,正是在于他知耻而不为,不为钱财贪欲烦恼,立起了廉官的榜样。宋代理学家朱熹在《朱子语类》中,同样强调“人有耻,则能有所不为”。

明朝思想家吕坤提出“五刑不如一耻”,认为“知耻”比国法更为靠谱。龚自珍意识到“教之耻为先”,认为要改变世道人心,不仅需要外在的制裁,根本上还在于人们内心的道德反省。
历史荒野上呼唤耻感的守望者
关于耻感意识,孟子有更为思辨的论述,他在《尽心》上篇中说:“耻之于人大矣,为机变之巧者,无所用耻焉。不耻不若人,何若人有。”这句话的意思是,羞耻对于人来说是很重要的,行巧诈之事从来不会感到羞耻。不把赶不上人看作羞耻,怎么能赶上别人呢?
这句话的后半句,跟孔子所言的“知耻近乎勇”异曲同工。在孟子这里,君子必须把耻感当成重要的事情,时刻告诫自己敬畏的律令,以此防范贪欲和玩弄机谋。除此之外,君子要以羞耻感作为进取的动力,来追赶别人。
儒家将个人耻辱与国家的兴亡联系在一起,“知耻”的精神榜样塑造着社会成员的共识、荣辱观,影响着国民性格。而耻感激发的积极力量,也常常融于历史上个人成败与国家荣辱的叙事中。
有的人以生命捍卫自尊自信的气节,而有的人以耻辱为激励,复兴一个国家。越王勾践卧薪尝胆,是一种积极的价值抉择。吴王夫差最后走投无路,勾践表示可以賜他百户人家,让他住在甬东(今浙江舟山)休养。夫差竟也是知耻之人,选择了自杀。
宋代靖康之耻后,高度发达和繁荣的宋文化为何再次遭受致命打击?尽管有岳飞“怒发冲冠”,有鲁迅在日本看到清国学生麻木不仁而弃医从文、投笔从戎,却都没有改变“国破”的最终结局。这就是顾炎武所忧虑的,“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
生活在王朝末世的顾炎武,目睹了贫国弱兵、厚黑横行,为唤醒社会的耻感而作《廉耻》一文,说:“朝廷有教化,则士人有廉耻;士人有廉耻,则天下有风俗。”
孔子和顾炎武的时代已然完全不同。在孔子的时代,“耻”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颇为寻常。而在顾炎武的时代,经历过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士人、百姓,对于家国与自尊的理解,都被异化了。
在历史的荒野上,不仕于清的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们,才是能说“太难了”的那群人,因为他们是鹤立鸡群的知耻者,孤独而无助。
——评章越松著《社会转型下的耻感伦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