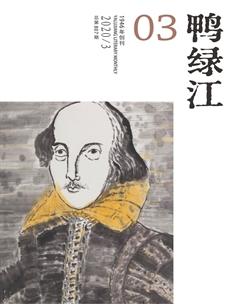论《了不起的盖茨比》盖茨比个人身份的追寻及幻灭
张益清
摘要:本文着眼于盖茨比的人物形象,以盖茨比对个人新身份的追寻及其幻灭为线索,从盖茨比身份的构建中抽象出“现实”和“浪漫”两种对抗的力量,试图透视1920年代美国社会在繁华喧嚣的社会现实背后社会文化不平衡发展的状况,并以盖茨比的个人命运为例寻找道德缺席的后果,以此作为探究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美国社会现状及其内在矛盾的一个侧面。
关键词:身份;现实;浪漫;爵士时代;道德
(一)现实与浪漫的二重奏
“浪漫”与“现实”始终是《了不起的盖茨比》乃至菲茨杰拉德研究的重要关键词。在《菲茨杰拉德学术史研究》中,程锡麟先生总结菲茨杰拉德作品中的现代性时提到:“菲茨杰拉德是1920年代最后一位浪漫的批评家,其批评思想在于以浪漫主义反抗现实主义范式的统治,即用浪漫主义的理解和创作去表现浓厚的现实细节,从而实现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理想结合。”①[2]
随着对1920年代到1930年代历史文化背景的关注,从外部视角对《了不起的盖茨比》进行批评的著作增多,“现实”具有了“物质”的意义。理查德·利罕在提出“作为一种建构的文本,《了不起的盖茨比》的意义出自浪漫主义与自然主义叙事模式之间、理想的信念与来自物质世界的对此种信念的限制之间的博弈”②,理查德已经指出菲茨杰拉德是在表达“一种浪漫幻想被物质主义所背叛的悲哀感”,这里进一步强化了物质和理想两种力量的对立。③[2]
菲茨杰拉德是美国景象称职的观察家,《了不起的盖茨比》的书写建立菲茨杰拉德对于1920年代社会的观察与评价之上,是有关整个美国社会在所谓“爵士时代”的价值追求和生产现实的记录。在保留对现实记录的同时,《了不起的盖茨比》中不乏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写法:既包括菲茨杰拉德在创作中自由的想象与包含作者情感态度的细致刻画,也指具体体现在盖茨比这一人物形象所具有的理想主义。笔者试图用“浪漫”与“现实”概括《了不起的盖茨比》中两股复杂缠绕的力量。而盖茨比正是在这两种力量的博弈中,找寻自己在美国社会中的新身份。
(二)身份的模糊性与20年代的美国现实
“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这句话对于1920年代的美国同样适用。20年代是物质极其丰富的时代,一战后的美国大发战争财,工业化推动着整个社会在消费主义的高速路上狂飙突进,金钱让整个社会生机勃勃地运转着;20年代是文化转型的时代,媒体崛起,爵士乐青年文化流行,艺术随着物质的繁盛生长;20年代是传统道德失落的时代,妇女选举权的获得吹响了性解放的号角,战争让人们陷入空虚,“美国梦”却鼓舞着人们奋斗至。浮华的众生相是时代铸就的故事舞台,菲茨杰拉德在如实记录意识到在社会急剧变动中所暗含的精神危机,盖茨比这一人物形象则投射了作家对于物质当道的社会微妙的态度。
菲茨杰拉德首先赋予盖茨比以“神秘”印象,突出其作为一名美国公民之后其身份的模糊性和复杂性。一个只有含义不明笑容的盖茨比,其“神秘”承担着厚重的形象意义。首先,盖茨比是多重身份角色的集中:他挥金如土;他说自己在牛津大学读过书;他是个私酒贩子;他参加过战争。每一个关键词都带着时代的烙印,将盖茨比神秘的个人身份与美国的历史与现状联系在一起。付塞尔在《菲茨杰拉德的美丽新世界》中认为菲茨杰拉德的小说与美国大陆的新历史都具有“追寻”和“引诱”两大特征,前者是对浪漫契奇迹的索求,后者是对这一过程的物化。而这种对幸福的追求具有普遍诱惑,“却被永久诅咒”。④[2]模糊的身份源自盖茨比的刻意隐瞒,这是他对于美好生活争取与融入的表现,但是这模糊的身份背后却是不光彩的欺瞒与黑暗的发家史。
真正的盖茨比无法在美国社会中找到合适的定位,哪怕拥有十倍百倍的財富,他也无法像汤姆·布坎南一样在聊天中就“白人的文明”一样大放厥词。对于出身的慌张掩饰在造成一种跨越阶级焦虑的同时其实也带了身份认证的焦虑,对于盖茨比个人而言,从何处来是一个需要撒谎和装饰的事情,而去往何处,即为自己的新身份划定一个确切的定位也依然不可能。何宁在博士论文《现代性的焦虑:菲茨杰拉德与1920年代》中用“焦虑”概括这种状,他认为这种焦虑不仅局限于个人,同时代表着美国文化在欧洲文化中迷茫无措的心理。⑤[3]
尽管财富成为指引着社会阶层的变动的指挥棒,对身份产生统一认同却依然是“盖茨比们”与“汤姆们”共同面临的难题。社会的开放开放性仅停留在表面,社会阶级在流动中缺乏稳固的精神力量和配套的社会秩序。于是我们看到,沉迷声色的人们如蜉蝣般穿梭于盖茨比的繁华世界,他们如同飞蛾般趋向寻欢作乐之处,实则对于试图跨越阶级的暴发户冷漠如冰。盖茨比的失败正是跨越社会阶级的碰壁,菲茨杰拉德在记录繁华与开放表象的同时,也指出了阶级社会的残酷与社会秩序的脆弱,盖茨比的命运正是“对‘新世界的残酷现代性,对它的冷酷、虚幻和荒诞最辉煌的陈述。”⑥[2]
(三)浪漫的爱情:新身份的通行证
菲茨杰拉德不吝赋予盖茨比的“浪漫”光环,使得这一人物具有更多的可探讨性,而这浪漫因素,同样是时代症候在盖茨比身上的展现。
以绿光为象征的对黛西爱情,是构成盖茨比人物形象浪漫的最主要部分。在如同将黛西视作祭司女神一般的虔诚爱情中,盖茨比以颤抖的虔诚与夸张的付出其俗套的重逢桥段中取得读者的共鸣和同情。有批评家认为黛西在小说中相当于“文化偶像”,而笔者认为,这个范围要加一个定语“之于盖茨比”的。重逢后的黛西已经嫁给在社会地位和财富上有保障的汤姆,她沉浸在这一角色中——一个看上去非常依赖自己丈夫的女人。哪怕在汤姆出轨之后,她小声说一句:“她起码该顾点大体,不在吃饭的时候给他打电话嘛。你说呢?”五年后,紧张的盖茨比见到梦寐以求的旧情人,他说:“她的声音里充满了金钱。”
当盖茨比站在阳台上眺望远处的绿光,我们也很难说这不是一场自我的感动和确认。此刻在盖茨比自我的认知里,他不再是往日一穷二白被爱情遗弃的年轻人,同时也与脚下这群寻欢作乐的男女区分开来,伪造身份和家庭的污点被绿光照亮,如果这一场场花销巨大宴会只是为了吸引旧日恋人目光这样的动人理由,那这金钱来自贩卖假酒的黑暗交易的事实大可不必想起。
黛西之于盖茨比,不只是是精神上的寄托,更是弥补往日身份带来羞耻的唯一途径,是对自己新身份的合理性的必要肯定。只有征服黛西,曾经因为贫穷卑贱被爱情抛弃的小伙子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脱胎换骨。有批评家将盖茨比对于黛西的重新追寻称之为“一味地缅怀某个浪漫狂喜的时刻并不断地梦想回到这个时刻”,这个时刻不见得多么甜美和值得回忆,只是当下的盖茨比拥有绝对性物质上的压倒,才可以居高临下地对往日单薄的浪漫爱情聊以怀念,背后不过是对于这“翻身仗”的再次确认。因此黛西此时的声音是否“充满了金钱”并不重要,盖茨比是否对黛西的爱情出自对对方的欣赏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要赢回黛西,才能在往日与如今构筑一条通道。
盖茨比的理想主义既否定了卑微的过往,又要否定迷惘与堕落的当下,他在内心既想要有足够物质财富带来的底气,又同时在心理上拒绝与这群寻欢作乐的人共同沉沦,他将爱情作为寻求身份的圣经,而这浪漫的想法背后仍然逃不过自私的渴望。
当盖茨比将贵重柔软的衬衣堆越堆越高时,在爱情的火热下颤抖的盖茨比仿佛与过去发生决裂。爱情胜利在望,道德不堪一击,当盖茨比这场漫长的准备中自我感动的外衣被剥落,悲剧的钟声也敲响了。
(四)道德:对身份的再次审判
马尔科姆·考利在《菲茨杰拉德:金钱的罗曼史》中这样描述菲茨杰拉德:“他同时也像是个来自中西部的小孩儿,站在舞厅门外,鼻子凑着玻璃,盘算着花多少钱才能够买票聆听音乐。不过,他看的不是一场舞会,而是一场由他主演并观看、充满矛盾风格和雄心壮志的戏剧。......他观看且又领衔主演的戏剧是一部有惩有奖的道德剧。”⑦[2]
盖茨比不确定的身份正是美国社会阶级变动、资本地位逐渐上升的表现,他游走在浪漫与现实之间的矛盾正是与虚荣的社会的博弈。菲茨杰拉德在盖茨比投射了对于时代的困惑和忧虑,而道德,是菲茨杰拉德对“爵士时代”背后隐隐的精神危机试图作出的解答。
每个人都认为他自己至少有一种主要的美德,而这就是我的:我所认识的诚实的人并不多,而我自己恰好就是其中的一个。⑧[1]
在緊接着的情节中,盖茨比在讲述自己的家庭背景和成长经历时布下许多谎言。这番对比也进一步印证盖茨比在富足体面的表象下也同样沾染着社会普遍的弊病。当盖茨比将寻找身份的方式寄托在浪漫爱情上,而且是寄托在一位庸俗虚荣的资产阶级少妇身上时,道德的缺位自然被强烈的渴望掩埋。当偶然的车祸发生,根据盖茨比的反应,我们不难推测盖茨比会延续他生命并不鲜见不光彩手段,在法律和秩序的空隙里试图越轨。
当然,这部“有惩有奖的道德剧”显然是不够公平的,黛西和汤姆毫发无损地逃离了长岛,寻求着一个身份认可的盖茨比却要因为道德上的瑕疵蒙受残酷的审判。盖茨比作为一个仍然向往着爱情的人,其身上保留的“浪漫”因素反而加速了他的悲剧命运,这样的情节安排可理解为菲茨杰拉德的一种反讽:当金钱至上的社会将人的真情与美好品质吞没,并不纯粹的“浪漫”是否多余而愚蠢呢?当浪漫没有道德的保障,是否冷酷且势利的现实才是最终的归宿?
盖茨比在死后只有乡下父亲赶来送葬,他最终的也是最初的身份,依然是南部农民的儿子。无论是勇立直面现实的浪潮,还是追寻浪漫的爱情,盖茨比都是爵士时代向上攀登的的人群的缩影。人们在阶级变动中看似有着寻求新身份的机会,但金钱打造的热闹在冷酷的社会中仅仅昙花一现,道德的失序终成人生的幻灭。菲茨杰拉德的书写中暗含着美国社会冷酷与失序,道德的审判是菲茨杰拉德所能够提出的应对社会弊病的最直接方案,而尼克在结尾提出的关于幸福生活的追问,仍然是需要在社会发展与个人奋斗探索的永恒命题。
注释:
①程锡麟:《菲茨杰拉德学术史研究》,程锡麟编选,译林出版社,第1版,第170页.
②理查德·利罕:《<了不起的盖茨比>——文本作为建构:叙事情节与展开》转引自《菲茨杰拉德学术史研究》,程锡麟编选,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年,第170页.
③同上
④付塞尔:《菲茨杰拉德的美丽新世界》,转引自《菲茨杰拉德学术史研究》,程锡麟编选,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年,第61页.
⑤何宁:《现代性的焦虑:菲茨杰拉德和1920年代》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⑥埃德温:《菲茨杰拉德的美丽新世界》,转引自《菲茨杰拉德学术史研究》,程锡麟编选,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年,第250页.
⑦马尔科姆·考利:《菲茨杰拉德·金钱的罗曼史》,转引自《菲茨杰拉德学术史研究》,程锡麟编选,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年,第19页.
⑧菲茨杰拉德:《了不起的盖茨比》.巫宁坤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第50页.
参考文献:
[1]菲茨杰拉德:《了不起的盖茨比》.巫宁坤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
[2]程锡麟编选:《菲茨杰拉德学术史研究》 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年,第15-250页。
[3]何宁:《现代性的焦虑:菲茨杰拉德和1920年代》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