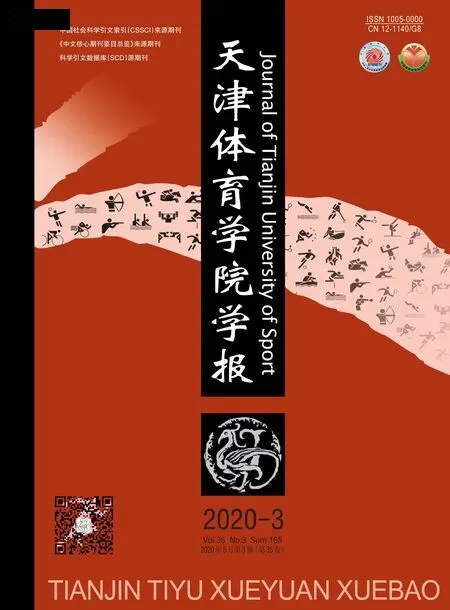百年学校武术发展中的教育权力实践及其新时代走向
王晓晨,乔媛媛,张 峰
教育权力作为学校教育场域实现公共秩序、保障教育权利与交往理性的必要存在而成为传统教育学、教育政治学乃至批判教育学研究的重要知识指向。学界对其类型、性质、结构、边界、渗透与消解过程及其伦理基础等都有着成熟思考。解构视向,教育权力被分为国家权力、规训权力、教师权力、知识权力、生命权力等内涵[1]。其中国家权力作为教育权力中的主流,决定着教育权力的实践向度,是不同时代国家需要在教育领域中或隐或显的时刻存在。制度、政策、课程内容、考评标准等是教育权力的运行空间。学校武术教育作为学校教育一脉,尤其是面对新时代体育强则中国强的发展诉求,其因具有构建和谐社会、弘扬民族精神、提升青少年体质与加强思想道德建设等价值而越发受到教育权力的关照。“国家对武术的需要程度决定了武术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2]“加强中华优秀文化教育、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落实立德树人的国家需要中,各级政府和地方教育主管部门开始重视学校武术教育的特殊意义和价值”[3]。国家与民族高度,学校武术教育在教育权力使然下将成为新时代发展的见证者、参与者和奉献者。回眸历史,学校武术时而成为培养国民尚武精神的手段,时而成为型塑“国家身体”的途径,时而又异化为西方体育形式。教育权力的如影随形引导了学校武术发展方向,也赋予了学校武术更多的工具理性。然而,历史表明,这种工具理性正是学校武术教育开展中诸多弊端的根源。那么学校武术百年历程中教育权力到底走过了什么样的实践过程?治理现代化背景下,如何运行教育权力才能更好发挥出学校武术应然的教育效果?教育权力实践下,未来学校武术将承继什么样的使命?在此聚焦教育与权力,一则发掘学校武术教育问题的根源,推动其发展;二则阐发权力在教育中的运行原则及学校武术教育的时代使命。
本研究创新之处是立足于微观权力视角,审视学校武术百年历程中教育权力的实践过程,归纳其在不同历史阶段呈现出的主要特征,为新时代教育治理现代化提供历史经验。这种通过批判与解构的思维方式来对个案课程中权力运行过程进行分析的思路,为教育权力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1 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是基于文献资料法,专家访谈法等手段而展开。文献资料主要来源于教育史、权力理论等方面的著作,如教育史学家陈青之的《中国教育史》、苏竟存的《中国近代学校体育史》、舒新城的《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王建华、高嵘的《学校武术》以及事关葛兰西的强权理论、马克思与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米歇尔·福柯的知识—话语权力理论以及涂尔干、吉登斯、鲍曼等社会学家对权力认知的书籍,并重点借鉴和参考了研究教育与权力的美国著名学者阿普尔的两本专著《教育与权力》《意识形态与课程》中批判教育学的研究思路和论证方法。同时在中国知网(CNKI)的期刊、硕博、报纸等数据中以“教育权力”为主题检索文献共计43篇,再以期刊层次、参考频率、论文质量,检索出2003—2019年间与本研究密切相关的博士论文2篇、核心论文6篇,为研究提供了一定的材料基础和清晰的研究进展。在此基础上,就近代以来我国教育发展中的教育权力实践主题先后对教育史博士、教育哲学博士及学校武术教育专家、学者等进行过半结构式访谈和学理分析(见表1)。

表1 访谈情况一览表Table 1 List of interviews
2 学校武术教育中的权力之维
卡西尔在其《人论》中指出,人有别于其他动物的文化定位就是人对“符号”的消费。人能通过“符号”去建构其族类的意义世界、创新着人的本质。如是,一个生物意义上的个体要变成一个社会意义上的人,就必须掌握有其族类业已发明使用且以“符号”为内容的文化。而文化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外化决定了它不可能像物种基因那样靠先天遗传,它必须借助一种后天的社会遗传机制来实现上代文化的下代化,而这种机制就是教育的滥觞。权力的分配与运作是同一场域内阶层与阶层或群体与群体间斗争与妥协的结果,其“无处不在性”对教育中的“文化传承”同样有着体现统治阶级或强势群体意志的切实干预。换言之,这种文化传承是为了实现对群体后代未成年人的培养,进而以此维系既有社会制度的延续和发展,才是其存在的根本。于是,教育作为一种“有意影响”的社会实践活动,往往承载着对人才的培养预期与愿景。当然,其意志也会渗透在教育环节的巧妙设计。如作为抓手的“课程从来都不仅仅是知识的不偏不倚的汇集,正如一个国家教科书里以及课堂中所显现的情形。它总是一种选择性传统的一部分,是某人的选择结果,是某个集团对合法性知识的见解”[4],要强调的“效果不是什么知识最有教育价值而是谁的知识最有教育价值”[4];教育功效更是“在儿童身上唤起和培养一定数量的身体、智识和道德状态,以便适应整个社会的,以及他将来注定所处的特定环境的要求”[5],其强调的是系统的社会化,以便社会秩序的维护;教育的实施过程更是利用纪律先行与奖惩分明、检查不断与评价反思等恩威并施、监视纠正的教育制度化模式,其科层组织化管理更是直接接受既有体制对教育的“赋权”,在结构与运作方式大同中学校教育场域也就实现了布迪厄所说的权力关系的再生产。一言以蔽之,权力与学校教育的偶联是一种固有特质。学校武术教育也不例外。不但如此,较之学校其它学科教育,学校武术教育与国家意志的关联更为紧密。这是因为项目文化传统延伸中,武术文化常常在国家内忧外患、社会动乱不堪之时,作为一面民族斗争的旗帜而凝聚着民族力量,鼓舞着民族的斗志[6]。因此,历代统治为了维护既有社会秩序的稳定,大都动用权力对武术实行“控制,干预,给它打上标记,训练它,强迫它完成某些任务、表现某些仪式和发出某些信号。”[7]总之,扬武也好,禁武也罢,都是权力基于时代需求而对武术的取舍和扬弃。置身历史传统,学校武术自近代开展以来就在权力的实践中工具性十足。
3 百年学校武术发展中的教育权力实践
“能知古始,是谓道纪”。近代百年是一个长时段,笼统地整体梳理与把握,难免概略与空泛;而其中数次变革对当时的学校武术教育的权力实践影响又成岭成峰,毕竟“时代变,斯学术亦当随而变”。因此,欲彰显百年学校武术不同历史阶段的教育权力实践特征,就必须对一如流水的百年学校武术教育史以宏观的变革为分期依据进行阶段划分,方清晰呈现学校武术不同发展阶段中教育权力实践的历史屐痕。
3.1 清末民国学校武术发展中教育权力的直接干预
众所周知,军国民体育教育思想肇始于清末,尚武强身乃其基本要义,而这正是武术的强项。况多事之秋的清末,无论是习武的社会基础还是武术理论与技术体系完善程度,都可谓集大成时期。然其体现“中体西用”思想的《奏定学堂章程》中并没有传统武术的身影而要“各学堂一律练习兵式体操以肆武事”,事实上其制定者张百熙、荣庆、张之洞等人并不主张全盘学习西方而西化。何也?近代学校体育史学者苏竟存一语成谶:“这并不是不认识武术的健身作用和尚武精神,也并非学习西方而排斥传统。可能是因为当时正当义和团运动之后,清政府对武术非常忌避,一般人也回避武术。”[8]也正如时人感叹:“庚子拳匪乱事初平,一般新人物,以识时务为俊杰的观念,孜孜乎稗贩外国体操作为训练学子的教材。谁敢说一句:我们中国有的是武艺,可以锻炼民众,是一种唯一的强民健族的体育啊!”[9]不难看出,清政府为了维护统治秩序,在学校体育课程内容的选择上有意规避了具有“狭以武犯禁”传统的武术。虽然这种具有僭越性质的权力运行方式时有与教育规律相悖之处,但其方式会直接影响到当时作为权力机器的学校、教育管理机构、媒体等社会单位。其实审视当时癸卯学制的办学宗旨“无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学生心术壹归于纯正……以仰副国家造就通才,慎防流弊之意”[10],也就不难理解为何清政府明知武术是学校体育的恰切教材,但在教育权力面前也不得不选择体操的无奈了。
及至北洋政府时期的1914年、1915年是提倡武术走进学校议案最多的年头,如徐一冰建议将武术列为高等小学、中学、师范学校正课的《整顿全国学校体育上教育部文》、徐禹生等人提出《拟请提倡中国旧有武技列为学校必修课》的议案等。然此刻也是袁世凯复古教育思潮澎湃之时,袁氏在1913年、1914年两年内先后颁布了《尊孔令》和《整理教育方案》,掀起了一股尊孔复古、保存“国粹”的逆流。有学者指出[11],此时武术走进学校作为一种教育手段,仅仅是袁世凯开展封建复古主义,尤其是恢复礼教来对抗新文化运动的手段。进而以图施行其“以道德教育为经,以实利教育、尚武教育为纬;以道德、实利、尚武教育为体,以实用主义为用,加以军队束伍进退之法”[12],即“爱国、尚武、崇实、法孔孟、重自治、戒贪争、戒躁进”[13]的教育要旨。马良的“中华新武术”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粉墨登场的,并被标榜为“我国之国粹,我国之科学”,得到了军阀政府和“国粹派”教育家的支持。于是始有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那班教育家,把‘九天玄女传与轩辕黄帝,轩辕黄帝传与尼姑’的老方法,改称‘新武术’又是‘中国式体操’,叫青年们去练习”[14]的辛辣调侃。其实主张推动武术和“新武术”进学校并不全是出于尊孔复古的动机,有众多教育家、体育家、武术家等社会精英是为了国家除弊振衰,但用力效果远远不如政府。如“《中华新武术》得到教育部的审定推行,迅速进入学校,由此也助长了纷纷扬扬的武术热”[15];而且马良以其政治地位以及议员王讷、北洋政要徐世昌、段祺瑞以及社会名流梁启超等人的助力将新武术在其主政的山东、江苏等地进行了广泛地推广[16]。即使是鲁迅、李大钊等新文化运动主将在看出北洋政府的教育意图,但也淹没在教育权力的强大意志洪流之中了。
1927年以来,国民党政府对学校体育课程中的学校武术进行了多次调试,如1929年颁布的《小学课程暂行标准》《中学课程暂行标准》中分别有“将乡土游戏和国术均列于教材之中”[16]“要加入适当国术内容”[17];以及1930年教育部勒令各省市教育厅“应于体育课程内酌增国术教材”[18]。课程标准上,虽强调基于青少年身心发展,但更强调训练“生活上和国防上所需之基本技能”[18]、国术与童子军及军事训练结合。意即社会内外交困、动荡不安的时局之下,学校武术教育不仅是国民党政府培养青少年尚武精神、粉饰盛世的手段,更是其强调党化教育的工具和载体,而且还会根据国家需要而刻意直接支配学校武术。
3.2 新中国学校武术发展中教育权力的有意影响
新中国成立之初,学校体育选择了弃美学苏,全面模仿与实践苏联学校体育理论。此背景下,武术被定位为一般体育。置身奥林匹克体育丛林的武术也白沙在涅,其项目文化个性差异被无视。加之当时社会稳定程度有待加强,部分国民党残余势力利用武术帮派进行反革命活动,造就了武术在当时政治背境下的负面形象。于是国家“对武术实行控制规模使之有节制的发展战略”[19],学校武术作为武术的重要板块也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人民政府应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20]的最高决议中亦步亦趋。最能反映这段史实的应该是这段时期学校体育中关于学校武术内容的设置。梳理发现,从新中国成立到1956年基本上没有学校武术课程内容,有的仅仅是具有武术意识的对抗和角力。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61年教育部颁布的第2 部学校体育教学大纲[21]。
1953年“全国民族形式体育运动大会”之后的社论与学校武术调整。一直以来学界对这次大会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它是建国初期较高水平地展示传统武术的一次大会。其赛事安排借鉴了1928年和1933年中央国术馆主办的国术国考的模式,特别是以击舞合一、打练结合为圭臬的选拔程序与经验。然而,这次大会却受到当时主张体育化改革人士的批评。《新体育》的社论:“毕竟是封建社会中形成的”“不免受到封建性的影响……所以,如何使民族形式体育更能具备锻炼身体的实用价值和树立优美的形象,被确立为今后的民族形式体育发展的方向”[22]。这次评论是新中国成立后武术改革的逻辑起点,也是学校武术走向套路化,“树立优美形象”的发端。始有国家体委武术负责人毛伯浩的“套路是武术运动的主要内容……会展现出矫健敏捷,勇敢优美的形象”,“可以看作是中国古代的自由体操或艺术体操”[23]等对武术学科发展影响至今,余绪未消之基调。
虽然到60年代初已经努力摆脱苏联体育模式,开始探索具有我国特色的学校体育课程,主张义务教育体育教学大纲要加大民族传统体育的比重,然“课程知识的选择和分配是社会权势者依据某一选择或组织原理而做的选择……它赋予某个群体文化资本而剥夺另一个群体的文化资本”[24]。如1961年版《武术》讲义中:“武术是以拳术、器械套路和有关的锻炼方法所组成的民族形式体育”的带有时代烙印之界定。1961年制定的的大中小学学校体育教学大纲就体现了这种典型性。访谈中戴国斌教授用“戴着镣铐跳舞”来形容可谓恰如其分。“矫健敏捷,勇敢优美”初级拳术与器械套路一统天下,举手投足间只为展示“练为看”与体现攻防含义的虚拟和写意,对抗形式销声匿迹。及至文革十年,对“唯技击论”的批判越发使那些提倡“打练并进”的武术家谨言甚微而又不甘苟同。如成都体育学院郑怀贤[25]在各省不成立武术队、院校撤销武术课程和专项、禁止技击的情况下,成立武术表演队进行了以革命样板戏为主题的武术创新表演;北京体育学院成立了“武术革命战斗队”,张文广基于工人劳动特点创编了“大小铁锤”套路、夏柏华和门惠丰将由刀和朴刀的对练改变成扁担与铁锨的对练进行表演[26],这些都可谓是局部意志表达。
3.3 改革开放以来学校武术发展中教育权力的无声渗透
改革开放后,在对建国以来的学校体育发展,尤其是文革十年反思的基础上,教育部建构了全日制十年制学校《体育教学大纲》,大纲中透露的工具理性明显淡化,强调体质与技能兼顾。即使是1979年“扬州会议”对体质教育思想的确立及其随后的体质和技能教育思想之争,都在表达着一个信息,那就是“以人为本”逐渐在强化。意即“这是我国学校体育课程第一次真正以系统的学科知识体系为课程设计的基础,学科本位价值取向具有鲜明的“知识理性”色彩,强调体育知识与运动技能的系统性和完整性”[27],在人的全面发展上越来越趋于文明和民主。蓬生麻中不扶而直,学校武术也在峰回路转中也有着相应调适。如1978年学校体育教学大纲可谓一改往日:“在注意科学性和增强体质的同时,要保留武术本身的风格和特点,在操作上不仅简化了套路技术内容,还首次规定从高一开始,除少年拳外,增加单人或双人攻防动作”[28]。接下来的1982年的第一次全国武术工作会议、1987年的《全日制中小学体育教学大纲》也都在提升和强调着学校武术教育的地位。而1988年修订的《中小学体育教学大纲》更是具有里程碑式意义,因为它不仅增设了更加体现以人为本的“五禽戏”和“八段锦”等养生内容,还确定了延展至今未变的“培育民族精神,弘扬民族文化”的学校武术教育主旨与定位。虽然竞技武术在1979年、1984年、1991年、1996年等的《武术竞赛规则》指引下,特别是90年代入奥目标确立后越发凸显其难美性和竞艺性,学校武术在其影响下也走过学校武术竞技化、竞技武术教材化的发展历程,但学校武术课程内容的构建一直是在教育与竞技的逐渐分野中试图打破以运动竞赛为中心的编排体系,恢复武术文化传承与精神培育的知识范式。
不难看出,改革开放后学校武术发展中的教育权力实践特征由清末民国时期的简单粗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有意影响后,在凸显人的主体地位的同时转向了隐秘而柔性。从“什么知识最有价值”到“谁的知识最有价值”的命题变迁中,以知识为中心的反思与追问已成为教育政治学思考的重要向度。阿普尔在其著作《教科书政治学》中指出,察视教育权力实践路向最好的办法就是对作为官方知识的课程内容的选择进行透视。基于此方法论,审视自1978年至2000年的6次中小学学校武术课程内容调整,基本上是围绕着技术知识体系的完善。在围绕“传承民族文化、弘扬民族精神”的教育主旨中持续实现了让习练主体不仅学会武术对身体的使用,而且实现武术对身体的控制。学校武术通过其具有“自我技术”属性知识的规训而完成了对学生的社会化过程。进入21世纪,尤其是2003年“全国两会”再次提出教育的民族性问题上,指出民族传统体育要发挥应有的作用以及2004年中宣部和教育部联合颁发的《中小学开展、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教育实施纲要》又发出了“体育课中应适当增加中国武术”的号召之后,学校武术课程在理论知识内容的建构上有了更系统的归纳和提炼。如大学武术教材[29]中的武德与武礼及其主要规范的明确;武术的“兼容并包”“道德至上”“宗教中心”“务实精神和恒久意识”“崇尚权威”“追求中和”的主要文化特征归纳;武术对中国传统哲学“太极阴阳学说”“五行生克”“天人合一”“道论气论”“形神统一论”的融摄和对兵家、传统美学、传统医学、宗教、艺术等相互镜鉴的提炼等。这些知识的选择和搭配其实就是在传达着知识—话语权力,它就是通过知识表述来达到一种意义、价值和规范的建构。这种建构与制度、法律意义上的直接影响一样,规范着人们的思想行为、价值观念,让青少年习焉不察地实现了教育权力的预设。这也包括最新的学校武术教改理念及其课程知识选择[30]:“一校一拳”思路的指导下,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学校武术课程知识的选择上,除武礼、武德、基本功、套路、格斗等内容外,还添加了民族气息浓厚的武术典故、武术电影等文化手段。这些知识所构建的话语体系已经是权力的客观存在,因为课程知识作为权力抓手必然会使被教育者思想与行为的趋从。课程知识本质在社会层面上已经客观地成为一种用来维护国家意志和利益以及教育未来接班人的工具。只是这种“毛细血管式”知识—话语模式,以“更加弥散的‘规训权力’或者‘怀柔’取代了建立在压抑与禁止基础之上的集权式的和等级性的控制形式”[31]来创造了自己约束自己的对象。
4 新时代学校武术发展中的教育权力实践走向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伴随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确立,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也走进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如斯背景下,在梳理百年学校武术发展中教育权力实践的基础上,对其新时代的未来实践走向的反思就显得尤为重要。正如王岗所言:对于走进新时代的中国武术研究,我们必须紧紧围绕着“人”的个体需要,“社会”的发展需要,“民族振兴”和“国家治理”的需求。聚思之,未来如何调适使得学校武术在教育与权力的张力中保持“恰到好处”,让其最大程度发挥“立德树人”的教育价值,对接国家需求与民族伟业的同时越发呈现基于项目内源性的“现代化”。
4.1 继往开来:教育权力指引下学校武术教育续接文脉的历史担当
为了应对民族危机,学校武术成为了强种尚武的手段;为了维护民族情结,学校武术成为了“土洋之争”的工具;为了提升体质健康,学校武术成为了卫生之方;为了与西方体育同台竞技,学校武术又成为了奥林匹克的附庸。正如卢梭在其《社会契约论》中所言:“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一样,社会变迁也对学校武术必然提出新的挑战和机遇。新时代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这一近代以来民族夙愿的关键时刻。学校武术教育也必然基于“新的历史方位”而被赋予以“中华民族作为发展的定位、以民族认同作为发展的定向、以民族复兴作为发展的定性”[32]的文化使命。学理上,民族的认同、国家的认同始于文化的认同,然梳理近代以来的传统文化在教育场域的认同塑造却并不理想。自20 世纪初清廷废除科举后制定的“癸卯学制”始,就消解了由经学、史学、诸子、词章构成的“四部之学”的传统文化传承格局;民国更是将“四部之学”转变为囊括文、理、法、商、医、农、工的“七科之学”;及至新中国成立后,“历史积蓄的能量在西方科学与民主的引领下造就了五四‘反传统主义’的强大动力,它以摧枯拉朽的‘疯狂’造就了中国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中的‘文脉断裂’。”[33]毋庸置疑,以学制架构变迁为载体的教育现代化为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提供了坚实动力,但对传统文化传承的冲击也是等量齐观。学界反馈上,无论是文化学者余秋雨在其《中国文脉》一书中对文化传承的反思,还是文化遗产保护学者冯骥才在两会上《让孩子体验传统文化》的提案,更抑或是国家两办联合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均隐喻了近代以来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在教育领域的没落。正如邱丕相先生在访谈中多次强调的穿着牛仔、听着摇滚、吃着肯德基的青少年对传统文化却知之甚少的现实境遇一样,学校武术教育置身当前网络传播时代,在面对粗鄙、时尚、快餐式,甚至低俗的消费文化时,以文化传承来延续国脉,打造固本工程,成为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中坚之一已是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因此,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在两会上力推武术、太极进校园的呼吁;体卫艺司司长王登峰“以学校武术教育助力国运昌盛与国脉传承”[34]的呐喊,无不是这种时代诉求的直接反映。
4.2 进退有度:教育权力对学校武术干预要恪守学科规律与底线
“学科是一种话语实践的整体性陈述,每一个话语实践都可以由它所形成的知识来确定。”[35]意即学科作为科学的分门别类,有着相应的体系内涵和学科边界。诚然,这些也为学科教育实践提供了基本的操作框架。因此,学科正如其“discipline”的英文表述一样有着“规训”的权力意味。这种学科权力“一方面具有生产性,致力于生产、培育和规范各种力量,另一方面则像毛细血管一样嵌刻于各种知识模块中。”[36]无疑,学科是通过知识模块小心谨慎地调适与安排来实现其话语权的,教育权力也需要通过这条路径来主张,否则就会破坏学科基于完整体系所建构的正常生态。20世纪60年代学校武术在“唯技击论”批判影响下对技击的阉割与套路的一统天下、改革开放后在入奥的国家指引下的竞技武术教材化的取向,无不是教育权力对武术学科影响的结果。只不过这种影响过分矫枉过正,使得学校武术在学科的正常轨道上发生了偏离,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异化。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国家实力的提升,体育的工具理性趋于淡化,“史上那种挟意识形态以壮声色而对武术横加干涉的时代已潮退汐逝,武术已进入全面恢复真正身份,在尊重学科规律下重构教育体系的时代”[37]。也就是说,学校武术教育实现青少年体质健康、培养其健全人格,同时让其正确面对人生的坎坷、输赢,恰切处理与对手和同伴关系的历史时刻到了,即使学校武术教育依然是被支配的教育。而要实现解构教育权力对学校武术教育过渡干涉的沉疴,让学科基于教育规律、学科特征而自我建构的目的,在方法论上就必须取道中庸的进退有度。进入21世纪初,随着学界对武术本原思考的深入,学校武术教育一改往日的竞赛套路模式。从2004年邱丕相、蔡仲林、周之华等人的“淡化套路、突出方法、强调应用”,到2006年吕韶钧、武冬的“突出拳种、优化套路、强调应用、弘扬文化”,再到2013年赵光圣、戴国斌的“一校一拳、打练并进,术道融合,德艺兼修”的教改理念和思路的变迁;虽出于满足弘扬民族精神、传承民族文化以及提升青少年体质的国家需要与号召,但教育权力对学科的干预已然兼顾了学科本源。时至今日,为了保障教育规律和学科特征的正常发挥和维护,在对接国家到2025年实现中华优秀文化传承发展体系基本形成的总体目标的基础上,在体育院校武术专业技术课程改革,这一培育学校武术教育师资的源头上,杨建营提出的“立足拳种、回归技击,形成体系、弘扬文化”[38]理念更是中庸了权力与学科之间的张力,凸显了学校武术教育主体性阐释立场。
4.3 以人为本:教育权力对学校武术教育主体应持的基本理念
“今天中国武术发展目标迷失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没有搞清楚‘为了谁’的问题”[39],历史总是惊人地重演,百年学校武术教育发展中也不乏这种迷失。特别是在教育权力使然下,学校武术教育中那种应然的“君子不器”式的教育理想与实践往往犹如羚羊挂角,以人为本常常挪作它用。如1915年的《颁定教育要旨》中,学校武术教育成为“卫身即卫国,卫国即卫身”的尚武手段;1928年《请令全国学校定国术为体育主课案》中学校武术教育成为了对抗欧美体操教育的替身;1940年《拟请由部通令全国大中小各级学校列国术为必修科案》中学校武术教育又成为健勇自卫、精神动员的工具等,这些都不一而足地表明教育权力影响下学校武术教育具有明显的工具理性和功利色彩以迎合当时社会诉求,而对置身其中者的“武以成人”却表达不足,意即人多被视为手段而非目的。康德在论其道德律时曾言:“你需要这样行为,做到无论是你自己或别的什么人,你始终把人当成目的,总不把他只当做工具。”[40]百年来学校武术教育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取得进步的同时,却逐渐消隐了“武以成人”的根本性宗旨,或者说淡化了正当的、具有善的价值的引导性力量。工具理性的放大与价值理性的萎缩使得学校武术教育目的已沦为一种迥异于人本的其他。因此,回归“立德树人”指引下,学校武术教育更应该在思考“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样的人”以及“如何培养人”的基础上,实现以人为本的终极追求。让学校武术教育真正实现基于中国文化立场,行为上以身体习练来体认文化传统,体悟融摄其中的传统文化精粹,使得文化传统和传统文化根植于心;心理上,通过“武德教化实现青少年价值观改造,圣贤引领匡正青少年信仰危机”[41];社会适应上,通过塑造“立如松”“坐如钟”“行如风”等的武术身体来实现青少年的果敢形象,以直面武术格斗成败来规训青少年的为人处世。正如吉登斯所言:“权力的运用并不是某些特定行为类型的特征,而是所有社会行动的普遍特征”[41],学校武术教育原本是一项以育人为主、教人向善的道德性事业,而权力的运用为学校武术做了很多“加法”,使得其既定育人功能因处于多元之一而趋于淡化。然在教育的公共生活中没有人能逃离权力的护佑而孤立存在,因为这关涉到个人权利实现的秩序。因此,教育权力实践的高明之处就是使青少年实现基本人权自由之后,又使得“能够个别地或集体地为他们自身(个体的或集体的)设立藩篱”[43]。当然,实现这种“藩篱”自我建构、这种由身体技术到技术身体转化的条件,不仅仅需要教育权力运行下公共秩序的维护,更需要大力阐扬权力中以人为本的善。
5 结 语
学校武术教育场域内,教育权力的实践逻辑一直是一种实实在在而又被长期忽视的客观存在。然而正是权力实践的不离日用和与生俱来,让人们在面对不堪重负的学校武术教育做减法时找不到真正的源头。因此,对百年学校武术教育中的教育权力实践进行多维透视,其意图并不是肤浅地回到当时的社会环境和历史现场,归纳出教育权力与教育互动的一些具体的、相对性的认知,而是要从事学校武术教育的人们更好地审视、把握教育权力运作机制对教育实践的影响规律,以便做出更科学的应对,并时刻保持高度的自觉,从而使这些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者真正成为教育实践的主人和拥有者,参与实现教育治理的进一步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