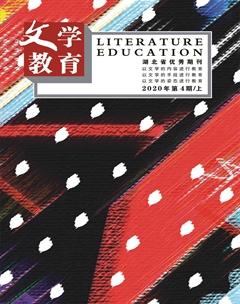曲阳苏轼《满庭芳》石刻题署时间献疑
内容摘要:苏轼有词《满庭芳》(归去来兮),今注本皆列元丰七年甲子作,又,曲阳县北岳庙内有石碑刻《满庭芳》,末题“元祐六年十月二日,眉山苏轼书”。今考相关史籍知:该词作于元丰七年四月,即东坡自黄州移汝阴时,其后于元祐八年十月知定州,刻于曲阳石碑。故石碑上“元祐六年”当作“元祐八年”。何以有误,蓋因风化脱落,后人讹补所致。
关键词:苏轼 《满庭芳》 曲阳石刻 题署时间
苏轼有词《满庭芳》:
公旧序云:元丰七年四月一日,余将去黄移汝,留别雪堂邻里二三君子,会仲览自江东来别,遂书以遗之。
归去来兮,吾归何处?万里家在岷峨。百年强半,来日苦无多。坐见黄州再闰,儿童尽、楚语吴歌。山中友,鸡豚社酒,相劝老东坡。 云何,当此去,人生底事,来往如梭。待闲看,秋风洛水清波。好在堂前细柳,应念我,莫剪柔柯。仍传语,江南父老,时与晒渔蓑。[1]
上为《全宋词》本。毛本(明毛晋《宋六十名家词》,收《东坡词》一卷。)题序上无“公旧序云”四字,“遗之”后有“旧词七首,考《北苑龙图》是淮海作删”,词文“去”作“自,”“酒”作“饮”,“此”作“远”[2]。傅注本(傅干注《东坡词》12卷)“去”作“自”,“酒”作“饮”[3]。彊村丛书本(朱祖谋《疆村丛书》收《东坡乐府》三卷)题序上无“公旧序云”四字[4]。各本皆列此词为元丰七年四月作。
今曲阳县北岳庙内两碑石上,有苏轼手书此词,篇末题“元祐六年十月二日,眉山苏轼书”。
一.碑石所书“元祐六年十月二日”有误
曲阳北岳庙,今属河北省保定市。《元和郡县志》卷二十二云:
(河北道)定州,禹贡冀州之域。……管县十:安喜、新乐、义丰、唐、望都、北平、无极、陉邑、深泽、恒阳。
……
恒阳县,本汉上曲阳县,属常山郡,后汉属中山国。高齐天宝七年,除上字,但为曲阳县,属中山郡。隋开皇六年改曲阳为石邑县,其年移石邑于井陉县,属恒州。七年于此置恒阳县,属定州。[5]
庙内留有北魏以来的历代碑碣二百多通,其中两通汉白石玉料石碑,面东并立,上有三首苏轼手书词:左侧为《行香子·述怀》,右侧为《临江仙·惠州改前韵》,两通碑背面合刻一词,为《满庭芳》。《满庭芳》词首行上题“中吕”二字,下题“庭芳”二字,末题“元祐六年十月二日, 眉山苏轼书”,词文“载闰”,今本作“再闰”。
据傅藻《东坡纪年录》载:
辛未……是年作感舊别子由诗序云:“元祐六年,予自杭召还,寓子由东府,数月复出领汝阴时,予年五十六矣。乃作诗,留别子由而去。[6]
由此可知元祐六年,苏轼移任汝阴。
汝阴郡,宋时即为颍州,今属安徽省阜阳市治。《宋史》卷八五《地理志》载:
顺昌府,上,汝阴郡,旧防御,后为团练。开宝六年,复为防御。元丰二年,升顺昌军节度。旧颍州,政和六年,改为府。……县四:汝阴,泰和,颍上,沈丘。……汝州辅临汝郡。[7]
考《续资治通鉴长编》:
(元祐六年二月)癸巳龙图阁学士吏部尚书苏轼为翰林学士承旨[8]
(元祐六年三月)乙酉龙图阁学士前知杭州苏轼言:“臣近蒙恩诏,乃赴阙庭。”[9]
(元祐六年五月)翰林学士承旨苏轼兼侍读。[10]
(元祐六年八月)壬辰翰林学士承旨兼侍读苏轼为龙图阁学士知颍州。[11]
同年,《颍州谢到任表》载:
臣轼言。伏蒙圣恩,除臣龙图阁学士知颍州,臣已于今月二十二日到任迄者。[12]
由此知:苏轼于元祐六年二月以翰林学士承旨诏还,五月复兼迩英殿侍读,八月出知颍州,八月二十二日到任。
再有,据《奏论八丈沟不可开状》载:
元祐六年十月日龙图阁学士左朝奉郎知颍州苏轼状奏。[13]
由此知:苏轼十月应在颍州任上,而颍州与定州相去甚远,一月内来回奔走的可能性不大。故曲阳县碑石所书“元祐六年十月二日,眉山苏轼书”有误。
二.此词作于“元丰七年四月一日”有误
今各注本,皆将此词列为元丰七年作。其依据多出自傅藻《东坡纪年录》和王文诰《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总案》。
《纪年录》云:
(元丰七年甲子)正月二十五日,特授汝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四月一日将自黄移汝。以留别雪堂邻里作《满庭芳》。
《总案》卷二十三亦云:
元丰七年甲子三月,告下,特授检校书尚书水部员外郎,汝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四月一日将自黄移汝,留别雪堂邻里二三君子,作《满庭芳》词。会李仲览自江东来别,遂书以遗之。
两本所记均与词序相和。然考《苏轼文集》卷二十三《谢量移汝州表》:
臣轼言。伏奉正月二十五日诰命,特授臣汝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者,稍从内迁,亦不终弃。[14]
又《赠别王文甫》卷七:
仆以元丰三年二月一日至黄州……尔后遂相往来。及今四周岁,相过殆百数,遂欲买田而老焉,然竟不遂。近忽量移临汝,念将复去此而后期不可必,感物凄然,有不胜怀者。浮屠不三宿桑下,有以也哉。七年三月九日。
由此知其确于元丰七年甲子正月二十五日有命移汝,三月告下。
然据《黄州安国寺记》载:
(元丰)七年,余将有临汝之行。连曰:‘寺未有记。具石请记之。余不得辞。……四月六日,汝州团练副使眉山苏轼记。[15]
又据《再书赠王文甫》载:
昨日大风欲去而不可,今日无风可去而我意欲留。文甫欲我去者,当使风水与我意会,如此,便当作留岁过客准备也。[16]
又有《歧亭五首》序云:
(元丰)七年四月,余量移汝州,自江淮徂洛,送者皆止慈湖,而季常独至九江。
再有《跋太虚辩才庐山题名》:
元丰七年五月十九日慧日院,大雨中书”[17]
由以上材料可知:元丰七年四月六日时,苏轼尚在黄州。故《纪年录》、《总案》及毛、傅注本题序中云苏轼于“四月一日将自黄移汝”有誤,其当于四月六日后离黄。另据《黄州安国寺记》一文中时已自称“汝州团练副使”,可知其离黄时间当在作文后不久,又《跋太虚辩才庐山题名》中书其五月十几日已至庐山,故推测东坡概于四月七日或八日启程赴汝州任,且将行又遇大风,多宿留一夜。
虽题序时间稍有讹误,然此词应确作于元丰七年东坡自黄移汝时。原因有三:
1.时间契合。词中云“百年强半,来日苦无多”,元丰七年,苏轼四十九岁,将值半百;又苏轼自元丰三年二月到黄州,七年四月移汝州,故其在黄州四年零两月。元丰三年闰九月,六年闰六月,与“黄州再闰”对应。
2.有史料为据。题序中云:“会仲览自江东来别,遂书以遗之。”序中仲览即李朔要,见《雪山集》:
杨元素起为富川,闻先生自黄移汝,欲顺大江,逆西江,适筠见子由,令富川弟子员李朔要先生道富川。《蒲(满)庭芳》叙所谓“会仲览自江南(东)来者是。[18]
又,《满庭芳》题序云:
余谪居黄州五年。将赴临汝,作《满庭芳》一篇别黄人。既至南都,蒙恩放归阳羡,复作一篇。[19]
以上皆可为证。
3.情绪吻合。《满庭芳》词,极写离乡之感,与黄人相爱之情及厌倦风尘奔波之意。此与苏轼离黄前赠友人王文甫书中所抒之情类同,《赠别王文甫》:
及今四周岁,相过殆百数,遂欲买田而老焉,然竟不遂。近忽量移临汝,念将复去此而后期不可必,感物凄然,有不胜怀者。浮屠不三宿桑下,有以也哉。[20]
苏轼受命移汝不久,即上表求常州居住,亦可为证。见《续资治通鉴长编》:
(元丰七年)辛酉责授黄州团练副使苏轼言,汝州无田产,乞居常州,从之。[21]
又见《乞常州居表》:
但以禄廪久空,衣食不继。累重道远,不免舟行。自离黄州,风涛惊恐,举家重病,一子丧亡。今虽已至泗州,而赀用罄竭,去汝尚远,难于陆行。无屋可居,无田可食,二十余口,不知所归,饥寒之忧,近在朝夕。与其强颜忍耻,干求于众人;不若归命投诚,控告于君父。[22]
故《满庭芳》(归去来兮)应于元丰七年甲子四月六日以后,是苏轼自黄移汝留别黄州友人而作。
三.苏轼于元祐八年十月重书于曲阳石碑
苏轼《朝辞赴定州论事传》云:
元祐八年九月二十六日,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左朝奉郎新知定州苏轼状奏。……臣虽不肖,蒙陛下擢为河北西路安抚使……祖宗之法,边帅当上殿面辞,而陛下独以本任阙官迎接人众为词,降旨拒臣不令上殿,此何义也?……臣已于今月二十七日出门。[23]
又有《乞降度牒定州禁军营房状》云:
元祐八年十月日,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左朝奉郎知定州苏轼状奏。[24]
由此知:苏轼于元祐八年九月二十七日以二学士出知定州,十月到任。
又据《重修曲阳县志》卷十二《金石录》载:
(知定州苏轼石刻)谨案此《行香子》、《临江仙》、《满庭芳》词三首。据明正德中浮休寺碑,此词刻初在济渎寺,后移于黉宫。今在县署二堂前西壁,共四石。诸家俱未著录,盖轼知定州时所书,字已多泐,邑士彭堃藏有旧搨,取而校之以补其阙,书其可辨者为大字,用旧搨补者侧注于下。……后首首行上题中吕二字,下文旧搨亦泐。下题庭芳二字,庭芳上满字亦泐。其词曰:‘略。末题‘元祐六年十月二日眉山苏轼书,见祇‘元祐二日及‘山苏轼书八字,尚有形可识,余则皆旧搨所有也。[25]
由此知碑石所记“元祐六年十月二日”,可识者只“元祐二日”四字,“六年十月”四字乃后人彭堃据旧搨补刻。而事实上,苏轼于元祐八年十月才至定州,且“八”字与“六”字在形体上确有误认的可能性。故私以为石碑上所书“元祐六年”之“六”,原作“八”,后因风化脱落,后人讹补所致。
故该词实于元祐八年十月二日,重书于石碑。
那么苏轼为何在九年后,又重题《满庭芳》于此?或出于两时之遭际和心境相同之故。
元丰七年,神宗念及“苏轼黜居思咎,阅岁滋深。人才实难,不忍终弃”,将其从黄州调至离京城较近的汝州担任团练副使。这本是个重归仕途的好机会,然苏轼却不愿去汝州,据上文《赠别王文甫》知此时苏轼已失望于朝廷的政争,有意归隐。又因其赴任途中幼子苏遯病亡,故才一面北行,一面上书乞常州居住。明年,元丰八年正月,神宗“报可”诏旨刚至,东坡即作《满庭芳》以示庆贺,词有云“船头转,长风万里,归马驻平坡。”[26]
元祐初,苏轼颇受朝廷重用,然自元祐八年八月起,苏轼的人生又一次滑落至低谷。八月一日,苏轼的继室王润之卒于京师。苏轼在《祭亡妻同安郡君文》悲诉其丧妻之痛,文中再一次流露出退隐之志,云:
我曰归哉,行返丘园。曾不少须,弃我而先。孰迎我门,孰馈我田。已矣奈何,泪尽目干。旅殡国门,我实少恩。惟有同穴,尚蹈此言。呜呼哀哉![27]
同年九月哲宗命苏轼出知定州,且出守日,拒绝苏轼上殿面辞。苏轼对此深感惶恐,故其在赴定州前所作《东府雨中别子由》中云:“今年中山去,白首归无期。”料此时,苏轼已经预感祸变将临,其心境之抑郁可知矣。
或许正是因为在这两个时间段,苏轼俱失亲人,又都失意于仕宦,故其到任定州后不久,重书《满庭芳》(归去来兮)于石碑之上,聊以自宽。
参考文献
[1]唐圭璋编.全宋词[M].北京:中华书局,1988.
[2][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O].清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
[3][宋]傅藻.东坡纪年录[O].四库丛刊本.
[4][元]脱脱.宋史:卷八十五[O].清乾隆武英殿刻本.
[4][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百五十五[O].
[5]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M].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6][宋]王质.雪山集:卷七[O].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清]周斯亿、温亮珠修,清董涛纂. 重修曲阳县志:卷十二[O].清光绪三十年刻本
[8][清]王文诰辑注,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2.
[9]苏文珠.曲阳苏轼手迹考[J].社会科学论坛(学术研究卷),2007(06):152-153.
注 释
[1]《全宋词》(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278页。
[2][明]毛晋辑:《宋六十名家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63页。
[3][宋]傅干注,刘尚荣校证:《东坡词傅干注校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13页。
[4][清]朱孝臧辑:《彊村丛书》,民国十一年归安朱氏刊本。
[5][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清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第221-224页。
[6][宋]傅藻:《东坡纪年录》,[四库丛刊本]。
[7][元]脱脱:《宋史》(卷85),[清乾隆武英殿刻本]第911页。
[8][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55),[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5698页。
[9][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56),[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5711页。
[10][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58),[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5735页。
[11][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63),[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5786页。
[12]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24),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690页。
[13]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33),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940页。
[14]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23),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656页。
[15]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12),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91页。
[16]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71),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261页。
[17]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71),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261页。
[18][宋]王质:《雪山集》(卷7),[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73-74页。
[19]《全宋词》(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325页。
[20]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7),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260-2261页。
[21][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42),[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4227页。
[22]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23),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657页。
[23]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36),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018页。
[24]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36),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021頁。
[25][清]周斯亿、温亮珠修,清董涛纂:《重修曲阳县志》(卷十二),[清光绪三十年刻本],第101-103页。
[26]《全宋词》(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325页。
[27]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63),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960页。
(作者介绍:张鑫,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在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