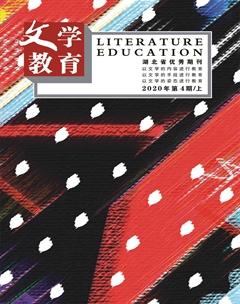试论汉赋的生态意识
内容摘要:汉赋的创作迎合了汉代的国情和社会历史条件,其展示的时代感,极具思想家的光彩。它在润色鸿业、歌功颂德之余,也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政治风气、政治环境和天子王朝一统天下的声威以及注重对自然景观的描绘,透过众多作品中记叙的生态环境的形势,烘托出浓重的自然主义意识。
关键词:汉赋 政治生态意识 然生态意识
汉赋被称为“一代之文学”[1]。汉代赋作家突破先秦的历史思想和诸子笔法,摒弃传统的创作拘囿,以自为自主的眼光审视国家社会和大自然,给人们带来了更深切、更阔远的认识。“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揽人物”[2],汉赋以其炽烈的政治激情、广大的容量、恢弘的气势给人以崇高感和巨丽之美,它在颂上德之余,总要寄寓积极干政、劝百讽一的理想,所谓“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3]同时汉赋又“图状山川,影写云物”[4],注重对自然景观的描绘,很多作品中记叙的生态环境的形势,透露出浓重的自然生态意识。可以说汉赋蕴含着赋家鲜明的政治生态意识和自然生态意识。
一.汉赋中包蕴的政治生态意识
政治生态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政治生活现状以及政治发展环境的集中反映,是政风、社会风气的综合体现。西汉王朝是在暴秦灭亡后建立起来的新兴政权,如何巩固新政权,根除社会潜在的矛盾和危机成了很多汉代文人关心的话题,汉初的散文就是紧贴新时代的产物,如《论积贮疏》《陈政事疏》《守边劝农疏》《天人三侧》《难蜀父老》《盐铁轮》等。同样,汉代的赋家也具有极强的时代感,居安思危,其赋作在颂其上德、彰显时代精神的同时,总要从不同的角度反映当时的政治风气、政治环境和发展趋势,表現出深切的社会终极关怀。
1.批判了是非颠倒的政治风气和用人风气,抒发士不遇时的愤懑。
汉初统治者基于亡秦之鉴,选择了无为而治的“黄老之术”作为治国之道。重礼乐,兴王道,举贤良方正,广泛搜罗人才,给士人带来革命式的希望。在这个历史的上升期,汉代文士普遍具有朝气蓬勃的进取精神。但最高统治者及其代表的集团由于自身的出身、地位和政治利益的需要,时不时的也表现出对儒士轻蔑和利用的态度,从汉高祖(刘邦)到文帝、武帝、宣帝、恒帝、灵帝等莫不如此。而到了东汉中后期,宦官专权,构害贤明,“主荒政繆”,文士的理想和尊严受到极大的伤害,“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5],不平的幽怨和愤怒,失意的抑郁和生不逢时的感伤和对求贤用贤理想社会的向往之情便贯穿在他们的赋作中。
汉初贾谊曾凭才学宣传礼仪,帮助汉文帝剪除诸侯王的威胁,“天子议以为贾生任公卿之位”,但“绛(侯)、灌(婴)、东阳侯、冯敬之属尽害之,……於是天子后亦疏之,不用其议,乃以贾生为长沙王太傅。”[6]“既以谪去,意不自得;及度湘水,为赋以吊屈原”(《吊屈原赋》)。赋中揭露了一个善恶颠倒,贤愚混淆的黑暗世界:“鸾凤伏窜兮,鸱枭翱翔。阘茸尊显兮,谗谀得志。贤圣逆曳兮,方正倒植。世谓随夷为溷兮,谓跖蹻为廉。莫邪为钝兮,铅刀为銛。……嗟苦先生,独离此咎兮”表达对屈原深深的同情,虽“追伤之,因自喻”,字里行间,流露出对自己无辜遭贬的愤慨。
东汉赵壹的《刺世疾邪赋》则将批判的矛头直指最高统治者,列举了汉末人情虚伪、世风日下、小人得志、贤者失位等种种龌龊的现象:“于兹迄今,情伪万方。佞诌日炽,刚克消亡。舐痔结驷,正色徒行。……偃蹇反俗,立致咎殃。……邪夫显进,直士幽藏。”对时政的揭露直率猛烈,针针见血,痛快淋漓。
当正义和真理被扭曲,士人的命途就充满不测,“哀哉复哀哉”的情调便弥漫开来。东方朔的《答客难》道出了士人任摆布,没有人格独立,怀才难展的境况:“尊之则为将,卑之则为虏;抗之则在青云之上,抑之则在深泉之下;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司马迁的《悲士不遇赋》发出整个时代士人的共同际遇、相同的感愤:“虽有形而不彰,徒有能而不陈。何穷达之易感,信美恶之难分。”
蔡邕有气节,“恒帝时,中常侍徐璜、左悺等五侯擅恣,闻邕善鼓琴,遂白天子敕陈留太守督促发遣,邕不得已,行到偃师,称疾而归”[7]。他的《述行赋》借古刺今,抒发志士仁人被压抑的愤慨:“弘宽裕以便辟兮,糺忠谏其侵急。怀伊尹而黜逐兮,道无因而获入。……周道鞠为茂草兮,哀正路之日涩。”他的《上封事文》提出七事表左,对求贤之道忠言锵锵:“夫求贤之道,未必一涂。或以德显,或以言扬。……臣愚以为宜擢文右职,以劝忠謇,宣声海内,博开政路。”[8]描绘了求贤用贤的理想政路,从这里,我们看到了蔡邕“并非单单的老学究,也是一个有血性的人”[9]。扬雄的《解嘲》《解难》对社会和世俗的批判,无论是“县令不请师,郡守不迎师,群卿不揖客,将相不俯眉,言奇者见疑,行殊者得辟”,还是“声之渺者不可同于众人之耳,形之美者不可混于世俗之目,辞之衍者不可齐于庸人之听”,都展现了对社会和世俗改良的期待。其《反离骚》正如李贽所云:“《离骚》,离忧也;反其辞,其亦忧也,正为屈子翻愁结耳”[10],即借批评屈原来发泄有志难伸的愤懑之情。
“悲士不遇”是汉赋一个重要的抒情主题,所谓治世叹存没,衰世叹治乱,乱世叹兴亡,历史的沧桑感赋予了赋家理性思考的空间,“悲时俗之险阨兮,哀好恶之无常。”(冯衍的《显志赋》)那种对世事变幻难以自主的彷徨无奈在祢衡的《鹦鹉赋》中得到宿命般的印证。该赋以鹦鹉自况,抒写才志之士生于末世屡遭迫害的感慨:“感生平之游处,若埙篪之相须。何今日之两绝,若胡越之异区。顺笼槛以俯仰,窥户牖以踟蹰。想昆山之高岳,思邓林之扶疏。顾六翮之残毁,虽奋迅其焉如。心怀归而弗果,徒怨毒于一隅。”以人鸟一境的氛围烘托了主人公身不由己,寄人篱下,听天由命的凄惨心境。
2.暴露了部分地方诸侯王与天子王朝的分庭抗礼之心
汉初仿秦实行郡县制,又分封诸侯王。而随着诸侯王势力日益强大,对朝廷对皇权逐渐构成威胁,成为当时政治格局中一件令人忧心的问题。如刘濞被分封吴王后,“乃益骄溢,即山铸钱,煮海水为盐,诱天下亡人,谋作乱。”[11]处处与朝廷对抗。枚乘《七发》就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表面上在劝诫楚太子不要纵情声色、贪恋安逸、沉湎享乐,实则暴露其抗衡皇权的野心,有谏反的意旨。李善认为枚乘作《七发》是“恐孝王反……以谏之”[12],这种推测不太合理,因为赋中提到的观涛之地曲江在广陵,而刘濞为吴王的封国统辖东南三郡五十三城,就定都于广陵(今江苏省扬州市),所以朱绶断定“《七发》之作,疑在吴王濞时。扬州本楚境,故曰楚太子也。若梁孝王,岂能观涛曲江哉!”(梁章钜《文选旁证》引)枚乘委婉提醒过吴王:“夫吴有诸侯之位,而实富于天子”,天子“修治上林,杂以离宫,积聚玩好,圈守禽兽,不如长洲之苑。游曲台,临上路,不如朝夕之池。深壁高垒,副以关城,不如江淮之险。”[13]邹阳也奏书谏说:“臣闻鸷鸟累百,不如一鹗……今天子新据先帝之遗业,左规山东,右制关中,变权易势,大臣难知。大王弗察,臣恐周鼎复起于汉,新垣过计于朝,则我吴遗嗣,不可期于世矣。”[14]但吴王不纳其言,难以改弦易辙,最终谋反而兵败被杀(参与七国谋反的胶西王卬、楚王戊、赵王遂、济南王辟光、菑川王贤、胶东王雄渠皆自杀),封国被废。
《子虚赋》是司马相如为梁孝王门客时作,赋中浓墨重彩的铺写楚王之淫乐侈靡,无不带有影射和劝谏孝王的意味。《史记·梁孝王世家》记载了孝王评定吴楚七国之乱后得到了其他诸侯王无与能比的优越:“於是孝王筑东苑,方三百馀里。广睢阳城七十里。大治宫室,为複道,自宫连属於平台三十馀里。得赐天子旌旗,出从千乘万骑。东西驰猎,拟於天子。”[15]司马相如显然看到了这种势头背后的隐患,通过齐王与楚王的比富斗奢、不守相关制度来批判诸侯王的僭越侈靡。如楚王出行“驾驯驳之驷,乘雕玉之舆,靡鱼须之桡旃,曳明月之珠旗,建干将之雄戟,左乌号之雕弓,右夏服之劲箭。”(《子虚赋》)文中的“雕玉之舆”“明月之珠旗”,按周礼官制,只有天子在隆重的场合才有资格享有的。《周礼·春官·宗伯·巾车》载:“王之五路:一曰玉路,钖,樊缨十有再就,建大常,十有二斿,以祀;金路,钩,樊缨九就,建大旗,以宾,同姓以封;象路,朱,樊缨七就,建大赤,以朝,异姓以封;革路,龙勒,条缨五就,建大白,以即戒,以封四卫;木路,前樊鹄缨,建大麾,以田,以封蕃国。”[16]这里,天子乘用的车辆叫“路”,所谓玉路、金路、象路等,是指车辆主要部件的两端采用的装饰物分别是玉、金、象牙等罢了;而“大常”就是太常旗,上画有日月星辰,代表天子气象。面对楚王等越礼的行为,亡是公警告说:“不务明君臣之义、正诸侯之礼,徒事争于游戏之乐、苑囿之大,欲以奢侈相胜,荒淫相越,此不可以扬名发誉,而适足以贬君自损也。”
汉代的分封是奖励功臣及优宠皇室、外戚等人的特殊的俸禄制度。诸侯王在其封国内得“自置吏”、有部分治民权,并且有权向封国内的人民征收赋税和征发徭役,诸侯王还有一定数量的军队。这种制度本身就容易滋生诸侯王的独尊意识,因而荒淫享乐、大逆不道、为所欲为,对抗天子王权的现象常有发生。除上述吴王、孝王外,江都易王非“好气力,治宫观,招四方豪桀,骄奢甚”[17],胶西王端“数犯上法,汉公卿数请诛端,天子为兄弟之故不忍,而端所为滋甚。有司再请削其国,去太半。端心愠,遂为无訾省。府库坏漏尽,腐财物以巨万计,终不得收徙”[18]。《汉书》卷六记载武帝时“(元狩元年)十一月,淮南王安、衡山王赐谋反,诛。党与死者数万人。”的事件[19]。就是到东汉朝这种特殊俸禄制导致的弊病也没有根本改变。如明帝时楚王英“与渔阳王平、颜忠等造作图书,有逆谋,事下案验。有司奏英招聚奸猾,造作图谶,擅相官秩,置诸侯王公将军二千石,大逆不道,请诛之。帝以亲亲不忍,乃废英,徙丹阳泾县,赐汤沐邑五百户。”[20]章帝时的济南安王“康在国不循法度,……多殖财货,大修宮室,奴脾至千四百人,厩马千二百匹,私田八百顷,奢侈态欲,游观无节。”[21]明帝永平十三年“十一月,楚王英谋反,废,国除,迁于泾县,所连及死徙者数千人。”[22]永平十六年“夏五月,淮阳王延谋反,发觉。癸丑,司徒邢穆、驸马都尉韩光坐事下狱死,所连及诛死者甚众。”[23]等等,不一而足。
3.凸显对大一统天子王朝的认同感
赋家有意识地暴露诸侯王的奢侈、僭越行为,显然是站在维护天子王朝的立场上来审视问题的,表现了直切时弊的勇气和对大一统中央集权的认同,很多作品都热衷于精心塑造一个物质丰富、国泰民安、国力强大、崇德尚义的盛世帝国形象。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在表现诸侯王竞富斗侈同时,也有将其与强大的中央王朝相比,使之黯然失色的意图。《上林赋》特意写天子对奢侈享乐生活的反省,革新政治,兴道义,惜民力,展现天下大治的盛世景象,凸显了对大一统中央王朝的认同感。
在西汉统治的二百多年里,都城建设主要以宫殿、园林为主。从刘邦入主长安,经“文景之治”,到武帝朝,“七十年间,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24]在国富民强之际,大兴土木之风日盛,于是殿宇台阁“千门万户”[25],林苑广布,“举籍阿城以南,盩厔以东,宜春以西,提封顷亩,乃其贾直,欲除以为上林苑,属之南山”[26]专供皇帝游猎。而赋家也将注意力集中在宫殿与园林的描写和歌颂上,以此表现天子王朝不可一世的气魄。继司马相如,扬雄的《羽猎赋》《长杨赋》都以天子游猎为题材,极力描写畋猎场面的壮观和天子气象的恢弘。《甘泉赋》则大肆渲染甘泉宫的崇殿华阙、金碧辉煌。扬雄用丰富的想象力写甘泉宫崔巍嶢嶢,通天绎绎;大厦云谲波诡,眼眩目晕;宫殿交互映衬,飞檐斗角,纷披叠出,气势雄奇。甘泉宫也是汉武帝接待外国宾客的地方,如太始“三年春正月,行幸甘泉宫,飨外国客。”[27]它的宏大壮丽代表着大汉王朝雄视天下四海的野心。《汉书》卷六十一载张骞说出自己在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等国的见闻,汉武帝“既闻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属皆大国,多奇物,土著,颇与中国同俗,而兵弱,贵汉财物;其北则大月氏、康居之属,兵强,可以赂遗设利朝也。诚得而以义属之,则广地万里,重九译,致殊俗,威德遍于四海。”[28]于是在甘泉宫接见张骞,“拜骞为中郎将,将三百人,马各二匹,牛、羊以万数,赍金币帛直数千巨万,多持节副使,道可便遣之旁国。……骞即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月氏、大夏。”[29]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陆上的丝绸之路,西域诸国纷纷发使来汉,看到的大汉帝国的“尊贵”和“广大”[30],从此大汉王朝的声威远播四方,这也从侧面证实了西汉赋家在赋作中所言并非一味的虚夸,还是有其真实的成分。
东汉时期的京都赋进一步延续着西汉人的大气风范,凸现了帝都的中心意识。无论是班固的《两都赋》还是张衡的《二京赋》,都以帝都为描写中心,逐步向四面辐射开去,反映出汉人在大一统帝国下业已形成的中心辐射心理。正是站在以帝都为中心的心理制高点上,赋家才能俯视天下,鸟瞰四方,将都城的山川形胜、宫殿园林、人物风俗、草木鸟兽尽收眼底。班固的《西都赋》从历史渊源、形势险要入笔,力举都市繁荣、沃野千里、宫阙华美、娱游壮观等事项,盛赞长安的富庶和繁华,表达希望皇帝能眷顾西土迁都长安理由。《东都赋》强调光武帝迁都洛阳,不是违背祖制,而是对西汉基业的发扬与光大:“迁都改邑,有殷宗中兴之则焉;即土之中,有周成隆平之制焉。不阶尺土一人之柄,同符乎高祖。克己复礼,以奉终始,允恭乎孝文。宪章稽古,封岱勒成,仪炳乎世宗。按《六经》而校德,吵古昔而论功,仁圣之事既该,帝王之道备矣”。并指出明帝继光武初备王道之后的历史功绩:“增周旧,修洛邑,扇巍巍,显翼翼,光汉京于诸夏,总八方而为之极”。这样既维护了前汉的皇权威信,又突出了后汉帝都无可替代的历史地位。
《汉书·王褒传》载:“上令褒与张子侨等并待诏,数从褒等放猎,所幸宫馆,辄为歌颂,第其高下,以差赐帛。议者多以为淫靡不急。”[32]汉宣帝针对这种批评,回答说:“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辟如女工有绮縠,音乐有郑卫,今世俗犹皆以此虞悦耳目,辞赋比之,尚有仁义风谕,鸟兽草木多闻之观,贤于倡优博弈远矣。”[33]汉宣帝评价汉赋时对“鸟兽草木多闻之观”的肯定之辞以及汉赋大量关于“鸟兽草木”内容的描述,足以说明当时的人们对自然生态环境的重视。
3.对生活环境自然美的理想选择
汉赋向我们展示了汉人对生活环境自然美的理想选择,不仅林苑、湿地草木葱茏,生机盎然,就是宫廷居处,也是花草炜炜,果木阴茂,绿树成行。如班固《西都赋》所列后妃之室,有“合欢、增城、安处、常宁、茝若、椒风、披香、发越、兰林、蕙草、鸳鸾、飞翔之列”,张衡《西京赋》写德阳殿内的美景:“濯龙芳林,九谷八溪。芙蓉覆水,秋兰被涯渚戏跃鱼,渊游龟蠵永安离宫,修竹冬青。阴池幽流,玄泉洌清。鹎鶋秋栖,鹘鸼春鸣。鴡鸠丽黄,关关嘤嘤。”李尤《德阳殿赋》从西、中、北三个方位写林木布局:“达兰林以西通,中方池而特立。果竹郁茂以蓁蓁,鸿雁沛裔而来集。德阳之北,斯曰濯龙。葡萄安石,蔓延蒙茏,橘柚含桃,甘果成丛。”冯衍《显志赋》写居处环境之美:“揵六枳而为篱兮,筑蕙若而为室;播兰芷于中廷兮,列杜衡于外术。攒射干杂蘼芜兮,构木兰与新夷;光扈扈而炀耀兮,纷郁郁而畅美”,都说明当时的人们会生活,懂得享受。
张衡《归田赋》营构一个心与外物和谐融洽的精神家园:“仲春令月,时和气清;原隰郁茂,百草滋荣。王雎鼓翼,仓庚哀鸣;交颈颉颃,关关嘤嘤。于焉逍遥,聊以娱情。”仲春时节,阳光和煦,空气清新,广袤的原野上百草丰茂,各种鸟鸣声充溢其间,这赏心悦目的境界让人意醉神迷,以至于作者或“龙吟方泽,虎啸山丘”,或“仰飞纤缴,俯钓长流”,逍遥自乐,“安知荣辱之所如”。东汉思想家仲长统也曾经表述自己“欲卜居清旷,以乐其志”的生活理想:“居有良田广宅,背山临流,沟池环帀,竹木周布,场圃筑前,果园树后。”“蹰躇畦苑,游戏平林,濯清水,追凉风,钓游鲤,弋高鸿。”[34]
人和自然的亲近和融合,可以净化心灵,涵养精神,提升思想境界。蔡邕《弹琴赋》谈及如果遇到像“丹华炜炜,绿叶参差,甘露润其末,凉风扇其枝,鸾凤翔其颠,玄鹤巢其岐”之木,则最适合制作琴瑟。演奏时,就会产生致“青雀西飞,别鹤东翔”,“走兽率舞,飞鸟下翔,感激兹歌,一低一昂”的艺术效果,表现了作者对理想精神生活的憧憬。
三.结论
总之,汉赋的创作迎合了汉代的国情和社会历史条件,其展示的时代感,极具思想家的光彩。
汉赋虽然主要写“京殿苑猎,述行序志”,有“兴废继绝,润色鸿业”(班固《两都赋序》)的政治文化功能,但也“并体国经野”[35]即要考察国家体制,观看田野规划。这说明汉代赋家对现实政治风情的关注、对自然生态环境的倾心是自觉理性的表达,至少是意义广大的精神意向。在现代中国生态工程建设的进程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自然生态要山清水秀,政治生态也要山清水秀。”[36]面对这种发展信念,我们理解、回味和探讨汉代赋家的生态观念,引发人们对未来的参悟和警醒,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
参考文献
[1]王国维.宋元戏曲考·自序[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9.
[2]葛洪撰,周天游校注.西京杂记[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93.
[3][16]吕友仁.周礼译注[M].郑州:中州出版社,2004:368,454.
[4][35]周振甫.文心雕龍选译[M].北京:中华书局,1980:211,78.
[5][7][8][20][21][22][23][34]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六十七、卷六十、卷四十二、卷二、卷四十九)[M].北京:中华书局,1999:1476,1338,1348,965,966,80,
82,1109.
[6][11][15][17][18]司马迁.史记[M].长沙:岳麓书社,2001:498,602,369,374,
375.
[9]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171.
[10]李贽.焚书·读史·反骚[M].北京:中华书局,1975:197.
[12]萧统,李善注.六臣注文选[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616.
[13][14][19][24][25][26][27][28][29][30][32][33]班固.汉书(卷五十一、卷六、卷二十四、卷六十五、卷六、卷六十一、卷六十四)[M].北京:中华书局,2009:2023,2002-2003,166,606,2531,2520,194,2348-2349,2352,2353-2355,2499-2500,2499-2500.
[31]徐志刚.论语通译.[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224.
[36]林亦辰.努力营造山清水秀的政治生态[N].中国纪检监察报,2016-3-11(02).
(作者介绍:严晴,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2017级中文六班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