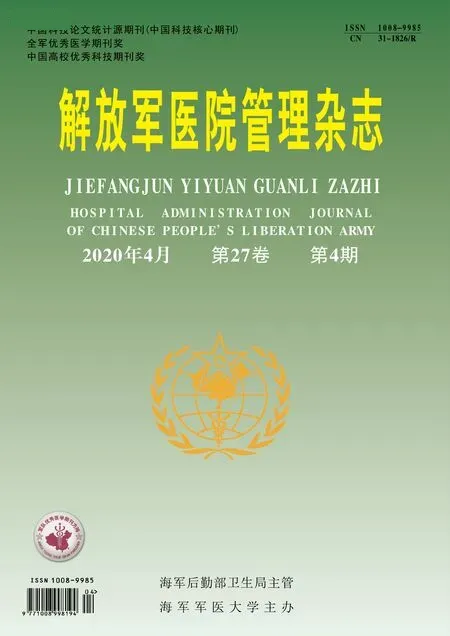现代海上医疗后送五级救治体系
胡家庆,刘 旭,康 鹏,唐碧菡,丁 陶,张鹭鹭
(海军军医大学卫生勤务学系卫生勤务学教研室,上海 200433)
早在100多年前,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的《海权论》为美国的繁荣强大指明方向,提出“强大的海上力量保障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繁荣富强的最佳模式”[1]。从军事历史看,海权对陆权在战略和战术上具有优势的普遍规律,被两次世界大战及英阿马岛战争等完全证实。
优良的海上医疗后送能力是强大海上力量的关键要素之一。新世纪以来,我军海上医疗后送能力逐步完善,标志是海上分级救治体系的初步形成和以920型医院船为主体的一批海上医疗后送骨干装备的入役。但是,从现代卫勤保障能力建设、适应海军远海转型需求来看,目前我军海上医疗后送体系建设还不完善,海上医疗后送保障能力尚不能满足多样化军事任务需要,特别是未来远海作战需要。本文结合多年海上卫勤保障实践、科研训练情况,提出构建现代海上医疗后送五级救治体系,为下一步海军卫勤建设和发展提供理论参考。
1 远海海上医疗后送的特点和要求
海军应具备应对多种海上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特别是要具备远海防卫作战的能力。现代海上作战是信息化条件下高技术战争,是大量使用新型武器装备和相应作战平台的现代化战争,是多军种联合、立体式和一体化作战,给海上医疗后送的组织实施带来巨大挑战[2]。陈国良等[3]概括现代海战中伤病员医疗后送的特点和要求,远海海上医疗后送还具有以下特点。
1.1 舰艇独立救治能力要求高 必须具备优良的官兵自救互救和卫生急救能力远海条件下,单舰艇是海上军事行动的一个基本战术单元,卫勤支援困难。一旦出现批量伤病员,首先将依靠本舰艇展开初级医疗救治,一般为自救互救或卫生人员急救。舰艇本单位的救治能力直接关系到伤死、伤残率的高低和预后。近年来的研究,将战场救治的时效性提到愈加重要的地位[4]。舰艇救治力量作为第一级反应单位,承担着伤员紧急救治“第一反应人”的角色。这也对舰艇救治能力提出巨大的考验。作为舰艇救治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官兵的自救互救能力以及军医、卫生员等的卫救水平,直接体现着本舰艇的医疗救护水平,直接决定着本舰艇伤病救治的能力。各国海军都十分重视官兵自救互救和卫生急救能力,美国海军[5]海上第一级救治阶梯由舰艇看护兵、医助和军医组成,主要采用自救、互救和急救等方法完成战术战伤救治(Tactical Combat Casualty Care,TCCC)。美军十分重视TCCC培训工作的普及化,要求每个海军官兵都要接受TCCC的培训,以此提高其自救互救能力。
1.2 编队早期救治能力要求高 必须具备优良的紧急外科和早期复苏能力舰艇编队是一个作战系统,是在一定的海洋战区内遂行战略任务而组织的战略战役军团,主要有航母编队、战斗舰艇编队、海上护航运输编队。舰船编队除了各舰艇的医疗救治力量外,一般在大型作战舰艇或运输补给舰上配置1个以上的编队救护所,承担编队伤员的早期救治任务,根据战伤救治规则规定,必须具备紧急外科和早期复苏能力。柴培俊等[6]指出,海上伤情的复杂性对编队早期救治能力提出较高的要求。编队卫勤力量首要的任务是开展伤病员的基本复苏治疗,稳定伤病情,保存受伤的肢体,为后送到下一级医疗机构接受确定性治疗打下基础[7]。美军经历多次局部战争和非战争军事行动的检验,发现编队良好的早期救治能力,将大幅度降低参战人员的阵亡率和伤死率。美军部署舰队外科手术队作为编队早期救治中重要的前沿复苏手术力量,目前编制18人,具备海上二级救治能力,能开展损伤控制手术,稳定伤员伤情,使其能在24~48小时内后送至下一级救治阶梯[8]。经历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美军前沿复苏手术力量优良的紧急外科和早期复苏能力已经得到检验,前沿复苏理念也逐步被大多发达国家采用(表1)。
1.3 后送时间长、空间大 必须具备优良的途中救治和重症监护能力远海行动中,海域辽阔、海况复杂多变,且任务区域一般距离后方卫勤保障力量较远,在进行伤员的医疗后送时,所需的时间长、空间大,伤员的伤情可随时发生变化。因此,在对海上伤员进行后送时,需要进行必要的后送准备,除了经过前一级救治阶梯确保其生命体征足够平稳外,要配备优良的途中救治和重症监护力量,及时应对伤员伤情的变化。根据我军伤员后送的原则和相关程序规定,在后送大批量伤员或危重伤员时,应指派专门的医护人员携带急救的药材和器械护送。后送途中,要随时观察伤病员情况,特别注意有无休克、窒息和大出血发生,并及时给予治疗。根据胡朝晖有关海战伤特点的研究[9],海战伤员多为烧伤和爆炸伤,且伤情一般较陆上更为严重,再加上海上特殊环境,伤员极易受到海水浸泡出现低体温症状。因此,在对伤员进行后送时,要建立静脉通路,进行补液同时要做好复温救治工作,而这些都要求我军在进行远海医疗后送途中,要配备专业的医护人员,具备优良的途中救治和重症监护能力。

表1 美军舰队外科手术队主要技战术指标
1.4 远离岸基依托 空运快速后送及海上预置保障成为主要手段目前发达国家海军普遍采用空运方式后送伤员,美军从朝鲜战争起在以后的历次战争中主要采用空运医疗后送方式,后送时间短、快捷高效[10-11]。马岛战争、阿富汗战争等实战检验证明空运后送方式是伤员后送最佳模式,同时也是伤员感觉最舒适的后送方式[12]。进行远海医疗保障时,远离岸基环境依托,不能仅依赖空运医疗后送,因此海上预置保障船队,能提高远海行动的机动速度和快速反应能力。即使是在全球拥有500多处海外军事基地的美军(据美国防部2018年12月公布的“军事基地结构报告”,美军在海外军事基地数量为514处),在多个敏感海区部署16艘海上预置船用于储备武器装备。我海军目前仅有吉布提保障基地,其他远海方向应该建设预置力量进行保障,可以使用远洋综合保障舰船或开设海上浮动基地保障,远海伤病员可以通过直升机“蛙跳”式从预置船上补给后连续快速后送。
1.5 医院船保障成为战时主要保障模式医院船作为海上移动医院,不仅具备强大的伤员救治能力,可提供确定性治疗,为包括复苏、创伤救治一期手术和术后治疗提供保障等,而且可跟随部队进行伴随保障。英阿马岛战争英军“乌干达”号加改装医院船共接收730名伤病员,施行500多例手术,死亡率极低,仅有3名伤员死亡。马岛战争作为现代真正意义上的远海作战行动,医院船保障起到降低伤死率和伤残率的关键作用。因此,医院船的伴随保障将会成为战时主要保障模式。美国在上世纪70年代末战略考虑大西洋和太平洋两个战略保障方向,由超级油轮改建2艘1 000张床位的医院船,“仁慈”号医院船隶属大西洋舰队军事海运司令部管辖,“舒适”号医院船归属太平洋舰队军事海运司令部管辖,分别部署于诺福克和圣迭戈海军基地[13]。在海湾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期间,医院船开展各类手术例数均超过300例,很大程度上降低美海军伤病员致残率和死亡率。
2 海上医疗后送五级救治体系的构建
世界发达国家海军均有一条清晰的海上医疗后送分级救治体系。美海军海上医疗后送由伤员后送、战术医疗后送和战略后送三个阶段,舰艇救护、大型作战舰船救治平台(如航空母舰、两栖攻击舰、大型辅助船等)、快速部署医院或医院船、舰队医院或海外驻军医院、本土医院等五个医疗阶梯组成。英国海军海上医疗后送设置四级阶梯,分别为小型舰艇和潜艇、航空母舰或大型两栖舰船、医院船、本土医院。美英等海军均未区分单舰艇官兵的自救互救和军医救护。
自救互救作为战伤救治的逻辑起点,是降低战斗伤死率的关键因素。“白金十分钟,黄金1小时”、“救治伤员惟一最关键的时间是最初的10分钟” ,研究表明,伤后60分钟内死亡的伤员约占总死亡人数的50%,尤其重要的是,在60分钟内,前10分钟起着决定性作用,如果伤员在伤后10分钟内得到初级救护,起码1/3的伤员能够延缓生命[14-15]。
基于以上因素,结合全军战伤救治规则和海军相关实践,从理论上把海上医疗后送救治体系分为以下五级。
2.1 第一级:单兵自救互救我军的“战伤救治规则”(2019,试行版,以下简称“规则”)规定广大官兵、卫生战士、卫生兵履行初级急救职能。该级的核心是全体作战官兵必须掌握止血、通气、包扎、固定、搬运及口对口人工呼吸与胸外心脏按压等6项自救互救技能。海军部队特别是海上作战,由于环境特殊、兵力构成多样,在6项共同技能的基础上,应该增加海上生存待救、落水人员捞救、低体温复温及海洋生物伤处置等4项自救互救技术。“规则”规定初级急救应该在10分钟内实施,在海上舰船遭击中后伤员发生数量大,缺乏军医急救等卫救条件,必须紧紧依靠官兵自救互救完成初级急救。
2.2 第二级:舰艇救护所急救“规则”规定舰艇救护所执行高级急救职能,主要技术范围为高级的检伤评估、出血控制、气道开通与呼吸维持、防护与洗消技术、药物应用、急救处置等。随着未来海战海域空间的扩大,舰艇救护所在海上很难在黄金1小时以内把批量伤员后送至下一级救治机构。立足远海转型,结合海上医疗后送及救治的特殊情况,必须扩大舰艇救护所急救职能的技术范围,以提高舰艇救护所独立救治能力。舰艇救护所急救应该纳入部分早期救治职能,特别是紧急外科处置、麻醉技术、紧急内科重症处置、生命体征及器官功能监护的部分技术范围,主要包括气管插管术、颈部血管伤止血、软组织清创术、胸腔闭式引流术、肢体挤压综合征防治、局部麻醉和椎管内麻醉、休克判定与评估、低压容量复苏、野战输血技术、心肺复苏术、各种生命体征及血流动力学监测等救命的内外科紧急处置技术。
2.3 第三级:编队救护所早期救治“规则”规定编队救护所执行早期救治中紧急救治职能,主要技术范围为检伤分类、基本检查、麻醉、防护与洗消、紧急外科处置、生命体征及器官功能监护、紧急内科重症处置等七项技术。如前所述,海军编队将以航母编队为主要形式,其他包括大型两栖编队等,执行战略战役作战任务,远离岸基,甚至缺乏大型远洋适用的医院船保障,更加难以在3小时内后送伤员至医院船或岸基医院,因此,海上医疗后送需进一步扩大编队救护所救治技术范围,纳入部分易致残、致死伤情的专科手术能力。
2.4 第四级:医院船早期和部分专科救治“规则”规定医院船执行早期救治的外科复苏职能,对重伤员实施以手术为主的救治措施,实现稳定伤情、安全后送。具备外科急救手术、损伤控制手术、重症监护与复苏等能力。未来远海作战具有后送距离远、难以快速后送至岸基救治机构等特点,因此866医院船在设计时,技术范围包括部分专科治疗的内容,在未来远海作战医院船成为主要保障模式的条件下,新一代医院船的收容救治能力须进一步扩大,救治技术范围将覆盖大部分的专科治疗能力。
2.5 第五级:岸基医院/岛礁医院/海外保障基地医院专科救治除了本土岸基医院外,南沙岛礁医院、吉布提海军保障基地医院也是海上医疗后送的确定性救治机构。主要执行专科治疗职能,并开展功能恢复治疗。技术范围包括全面检查与确定性诊断,系统性专科治疗和确定性手术,并发症防治,继续抗休克、抗感染,功能恢复性手术和整形手术,并对核、生、化武器损伤伤员进行确定性专科治疗。
3 对海军卫勤建设的启示
现代海上医疗后送救治体系的构建是一项综合性、战略性、长期性的工作,海军兵力构成复杂,武器装备迭代生成,海上医疗后送不会是一条简单救治后送链条,而是包括援潜救生、核事故医学救援、落水飞行员搜救、两栖作战保障等相关体系的综合医疗后送救治网络。
3.1 夯实基础 大力加强海军官兵自救互救能力建设自救互救是战现场一线救治能力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对挽救伤员生命、避免再次负伤、防止伤情加重、巩固和提高部队战斗力具有重要意义。从近年来对海军部队自救互救能力的考核评估来看,普遍存在认识不足、兵好官差、训练落实不够、对口指导欠缺和器材配备老化漏缺等问题。经试点建设,试点单位的自救互救能力考核合格率、优秀率均有显著提升。下一步,应该在6项共同技术基础上,组织开展海军4项自救互救技术的组训工作,尽快配套教材、器材、训练考核标准等条件建设,形成自救互救技术训练新局面,提高官兵战伤急救能力。
3.2 制定标准 把提高舰艇和编队医疗救治能力作为重中之重海军舰艇船机种类众多,其医疗设施条件及医疗舱室功能定位参差不齐,医务人员配置也各有不同。提高舰艇和编队医疗救治能力的根本途径在于制定舰艇船机医疗舱室设计系列标准,规范救治能力目标,规定卫生人员配备使用办法,修订舰艇伤员救治规范,编制编队伤员救治规范,使之与海军战略相一致,跟上海军转型发展的速度和力度。
3.3 新建新一代医院船 是满足远海卫勤保障的必要条件笔者前期已论证回答“为什么要新建医院船”、“建设什么样的医院船”的问题[16],在远海卫勤保障上,医院船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一方面基于战时运用,医院船受国际法保护,“在任何情况下不得加以攻击和拿捕,而应随时予以尊重和保护”;另一方面,和平时期运用不仅可以保障远海编队多样化军事任务,还可以开展广泛的人道主义医疗援助行动,作为和平代言的“中国名片”。866医院船入列11年以来9次走出国门,到访43个国家和地区,广受国际好评。
3.4 及早谋划 建设远洋基地和海上预置保障力量2017年8月1日,我海军第一个海外保障基地投入使用,标志着人民海军真正成为有远洋基地保障的远海海军,吉布提保障基地医院为我亚丁湾护航编队提供强有力的岸基依托医疗保障。但是随着国家利益的快速拓展,未来远洋护航、海上维和行动、人道主义救援行动等均需要远洋基地支持和海上预置力量支撑,需及早谋划,在南太、西非等地新建保障基地,在印太战略通道上建设海上预置力量,为海上医疗后送体系提供配套保障。
3.5 瞄准未来 把智慧卫勤作为建设一流海上医疗后送体系的重要抓手信息化、智能化程度的高低是未来战场决战决胜的核心问题,未来海上医疗后送体系离不开智慧卫勤建设。美军从2003年对伊拉克的战争始,全方位启用太空信息支援系统,通过战场伤员医疗救护通信设施 (Medical Communications for Combat Casualty Care, MC4),远程支援直达单兵,以实现美军提出的“零伤亡战争”。2012年3月,美军就发布“大数据研发倡议”,国防部同期发布“从数据到决策”的研究计划,近几年提出多尺度异常检测(ADAMS)计划、机读(Machine Reading)计划、心灵之眼(Mind’s Eye)计划、面向任务的弹性云(Mission-oriented Resilient Clouds)计划以及XDATA计划(美国国防部大数据研发核心项目)等。我海军卫勤信息化建设主要依赖于全军卫勤信息化,目前滞后很多,可用的系统、装备、技术不多,但智能化方面民用技术发展迅速,智慧卫勤建设可以发挥融合优势,迎头赶上、弯道超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