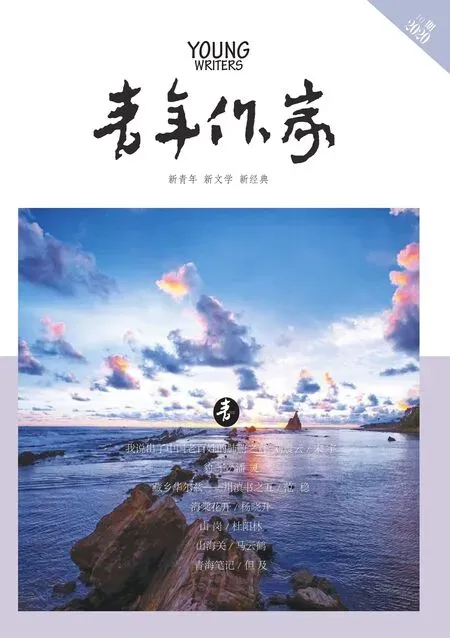【评论者说】细节的诗学与虚构的嬉戏
贾 想
马云鹤和岑攀的小说,分别在细节和虚构技巧这两个层面,给了我久违的新鲜感。说新鲜,是因为对比当下普遍早熟的青年作品,这两人的文字有稚气未脱的实验意味。说久违,是因为我所说的新鲜并非前无古人。每一代初出茅庐的文学青年身上,都有这样一股子新鲜的气息。这股气息来自于小说背后纯粹的艺术冲动,而不是功利冲动。
阅读马云鹤的《山海关》过程,我视为一次穿过雾中风景的过程。我跟随作者蒙太奇一般的叙事镜头,在浓雾中一点点逼近事物的脸,一个个辨认,然后又一次次离开,重新陷入语言的大雾。当我彻底离开雾中世界的那刻,得到了什么?应该是一幅现代工业社会中人的中年“冷风景”——印象派的“冷风景”。正如张岱对湖心亭的印象,我的印象,也惟一痕、一点、雾中人两三粒而已。
一痕、一点、两三粒,即小说的细节。在《山海关》中,不存在连续性的、戏剧性的情节;突出的,是数不胜数的精确细节。细节越具体,整体结构就越漫漶。细节晕开了,情节就混淆了。如果说,情节是人与事物的运动所形成的,那么,细节就是人与事物静止时呈现的状态,是作者通过发达而细腻的内外感官——色受想行识,捕捉到的美。时间在细节这儿停止了,作者沉迷在对于一种气味、一道铁锈、一丝声响的“全息形容”当中,正如蜜蜂沉迷于蜜。
这蜜,一方面是语言的蜜,也就是修辞的美;一方面是私人情绪分泌的蜜,也就是作者的美。沉迷细节,也许是一种语言意义上的自恋。这让我回忆起阅读郭敬明和早期张悦然的体验——一种“甜”的体验。当然,更确切地说,马云鹤的语言是一种“冻住的甜”,兼顾精确的形状和克制的抒情。
如果存在一种艺术的“味觉学”,那么,抒情诗可以说是“甜”而“酸”的(波德莱尔之后可以说是“酸”而“涩”的);小说则无味不包,是“五味杂陈”的。从时间的角度看,诗着眼于“时间的凝固物”——意象,因此是静态的、抒情的,是“点的美学”;小说起源于史,也就是时间的流动,因此是动态的、叙事的,是“线的美学”。
我由此辨认——既是对内容的辨认,也是对美学风格的辨认——《山海关》表面是小说,灵魂却是抒情诗。小说涉及的细节:生活、质数魔咒里的蝉、阴冷仓库的铁臂阿童木、氧化层,其实是属于一个隐喻轴上的联想物。所以,事物没有动起来形成完整的故事,只是“加深”了自己。故事中那些弥散的细节,是围绕凡士林、赛车轰鸣声、铅块、蝉、宝塔这一系列意象运转的。小说因此形成了一种“星系”结构,其中囊括诸多围绕意象运转的“修辞的恒星系”。我曾经总结过青春写作的一个突出特质:“拜意象教”。这篇小说也不例外。
细节(意象)为什么会令作者沉迷,也令读者流连呢?我试着提供一种阐释:所有情节都是奔跑的,但奔跑的尽头,无外乎人生的死和时间的无,情节的命运是悲剧性的。这时候,能静止时空的细节就是喜剧性的,就是一种拯救的力量。细节拼尽全力,拖住了情节朝深渊飞奔,拖住了一个去意已决的故事,造成了一瞬间春龄永驻、年岁冻结的“永生假象”。这就是细节的诗学。细节的诗学,就是时间的诗学。
深谙细节诗学的小说家,当数张爱玲。在张爱玲艺术之手的摩挲中,日常生活中的俗物(《色戒》中的大钻石),可以突转成为圣物。摩挲的手势,突然成为一种祭礼。“艺术的摩挲”,让一切经手之物散发出内在的光晕。然而,和张爱玲的摩挲相比,马云鹤的摩挲,还没有让事物(比如那罐凡士林)散发出一种公共的、情感的、意义的光晕,而只是散发出一种私人的、情绪的、美的光晕。这种光晕是不可对话、难以扩散的,因此只能是一种质数型的孤独光晕。
小说中,对细节诗学的敏锐,与对于数字的好奇结合在一起。《山海关》中提到一部有着12 个结尾的小说,还提到一座宝塔正在以每年1.2 厘米的准确速度下沉。我想,对于作者而言,12、1.2 这样的数字,一定是没有深度原由的,这些数字存在的意义就是本身的精确。而精确,会给小说带来一种后现代风格。后现代文学对于数字的崇拜,是与对于意义的否定冲动一并产生的。
如此说的话,《山海关》是抒情诗的,也是后现代的。里面有如此清澈的甜腻,如此丰沛的哑谜,如此绚烂的能指和如此精确的无意义。就像鱼脱离了水,这是一篇脱离了传统小说边界的小说。因此,我将我的阅读视为一个逐渐辨认的过程。随着小说的结束,我想,我对小说的认识,也终于“着陆在了春天的堤坝上”。
如果说《山海关》是美驱动的故事,那《外卖中的人》就是智力驱动的作品。岑攀一定十分在乎文学的“趣味”,而不仅仅是文学的“意味”。“意味”是作者的思想和情感支撑的,“趣味”是作者的智力和技巧支撑的。二十世纪之后的文学,由于构成“意味”的西方观念世界遭遇了严重危机,有“意味”的文学渐渐被有“趣味”的文学代替。原本古典作家使用起来十分谨慎的智力得到了某种程度的解放,甚至是放纵。最热爱智力的作家之中,一定有米兰·昆德拉。岑攀的这个故事,就很有一丝昆德拉的狡黠。
同托尔斯泰一样,昆德拉的故事也大多是“上帝视角”,全知全能,操控一切。但这不是一个严肃客观的上帝,而是一个主观的、调皮的、讥讽的上帝。如果说托尔斯泰的上帝是一个成人,那昆德拉的上帝就是一个恶作剧的孩子。他并不低调,也不庄重,对奔走在云层之下的人间男女,他没有怜悯或者疼爱,而是冷眼旁观,处处捉弄。而上帝形象,其实就是显露在小说中的小说家形象。
《外卖中的人》当中最有趣的一个细节,就是作者对“()”的使用,这也是让我联想到昆德拉的原因。在我们现在熟悉的小说叙事学中,“()”的使用几乎是一个大忌。为什么呢?“()”的功能,就是提示和补充,谁提示和补充呢?当然是作者。所以“()”堂而皇之地出现,就是作者堂而皇之地出现。这无疑会破坏小说的“浸没体验”,让读者“出戏”。但昆德拉是明知故犯的,他就是要破除某种小说的美学。
“()”的使用,还让我想到戏剧的技法。尤其是“第四堵墙”倒塌之后的戏剧。创作者、剧中人和读者,被并置在一个时空之中。布莱希特将这种破坏浸没体验的戏剧技法,称之为“间离”。“间离”术,让读者跳脱出来,成为一个“旁观者”,而不再是“角色共情者”。读者于是感知到了“虚构”的存在,意识到小说是一种编造。
通过“()”等叙述方法的使用,岑攀将《外卖中的人》变成了一个关于虚构的沙盘游戏。他以一个富二代外卖员的游戏身份,带领着读者,思考如何从一个外卖员的碎片经验中,如何在与顾客的片刻接触中,构思出一些有戏剧性的故事。他将整个故事称之为一场戏剧性收集之旅。他在虚构作品中展现虚构的发生学,在小说中解剖小说,在无聊中消解无聊。
有趣的情节发生在小说后半段,一直虚构故事的外卖员,当真跌入了一个戏剧性的故事。他迷上了酒店里的一个陌生女人。情欲催动他做出了一系列古怪又冒险的行动。这一次,外卖员没有从这些行动中跳脱出来,他的智力停止了运作,荷尔蒙占领了高地,文本之外那个顽皮上帝的议论也消失了。最终,这场追踪随着女人的人间蒸发而告终。这个非正经外卖员的喜剧性故事,在与另外一个真实外卖员的悲惨故事匆匆形成互文之后,小说就结束了。
对于小说的结构,可以做两种解释:一,一个拒绝入戏的人,意外入戏了。讽刺剧变调为悲剧,一个布莱希特式的故事,突转为一个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故事。故事的前半段,作者用玩弄虚构的现代写法,讽刺了沉浸虚构的古典写法。后半段,他又似乎以庄重的古典写法,否定了轻佻的现代写法。通过讲述一个真实而普通的外卖员的悲剧命运,将故事的落点重新安置在人文主义的范畴内。如此理解的话,小说就是一个意义撕裂和结构互斥的文本。作者为了实现“通吃”的野心,牺牲了某种从一而终的艺术统一性。
二,小说自始至终都是一个布莱希特式的故事。从主人公被酒店房间中的陌生女人迷住心窍至故事最后一个字,其实是这个富二代外卖员一个更为漫长的虚构而已,只不过这次的虚构自始至终紧绷着弦,没有“破功”,没有“出戏”。如果相信这种解释,那么这就是一个内部结构统一的故事。作者的把玩让我们回忆起一些遥远的日子,那时候,虚构在嬉戏,游戏在继续,小说家还很调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