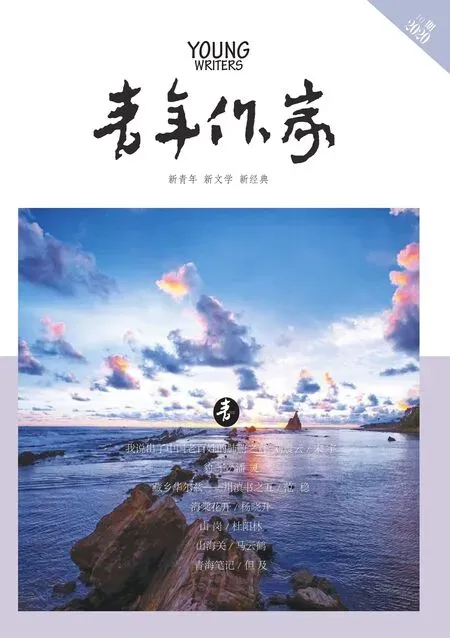夏日的等待
张语婷
阴 天
她养的花花草草在这间逼仄的房子里都活不长久。一个白色四层架子的最上面,一盆绿萝低垂着黄黑相间的叶子,轻飘飘地搁置在那儿,大概已经快一个月了。她已记不清这是第几个濒临死亡或已经死去的植物。客厅里常青藤的五角树叶也从柔软的嫩绿色变成一个坚硬的黑色标本,发出沙沙的脆响。几盆多肉植物从干瘪的泥里开始暴露出根茎来。对此,除了更多时候漠然地看着和偶尔胡乱地浇一盆子水,她没有想过认真去营救它们。直到最后一片叶子腐朽并从枝桠上掉落下来,她才把这些光秃秃的盆从房间里移出去。
她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接二连三地养植物。她也不知道这些植物到底是因干枯而死还是被水淹死的。在她办公室的左边和右边正好是两名副主任的房间。一间墙上以鸾翔凤翥的笔法写着:万物生长靠太阳,另一间则美女簪花式地写着:雨露滋养禾苗壮。她刚搬进房子和买来花草时会在百度上提问:怎么养常青藤、怎么养海棠、白掌怎样浇水、红掌怎么浇水、多肉植物怎么养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大致的答案都是离不开阳光与水。这时,她就想起那两间办公室墙上的书法作品,多么意味深长。
有关阳光雨露的问题,这也不能完全责怪她。这是一间建筑面积只有47 平方米的房子,《房屋所有权证》上的实际面积只有32平方米。两年前,她和丈夫在房价疯涨时慌忙买下了这间有些发旧的二手房。唯一的优点是在市中心,生活便利,离她上班的地方近。一室一厅,面朝北方,没有阳台。娇滴滴的植物来到这里后迅速黯然,失去了生机。她想起来的时候,给它们灌溉一大片人工雨露。有时索性半个月或更久也不会理睬。都说绿萝啊、多肉啊、仙人掌是最好养的植物了,可她一点儿都没有感受到它们生命力的顽强。
除了照顾花草,她对一个人的生活也没有太得心应手。丈夫一年里大多数时间都在外出差,一个月回来一次,每次呆在她身边的时间不超过三天。结婚两年半了。她常会觉得自己和深居简出的单身者并无区别。工作朝九晚五按部就班,一个人一日三餐。她常年背着一只深灰色皮质软塌的包,在单位和家两点一线之间来回。这只包灰头土脸,并不好看,她只觉得它简便实用,更是懒得去随衣服色彩样式的变化,去更换不同的包和心情。
她的心情大多是一样的。即使是周末不上班的日子,一个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在她那儿都是阴天。她甚至讨厌遇见周末的太阳。窗外的好天气和朋友圈里的热闹出行,都加剧了她一个人在这座城市的孤独与颓废。窗帘拉上,明晃晃的白天被伪装成夜晚的样子,她在床上又躺了一天。一种不用动脑筋的游戏已经闯过了4000 关。饿了就点美团外卖,她打开上一个订单,直接点再来一单。她懒得再去想吃什么。
“当一个女人不再关心自己的体重,或许她已经堕落了。”刷微博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她感到了一阵悲哀。这几年,她的确胖了不少。研究生毕业,她顺利考进了一家省级直属事业单位,不久后她与在一起多年的男友结婚了。一切都好似渐渐落入了安稳与平静。在这样的日复一日里,她忘却了纤细曼妙的身体,还有其他很多事。
她觉得自己又重新鲜活起来,是从每一次丈夫回来前的那个下午开始的。这时,她把房间的窗帘拉开,明亮的光线使得小屋四处的灰尘腾空而起。她拿出吸尘器把遍地的灰尘和头发吸进一个椭圆形的容器里。很快,容器被填满了。她终于想起走进厨房,把一周前或更久前泡面的碗和冲泡牛奶的几个杯子洗干净。沙发上横七竖八倒下的娃娃,又重新整齐地站立成一排迎接男主人的回家。
她在等待丈夫的归来,好比房间里这些不说话的植物在等待一场及时雨。
多 云
打扫完房间,她走到楼下的家乐福去买这几天在家做饭的各种食材。明天就是周末了,她的心情变得明快起来。此刻,她像一个无忧无虑的主妇,愉悦而认真地挑选着猪里脊、牛毛肚、鸡胸肉、土豆、花菜、黄瓜、胡萝卜、西红柿等等。她提着满满的一口袋,把早已空荡荡的冰箱再次塞满。
他喜欢吃火锅。在他每次回来的周五晚上,他们一边吃着麻辣而滚烫的牛油火锅,一边看他喜欢的怀旧电影。《无间道》一二三部她都记不得陪着他看了第几遍了。未来两天计划的菜单还是砂锅米线、咖喱饭,还有他最爱吃的椒盐土豆。她不是一个会做饭的人,但这几道菜由于常做的缘故,已成了她的拿手菜。她喜欢自己穿着围裙在厨房忙碌的样子。她从前几周的昏然中复苏,感到这一切充满生活的气息。这时,他也会走进厨房,从背后抱住她,贴着她的脸夸她可爱又能干,然后帮着她洗净还混着泥的小葱、香菜以及压碎蒜泥。
这天,一直到晚上八点,他才拖着重重的行李箱回到家。他在川西南小凉山山脉中部的一个地方负责水电移民安置工作。她有一次出差路过那儿,山高水阔,路面崎岖,还没有通高铁和高速路。一般他吃过午饭后出发,先坐汽车到峨眉,然后再从峨眉坐高铁回到成都。正常时候,他会在下午五六点钟到家。
今天在路上堵车了三个多小时,他满脸疲倦地说道。
今天吃火锅。带着一丝安慰并期待的心情,她说。
在等待的几个小时里,她把将要放进锅里烫煮的食物一一切片并精心摆好。他看着一桌子还没下锅的生菜说,你饿了快吃。昨晚陪业主吃饭酒喝多了,今天在车里又闷了很久,还很难受。
她记不得一个人吃火锅是网上流传孤独排行中的哪一个等级了。此刻她一个人吃着,觉得这回买的毛肚一点儿也不好吃,又辣又硬,难以下咽。
他打开电视机,遥控器上下左右翻看了一圈却不知道看什么。他不喜欢现在的综艺节目,九十年代的港片已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他随意点开了一部刚上映不久的新电影。没过一会儿,一阵轻微的呼噜声传来。
短暂而难得的相聚,却没有换来他们小别胜新婚的身与心的交流。这次回来,他的手机成了热线电话,响个不停。他说最近当地政府和业主都在加大推进这个项目,周末还得加班写报告,太累了。他对她说,我们今天不做饭了,出去吃。
为什么上个周末还是阳光灿烂,这个周末就蒙上多云天气里一层灰。她看着头顶的天空失落地想。他们走在一条早已烂熟于心的路上,街道两旁的行道树在初夏时节又绿了。他们走到繁华的春熙路,在科甲巷的良木缘咖啡又点了一份双人套餐。周末人流如织,四周都是聚会的人们。他们俩像两只落单的蚂蚁,迁移来到这座并不属于他们的城市,好似和其他人并无交集。
他们在研一结束的那个夏天相遇。已经第六个年头了。浪漫的双人套餐变成了孤单的双人派对。他们俩面对面坐着,凝视的只是各自手心里的一部手机。他们安静地坐在那里,像是来听别人的故事和热闹。他们过去总有说不完的话,可此刻却变得有些无话找话。她发现生活越来越像自己不喜欢喝的美式咖啡:没有鲜奶油,没有牛奶,也没有摩卡的巧克力酱,单调而发苦。
这时,远在杭州的表姐在微信上发来一段视频,嘟嘟已经会背唐诗了。表姐只比她大三个月,她的孩子已经快满三岁了。
“《乐游原》怎么背的呀?”
“不会背。”
“你会背的呀,向晚意不适……”
“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嘟嘟用稚嫩的声音、加快的语速,一股脑儿地背出来了。
她反复看了这个视频好几遍。她喜欢孩子。那些稚嫩的声音、无瑕的脸庞、天使一样的笑容,让她在这几十秒的时光里,感到了生活的甜度。
她想,也许有一个孩子,会改变眼前的一切。
大 雨
还是二十多岁的时候,对于生孩子的事情,她从未放在心上。时间在女人的路径里走起来像是凌波微步,一晃眼,她今年三十岁了。她有些无法接受,还包括右边脸颊猝不及防爬起来的一道法令纹。忽然之间,她就变得惶恐和焦虑起来。
丈夫又去项目上了,她一个人躺在床上难以入睡。她拿出手机,找来了很多和怀孕生孩子有关的内容看了又看。第二天她起了一个大早,去附近的一家医院做了一个全面检查。她拿到报告,显示各项指标都很正常。她放下心来——现在可以安心安排这件人生大事了。
她对生活又有了一份新的期待。她认真地勾起手指想着一个还未在子宫里安家的宝宝,在未来的哪一月降临呢。她在网上看到有一种排卵试纸,能准确地检测出排卵的具体日期,增加受孕的几率。她是第一次知道这个女人的奥秘:原来每个月只有一天是排卵日,由一侧的卵巢只能产生一个卵子。一个女人一生大约排出四百个卵子……
她从月经走后的第五天开始检测。4 月26 日下午两点,她记得这个神圣的时刻。她看见那张小小的试纸上出现了深浅度一致、两道粉红色的线。她感到了身体的万分奇妙,而这两条线和电视剧里那些第一时间发现怀孕的情节线重叠起来。她迫不及待地给他打电话,仿佛是在提前庆祝他们即将迎来的小生命。
2019 年4 月26 日,星期五,风和日丽,时间合适。她想让他这个周末回一趟家。甚至是此刻,立刻出现在她的眼前,与她拥抱、缠绵。
他对她说,院领导来检查工作了,这个周末实在走不开。
她眼睁睁地看着两道一致的深红色变成一深一浅,第二天晚上她再次测时,只剩一条没有故事的粉红色。她的心再次落入了灰暗。
听说怀孕前还要去看牙医。她的牙齿一小瓣一小瓣,疼痛了无数次,也已修补了无数次。大名鼎鼎的华西口腔肯定短时间内挂不上号。她听同事说,有一家的私立诊所还不错。
五月的一天,她在回家的路上突然掉转头,还是决定去看看牙齿,虽然这几年那种撕扯神经的疼痛没有发生。
牙医诊所在骡马市附近。据说骡马市一带原是成都官府衙门最集中的地区之一,还有古色古香的书店、中西合璧的建筑、极富特色的美食,是老成都的繁华之地。这家私立诊所有一点遗风余韵和更新式的富丽堂皇。
她走进里面,和人声喧闹、混合着类似福尔马林味道的医院完全不同。护士们都穿着橘色的衣服,说话的声音轻柔地像在云朵里。
在了解她的需求后,护士说,介意我们给您安排了一位外籍医生吗?
她立刻想到的是一名男性,比她要白很多的皮肤,金发碧眼的模样。
护士带她穿过静谧的拱形走廊,来到一个小房间里,见到的却是一名女性,比她还要黑很多的皮肤,黑色的头发和眼睛。护士介绍道,这是来自印度的婉丽医生。
护士又带着她去拍了一个全口的牙片。她的牙齿情况确实很糟糕。它们在看不见的深处溃败。婉丽能说一些简单的中文。她拿笔指着牙片说,这颗不好,这颗不好,这颗也不好。
最后的结论是两颗浅表面的龋洞可以直接补上,而上门牙右边的第三颗要根管治疗。
那时她还不知道所谓的根管治疗,就是要把牙髓神经剿灭,让它们失去疼痛的知觉。她后来想起来万分后悔,真是没必要去遭受这一场罪。这一颗此前并未疼痛的牙,说不定早已自己走失了神经。
躺在房间的椅子上,她看见印度医生拿出像针脚一样的仪器,向她的牙齿深处猛烈地攻击。
不到一周,那颗经过“治疗”的牙开始剧烈疼痛。
她再次去诊所,又拍了一次牙片。她看见护士和婉丽的脸上都写着欲语而未语的阴沉。
婉丽说,等我一会儿。然后她拿着牙片出去了。
婉丽只是去了隔壁。她清楚地听见隔壁的对话。一位女医生用中文对婉丽说道,我们中国有句古话:“两害相较取其轻。”
但是她还不知道什么是害,什么又是轻。她还躺在椅子上,把张大的嘴慢慢闭合。她的心在未知的恐惧里,比她的牙还要疼痛。等婉丽和护士都回来时,她们两人再次以遗憾的神情看着她,而她则以委屈又还怀有一点期待的表情看着她们。
护士终于开口,她指着牙片说,你看,这颗牙齿的牙根是弯曲的,导致断针在里面了。
她欲哭无泪。她问,这算医疗事故吗?护士摇摇头表示否定。
可明明事先是拍了牙片的呀。如果牙根弯曲有风险,就不应该考虑这样的治疗。她对着印度来的医生婉丽说。
她不知道她听懂了没有。印度医生无奈地看着她,用不流畅的中文说,你没有保护好自己的牙齿。
最后是最不好的结果,那颗牙被拔除了,考虑到离门牙的位置较近,为了不影响美观。另一位牙医说可以即刻种植。种植牙的周期将长达半年,期间还要照两次头部CT。她记得收藏的备孕知识里,其中一条是说在经过X 线照射以后至少3 个月才能怀孕。这样前后加起来,又是很长的一段时间。她计划这一年生孩子的事又泡汤了。
她只身躺在手术台上。一盏炽热而刺眼的光源照在她的脸上。她的眼被一块布遮挡住了。只有她自己知道此刻她的眼眶里充盈着泪水,她的心大雨如注。她明白,拔掉的不只是一颗牙,也是自己对未来日子的期待与希望。
暴 雨
六月,端午节的小假期,他们计划出去散散心。
去泰国清迈,这是她突然决定的。朋友圈正好有人发了一条“粽情清迈,北城玫瑰”的广告。在此之前,她对清迈一无所知。她看到图片的介绍后,才知道这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城市,有许多古老的寺庙。
她把图片发给丈夫,他看后表示不想去,他想去岛屿,看阳光和海滩。
可当他拿出手机查询了几个海岛的天气之后,他同意了。天气预报说,那几天普吉岛、沙美岛、苏梅岛、皮皮群岛、甲米岛,还包括其他的岛屿都将有暴雨来袭。
泰国北部山区的清迈将是阳光普照。
她开始期待和规划这次旅程。她在马蜂窝和小红书上察看各种攻略。她发现上面的内容零零散散又眼花缭乱,她决定出门去书店找找看。一石激起千层浪。傍晚时分,她在家里试了一件又一件衣服后,最后换上了一条颜色明丽、几乎不常穿的长裙。她重新把灰蒙蒙的脸洗干净,涂上了比她的脸要惨白很多的粉底液,再往眼眶处抹上珊瑚红的眼影。三年前买的睫毛膏还没有完全干掉。她用还是会颤抖的手画上几条苍蝇腿。
终于,她换上一个淡蓝色的小包,走在夏天的风里,迎面有一种久违的美好。
出发前的几个晚上,她有些激动地睡不着觉。睁着眼闭着眼,忙碌的脑电波都在勾画行程。她在本子上一笔一画地记下他们将要去游玩的景点,并想象每一处出现时让他们雀跃的样子。她想,那三天要穿哪件衣服呢,是穿裙子还是短裤呢,是白色配蓝色好看还是白色和黑色的经典搭配呢。这一幕的场景,很像他们约定第一次见面的前一晚。
他们从不同的地方赶到双流机场。昨天在电话里,两人为买电话卡的事有些争吵。
在机场自助值机时,当她选择家庭值机后,却发现无法添加他的信息。工作人员建议说,你们分开值机试一试。原来他一个人在头等舱。她不明白付的是同样的钱,怎么两个人的位置相隔这么远、这么大。
她看出了他的脸上还垂挂着昨晚的一丝不愉快。她赌气又娇嗔地说,我要坐你的头等舱。
他淡淡地回答了一声,嗯。
飞机上的头等舱服务,是从落座的那一刻开始的。美丽的空中小姐,步履轻盈地走到身边,用无比甜美温柔的声音问道,您好。请问您需要喝点什么呢。我们为您准备了绿茶、红茶、气泡水、苏打水、果汁、牛奶、咖啡。
她要了一杯湖蓝色的气泡水。
这是她第一次坐头等舱。她也第一次发现飞机上的晚餐这么好吃。空姐又春风般地走到跟前,把原本质朴的桌面铺上了白色的餐巾布,把发出明晃晃光亮的刀、钗放在上面。不一会儿,端上来的是一份像日料一样小巧而精致的晚餐。
美丽的空中小姐轻轻地放下身后蓝色的布幔。
她忽而想起一部叫《雪国列车》的电影。一列开往新世界的列车,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那刚被放下的布幔也意味着是一扇不能被看见和不能被逾越的等级之门。
她想,这是一个秘密,如同雪国列车的秘密一样。她决定不告诉他。
飞机落地,她站立起来,等后面的人拖着行李逐一走出舱门,她留在原本属于他的位置上等他。她决心以释怀的微笑来消解此前的不愉快和迎接即将开始的美丽旅程。
等他慢慢走近时,他回应式地对她抿嘴一笑,但有些生硬。她想说一些悦耳的话,一时也堵塞了。她的脸也很快僵硬了,和他僵硬的笑如出一辙。
两人各自拿着自己的行李箱,一声不吭,一前一后,往一个陌生的地方走去。
到出海关的地方,把他们吓了一跳。密密实实的人海,都是在排队落地签,已看不见哪里是头、哪里是尾。他们被环抱在四面八方而来的人群中间,闷热炙烤,流汗焦躁。
出门前,她说要带箱子,而他说背书包。此时,她觉得后背像燃起来一团火,又像被一盆水浇湿透了。她开始责怪他。他不说话。她继续说。他开始用一把刀子似的锋利眼神看着她。她忘了说出那一句加重的话。刀子向她劈过来时,她的泪珠就从眼眶里滚下来了。
清迈时间比北京时间晚整整一个小时。他们下午三点赶去机场,经历了飞机延误和无比漫长的排队后,当她再看手机时已是凌晨两点。回到酒店,来不及哭泣和悲伤,她就沉沉地睡着了。
第二天,按照攻略,他们要去的第一个景点是清迈古城。他们搭了一辆红色的“双条车”,复古得像坐在一辆敞篷的小型货车上。她确定自己对司机准确表达了目的地“清迈古城”。可当司机把他们放在一片彩色的居民房子附近,她始终觉得不对,不是这里。
她记得看别人分享的照片,是一片红砖的城墙,还有一大群鸽子。对,叫塔佩门。
他打开百度地图。他们暴露在烈日下走了一大圈。他的脸上悬浮着大颗的汗珠,他的衣服已湿透了一大片。当他们走到塔佩门前,才发现原来他们刚刚一直都在古城的里面。
他们现在站在城的外边。他湿哒哒地看着她,显然他不想再走进去,去看那些错过的古老寺庙。头顶的白日焰火正向他们垂直移动。
原计划一个上午的古城漫步意外地早早结束。
瓦洛洛市场在古城外的东北角。攻略里说,这是一个原汁原味的当地集市,体验当地人的生活必去。他们穿过混合着鸡鸭鱼腥味的一条街,一路所见,都是破旧的房子、脏乱的道路。这个庞大而原始的批发市场又与他们的想象相去甚远。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她偶然看见了攻略里面提到的网红恐龙油条,而她看上去不过是一只扭曲的壁虎。
他说得没错,这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小城镇。她在心里略微苦笑了一下,然后安慰他说,破旧也有意义。他完全不能理解文科女生的思维,对于他而言,破旧就是破旧,毫无意义可言。
其实她何尝也没有这样想呢。只是也安慰自己罢了。远处的是风景,别人那儿是风景,当自己贴近一看,才发现大多数不过尔尔。
两人在马路边发呆了好一会儿,还是决定回酒店。一个下午便睡过去了。
她发现,世界依旧孤单,还是只有他们两人。只是换了一个地方,吃饭、睡觉和闲逛。
明显她执意要来的地方让他大失所望。晚上,两人终于爆发了。把白天或者昨日,或者前几日,再或者之前的日子里所有的委屈和不满,暴风雨般地气势如虹地争吵开去。
吵了好一阵,两人背对而卧。
她渐渐平静下来。她以为他会像往常一样,争吵完后过不了多久,转过身来抱住她。
可他睡着了,连绵起伏的呼声在一个没有车水马龙之声的夜晚特别清晰。
她独自走到阳台外,发现夜晚比白天要冗长。她听了一首歌,是一个叫“刺猬”的乐队的《火车》:
黑色的不是夜晚,是漫长的孤单
看脚下一片黑暗,望头顶星光璀璨
万物皆可盼,唯真爱最短暂
逝去的永不复返,世守恒而今倍还
摇旗呐喊的热情,携光阴渐远去
她突然也想起了二十岁那年看的那本有关摇滚和青春的书,春树的《北京娃娃》。整整十年过去了,万丈激情的日子也一去不复返。那时的她充满了生气和力量,她不甘心在一个地方被动生活。现在,她被自己固定在了一个地方,原地等待。
六月的风凉凉地吹拂,她看见黑色的夜晚被远处五彩斑斓的灯照耀着,好像一道彩虹。
也许暴雨过后会有彩虹的。她不愿再这样想。
她发现自己很好笑,很像《等待戈多》里面的那个人。此时,她心底浮现了若干年前写下的一个句子:
我在希望,我的希望都会落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