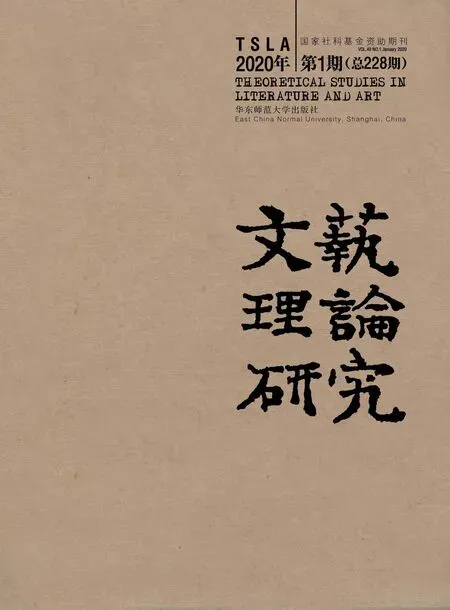从《夷坚志》自序系列看志怪小说家洪迈的生命体验
詹 丹
一、 问题的提出
洪迈的《夷坚志》因其420卷的浩繁篇幅而成为中国古代小说创作中的奇观。而且,他每完成一集就写成自序(总计31篇),每篇自序又基本做到“各出新意,不相复重”(赵与时语),这是古代小说家无人可比的。虽然其自序只有13篇保留了下来,但所幸赵与时在《宾退录》中把每一篇的大意都作了摘要性介绍,而留存至今的《夷坚志》作品也有近二分之一卷帙可与自序互为对照,同时,他的另一名作《容斋随笔》也涉及一些相关内容。这是我们在今天讨论其自序的价值时可资利用的。
不过早些时候,学者在论及这些自序时,对其总体价值,评价并不很高。如黄霖和韩同文在编选《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时虽然选录了《夷坚乙志序》,但认为:“现据所存的各序原文及《宾退录》摘录各序的大意看,多述其成书过程,于小说理论批评方面新意不多”(黄霖 韩同文63),在确立其“新意不多”的大前提下,才承认该自序对“‘怪怪奇奇’小说特点的论述尚有可观之处。其一,强调了志怪之书‘寓言于其间’,有所寄托,而不是简单地记录怪事异闻;其二,对于志怪小说的‘实’与‘虚’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即认为这些故事的来源尽管是‘耳目相接’,似‘皆表表有据依’,但实质上是虚的,只能问之于乌有先生”(黄霖 韩同文63)。这是从艺术真实角度,对洪迈的论述作了总结。而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文学批评史研究者持论几乎无出其右,都认为洪迈就是在谈艺术真实问题(顾易生 蒋凡 刘明今716)。晚近的研究者,虽然强调这些自序在小说理论史上具有重要价值,如程毅中《宋元小说研究》认为这些序文“在宋代小说史有非常重要的价值,甚至不在他的创作之下”(程毅中133),但因为该论著主要是研究作品,所以对序文的讨论没有充分展开。也有学者撰写专论,对前人已经揭示的寄托性(“寓言其间”)和虚构性(“乌有先生”)这二点加以拓展,又增补上“好奇尚异的习性”和“随闻即录的材料来源”二点,从而形成总体评价的四个方面,①但因为这一总体评价,是在固有的理论框架上作的增补,所以其梳理出的诸要点,仅仅是一种量的增加,没有构成对其价值评估的质的突破,这不能不说是令人遗憾的。
围绕着评价洪迈的小说理论贡献,有些现象也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关于洪迈论述唐传奇的观点与他在《夷坚志》自序中谈自己的小说编撰,学术界的评价似乎呈现出一定的反差。他关于唐传奇的评价流传至今的,主要是这样两段:
唐人小说,小小情事,凄惋欲绝,洵有神遇而不自知者,与诗律可称一代之奇。
[……]大率唐人多工诗,虽小说戏剧,鬼物假托,莫不宛转有思致,不必颛门名家而后可称也。(黄霖 韩同文64)
我们发现,对《夷坚志》自序作出“尚有可观”这样较勉强评价的黄霖和韩同文,对洪迈关于唐传奇的论述,却有相当高的赞誉。他们认为“洪迈是一个真正有小说眼光的人。他把小说理论批评提到了一个新的境界”(黄霖 韩同文64),“这突出反映在他对唐传奇小说的中肯的评价上”(64)。而顾易生等编撰的《宋金元文学批评史》中的相关论述,虽然没有呈现如此明显反差,但也是在引述其关于唐传奇小说评价后,作出了“洪迈是宋代一个真正具有小说眼光的批评家”(顾易生 蒋凡 刘明今715)的判断。但恰恰是随后下的一个总结性断语,又弱化了其小说理论的整体意义。他们认为:“不过,比较而言,宋代小说理论观念的迅速发展,对于小说艺术的分类、本质及其特征的揭示,主要还是来自对于当时的新兴白话小说的研究和总结。”(716)由上述的评价反差归结起来看: 第一,与对唐传奇评价相比较,洪迈关于《夷坚志》自序的理论价值是不高的。第二,与当时有关白话小说的理论迅速发展比,属于文言小说理论整体一部分的洪迈观点并没有得到充分发展。这恐怕就是古代小说研究界对洪迈小说理论给出的主流意见。但是,洪迈作为一个志怪小说的收集整理者,同时也可能是部分作品的原创者,其活动几乎贯穿了他人生的大半辈子,积累了相当丰富的实践经验,何以他谈自己的志怪编撰创作经验,反不能像他谈唐传奇那样得到别人相应的重视?这究竟是理论和创作的脱节,还是因为他谈自己的创作反不能如同谈别人的创作那样冷静客观?或者我们自身的评价标准还有待斟酌?这正是下文所要讨论的。
二、 一种记录书写过程的生命实践
前文引述《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提及,该“论著选”对洪迈《夷坚志》自序的一个总体评价是,“多述其成书过程,于小说理论批评方面新意不多”。这一评价,在很大程度上道出了洪迈自序没有获得充分肯定的原因所在。这话可以有两种理解,一种理解认为自序主要是记叙《夷坚志》成书的过程,涉及小说理论批评上的观点,没有什么新意。但还有一种理解是,作为主要是记述成书过程的《夷坚志》自序内容与小说理论批评本来就没有多大关系,所以就谈不上有什么理论新意。这两种理解虽然有差别,但以一个预设的理论框架为评价前提,倒是十分相似的,即都把有关成书过程的记述,与小说理论批评割裂开了。而这才是洪迈自序无法得到充分肯定的关键所在。
其实,把对小说理论批评的研究限制在抽象的理论层面,这一直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是保持研究对象的确定性和合法性所必需的。很少有人会有意突破这一研究对象的框架,将研究触角伸向小说家实践活动的记录。尽管我们十分需要从一个作家或者评论者谈及的小说创作活动中,揭示出一种理论自觉,揭示出其对小说本质的理解、对创作活动的认识等,但也必须意识到,理论的自觉在整个创作活动中,只占一部分,即便是就抽象的理论谈理论,构成理论思考原动力的,常常是非抽象理论的一些因素。所以,只有把有关小说家整个写作实践活动的记录纳入思考的范畴,才能对小说理论批评问题有深入理解。从这一意义上说,洪迈自序有关“成书过程”的记述,倒恰是其小说理论批评能给人以新意的一种特色。
因为“甲志”自序未能流传下来,而赵与时的摘录也唯独对这篇内容语焉不详,仅说是“甲志序所以为作者之意”(丁锡根104),使得较多学者把注意力放在“乙志”自序上,大有把它当作自序的首篇来研究之势。就这篇自序来看,也确有丰富内容可以分析。先转录其序于下:
《夷坚初志》成,士大夫或传之,今镂板于闽、于蜀、于婺、于临安,盖家有其书。人以予好奇尚异也,每得一说,或千里寄声,于是五年间又得卷帙多寡与前编等,乃以乙志名之。凡甲乙二书,合为六百事,天下之怪怪奇奇尽萃于是矣。
夫《齐谐》之志怪,庄周之谈天,虚无幻芒,不可致诘。逮干宝之《搜神》,奇章公之《玄怪》,谷神子之《博异》《河东》之记,《宣室》之志,《稽神》之录,皆不能无寓言于其间。若予是书,远不过一甲子,耳目相接,皆表表有据依者,谓予不信,其往见乌有先生而问之。(丁锡根94)
前节文字因为较少涉及对小说的看法,所以少有人注意。只有学者李剑国在借助自序考证《夷坚志》成书时间的过程中,论及了这篇自序前节文字中提到的“家有其书”这一轰动效应,认为这是推动洪迈把更大精力投注于《夷坚志》续集编撰的重要原因,这当然有一定道理(李剑国60)。从另一个角度看,这段文字固然是在表明洪迈的“好奇尚异”,但叙述传播以及素材来源之广,其实意在勾勒一个编撰过程中的互动效应。作者以拓展开的一个开阔的时空世界,给怪怪奇奇之事的存在找到合法的现实理据。而洪迈本人,则无意间构成了传播这个奇怪之事的中心,并引发了关于如何看待这些事件的进一步讨论。以往学者从“寓言”中提出了寄托性,从“表表有据依”和“乌有先生”的结合提出了艺术真实问题,都能给人以启发。但我们也不妨认为,当他提出一个“乌有先生”来和“表表有据依”的“予”相对时,其实是从现实世界的“予”中分离出另一个相对独立的小说家“我”(乌有先生)。这样,先于艺术真实问题讨论的,是作为创造了这一艺术真实语境的假想中的主体“我”(乌有先生)的存在,以及对现实中的主体“予”的影响,这才是值得我们关注的。概而言之,这一个“我”既是志怪小说的编撰者,也贯穿于所有的自序中;这一个“我”全身心投入“夷坚”各志的编撰时,又常常在自序中为“我”的合法性与人论辩。久而久之,这一个“我”的著述行为,甚至内化成现实生活中“予”的一种心理需要和生理本能,似乎“予”顽强的生命力,就是由“我”这种著述行为所激发的。洪迈有多篇自序谈到了他的志怪著述活动与自己身心健康的关系,保留下来的《夷坚支乙集序》就较为典型,其文谓:
绍熙庚戌腊,予从会稽西归。方大雪塞涂,千里而遥,冻倦交切,息肩过月许,甫收召魂魄,料理策简。老矣,不复著意观书,独爱奇气习,犹与壮等。天惠赐于我耳力未减,客话尚能欣听;心力未歇,忆所闻不遗忘;笔力未遽衰,触事大略能述。群从姻党,宦游岘、蜀、湘、桂,得一异闻,辄相告语,闲不为外夺。故至甲寅之夏季,《夷坚》之书绪成辛壬癸三志,合六十卷,及支甲十卷,财八改月,又成支乙一编。于是予春秋七十三年矣。殊自喜也,则手抄录之,且识其岁月如此。(丁锡根97)
自序中所说的绍熙庚戌年为1190年,当时洪迈已经68岁(钱大昕17)。在腊月大雪天千里赶路回家,给他的体力造成极大消耗。他在家调理了一个多月,身体才得以稍稍恢复,但其爱奇的内驱力却没有减弱,而编撰所需要的耳力、心力和笔力似乎与他的内驱力浑然为一,显示出一个为编撰而生的主体的力量。有意思的是,另有两篇失传但被赵与时摘录的自序,也记录了这一独特生命个体与著述行为互为支撑的真切体验。“夷坚支壬”的自序,谈及了洪迈子孙辈的一个看法,认为像他这种掇录怪奇,未尝少息,并不是老人“颐神缮性之福”(丁锡根106),故劝其把这一习惯去除。然而他一旦接受了这些意见,安心养生,还没过几天,他的身体反出现了状况,所谓“膳饮为之失味,步趋为之局束,方寸为之不宁,精爽如痴”(丁锡根106)。这让那些曾经劝阻他的儿孙们深感恐惧,只能让他重新进入编撰状态,使他能活得像一个健康人。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岂吾缘法在是,如驶马下临千丈坡,欲驻不可”(丁锡根106)。而在“三志丁”的自序中,洪迈说,如果遵从习俗,到了七八十岁的人退藏一室,早睡晚起,不再著书,就会像婴儿被禁止去品尝美食那样,越是被禁止,反弹就会越发厉害。所以,以后即使再有充满说服力的劝说,他也不理睬了,所谓“倾河摇山之辩,不复听矣”(丁锡根106)。
三、 书写中的生命动力与感悟
上述从生命体验角度来记录自身著述的心得,我们又该如何理解?
在古代社会,除开一些被朝廷选中去修国史的人,许多个人著述活动并不具有职业色彩,更不是他们安身立命所必需的,至多只是他们参与社会活动的一种余兴节目。洪迈从20岁出头开始编撰《夷坚志》,起初只能利用业余时间来从事著述活动。他的成书过程是比较缓慢的,到40岁左右才完成“甲志”共二十卷,这几乎花去近二十年时间。但因为编撰“甲志”获得了巨大成功,再加上许多人纷纷提供素材,使得他从编撰“乙集”开始提高了速度,同样的篇幅,五六年间就能成书。而越往后,洪迈担任了闲职,后来又告老回家,成书就越发迅速,有时候他直接把别人稿子纳入自己的著述中,几个月就能成一集。李剑国曾在考证文中将此种情况作为一种“洪迈现象”来加以论述,认为他写作速度的提高,主要是有闲、有受众的鼓励、有他人著述的支援等等。但还有一个不应忽视的因素是,洪迈鲜活的写作对象也支撑了写作主体自身的生命。这种支撑,姑且把它称之为生命的回流。以往一些文艺理论家在论及古代文学作品时,常常会提及作家主体生命向对象的灌注,形成了作品饱满的活力。他们把这称为一种生命体验向审美体验的超越,如陈伯海有关唐诗美学的论述(陈伯海13)。但对于对象的生命力向写作主体的回流或者说回报,并进而形成一种双向互动性方面,却较少论及。而这在洪迈的写作编撰过程中,却比较明显。因为洪迈的书写较少是无中生有,较少从自己的内心世界或者生活经验直接挖掘素材,而更多是对“表表有据依”的奇怪之事的编撰和再创作。这样,奇怪之事对他的吸引和激发,在很大程度上也成了对他生命欲望的激发和开悟,并反过来促成其作品得以源源不断地编撰成集、广为传播。虽然其作品似乎都是实录其事的写作,较难看出其本人的情感波动,但不可抑制的情绪力量,还是能够从一些作品直接或间接中约略捕捉到。比如《夷坚丙志》卷十三“蓝姐”篇,描写绍兴年间王知军宠幸的一位婢女蓝姐,跟主人寓居在郊外寺庙中,遭遇数十个强盗打劫,蓝姐沉着冷静,主动奉上所有财物,却偷偷用烛泪在强盗的衣服上留下了污迹。官府凭此线索,把强盗一网打劫,并追回了财物。作者结尾感叹说:“婢妾忠于主人,正已不易得,至于遇难不慑怯,仓卒有奇智,虽编之《列女传》不愧也。”(《古体小说钞·宋元卷》388)以往的论者,较多从作者书写的人物对象身上揭示意义,却往往忽视了,当作者发出这样的赞叹时,正可以见出笔下人物对书写者主体所发生的影响。
有时候,这种对主体生命体验发生的影响,不是以自身的直接感叹,而是以贴着笔下人物的思想情绪波动的方式,让读者捕捉到的。《夷坚丁志》卷九“陕西刘生”一篇,写陕西刘生救助南宋派往北方伪齐统治区做间谍的李忠一事。内容大意写李忠在北方从事秘密活动时,被奸人田庠认出,田庠知道李忠不敢声张,就以他欠债不还来要挟。刘生得知内情,就劝李忠把财物暂时给田庠,许诺以后定会悉数归还。李忠起初怀疑刘生是田庠的说客,不料刘生用财物把田庠诱骗到无人处除掉后,把财物归还李忠,便一别而去。该篇最后说:“李南还说如此,而失刘之名,为可惜也。”(《古体小说钞·宋元卷》395)这里的感叹,发出者既可以指李忠,也可以指本文的书写者。尤其是事件经由李忠回到南方来陈述,那么,刘生在铲除奸人田庠前的一段话,就有了特别的意味:“吾与汝无怨恶,但恐南方士大夫谓我北方人皆似汝,败伤我忠义之风耳”(《古体小说钞·宋元卷》395)。从这一意义上说,“失刘之名”固然可惜,但从刘生立场说,却并不可惜,因为他是以这种行为来彰显北方忠义之风,相比之下,其个人的名声是不重要的。我们可以想象,刘生这番话在作者笔下虎虎有生气的呈现,它是如何深刻地同步影响着作者这样一个南方士大夫的生命尊严的。
需要说明的是,作为见闻实录型的作者在书写时,感受到笔下对象对作者生命的回流式激发和感悟,这并不否认作者生命体对笔下对象的生气灌注,毋宁说,这更是一种双向往复的流动。不过,用历史眼光看,生命体验性的深入,即便在志怪小说中,也能依稀看到差异。这里试比较两篇类似题材小说的描写差异,都写了男子在世外遭遇女子的故事。其一是收在《幽明录》的刘晨阮肇故事,节略大意如下:
汉明帝永平五年,剡县刘晨、阮肇共入天台山取谷皮,迷不得返。在溪边遇见两位女子,资质妙绝,后留宿山里与之共居,遂停半年。当春天到来时,百鸟啼鸣,更怀悲思,求归甚苦。女子遂唤众人来,集会奏乐,共送刘阮,指示还路。既出,亲旧零落,邑屋改异,无复相识。问讯得七世孙,传闻上世入山,迷不得归。(鲁迅149)
这篇当然有作者宣扬的神仙思想,但刘、阮与女子相处半年而分离,涉及的情感体验,并没有在作品中得到很好表现,或许是,需要表现的神仙思想把基于人的生命体验的感情世界给遮蔽了。类似的故事,也发生在《异坚之甲》卷十“海王三”中,但后者所呈现的情感力量,那种分离的痛苦,是极为不同的。该篇内容大意是叙述一王姓往来海上经商者,遭遇风浪,船被倾覆,靠着木板漂到某岛屿,遇到一女子留他在山洞同居,他们依靠在岛上采野果生活,一年后生下一个儿子。接下来,发生了这样一幕:
女采果未还,王信步往水涯,适有客舟避风于岸隩,认其人,皆旧识也,急入洞抱儿至,径登之。女继来,度不可及,呼王姓名骂之,极口悲啼,仆地气几绝。王从篷底举手谢之,亦为掩涕。此舟已张帆,乃得归楚。(《古体小说钞·宋元卷》400)
王姓商人突然登船离去导致女子悲痛不已,但他自身也为之掩泪。这里的细腻描写,引起的感情震荡,似乎绝不是《幽明录》中刘、阮与女子分别所可比的。当然,女子的这种悲情流露,可能还掺杂了与儿子分离的因素。但有一个令人震惊的相似故事是,当男子匆匆上船而未能把儿子抱走时,追赶不及的女子当着丈夫的面把孩子杀死以达到报复的目的。书写这样的近乎畸形的反常故事,会给作者自身带来多大的生命冲击力呀!(洪迈59)
在此还可以讨论陈振孙关于《夷坚志》的一个说法。他在《直斋书录解题》著录该书后,加以批评说:“稗官小说,昔人固有为之矣。游戏笔端,资助谈柄,犹贤乎已可。未有卷帙如此其多者,不亦谬其用心也哉。且天壤间反常反物之事,惟其罕也,是以谓之怪;苟其多至于不胜载,则不得为异矣。”(黄霖 韩同文66)这里讨论反常与常态的关系,说法看似辩证,却忽视了一点: 洪迈一生求怪求异累积下那么庞大的怪异之事,结果让这种集反常于一人的行为,把自身的异常给突显了。换言之,就著述家而言,陈振孙所谓的“不得为异”,是就洪迈跟自己比较的结果,而在与他人常态的比较中,却显示了洪迈的反常态,或者说,一个生命体贯穿始末的新常态,与其他人的常态行为构成了真正的辩证关系。从这个角度看,陈振孙的观点显得机械和教条。
总之,这种书写活动内在的辩证关系,还有待我们去深入分析。
四、 志怪小说编撰意识的自我反思与发展
把志怪小说家记录的自身生命过程纳入小说理论批评的视野,其实是为了更深入分析这些理论批评。在此前提下,作为理论层面上的编撰者自觉的思想意识,也当然不可忽视。因为就人作为生命体而言,自觉的理性活动,构成人的整体生命活动的重要部分,体现出其对世界的深刻认识,更何况人的理性意识,与人的行动热情是紧紧结合在一起的。类似的理性活动,曾被西方一位理论家称为人物形象的智慧风貌。②那么,聚焦于《异坚志》的编撰活动,洪迈的自序又体现了怎样的一种自觉思考呢?
与常人所理解的理性活动追求逻辑自洽不同,洪迈的自序在涉及创作的思考活动时,常常是把自己的一种思想矛盾暴露在读者面前。以前文所引的《夷坚乙志》自序论,他一方面强调自己书中的内容“远不过一甲子,耳目相接,皆表表有据依者”(丁锡根94),这样的言出有据,似乎与“寓言于其间”的诸多前人所撰志怪书不同,足可以补史书之所遗。但他笔锋一转,又马上说:“谓予不信,其往见乌有先生而问之。”(丁锡根94)虽然我们可以借用艺术真实的思考范畴,把“乌有先生”理解为写作主体从现实世界中的“予”中剥离后的结果,但他直接呈现在表达上的矛盾,也是无法回避的。有学者据此认为,这是在前人把小说看作史书分支影响下进行虚构实践的“二难命题”(《宋元小说研究》133)。这当然也不失为一种解释,更何况洪迈自身就有史书著述者的身份。但洪迈似乎并没有停留在“二难”中,结合以后的自序以及其作品本身的编撰来看,他把这种“二难命题”展开为志怪小说编撰中的进一步思考。
其一,志怪小说在题材的选择上是否应该与人事实录有所区分,从而确保志怪不致受质疑?
当洪迈编撰《夷坚》甲乙两志,为“天下之怪怪奇奇尽萃于是”书而颇为得意时,他也发现其中有些记录并不符合事实。用他在丙志的自序来说,他是“颛以鸠异崇怪,本无意于述人事及称人之恶。然得于容易,或急于满卷帙,故颇违初心”(丁锡根95),不但有些记录不合事实,而且“其究乃至于诬善”(丁锡根95)。他把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分为两方面,既有素材提供者的问题,也有自己“听焉不察”的问题。所以等到他编撰“丙志”时,规定自己“但谈鬼神之事足矣,毋庸及其他”(丁锡根95)。但这种划分边界的自我约束,其实并不容易做到。事实上,就是在“丙志”中,也大有记录人事的故事。例如就在“丙志”的卷十三中,前文所述的“蓝姐”故事,有他最后感叹的“虽然编之《列女传》不愧也”一句话(《古体小说钞·宋元卷》388)。类似感叹,似乎就把志怪小说与史传等同了起来。正是这种“但谈鬼神之事足矣,毋庸及其他”的划分难以实现(丁锡根95),所以在后来的自序中,关于这一问题,就不像在“丙志”中说得那么机械。他在《夷坚丁志》自序中,直接以《史记》为例,说明人事与神怪迹象其实不能严格区分,对故事传闻者的身份,也无须加以严格甄别。这在很大程度上,推翻了“丙志”中的观点。他说:“彼记秦穆公、赵简子,不神奇乎?长陵神君、杞下黄石,不荒怪乎?书荆轲事,证侍医夏无且;书留侯容貌,证画工。侍医、画工,与前所谓寒人、巫隶何以异?善学太史公,宜未有如吾者。”(丁锡根96)
其二,志怪小说在编撰中,是否也要受讲述人逻辑的制约?
在赵与时引述的序言大旨中,提到的“戊志”自序,就涉及了这一点。现将该引述摘录在下:
戊志谓在闽泮时,叶晦叔颇搜索奇闻,来助纪录。尝言近有估客航海,不觉入巨鱼腹中,腹正宽,经日未死。适木工数辈在取斧斤,斫鱼肋,鱼觉痛,跃入大海,举船人及鱼皆死。予戏难之曰:“一舟尽没,何人谈此事于世乎?”晦叔大笑,不知所答。予固惧未能免此也。(丁锡根104)
这里的主客对谈,看似戏言,但也曾是小说叙述学中值得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
中国古代小说创作毕竟受史书的深刻影响,所以真实性要求作为一个巨大投影,始终笼罩在小说著述家身上。即便他们能够以寓言说来与之抗衡,借助于事件本身的假设性来弱化其真实性,但是,对真实性的执着要求又会从事件本身挪移到对事件的讲述者身上。如果事件有可信的也有可疑的,那么信者传信、疑者传疑。关键是,这个传信、传疑的传播者,似乎是应该得到确定,而不能让人生疑的。所以,之前流传甚广的《搜神记》,即便所记录的事情荒诞无稽,但著录者总习惯记录一些可资求证的遗迹或者人言,使得这些故事似乎也变得可信起来。比如著名的《宗定伯》一篇,结尾会有一句“时人语曰‘宗定伯卖鬼,得钱千五百’”(李剑国辑校383)。对洪迈来说,因为其编撰的素材来源大多为他人讲述,所以对讲述人以及材料来源真实性的考量似乎也成了逻辑的必然。
但仔细想来,这样的追问包括洪迈的自我反思,其实都没有必要,甚至可以说,无论古代还是现代,对小说讲述人获得材料的真实性的质疑都不必理会。像美国小说《白鲸》那样,让一个大洋上的幸存者来讲述追踪白鲸的故事,也许是过于谨慎了。因为在现代,有关小说的假设性,使得作家们可以很方便让死人开口说话,且不论西方所谓的魔幻现实主义作家,即便如中国新写实主义作家方方所写的《风景》,都有这方面的写作实践,也并没有受到过读者的质疑。而古代操作起来似乎更为便利,灵魂不灭的观念,人变鬼的普遍想象,使得幽界和人世可以随便沟通。即以《夷坚志》而论,记录鬼向人的述说比比皆是。所以,“一舟尽灭,何人谈此事于世”(丁锡根104)的疑问说明洪迈不但在编撰《夷坚志》的早期生涯中,曾经为书写的史实问题而纠结,而且到了写“夷坚戊志”的中期(李剑国考证其成书时间约在淳熙十年,他62岁时),③史学的思维方式还隐隐地影响到其写作活动。类似的思维活动,必然会引发小说编撰中的一个无法回避的根本性问题,即下文讨论的又一问题。
其三,如何看待志怪小说编纂中的描写不真实问题?
对于这个问题,洪迈的思考体现出矛盾的充分展开。也许就自序系列本身看,他对此问题的认识开始变得越来越合理,也越来越通达了。他72岁完成了《夷坚初志》十集后,又开始了《夷坚支志》等撰写,④在留存下的《夷坚支丁》《夷坚支戊》自序中,他都谈到了书写内容的不真实问题。不过在谈及这一问题时,他并没有像他在乾道七年的47、48岁时写《夷坚丙志》序那样,对自己书写中的不真实问题那么焦虑。在“支丁序”中,他开门见山,点出了小说的特性,也毫不隐晦自己有些书写的不真实问题。他说:“稗官小说家言,不必信固也。信以传信,疑以传疑,自《春秋》三传则有之矣,又况列御寇、惠施、庄周、庚桑楚、诸子汪洋寓言者哉!《夷坚》诸志,皆得自传闻,苟以其说至,斯受之而已矣。聱牙畔奂,予盖自知之。”(丁锡根99)然后他举出一些不可靠的实例,加以总结说:“爱奇之过,一至于斯。读者曲而畅之,勿以辞害意可也。”(丁锡根99)其结论,表明他不再纠结此问题,只要求读者能够领略大意即可(丁锡根99)。而在“支戊序”中,他又进一步举《吕览》中的怪事,认为像他书中那样写一人因为梦中受到陌生人侮辱而约友人白天去寻此人报仇,结果因为无法找到而恨恨至死,实在是不可能的。他是这样说的:“予谓古今人志趣虽若不同,其直情径行者,盖有之矣。若此一事,绝非人情所宜有,疑吕氏假设以为词。”(丁锡根99)把他所谓的“假设以为词”与前序的“勿以辞害意”连起来看,就可以理解,他此时的立论,已经较能触及小说虚构问题的真谛,而最后他说,“予每读其书,必为失笑。支戊适成,漫戏表于首,以为好事君子捧腹”(丁锡根100),看似游戏之笔,但这种游戏的接受心态,并希望读者也能有此态度的观点,其实与史书的著述和接受的谨小慎微态度,已经距离较远了。
耐人寻味的是,这种态度的变化仅仅是就《夷坚志》的著述和接受系统而言的。在他晚年撰写的偏于学术性的《容斋四笔》中,以“辨秦少游义娼”一篇短论,对较早时期收录在《夷坚己志》中的“义娼传”一篇予以了质疑。该故事叙秦少游在贬途中经过长沙,与一爱慕其诗词的娼女相遇后,停留了几日,娼女与少游相约日后重聚。几年后,娼女闻知少游客死他乡的消息,数百里奔丧,哭死在少游的棺柩旁。叙述的末尾还引述了该传的作者钟将之的赞语和为娼女所作的一首长诗。但洪迈在“随笔”中说他反复思考的结果是“定无此事”(《古体小说钞·宋元卷》425),一方面是之前发生过秦少游认为侍妾妨碍学道而拒绝女色的事件;另一方面,当时被贬之人受到严格监管,都是被催着匆匆赶路的。据此,洪迈认为:“以是观之,岂肯容少游款昵累日?此不待辩而明,《己志》之失著矣。”(《古体小说钞·宋元卷》425)程毅中的《古体小说钞·宋元卷》在录入的“义娼传”后附录了洪迈对该篇的辩证,又加按语说“此本小说,正不必以实录视之”(《古体小说钞·宋元卷》424),这当然是对的。但这样的所谓失实问题相当普遍,也不仅仅是小说中才有的现象。程千帆曾在《论唐人边塞诗中地名的方位、距离及其类似问题》一文中,从边塞诗入手,探讨了诗歌中的地名、距离与现实不符的普遍现象。就“义娼传”来说,洪迈所说的现实中被贬之人不得停留,在小说中变成娼女所谓的“学士以王命不可久留”(《古体小说钞·宋元卷》423),从而在不可久留和不得留之间打开了一道时间的裂缝,让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娼女和被贬士人秦少游结合在一起,演绎了感人一幕,并使这篇作品在传统文学史上具有了一定的典型意义。洪迈在《夷坚志》自序系统中有关小说真实的见解日渐通达,又在《容斋四笔》中阐发他的自我否定性议论,这表明针对同一内容,他作为小说家兼史学家两种眼光间的分裂。这种分裂,其实在《夷坚乙志序》中,当他以提出“表表有据依”的“予”和求证于小说的“乌有先生”对应时,就已经初露端倪了。而这种现象才是更令人深思的。
结 语
宋代是史学思想充分成熟的时期,其重要标志体现在不少史学家在世界观中,把“天道”与“人事”进行了区分。欧阳修以编撰《新唐书》和《新五代史》而闻名,《新唐书·五行志》中,欧阳修依据孔子著《春秋》例,说孔子“记灾异而不著其事应,盖慎之也”(欧阳修 宋祁873)。同样,他记录唐代灾异时,也“削其事应”(873)。而在为人熟知的《新五代史·伶官传序》中,劈头就提出“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欧阳修397),从而以实际行动对天谴事应说予以否定。类似的思想,影响是极为深远的。日本专治中国思想史的沟口雄三在《中国思想史》一书中认为,宋代的“天观”,是从以往的一个“有意志的即人格性、主宰性转变为无意志的即自然性、理法性的天”(沟口雄三6)。举出的重要例证之一,就是欧阳修对天谴事应说的否定(沟口雄三28)。问题是,当靖康之难后,怪异妖孽之说在社会流传,谈怪崇异形成了巨大的文化氛围,洪迈著述的《夷坚初志》成为“家有其书”。这不单单是对洪迈持续编撰的一种激励,也成为对史学家理法性天道思想或者说强调人事规律的一种抗衡。洪迈在被怪异传闻深深吸引的过程中,他的志怪著述家与历史学家的双重身份并不能很好地协调起来。虽然在《夷坚志》的小说编撰系统中,他渐渐弥合了史家著述和寓言家著述的旧有裂缝,但在小说编撰系统之外,他又以一个历史学家身份质疑了“义娼传”的真实性。这在一定程度上表征了当时社会思潮的多元和复杂。而这种深刻反映社会复杂思想的状况,又反过来把洪迈通过自序及相关论述所呈现的一个生命实践过程中的丰富自我形象提到了新的高度。
其实,不论是史家的立场还是寓言家的观点,自序系列的一个细节变化,是非常微妙的,就是在其保留下的十三篇自序中,落款方式是不同的。见下表:

序言落款夷坚乙志乾道二年十二月十八日,番阳洪迈景卢叙夷坚丙志乾道七年五月十八日,洪迈景卢叙夷坚丁志缺夷坚支甲序绍熙五年六月一日,野处老人序夷坚支乙集序庆元元年二月二十八日,野处老人序夷坚支景序庆元元年十月十三日序夷坚支丁序庆元二年三月十九日序夷坚支戊序庆元二年七月初五日序夷坚支庚序庆元二年十二月八日序夷坚支癸序庆元三年五月十四日序夷坚三志己序庆元四年四月一日序夷坚三志辛序庆元四年六月八日序夷坚三志壬序庆元四年九月六日序
上述落款大致分为如下四类: 详细记录了时间籍贯和名字的第一类,把籍贯删除的第二类,删除籍贯而用别号代替名字的第三类和只剩下时间的第四类。从这四类的变化看,其信息是日益减少的,但时间则一直保存着。这样的变化,也许说明他早年的编撰较少袭用他人的作品,所以要特意署名?或者说明他书写的寓言化意识越来越自觉而不在意现实中的名字?或者有其他我们所不知道的原因?但有一点是明显的,就是其编撰有一以贯之的时间意识,这种自觉的时间意识,在他的自序中也不时被提到。虽然传统序跋大多有记录时间的习惯,但对于《夷坚志》的作者来说,却有着与众不同的意味。
其一,就其自身来说,他的分集用天干来表示,就明示一种时间的意义。这种时间意义,如果里面浸染着史家眼光的话,那么随着编撰中的寓言意识的强化,这种史家眼光,其实已经内在于其个人的生命历史过程中,所以,每当他完成一集而写下自序时,似乎既是对完成了志怪的时间记录,也是对自身生命过程的记录,并由此形成一种连绵不断的时间延续,每一集的完稿时间越来越接近,显示了作者的一种强烈时间紧迫感。最后一集的自序连同时间记录的阙如,恰显示了他记录小说也即记录自身生命历程的突然中断。
其二,当后代甚为流行的《分类夷坚志》把残存的作品根据忠孝节义、阴德冤报等分为三十六门重新归入天干十集时(张祝平73),看似彰显了小说的寓言意识,但一个著作家的生命实践过程,他的时间记录意义,都已经湮灭不闻了。
注释[Notes]
① 周榆华、罗宗阳:“《夷坚志》的编撰及洪迈对志怪小说的看法——从《夷坚志》的多篇序言谈起”,《南昌大学学报》1(2004): 140—44。
② 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编: 《卢卡契文学论文选》,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172—221。
③ 李剑国:“夷坚志成书考——附论‘洪迈现象’”,《天津师大学报》3(1991): 58。
④ 《洪文敏公年谱》,《嘉定钱大昕全集》第四卷(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18。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陈伯海: 《生命体验与审美超越》。北京: 三联书店,2012年。
[Chen, Bohai.LifeExperienceandAestheticTranscendence.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12.]
程毅中: 《古体小说钞·宋元卷》。北京: 中华书局,1995年。
[Cheng, Yizhong.AnthologyofAncientChineseNovels(SongandYuan).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95.]
——: 《宋元小说研究》。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
[- - -.AStudyoftheNovelsduringtheSongandYuanDynasties. Nanjing: Jiangsu Ancients Books Publishing House, 1998.]
丁锡根: 《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
[Ding, Xigen.CollectionofPrefacesandPostscriptstoChineseNovelsacrossDynasties.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96.]
顾易生 蒋凡 刘明今: 《宋金元文学批评史》。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
[Gu, Yisheng, Jiang Fan, and Liu Mingjin.AHistoryofLiteraryCriticismduringtheSong,JinandYuanDynasties. Shanghai: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1996.]
洪迈: 《夷坚志》。北京: 中华书局,2006年。
[Hong, Mai.YijianZhi(RecordoftheListener).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06.]
黄霖 韩同文: 《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上。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
[Huang, Lin, and Han Tongwen.SelectedCriticalWritingsonAncientChineseNovelsacrossDynasties. Vol.1. Nanchang: Jiang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82.]
李剑国:“夷坚志成书考——附论‘洪迈现象’”,《天师大学报》3(1991): 55—63。
[Li, Jianguo. “An Evidential Study of the Compilation ofYinjianZhi: The Phenomenon of Hong Mai.”JournalofTianjinNormalUniversity3(1991): 55-63.]
——: 《新辑搜神记》。北京: 中华书局,2007年。
[- - -.NewlyCollatedin Search of the Supernatural.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07.]
鲁迅: 《古小说钩沉》。济南: 齐鲁书社,1997年。
[Luxun.RecollectedOldStories. Jinan: Qilu Book Company, 1997.]
沟口雄三: 《中国思想史·宋代至近代》,龚颖等译。北京: 三联书店,2014年。
[Mizoguchi, Yuzo.AHistoryofChineseThoughts:FromtheSongDynastytotheModernPeriod. Trans. Gong Ying, et al.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14.]
欧阳修 宋祁: 《新唐书》第三册。北京: 中华书局,1975年。
[Ouyang, Xiu, and Song Qi.NewBookoftheTang. Vol.3.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75.]
欧阳修: 《新五代史》第二册。北京: 中华书局,1974年。
[Ouyang, Xiu.NewHistoryoftheFiveDynasties. Vol.2.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74.]
钱大昕: 《洪文敏公年谱》,《嘉定钱大昕全集》第四卷。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
[Qian, Daxin.AChronicleofHongMai.TheCompleteWorksofQianDaxin. Vol.4. Nanjing: Jiangsu Ancients Books Publishing House, 1997.]
张祝平:“〈夷坚志〉版本研究”,《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2003): 66—77。
[Zhang, Zhuping. “A Study of the Different Editions of Yijian Zhi.”JournalofAncientsBooksCollation2(2003): 66-77.]
周榆华 罗宗阳:“《夷坚志》的编撰及洪迈对志怪小说的看法——从《夷坚志》的多篇序言谈起”,《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2004): 140—44。
[Zhou, Yuhua, and Luo Zongyang. “The Edition ofYijianZhiand Hong Mai’s View on Mysterious Novels as Exposited from his Series of Prefaces.”JournalofNanchangUniversity(HumanitiesandSocialSciences) 1(2004): 140-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