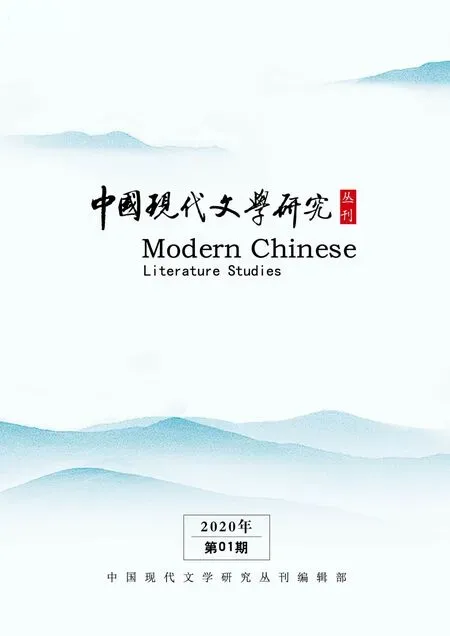高晓声的“糊涂话”
内容提要:高晓声创作谈中有非常重要的一块内容是谈他对中国农民的认识,这里边的许多话一直以来被视为典型的国民性批判话语而在研究者中反复引用,但是细读高晓声创作谈原文特别是放在上下文中去仔细体会这些话的含义,却发现高晓声的原意与国民性话语的解读存在相当的距离,甚至是龃龉。高晓声绝非以往经典评论家所论定的那样一个刻板形象,他与国民性话语之间的复杂关系有待大力的研究。
高晓声因成功塑造陈奂生等农民形象而蜚声海内外,但除此之外,他还有不少创作谈中的“名言警句”为历来研究者所乐道。比如“我敬佩农民的长处,也痛感他们的弱点”,“他们的弱点确实是可怕的,他们的弱点不改变,中国还是会出皇帝的”,又比如“当我探究中国历史上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浩劫时,我不禁想起像李顺大这样的人是否也应该对这一段历史负一点责任”,以及“我不得不在李顺大这个跟跟派身上反映出他消极的一面——那种逆来顺受的奴性”,等等。
高晓声的进入文学史和经典化过程,是在国民性话语的推动和主导下完成的。可以认为,以上名言警句,在一定程度上是国民性话语参与筛汰的结果,甚至这些名言警句本身就带有国民性话语介入“创作”的印迹。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段里,甚至直至今日,它们还常常被视为作家批判农民“劣根性”的明证而反复被征引。然而,高晓声意图表达的真实内容,果真如以往评论家们所认为的那样确定吗?已经有人提出了质疑,如王彬彬就评价前引让李顺大“负一点责任”那段文字,认为要么是作者“迂阔、浅薄”,要么是“为迎合某些人而故作高论”①。其实,未必是高晓声本来要说糊涂话的,但是他的某些表达通过特定的学术滤镜看来,确乎容易让人发生理解上的歧异,而高晓声与国民性话语之间欲拒还迎、若即若离、既对抗又交缠的复杂关系,尤其耐人寻味。本文通过高晓声引用率最高,同时也可能是被人误解最深的五段文字,阐述个人自认为或许有些新意的理解,以此呈现我心目中高晓声形象的多面可能。
“糊涂话”一 我写《陈奂生上城》,我的情绪轻快又沉重,高兴又慨叹。我轻快、我高兴的是,我们的境况改善了,我们终于前进了;我沉重、我慨叹的是,无论是陈奂生们或我自己,都还没有从因袭的重负中解脱出来。②
理解这段话的关键,在于“因袭的重负”一词。陈奂生没有摆脱出来的“因袭的重负”到底是什么?以往研究者普遍解读为懦弱、卑怯、狭隘、盲目自负等小生产者精神缺陷,阿Q式的奴性心理和精神胜利法,封建文化残余,民族劣根性等③。这些理解恐怕并不符合高晓声的本意。
原文后面接着说:“这篇小说,解剖了陈奂生也解剖了我自己(确确实实有我的影子,不少人已经知道这一点),希望借此来提高陈奂生和我的认识水平,觉悟程度,求得长进。”高晓声对于“因袭的重负”的发现,正是他“解剖了陈奂生也解剖了我自己”的结果,知道了高晓声如何“解剖了自己”,也就知道他“因袭的重负”是什么了。我们注意到,在“解剖了我自己”后面,高晓声解释说:“确确实实有我的影子,不少人已经知道这一点”,这很难解释为作家也具有陈奂生那样的精神缺陷(评论家所认为的),且这些精神缺陷是很多人知情的,而显然是指高晓声多次讲过的他复出后住宾馆的经历和体验:“我从农村上来,住招待所很想不通,为什么住一夜要花那么多钱”④,虽然有公家报销,但“总感到不习惯”⑤,想到跟陈奂生们的经济落差,躺在招待所的床上“难以入眠”⑥……(这是多么动人的感情呵!)
高晓声在另一篇文章中的自述,就把“我的影子”表述得更清楚直观了:
我写的那些小说,如《李顺大造屋》《“漏斗户”主》《陈奂生上城》,既是客观的反映,也都有我自己的影子。我不光看到过那些李顺大们造屋的困难,我自己也有这焦头烂额的经历。我不光看到“漏斗户”主们揭不开锅,我自己也同他们一道饿着肚子去拼命劳动以争取温饱的生活,同他们一起挺直了腰板度过那艰难困苦的时期。所以我说:“我写他们,是写我心”。我恢复工作以后,也确实困在五元钱一夜的高级招待所的床上难以入眠,因为我不能不想起陈奂生们的生活。我习惯于和他们一样去看问题了。⑦
可以看出,高晓声说的“都有我自己的影子”,就是指他本人有着和李顺大造屋、陈奂生饿肚子相类似的经历,而陈奂生上城的故事,也是从作者本人住招待所的切身经验上联想、创作而来。
高晓声说《陈奂生上城》“解剖了陈奂生也解剖了我自己”,就是指他本人住宾馆时的那些感受:因为高消费而惶惶不安,更因为对比陈奂生们的辛苦收入而辗转难眠……他忍不住再三地追问:“人的价值为什么这么小,床的价值为什么这么大?”⑧高晓声没有能力给出解答,他将这些没有答案的问题,笼统归结为“因袭的重负”。如何摆脱这“因袭的重负”,是高晓声抛给读者的问题,但他首先要做的,是把这“重负”呈现出来,揭示出来。陈奂生在宾馆所经历的如过山车般的情绪的跌宕翻转和种种可怜复可笑的失态的表现,正是这“重负”在人的精神上的反映。
《陈奂生上城》的主题,作家似乎并不愿意多谈,但他从未说过作品是暴露陈奂生的“愚昧落后”,甚至也否认小说是表现城乡差距⑨,他只是呼吁读者回到文本,回到文本不就是去体会陈奂生的感情吗?其实,高晓声并不是没有谈《陈奂生上城》的主题,他谈得已经够清楚了,他说:“《‘漏斗户’主》写粮食问题解决了,农民很激动,《陈奂生上城》告诉你,解决就解决到这样,不要看得太好,看得太好也不行,就是这么个情况。”⑩作家清醒地意识到,陈奂生们的境况依然不容乐观,他为此而“沉重、慨叹”,他要“借此提高认识水平,觉悟程度,求得长进”。高晓声说得这样清楚了,奈何评论家们听不懂也听不进大白话,他们自有另一套高大上的权威解释。
“糊涂话”二 他们的弱点确实是很可怕的,他们的弱点不改变,中国还是会出皇帝的。.⑪
这里提及农民的“弱点”,具体指什么,文中并没有明确表述,不过话说得很重:“他们的弱点不改变,中国还是会出皇帝的。”如果孤立地看这句话,确实很有些惊人,很容易就把后文忽略过去了。其实,这句话后面给出的解决出路才是重点。高晓声说,对农民的弱点,“我们没有别的办法,我们只有从经济上进一步解放他们的生产力;另一方面,我们的文学工作者,科学工作者,要用很大的力气,对农民做启蒙工作,这个工作是责无旁贷的”。不要看见高晓声使用了“启蒙”二字,就认为必定是思想启蒙那样“深刻”,似乎不义正词严地批判教导农民一番,就显不出“启蒙主体地位”,知识分子就失落了似的。从高晓声给出的解决路径,可以回头逆想一下,他未作展开说明的“农民弱点”大约是什么意思。如果像以往那样,将农民的弱点作一种本质化的理解,即认为其源于农民的某种本性,或者只是来自农民头脑中的某种东西,那么只要启蒙家们继续其启蒙大业,批判家们继续其国民性批判就是了,何来高晓声的解放农民生产力之说?何来高晓声的提高农民文化水平之说?农民通过转变思想,幡然觉悟,然后自己去提高自己的生产力,自己去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不就行了?难道他们懒惰倦怠,拒不提高自己的生产力,自甘蒙昧,拒不接受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吗?
高晓声通过“因袭的重负”,给刚刚感受到时代春风的陈奂生们浇了一杯冷水,以轻快幽默的笔调剖示他们与“现代生活”的尴尬距离。他心中系念着八亿农民缺乏文化“还不会表现自己”,呼吁作家多多地去关注农民、熟悉农民、表现农民,将其视为写作者神圣的历史使命。他同情农民苦难的历史,感叹于农民依然落后的现实,呼吁人们为彻底消除农民物质和文化的双重贫困而努力。高晓声对于农民的感情和认识,源于他们几十年同甘苦、共命运的血脉相连,源于“我习惯于和他们一样去看问题了”的心灵相通,不是受了任何抽象概念或宏大叙事的教育,不是后者所能涵盖和轻易改变的。他对于农民出路的思考,诚然是不无粗疏和空洞的,但是与那些以批判国民性为职志的道德精英相比,却有着和风般的温煦与实在,体现着农民本色的拳拳之心。
“糊涂话”三 他们身上有许多值得称道的品质。但根本的弱点在于没有足够的文化科学知识和足够的现代办事能力,没有当国家主人公的充分觉悟和本领。⑫我们的国家,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只有让九亿农民有了足够的觉悟,足够的文化科学知识,足够的现代办事能力,使他们不仅有当国家主人翁的思想而且确实有当主人翁的本领,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才会立于不败之地,我们的四化建设才会迅猛前进⑬。
这两段话可以说是高晓声对于“农民弱点”的比较完整的正面表述,这样的话他在不同时期不同场合多次提到⑭。对这两段话的解读,笔者认为有几点值得注意。首先它的“声音”是不纯粹的。对于农民的“根本弱点”的表述,前一句,“没有足够的文化科学知识和足够的现代办事能力”,这是高晓声自己的语言;后一句,“没有当国家主人公的充分觉悟和本领”,就不像高晓声的口吻了,很可能是他吸收了某些报刊语言,或者某些批评家语言的产物。很难想象,当年只因为想“探求”点什么,就被打入底层二十多年不得翻身的高晓声,当他刚刚恢复了身份,就说出农民“缺乏当国家主人公的充分觉悟和本领”这种话。只有把“主人翁”云云,视为高晓声后天学习并努力接受的一种语言,才比较容易读懂这种言、意之间的分裂和背离。
高晓声带有迎合意味的表达,反过来也深刻影响甚至是误导了人们对他的研究,以至于长久以来人们都忽略了一个事实,即高晓声对农民问题的表述,不论是在语义偏重,还是在表述方式上,都与启蒙派评论家存在着重要的差别。以上文为例,“使他们不仅有当国家主人翁的思想,而且确实有当主人翁的本领”,“不但……而且”的语法意义是前轻后重的,也就是说,相较于强调让农民有当主人翁的思想觉悟,高晓声更强调的是切实锻炼和提高农民当家做主的本领。农民有没有主人翁思想?我认为高晓声心里的答案是“有”。农民首先不缺乏做自己的主人公的思想。李顺大为了造三间屋,白手起家,坚韧不拔,百折不挠;陈奂生恪守做人信用,不偷不抢,即使饿得头晕目眩,照样还是和社员们一起下田劳动,他们无不展现出要做自己命运的主宰的惊人意志力。对于农民的创造能力,高晓声由衷地赞叹说:他们“无一不是耍弄粮食的超级杂技演员,能够用他们各自特有的方式将它变出千百万种无穷无尽的奇珍异宝”,在获得经营自主权的农村新天地里,他们“每一个人都成了独立作战的将军”。⑮这些说明,农民不仅有做自己的主人的强烈思想,也有做自己的主人的充分的内在能力。至于农民有没有当国家主人翁的思想,这个提问是没有意义的。李顺大没招谁惹谁,已经“吃足了苦头,从主人的宝座上跌下来,跌得连变牛变马都不在乎了”⑯,陈奂生还想请当老师的堂兄写信,替他向报社反映情况,幸好给及时拦下来。空有当国家主人翁的思想是没用的,关键是让主人翁思想落到社会生活的实处,这应该就是“使他们不但有当国家主人翁的思想,而且确实有当主人翁的本领”的真正意思吧。
同是对于农民弱点的表述,高晓声与启蒙派评论家的方式也是不一样的。启蒙评论家惯常使用的是肯定语式,即“农民的缺陷是什么、是什么(愚昧、奴性、狭隘……)”;高晓声使用的是否定语式,即“农民的根本弱点是没有什么、没有什么(文化科学知识、现代办事能力、主人翁思想……)”。其中的差别在于,肯定式表达的是对农民弱点的直接指认,而且往往是一种本质化的指认,否定式则是指向解决问题的努力方向,是正面的、开放的和动态的过程。高晓声指出的所谓“方向”,当然是非常宽泛的大致方向,需要注意的是,它的行为主体甚至也是不明朗的,是含含糊糊的。在“我们的国家……只有让九亿农民……使他们……才会立于不败之地”这段话里,高晓声提出告诫,或者说提出希望的对象,是应该理解为“国家”呢,还是应该理解为“农民”?是由“国家”而至“农民”,还是由“农民”而至“国家”?这是一个颇显暧昧但至关重要的问题。
“糊涂话”四 他虽然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好人,却也是营养丰富的坏人培养基。⑰.
“坏人培养基”,“中国还会出皇帝的”,这两个说法,自然有理由被视为对农民弱点的某种追责。出于对“皇帝”和“坏人”的义愤,启蒙批判家似乎格外能从中体会到农民的罪过的深重,同时格外能体会到作家说这话时的悲愤之情:“在此时的高晓声看来,陈奂生们居然成了‘坏人培养基’——他们应该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不但美国的‘现代’,连中国的‘现代’也不属于他们!在此,高晓声表现出了刻骨铭心的恨。”⑱.
高晓声真像上面这位论者说的,由农民的“代言人”变成“农民的鄙视者和否定者”了吗?紧接着“培养基”这句,高晓声继续写道:
我曾经说过:“我写陈奂生,既是客观的反映,也有我自己的影子。”“我沉重、慨叹的是,无论是陈奂生或我自己,都还没有从因袭的重负中解脱出来。”我是自觉地和陈奂生认同的一个。作为作家,所以我就会说:“我写他们,是写我心。”说了这话,过了12年,写到现在,我仍只认准那句话是最根本的。作为个人,我也类似陈奂生,不会钻营,不会保护自己。我当然不及陈奂生纯朴,但是做培养基却比陈奂生多些经验。我被打倒在地、横躺着让那些脚踏着(自然是乖得动也不动决不翻身的)的时候,脚支撑着的那些个躯干总比原来高了一截吧。只不知可曾够得上伸手揽着月,倘还不够高,再加垫一个陈奂生试试。
按照国民性批判家的思路,高晓声在判定陈奂生是营养丰富的坏人培养基之后,说“我是自觉地和陈奂生认同的一个”,“我写他们,是写我心”,“作为个人,我也类似陈奂生”,这些话大概可以笼统地也是惯常性地理解为“显示了作者可贵的自我批判精神”。但是高接着又说“我当然不及陈奂生纯朴,但是做培养基却比陈奂生多些经验”,引出对当年挨整经历的一番愤慨,这总不能还理解为作家在自我批判吧!高自称做培养基比陈奂生有经验,系指他作为“右派”被打倒的那段惨痛经历,培养基就是指称作者自己,是他同情、悲悼、自伤自怜的对象;另一方面,他的批判锋芒,显然是指向那些在政治运动中见风使舵、欺压良善、损人以自肥、害人以自傲者,从大的方面讲,则是指向那个让坏人得势、恶行肆虐的社会。既然作者对自己做培养基是同情的而非批判的,就没有道理说他对陈奂生这个培养基是批判的而非同情的。同情谁,批判谁,这里是没有丝毫含糊的。
那又怎么理解“营养丰富的坏人培养基”这句话所明明包含的否定倾向呢?可以认为,这里隐含着作者的情感与理性的冲突,即作者的感情立场是在“培养基”一边的,但是在理性上他不能不主张让他们“退休”。主张让陈奂生(“培养基”)退休,不代表主张让陈奂生的对立面(“坏人”)霸占历史舞台,退休不是消灭,不过是自我批判、自我扬弃、自我更新、保持前进的另一种说法,是希望陈奂生们克服自身弱点,以新面貌面对新形势的意思。这里也包含着作家对自我的一种扬弃,包含着他对像陈奂生这样实实在在的好人,为何会成为营养丰富的坏人培养基的反思。“我也类似陈奂生,不会钻营,不会保护自己。”好人不会钻营,难以适应激烈的乃至是恶性的竞争的环境;不会保护自己,就容易上当受骗,被坏人欺负,让坏人得势。“坏人培养基”,大略就是这意思。
这也使我们联想到高晓声对“忠厚老实”型的农民性格的评价。他认为不能离开具体环境去评价一个人,因为“一个人的优点和缺点往往是联系在一起的,缺点有时候会变成优点,优点有时会变成缺点。由于情况不同,就会反映出两种不同的效果来”19,“善良的人们喜欢忠厚老实的人是怕吃亏,另外一种人,称赞和喜欢忠厚老实的人是为了便于统治、容易沾光。……世道变了,并不是变得不要忠厚老实,而是光靠这一点已经不能评价一个人物了,还需要有更重要的东西。那些东西是什么呢?我很难回答,不过我赞成要有”⑳。
高晓声希望农民不仅有“忠厚老实”的品格,还得更“厉害”些,更“能干”些,这样在生活中才能不吃亏或者少吃亏,给坏人得逞的机会也就少了。这自然是为农民好。其实农民中是不乏精明能干之辈的,高本人就是一个,但是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阶层来说,农民何尝不想让自己变得更强大、更“厉害”些呢?可是除了跳出农民阶级,却实在是缺少办法。是哪些因素在阻碍着他们?高晓声说“还需要有更重要的东西”,虽则他很难回答那是什么,但我想那便是了。就像高晓声也没有说明,到底怎样能“让九亿农民有足够的觉悟,足够的文化科学知识,足够的现代办事能力”一样,他的直接目的,可能真的就像他自己说的,“只是想引起人们更加广泛的注意和研究而已”㉑。这是高晓声的现实主义。
“糊涂话”五 李顺大在十年浩劫中受尽了磨难,但是,当我探究中国历史上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浩劫时,我不禁想起象李顺大这样的人是否也应该对这一段历史负一点责任。九亿农民的力量哪里去了?为什么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难道九亿人的力量还不能解决十亿人口国家的历史轨道吗?看来他们并不曾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他们或者是想当而没有学会,或者是要当而受着阻碍,或者竟直是诚惶诚恐而不敢登上那个位置。造成这种情况的历史原因和社会原因值得深思。我不得不在李顺大这个跟跟派身上反映出他消极的一面——那种逆来顺受的奴性。㉒.
引文出自创作谈《〈李顺大造屋〉始末》第三小节的结尾。但这是一个莫名其妙的结尾,与其说它是结尾,还不如说更像是刻意加上去,给前面的文字捣乱的。
第三节的全部文字,不算这个所谓的“结尾”,一共1453字。这一千多字组合在一起,可以视为一篇结构完整、气韵连贯、说理透彻的说理文。如果给它加一个标题的话,可以叫作“论李顺大是个好公民”。
李顺大怎么个好法?首先,他信仰坚定,体会到共产党是真心为人民谋福利的,“要跟着共产党走到底”。其次,他忠厚善良。党的路线发生了错误,损害了他利益的时候,他明白了那是“自家人拆烂污”,人家向他道歉说好话,他就“非常感动”地原谅了,并且“从心底里真诚地称赞共产党”。最后,他也并不笨傻。他一个平头百姓,虽然“不理解上层发生了什么”,却也渐渐“被生活逼出了一点觉悟”,“开始能够辨别是非”。李顺大就是这样一个值得敬爱、值得依靠、值得同情的好公民,他的脉搏“是和全国人民一起跳动的”。
高晓声写这篇“李顺大赞”,特别突出了李顺大在政治上的正面形象,其主要目的,应该是回应诸如“小说反党”之类的政治构陷。但这不是全部,读者从文字中能非常真切地感受到,通过对李顺大与共产党的相互关系的历史回顾,作者对李顺大这类农民的美好心灵的由衷热爱,对他们的历史苦难所寄予的无限同情。
那么在这样的文字后面,怎么突然就追究起李顺大的“历史责任”来了?而且这段凭空而来的生硬议论,仅有一副论人以罪的严厉态度摆在那儿,并未显示丝毫耐心和诚心去摆事实、讲道理,全部加起来237字,态度非常粗暴专横,却偏偏作为结尾,补缀在深情流利的“李顺大赞”后面,完全是两种语言,两种格调,两个大脑。
这么显而易见的不协调,一定有它埋藏的秘密。它使人们不由得疑惑:这段结尾的真实意思,真的像它的字面意思所显示的那样么?我们必须仔细再仔细,寻找真正能打开语言迷宫的那把钥匙。
是的,“追究农民责任”这段文字,的确极易使人产生“就是如此”的印象。但是仔细推敲的话,可以发现原话讲得其实并没那么确定。“是否也应该对这一段历史负一点责任”,这句话算是“试着这么一问”的语气,答案本来就应该包含“是”和“否”两种可能的。“九亿农民的力量哪里去了?为什么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难道九亿人的力量还不能解决十亿人口国家的历史轨道吗?”一连串排比式的质问,看起来声色俱厉,可是平心静气地想一想,其实也仅只是止于“问”,终不曾把问号变成句号或者叹号。看来,作家似乎是用了十分闪烁和隐曲的语言,把自己的真实态度层层包裹起来,小心隐藏在对农民追责的表象背后了。好比是大人打孩子,巴掌举得很高,可是落下去是虚的,并没真挨在身上,只是做做样子罢了,有时候竟是为了演给别人看的呢。
但是,一连串的质问,即使没有坐实对象,其分量是沉重的,其锋芒是尖锐的,不能不引人深思,让人进一步去探究:巴掌没有打在孩子身上,是不是打在了别处?“九亿农民的力量哪里去了?”这些不无怨怒的问责,其真实锋芒完全隐藏在紧跟的后一句话里了:“看来他们并不曾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他们或者是想当而没有学会,或者是要当而受着阻碍,或者竟直是诚惶诚恐而不敢登上那个位置。”这是对上面悬设的连串质问的完整回答。为什么本该发挥作用却没发挥作用?因为他们“不曾真正成为国家主人”。是他们不愿意当主人吗?不是。他们或者是“想当而没有学会”,或者是“要当而受着阻碍”,或者“竟直是诚惶诚恐而不敢登上那个位置”。以上三种“或者”的情况是有关联的:“受着阻碍”是核心关键,因为受着阻碍而主观上“不敢”,也因为受着阻碍而客观上“没学会”。所谓“逆来顺受的奴性”,不过是“不敢”的贬义说法。作家皮里阳秋,指桑骂槐,他的愤慨不敢痛快直接地发出来,但倔直的性格又让他必须要发表自己的思想,所以借了“农民落后性”的“桑”,骂他认为真正应该指责的“槐”。
但指桑骂槐,我想并不是这段让人看不懂的奇怪结尾的直接目的,如果说它前面的一千多字正文是为了化解“利用小说反党”的政治风险,那么这段二百多字的结尾则是为了回应启蒙家们对他的极力拔高。他回应的方式亦耐人寻味:对前者,他以政治抒情诗的调式唱出他对农民的深情礼赞;对后者,他似乎是很不耐烦地胡乱扯起“国民性批判”的大旗,然后小心翼翼地包藏起他“现实批判”的“祸心”。
结束语
高晓声的五段“糊涂话”,除了最后一个,他可能确实要使读者不妨“难得糊涂”一点,其他的基本都属于正常表述,没有转弯抹角,也难说有什么微言大义。然而之所以成了糊涂话,不是话说得不够清楚,也不是道理讲得不对,而是因为受到了启蒙评论家们的特殊礼遇,“两眼一眨,老母鸡变鸭”,不期然成了国民性批判话语的座上宾。从高晓声本来的意思看,他本不属于那个位置,吴楚嫌大的呢帽转送陈奂生,大小正好,批判国民性的帽子戴在头上是什么滋味,只有高晓声自己的头皮知道。然而从外界看来,他选择了沉默是金:既不点头接受,也不摇头拒绝。他曾否认过自己同鲁迅的关系,不过那是故事开始时候的事,很快他就不再说那种“傻话”了。㉓.他主观上应该是乐于期望自己与国民性话语“求同存异、和平共处”的,那是互利共赢的事,国民性话语在极力地发掘他、打造他、利用他,他在不损害自己本意的前提下,也偶尔吸收对方的语言外壳来表达自己的思想,他们都在“借对方之力为我所用”。然而高晓声实在过于乐观了,他不明白自己跟国民性话语完全不是一个量级上的,他幻想中的愉快合作事实上并不存在,他几乎可以说是被人家绑架着走完了他的一生。被绑架的并不只有作家高晓声,还有他所创造的陈奂生、李顺大们,以及并非他所创造的“沉默的大多数”。
注释:
——评滑稽戏《陈奂生的吃饭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