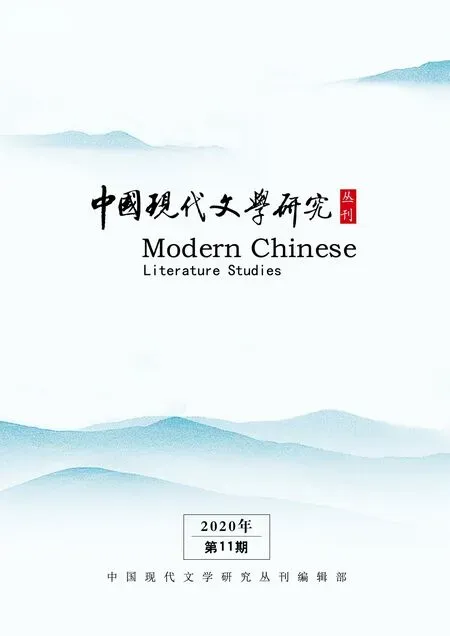乡土中国与民间戏曲的互文※
——陈彦小说《主角》新论
内容提要:陈彦在《主角》中塑造了忆秦娥这一主角形象,却无意中展示了乡土文化在城市文明进程中不断变化、革新甚至缩减、消亡的过程,主角忆秦娥通过秦腔这一艺术所体现的“生存美学”,感受庄周传统与佝偻承蜩,正是其精神还乡最重要之所在。他在《主角》中以秦腔这一传统戏曲为纽带,以儒释道为载体,搭建起民间(秦岭九岩沟)与城市(西京)之间的一座桥,看似对乡土、民间着墨甚少,实则是形散而神不散的“新乡土”书写。
《主角》是陈彦继《装台》之后的又一部力作,并获得第十届茅盾文学奖。在小说《主角》中,陈彦塑造了忆秦娥这一主角形象,却无意中展示了乡土文化在城市文明进程中不断变化、革新甚至缩减、消亡的过程,在其中围绕着主角忆秦娥的不同人生阶段的代表戏,回应不同阶段的出走—回归的过程,恰好与这个文化之根紧密联系起来。同时,在走出乡土中,忆秦娥从不得不学秦腔到爱上秦腔、痴迷秦腔,在快乐和痛苦的双重考验中,体会和掌握到了人生的审美艺术,在改变与适应中确定了符合自身的“艺术风格”(或者可以称之为艺术作品),她既是传统艺术秦腔培养和塑造的最好艺术作品,同时也成就了秦腔这个传统艺术经典,让秦腔在不断改变和调整中呈现出新的内容。而这,恰好说明乡土与民间中国在不断调整和适应的社会变迁中走向了一种新的形式。陈彦的家乡位于秦岭南部的商洛(镇安),恰恰是贾平凹的故乡,商洛地处陕西东南部,被秦岭深山包围,同时位于秦楚豫三地交会处,民间的文化保存相对丰富。这个秦岭深处的小城镇,是秦岭的一道弯,带着民间的文化、艺术和乡俗一同进入新世纪,如果说贾平凹的小说是在诉说乡土中国中最深层的巫魅文化,那么陈彦的《主角》则是用最原始和民间的传统艺术诉说“变与不变”,其中所承载的不仅仅是“秦腔”与中国正在经历消亡的传统艺术,也是儒释道之间的消长。忆秦娥用自己的方式生存,即经历长期曲折的磨炼和陶怡,在快乐和苦难的双重考验中实践的“生存美学”。而这正是她作为自身主体性的一种价值实现和精神满足,在自我感受到的“艺术世界”中,实现了自我欲望最大化,不再去徒劳地解放“内在的”“被压抑的”自我,而是创造了真正的自我。在《主角》中,真正的主角忆秦娥一直是与乡土、民间若即若离的,既置身于城市中,又一直在精神上眷恋着乡土,这种内心的“望乡”书写恰是转型中国“传统与现代”最典型的一个缩影,通过忆秦娥这一秦腔主角生发、扩展,在她执着于秦腔艺术来体现主体价值时,也正是她在乡土和城市之间构建的桥梁,这一桥梁既是“主角”本身,也是秦腔艺术本身。在书写传统时,陈彦没有像贾平凹那样置身于传统,或者对传统的消解产生隐忧,而是在现代文明中找寻传统的意义,在城市中回望乡土价值,不是简单的二元对立,而是相互交融,构成了当代陕西的“新乡土”书写,作者通过对秦腔戏曲的大量转换和运用,开启了戏曲小说的全新模式。作品中大量出现的秦腔戏曲与主角忆秦娥人生轨迹的微妙呼应,儒释道在其中的此消彼长,以及忆秦娥从最开始走出秦岭选择秦腔,到最终回归秦岭继续唱起秦腔的过程,都是陈彦在《主角》中致敬传统与民间的方式。
一 “生存美学”与“佝偻承蜩”的庄周之道
陈彦对民间的阐释是通过儒释道这一载体而实现的,首先是“主角”忆秦娥戏曲的执着与“佝偻承蜩”的庄周之道的内应。忆秦娥在追求艺术时忘我的精神、与世隔绝的态度看似一种脱离现实的“痴”,实则是对自我的坚守。在忆秦娥内心深处,潜藏着一股巨大的力量,推动着自我不断朝艺术巅峰前行,“每一个女性身上,都有一个完美的女性等着去恢复本真。所以可能的方案就不仅是‘解放’,不仅是自我创造,还有拒绝——拒绝外界加给自己的身份”①。忆秦娥拒绝了其他身份,只想释放出自己作为一个秦腔演员的“自我创造”,连她的丈夫刘红兵都认为她是一个怪物,一个只会唱戏、练功、睡觉,其余啥都不懂的怪物。甚至所有世俗的功利、享乐在她看来都是“原罪”,都是可耻的。特别是当她在剧团目睹了舅舅胡三元与胡彩香的苟且,经历了厨子廖耀辉的猥亵,看到了胡彩香与米兰为了角色而争夺时,她认为只有艺术是纯粹的、快乐的,沉浸在秦腔的表演中才能忘记烦恼,当她处于人人羡慕的辉煌中却经历了舞台坍塌、儿子痴傻、丈夫背叛、事业下滑时,仍然没有放弃她所坚守的艺术,正如西塞罗所言“经历长期曲折的磨练和陶怡,在快乐和苦难的双重考验中,才能真正地体会和掌握到人生的审美艺术”。支撑她走下去的秦腔艺术,是她快乐的源泉,而“秦腔”又与传统和民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这个“生存之道”,恰好与古代庄子的“养生”“葆真”寓意相近,“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的庄子思想,正是追求自身的满足,完全注重个人天性的施展。小说中描写秦八娃老师买了一本《庄子》送给她……秦老师走后,她就一直在翻这本书,并且跟背台词一样,先把“佝偻承蜩”背了下来,背着背着,她突然从驼背翁练捕蝉的专心致志中,体悟到了一种过去不曾明白的东西。②“佝偻承蜩”出自《庄子·达生》:“仲尼适楚,出于林中,见佝偻者承蜩,犹掇之也。”③意为做事情专心,全神贯注,方能成功。正如忆秦娥执着于每日练功,无论是烧火丫头还是成名的角儿,她都数年如一日,对秦腔戏曲的热爱,也成为她离开家乡后的精神信仰。其次,忆秦娥对艺术的追求还表现在对欲望的克制上,正如庄周所谓“嗜欲深者天机浅”。艺术追求的是灵魂的修养,而“完美的灵魂来自于求知,灵魂只有朝向唯一真实的来源,才能摆脱肉体的束缚,回归真实的世界”④,忆秦娥与第一任丈夫是在证明身体的“纯洁性”开始的,又是在“身体”的背叛中走向瓦解。忆秦娥对身体纯洁性的要求,正如她对艺术的要求一样,是绝对的排他性。因此当她看到刘红兵与其他女人赤身裸体在一起时,她想到了舅舅胡三元与胡彩香老师的偷情,产生了深深的厌恶。最终刘红兵出车祸瘫痪,正是这一思想的某种暗合。第二任丈夫石怀玉为了占有她的身体,不惜采取各种办法,最终在她的妥协中满足了他的欲望,却因此让儿子刘忆送命,也让石怀玉自杀身亡,又间接说明对欲望的克制才能成就她自身。“任何一个存在于此的身体当然是自然给予的,是父母剩余和基因遗传的,但同时也是文化塑造的,是历史和社会的结果,因此,身体是自然与文化的双重产物,而且是一个始终更新的作品。”⑤灵魂因为“附上了一个尘世的肉体”而“葬在了这个叫做身体的坟墓里”。⑥民间传统是不容亵渎的。因此当刘红兵和石怀玉分别提出想让她带妆(秦腔表演时化的妆)进行性行为时,她都十分愤怒地拒绝了。忆秦娥实践着秦八娃老师所说的“佝偻承蜩”之道,但她这种完全置身事外的处事方式,却被所有人认为是“傻”,是脑子不开窍,陈彦在塑造忆秦娥时有意把她塑造成一个脱离现实,只活在秦腔中的人物,并非是对执着于传统戏曲人物的有意夸大,而是通过庄周之精神来远离身体之谱系,附着灵魂之世界,这一世界是传统戏曲——秦腔给予的,而秦腔来自民间,民间是它的“根”。这就构成了生存美学(庄周之道)—灵魂—秦腔戏曲—民间的一个回环,看似对欲望“不开窍”的忆秦娥,实则是传统艺术在对抗现代文明时的一种坚守,是对现代文明冲击下逐渐式微的传统艺术的一种致敬。
二 戏曲与乡土民间之呼应
忆秦娥对外界事物的有意疏离,对秦腔艺术的极致追求,是庄周思想的一种外化。小说中除了庄周之道外,对儒、释同样有较多着墨。小说与中国古代传统的融通、传统艺术的糅杂、儒释道三家的登场,是要表达一个更深层次的思考:文化遗留物与民间中国的走向,其中忆秦娥代表的出世之道和惩恶扬善的道教审判(阎王、地狱与黑白无常),刘红兵等人表现出的积极的入世之儒,尼姑庵中大师对一切事物宽恕的佛法心态,皆不言自明。入世即儒家所强调的“治国平天下”,要参与到社会之中,而出世则恰相反,更关注自身,超越人生困境和世俗情欲,使人获得一种宁静的自由和圣洁的心境。积极入世者的心态或者宁静自由的出世心态,在民间都有存在的合理性,而惩恶扬善的道教、因果轮回的佛教则包含了民间老百姓的朴素价值观,人们对“鬼神”的敬畏和恐惧,皆因对死后之事神秘叵测的未知感。对现实中“恶”的无力感,寄托在阴曹地府中判官(阎王)的公正上,所谓加入儒释道的笔法,则是民间原始的文化遗留物之象征。小说中儒释道虽均有着墨,但陈彦更侧重于布道和惩恶扬善的正义感,这是在看清现实之后对民间信仰的书写,透过陈彦所传递的“表”,看到了他对民间的挚恋的“里”。同样出生于秦岭山区,陈彦不同于贾平凹对故土的直白,而是以一个从秦岭山区走出来,最终回归到秦岭山区的一代秦腔主角来表达一种乡土情怀,小说自始至终都以“城里”的视角观照与写作,通过戏曲这一传统形式把乡土与民间隐藏在骨架中,虽形不明却神不散。而儒释道精神与中国古代传统戏曲又是相互关联的,忆秦娥在舞台坍塌、丈夫出轨、孩子痴傻等一系列打击下,去尼姑庵修行,最终却在住持的开化下顿悟:唱戏,亦是一种“布道”,是“度己度人”的“大修行”。小说中人物与儒释道的不解之缘,印证了秦腔戏曲中众多情节,比如《白娘子》的人情与佛法恰好对应了忆秦娥,《杨排风》舍身为国的入世情怀,《游西湖》在阴间惩恶扬善的道教……他在小说中着墨较多的是以忆秦娥为代表的“老庄之道”,还有连通佛教与道教的阎王、牛头马面与黑白无常。阎王最初起源于佛教中的阎罗王,之后传入中国,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成为民间非常重要的文化遗留物。因此当乡土和民间成为文化遗留物的载体时,所谓原始的巫鬼传说、因果轮回才得以显现。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认为人们的语言、文化最终在长期发展演变过程中构成“文化遗留物”⑦,并形成了万物有灵,即“相信所有生物的灵魂在肉体死亡或消失之后仍能继续存在;相信各种神灵可以升格,进入威力强大的诸神行列。神灵和人又是相通的,人可以引起神灵的高兴或者不悦”。儒释道和文化遗留物相辅相成,同时又在戏曲中得到最佳体现。戏曲是乡土中国最受欢迎的艺术形式,而通过戏曲传递的原始遗留物以及天道轮回的宿命因果恰好是普通百姓最为津津乐道的。阎王、小鬼与黑白无常都是“阴间”之“鬼”,黑白无常,亦称无常。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对神祇,也是有名的鬼差。牛头马面则取材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勾魂使者的形象,被道教吸收,并充当了阎罗王及判官的下属。《红楼梦》就有著名的《恨无常》一曲,“喜荣华正好,恨无常又到”。鲁迅在《无常》一文中也用到“鬼卒、鬼王,还有活无常”⑧。民间文化对“鬼”与“神”都有很深刻的阐释,做了恶事要下地狱,这是民间对恶人的一种原始审判。《周易·坤·文言》云:“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⑨而陈彦在《主角》中不止一次提到了阴曹地府与阎王、牛头马面。第一次是隐藏在《游西湖》戏本中的“鬼怨”“鬼辩”,《游西湖》是秦腔经典传统剧目,包括十四场,讲南宋御史之女李慧娘与太学生裴瑞卿一见钟情,互托终身,后被奸相贾似道强纳为妾,李、裴西湖相遇,船头互诉衷肠,贾窥其情,盛怒回府,一剑刺杀慧娘。又命家奴诱裴生至贾府欲杀害之,慧娘阴魂不散,怨气腾腾,九天玄女怜其不幸,差土地神赠阴阳宝扇与裴相会,慧娘魂返贾府,星夜救裴逃生,并严惩了奸相贾似道。虽未直接提及阎王、小鬼,却也以阴间魂魄及惩恶扬善为内容,为第二次和第三次出现的阴曹地府埋下伏笔。第二次是在忆秦娥因舞台坍塌事件死伤了别人的孩子之后,梦到自己被阎王招了去,严刑拷打,同时还有牛头马面带着她,让她看到了昔日争名逐利的大腕儿、名人,在阴间的“下场”,曾经为了名利不择手段之人,在阎王的阴曹地府中成为接受酷刑的鬼魂。第三次是她的孩子刘忆意外死亡之后,她又一次到阴间接受审判,“醒过来之前,她一直在做着一个噩梦,梦见自己让人用铁链子拴着手脚,拉到了一个似曾相识的地方。她猛然想起,就是那次演出塌台,死了几个孩子后,那场噩梦中的地方。依然还是牛头马面把她拉着……”⑩延续着同样的场景,“鬼”与阴间的判官是民间的集体想象,最原始的意象与图腾,也是根植在民间百姓心中的信仰。中国自古就有对“鬼神”的崇拜,在古代戏曲中尤甚,在情节发展当中出现神佛形象或鬼魂形象的作品数不胜数。特别是明清两代,十之六七的传奇作品会出现神佛鬼魂。元杂剧《倩女离魂》、宋元南戏《赵贞女蔡二郎》、元孔文卿的《地藏王证东窗记》杂剧、明姚茂良的《精忠记》传奇,都是通过鬼神判官来惩治奸臣。而在《主角》中儒释道与中国传统戏曲亦有微妙关联,比如《白蛇传》中的人情与佛法,《杨排风》中舍身为国的入世情怀,《游西湖》中在阴间惩恶扬善的道教,《狐仙劫》中狐仙即鬼神之化身……陈彦在小说中把现实中无法实现的惩恶扬善通过一出出戏曲和梦境得以实现,在最古老的戏曲中寄托着最原始的民间。整部小说并没有直接介入民间,或者书写乡土,但正如小说中秦八娃所说:“戏曲天生就是草根艺术,你的一切发展都不能离开这个根性。”[11]陈彦写传统艺术,写文化遗留物,都通过戏曲传递生老病死、宠辱荣枯、饥饱冷暖、悲欢离合。无论是儒家、道家、释家,都或隐或显,或多或少地融入了戏曲的精神血脉,既形塑着戏曲人物的人格,也安妥着他们以及观众因现实的逼仄而躁动不安、无所依傍的灵魂。
陈彦之前是一名秦腔编剧,《西京故事》《大树西迁》等秦腔现代戏已经大获成功,之后转型写小说,《装台》《主角》都围绕秦腔戏曲而作,可以说他开创了新戏曲小说(或者可以说是新世情小说)之先河,每一个人物都是戏曲中的人物,即使是游离于戏曲之外的人物,也能在戏曲中找到自己的命运轨迹。《装台》人物的脉络,看似游离于戏曲之外,实则点睛之笔还在仅有的几段戏曲唱段,与故事中的人物产生了共鸣。《装台》结尾以《人面桃花》唱词昭示刁顺子的个人命运:“花树荣枯鬼难当,命运好赖大裁量。只道人世太吊诡,说无常时偏有常。”[12]而《主角》不仅以戏曲(秦腔)开始,以戏曲(秦腔)终结,每一个人物都是戏曲里逃不掉的众生,无论主角还是配角,“主角是聚光灯下一奇妙;主角是满台平庸一阶高;主角是一语定下乾坤貌;主角是手起刀落万鬼销;主角是生命长河一孤岛;主角是舞台生涯一浮漂;主角是一路斜坡走陡峭;主角是一生甘苦难嚎啕”[13]。秦腔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与民间和乡土是紧密相连的,它的故事原型皆来自民间,同时主角忆秦娥也来自民间,创作者秦八娃同样来自民间,而创作的内容《杨排风》《白蛇传》《游西湖》等都出自传统民间。主角忆秦娥努力追求的生存价值,与众生徘徊在儒释道之中,则是戏曲人物必要的安排,通过戏曲的台本来诉说整个乡土中国的故事,故事中儒释道的频繁更迭,忆秦娥既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又肩负着“度己度人”的重任。她从家乡的出走,正如戏曲开场之热身,拉开了一场巨大的戏曲表演。整部小说处于戏曲与故事的融合汇通之中,不仅书中大量写入秦腔唱词和剧本内容,甚至忆秦娥[14]的名字和人生轨迹也是戏曲中的词牌名与唱词。一方面是乡土承载着戏曲,滋养了戏曲;另一方面戏曲又支撑着乡土的情怀,甚至是乡土中最原始的图腾和遗留物。因此在陈彦的小说《主角》中,乡土的隐退并非隐没,而是在戏曲中显现的另一种形式,构成与戏曲的互文。
三 精神原乡与新乡土书写
陈彦在《主角·后记》中说道:“拉美的土地,必然生长出拉美的故事,而中国的土地也应该生长出适合中国人阅读和欣赏的文学来。”[15]整部小说拉拉杂杂写了忆秦娥四十年,“围绕着她的四十年,又起了无数个炉灶,吃喝拉撒着上百号人物”[16]。这上百号人物,涉及儒释道,同时杂糅了传统戏曲和民间故事,其中不乏忆秦娥的爱恨情仇,但整部小说读下来,仿佛有一条主线贯穿着,无论怎么拉扯都被这个主线支撑着架构,是整部小说的“魂”。这个主线就是忆秦娥的故乡(原籍):秦岭。作者陈彦的故乡在陕西商洛镇安,与贾平凹故乡同属陕南商洛,位于秦岭南麓,与鄂豫两省交界,世世代代被大山包围,又受大山滋养,这里因为深处秦岭,同时在地理位置上与“鄂”(湖北)、“豫”(河南)相邻,交杂着秦楚豫三种文化,既有巫鬼图腾,也有祭祀信仰。秦岭有着太多可以抒写的传统,小说中着墨最重的秦腔、儒释道与鬼神审判都与忆秦娥的原籍秦岭有着千丝万缕之联系,“秦岭”总是在忆秦娥的人生关键时期突然显现,支撑着她继续前行。第一次是主角儿的出场——“1976年6月5日的黄昏时分,一代秦腔名伶忆秦娥,跟着她舅——一个著名的秦腔鼓师,从秦岭深处的九岩沟走了出来。”[17]与最后一次主角儿的退场——“忆秦娥突然那么想回她的九岩沟,她就坐班车回去了”[18]形成首尾呼应,让整部小说从乡土而始,又回到乡土。除了首尾,中间四处出现了忆秦娥想要回到故土的情形,前两次是她成名之前(一次是她无意中听到她舅与胡彩香偷情,她想回到农村,“那时候她只想回去放羊,她觉得回去放羊,都比在这里好一百倍……”一次是她得知自己成了烧火丫头之后偷偷回到了九岩沟,想继续自己放羊娃的生活)。后两次是她成名之后(当她经历了丈夫刘红兵出轨、舞台坍塌之后返回西京,火化完单团,忆秦娥就回九岩沟去了……忆秦娥把一百多只羊吆喝到山上,把儿子背着,抱着,驮着,跟着羊滚搭着,似乎是暂时忘了那凄惨的塌台一幕)。每一次她撑不下去的时候,都是回到秦岭,看到自己生活的原籍与滋养自己的土地,即从飘忽不定中安定下来,即使被阎王、小鬼噩梦缠身,也会在秦岭深处最为宁静的尼姑庵中得到心灵的支撑,一个人的故乡就是他的“根”,正如我们无论到哪里都会冠以籍贯。在乡土中国中,文化是依赖象征体系和个人的记忆而维护着的社会共同经验,“这样说来,每个人的‘当前’,不但包括他个人‘过去’的投影,而且还是整个民族的‘过去’的投影”[19]。相比贾平凹立足于乡土的创作,陈忠实依托乡约的传统文化,陈彦是站在乡土高地上与城市回望乡土,他的《装台》也好,《主角》也罢,都是一种新戏曲小说的全新阐释,用秦腔这一从古自今流传下来的传统艺术,架构起乡土与城市之间的桥梁。在小说结尾处忆秦娥又一次从九岩沟回去,她回到了更广大的农村,回到更需要秦腔的山里洼里、沟里岔里,虽然她被胡三元说得待不下去了,但整个秦岭深山都是她的藏身之处,是她大显身手的地方。《主角》没有描写沟沟洼洼的农村生活,没有直接描写农村的人和事,没有把忆秦娥写成一个农村人,却和城市并非二元对立,反而是一种返璞和回归,秦腔蕴含着中国古代文化、民间信仰和宗教,农民对乡村宗教、民间信仰既有无意识的继承,也有转型时代的功能性、价值性,还有对乡土文化传统的自觉坚守。无论走出去多久、多远,“原乡情结”始终是无法回避的,乡村的现代化、城镇化,以及现代乡村的城市化进程逐渐削弱与遮蔽了文化的地域性,或者在逐步吞噬乡村,留守在乡村的人越来越少,但是文化遗留物、民间的原始信仰与习俗始终存在,“成功的作家都有一个自己的文化记忆,他的原乡。莫言的高密东北乡,陈忠实的关中,贾平凹的陕南,王安忆的上海,他们都有自己的原乡,自己的根据地……”[20]在《主角》中陈彦设置的秦岭九岩沟和鲁迅的“鲁镇”、沈从文的“湘西”、许钦文的“松村”、贾平凹的“商州”、陈忠实的“白鹿原”是有区别的,之前的乡土作家更侧重直接描写乡村,勾勒的是原乡的场景,而陈彦的九岩沟却是一种精神还乡,是通过戏曲连接西京城市与九岩沟乡村之间的桥梁,整部小说不露痕迹地用传统戏曲诉说主角儿及舞台众生相,背景切换也是从县城的剧团到省城的剧团,甚至可以说没有一点乡土气息,“《主角》的现实主义,不是那种摹写式的追求‘客观’效果的现实主义,亦非建立在主客间距和二元关系基础上的批判性现实主义,而是带有强烈主观性、抒情性和理想情怀的现实主义,这种现实主义师徒从中国文化的特殊性中开掘普遍性,是一种以权执行和总体性叙述重建‘文化中国’主体的文化政治实践”[21],是透过民间的镜像来观照中国历史、现实与传统,不是置身其中,而是在戏曲搭建中被“激发”的民间,是在日渐式微的乡土中寻找永久留存的遗留物,放置在现代文明中,无法被吞噬和淹没,这大概是陈彦致敬传统与乡土的书写表达,“也是对民族戏曲的存货与拓展潜能有了更加乐观的认知与提升”[22]。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