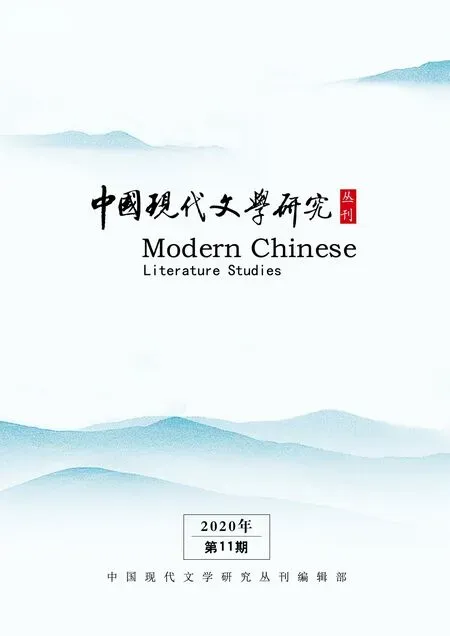论叶维廉对传统“诗画相通”美学的阐释
内容提要:叶维廉对于传统“诗画相通”美学视境的探讨一直作为明确的创作意识和行动纲领深植于其五十余年的诗学实践之中。首先,叶维廉的“诗画相通”观受到钱锺书论述“出位之思”的启示,但突破了后者“诗本位”的批评倾向,并且在肯定“出位之思”的同时强调诗、画作为艺术媒介的自主性,于“出位”与“本位”的张力中丰富艺术表现形式。其次,叶维廉将对于中国传统诗画关系的考察融汇于“纯粹经验”美学理想,以道家“以物观物”等美学精神沟通着诗歌与绘画的美感经验,并在此基础上思考现代诗和现代画如何在中西美感意识和创作技法的碰撞中获得新的活力。
“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中国传统诗画融通的历程自唐宋始,诗人于画外题诗,画家以诗意入画,彼此在创作技法、情意表达等方面相互激荡启发,共同拓宽了中国传统美学的审美视境。近现代以来,在莱辛的《拉奥孔》等西方文艺美学思想的影响下,中国学者开始借以新的视角来重审传统诗画理论与实践,通过符号学、现象学等方法来探源作品背后的文化符码意涵,站在中西会通的节点上寻找中国传统文化自立于世界的独特魅力以及艺术再创新之可能,给当代中国的文艺创作带来丰厚的理论资源和生机活力。
叶维廉关于传统“诗画相通”美学视境的探讨将中国道家美学、禅悟精神与西方现代主义“纯粹经验”“瞬间美学”等思想联系在一起,在中西美学视境的比较与会通之中重新阐释和肯定中国传统宇宙观和美学精神,并且在传统“诗画相通”的启示下开始自觉思考艺术表现的媒介性能问题,从而生发出一系列对当代情境的艺术精神与流变风貌的思索。
一 重读《拉奥孔》:叶维廉与钱锺书观点辨异
叶维廉在1977年发表的文章《出位之思:媒体及超媒体的美学》中首次透过莱辛《拉奥孔》和白璧德《新拉奥孔》来重新探讨诗画关系。“出位之思”这个概念在现代思想和艺术领域的含义来源于英国批评家佩特(Pater)借用歌德使用的streben与anders所组成的合成词Anders-streben,本义为艺术的“兼容互摄”①。叶维廉将其定义为“一种媒体欲超越其本身的表现性能而进入另一种媒体的表现状态的美学”②。这个美学概念最早由钱锺书引入并阐释,他在《中国画与中国诗》(1947)中讲道:
一切艺术,要用材料来作为表现的媒介。材料固有的性质,一方面可资利用,给表现以便宜,而同时也发生障碍,予表现以限制。于是艺术家总想超过这种限制,不受材料的束缚,强使材料去表现它性质所不容许表现的境界。譬如画的媒介材料是颜色和线条,可以表现具体的迹象;大画家偏不刻画迹象而用画来“写意”。诗的媒介材料是文字,可以抒情达意,大诗人偏不专事“言志”,而要诗兼图画的作用,给读者以色相。诗跟画各有跳出本位的企图。……这种“出位之思”当然不限于中国艺术。③
钱锺书可以被视为较早地使用中西互照的方法来探讨中国传统诗画关系观的学者,《中国诗与中国画》以及后来陆续发表的《读〈拉奥孔〉》《通感》④被称为《拉奥孔》在中国的“姐妹篇”⑤。在文章中钱锺书结合中国传统文论肯定和发展了莱辛的“诗画异质论”,从王维在诗坛与画坛的不同地位出发,认为虽然“南宗画和神韵诗是同一艺术原理在两门不同艺术里的体现”,但南宗画可以被视为中国传统绘画的正宗,神韵派大师王维却远逊于杜甫的历史评价,诗歌也鲜称高品。⑥由此,钱锺书批评了传统的“诗画一律”观,认为诗画虽然有互通互融之处,但总体上以诗为代表的文学艺术还是胜过以画为代表的造型艺术。比如钱锺书以徐凝的题画诗《观钓鱼台图》为例,强调了中国古典诗歌在空间造型方面依然广阔的表现力。即使是莱辛强调的造型艺术中表现“富有包孕的片刻”这一重要美学原则,文字艺术也可以采而纳之,作为丰富其表现力的有效手段。而诗歌中所特有的一些修辞和表现手法是文学艺术所独擅,难以用在绘画等造型艺术作品当中。所以钱锺书所认为的“出位之思”其实是立足于诗画在模仿论的层面上所要传达内容的一致性,两者可以互相借鉴与启发;虽然说绘画在媒体性能方面也有其独到的艺术效果,但总体来说诗的表现力还是要高于画。历来有诸多学者认为钱锺书的这个结论反映了其“诗本位”的批评倾向,有很大的漏洞。比如过晓就在文章中指出钱锺书并未详细分析绘画相对于诗歌所具有的“不能取代的功能”,钱文中那句“这当然不是否认绘画、雕塑自有文字艺术无法比拟的独特效果”更像是一种“礼节性的表态”⑦;唐卫萍同样也认为钱锺书“对于诗歌表现力的挖掘越来越精细,而对绘画观念的理解和运用仍嫌不足和简单化”⑧。而这一点也成为学界反思诗画问题研究时的一个热门话题,即当前的探讨往往“仅立足语言艺术(文学)的本位去理解出位之思”,而应该从“多样性与差异性”的视角来切入,避免因个人的兴趣偏狭和视角固化等问题造成研究的遮蔽⑨。
令我们惊喜的是,叶维廉在《出位之思:媒体及超媒体的美学》中就对这个问题有了较为深入的讨论。总的来说,叶维廉在文章中以“出位之思”来指涉“超媒体美学”的重要特点显然是受到钱锺书论述的启示,但主要观点却与后者有很大不同。一方面,叶维廉认为诗画等媒体之间的界限并不像莱辛所说的那么泾渭分明,诗歌与绘画具有超越媒体性能差异的内在同一性。例如莱辛在《拉奥孔》中认为诗的独有题材是动作,画的独有题材是物体;而“诗无法呈现物象的实体性”,“画无法表现动作的持续性”。叶维廉指出莱辛的美学假定“颇有漏洞”,由此援引中国传统美学以及西方赫尔德(Herder)、斐德(Pater)等人的观点来进行批驳,例如其中以《江南可采莲》《辛夷坞》《江雪》三首诗作为例证,认为这三首诗均展现着“时间空间化”的特质;而中国画当中“多重透视”“回旋透视”⑩的特点也证明了莱辛“单一瞬间的呈现”的理论之偏狭。在此基础上,叶维廉创造性地将中国传统“气韵生动”“意在言外”的美学理想与赫尔德所提出的“Kraft”(叶维廉翻译为“气”“力”)、法莱(Roger Fry)的“律动论”等联系在一起,强调诗歌可以超越文字,绘画可以超越形、色、线条,从而共同指向媒体以外的“明亮世界”,最终跃入“美感状态的共同领域”。另一方面,叶维廉虽然鼓励艺术家创作时打破自身媒介的壁垒,借由其他媒体的表现性能的眼光来获得对一个作品整体的美学经验;但与此同时他也吸收了《拉奥孔》与《新拉奥孔》的合理成分,警示人们要对于诗画的媒体“本位”有着更为清醒的认识,即“出位”的前提是要把握好媒体自身的审美特质和表现性能,绘画作品不能罔顾本身的视觉性去刻意追求语言的表意功能,诗歌创作也应当把握语言媒介自身“说明、陈述思想与情感”的主要性能特质,不能消弭文字的述义性,最终成为“绘画的诗”[11]。
综上所述,钱锺书与叶维廉关于诗画关系的探讨都以中西会通的视角,从莱辛《拉奥孔》等西方近代美学思想中得到启示并以此来重审中国传统诗画观;同样双方也都认为诗与画具有媒介性能上的本质差异,却在美感对象上具有可互通有无的同一性。但两者在最终结论上却走向了殊途:钱锺书在1960年代重读《拉奥孔》后,将《中国诗与中国画》当中关于“出位之思”的论述删除并重新修改发表,成为莱辛“诗画异质论”的重要支持者,认为“诗高于画”;而叶维廉则承接了白璧德、赫尔德等人对莱辛的批评,结合中国传统美学思想,并不认为诗画具有艺术品级的高低之分,强调诗歌与绘画创作应该在坚守媒体性能本位的同时积极互通互鉴,共同达致人类原质经验的纯然展现。综合来看,我们可以发现叶维廉不但突破了“诗本位”的批评偏向,借由中国传统绘画技法的分析来批驳莱辛观点的偏颇,而且在肯定“出位之思”的同时强调艺术媒介的自主性(autonomy),在“出位”与“本位”的张力中丰富媒介的表现形式。这两点是叶维廉的理论阐释中相较于钱锺书更为成熟的地方,也是他展开“诗画相通”论述的美学基石和准绳。
二 以“纯粹经验”为主轴的“诗画相通”理论
叶维廉对于传统诗画关系的重新体悟始于钱锺书的“出位之思”,展开并成熟于“纯粹经验”的理论建构之中。“纯粹经验”美学往往被视为叶维廉诗学理论的重要特质,援引自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中借用詹姆士(William James)的“pure experience”这个心理学概念来论述《庄子》中“心斋”“坐忘”等哲学思想,叶维廉受此启发并结合当时台湾艺术创作的具体情状,将这个概念转化到自己的文学批评体系之中,由此展开对于中西美感视境的探讨,并成为其此后对诗歌、小说、绘画等艺术门类进行阐释和比较的重要美学标准和审美态度。
叶维廉于1963年赴美进修,先后取得美国爱荷华大学美学硕士、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比较文学哲学博士,1967年进入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任教,教授比较文学、现代诗歌、道家美学等内容。身处跨文化的场域之中,叶维廉在由文化错位而产生的焦虑和忧患的挤压之下“冥思游移”“上下求索”,更加明确自己身上所肩负的使命:在文化传播方面,叶维廉在美大量翻译和推介中国古典诗歌并争取出版,比如1972年美国格罗斯曼出版社(Grossman Publishers)出版了叶维廉英译王维诗作合集Hiding the Universe,在美国学术界产生一定范围的讨论。另外,美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兴起的“中国诗歌热”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着叶维廉深入王维山水诗、禅宗和道家美学的研究,以寻根式的姿态去对比中西诗歌的美感意识、观物方式、语法差异等内容,从而不断丰富着其“纯粹经验美学”理论的典律建构和创作实践。叶维廉在文章《王维与纯粹经验美学》中将王维与西方现代主义诗人庞德、威廉斯的诗歌创作进行比较,并结合中国传统绘画理论较为具体地阐述了“纯粹经验”美学的理论特质,即事物的纯然演出应该实现“具体形态的直接表达”与“自生自化”,不需要人为的认可,“现象就是本体”;排除知性的干扰从而实现因果关系的切断,“藏天下于天下”;作者应当融入事象的千变万化中,以物观物,“和现象合一而使自己成为现象”[12]。由此看出叶维廉“纯粹经验”美学观的形成受到西方现象学、中国传统诗学、道家美学的影响,其中提出的诸多要素也可以被视为其汇通传统诗、画的审美境界的重要美学原则与方法,在其后期关于南宋山水诗画的具体论述中逐渐得到发展与完善。
相较于儒家“诗言志”的诗教传统,叶维廉更为偏爱以道家美学为精神源头的神韵派诗和南宗绘画,关键原因在于两者都包蕴着“任物自然”的山水观和“以感代思”的禅宗精神,追求一种跃出因果逻辑的灵动神思,从而达致让“景物自现”的纯粹审美境界。在这个基础上诗画可以实现互通互照,使得绘画能够借用视觉的兴会“唤起一种超乎‘叙’‘说’得到的感受”,诗歌语言也排除知性分析和抽象思维的侵扰,“不涉理路,不落言荃”,从而让读者/观者“游入浸入”,去感受激发诗人/画家“原有瞬间的气脉活泼泼的拍击力”[13]。由此叶维廉从“纯粹经验”的美学理想出发,借用道家美学的观物方式和表达策略来展开其对中国传统诗画互通的论述。
首先,诗、画创作都需要坚守“以物观物”的观物感物方式,追求一种消解中心、物物契合、大制无割的“天放”境界。“以物观物”语自北宋邵雍《皇极经世》的观物篇,与“以我观物”相对,强调一种忘却“情累”、恢复“本明天性”的修养观,显然是对先秦老庄思想的承继。叶维廉受其影响,并结合胡塞尔现象学中关于物我关系的思考,认为“以物观物”本质上应被视为道家跳脱名言枷锁、断弃私我名制的美学策略,在绘画中体现为一种“自由浮动的印记活动”,古典诗歌则需要“语言的重新发明”来实现主体虚位,保持物象“多重空间与时间的延展”[14]。正如宗白华所言:“俯仰往还,远近取与,是中国哲人的观照法,也是诗人的观照法。而这观照法表现在我们的诗中画中,构成诗画中空间意识的特质。”[15]叶维廉常以范宽的《溪山行旅图》为例,认为画作前景右下方细小的行旅与树群表示观者的视点很远,而后景本应更远的溪山却向观者庞然压下,似近在眼前。前景与后景之间的云雾消解了常规的距离感,让观者可以从不同距离、角度对画作进行观赏,从而获得不同的审美效果;行旅的人也从主位退却,化入万物万象的全面运作之中。《溪山行旅图》典型体现了中国传统绘画“多重透视”“回旋透视”的技法特点,而诗歌中“语言的重新发明”则着重表现为文言文语法的灵活性,即“不确切定位、关系疑决性、词性模棱和多元功能”[16],通过意象的多重并置来形成一种视觉的张力,借由视点的迅速转换来达致瞬间经验的多重聚合,比如王维的《终南山》各句分别从远处、山前山后、最高峰等各角度进行观看经验的呈现,“从四面八方,从不同的时刻和角度同时呈现自然现象的每一面”[17],由此实现“物现物显”的“全面网取”。在这个过程中物象呈现为一种“指意前”的自由状态,获得如画般的意义浮动空间的同时破除前设意义的圈定,达致“以物观物”的澄明视境。
其次,叶维廉认为道家“离合引生”的辩证方法是中国传统文艺理论的主轴,即以“无为”“断弃”的负面建构去肯定“未始有名”的原真世界,实乃一种积极的精神投向,证诸画中是“山色有中无”的虚实相生,在诗中则指向言外的大有,呈现为“空白”的美学。比如南宋水墨画中常用“云山烟水”来烘托出“空盈”的气韵,将“无”和“寂”作为主要审美对象来引向一种沉入万境的冥思。马远的代表作《山径春行》中观者伫立左下角将视线投向对面,远方的山形由深及浅,随着空间的无限延展终至潜入似有似无的恍惚之境当中,正如叶维廉在诗歌《夜雨怀人》中所表达的感受:“我和你走入画图的一角/静静地/眺看/一片空茫里/那条难以辨别的单线/起伏入/更深更深的远方,那/若有若/无的天空,大虚大寂/而全然璨丽”[18]。而在诗歌中则强调“弦外的颤动”,在“寂然凝虑”中“思接千载”(刘勰),以“无言”来指向“独化”的全然境界,例如王维的“大漠孤烟直”,在整片死寂的大漠中连风都趋于静止,一缕“孤烟”作为唯一可以凝注的实体,将诗人与读者的思绪引向边关戍卒的苦怨、历史风云的翻腾变迁等更为延绵浩大的内容,以有限的甚至是凝缩性的文字来“点逗”出景外的无限生机,从而也帮助读者跃入诗中,感受诗人彼时观物感物的全部细节与过程,直接拥抱这个瞬时、开放、自由的审美境界。
最后,叶维廉认为诗与画都可被称为“凝注的艺术”,诗人/画家需要去抓住生命中偶发性的瞬间经验,以一种具有高度敏感性的出神状态潜入物象细微的跳动之中,从而获得一种类似于宗教的“异常瞬间的灵会”,最终达致“纯粹的抒情境界”。叶维廉这种“瞬间美学”的理论还是得益于其对于中西美感经验的多重比较,作为其“纯粹经验”美学的重要批评角度,一方面承接西方现代主义诗人在诗歌中对于生命“充满激情、脉搏跳动的空隙”的凝注,“不断燃烧,以这种坚硬的晶石的火焰来保持这种狂喜”[19];另一方面也从中国传统的美学精神中得到启发,从道家的“目击道存”“虚室生白”到禅宗的“顿悟”,艺术家往往选择追求观物感物过程中“瞬间的灵悟”去达致“神与物游”“万籁齐响”的美学理想。柯庆明在文章中也认为中国传统山水诗画的创作“往往在于借刹那的景象捕捉宇宙自然的永恒律动,因而使得这一片刻的光景,因其‘目击道存’而深具一种戏剧性的机转,同时又呈现为含蕴深远而韵味无穷”[20]。例如“云来万岭动,云去天一色”一句,诗人(罗浮仙)在远观群山的审美活动中逐渐沉入自然本真的律动里,于一片光影交织、天地辽阔的浑茫之境下拥抱瞬时的禅悟,由此获得另一种听觉、另一种视觉,抛开语言因果逻辑的束缚,以一种入梦般的出神状态去感受和捕捉世间万物的无尽造化,最终可以超越时空与宇宙天体的运作相冥契。同样的感受也可以在米友仁的《潇湘奇观图》当中得到,缱绻多姿的云雾随画轴的展开而缓缓游动,山形与树木也伴着云气的变化而由淡远渐趋明朗,直至中段主峰完全清晰地呈现于观者面前。在末端景色又转入迷蒙空冥,山形也再次融入巨大无垠的浓雾之中,若隐若现。整幅画观来明晦交替,气象万千,米友仁也在题画中写到此山水奇观“变态万层,多在晨晴晦雨间,世人鲜复知此”,从而以近乎现代西方表现主义的笔法恣意泼染,力求抓住其中最摄人心魄的瞬间“真趣”,使观者随着云雾的流动和视点的游移逐渐沉入冥思静听的出神状态中进进出出,获得丰厚而又独特的审美感受。
三 比较视角下《诗章》与“潇湘八景”的“神遇”
叶维廉在《庞德与潇湘八景》中主要以中西诗学对照的视角和传释学[21]的研究方法,探讨了庞德如何在中日古典诗画美学尤其是潇湘文化的启迪下创作出《诗章》第49首这样开一代诗风的全新作品,可以作为其在比较视域下思考中国传统“诗画相通”美学的重要研究成果。
所谓的“潇湘八景”原义为“湖南地区的八种景观”,据沈括在《梦溪笔谈》记载,具体指的是北宋文人画家宋迪所绘的八处“平远山水”,后世也基本上将宋迪作为《潇湘八景图》的首创。以“潇湘八景”为母题的诗画创作在南宋开始盛行,并逐渐脱离了地域风景的限制,成为一种文化地理符号,文人墨客借以抒发恨别思归、壮志难酬等不遇之感,比如上文所举的《潇湘奇观图》便是米友仁在镇江所见之景,表达的也是盛衰之思、浮沉之叹。值得注意的是,“潇湘八景”的创作充分体现了南宋文人画幽远深微的特色,不仅为后世的诗画风格树立典范,更是随着文化交流漂洋过海,在日本、朝鲜、越南等地产生深远影响,成为东亚各地区共同的文化意象和创作母题。[22]以日本为例,13世纪时大量的日本僧人到中国学法修禅,从而带回诸多南宋时期的艺术作品;中国的著名禅师(如一山一宁)也选择东渡日本进行讲学,同样传入了不少“潇湘八景”的相关诗画。比如日本圆觉寺的祖元禅师在宋学法时曾与禅画家牧溪交游,并极力收集他的画作带回日本,牧溪的代表作《潇湘八景图》也被当时的日本绘画界称为“天下首屈一指”的珍宝,具有极为崇高的地位,与马远、夏圭等人的创作一起奠定了日本室町时代的水墨画传统,影响深远。
众所周知,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作为西方意象派的重要诗人,被艾略特称为“我们时代中国诗的创造者”,热衷于将中国古典诗学、哲学传统引入西方现代派诗歌创作当中,《华夏集》(Cathay)里的中译诗为当时美国诗坛带来一场颠覆性的“东方风暴”。叶维廉自1960年代后期开始转向对庞德的集中研究,1969年在美国出版的博士学位论文《庞德的〈华夏集〉》(叶维廉翻译为《国泰集》)至今仍是庞德研究者的案头之作。在这一时期,叶维廉就发现了庞德代表作《诗章》的第49首大部分内容都与“潇湘八景”有关,并在此后多年的考证与研究的过程中前往欧洲、日本等地寻根溯源,在2006年由岳麓书院出版了《庞德与潇湘八景》一书,并于2008年台大版中增添了英文对照内容以及庞德私人收藏的册页。
一如叶维廉在书中指出,庞德所接触到的“潇湘八景”直接来源于17世纪日本画家佐佐木玄龙的作品,后者的诗画风格及美学策略正是承接日本室町时代周文、思堪等人的创作而来,毫无疑问受到了南宋山水诗画传统的浸染。[23]并且佐佐木玄龙册页上的题诗由曾宝荪(即曾国藩的曾孙女)协助庞德译成英文,由此被庞德在《诗章》中进行创造性的发挥。[24]结合上文对“潇湘八景”产生及流动情况的梳理,我们可以发现“庞德与‘潇湘八景’”这个题旨涉及文化传播、文本互文、艺术转换等当代历史美学研究的核心议题,而叶维廉在文章中重点翻译了第49首的前28行(即“七湖诗章”部分),并将其与佐佐木玄龙册页上的题诗、曾宝荪的译文相对照,发现庞德的诗歌并不是对题诗的简单复写,而是抓住在观看“潇湘八景”时所涌现的瞬间悸动,并结合着自己对于潇湘文化传统的理解去进行诗歌意象的构造,利用类似中国古典诗歌“罗列的句法”和“明晰的细节”去让景物自现,从而营造一种冥无雄浑的气氛,“呈现的由中国式以烟雨云山为主的山水构成的寂然世界”[25],与道家的表意策略和美学取向相吻合。
所以,庞德与“潇湘八景”的“神遇”是一个复杂的跨文化、跨艺术媒体的综合议题,可以视为叶维廉“超媒体美学”个案研究的典范,即不在狭义的范围内讨论艺格的相互转换,而是以一种历史整体性的观点去寻根溯源,最终目的还是寻找中西文化的共同规律。无独有偶,当代文艺理论界也往往选择以跨艺术理论来解读《诗章》第49首,比如欧荣在文章中就借此来探讨ekphrasis的界定与翻译问题,认为这种“艺格符换诗学”让我们注意到“不同艺术媒介之间持续、动态的相互影响”,体现了艺术的“永恒运动”。[26]台湾学者刘纪蕙将这种现象称为“跨艺术互文”,即是要探讨“不同艺术符号并置时,会呈现什么形式的符号系统差异,而此差异又会产生什么‘诠释上的问题’”。[27]这些理论的介入都极大拓展了《诗章》第49首的诠释空间,带来诸多新的研究思路。
四 结论
综上所述,叶维廉有关“诗画相通”的理论阐释始终坚持着一种中西交汇、古今贯通的视野,在强调媒介平等的基础上由诗、画两个视角共同切入,以突破固有艺术规位与开拓新的美感领域为使命,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一直延绵至今,并在与时代思潮和文学脉络的持续共振中愈加体现出鲜明的体系性和独特性。
对于“诗画相通”美学视境的探讨作为叶维廉“超媒体美学”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出位”“换位”的过程中不断寻找艺术媒介表现的张力,要求艺术家既能够清楚地辨识各种媒体自身的审美特质和表现性能,又能够突破僵硬的媒介限制,以一种媒体融合和超媒体的态势去达成艺术表现的突围,由此带来更多的理论思考和审美可能性。所以一方面,叶维廉在创作中常以中国传统山水画和西方印象画派的表达技法来提升现代诗语言的视觉效果,深入符号表意机制的内部去探讨诗画两种媒体相互交融的可能,也往往通过“诗画互文”“文图互涉”等形式的实验来寻求艺术媒介表现的张力;另一方面,叶维廉一直强调“诗”与“画”的媒体本位,这是二者得以区分、获得独立性和合法性的基础——尤其是在跨媒体、新媒体艺术的创作与研究呈现为一种“井喷式跃进”的当下,这一点无疑具有着强烈的警示作用。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