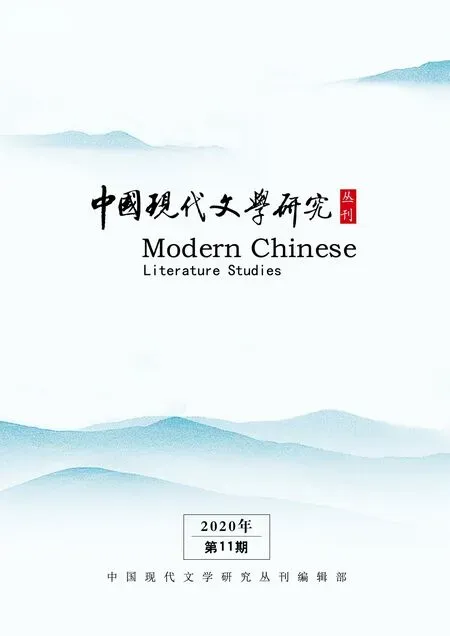近代“自然”的产生与早期新诗的兴起
内容提要:抗战前后,在一系列的总结文字中,朱自清充分注意到了早期新诗中的“自然”因素,这并非叙述视角的后设,而是来自新诗发生现场的深刻体验。近代“自然”的产生与早期新诗的兴起共同衍生于近代以来打造现代主体的思想脉络。由此,作为方法策略、主题内容,“自然”不仅在新旧争辩中为新诗建立合法性基础,也涉及现代抒情方式的建立以及现代诗意机制的产生。对于早期新诗而言,借助于“自然”的观察视角,一方面能够捕捉新诗自身的成长轨迹;另一方面,在“形式的政治”的审美逻辑之中,早期新诗的兴起也指向了一种历史现实与主体自我的生产。
1935年8月朱自清完成了《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的写作,勾勒早期新诗整体发展面貌的同时,朱自清也从细部注意到了早期新诗中的“自然”因素。①抗战时期,在延续此前思路的基础上,朱自清对“自然”作了更为整体性的判断和整合。②这其中,既涉及早期新诗的内容构成,也关系着早期新诗的音节问题,更与新诗的写作机制、动力来源密切相关。而这些认知判断并非来自一种后设的叙述视角,而是其身临新诗发生现场的切身体会。③换言之,对于早期新诗而言,“自然”不仅不是一种强行闯入的外在视角,反而是一种更为内在的路径方向。
近代以来,在救亡图存的时代氛围中,“新民”“立人”的主体吁求,弥漫在不同话语力量的思想方案之中,对一种现代主体的打造一时间成为各方不谋而合的思想共识。在众多的思想方案中,一条“鼎革以文”的实践思路也隐现在其间。早期新诗的发生就衍生于此一脉络。与此同时,在从“天下”到“世界”的视野转变中,东西之间开始接触、碰撞、融合,西学作为“他者”不仅成为观照自我的一种有力的批判力量,更作为“方法”参与到不同的建设方案想象之中,这不仅包括知识结构、生活方式等外在框架的更替,心理习惯、情感伦理、思维方式等与自我想象密切相关的内面精神的再造也暗含在其中。近代的“自然”就产生于此一过程之中,“自然”的近代性意义也由此获得。它既有物质实体的一面,也意味着主体的自发性,同时还包含万物的本性、法则规范等意义层级。④
在“新诗”与现实、历史与形式之间,“自然”作为一个流动的概念,实际担当了游走于内外之间的一个观察视角。因为,无论是草创的“新诗”还是主体自我,二者并没有形成一种成熟完整的理想形态,而是共同处于现代性的开端,分享着共同“成长”的历史位置。对于二者而言,“自然”既作为内容构成,也关乎形式创造,更重要的是“自然”本身的规定性还设定着一种形式与内容有机统一的审美标准,这些对于草创的新诗而言无疑是相当重要的。借助于“自然”的观察视角,一方面能够捕捉新诗自身的成长轨迹;另一方面,在“形式的政治”的审美逻辑中,早期新诗的兴起也指向了一种历史现实与主体自我的生产。
一 “自然”的近代性
“自然”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本身有着完整的语义谱系和思想内蕴。一般认为,“自然”一语,最早见于《老子》:“夫莫之命而常自然”,“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⑤按照沟口雄三的理解,“自然”概念的起源在于万物的本性,自我生成、自我运动,因而也意味着法则性。⑥而在两汉,“自然”开始与“理”相关,并且推演至世俗领域,强调秩序观念,郭象的《齐物论》注云:“故知君臣上下,手足内外,乃天理自然。”⑦魏晋时期,与名教相对,“自然”出现了内在化的倾向,突出人的性情本性,《文心雕龙·明诗篇》曰:“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⑧在此基础上,随着山水诗的兴起,“自然”也逐渐蔓延为一种诗美标准。《文心雕龙·定势篇》又云:“夫情致异区,文变殊术,莫不因情立体,即体成势也。势者,乘利而为制也。如机发矢直,涧曲湍回,自然之趣也。”⑨唐宋之后,“自然”的这些含义作为相对稳定的价值基础逐渐锚定在人们的思想世界。
作为“自然”的对译物,“Nature”在西方世界并非是迥然不同的“异质”。从语源上看,“Nature”来自拉丁文“Natura”,而“Natura”又是希腊文“Φυσιs”的对译。根据柯林伍德的研究,在古希腊,“自然”最早作为与存在方式相关的根源、原则来看待。⑩中世纪之后,在笛卡尔“心物二元”的哲学逻辑中,“自然”经历了由内在性到外在性的翻转,“自然”不仅作为一个实体面目开始呈现,同时也作为一种思想方式参与到文艺复兴之后的主体建构之中。然而物我的分离、身心的割裂,主体不仅陷入机械的人生困境,更丧失了他者的调适机制,不仅主体的统一性难以保持,当主体作为社会构成、民族成分呈现的时候,自我的困境也将扩展成社会、民族层面的问题结构。“浪漫主义”的兴起正是以此为批判基础,“自然”重新回到主体自我的内在视野,作为一种修正,“自然”的有机性、统一性和自由扩展的面相得到凸显,“自然”与自我从主客对立的位置转换到彼此融合的境界。
从比较的视野来看,东西的“自然”起源都与万物的本性密切相关,由此构成作为一种存在方式的伦理学基础。而近代以前,中国的“自然”始终没有发展出物质实体的一面,这是与西方“自然”最为显著的差异,而这一差异不仅影响到东西文明各自的发展取径,更为本质的是对世界图景、全球秩序进行一种新的想象和建构。因为,物质“自然”不仅仅作为一个活动空间和征服对象,而是作为一种思想方式催生了近代的自然科学,开启了工业革命的浪潮。伴随着新秩序的落成,“自然”也逐渐由“物”变“理”,由物质实体沉淀为一种人们普遍接受的思想真理。鲁迅对此就深有感触:“盖科学者,以其知识,历探自然见象之深微,久而得效,改革遂及于社会,继复流衍,来溅远东,浸及震旦,而洪流所向,则尚浩荡而未有止也。”[11]
然而,“自然”的跨语际实践并不是简单的知识旅行。在晚清的翻译情境中,很多情况下,观念双方的亲和性、相似性构成了接受的基础。换言之,在晚清的思想语境,东西之间在知识结构、思想价值层面并非是简单的替换和更新,更多的是一种参照和融合,也可以说是一个“西化”与“化西”的过程。在《天演论》中,严复介绍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时说道:“斯宾塞之言治也,大旨存于任天,而人事为之辅,犹黄老之明自然,而不忘在宥是已。”[12]在对斯宾塞的理解中,严复固有的知识传统起到了相当的促进作用。而在另外一些时候,西方的知识方法则以一种逆向的形式赋予传统知识不一样的体悟视角。在博士学位论文中,胡适就以一种西方的知识视野重新打量先秦的“自然”思想。[13]可以说,时人并不把“自然”作为静态的知识来对待,而是力图在具体的运用方式中激活“自然”作为“力”的一面。在鲁迅早期思想中,“自然”既有物质的一面,但更多的时候,则指向“本有心灵之域”。[14]在此,“自然”不仅作为一种对物质文明的批判,同时以“不伪”的品格更揭示了一种主体自我的打开机制。
以上不难发现,近代“自然”的产生是一个互融互涉的综合过程,“自然”不仅作为知识话语被接纳,更主要的是在现代与传统之间翻转出一种看待世界、想象自我的思想方法。“自然”的近代意义正在于此。正如胡适所总结的:“西洋近代科学思想输入中国以后,中国固有的自然主义的哲学逐渐回来,这两种东西的结合就产生了今日自然主义的运动。”[15]实际上,这不仅是胡适一以贯之的思想方式,同时也是整个五四时期的思想惯习与文化氛围。而在早期新诗的兴起中,“自然”的方法论意义也是新诗的提倡者所不曾忽视的。
二 从“声音”到“意义”
早期新诗的发生,激起了不同层次的心理回应。这其中,既有彻底的攻击怀疑,也有不同方案之间的话语措置,还有相当多的误读和歧义。因而,新诗的展开既是一个相互争辩的过程,也是一个廓清障碍呈现自我的契机。在众多的讨论中,新诗的音节问题尤为典型。据胡适当时的观察:“现在攻击新诗的人,多说新诗没有音节。不幸有一些做新诗的人也以为新诗可以不注意音节。这都是错的。”[16]朱执信甚至认为不澄清音节问题可能会导致“诗的破产”。[17]可以说,音节不仅在新旧之间存在认知落差,就是在新诗内部也存在混沌模糊的解读。因而,讨论音节就不再只是一个形式技术的争辩,作为一种矛盾结构的扭合,音节更主要的连带着新诗能否成立的合法性基础。借助音节不仅可以透视新旧之间历史终结的形式逻辑,更能够清楚辨析新诗成立的思想起点和历史起源。
1919年10月,胡适应《星期评论》之请,完成了《谈新诗——八年来一件大事》的写作,其中,音节问题是胡适讨论的重点。针对音节的误读,胡适提出“自然的音节”的说法,将其看作新诗发展的“趋势”和“公共方向”。所谓“自然的音节”具体包含两个方面:一是节奏依照意义和文法的自然区分;二是,“音”的一面“平仄”“用韵”要自然。[18]在口头倡导之外,胡适更身体力行地参与到自然音节的“试验”中,以期“供新诗人的参考”。[19]此后,“自然的音节”在新诗坛内部迅速蔓延开来。[20]可以说,“自然音节”已经成为当时流行的“自由诗及小诗的根据”。[21]
事实上,胡适“自然音节”的提出并不完全为了回应对新诗的批评和质疑,而更大程度上是衍生于其归国前后对文学革命的整体方案构想。“自然”不仅作为方法,将新诗从新旧纠缠中挣脱出来,建立自身的历史起源和文体合法性,胡适更从文体流变中为新诗设定了新的形式标准。
早期新诗的提倡,并非是一种粗暴的历史生造。在求新的历史态度中,旧诗始终作为一个“他者”埋伏在新诗的自我建构中。因而对于新诗而言,不能将旧诗仅仅作为一种历史的重负和影响的焦虑而加以横切、否定和排斥,更重要的是,作为方法机制的“否定”动作,本身就内含着一种新的历史形象和生成法则。旧诗变革自清末以来已成为一种历史定势,在梁启超看来,“诗界革命”的要旨在于“当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具体来看就是“能以旧风格含新意境”[22]。事实上,不只梁启超抱此看法,旧诗的文质分离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批判共识。在与胡适有关“作诗如作文”的讨论中,梅光迪就明确指出旧诗“只知效其形式”的疲敝。而胡适的思考起点其实也在于此,在他看来,旧诗的“病根在于重形式而去精神,在于以文form胜质matter”[23]。只是胡适对于诗界革命者“矫枉过正,强为壮语,虚而无当”[24]的方法策略并不满意。而任鸿隽“文人无学”[25]的回应虽然更进一步,但仍流于空谈泛论。对于注重实验、讲求效果的胡适来说,一种能够将诗的变革由口头引入行动、由想象转变为现实的方法路径的获得或许更为重要。
在方法方面,胡适并非没有尝试。即便在做旧诗阶段,胡适也抱有清醒的方法论意识:“吾近来作诗,颇能不依人蹊径,亦不专学一家。命意固无从摹效,即字句形式亦不为古人成法所拘,盖胸襟魄力,较前阔大,颇能独立矣。”[26]不同于梁启超仅仅注重意境的新造,胡适在内容与形式之间进行了一种方法的倒置,搁置内容,优先从形式入手。依照他的做诗经验,一旦在形式上突破成法,那么一个“胸襟魄力,较前阔大”的“独立”主体也会在形式的自由流动中被生产出来。可以说,以形式变革为方法是胡适与梁启超、任鸿隽等人最为根本的差异,虽然他们都注意到了旧诗的形式弊病,但梁任等人都将其归结为内容空疏,以求新意境的补足、修正,而胡适则以一种辩证的眼光偏执于形式本身的更新,不仅看到形式对主体的压抑拘束,更从形式的创造中看到了一种主体生产的可能。而形式方法的产生也并非一蹴而就,胡适开始只是注意到诗文的交通、杂糅,而在文学革命讨论最为火热的1916年2、3月间,胡适“思想上起了一个根本的新觉悟”[27],他开始以“自然进化”的观念重新整合整个中国文学史:“一部中国文学史只是一部文字形式(工具)新陈代谢的历史。”[28]依循这样的分析视角,新诗的发生不仅不是无中生造,反而是“中国诗自然趋势所必至的”[29]。不仅新诗被编织进入一种流畅的历史线索,从而制造出历史起源的连贯效果,并且借助进化的思想逻辑,旧诗与新诗也不再只是简单的文体兴替,新旧之间更主要的是一种形式的阶级排序。
而在诸种文体的历史承继中,词曲等最为胡适所看重。从词曲看似连贯流畅的进化趋势之中,胡适抽取出了一种崭新的形式标准——语言的自然。[30]此时,“自然”经历了由外在规律到内在品质的含义内转。实际上,正是“自然”标准的内在设定,以自然本性为目标的文学迁变才呈现了“自然趋势”。不仅如此,当胡适把“自然”与“自由”对举的时候,语言与人格也就发生了一种一元想象的扭结,与旧诗的形式规程相比,“自然”更意味着一种自由的人生境界。因而,所谓“诗体的大解放”的意义,就不只在于具体诗法形式的再造,更重要的是指向了一种新的主体生成方式:“有了这一层诗体的解放,所以丰富的材料,精密的观察,高深的理想,复杂的感情,方才能跑到诗里去。”[31]由此,新诗一方面打通了新旧壁垒、澄清了历史线索,同时,经由“自然”的内外转化,在文学与思想之间也构造出了一种广泛的联结。借助于对“自然”的理解和认同,创作新诗,不再只是一种技艺操练,而是达成自由境界、自由人格的路径、方法和修养。在“自然”的感召之下,新诗迅速由一种文类形式扩展为一种社会参与的方式。这对于过渡时代新的主体方式的生成是相当重要的。
而“自然”由外在规律到内在品质的跃进,或许并非仅仅出于一种历史经验的观察或者一种“历史的文学进化观念”的强制阐释,更大程度上来自胡适自身做诗经历中对于“新”“旧”辩证的深刻体悟。
尽管胡适有了方法工具的自觉,开始采用白话做诗,但这一阶段的实践并不成功。回国之后,胡适曾将留学阶段的新诗“尝试”交与钱玄同审阅,而钱玄同并不十分满意,在他看来“不能和语言恰合”是胡适的问题所在。[32]其后,胡适自己对此也有所反思:
句法太整齐了,就不合语言的自然……音节一层,也受很大的影响:第一,整齐划一的音节没有变化,实在无味;第二,没有自然的音节,不能跟着诗料随时变化。因此,我到北京以后所做的诗,认定一个主义:若要做真正的白话诗,若要充分采用白话的字,白话的文法,和白话的自然音节,非做长短不一的白话诗不可。[33]
在胡适的实际体验中,旧诗的“整齐”不但不是一种形式优势,反而在“言”与“心”之间形成了一种阻碍。“言为心声”,本来“心”构成了“言”的内在能动,支配着“言”的具体形式面貌。但在旧诗的程式中,“言”与“心”发生了地位的颠倒,“心”的自发性在向外展开裸露的同时,不得不受制于“言”的规定和牵制。由“文言”到“白话”的转换,胡适在拒绝一套僵硬的诗法的同时,也为新诗设定了一套崭新的形式标准——“自然的音节”。胡适意识到,新诗不仅需要白话作为工具,在抛却旧形式的同时还需要创造出一种内外有机统一的自然形式。
但在当时“自然音节”的提法并非没有反对的声音。为胡适“改诗”的胡怀琛就曾对音节怎样才算自然提出过不同的看法。[34]在朱执信看来,音节并不能孤立来看,而要力图做到“声随意转”。[35]换言之,声音形式不仅要与意义内容有机统一,更要以作为动力来源的意义内容为主导。胡适虽然从自然音节入手,与旧诗“因声求义”“文质分离”的形式弊病相对,为新诗建立了崭新的形式面貌,并且注意到形式对一种新的主体方式的生产作用,但也陷入新的形式陷阱,在声音与意义之间进行了机械的割裂。任叔永很早就提醒胡适,“自然音节”并非抽象生硬,而是“如人体血液之循环,呼吸之往复,动作寝息之相间”一样,都出于一种生理天性。[36]此后,闻一多不仅批评了“自然音节”对旧词曲音节的机械挪用,同时也将自然音节从形式问题引入诗歌起源的“生理基础”。[37]而这样的思考方向或许并不完全是来自个人的知识积累与视野方法,而是与五四前后一种以“科学”为底色的思想氛围有着整体性的联结。可以参照的是,无论是对父子伦理的批判,还是对现代“人”的整体构想,周氏兄弟都采用生理学的知识方法,以一种生物还原的方式重塑“人”的自然本性。[38]沿着“鼎革以文”的思想线索,这种思路也被周氏兄弟自觉带入文学实践中。在“新生”阶段,鲁迅已注意诗歌“凝为高响,展卷方诵,血脉已张”的生理“热力”。[39]在谈论“口语作诗”时,周作人不仅刻意回避“五七言”的句法和“押韵”的形式,而且强调“只要照呼吸的长短作句便好”。[40]回到早期新诗的讨论,当音节的自然性与抒情自我的生理性基础进行深刻的联结,自然音节的意义就不仅仅是一种抽象的诗歌体制,它更意味着在新旧之间“声音”与“意义”的位置翻转,进而重新建立了语言与主体的意义关联。
三 “自然流露”与早期新诗的抒情
在回忆自己的诗歌生涯时,郭沫若也提到一种以“近代医学、尤其生理学的知识”[41]为基础的诗歌构想,在他看来,文艺的本质在于一种有节奏的情绪,不再只是抽象的文类形式,而是以人的生理学为基础将形式导入为主体的外发行为,在形式与主体之间建立了不可分割的有机统一。以此为基础,对于早期新诗中的音节讨论,郭沫若有着相当不同的理解。
在与《学灯》建立联系之后,郭沫若对国内的新诗动态更为敏感。在李石岑同时主编的《民铎》上,胡怀琛的《诗与诗人》一文引起了郭沫若的注意。胡怀琛借引《尚书·虞书》中“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来解说诗的起源问题,在他看来“诗的重要部分在乎音节”。针对胡怀琛的诗乐杂糅,郭沫若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认为“诗之精神在其内在的韵律Intrinsic Rhythm”,而所谓“内在的韵律便是情绪底‘自然消涨’”。[42]
相比于胡怀琛对诗的“声律”这一外在形式的看重,郭沫若更在意形式的内生机制。换言之,形式虽然以声律现象为表征,但并非就等同于声韵的机械杂凑、拼补,而是有着自身内在的发动机制,它是诗人内心情绪“自然消涨”的显影赋形,正是情绪而非形式决定了一首诗的生成。由此,郭沫若将早期新诗讨论由“声”的形式层面引入“心”的内在维度。以此为据,诗歌的形式与内容、言与心就不再是内外之间、物我之间、主客之间的分离和对立,而是因共享同一的内生机制而呈现出统一连贯的一致性。
而如果将“内在韵律”的看法扩展来看,那么,郭沫若对胡怀琛的批评就并非是偶然为之,而是内在于他自身一以贯之的思考脉络。在留学生与新诗人的身份转换之间,宗白华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他不仅从此前积压的诗稿中发现了郭沫若,更以交谊组织的形式在他、郭沫若与田汉三人之间制造了一种紧密联结的诗歌讨论氛围。[43]在宗白华的记忆中,把他们三人扭结在一起的既有“兴趣爱好”,也有知识基础,更有共同的时代经验、心理感受,这些不仅共同造就了他们的情感联系,实际上也构成理解他们诗歌经验的重要方法。对于郭沫若的诗,宗白华评价道:“你的诗是我所最爱读的。你诗中的境界是我心中的境界。我每读了一首,就得了一回安慰。因我心中常常也有这种同等的意境。”但在这种诗歌认同中,宗白华也产生了一种困惑,就是虽然偶有意境感觉,但“得不着名言将他表写出来”[44]。换言之,在“诗的冲动”与诗的完成之间,宗白华缺乏一种有机的转化,如他所说,虽偶有“诗的冲动”,但“不能得着有机的‘形式’(亚里士多德 Form)化成活动自由的有机生命”,因而“正是因为‘写’不出,所以不愿去‘做’他”。[45]因此,宗白华“无形中打消的诗稿”并非因为他完全缺乏诗歌能力,而是对一种有效的写作机制的建立抱有迟疑。为了打消宗白华的顾虑,郭沫若结合自己的做诗经验作了宽解:
我自己对于诗的直觉,总觉得以“自然流露”的为上乘……亚里士多德说:“诗是模仿自然的东西。”我看他这句话,不仅是写实家所谓忠于描写的意思,他是说诗的创造贵在自然流露。诗的生成,如象自然物的生存一般,不当参以丝毫的矫揉造作。我想新体诗的生命便在这里。[46]
郭沫若认为,诗的生成在于情感的“自然流露”,依靠“自然流露”的抒情方法,在情感与诗之间建立起了一元的勾连想象。而“做”则意味着偏离情感的本真以至于“矫揉造作”。因而,只有“自然流露”的诗,才是“真诗,好诗”。可以说,“自然”在这里不仅关系到一种抒情机制的建立,同时也与一种新的审美标准相关。五四前后,就业、升学、恋爱、家庭等诸多问题的叠压,给青年造成了“苦闷”的心理态势,自杀在当时成为一种典型的社会现象。因而,一种及时有效的抒情方式的建立,对于青年疏通自我、整理心态相当重要。而“自然流露”的意义在于,抒情自我可以借此将内心郁结直接以诗的形式加以抒发。对此,汪静之就有很深刻的体悟:“我极真诚地把‘自我’溶化在我底诗里,我所要发泄的都从心底涌出,从笔尖跳下来之后,我就也慰安了,畅快了。”[47]在他的经验中,真诚的自我、情感的丰沛不仅构成了诗的内容,也产生了有效的抒情方式,而情感一旦经过诗的表达,一种“慰安、畅快”的崭新的主体感受也会被生产出来。对青年关注颇多的鲁迅就从汪静之的诗里读出了“自然流露”的抒情方法,得力于此,一种“天真清新”的阅读感受也由此产生。[48]换言之,“自然流露”不仅作为抒情方法为内在自我提供外向展开的发泄契机,更重要的是情感经过诗的重新编织,也为青年重新赋予了一种新的心灵秩序和自我形象。
对于郭沫若而言,“自然流露”也并不完全出自知识想象,他的个人生活和阅读体验或许与此关系更为重要。1923年,泰戈尔决定访华事宜,郭沫若此时也参与到这一事件的舆论氛围中,并由此展开了对留日时期阅读泰戈尔的一段回忆,与泰戈尔的遭遇,就像“探得了我‘生命的泉水’”。而在具体的“捧书默诵”中,“时而流着感谢的眼泪而暗记,一种恬净的悲调荡漾在我的身之内外,我享受着涅槃的快乐”。[49]
而此时是郭沫若“最彷徨不定而且最危险的时候”。自杀、出家等消极的想法占据了他整个身心。这在当时留日学生中并非个例,人生意义的丧失可以说是一种普遍的心理危机。虽然哲学宗教也被郭沫若当作修养方法拿来试验,但相比之下,诗歌的共情机制更为有效。在泰戈尔的诗中,郭沫若的内心苦闷很快得到纾解,并迅速从中读解出了“生命认同”。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在“捧书默诵”与“流着感谢的眼泪”之间,实际上暗含着的是由诗歌到身体、由文入心的一元感受机制,它直接触发了阅读者的情感流露,内在自我也由此经受了涅槃的新生。而这种自然流露的阅读感受也自觉地被郭沫若纳入做诗的方法尝试中。《地球,我的母亲》的产生就是如此,“诗兴的袭击”“感受着迫切”“诗的推荡,鼓舞”这样一种近乎“发狂”的状态触发了抒情的机关,而随着诗的生成,“自己觉得就好象真是新生了的一样”。[50]
写作的过程与阅读泰戈尔的过程有着相似的体验,诗的产生完全没有技术、情感的障碍。相反,难以自抑的情动不仅首先落实为一种身体触着,情感迫切的强度更使得抒情自我以“写”的方式在纸上自然地呈现出来。随着情感表达的完成,不仅自我获得了“新生”的主体感知,事实上,诗的形式也在这一过程中被构造出来。
《地球,我的母亲》全诗共二十三节,每节四句,在形式上,每节都以“地球,我的母亲”的呼语起首,进而每节都以“我……你……”或者“你……我……”的句式将抒情自我与“地球母亲”编织进一种互动关系中。整个抒情节奏围绕着抗拒虚无、确证自我的成长线索层层推进。前四节首先呈现“摇醒”后的“我”对“地球母亲”安慰的感知和感激;五、六、七、八节写对“农人”“工人” “草木”“动物”这些地球上实有存在的“羡慕”;之后六节表现对“缥缈的天上”等“虚影”的怀疑拒绝,对“实有性”的追求确证;十五节至二十一节抒写感知“深恩”后的“我”如何借助物我的一元想象,与“地球母亲”进行情感的承接、转化;最后两节呈现最终的抒情效果,“我”经由“地球母亲”的感化,经历了“成长”和“新生”,并将感化施与他人。整首诗有着明确的抒情方向,而正是呼语与重复的句式为诗歌确立了连贯的时间指向,在时间的层进中,抒情自我完成了脱离虚无、确证自我的成长历程。而这并非是抒情自我的主体自发性,而是来自“我”在不断呼唤中对“地球母亲”的感化。呼语通过不断的情感复沓使得“地球,我的母亲”这一超验的他者不断作为生命母体显形在场,在为“地球”赋予一种客观实在的同时,“我”的“实有性”也从它的“证明”中被构造出来,此时的“实有”不再是抽象静止的,而是像“劳动”一样被赋予了生命动作。由此,“新生”的自我不再满足于自我封闭,而是以“内在的光明”向外扩展、触着、关怀,从一种精神实体进而转变为一种社会实体。至此,不仅自我的虚无感受得到了有效表达纾解,一种更为开阔的具有实感体验和方向轮廓的主体感受也被生产出来。而呼语的意义还在于,随着“新生”过程的完成,诗的形式也在连贯流畅的抒情节奏中被塑造出来。对于郭沫若来说,“自然流露”不仅构成了他的抒情方式,同样也设定了他的形式风格。与《地球,我的母亲》相比,《凤凰涅槃》有着相似的抒情方法,只不过诗的生产不再仅仅指向自我的“新生”,而是指向了更为庞大的历史现实——“中国”。由此看来,形式并不完全是诗歌内部的技术生产,它还是能够生产主体、制造现实的“政治”手腕。而这些都依赖于一种“自然流露”的自发性机制。
在三人频繁通信之后,1920年5月底,宗白华赴德留学。而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宗白华开始了“流云”系列小诗的写作,有意味的是,他的“写诗的冲动”,与郭沫若的“自然流露”有着相似的经验成分。据他回忆,不仅时常感到“被一种创造的情调占有”,而且“有许多遥远的思想来袭我的心”,使得“一颗战栗不寐的心兴奋着”。[51]而诗的装置的开启事实上就蕴含在这种“罗曼蒂克”的氛围中。借助浪漫的情感想象,心、自然、人类之间实现了相互转化、打通,由此,自我不但被编织进入一种有机的生命节奏,并由一种连续感流畅性的获得而呈现出情感的自然流露。尽管宗白华身处德国古典哲学氛围,与浪漫派、歌德等产生深刻的思想触着,但结合此前的通信讨论,宗白华从“写不出”到“写得出”的转变,与对《三叶集》这一经验共同体的知识、情感进行接受、吸收、内化也并非没有关联基础。事实上,小团体、小组织的知识分享、情感交流恰恰是五四前后青年普遍的联结方式,而社会改造也以此为切实的行动起点。[52]
辩证来看,宗白华在讨论中对“自然流露”并非是机械接受,而是有着相当敏锐的批判反思。前面提及,“自然流露”将诗的写作由形式障碍深入内在情动,强烈的情感构成了诗的展开基础,为了达成抒情的流畅自然,势必要在形式上借助于复沓的呼语、雷同的句式。也就是说,无论是形式结构,还是抒情节奏都极易以一种单调、直白甚至是浅薄的面貌出现。因而,宗白华对郭沫若委婉告诫说:“我觉得你的诗,意境都无可议,就是形式方面还要注意。……还欠点流动曲折。”[53]进一步来看,这样的抒情手法对于思想无定、内心动荡的五四青年来说,固然容易接受,进而能够从中总结出方法路数,实现由读者到作者的身份更新,扩大新诗的社会生产效果。但从另一面看,单调浅露也极易造成模仿的弊病,不仅让新诗重新陷入一种抒情格套中,主体的能动性也会因为浪漫的过度消费而呈现出自溺、停滞的无效状态。这也成了1920年代新诗扩张过程中的问题根源,进而掀起了一种普遍性的浪漫批判。[54]而宗白华所谓“流动曲折”不但指向了形式改造,对一种更为理想的主体形态的呼唤也包含在其中。作为回应,郭沫若意识到了做诗与做人的互文关系:“我的诗形不美的事实正由于我感情不曾美化的缘故。我今后要努力‘造’人,不再乱做诗了。人之不成,诗于何有?”[55]这就提示着,无论是作为文类的新诗还是作为主体的抒情自我,在当时都还不具备独立成熟的自足性,二者之间是一种相互生产相互塑造的辩证关系,都需要一种持续的修养机制。
四 “写景”与现代诗意的产生
有关“自然流露”的讨论很快在新诗人中间扩散开来,作为经验反思,将做诗与做人进行一种整体性的观照成为普遍的共识,一时间,“修养”“源泉”[56]等字眼弥漫在新诗讨论的风气中。由此,在“写”与“做”之间,新诗也开启了新一轮的改造尝试。[57]这种批判反思并不局限在新诗内部,在具体的社会改造环节,人格修养、生活历练也是相当重要的成长步骤,在这种思想氛围中,“到民间去”“到社会去”“到自然去”成为青年统一的行动方向,它所要求的不仅是一种静态的内在提升,更重要的是一种向外的敞开与动态的触着,是主体在内外之间的相互激荡。回到新诗的内部来看,由“写”到“做”事实上也分享着相似的改造逻辑,“做”意味着,诗的生成不再仅仅满足于主体的自发性,而是把抒情主体放置在内在修养与外在展开的恒动过程中加以看待,这样一来,诗的重心就不再是一种流畅的抒情,它的关注焦点调整为一种过程性的凝视,注重主体如何处理现实,现实作为经验感受如何回收到主体的情感想象。在这一调整过程中,“写景诗”能够“发达”起来[58],成为一种“风气”[59]就并非偶然。因为写景不仅仅是简单的观看与复刻“自然”,它具体表现为内在心理与外在物象从感应、吸收到语言的转化。在新诗与自我、形式与主体之间,风景实际充任了它们的转化机制。换言之,风景的生成恰恰也是主体打开、诗意生成的过程。
在中国诗歌史中,写景有着清晰的脉络谱系,可以说是蔚为大观。在梁实秋看来,“中国诗里叙事的特少,写景的特多”,但是“中国山水诗所表现的只是一种意境,一种印象,一种对于实际人生之轻蔑”。[60]而对“意境”“印象”的过于执着,势必造成客观实在的感受体验的偏废,及至物我分离,写景流于知识概念的推演、形式规定的套用。这也构成了新诗人对古典写景批判的原因。其实不独诗歌,小说中也存在类似的状况。胡适认为:“描写风景的能力在旧小说里简直没有。”原因不仅在于缺乏“实物实景的观察”,以辞藻充数,更重要的是描写语言的程式化,缺少与实景对应的语言创造。[61]因而在文学革命的方案中,胡适尤其“注重实地的观察和个人的经验”以及“描写的方法”。[62]
在早期新诗中,描写事实上构成了相当重要的技术标准。在胡适所推重的新诗人中,康白情、俞平伯都是以描写见长。[63]在《草儿》评论中,梁实秋固然批评甚多,但也坦诚“写景是《草儿》底作者所最擅长”,称赞其“描写的功夫,可谓尽致了”。[64]在一批新诗人的写作带动下,“写景”很快形成了一种风气。但从风气之中,胡适也清醒地读出了写景的“流弊”:“最容易陷入‘记账式的列举’。”[65]换言之,描写虽然通过直观创造出一种实感与真实体验,但单调的描写只能让写景止步于物象的罗列、并置,诗意的生成在技术手段之外则需要更为复杂的转化方法。胡适之所以赞叹《庐山纪游》的“伟大”,在于他从康白情综合的形式风格中把握到了外在风景与内在自我相互激发、彼此调动的复杂情调、曲折意味。也就是说,写景并不单单需要细腻的技术刻画,风景意味的产生更有赖于主体的能动机制。
对写景的不满在一批更年轻的新诗人那里激起了更多的反思和讨论。在他们看来,自然不仅是一种内容构成和视觉呈现,如何写景更关系到对诗的理解和理想诗歌形态的构想,关系到诗的生成及现代诗意是如何产生的。在给杭州一师的学生李无隅的诗集《梅花》作序的时候,朱自清对其中写景诗的评价是“融情入景,并非纯摹自然”,又说“这可见他的心时时有所系了”。[66]在“融”与“入”之间,朱自清已经暗自设定了“情”与“景”的地位,在理想的诗风中,情与景并非并置对等,相比较而言,景更像是情的显影,以此内在的情感能够以自然作为形象被呈现、赋形,由抽象变得具体、可感,但此一过程又在根本上受制于情感的主观意愿,“心”既是情动的起点,同时也是诗意生成的落脚点。
如果说上述观察还只是专业视角的外在切入,那么,朱自清对俞平伯的评价则要更加体贴精细。在《冬夜》序文中,朱自清就注意到俞平伯与当时流行的写景方式保持距离:“他虽作过几首纯写景诗,但近来很反对这种诗……平伯要求这迫切的人的情感,所以主张写景诗,必用情景相融的写法。”[67]朱自清所说并非虚言,对于写景,俞平伯确实有过清晰自觉的转向,在给新潮社的信中,他谈道:
我现在对于诗的做法意见稍稍改变,颇觉得以前的诗太偏于描写(Descriptive)一面,这实在不是正当趋向。因为纯粹客观的描写,无论怎样精采,终究不算好诗……诗人的本责是要真挚活泼代表出人生,把自然界及人类的社会状况做背景;把主观的情绪想象做骨子;又要把这两个联合融调起来集中在一点,留给读者一个极深明的Image,引起读者极沉挚的同情。所以我并不反对做描写自然界的诗,我是反对仅仅描写自然。[68]
数月之后,在《草儿》的序中,俞平伯又重复了类似的看法,主张以“反射的”(reflexive)代替“描摹的”( representative)[69],在自然与自我之间强调情感的综合作用。一方面,抽象的情感需要附着于物质的自然进而显露自身;另一方面,情感的主观性也会对自然的无机、杂乱进行有机的想象、重组和塑造,借助于形式生产出新的形象。写景的转向不只停留于思想言论,俞平伯更将这些思考积极贯彻到这一时期的新诗创作中。在转向后的写景诗中,朱自清对《凄然》一首颇为看重,认为《凄然》是情景相融运用最成功的例子。[70]即便是对《冬夜》大加批判的闻一多也坦诚《凄然》“是上等作品”“完美的作品”。[71]
1921年9月30日,由苏州返杭之后,俞平伯写作了《凄然》。在诗的开头有一段小序交代了写作的背景起源:
今年九月十四日我同长环到苏州……夫寒山一荒寺耳,而摇荡性灵至于如此,岂非情缘境生,而境随情感耶?此诗之成,殆由文人结习使之然。[72]
在本事之外,这里也提供了一条“情缘境生,境随情感”的解读思路。全诗共四小节,大致以风景的视角转换进行展开。“文人结习”的自白粗看上去似乎并不脱古人已有之境,但在诗的开头,首先就以一种疑问的口吻将“古人”或者说历史排斥在纪游的现场之外,“哪里有寒山!/哪里有拾得!/哪里去追寻诗人们底魂魄”。 而这种历史感的丧失恰恰来自“失意”的现实所制造出的心理落差。不仅如此,“诗人魂魄”的无迹可寻更暗示着古典诗法的失效,由此,诗的展开就不只是风景的内容填充,这中间更关系到一种现代诗歌制度的生成。“失意的游踪”意味着对现实的不满,进而产生构造新的现实感的倾向,而“低徊踯躅”则将这种倾向由现实表层纳入抒情自我的内在空间,由此设定了现代诗意的起点。次节中,由“明艳的凤仙花”到“染红指甲”的“姑娘”,透过色彩的转接似乎产生一种调和的趋势,“掐”字透露出将“过去”切分的可能,但诗人并不耽溺于幻想以求快速脱离“不可聊赖的情怀”,而是又以疑问的口吻回应着情感的真实。在下一节中,这种“不可聊赖的情怀”不仅投射于“粉墙”“游廊”的物质表象,更借助于“剥落披离”“欹斜宛转”“陂陀”的体态形容呈现出曲折的感官。在进一步的铺叙中,静态的风景逐渐被“西风”的搅动所代替,在静动衔接中“西风”开启了由景及人的打开机制,由此风景的形态开始与“一双游人”的“摇落的心肠”接合,曲折也从一种感官深入情感内在。最后一节,“西风”的震荡作用被具体呈现,巧妙之处在于,这一过程不再投射于具体的风景,而是从听觉上借助于“镗然”“嗡然”“殷然”三个拟声词加以表现,不仅丰富了写法和抒情节奏,更贴合了抒情自我的情感真实。因为由上述的叙事内转,“游人”的情感重心逐渐从风景物象回收到内心世界,而此一过程的抽象情感对于如何表现有相当的难度。而当自我沉浸于内在空间的同时,势必发生一种感官的切换。因而,由视觉到听觉的转换,并非是生硬的诗歌技艺,而恰恰是以生理规律为意识基础将自我内转的过程以一种可知可感的方式呈现出来。进一步来看,诗的抒情指向并未到此为止,在大量写景的基础上,抒情笔触开始渐及人——“枫桥镇上底人,/寒山寺里底僧,/九月秋风下痴着的我们”。如果联系到“西风”的震荡以声音的形式激起的“依依荡颤”,那么“人”“僧”“我们”就不仅仅是身份之间不相关的并置,而是由此构造出了一种普遍性的命运关联。更为开阔的视野在于,诗人不满足于这种横向关联,而是在“寒山寺”与“旧时寒山寺”的比照中开辟出一种历史纵深,将“荡颤”的命运由一种社会生活引申为一种历史现实。并且,疑问的语调在与开头形成结构上的呼应,创造出一种完整的形式效果的同时,疑问的反复进而又将这种认知推演为一种不可知的境地。如果说按照俞平伯自己的陈述,《凄然》一诗“殆由文人结习使之然”,那么,所谓“结习”并非是古典的抒情套路、陈词滥调,而是一种深具历史感、命运感的生命感知和灵魂考问。如果将《凄然》的写作扩展开来考察,那么“触景生情”的“结习”或许能够得到更为充分的解构。
实际上,在写作《凄然》的前后,俞平伯还完成了《生活底疑问》[73]一文的写作。如果对《凄然》采用疑问语调的写法抱持警醒,那么不难看出二者之间深刻的互文关系。从主题上看,《生活底疑问》的意义构成并不复杂,与《凄然》其实分享着相似的讨论中心,即如何修养一种“有价值的生活”。由此反观他诗的写作,不难判断《凄然》并非是“触景生情”的“偶得”,而是有着相当深刻的情感积累和生活思考,因而“疑问”的抒情姿态既是对生活意义感的回应,也是一种心灵方案的构造。这不仅为《凄然》设定了一种现代的情感动力和思想底色,更在景与情的相互辩证中呈现了一种现代诗歌机制是如何生成的。
在柄谷行人的研究中,正是“风景的发现”构成了“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在日本古典时代的汉文学传统包括山水诗画中,风景的生成并非来自一种客观性的物质实感,而是先验地存在于“宗教、传说或者某种意义”等价值系统中。而现代风景恰好与此形成一种“颠倒”,它以自然的客观实体性为基础,要求一种实际的观察和在场的体验。[74]因而,风景的生成也连带出内面主体的显影。换言之,“文学”的“现代”起源并不完全是“风景的发现”,更主要的是内面自我的产生。在分析西方“自然史”的兴起时,福柯也采用了类似的思路,将生物从一种既成的语言体系和意义结构中分离出来,以“线条、表面、形态、立体感”等能够呈现生物客观本性的“标记”方式,赋予生物一种物质实感。这不仅确立了“自然史”的现代起源,同时也以认识论为基础,产生了“一种真正的语言”。[75]由此观照早期新诗中的“写景”,它不再只是题材分类与内容组织,风景的“颠倒”及其呈现,在语言的重新叙述中构造了现代诗歌的结构和诗意机制,由此,一个具有内在深度的抒情主体也被生产出来。
结 语
近年来,有关早期新诗的研究呈现出将其与“五四”关联起来进行一种整体性观照的研究趋势,从方法上来看,对以“审美”“内部”为讨论重心的研究范式进行了适当的偏移,在把早期新诗作为一种历史生成的现实结构的同时,也激活了更为丰富的讨论空间。但需要警惕的是这也预设了一个历史起点,将早期新诗的发生锚定于“五四”的历史现场。然而,如果将早期新诗的兴起进行一种视野的拉伸,那么,在一种现代文类的升沉起伏以外,早期新诗更内置在一种更为庞大复杂的思想氛围、知识背景之中。清末以来,在不同的改造方案中,对一种现代主体的构想和创制成为统一的理想目标。而主体自我并非是机械抽象的,它既需要充分的知识能量和思想支援,也要求一种发现内在、对主体进行不断更新和生产的表达机制。近代“自然”的产生和早期新诗的兴起都是对这一主体构造的某种回应。而“自然”的近代性并非只是简单的“拿来”“移植”,因为西学东渐并不仅仅是殖民动作,在“学”与“渐”中所翻转出的是一种方法借鉴、更新思想的眼光与心态。因而近代“自然”既保留了本性、自为的传统意义,也历经科学思维的塑造增添了物质空间的实体面向,进而发展出现代风景的内涵。在早期新诗兴起与现代主体想象之间,作为一种勾连机制,“自然” 不仅作为内容构成,也作为话语策略参与到新旧争辩中合法性的获取,同时它更关系到早期新诗抒情方式的建立以及现代诗意的生成。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