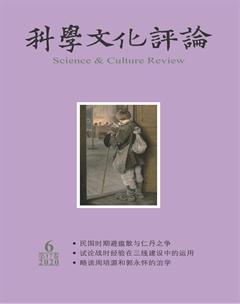《天文学史》中亚当·斯密的科学方法
赵泽铭
摘 要 斯密《天文学史》中有三个与科学观相关的问题: 科学研究的动因、天文学体系的评价以及天文学体系的演变。斯密在《天文学史》中使用了最佳说明推理的科学方法,将科学研究的动因归于名义上的“想象力”,实质为人类的逻辑和推理能力; 斯密对天文学体系的评价需检验其与经验和逻辑的符合程度; 斯密对天文学体系的变化的认识和库恩具有相似性。斯密通过对天文学体系的演化进行分析,构建了一种将哲学和科学相结合的思想体系,作为斯密在休谟之后关于“人性”的哲学体系的理论基础。
关键词 亚当·斯密 天文学史 最佳说明推理 想象力 范式
一 从自然哲学中提取道德哲学推理规则
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主要以其在经济学领域的贡献而为人知晓,但是斯密对学术界的贡献不止于此。除了经济学之外,斯密还涉猎自然哲学、道德哲学、伦理学、修辞学、自然科学、数学、文学等多个不同的学科领域。尤其是他的青年时期作品《天文学史》更是构成了斯密的思想基础,贯穿他的整个学术生涯[1]。斯密的经济学体系本质上和他对天文学体系的思考存在一致性。斯密认为天文学史上各体系在效果上是对经验现象的描述和解释,而斯密的经济学体系指向经济现象。方法论层面上,斯密经济学体系的构建和天文学体系的构建都符合牛顿主义的特征,用尽可能少的理论描述尽可能多的现象。此外,斯密的经济学体系和天文学史上的体系一样,都运用了数学工具对现象进行拟合和分析。方法论层面上,斯密和此前的天文学家们探索现象背后的理论的过程都采用了最佳解释推理(IBE)的模式。
《天文学史》(History of Astronomy)全名《天文学的历史——以天文学的历史为观照,论引领并指导哲学研究的诸原则》(The Principles Which Lead and Direct Philosophical Enquiries, Illustrated by the History of Astronomy),收于格拉斯哥版《亚当·斯密全集》的第三卷《亚当·斯密哲学文集》(Essays on Philosophical Subjects)中。与《道德情操论》(1759)和《国富论》(1776)这两部在斯密生前就已出版的作品不同,《天文学史》是在斯密逝世之后由后人进行整理和编著的。1795年,斯密去世5年时,由斯密生前的好友约瑟夫·布莱克(Joseph Black)和詹姆斯·赫顿(James Hutton)主编的《哲学文集》出版; 但《天文学史》的写作年份则早于上述两部作品,属于斯密学术生涯的早期,初稿作于1746—1748年之间,最后关于牛顿的部分则在1748年后的数年间不断增删修补,直至去世都未能完成。
正如《天文学史》的全名所示,斯密曾经试图通过《天文学史》的撰写探究哲学研究的一般原则。在斯密所处的时代,“道德哲学”包括后来社会科学的许多门学科内容。斯密在格拉斯哥大学讲授的道德哲学课程内容就包括了神学、伦理学、法学和政治学四大部分,其中政治学又包括当时所称的“政治经济学”。
起初,斯密曾计划分门别类地写出“道德哲学”细分领域的全部内容,揭示作为自然的人和作为社会的人的本性,揭示人类生活的目的、过程和形态,并在道德哲学领域内构建一个堪比牛顿体系的综合性思想体系。 这一点可以从斯密《法理学讲义》《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的撰写中得到证实。为了实现这个宏伟的构想,斯密在《天文学史》中先行阐述他的哲学和方法。与后世实证史学框架下的学科通史不同,斯密《天文学史》不是探讨一个个特定的天文学发现,而是探讨“天文学体系”的形成与发展的智力过程。斯密针对天文学体系的产生与发展,写出了他个人的事后重构,以致他的学生和传记作者杜格尔得·斯图亚特称之为“推测史”; 而且,恰恰是这样的一部“推测史”,对于对斯密构建其整体思想体系具有重要意义[2]。
斯密写作《天文学史》的真正目的,是要构筑一套关于科学研究的解释框架,指明科学研究的推动因素,概括科学知识体系的构建进程,并将其拓展为道德哲学体系中不同子研究领域可通用的、高度系统化的探索模式。金光述(Kim Kwangsu)对斯密的科学体系总结道,斯密科学知识体系的构建是随着想象力和溯因推理①、演绎推理和归纳推理的思维方式的运用,以及经验世界的形而上学架构和运行机制的构建而得以进行的[3],在这个过程中,科学的公理化进程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二 想象力作为科学研究动因
斯密在《天文学史》中的论述是从科学研究的推动因素开始的。人类的好奇(wonder)、惊讶(surprise)和赞叹(admiration)这三种情感, 在科学理论的产生,也就是斯密笔下的哲学进步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对于这三种现象,斯密在《天文学史》中做出了如下解释:
凡新鲜并令人觉得怪异的事物,都会唤起我们心中那种严格意义上应称作“好奇”的情感;出乎意料之物,会领我们“惊讶”; 而恢弘至美的事物,则会激发我们的“赞叹”之情。……以上三种情感,影响范围远远超过人们不经意间所能想象之极限。([4], pp.33—34)
斯密所提到的想象力与人类智力相关。彼时康德关于想象力的著作遠未诞生,斯密对想象力的认识很大程度上来自休谟的《人性论》中的论述[5]。休谟论述称,人类的经验和观察使之了解到,某种特定类型的事件通常与另一种特定事件相结合。这两个事件之间的持续联系使我们的头脑之中发展出了因果关系的概念。我们认为其必要性并非来源于某个单一事件,而是来自通过相似事件的重复而产生的习俗或是习惯。事件的持续联系和由此产生的习惯,都可以帮助我们得出事物的因果规则,而对现实事物的持续存在的信念与必要联系的观念有着很大的不同。在休谟看来,想象力是人类思想构建因果规则的力量,因此在构建常识的过程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正如休谟所述:
想象中的两种原则: 一种原则是恒常的、不可抗拒的、普遍的,就如由因到果和由果到因的那种习惯性的推移; 另一种原则是变化的、脆弱的、不规则的,就如我方才提到的那些。前者是我们一切思想和行为的基础,所以如果除去了那些原则,人性必然立即要毁坏、消灭。[6]
斯密假设所有人都有着与生俱来的能力和倾向,这些能力包括推理能力、思考能力和想象力,而倾向则体现在人们希望使这些能力达到一种快乐与满足的状态,与此同时避免痛苦和缺憾。这里所称的快乐来自想象力的一种自然的状态,也就是斯密在《论模仿艺术》中写到的:
头脑的所谓自然状态,就是那种既非欢喜又非沮丧的平静、安详、沉稳的状态。这时候,我们思维的步伐显得不徐不疾,比兴奋快乐时的速度要慢一些,各种想法之间的关联性也更显明一些; 但和悲伤消沉的时候相比,它的速度却要快得多,并且内容也更加纷繁多样。([4], p.197)
在斯密体系中,想象力的本质上是人类智力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其作用之一是联结惊讶与好奇。斯密认为人类的想象力具有懒惰的特性,也就是具有从简和从易的特征,换而言之,对于现象背后的原理和机制,大部分人认为其司空见惯,而哲学家们,也就是想象力强大的人,却能在这想当然之间找出问题,找出“惊讶”之所在。斯密写道:
由于习惯力量的支配,思维从前一对象到下一对象的过渡已经如此顺畅自如,它几乎顾不上推想其间是否存在这样的中间环节。([4], p.45)
想象力为观察到的现象、或者现象与现象之间的关系——前面提到的“中间环节”,提供解释。对于通过观察获得的关于世界的经验,斯密认为自然界似乎充满了表面看来与之前发生的一切不协调、不相干的事件,因而干扰了想象力的畅流。当异常现象出现、或是现象以不同寻常的顺序发生时,在原本顺畅的想象力之中就出现了中断,或者按斯密的说法:
想象力在按原来的方向自然流动或运行的过程中,受到了阻断和干扰。在前一事件和下一事件之间……出现了一道缺口或间隔。([4], p.42)
当这种缺口出现的时候,想象力出于它固有的倾向,努力探索能够填平这种缺口的方式,而想象力所寻找的其实是这两个出现缺口的事件之间的“一连串中间事件”,也就是两个事件的因果关系。“一连串的中间事件”存在于两个事件之间,“按照人的想象力已经熟悉的顺序排列,把两个看似彼此脱节的表面现象联结起来”, 从而使“想象力填平上述二者之间的缺口”([4], p.42)。在《天文学史》中,斯密对想象力的使用贯穿了整个第四部分,也就是对各体系的具体评述。
三 斯密对哲学体系的评价方式
斯密最初创作《天文学史》之时,“各部分之间联络最严密,令其它理论无法望其项背”的牛顿体系已经为众人所知晓([4], p.104),故而斯密在《天文学史》中考察的天文学体系是从最早的同心球体系、偏心圆体系开始,直到笛卡尔涡旋体系和当时被视作最为完善的牛顿体系为止。在《天文学史》中出现的体系在今天看来都是天文学体系,虽然牛顿、笛卡尔等用“自然哲学”或“哲学”体系用语。
斯密生活的18世纪,“哲学”和“科学”二者之间并没有明确区分,两者几乎可以互换[7],相应地,“哲学家”和“科学家”也是如此。从知识论的视角来看,科学和哲学可以被视为是“一条智慧探索铁链的两端”[8]。在这条链接上,科学被视为一阶学科,代表着一系列从经验和观察中得出的特定的规律或是法则;而哲学被视为二阶学科,为解释自然现象以特定的形式发生的原因提供智慧层面的原则。斯密在《古代逻辑学和形而上学的历史》之中就哲学写道:
既然这一切(物质世界大大小小的一切变化)都取决于物体的独特本性,那么,哲学作为一门致力于将尘世上发生的所有变化联结成一体的科学,判明每一物质的独特本性所在也就成了它责无旁贷的责任,如此方能预料此种物质可能发生怎样的变化。([4], p.119)
斯密认识到了经验世界和形而上学世界之间的区分,即可观察到的事物为一层,而可观察到的事物背后的“共同性质”,也就是隐藏在背后的性质为另一层;但是斯密并没有在论述中对科学、哲学或是形而上学进行明确区分。斯密并没有像今人那样区分科学与哲学,相反,他区分的是科学研究与形而上学思考,认为两者密切关联。认识到了科学知识的不同层次以及不同层次之间的相互连接,即可感知到事物以及事物背后的不可观察的本质。斯密的哲学思想在《天文学史》的不同体系的论述之中有着集中而明显的体现。
虽然想象力和填平缺口的倾向为所有人所共有,但是探索因果关系却是哲学家(包括科学家)所做之事。对于日常生活中已经司空见惯的、按照一定的次序出现的现象,一般人会简单地说“(这些)现象以这样的次序出现,乃是出于本性”,而哲学家则不同。哲学家们“总是想在全世界都司空见惯的连续事件之间找出隐形的中间环节”——他们“一辈子都在研究环环相扣的自然律,训练有素的思维常能捕捉到两个连续对象之间存在的缺口”,尽管这两个连续对象在一般人看来是紧密相连的。基于这样的理解,斯密为哲学下了一个定义:“哲学就是关于相互衔接的自然律的科学”,并更进一步地指出:“哲学可被视为一种与人的想象力交往的艺术。”([4], pp.45—46)
既然哲學①与想象力有如此关联,如何对哲学体系②进行评价就成为了斯密在《天文学史》中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斯密相比于其它同时期的学者的创新之处,就在于他为不同自然体系的评价所建立的评价标准。正如上文所述,对想象力的关注是斯密《天文学史》写作的核心轴线。按照斯密的说法:
我们且不管它们(自然体系)是否无稽之谈、有多大的或然性,与真理或现实是否相符,只从我们研究课题的特定角度出发来考量它们,只满足于探讨它们各自在何种程度上适于“安抚想象力”。([4], p.46)
一种自然体系,如果与经验现象存在一定程度的符合性,固然能够解释这些与之符合的经验现象,显而易见的是,它对于不符合之处便难以解释了。更进一步地讲,如果先后提出的两种自然体系都可以解释经验现象,那么孰优孰劣又如何评判呢?能否“安抚想象力”(soothe the imagination),是斯密在《天文学史》中提出的一个评价指标,但是这个评价指标本身是多维度的,它的本质是一种IBE的检验模式。斯密检验的不只是某种体系与经验现象本身之间的关系,也就是IBE中所称的可能性维度[9—10],尽管二者之间的不符合可能会导致上文中所说的缺口的出现,从而“干扰想象力的畅流”。斯密的IBE检验,在评价某种科学理论与现象的符合度的同时,还检验了这种理论体系背后的形而上学思想与当时流行以及后世发展出的形而上学体系之间的符合度。同时,斯密还将美学和社会学因素纳入考量,作为对理论体系进行评价的辅助要素[11]。
在对评价体系进行了论述之后,斯密回顾了天文学史上的四大主要体系,即托勒密体系、哥白尼体系、笛卡尔体系和牛顿体系,着重关注这些体系解释太阳、地球和星辰运动(这被认为是天文学的使命所在)的准确历史细节。认识到每个体系之间的不同,斯密对体系本身在论述开始之时做了定义。遵从了18世纪所流行的写作手法,斯密将体系同机器进行了类比。斯密把体系比作“一部假想的机器,它之所以被发明出来,就是要把现实中已经完成的各种运动和效果在想象中连成一体”([4], p.66)。对体系的复杂性,斯密的观念是:
无论是完成何种运动的机器,当它最初被发明出来时,构造通常最为复杂;后续的设计师们逐渐发现,如果去掉几个轮子,再简化其运动原理,这台机器反而更容易地达到原来追求的效果。([4], p.66)
在此,斯密用类比的方式将体系的变化同机器的进步进行了拟合。每个体系在提出之时都有可能不甚完美,以天文学体系为例,不论是天文学中全新提出的体系(如同心球体系、偏心圆体系),还是以已有体系为基础,对其进行革命性的颠覆,都需要经历一个不断完善和简化的过程,直至其最终能够通过“某个特定的关联或原理”对所有的“每一对看似松散的现象”进行解释([4], p.66)。
四 《天文学史》中的体系变化
斯密在重构整个天文学史体系的过程中是有着明显的溯因推理,或者说最佳解释推理的倾向的[11],这也导致了斯密在建构天文学史体系时首先从关于科学探究的一般体系开始。需要注意的是,斯密本人没有建构任何一个天文学体系,而是将他人构建天文学体系的过程或进程,进行了溯因推理式的解说。斯密关于科学探究的一般体系可以根据其具体功能大致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原初体系的建立,也就是通过想象力对经验现象的初始认识; 第二类则是既有体系的改善和演进,这一类解释了体系进行改善的原因和机制。
首先是原初体系的建立。经验现象的积累引发了作为认识主体的人的惊讶和好奇,并导致后者反过来对经验现象进行解释,通过溯因推理(表现为想象力的作用)构建起来一种关于自然哲学的原初体系。想象力在这个过程中起到的作用是在理论体系和经验证据之间的桥接作用。原初体系的建立除了对天文学之外,还对其它学科的经验证据同样有效。新增的现象则很容易导致新分类的产生,正如斯密所说:“我们在知识和经验上越是进步,(上述)种属(species)的数目也就越多。”([4], p.38)
其次是现有体系的改善。区分于原初体系建立时对于想象力的更大程度的依赖,现有体系改善时的主要动因,正如上文所述,既来自体系内部也来自体系外部。斯密的《天文学史》与现代视角下的天文学史的明显区别就是其更像是一部观念史,而非萨顿式的学科史本身,特别是在对经验证据的强调和对数学计算的运用方面[12]。因此,从观念层面上说,体系外部的推动因素更多来自新的现象的发现,以及由此引发的对既有体系的质疑。斯密将此表述为“想象力无法畅流”([4], p.42); 而从体系内部,当体系的复杂性累积到了一定程度(例如同心球体系的72个本轮)时,人们会展开对新的体系的探索,而新的体系一经出现,在理论的顺畅度上就会超越现有的体系,从而满足“想象力”的需求,并最终导致确证和认识层面的真理化。斯密用“想象力”这一人类本性作为“基础和纲领”来指导其“哲学史”不同分支的写作,不能不说是18世纪下半叶的一个独特的创举,并且构成了哲学的显著特征[5]。
斯密《天文学史》之中提到的主要天文学体系可以在原初体系建立和体系改善之中找到对应。斯密并没有过多地考虑技术层面的影响,在写作过程中更多地将天文学观测技术的发展和观测现象随时间的发展视作天文学体系发展背后的一种不具有取向的中立因素,而并没有涉及到观测技术的发展和观测现象的发现是否来自处于争论双方的某一方。這也是斯密的历史写作之中并没有呈现出明显的“辉格”特征的原因之一[12]。
天文学史上最早的体系,同心球体系的建立过程,就符合了斯密式的原初体系建构流程。最早的天文学研究者面对着如何解释日、月、星这三种不同天体运动的问题。将亚里士多德及之前的天文学思想归为想象力的成就,固然可能存在不恰当之嫌,但是对斯密来说,却是一个可以接受的做法。通过这样的方式斯密完成了体系的构建和体系的改善之间的统一,并且之后进一步将其拓展到斯密试图建立起来(而未完成)的道德哲学体系。受制于古希腊的天文学观测水平和对现象的认识,这种更多基于朴素的想象力的体系确实在古代维持了一段时间。而随着经验现象的不断累积,同心球体系被质疑自然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在古代天文学中,同心球体系到偏心圆体系的变化,最开始的目的同样是为了“引入和谐与秩序”([4], p.62)。但是偏心圆体系在得到发展之后,面临着和同心球体系同样的问题,那就是对于整个体系的不断修正导致了复杂度的提升,直到整个体系“尽管可能比亚里士多德的56层天球说更简单,当然也更符合客观天文现象,但它仍然过于复杂难懂,令想象力难以在其中得到完全的宁静和满足”([4], p.67)。斯密在论述到同心球体系到偏心圆体系的变化之时首次引入了一个新的评价标准,也就是说,除了单纯地进行体系内部的完善以满足对现象的解释之外,还将“能否找到这些看似互相冲突的现象之间的一致性”作为另一个对体系的评价标准[5], 即对IBE检验模式的第一次引入。偏心圆体系真正的危机,除了其复杂度之外①,就是“天体的运行在短期内便与依照这一假说所做的最精确的计算产生了相当大的偏差”([4], p.70)。这样一来,偏心圆体系便重蹈了同心球体系的覆辙,并最终被后来的哥白尼体系所取代。
哥白尼体系极好地证明了斯密论述中想象力的作用。与此前的体系相似,哥白尼体系的出发点一样是解释经验现象,但是与此前的体系不同的是,哥白尼体系引入的“机器”更为简洁、需要的“运动”更少。哥白尼体系为人接受的原因除了为现象提供解释之外,还有其“革命性”激起人们的好奇和惊讶,并使得“人们更加喜爱这个体系”([4], p.75)。但是,对于哥白尼体系并未为所有人所接受的原因,斯密认为应当归于体系中地球高速运动这一假说与人类固有意识之间的冲突。换言之,这个简单、连贯、可以解释观察到的现象的体系,在某些人看来,败在使用了一个令人如此不熟悉的理论之上[5]。
但是,哥白尼体系的意义不止于此。在西方天文学史上,哥白尼体系之所以被视为“革命”,就是因为他以日心结构替代地心结构,具有鲜明的反宗教世界观的特征。在过去的一千多年以来,人们已经深深地习惯了宗教世界图景。哥白尼体系的提出打破了这样的宗教文化,因此和偏心圆体系的意义有着更多的不同。哥白尼体系和偏心圆体系,虽然都在某种程度上将旋转的中心从地球上带离,但是它们的意义有着明显不同。偏心圆体系更多地是从数学意义架空地构想了一种对此前天文学体系理解的修正模式,而哥白尼体系,承接了以往的天文学体系,对于现象的解释具有高度连贯性。
斯密认为,在哥白尼体系提出之后的一系列天文学观测支持了哥白尼体系逐渐为人所接受。包括伽利略、开普勒在内的天文学家,从经验层面提供证据完善了哥白尼的理论。斯密重点提及了开普勒对哥白尼体系的贡献,即开普勒确定了“行星以椭圆轨道做非匀速运动”的运动模式,但是却因为“关于匀速圆周运动的先入之见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从而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4], p.87)。然而,即便从经验层面提供了证据,斯密所称的哥白尼体系的唯一阻碍,也就是“地球和其他行星这样巨大而笨重的物体如何能够围绕太阳如此高速地运转”这个问题的形而上学本质,即星体之间的力的相互作用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笛卡尔在这个背景下提出的天文学体系,尽管形式上与哥白尼有所不同,但是事实上为哥白尼体系的接受铺平了道路。笛卡尔以“涡旋”的形式重新引入了以太概念,认为宇宙之中的行星在涡旋的裹挟下运动。古代的以太概念本身已经久存于人类观念之中,笛卡尔的再次提出对于人类的想象力来说无需突破太大的阻碍。想象力一旦接受了这种设定,按照斯密的说法,笛卡尔的体系便将“哥白尼体系中最难理解的部分,即硕大的行星体何以能够告诉运动的问题,带入人类想象力所熟悉的领域”而解决掉了([4], p.96)。
按照斯密的IBE检验模式,哥白尼体系和笛卡尔体系分别对之前的体系进行了科学和形而上学层面的革新,两种体系却又各有各的问题所在。哥白尼虽然引入了公转的概念,抛弃了传统的本轮,但是体系本身的复杂度依然居高不下;笛卡尔则缺乏足够的天文学观测,对天文现象的预测和解释能力不佳。在斯密看来,直到牛顿体系的正式提出,以往的天文学体系之中存在的固有问题才真正地得到相对彻底的解决,没有得到有效处理的就是一直以来困扰着天文学家们的超距作用。关于牛顿体系相比于此前体系的变化,斯密并未给出一个完整的评价,但是在《天文学史》最后的段落中,斯密最着重强调的就是“这些原理(指牛顿体系)不仅极其完美地将此前各个世代所观测到的天文现象全部联结为一体,而且包容了后世天文学家们凭借不懈的努力和更完善的观测仪器新揭示出的更多的天文现象——这些都是以前我们做不到的”([4], p.105)。站在斯密的视角,牛顿体系为所有当时所知的天文学现象提供了一种最佳解释,在一致性方面是毫无疑问地超越此前其他已知的天文学体系的[13]。
此外,值得强调的一点是,斯密在理论体系中的“定理化”尝试,即用一些基本原则来对现象进行演绎的方式是一种明显的牛顿主义方法,特别是在《道德情操论》中[7]。
虽然斯密对天文学的理解在现代视角看来可能还不够完善,但是在18世纪中叶的写作时期,斯密的理解还是相当深厚的①。基于斯密对不同天文学体系的理解,斯密在天文学史,或者说科学史上的值得一提的成就和创举,就是首次将体系及其变化的规律纳入考量[5]。彼时大写的科学革命的说法还没有出现在学术界[14],斯密未能实现基于科学革命视角的反思,但是斯密关于体系的思想和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的范式转换思想在形式上具有相似性。斯密(库恩)关注了一种体系(范式)及其内部的发展(科学的进路),直到其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危机开始出现,之后出现了体系的取代(一种范式被另一种范式所替代);二者的进路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一致性,均在研究天文学史之后提出这一观点,也都认为哥白尼在《天体运行论》的前言中提到的“传统天文学在关于天球运动的研究中的紊乱状态”([15], pp.4—7)。理解為描述了体系的“危机状态”。然而,斯密并不是一位革命论者。斯密所构建的天文学知识进路反而具有连续性,这也为斯密想要表达的人类知识进步提供了支撑。
五 结论
对斯密的《天文学史》中的思想进行总结,我们可以看到,斯密首先论及科学认知过程中想象力的本质,并由此开始引出斯密版本的对科学史发展进路的理解。在斯密看来,人类的感官和认知的共同作用使得人们能够通过科学的方式理解和认识世界。
斯密认为,现实世界中的各种现象在本体论意义上是复杂的、多维度的、相互连接的。此外,斯密对科学发现和公理化进程的评价整体上基于最佳说明推理的检验模式。科学家们试图找到各种经验现象背后的真正的因果机制,这个过程不仅要求对现象的观察和描述,更需要通过构建一系列理论假定作为理论框架并构建解释体系。考虑到人类思维和科学进程的社会性,斯密认识到美学和社会学因素也可能会影响人们对科学理论体系的评价。
不断重复出现的现象,激起了人们对解释的需求。之后体系开始构建,人们开始用想象力构造一个最原始的系统。一旦最初的系统完成构建,理论与现象之间的二元模式就开始生成。理论与现象之间的差异,当理论不足以解释所有现象、或者当新的异常现象出现时,会导致想象力的缺口,从而使人们陷入矛盾之中。基于人的本性,想象力会自然而然地试图去弥合这种缺口,也就是通过对理论进行修缮来实现理论对现象的重新覆盖和解释。直到某种理论体系再也无法应对现象,新的理论被提出,人们会转向新的理论。但是,这个过程不是自然而然地发生的,在体系的革命过程中不可忽略的是社会因素。正如牛顿体系已经被提出,欧陆上依然有人遵从笛卡尔体系一样。
本文基于上述对科学和哲学之间的关系的理解,试图梳理斯密的科学方法。首先,斯密意识到本体论层面的预设和假说是科学研究的必要先决条件,但是如果只是对本体论的关注则并不足以支撑知识的进步,因此斯密倾向于使用一种结合了科学和哲学的检验方法评价天文学史上的理论体系。其次,斯密认为IBE检验的基本标准之一就是科学假说与当时为人所知的形而上学假说的对应程度,也就是“可爱性”的维度。在《天文学史》中,斯密论述道,经验证据和模型必须不仅在内部与物理天文学想合,還需要在物理学的大背景下与作为智力成果的形而上学理论相适应。最后,斯密对天文学史的回顾还暗含了在科学知识进步过程之中科学与哲学螺旋上升的思想。在对宇宙图景的评价方面,斯密认为,随着同心圆和偏心圆体系的逐渐衰落,经院哲学的宇宙图景渐渐失去了形而上学的主流地位,也越来越不被后人视作科学的指导。在18世纪中叶的背景下,后继兴起并且最终获得成功的哥白尼体系和牛顿体系背后的科学化的天文学系统推动了一种更加现代的形而上学理论的发展。斯密当时并不是完全确定天文学体系当时的发展是否能够完全印证牛顿体系在形而上学层面的有效性,但是斯密还是表现出了对牛顿体系的明显的支持。
斯密从整个《天文学史》的撰写过程中获得的并不仅仅是从古代天文学萌芽到当时认为是相当现代的牛顿体系下的天文学史新进展的脉络的梳理,从斯密的整体学说出发,更多地是构建起了一个斯密自身的哲学框架。一直以来斯密本人的研究兴趣都是更多地集中在人而非天文学或是某种特定科学本身,因此,通过对天文学历史上的各个理论之间的演化的评述以及对当时毫无疑问占有主导地位的牛顿理论体系的理解与分析,斯密构建起了一种整体性的、覆盖人的各个方面的思想体系与分析模式,并最终将其在《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之中加以运用,试图构建起斯密版本的关于人的科学体系。站在现在的视角进行回顾,斯密的系统化的思维方式才是最终实现斯密道德哲学理论构建的重要基石。
参 考 文 献
[1] Ross, I.. The Life of Adam Smith[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2010.
[2] Stewart, D.. Account of the Life and Writings of Adam Smith, LL. D. [A]. Smith A. and Wightman, W. P. D. (ed.). Essays on Philosophical Subjects[C].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0.
[3] Kim. K.. Adam Smiths ‘History of Astronomy and view of science[J].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2012, 36(4): 799—820.
[4] Smith, A.. Wightman, W. P. D. (ed.). Essays on Philosophical Subjects[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0. 33—34.
[5] Skinner, A. S.. Adam Smith: science and the role of the imagination[A]. Todd, W. B. (ed.). Hume and the Enlightenment[C].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74. 164—166.
[6] Hume, D.. 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 [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0. 225.
[7] Campbell, T. D.. Adam Smiths Science of Morals [M]. London: Allen & Unwin, 1971. 25.
[8] Frank, P.. Philosophy of Science: The Link between Philosophy and Science [M]. 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 1974. 1—47.
[9] Lipton, P.. Inference to the Best Explanation [M]. London: Routledge, 2004. 59.
[10]荣小雪, 赵江波. 最佳说明推理与溯因推理[J]. 自然辩证法通讯, 2012, 34(3):13—18, 37, 125.
[11] Kim. K.. Philosophy and Science in Adam Smiths ‘History of Astronomy: A metaphysico-scientific view [J]. History of the Human Sciences, 2017, 30(3): 107—130.
[12]张正萍. “推测史”与亚当·斯密的史学贡献[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8, 48(4): 227—240.
[13]徐竹. 亚当·斯密的科学观初探—基于《天文学史》手稿的解读[J]. 科学文化评论, 2011, 8(2): 111—126.
[14]袁江洋. 重构科学发现的概念框架: 元科学理论、理论与实验[J]. 科学文化评论, 2012, 9(4): 56—79.
[15] Copernicus, N.. On the Revolutions of Heavenly Spheres[M]. New York: Prometheus, 1995. 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