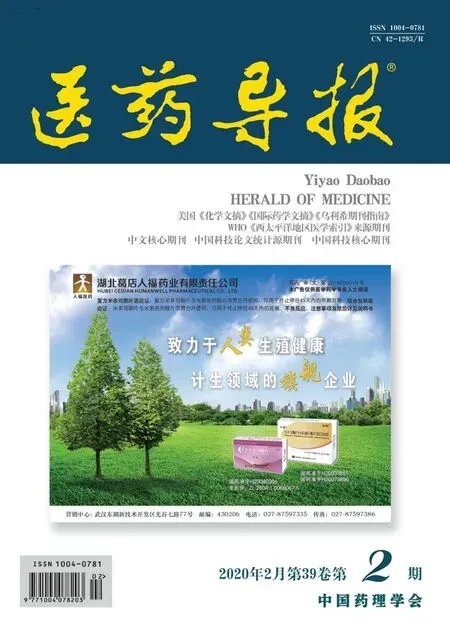肠道微生物群影响糖皮质激素体内代谢过程的研究进展
季可非,张瑜,张文婷
(1.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药学部,武汉 430030;2.湖北省仙桃市第一人民医院药剂科,仙桃 433000;3.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儿科,武汉 430030)
人类的肠道微生物群具有高度的多样性,可涉及3000~5000种细菌,主要以厌氧菌为主。其中许多细菌的菌种现在还尚不明确,大部分可分为厚壁菌门、放线菌及拟杆菌,以上三大类细菌约占微生物群总类的90%。现已发现人类肠道微生物群参与人体内多种生理过程,例如对抗病原体以对机体产生保护功能;参与免疫系统的调节;代谢发酵不易消化的膳食纤维及影响宿主体内的代谢过程,该过程涉及多个器官,包括肠道、肝脏、肌肉和大脑等,共同构成宿主-微生物代谢轴[1]。此外,肠道微生物群也可影响药物在体内的代谢过程,研究表明,至少有30种以上药物在人体内的代谢过程可受到肠道微生物群的影响,其机制可能与肠道微生物介导的酶促反应有关,涉及的反应,如:前体药物的活化(如氨基水杨酸)、药物失活(如地高辛)、药物的早期解离(如伊立替康腹泻毒性的产生)及天然糖苷的水解及所释放苷元的进一步代谢等[2]。近期研究发现经抗菌药物治疗后,随着乳酸菌和双歧杆菌的丰度降低,抗菌药物联合瑞伐他汀组降脂效果较瑞伐他汀单药组明显降低。而在抗菌药物治疗后4周,随着肠道菌群丰度的恢复,抗菌药物组降脂效果也恢复到单药组水平,其作用机制可能与肠道菌群介导的细胞运转体有关[3]。
越来越多的研究报道肠道微生物参与药物在人体内代谢及免疫调节过程,笔者在本文主要综述国外关于肠道微生物群参与糖皮质激素代谢的较新研究进展。通过介绍糖皮质激素在体内的代谢过程,肠道微生物群在介导糖皮质激素代谢过程中的作用,及其对皮质醇血浆浓度的影响,解释了部分临床症状出现的原因。
1 糖皮质激素的体内代谢过程
内源性糖皮质激素有可的松和皮质醇(cortisol,即氢化可的松),外源性糖皮质激素包括泼尼松、泼尼松龙、甲泼尼龙及地塞米松等。无论是内源性糖皮质激素可的松还是外源性的泼尼松,都需要经肝脏代谢活化从而发挥药理作用。皮质醇和泼尼松龙无需肝药酶活化即为活性成分,适用于肝功能障碍患者。皮质醇代谢的主要部位在肝脏,经3-酮基,δ-4双键结构还原,氧化去除C20,C21侧链产生具有17-酮基的C19类固醇或6-β羟基化后被代谢为硫酸盐或葡糖醛酸的结合物而成为水溶性物质,随后经尿液排出体外。其中,四氢皮质醇和四氢可的松占尿液糖皮质激素代谢物的含量最高,平均约占总量65%,而皮质醇和皮质酮(corticosterone)约占尿液糖皮质激素代谢物30%[4]。该代谢过程主要涉及5α-还原酶、5β-还原酶、3α-羟基类固醇脱氢酶、20α-羟基类固醇脱氢酶及20β-羟基类固醇脱氢酶等[5]。
11β-羟基类固醇脱氢酶1型(11β-HSD1)及其2型同工酶(11β-HSD2)也是皮质醇代谢过程中的关键酶,两者涉及反应是逆向的。11β-HSD1具有脱氢酶和还原酶的活性,在肝脏、脂肪组织、骨骼和中枢神经系统中均有表达,也可在多种其他组织中诱导产生[6]。在肝脏中一般以经11β-HSD1将皮质酮氢化转化为皮质醇为主。此外,11β-HSD1也见于很多其他的糖皮质激素靶组织,在调节靶细胞的局部皮质醇浓度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例如脂肪组织中过度表达11β-HSD1的转基因小鼠可出现肥胖和代谢综合征[7],提示皮质酮在脂肪组织中过度转化为皮质醇可能与该疾病产生有关。
11β-HSD2是11β-HSD的同工酶,可将皮质醇去氢化转化为皮质酮。而皮质酮不与盐皮质激素受体结合,属于无盐皮质激素活性的代谢物[8]。肾脏是肝外皮质醇代谢的另一主要部位[9]。在肾脏,皮质醇同样被高亲和力的11β-HSD2转化为皮质酮。由于皮质醇与盐皮质激素受体(mineralocorticoid receptor,MR)结合的亲和力与醛甾酮相似,且均高于皮质酮,故这种转化限制皮质醇更多的与MR结合[10],从而降低盐皮质激素的作用。
2 肠道微生物群介导糖皮质激素代谢产生甘草次酸样物质(glycyrrhetic acid like factor,GALFs)
甘草类化合物中的甘草次酸可抑制11β-HSD2酶的活性,从而抑制皮质醇在11β-HSD2的作用下转化为皮质酮[11]。早在1981年,MURPHY等[12]就首次在胎儿的血清和脐带中发现了对11β-HSD脱氢酶有抑制活性的内源性甾体物质。这类化合物的结构与类固醇激素相似,并与甘草次酸一样,均可双向抑制11β-HSD1及11β-HSD2的活性,因此被称为GALFs。内源性的GALFs可能增加肾脏、血管内皮和其他组织的局部皮质醇水平。
近年来的研究表明,除了内源性甾体物质,外源性糖皮质激素也可产生GALFs,如在肠道细菌的作用下,由皮质酮经C-21脱羟基产生的衍生物3α,5α-四氢-11β-羟基孕酮[13]。肠道微生物群产生相应的酶可参与糖皮质激素的代谢,产生具有GALFs活性的物质,从而调节皮质醇和皮质酮的局部组织代谢。介导皮质酮主要肠道细菌代谢酶有17β-HSD、Steroid-17,20-desmolase、3α-HSD,3β-HSD、5β-reductase、5α-reductase、21-dehydroxylase;介导皮质醇主要肠道细菌代谢酶17β-HSD、Steroid-17,20-desmolase。
皮质醇在肝脏经还原、氧化或羟化后,其原型药物及其代谢产物与硫酸或葡萄糖醛酸结合后变为水溶性,随后经尿液排出,此外仅有一小部分(<4%)从胆汁中排出。与皮质醇不同的是,人体可通过胆汁排泄大量皮质酮及其5α-还原代谢产物,如3α,5α-四氢皮质酮,并经胆汁进入肠道。BOKKENHEUSER等[14]在1975年就在健康人体大便微生物群混合培养物中观察到其具有脱羟基作用,皮质酮可在肠道被厌氧菌转化为21-脱羟基化产物,11β-羟基孕酮或11β-羟基- 5α-前列腺素。而这两类皮质酮衍生物均对11β-HSD的两种同工酶具有一定抑制活性,即属于GALFs。
而皮质醇在肠道细菌合成的酶的作用下发生侧链切割,是GALFs产生的另一重要途径。皮质醇可在厌氧菌作用下,经侧链裂解产生一系列C21及C19代谢产物。其中C21代谢产物包括21-脱氧皮质醇,四氢-21-脱氧皮质醇和四氢皮质醇等;而C19代谢产物包括11β-羟基雄烯二酮等[15]。虽然11β-羟基雄烯二酮对11β-HSD两种同工酶的抑制活性较弱,但其可经过17β-HSD酶转化为11β-羟基睾酮,可明显增强其对11β-HSD两种同工酶的抑制活性。由于该酶促反应,11β-羟基雄烯二酮与11β-羟基睾酮在组织中保持动态平衡,以激活GALFs的活性[16]。
3 GALFs对皮质醇浓度的影响
由上可知,皮质醇及皮质酮均可在肠道细菌产生酶的作用下产生GALFs,反过来参与调节皮质醇和皮质酮的局部组织代谢。11β-HSD2-GALFs通过抑制11β-HSD2酶的活性,阻碍皮质醇转化为皮质酮,从而引起皮质醇的血浆浓度增高,见图1。其影响程度可能与糖皮质激素经肠道排泄的比例及产生的GALFs物质的量有关。MORRIS等[17]研究尿液中11β-HSD2-GALFs物质的水平与尿游离皮质醇(urinary free cortisol,UFC)水平和血浆肾素活性(plasma renin activity,PRA)的关系。其中,GALFs的水平代表其对11β-HSD2的抑制活性,而不是绝对的某一物质的具体含量。结果表明随着GALFs水平的增加,UFC增加,游离皮质醇与可的松比率增加,导致皮质醇在靶组织的半衰期(t1/2)延长。另外,PRA与UFC也呈正相关。

图1 皮质醇、皮质酮及GALFs间的相互关系
Fig.1 Relationship among cortisol,cortisone and GALFs
BAHR等[18]尝试通过测量皮质醇及其代谢产物在尿液中的含量,以预测皮质醇进入肠道的量。给予绒猴、长尾猕猴和黑猩猩三种灵长类动物的成年雄性个体静脉输注放射性(40~100 μCi)的3H-标记的皮质醇,并在注射后5 d内收集排泄物。结果表明,尿代谢物主要以结合物的形式排出,其放射性主要在尿液中被检测到(61%~87%),粪便中的共轭代谢物低于50%,而由肠道细菌产生的皮质醇代谢产物的含量则更低,包括11β-羟基雄烯二酮等,为1~3 μg·g-1粪便。因此,肠道微生物群通过该途径对皮质醇浓度影响的程度也是今后研究的一个方向。
4 GALFs与表观盐皮质激素过多综合征(apparent mineralocorticoid excess,AME)
AME是一种症状类似于原发性醛甾酮增多的疾病,可表现为青少年患者中高血压,并伴随低钾血症、代谢性碱中毒和低血浆肾素活性等。根据其病因可分为原发性和继发性,前者为11β-HSD2基因突变的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病[19],后者可因慢性摄入外源性的甘草酸或GALGs而表现出类似于原发性醛甾酮增多的症状。皮质醇与醛甾酮一样可与盐皮质激素受体结合而表现出盐皮质激素的活性。然而,与原发性醛甾酮增多症不同的是,AME中血浆醛甾酮水平会降低。而且血浆皮质醇的浓度比血浆醛甾酮浓度高约100倍,皮质醇血浆浓度持续增高,最终表现为盐皮质激素活性明显升高[20]。由于外源性糖皮质激素可在肠道细菌酶的作用下产生GALFs,通过抑制11β-HSD2酶的活性,阻碍皮质醇转化为皮质酮,从而引起皮质醇的血浆浓度增高,因此临床上长期口服糖皮质激素的患者可能出现AME。
在上述GALFs的作用下,血液中过量的皮质醇可与存在远端肾单位的盐皮质激素受体结合,从而增加Na+重吸收,导致肾脏扩张细胞外(血浆容量)体积和高血压[21]等,提示肠道细菌来源的糖皮质激素代谢物可能也会通过类似的机制引起一些患者的原发性高血压,但仍需要进一步的临床研究予以证实。
5 结束语
在肠道细菌酶的作用下,皮质酮及皮质醇均可产生GALFs,抑制11β-HSD2,导致皮质醇局部浓度的增加,临床可出现AME。提示除了肝脏代谢酶的影响外,胃肠功能也可影响糖皮质激素体内代谢。此外,长期服用糖皮质激素等药物对肠道菌群也会产生影响。如在口服泼尼松龙、他克莫司及吗替麦考酚酯等免疫抑制药的患者中常可观察到腹泻等不良反应,可能与体内微生物群结构受到免疫系统的调节影响有关。口服泼尼松龙14 d后,小鼠大便及回肠中微生物群落结构与给药前相比被破坏,拟杆菌的丰度降低,厚壁菌的丰度增加。而联用泼尼松龙、他克莫司及吗替麦考酚酯后,小鼠大便及回肠中致病性大肠杆菌菌株536的定植量明显增加,这是3种免疫抑制药共同作用的结果[22]。肠道微生物对糖皮质激素代谢影响程度的大小与在肠道产生的GALFs的量有关,不同给药途径也可能是导致差异产生的原因,也提示在临床用药中结合糖皮质激素类别和剂型选择更适合的药物,从而减少肠道微生物群对药物的影响,如将泼尼松调整为甲强龙等。但由于GALFs是一类物质的总称,直接测定其具体浓度较为复杂,采用其对11β-HSD2的抑制活性的大小来表示的准确性有待考证,其测定和分析可能成为今后研究的一个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