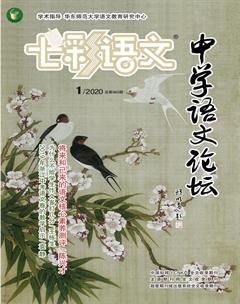口语化表达与小说的当代意味
王学森
徐则臣的长篇小说《北上》发表在2018年《十月·长篇小说》第5期,2018年12月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单行本,2019年获得第十届茅盾文学奖。可见,这是一部快速引起关注、得到评委认可的作品。它将“运河两岸的城池与人群、悲欢与梦想次第展开”,刻画了百年历史的兴衰,把大运河的命运汇入“中国精神的深厚处和高远处”。徐则臣的独特之处还在于,他把运河历史写出了鲜明的当代意味,或许这是作品能够快速传播的重要原因。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言是作者面对生活和文学的姿态,是现实世界转向文学世界的密码。徐则臣能够把百年历史呈现出当代意味,起到关键作用的便是充斥作品的口语表达。《北上》处处可见日常生活用语、俗语以及时下流行语。这样的文学语言将百年运河史转变成一个今天的故事,引领读者越过沉重的岁月一览历史的芜杂。
一、历史向当代的转身
长篇小说往往会有多个鲜明的人物形象,读者根据他们的形象和故事,体会这个世界的惊险、怀疑、丑恶、善良。在口语化的表达中,《北上》的历史从远方走到读者面前,历史人物个个长着一副当代人的面孔,说着当下人的话,演绎的更像是当代故事。
小说以一份运河考古报告开始,其中的一封意大利人的信件牵出了整个故事。意大利人马费德钟情于大运河,以水兵的身份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他爱中国的河流和姑娘,又不得不参与八国联军,攻打清军和义和团。在一次负伤后,他给家人写下这封信,便逃离队伍,更名马福德,与一个中国姑娘过上了隐姓埋名的普通生活。后来他的哥哥小波罗来中国寻他,雇佣了几个中国人沿着运河从无锡一直北上,最终小波罗没有找到弟弟马费德,死在了行往北京的船上。马费德和小波罗仿佛是一双历史之眼,带我们浏览运河、百姓、国家的百年面貌,认识生命的愚昧、残忍和坚强。即使他们去世,其事迹对后辈人的生活和精神一直有着深远影响,他们与运河仿佛有着命中注定的姻缘,从运河的昌盛到衰落,从充盈到干涸,从实在的生活到文化建构,世世代代的生命回应着百年前灵魂的召唤。
徐则臣没有强调这两个意大利人的异域特征,反而让他们表现得像个地道的中国人,这是语言的效果。如,马费德受伤后,他在给家人的信中写道:“医生说,好利索了我也只能是个瘸子。瘸子就瘸子吧,总比死了好……想顺顺当当活下来不容易。……多事之秋,战争、瘟疫、饥荒、河匪路霸,遇到哪一个都可能活不成,蹿个稀也没准再站不起来。”这个外国人说的不是标准的普通话,也不是一般的翻译体语言,而是一口正宗流利的百姓话。“好利索了”“顺顺当当”“蹿个稀”这些日常口语,通俗、不雅致、不漂亮,在中国白话文写作中也不常用。一个西方人能说出这样的话,或许我们也就忘记了他的外国身份。当马费德的哥哥小波罗来到中国,站在无锡城外对着两个当值的喊:“哥们儿,行个方便,五文钱的事。”这句话一出来,哪里还有外国人的样儿,分明是一位北京胡同的浪荡哥儿。由于少五文钱,小波罗被两个当差的捉弄吊在半空,作者如此形容他:“别人有来处也有归处,他却孤悬异乡,吊在半空里憋着一膀胱的尿。”作者显然不是嘲讽他,而是用饱含乡土气息的粗言秽语把外国人转化成地道的中国形象。
徐则臣不仅把外国人描绘成活灵活现的中国样子,还把旧中国写出了时下味道。小波罗雇佣中国翻译李赞奇随同北上,中途李赞奇受伤不能继续前行,他推荐了之前的同事谢平遥。谢平遥再遇李赞奇时,作者写道:“李赞奇跟十年前他们分别时比,颧骨高了,发际线大踏步后撤,前额的头发根本用不着剃,辫子也细成了老鼠尾巴。”“发际线”这种现代化的词汇伴随着“大踏步”这种人物动作词,让一个一百年前的场景变得滑稽可笑,它转变了我们看待古人的眼光,仿佛我们正站在病床前跟好友开玩笑。类似的语言在《北上》中比比皆是,比如李赞奇给谢平遥写信时说,“老弟,矜持点,伟大的时代不是煮熟的鸡蛋”;作者这样描写谢平遥所在的造船厂的工作状态,“就算屁事没有,大家也都装模作样地上下班”;李赞奇与谢平遥重聚庆祝时,作者写道,“兄弟多年不见,必须喝到位才行”;谢平遥对小波罗的认识是,“尽管小波罗无比热爱中国文化和风物,但欧洲人傲慢和优越感的小尾巴总是夹不紧”……徐则臣不避流言俗语,善用油滑的方言。在新历史视野里,历史成了当代史,一个百年的故事成了彻头彻尾的当代闲篇。
二、个体与运河的交融
徐则臣的文学世界里,普通个体除了能够轻易地接受历史,也能够切身参与历史建构,在历史语境中认识自我的意义。历史书写似乎应该是宏观的,而不是细微的,应该描述整体,而不是聚焦个体。然而口语化表述像是一条涉渡之舟,承载那些说着粗言秽语的平凡肉体,进入历史之境,发出平凡的声音。
意大利人沿河北上,考察中国运河的全貌,这听起来应该是件庄严的事,这是塑造英雄的契机。但那些参与者都是极其卑微的生命体,没有太多英勇的光芒,更多的是苦命的呻吟。挑夫邵常来被问及是否愿意和小波罗一起走,邵常来最初以为是去意大利,表示不同意,但当听说是去北京,小波罗又拿出一锭银子的时候,邵常来当即叩头感激不尽,他可以用这些钱回家买田娶妻,终于看到了生活的希望。最开始的船夫老夏和两个徒弟,以及后来的船夫老陈和妻儿,都不是叱咤江河的英雄,而是水上卖命的穷苦人。徐则臣在历史中给了小人物一定的空间。除此之外,他还给予穷苦人平等的地位。小波罗问邵常来“愿意跟我们走不”,这种缺少主语有一点倒装的疑问句,是日常口语的重要特点。邵常来则回答“太偏了”,这也是明显的日常俗语,既涵盖路途遥远又包含地方陌生的意思,这是很多书面语不能表达的;同时,语言简单有力,有极强的目的性、指向性,区别于一般文学语言的含蓄多义。徐则臣把所有人的语言处理成口语化的状态,把所有人拉到同一个层面,他们使用同一种语言,说着同样的话。在权力、金钱、知识面前,“邵常来们”的要求和意义均能够得到回应和确认。徐则臣或许想说:运河带来了生命,它是所有人的生命,是一切平等的生命。
历史向前推进,但世世代代的人们牵系着大运河的灵魂。大运河的灵魂是所有人生存的渴望,是水上人死后的归所,《北上》要展現的正是运河人家的生活气息与生命意志。小波罗死后,他的中国伙伴纷纷开始了新生活,邵常来不再做挑夫,落户济宁,做起世世代代的水上生意。然而时间来到新世纪,陆上运输、空中运输逐渐便捷、繁荣,运河生意渐次没落,运河的生态也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年轻人纷纷跑到岸上寻找生活,运河失去了养育人们的能力。邵常来的后人邵秉义说:“过去运河水也不干净,但那是水草啊、死鱼烂虾子啊沤坏了的脏;现在才真叫脏,各种塑料袋、垃圾,取土、打沙,工业废水,还有机械船漏的油。你看看,从南到北,有哪段运河水还能淘米洗菜。”这种说法是对当下生态环境普遍的认知,作者直接借用过来,并且在一句话里连用两次“啊”,凸显了口语表达的重复和情绪化特点。徐则臣用这样的语言塑造了一位关心自身吃喝拉撒的运河人,也形象地表达了百姓对运河现状的痛惜。
运河给予了人们生命,人们也赋予了运河气息。大运河从历史流淌而来,它谱写着一个个平凡生命的故事,感叹运河人家的伤痛与温情。这或許就是《北上》的一层意义,徐则臣不仅把历史转化成当下图景,还把运河的整个生命脉络汇成世世代代平凡的生命之流,这是历史与当代的交融,是运河与人生的共鸣。可以说,这一切形象的有机结合得益于口语化的表达。
三、口语表达与价值的瓦解
俄国形式主义提出了文学语言的“陌生化”理论,认为文学语言的意义在于区别日常语言,让读者产生独特美的感受。什克洛夫斯基在《词语的复活》中说:“艺术的技巧就是使对象陌生,使形象变得困难,增强感觉的难度和时间的长度,因为感觉过程本身就是审美目的……”《北上》则避免陌生化,偏爱日常生活状态,然而从文学性的角度来说,反其道而行之的口语化表达似乎又成就了新的美学特征。追求白话风格的语言意识延续了一百年,它不断催生新的文学世界,《北上》与之一脉相承,但又有自身的独特性。它滑稽庸俗的语言不断削弱文学意义,使历史书写越来越像碎片组合。
白话文运动引领的现代文学摒弃佶屈聱牙的文言文,选择通俗易懂的讲述方式,诉说“为人生”的文学理想。自此文学能够进入更多人的视野,被普通人接受,读者能够在文学中见到自己的现实状态和生命渴求。后来革命不断壮大,大众语和口语创作逐渐成为主流,作家们向工农兵学习,为工农兵服务,因此作家要用日常生活的语言创作工农兵看得懂、易接受的文学作品。这种创作意识从未停滞。20世纪90年代经济发展日盛,人们的生活状态趋于稳定,日常物质需求、日常情感、日常交往成为这个时代人们关注的重点。人们关切个人的利益,纠结男女情爱,在意身体保健,日常生活创作成了文学主流。文学的变迁史也是语言的变迁史,任何事情任何细节能走进文学,任何人能在文学中发现自己的身影,至关重要的原因是那些人能够在文学世界说出日常语言,那些事物能够被日常语言所描绘。
《北上》与白话文写作、大众语写作仍有所差别。以往的白话文创作还保留一定的文学性,追求文学美、人性美,回应现实生活的要求。《北上》则把口语、俗语当成陌生化的手段,解构了日常生活的价值,因此严肃的地方失去了严肃的意味,大历史被滑稽和幽默肢解破碎。邵秉义的儿子邵星池婚礼之前,父子俩去给祖先上坟,由于儿子即将放弃船上生活,邵秉义感到愧对祖先号哭起来,邵星池不以为然,他眼中的父亲“撅着屁股,脑门捣蒜一样磕在石头、泥土和野草上”。邵星池等了一会儿后,看到父亲屁股撅得更高了。作者两次用“屁股”形容邵秉义的丑态,刻画了邵星池不屑的神情。除了这样生理性的丑词,作者还使用生理器官描写美的感受。大运河申遗前期,谢平遥的后人、大运河主题纪录片《大河谭》的策划人谢望和来到淮安找一位摄影师孙宴临,邀请她加入《大河谭》的制作,作者第一次描写孙宴临突出的是她的性感:“唇形很好,很多女人化了妆也未必有她素颜时的唇线饱满清晰。”这是一种容貌描写,也可以说是一种性暗示。作者第二次描写时这种性暗示更加明显:“我从下往上慢慢看,小腿,膝盖,大腿,腰,肚子,胸部,双肩,脖子,然后脸。”孙宴临意识到谢望和的眼神后则说:“看够了?”男士以性的角度扫视女士身体,而女士娇嗔的回话,像极了网络小说的桥段。徐则臣熟悉当下流行的审美特点,显然他乐于使用这些元素,给读者带来感官的刺激和阅读的快意。此消彼长,作品因此削弱了对历史和人生的严肃思考。
无论如何,《北上》是一部野心勃勃的巨作,它指向悠远的历史,又着眼当下生活,它想写出文化内涵,又想写得通俗幽默,它想坚守历史主义、现实主义的价值,又想用现代风格、流行元素吸引读者,它想替普通百姓说话,又想贴近时代政策。总而言之,这部巨作呈现的远比我们想要的更丰富。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栏目编辑:陈梦琪)
——论徐则臣文学的发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