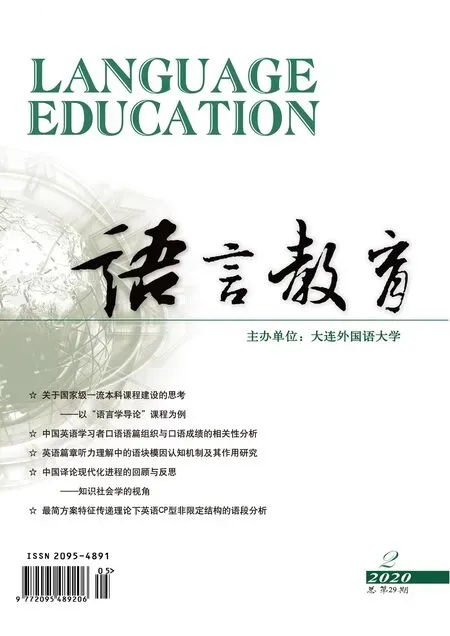新历史主义视阈下安妮·布拉德斯特里特诗歌中的协合
李文萍 赵巧利
(1.大连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辽宁大连;2.郑州工商学院人文艺术学院,河南郑州)
1.引言
安妮·布拉德斯特里特的诗集《美洲新崛起的第十位缪斯女神》(The Tenth Muse,Lately Sprung Up in America)的公开出版,开创了美国诗歌与女性诗歌的先河。作为美洲大陆第一位公开出版诗集的女诗人,布拉德斯特里特与爱德华·泰勒共享美国早期诗歌创作的最高成就。美国史学家塞缪尔·莫里森称其为“新英格兰第一批定居者中与众不同的一位,因其诗歌展现出的个人品质,思想及宗教信仰对后世产生了深刻持久的影响”(Morison, 1981: 335-36)。布拉德斯特里特诗歌反映的协合与新历史主义理论中的协合不谋而合,因此,本文通过新历史主义理论,分析布拉德斯特里特宗教诗歌与家庭诗歌中物质与精神的协合以及对世俗的爱与对上帝的虔诚间的协合,揭示了十七世纪清教社会神权体制对人们思想的束缚与觉醒的女性意识。
新历史主义理论为探究布拉德斯特里特诗歌中的协合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新历史主义者尤其关注文本与作者间的相互关系。新历史主义的核心概念包括:协合、颠覆与抑制。协合是指创作主体的能动性。颠覆是指对代表统治秩序的社会意识形态的反叛。抑制是对颠覆性力量的压制。协合最终在颠覆与抑制中得以实现。斯蒂芬·格林布拉特在《莎士比亚的协合》中,以莎士比亚戏剧人物为对象,探讨了文学与社会的关系,称“艺术作品虽然深受个体创造才能与私人情感的影响,但它们仍是集体协合与交换的产物”(Greenblatt,1988:7)。换言之,在格林布拉特看来,处在社会能量的协合作用与巨大的社会文化网络下的文学艺术,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社会现象的影响,从而表现出鲜明的颠覆与抑制功能。
2.安妮·布拉德斯特里特诗歌中的协合
协合是布拉德斯特里特宗教诗歌与家庭诗歌反映的核心主题。宗教诗歌《灵与肉》与《屋舍焚毁后》诠释了布拉德斯特里特物质与精神的协合。而家庭诗歌《献给我挚爱的丈夫》与《纪念我亲爱的孙女伊丽莎白·布拉德斯特里特》表现了布拉德斯特里特对世俗的爱与对上帝的虔诚之间的协合。宗教诗歌与家庭诗歌中折射出的协合是布拉德斯特里特责任心与诗歌作品复杂性的体现,而协合在颠覆与抑制中得以实现。本文将基于新历史主义理论对布拉德斯特里特诗歌中的协合展开深入探究。
2.1 宗教诗歌中的协合
协合是安妮·布拉德斯特里特的宗教诗歌《灵与肉》、《屋舍焚毁后》与清教社会发生关系的方式,也是布拉德斯特里特主体性的体现。作为一位清教徒诗人,布拉德斯特里特在宗教诗歌中集中表达了宗教体验的所思所想。布拉德斯特里特在《灵与肉》中通过构想孪生姐妹“灵”与“肉”之间的激烈辩论表现了想象层面物质与精神的协合,彰显了其为达到清教徒的理想状态所经历的心理挣扎。而《屋舍焚毁后》则是基于布拉德斯特里特的亲身体验,反映了现实层面物质与精神的协合,揭示了其现实生活中对清教规约的反抗与屈从。这两首诗歌均是布拉德斯特里特宗教思想的真实表露,不同程度上抨击了清教主义对人们思想的束缚。
想象层面物质与精神的协合集中体现在《灵与肉》一诗中,并通过对清教理想状态的颠覆与抑制得以实现。基思·布克认为,“文学作品实际上是作者复杂的社会交换与协合的产物,因此文本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密不可分”(Booker ,1996:138)。清教社会崇尚诗歌创作以教化大众为主旨,而布拉德斯特里特在该诗中以非说教的方式表达个人思想。艾德里安·里奇称布拉德斯特里特为“美国第一位非说教,第一位赋予美国特性,第一位受个人意图而不是清教规约启发而从事创作的诗人”(Rich,1979:26)。非说教的表达形式不仅使该诗受到了大众青睐,而且表现了布拉德斯特里特独具一格的清教思想。该诗共有108行,“灵”与“肉”这对孪生姐妹间水火不相容的辩论贯穿全诗。该诗以“我”为第一人称,占用4行引出“我”听到的“灵”与“肉”之间的辩论。“灵”代表着虔诚的宗教信仰,“肉”代表着世俗生活中物质的诱惑。而“我”,作为一位旁观者,成为辩论的裁判员。布拉德斯特里特借“灵”与“肉”的激烈辩论生动再现了清教徒内心的矛盾挣扎,实现了物质与精神想象层面的协合。
一方面,“肉”对“灵”的质问反映了布拉德斯特里特对清教理想状态的颠覆。在格林布拉特看来,颠覆是指:“历史或文学文本创作中对政治权力与意识形态的反叛”(Greenblatt,1980:40)。在《灵与肉》开篇,布拉德斯特里特借“肉”的口吻提出了自己的疑问:“姐姐呀,你何以为生啊?/除了冥思,就什么都没有了吗”(Bradstreet,1967:215)。这个问题在当时的殖民地生活背景下显得尤为突出。1630年夏天,布拉德斯特里特同家人搭乘以约翰·温斯罗普为首的“阿贝拉号”,离开英国前往“应许之地”新英格兰,最终在马萨诸塞殖民地定居。清教徒们坚信自己是上帝的选民,热切渴望在这片土地上建立“山巅之城”。清教主义是他们的生活方式。生活在这个世界而又不在其中是其理想状态。埃德蒙得·摩根将此矛盾性称为“清教徒的双重困境”,即“清教主义要求清教徒终生致力于自我救赎,又告诫他们除了邪恶无能为力”(Morgan,1958:20)。面临食物的严重匮乏,阴晴不定的气候,与土著人的不和,疾病的突袭等问题,清教徒们渴望建立山巅之城的满腔热忱不免遭受沉重一击。“肉”的这一质问恰恰印证了清教徒们内心存在的疑问。紧接着,“肉”以真实存在的物质诱惑“灵”:“除了思想以外,就没有现实的东西了吗/难道你真认为能到月天之外去居住吗”(Bradstreet,1967:215)。在“肉”看来,生活在人世间,应该追求的是名誉、财富、快乐而不是虚无缥缈的信仰。实际上,这些疑问代表了布拉德斯特里特对殖民地生活的质疑与对清教理想状态的颠覆。首先,处在以上帝为核心的清教社会,女性丧失了话语权。女性应当无条件地信仰上帝,向上帝提出疑问则是对上帝的亵渎。虽然布拉德斯特里特是借“灵”与“肉”这样为人熟知的题材间接传达了自己的疑惑,但是质问本身足以表明布拉德斯特里特对清教理想状态的否定。其次,下文“灵”对这些尖锐问题的无力反驳恰恰认证了该事实。从根本上来说,布拉德斯特里特无法从清教教义中找出强有力的证据来打消自己的疑惑,从而坚定了其对清教理想状态的颠覆。
另一方面,“灵”对“肉”的谴责反映了布拉德斯特里特对颠覆清教理想状态的抑制。格林布拉特称:“抑制最终消解了颠覆力量,在这一过程中权威自身足以轻松抑制异端力量”(Greenblatt,1994:29)。首先,针对“肉”犀利的质问,“灵”并未进行正面回应而是讽刺了“肉”的庸俗:
你不必嘲笑我以何为生,
我吃的肉你从未见过;
我吃的是天堂的食物,
生活的箴言便是我(吃)的肉。(Bradstreet,1967:216-7)
“灵”以此表明自己的立场:只有天堂才是她的归宿。清教主义轻视现世的生活,崇尚天堂的美好。对于布拉德斯特里特而言,接受殖民地艰苦生活的洗礼是痛苦的,但是作为一名清教徒,她又渴望实现自我救赎。她在手稿《致我亲爱的孩子们》中写到“我来到这个国家,发现了一个新世界,新风俗,我的心倔强的跳动着[以示抗议]。但当我发现这是上帝的旨意后,我顺从了,加入了波士顿的教会”(Hensley,2010:240)。接着“灵”表明了自己与“肉”斗争到底的决心,称:
你我之间的战斗必将继续,
直到我看见你躺在泥土里。
我们虽是姐妹,
但却有着不共戴天之仇。(Bradstreet,1967:216)
虽然“灵”与 “肉”是姐妹,拥有同一个母亲,但是他们的父亲不同。诗中强调“肉”的父亲是听谗言、食禁果的亚当,而“灵”的父亲是万能的上帝。因此,两姐妹之间的斗争势必会持续下去。面对“灵”与“肉”的持续冲突,作为旁观者,布拉德斯特里特也一直在反思自己。她曾谈到:“我经常感到茫然和困惑,因为在朝圣旅途及对此的反省中我并没有找到其他圣徒们所拥有的永恒的喜乐”(Hensley,2010:238)。虽然布拉德斯特里特很迷茫,但她最终打消了自己的疑惑,屈服于上帝的意志。
最后,“灵”对天堂的追求与向现实的屈服反映了布拉德斯特里特宗教思想上的协合。“灵”对圣城的描述违背了她的志向,却表达了自己的渴望:
我希冀栖身在一城中,
尘世无法与之相比。
雄伟的城墙高大而坚固,
用贵重的碧玉砌成。(Bradstreet,1967:217)
针对之前“肉”的质问,“灵”表明了自己坚决抵制物质诱惑的决心,但从“碧玉”、“精金”等富丽堂皇的装饰来看,“灵”的确受到了“肉”的思想的左右。从表面来看,两姐妹的争辩中“灵”占据72行而“肉”只占32行,“灵”赢得了这场战斗。作为旁观者,布拉德斯特里特并未明确表明获胜一方,体现了她的协合意识。这种协和与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诗歌中的“单纯与强硬”不谋而合,“单纯不反抗的隐忍对诗人的坎坷人生来说无济于事,但如果选择强硬将会由于锋芒毕露而令自己潜入危险之境”(姜美冰 殷晓芳,2017:88)。因此,在这首诗里,布拉德斯特里特以旁观者身份协合了“灵”与“肉”的冲突,在清教神权社会这一社会能量流动中达成了物质与精神间的平衡。
《屋舍焚毁后》展现了布拉德斯特里特在现实体验与宗教信仰之间达成的协合。协合意味着主体虽然“受到社会规约限制但它有自身的能动性”(杨正润,1994:116)。该诗是布拉德斯特里特的房子于1666年被烧毁后所作,反映了布拉德斯特里特在现实层面物质与精神达成的协合。
《屋舍焚毁后》中布拉德斯特里特对上帝的抱怨是其对清教教义的颠覆。在新历史主义中,颠覆意味着对主流社会意识形态的反抗。该诗大部分笔墨呈现了布拉德斯特里特对上帝的抱怨。起初,当布拉德斯特里特从熊熊燃烧的大火中惊醒,作为一名清教徒,她脑海里回荡的还是基督的话语:
我赞美您那施与和收回的大名,
它使我的财产在瞬间化为乌有。
是的,没错,本来就应该这样,
那一切都是他的,不是我的。(Bradstreet,1967:292)
从该诗表面来看,布拉德斯特里特表达了她对上帝权威的敬畏,但字里行间暗讽的语调传达了其对上帝的不满。“瞬间”一词将布拉德斯特里特愤懑的情绪暴露出来。清教教义规定清教徒不可过分贪图世俗之物,世间一切归上帝所有。布拉德斯特里特作为一位虔诚的清教徒,她虽然尊崇上帝权威,但是也很珍爱身心的栖息之所。烧毁的房子是丈夫西蒙·布拉德斯特里特精心建造的别墅之家,内设有从英国购置的精致家具、藏书八百余册的小型图书馆。最重要的是,它是布拉德斯特里特所有回忆的归属地。接下来,布拉德斯特里特谈到每次经过废墟时自己内心的绝望:“我所喜欢的一切全部化为灰烬,/而我再也没有机会把它们来看”(292)。此时,布拉德斯特里特表达了内心的极度不满:
再也没有客人坐在你的屋檐下,
也不会有人坐在你桌子旁用餐,
再也没有人讲起那有趣的故事,
也没有人回忆起先人做的事情。
在你的屋子里再也看不到烛光,
人们在那不在听到新郎的声音。
你静静地、永远地在那里躺着,
再见吧,再见!一切皆为虚无!(293)
一连串的“再也”强调了布拉德斯特里特欲哭无泪的心理状态,暗示了她对上帝摧毁她与家人劳动成果的怨恨,颠覆了清教教义中的禁欲思想。米勒形象地描述了该教义“人们在葡萄园里劳作,却又要求他们对葡萄不能有不适宜的爱好”(Miller,1954:44)。最终,“再见吧,再见!一切皆为虚无!”(Bradstreet,1967:293)。反映了布拉德斯特里特无奈的抵抗。房子的烧毁是上帝的行为,上帝的旨意是不容质疑的,但是此处布拉德斯特里特的确表达了自己的疑惑,颠覆了清教教义。
抑制是《屋舍焚毁后》中布拉德斯特里特顺从上帝意志的表现形式。“在文学作品中我们能够找到个人的反抗,同时也可以看到这种反抗被权力机制利用或招安的过程”(陈榕,2006 :678)。虽然布拉德斯特里特在《屋舍焚毁后》中表现了个人的反抗,但是她终究没有逃脱清教徒身份的束缚。首先,以上帝为核心的神权政治社会,圣经是清教徒参照的行为规范。圣经中索多玛城的人们因欲望过盛遭受了大火洗礼,罗德之妻则因违背上帝的旨意回头看燃烧中的索多玛城而瞬间化为盐柱。作为一名虔诚的清教徒,布拉德斯特里特从未想过僭越上帝的权威。其次,不得不说,火给布拉德斯特里特留下了深刻的心理阴影。多年前纽顿的父母家与伊普斯威奇的妹妹家都遭受火灾。此外,布拉德斯特里特的房子被烧毁前,一场大火席卷了伦敦,百分之八十的区域化为灰烬。火是上帝对人们的惩罚与告诫。最后,在诗歌中布拉德斯特里特进行了自省并声称:“世界不再给我机会,让我去爱,/我的希望和宝藏藏在天上”(Bradstreet,1967:294)。布拉德斯特里特选择寄希望于天堂,抑制了对世俗之物的贪恋。
布拉德斯特里特现实境遇中物质与精神的协合在《屋舍焚毁后》中凸显出来。格林布拉特认为,协合表明创作主体在社会能量中所起的交流协调作用,在这一过程中,作家成为协合的主要承担者,而文学的主要功能就是协合。不同于布拉德斯特里特冥想中“灵”与“肉”的争执,《屋舍焚毁后》展现了布拉德斯特里特在艰苦的殖民生活与狭隘的清教教义间的协合。
2.2 家庭诗歌中的协合
对世俗的爱与对上帝的虔诚之间的协合是安妮·布拉德斯特里特家庭诗歌《献给我挚爱的丈夫》与《纪念我亲爱的孙女伊丽莎白·布拉德斯特里特》的主旨所在。受社会话语权限制,布拉德斯特里特聚焦女性专属的家庭领域。《献给我挚爱的丈夫》与《纪念我亲爱的孙女伊丽莎白·布拉德斯特里特》反映了布拉德斯特里特在对待家人与上帝情感关系的社会能量之间的协合。《献给我挚爱的丈夫》既展现了布拉德斯特里特对丈夫超越世俗的爱又暗示了其对上帝的敬畏,表现了布拉德斯特里特婚姻中对丈夫的爱与对上帝的虔诚之间的协合。《纪念我亲爱的孙女伊丽莎白·布拉德斯特里特》表现了布拉德斯特里特对孩子离世的痛惜与不满。同时,传达了诗人对上帝意旨的屈服。该诗表达了布拉德斯特里特在孩子的爱与对上帝的虔诚之间的协合。
协合是《献给我挚爱的丈夫》所反映的布拉德斯特里特对丈夫与上帝感情的平衡方式。在新历史主义中,协合用来表明不同范畴中的主体在“社会能量”或社会关系、文化网络所起的沟通、协调作用。在《献给我挚爱的丈夫》中,布拉德斯特里特协调了其对丈夫与上帝的爱,具体表现在其对清教徒不被允许对任何人的爱超过上帝的教义的颠覆与抑制。
颠覆是《献给我挚爱的丈夫》一诗中布拉德斯特里特对丈夫的爱的外在表现。“颠覆不仅仅是反抗权威,而是对权威所基于原则的挑战”(Dollimore & Sinfield,1994:13)。该诗传达了布拉德斯特里特对丈夫真挚、炽烈的爱,颠覆了清教徒不被允许对任何人的爱超过上帝的教义。一方面,该颠覆体现在该诗标题中“挚爱的”这一字眼。原因在于殖民地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即妇女在家庭中必须服从丈夫,而且丈夫对整个家庭,包括家里的奴隶,有绝对的控制权,女性在家中是没有发言权的。此外,女性对丈夫应使用尊称,若使用“亲爱的”“宝贝”“爱人”等称谓则将遭受强烈的谴责。显然,布拉德斯特里特颠覆了清教教义对女性情感表达的束缚。虽然在诗集《美洲新崛起的第十位缪斯女神》未发表前,布拉德斯特里特只是写给丈夫看的,未曾想过将其公布于众。塞缪尔·莫里森曾就此提到布拉德斯特里特:“在早期的马萨诸塞殖民地有位诗人因诗歌创作诗歌,仅仅为了表达自己的想法与心愿,且从未对家人与朋友之外的观众有过期待”(Morison,1981:320)。诗歌本身的确印证了布拉德斯特里特对教义束缚的挣脱。另一方面,布拉德斯特里特对丈夫爱的表达同样颠覆了清教规约。该诗开篇布拉德斯特里特强烈表达了她与丈夫之间深厚的爱:
假如曾有两人合一体,那当然就是我和你,
假如曾有男人被妻爱,那当然就是你。
假如曾有妻子因丈夫的爱而感到幸福,
就和我相比,女人们,如果你们能够。(Bradstreet,1967:225)
布拉德斯特里特运用首语重复法,结构均衡,层层递进,强调了夫妻间相互的爱,颠覆了清教社会的男权体制,突出了布拉德斯特里特觉醒的女性意识。清教教义主张男女平等,但性别化领域的社会分工将女性局限在家庭领域。而家庭成为布拉德斯特里特突破女性身份——越界公共领域创作诗歌的纽带。虽然布拉德斯特里特的诗集《美洲新崛起的第十位缪斯女神》由其妹夫约翰·伍德布里奇在其不知情的情况下秘密出版的,并且伍德布里奇还在卷首语中一再强调她是在照顾好八个孩子的前提下利用闲暇时间创作的,但实际上,她诗集的成功出版成为其向清教社会发出挑战的标志。
此外,布拉德斯特里特以暗喻的方式描述了其对丈夫真挚的爱:“我珍惜你的爱胜过所有的金矿,/或者胜过所有东方的财富”(225)。布拉德斯特里特暗指拥有了丈夫的爱就像拥有享受不尽的财富一般。此外,“我的爱如此炙热河水不能浇熄,/除了你的爱任何东西无法补偿”(225)。布拉德斯特里特对丈夫的爱就好比燃烧的火焰,水是不足以熄灭的。并且,她的爱“任何东西无法补偿”(225),唯独其丈夫的爱。海伦·坎贝尔将其与丈夫之间的爱描述为“平淡却热烈”(Campbell,2015:86)。两人聚少离多,丈夫忙于公务,布拉德斯特里特在家照顾孩子、料理家务之余多以创作诗歌的方式寄托对丈夫的思念与牵挂,这样的生活固然平淡却也热烈。对于布拉德斯特里特而言,丈夫的爱不可超越。显然,她间接颠覆了清教教义中清教徒不被允许对任何人的爱超过上帝的规约。
抑制在《献给我挚爱的丈夫》中表现为布拉德斯特里特对上帝的祈求。新历史主义中,抑制表现在对颠覆性力量的压制与对权威的顺从。布拉德斯特里特的爱只有丈夫的爱可以平衡,而丈夫的爱她是无法回报的。“我无法报答你对我的深爱,/我祈求上天给你多种回报”(Bradstreet,1967:225),此处,布拉德斯特里特表现出了对女性身份卑微的认同。作为一名清教徒“按照现世的律法活在这个世上,但不能忘记还有个更高的世界”(Miller & Johnson,1963:287)。因此,每当布拉德斯特里特感到力不能及时,她习惯性地求助于上帝来实现自己的愿望。一首个人体验上帝的诗歌,“其最终价值便是上帝的显现”(Rich,1979:26)。虽然该诗表达了布拉德斯特里特对丈夫炽烈的爱,但是只有上帝对这份爱的维护才可以使其持久。此外,她还在《写给因公出差在外的丈夫的信》一诗中与上帝协商并祈求保佑丈夫。
婚姻中对丈夫的爱与对上帝的敬畏在《献给我挚爱的丈夫》中得以实现。在该诗的结尾处,“那么在世时,让我们在爱中相守。/当我们谢世时,我们在爱中永生”(Bradstreet,1967:225)。一方面,清教教义主张肉体的死亡即代表世间一切关系的结束,而布拉德斯特里特试图跨越时间与空间寻求真爱的永恒。另一方面,布拉德斯特里特将世俗中肉体的结合作为其精神协合的保障,协合了对丈夫的爱与对上帝的虔诚。在温迪·马丁看来,布拉德斯特里特的诗歌“反映了她在爱丈夫和孩子与对上帝的虔诚之间的挣扎,她反复提醒自己在协助其家庭服务上帝中她作为妻子与母亲的责任。为了丈夫与孩子的幸福而爱他们是对现实世界危险的依附”(Martin,1979: 41)。在《纪念我亲爱的孙女伊丽莎白·布拉德斯特里特》中,布拉德斯特里特在对孩子早逝的哀恸与栖于天堂的宽慰中达成了协合。
颠覆是布拉德斯特里特在《纪念我亲爱的孙女伊丽莎白·布拉德斯特里特》中抱怨孩子早逝的表现形式。在新历史主义者们看来,颠覆即是对权威的反抗。首先,这首挽歌颠覆了文艺复兴时期的挽歌传统。虽然布拉德斯特里特早期创作了三首对锡德尼,雷利爵士与伊丽莎白女王的挽诗,顺应了英国17世纪20年代一度盛行的用伊丽莎白时期英雄人物作挽歌,展开政治批判的传统,但是在后期创作中,布拉德斯特里特颠覆传统,聚焦家庭内部,创作了许多哀悼家人离世的挽歌。其次,这些家庭挽歌并非简单反映了布拉德斯特里特对亲人的悼念,而是其与上帝协商的见证。其中,该诗传达了布拉德斯特里特对一岁半孙女夭折的痛惜与对上帝的抱怨,颠覆了清教社会的权威。这首诗开篇,布拉德斯特里特连续用了三个“再见”,貌似以平和的语气与亲爱的孩子告别,相信她一定会在天堂继续享乐,但实际上是在为提出对上帝的不满作铺垫。“通常树木等到茁壮才开始萎缩/李子与苹果成熟了才会脱落/谷物与植物在合适的季节才被收割”(Bradstreet,1967:235),布拉德斯特里特深知世间万物由上帝掌管,清教徒应完全服从上帝的旨意,不断否定和反省自身的缺点和错误并对照教义来纯洁自己的灵魂。但是此处,布拉德斯特里特将万物的自然生长作为与上帝协商的筹码。“新长出来的嫩芽便急于根除/开放时间如此短暂的新生花蕾/命运全掌握在他的手中”(235),布拉德斯特里特将一岁半的孙女比作新长出的嫩芽,抱怨上帝的不公,指责其对植物仁慈却对有旺盛生命力的孩子残酷。向上帝讨公道、对上帝的善与否进行质疑无疑是对上帝权威的攻击。布拉德斯特里特与上帝的协商颠覆了清教教义中完全服从上帝的教义。
抑制是布拉德斯特里特与上帝协合的另一表现形式。一方面,上帝的意志是任何人无法左右的。孩子的早逝已成事实,布拉德斯特里特不得不接受这一事实;另一方面,作为祖母,布拉德斯特里特对孩子无比疼爱,孩子受尽了世俗之苦,因此,希望孩子能在天堂享乐。诗歌开篇的“再见”包含着布拉德斯特里特对孩子的无限祝福。为了孩子的幸福,布拉德斯特里特选择抑制自己的不满去相信天堂可以带给孩子快乐。
协合表现了布拉德斯特里特对上帝的妥协。尽管布拉德斯特里特因孩子早逝对上帝无比抱怨,但她仍然认为上帝的旨意自有道理,人生历练是上帝教化人的灵魂的过程。因此,她接受了孩子早逝的事实,融合了对孩子的爱与对上帝的虔诚。
3.结语
安妮·布拉德斯特里特以女性视角书写了清教社会意识形态下女性的宗教体验与家庭生活,其诗歌所反映的协合既助其逃脱了神权体制的审查又推进了其文学理想的实现,这也恰恰是布拉德斯特里特文学独创性的突出体现。布拉德斯特里特鲜明的个人主义、女性意识与协合既启发了读者对神权体制的反思又为后世女诗人如艾米莉·迪金森、玛丽安娜·摩尔、伊丽莎白·毕肖普、西尔维亚·普拉斯等优秀女诗人开辟了追求女性解放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