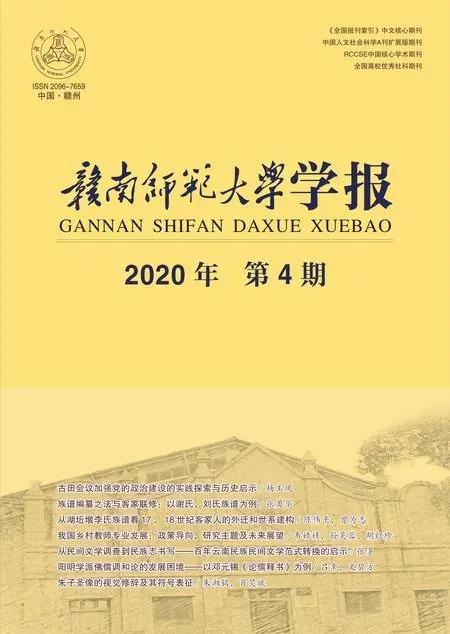江右王门刘元卿的教育实践与思想*
彭树欣,朱晓丽,彭雨晴
(1.江西财经大学 a.人文学院;b.图书馆,南昌 330013;2.内蒙古师范大学 经济学院,呼和浩特 011517)
刘元卿(1544—1609),字调父(甫),号泸潇,江西安福县人,是明代江右王门中后期代表性人物之一,既是心学(阳明学)大家,又是教育家。其一生主要从事教育事业,办学、讲学几乎贯穿其成年后的整个人生,并形成了自己的教育思想。其教育实践、理论受其心学思想的影响,特别是仁学思想是贯穿其整个教育的核心和灵魂。目前尚未见对其教育进行全面研究的论文,故值得深入探讨。
一、刘元卿的教育实践(1)此内容主要依据笔者编纂的《刘元卿年谱》(未刊)而成,其中内容多未加直接引证。
刘元卿的教育属于广义上的教育,包括学校(书院)教育、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但不包括科举教育。他从20几岁开始从事教育,一以贯之,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年,几乎从未间断过。他首先是活跃的教育实践家,实践活动非常丰富,包括创办书院、举办讲会、受邀到各地主盟讲会、礼请同道来讲学等。
(一)创办书院(会馆)
刘元卿是地方性教育活动家,其教育活动的据点主要在家乡安福西乡(2)安福县历来被分为东南西北四乡(即四片),其中西乡又习称西里。一带。西乡历来是安福教育、文化最为落后地区,在刘元卿以前,从未出现过书院。他与同道一起创办了复礼、识仁、一德、近圣、中道五大书院,其中四座书院是他直接主持创建的。隆庆六年(1572),29岁的新科举人刘元卿联合西里24姓,于书林村创办复礼书院,并作《复礼书院记》阐释其“复礼”以复性归仁的思想。从此西乡有了第一座书院,该书院后来成为当地的文化地标和教育重镇。这一书院是刘元卿从事教育最为重要的场所和据点,其教学的主要活动大多在此展开。万历十九年(1591),与刘孔当、周惟中联合西乡58姓士民于九都东江村创建识仁书院(又称“讲院”),并作《识仁书院记》申述其仁学思想。万历二十六年(1598),王、严、张、谢四姓于西乡岭背村建一德会馆(相当于书院),刘元卿作《一德会规引》。这一会馆是在其影响下创建的,一般也视为其所办。万历二十八年(1600)冬,于城西建近圣会馆(相当于书院)。该会馆在安福县城西,乃属于西乡的范围,刘元卿卒后改为泸潇公祠,成为祭祀兼讲学之所。万历三十一年(1603),与赵思庵、郁达甫等于西乡杨宅建中道会馆(相当于书院)。此会馆规模宏伟,为西里诸书院之最。甚至卒前,还约弟子洪云蒸、江尔海议建吴楚书院于攸县东凤山,惜未成而卒。近圣、识仁、中道、复礼、一德五座书院呈从东到西的分布状态,大约每相隔三四十里有一座书院,从而方便西乡各地村落的士民就近学习。这些书院都是讲会式书院,其创办使讲学、讲会有了固定的场所,从而奠定了西乡教育的基础和格局,大大提升了整个西乡的教育水平,改变了当地文化生态、民风民俗。西乡书院在明中后期刘元卿时达到了辉煌,从此以后直到民国,西乡书院大体保持了这一规模和格局。其中复礼书院的办学最为成功,成为与复古、复真齐名的书院,乃至明清时期吉安府的著名书院之一。
(二)举办讲会
刘元卿的讲学主要以讲会的形式开展(但不限于讲会)。他开始讲学是从家会开始,25岁时,即在家族中倡家会,并著《家规》18条。27岁在省城参加乡试,“时与克所刘公、泗山邹公、毅所彭公及仲弟上卿谋举大会,并联小会,朝夕商证不倦,歌声彻于馆。”[1]此年以全省第五名中举后,声名远播,次年就有临县湖广茶陵州的谭希思、谭子习、尹介卿、彭惟馥等前来纳贽拜师。遂讲学于里中顶泉寺,从此开启其独立授徒、讲学之历程。随后联合茶陵学者刘应峰举办两地葵丘之会,又与西里好友赵师孔、贺宗孔、甘则禹、冯梦熊等至里中各姓讲学,甚至在洞溪村的书林洞中讲学。自复礼书院创办后,讲学步入正轨,从而常规化。复礼书院的讲会有大会、同门会、月会。大会面向整个西乡士民,每年十月举办一次;同门会在五月,面向所有同门师友、弟子;月会除了十月、五月外,每月一次,面向参与书院创办的24姓士民。此外,还有少量同门参与的不定期的小会。后来创办的识仁书院等也大体采用这几种讲会形式,其中各书院大会主要由刘元卿主盟。书院定有会规,现可知者有《复礼书院会规》《识仁讲院会规》《一德会规》。在书院讲会的带动下,书院外还出现了不少家族(祠堂)、家庭式讲会,甚至几姓联会的讲会。这些讲会或者刘元卿亲自主持,或者由其弟子主持。如路溪刘氏祠堂在其弟子的主持下,先有月会,后改为小会(即每月两次);又如他在自家举办众子弟参与的家会,又曾参与洞溪冯氏家会,并作《懒人会说》以开示;再如他联合甘、刘二姓作里仁会,王、严、张、谢四姓有一德会。可以说,刘元卿带动、推进了整个西乡的讲会,使这一文化、教育落后地区的讲会、讲学风生水起、盛况空前,甚至有盖过安福其他三乡之势。万历二十二年(1594)刘元卿到京城任职后,或参与阳明学者举办的大会(如万历二十五年的灵济宫大会),或由弟子发起而由他主盟的同门会、同道会(如万历二十四年的京城射所会),或参与少数同道论学的小会(如万历二十五年李文正公祠小会)等。这样,在某种程度上又与友人、弟子一起推进了京城的讲会。
(三)受邀到各地主盟或主动参与讲会
随着刘元卿学术、思想、教育的声名的日益扩大,安福县其他乡、临近州县的学者不仅慕名而来向其问学请益或互相切磋,而且邀请其外出主盟讲会或讲学。当然,他有时也主动外出参与各地讲会。隆庆六年(1572)冬,邹德涵联会永新西乡,刘元卿赴会,并拜访永新著名学者尹台,之后又与邹德涵、甘雨参与茶陵州茶乡首次举办的讲会,与茶陵学者论学。万历四年(1576),湖广攸县令徐希明请刘元卿主盟讲会,执贽问学者达数十人。万历十四年(1586),又到茶乡参与会讲,并作《茶乡月会序》,阐发其“不容已”思想。万历十七年(1589),应邀至茶陵辅仁书院、水口庙讲学。万历二十三年(1595)八月,受茶陵州守冯谖礼请,会讲于辅仁书院,并作《一气说》,阐发其重要哲学思想“一气说”。万历二十七年(1599)春,受邹德溥礼请,会讲于北乡宗孔书院。万历三十年(1602)秋,参与复古书院大会。万历三十二年(1604)正月,受永新县令庄祖诰之邀,会讲于明新书院志学堂,并作《明新纪会》。万历三十三年(1605)九月,王时槐在庐陵西原会馆举办同门会,特邀其与会。万历三十四年(1606),受门人攸县洪云蒸洪之请会讲于金仙洞。万历三十五年(1607)九月,赴吉安青原讲会。这些外出的讲学,加强了与同道的交流,传播了他的思想,推动了讲会的深入,影响了周边地区的学风、民风。
(四)礼请同道来书院讲学
为促进学术的交流,让学子接受更多思想的熏染,刘元卿常邀请同道好友前来西里讲学传道,因刘元卿讲学的据点主要在复礼书院,故多邀学者在此讲学。在该书院创办之前,他曾礼请安福北乡黄旦主盟西里杨宅大会,并借此讲会之机倡建复礼书院。万历六年(1578)春,延请吉水罗大纮来复礼授业,“集乡之茂才弟子及邻楚名士数十人,执经讲业数阅月。”[2]万历十二年(1584)春,礼安福南乡王时槐会讲于复礼书院。此后王氏还多次来复礼讲学。次年冬,又礼茶陵刘应峰会讲于复礼,再会于家祠。此外,邹元标、邹德溥等也曾受邀来复礼讲过学(但具体时间不可考)。这些学者均是著名的阳明学者,黄旦为布衣学者,被称为邹守益的“师门颜氏”,罗大纮、王时槐、邹元标、邹德溥均为江右王门中后期的代表性人物,刘应峰为湖广阳明学者(罗洪先弟子)。他们来复礼讲学,使复礼成为阳明学的一个重要学术交流平台,从而活跃了当地的讲会和学术风气,促进了西里教育、文化的发展。
此外,刘元卿还在自己家乡南溪联合兄弟和里中人士,置义田,建义馆,延塾师教子姓之贫者。因来学者日众,万历十八年(1590)还在自家屋附近建章南馆(家学馆),以待来学者。这是刘元卿晚年除复礼书院外的又一个重要的教学场所。
二、刘元卿的教育思想
刘元卿不仅是教育实践家,而且是教育思想家,其教育思想具有较为丰富的内容,总体上主要包括如下两大内容:
(一)“孔子贤于尧舜”的教育价值观
此言出自《孟子·公孙丑上》,孟子引宰予之言:“以予观于夫子,贤于尧舜远矣。”朱熹注引程子言曰:“语圣则不异,事功则有异。夫子贤于尧舜,语事功也。盖尧舜治天下,夫子又推其道以垂万世。尧舜之道,非得孔子,则后世亦何所据哉?”[3]234程子只从事功方面(即传尧舜之道)解释“孔子贤于尧舜”,刘元卿则从多方面阐释之,使之成为其重要的教育价值观。从地位上说,尧舜为君,是圣王;孔子为师,是素王。前者代表政治家,后者代表教育家。二者均追求行仁道于天下,何以后者贤于前者?
其一,从实践的主体看,尧舜以君相为仁,而孔子以师友为仁。刘元卿比较二者曰:“孔子而前,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以君相为仁。孔子起匹夫,独以师友为仁。以君相为仁,则所以仁天下者,惟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耳;以师友为仁,则人皆可以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夫使人皆可以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虽谓其贤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岂其过也!”[4]179-180就是说,以君相为仁,只能使君相自己成为仁者、圣贤,他们广施仁政于天下,使百姓受益,而百姓只是仁被、恩泽之对象,故道德实践的主体只是君臣;而以师友为仁,则是广施教化,以人治人,意在开启人心之仁,使人人皆可为尧舜,故人人都是道德实践的主体。孔子通过师友之间的教化、开启、点拨,使人认识自己生命的价值,挺立自己的德性人格,使自己成为自己的主人,从而使人取得了主体性地位。
其二,从实践的条件看,尧舜行仁需要各种条件,而孔子行仁则几乎是无条件的。刘元卿比较曰:“盖尧、舜学为君,得位而后行之;孔子学为师,大行如是,穷居亦如是。时时可学,时时可教,造化在手,博济无穷。”[4]564又曰:“尧舜得位,则相关之心遂;伯夷不得位而望望然不屑就,无术以就之也;柳下惠不得位而由由然不屑去,无术以易之也;伊尹不得位而栖栖然就桀就汤,无术以自致其相关之仁也。夫伯夷直去之耳,下惠能就之而不能易之,伊尹能易之而不能自致,其为术未神也。孔子游目于三圣人之外,而独得乎为仁之方,其心盖曰使为仁而必藉君相,则不得君相,仁终不流矣。今夫师友,固亦吾之君相也。切之砥之,君相之事备矣;明之觉之,君相之道著矣;引之垂之,君相之则立矣。”[4]109就是说,尧舜行仁,需要借助权位,需要贤臣辅佐,需要顺应时机,否则无法成功;作为臣子,则需要依靠仁君才能行仁,如伯夷、柳下惠没有遇到仁君就无法行仁,而伊尹只有易君而臣才能行仁。而孔子行仁,不需要君或臣之位,一介平民就可以设馆施教,以师友为君相,素位而行,处处可行、时时可行,无天下而仁天下。
其三,从实践的方法看,尧舜为仁之方是博施济众,而孔子则是己立立人、己达达人。元卿比较曰:“博施济众,尧舜之所以同仁(按:同仁即为仁也)也,而非孔子之所以同仁也。夫欲立则思立人,欲达则思达人,此人之本心也,吾如是,人亦如是。此不可近譬而得之乎?故立一人,则人之不立者,斯人将立之矣;达一人,则人之未达者,斯人将达之矣。以一人施天下,则用力甚劳,而其施不得不竭,此尧舜所以病(按:病,心有所不足也[3]92);以天下立达天下,则操术甚逸,而其济不得不博,此孔子所以不病。病者贤乎,不病者贤乎?斯宰我所以独高孔子也。而要之,孔子之所以独贤,诚得其同仁之术之巧者耳。”[4]230所谓尧舜博施济众,就是以一己之力广博施行于天下万众,就算尧舜用力甚勤,但总有其力所到达不了的地方,故尧舜仍有所不足之处。所谓己立立人、己达达人,就是先成就自己的仁心,然后推己及人再成就他人之仁心。此仁心、本心是一体贯通的,吾如是,人亦如是,通过立达之方使人人各得其仁心、本心,“人各得其真心,则天下平,斯至易至简之术也,斯孔子操之以开万世太平者也。”[4]19此立达之方操之甚逸,即师传弟子,弟子为师又传弟子,己立立人,己达达人,如此不断地推行天下后世,故能真正地博施济众,故孔子无不足也。
其四,从实践的效果看,在成己、成物以及功业上,孔子均贤于尧舜。刘元卿曰:“自其成己而言,真有贤于尧舜之所以进修者。尧舜得天虽厚,然不能如孔子一生处朋友之中,起予助我,发愤无已时。自成物而言,真有贤于尧舜之所以资益者。尧舜虽得五人,却原是天生之以赞帝治者,何能如孔子一向陶冶群才,虽勇夫、富贾,率成上贤。自其功在万世而言,有真有贤于尧舜之所以存心天下者。尧舜得位则仁行,无位者绝望于圣贤之路,自孔子以匹夫提七十子,明道觉世,流仁无穷,万世之下,莫不知人之皆可以为圣人。”[4]72-73就是说,在成己方面,尧舜是天纵之才,不主要得之于个人修养,而孔子则主要靠个人修养,好学不已、发愤不已。在成物方面,尧舜之臣,非其陶冶而成,而是天赐予者,而孔子则成就了一大批人才,所谓七十二贤人,且大都来自中下层士人。从功业看,尧舜可以施仁政于民众,但不能使民众走上圣贤之路,且其功仅在一世,而孔子则是开启人之仁心,使人人皆可以为圣人,仁流无穷,功在万世。
从以上各方面看,刘元卿认为“孔子贤于尧舜”,其隐含的意思其实是说教育家、文化人高于帝王将相,前者所从事的事业也优于或高于后者。这是对教育、文化价值的高度肯定,同时也是对权位、权力的委婉批评。这也是刘元卿对自我人生价值的认定。他为官时间不到五年(按:虽跨五个年头,实际为官时间只有三年多),几乎终生从事教育事业,且如孔子般不厌不倦地投身于办学、讲学中。应该说,对于这种教育人生,刘元卿是自我满足的,其释孔子之言曰:
其(即孔子)自言曰:我时习此学而悦,朋来共学而乐,人虽不知而不愠也。夫且不知不愠,而又何必于得位?是故日与二三子,为政于洙泗之上,不问治乱,不关进退,赤身扶元,化为万世开太平。[4]503
人生能如此,何必要追求权位?又有何遗憾呢?这虽是说孔子,其实也是刘元卿自己的“夫子自道”。这种观念也是明中后期以来,士人的人生价值的一种重要转变,即由“得君行道”转向了“觉民行道”。刘元卿可谓为“觉民行道”找到了人格典范及重要的理论依据,即孔子其人及“孔子贤于尧舜”之说。
(二)教育即是仁教
刘元卿的教育思想与仁学思想交融在一起,在本质上是不可分的,只是由于现代学术言说的需要而分之。上述其教育价值观即与其仁学思想相关,此专论融合其仁学的教育思想。可以说,其教育思想主要是对儒家仁学(或仁教)思想的阐释、发挥和丰富。其教育无关乎科学知识,本质上是仁教,是仁德之教、仁爱之教、人性之教,目的在于使天下同归于仁。刘元卿的仁教思想主要包括如下五个方面的内容:
其一,为学首在辨志(志仁)。“辨志说”首发于陆九渊,其辨志在于“义利之辨”,志于义为君子,志于利为小人。刘元卿继承了这一思想,提出“吾侪为学,须先辨志者,辨大人之事、小人之事”,[4]376即为学须先辨别何者为小人之事,何者为大人之事,从而选择大人之事。他认为,小人之事易知(按:无非为个人衣食、名利谋),而大人之事难知。何谓大人之事?“居广居,行大道,斯大人之事也……夫大人之事曰仁与义,杀一无罪,恻然而不忍,非其有取之,赧然而不为,人皆有是心也。达之于所忍所为,此为大人而已矣。是故得志,则以此泽加于民,是为大人在上位者之事;不得志,则以此修身见于世,是为大人在下位者之事。”[4]376-377也就是说,大人之事就是仁义之事或行仁义之事。他又认为,择术就是要选择处仁而非处不仁:“择学术者,无如处仁。处仁者知仁无尽,为仁之功亦无尽。爱人不亲以反其仁,行有不得皆反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是役天下之术也。孔子处仁,七十子中心悦而诚服焉,盖其验已。处于不仁者,一副精神只在人身上寻觅,全不干当自己事,到底来人亦绝不亲附,是为人役之术也。耻为人役,则莫如为仁。仁岂有他道哉?反己而已。”[4]391所谓择术(也称慎术)就是辨大人之事、小人之事,为大人之事就是处仁,为小人之事就是处不仁。比较而言,陆九渊“义利之辨”重在说义,而刘元卿“辨大人之事、小人之事”重在言仁,虽有时仁义连说,核心仍是仁。如此,为学辨志就是要志仁、处仁、行仁,就是“精神归着一处,真正研磨孔孟血脉,步步踏着孔孟路径”。[4]46
其二,学与教之本体或内容为仁。仁是刘元卿哲学的核心概念之一,而仁与学、教之关系密切。刘元卿曰:“说个‘仁’字,真是天地此仁,万物此仁,吾身此仁,原无自他可分,亦无今古可间。吾辈今要求仁,功夫无处说起,故孔子于此只得点个‘学’字。见得心量原无穷,吾学亦无穷,此方是大工夫。然此‘学’字,又非空空茫无着落。盖学也者,所以学为君也,所以学为师也。欲明君道,须明师道,故学即在教上,学此,方是大学术。即教以学,即学以教,用以此行,舍以此藏,不假权势,其仁常流。”[4]66就是说,仁在天地万物(包括人)之中,无人我之分,无古今之间,是一个形上本体,为仁功夫在于学,仁即在学中。如何学?学是学为君、学为师。而君师即是仁之主体,其精神就是行仁于天下,其手段就是教、就是让人学。故学是为了教,教是为了学。如此,为仁之功,在于学,亦在于教。刘元卿又认为,仁即人之本心、仁心,“默识此心,本通天下,本贯万世,直欲与天下万世之人归于善则已矣。以此学,即以其学为教;以此教,即以其教为学。……故曰惟孔子识仁。”[4]220所谓“以此学,即以其学为教”,是说以此仁作为学的内容,就是以此学的内容(即仁)来教人;所谓“以此教,即以其教为学”,是说以此仁作为教的内容,就是以此教的内容(即仁)来使人学。如此学与教的内容即是仁,所谓学与教就是直接默识、体证此仁心之通天下、贯万世、止于至善。总之,在刘元卿看来,仁是本体,学与教是工夫,或仁是内容,学与教是手段,仁体现于学与教中。
其三,教学之方。上文言“孔子贤于尧舜”,其中原因之一是,从实践的方法看,尧舜为仁之方是博施济众,而孔子则是己立立人、己达达人。其实,在刘元卿看来,己立立人、己达达人,是为仁之方,也是教学之总方、总则,教与学无非是立达之事。同时,他又认为“教无定术,医不执方”,主张因病施药,因材施教。如其曰:“吾人眼底看得圣贤太高,是害虚怯症,须服大承气汤;看得俗人太低,是害呕吐症,须服平胃散。看得自己浑身是病,是害忧疑症,须服朱砂定心丸;看得自己浑身无病,是害麻木症,须服消风败毒散。看得此道太玄,耽无溺妙者,是名脱阳症,须用参着补中益气;看得此道太浅,不著不察者,是名青光眼,须用金针拨转瞳人。故教无定术,医不执方。”[4]485这是用比喻的说法针对不同人的毛病,提出不同的救治方法。故元卿肯定孔子教学的灵活性,而批评当时学者教人只言“良知”“致知(致良知)”“孔子以仁为宗,而《鲁论》二十篇中,未尝语语揭仁之。虽未尝语语揭仁,而语语仁也。懿子问孝,告之无违,他日所以语武伯者,迥乎与无违旨远矣。子游问孝,告以敬养,他日所以答子夏者,迥乎与敬养之旨又异矣。藉第令语道于今日,必以为舍良知无本体,舍致知无工夫……今有人问孝,而告之曰致良知,此亦无不可者。然执人人之手,而教之曰良知,则懿子聆焉而武伯可以退矣,子游闻焉而子夏可以出矣。教亦多术,何必若是其局且拘乎?”[4]490其实这也是对王阳明的批评,阳明认为自己“除却良知”,别无所讲。[5]不过,刘元卿也提倡常用之方,“若颜之‘四勿’,孔之‘四君子’,可谓仁之方也已,不拘冷热,服之神效。”[4]485“四勿”,即“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3)刘元卿特制“四勿汤”以药人:“五色令人目盲,人能非礼勿视,是医眼妙方;五声令人耳聋,人能非礼勿听,是医耳妙方;多语令人口噎,能非礼勿言,是养气妙方;妄动令人体疲,人能非礼勿动,是养身妙方。此吾孔氏‘四勿’汤也。”见:刘元卿《书蓝秀南扇》,《刘元卿集》,第486页。“四君子”,即“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论语·公冶长》),是指君子四个方面的为人之道。
其四,师友(弟)间教学之乐。自周敦颐提出寻“孔颜之乐”以来,乐学一直是宋明儒者一个重要的主张,王艮甚至创作《乐学歌》以总结为学之乐。所谓乐学,本质上是反求生命本体之乐,也就是说乐学是对生命本体的体证、觉悟,只有见体、见道才能得真正的生命之乐。刘元卿受到这一主张的一定影响,但其关于教学之乐的思想主要来自对《论语·学而》“时习”章、《述而》中“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为之不厌,诲人不倦”的创造性阐释。刘元卿曰:“盖古之学者必有师,言学即学于师也。故传习以时,夫子以为悦;朋来自远,夫子以为乐;得师友而遯世不见知,夫子以为不愠。不愠者,言乎以师友为仁,固不藉名位,不求声闻也。彼其所重、所乐在为仁,故其所取以为仁者在师友。”[4]108-109此言师友(弟)间教学相长、交流之乐,此乐的关键在于相互间都在为仁,而为仁不藉名位,亦不求声闻,此间固有真乐在也。此为仁之乐又何在?在于此学不厌,此教不倦。元卿认为,“仁道至大”,学是学此仁,“学则不厌,默识其万物备我者而全之,故不厌也”;教是教此仁,“教则不倦,默识其万物皆我者而公之,故不倦也。”[4]41又曰:“故学也者,长养微阳之真舟也。从此用力愈约,而进机愈无穷……学惟无量,故不厌;教惟无方,故不倦。”[4]34正是见得仁道至大、心量至大,即默识、体证到心与天地万物一体,生命进入无限广阔之境,从而脱离了狭小的自我,故学才不厌,教才不倦。不厌不倦就是至乐之境,此乐是师友(弟)间共之,与天下人共之,乃世间之大乐也。
其五,为学如探海攀天。刘元卿认为,所谓学者,即仁学也。关于仁,其曰:“仁也者,吾人之生理也,探之无朕,达之无垠。”[4]1410又曰:“仁道至大,本无一物不备,亦无一物不体。”[4]562正因为“吾仁之本通天下、本贯万世”“仁无尽”,故“为仁之功亦无尽”。[4]502,391“为仁之功”即是为学,对此,刘元卿曰:“为学如探海,如攀天,游乎无穷,本无所及也。故学如不及,犹恐失之,况自以为及,宁有及乎?孔子学不厌,默识其无所及者而学,故不厌也;教不倦,默识其无所及者而教之,故不倦也。伯夷及乎清,下惠及乎和,清和之外,学则厌、教则倦矣。厌与倦,皆不可已而已者。不可已而已也,不仁者也。惟不能默识吾仁体之全,是以有所及,必有所不及。学至于无所及,斯其及大矣。”[4]470此言为学如探海、如攀天,无有止境,孔子正是学无止境的代表,而伯夷止于清、柳下惠止于和,是有止境者,学至于无所及、无止境才是“大”学。为学是仁心的不断扩大,“仁,人心也。求之念,譬之犹浚井也;求之家,引而之川也;求之立人达人,引而之海也。海则无尽矣,观于海者难为水,孟子盖识之也。”[4]369孔子讲立达功夫,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仅己立己达还不够,必须立人达人,人以及人,立达无尽,才是学之无尽。“为学如探海、如攀天”,本质上是指其学走出个体狭小的自我,通向了家国天下、宇宙万物,也通向了过去与未来,通向了无穷无尽的生命境界、天地境界。
总之,仁学渗透、贯穿于刘元卿教育思想的方方面面(主要包括教育的目的、内容、方法、成效、境界等五个方面),使其教育成为其仁学的具体体现,使教育本质上成为一种仁教体系,从而一方面丰富了其仁学思想,另一方面又深化了其教育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