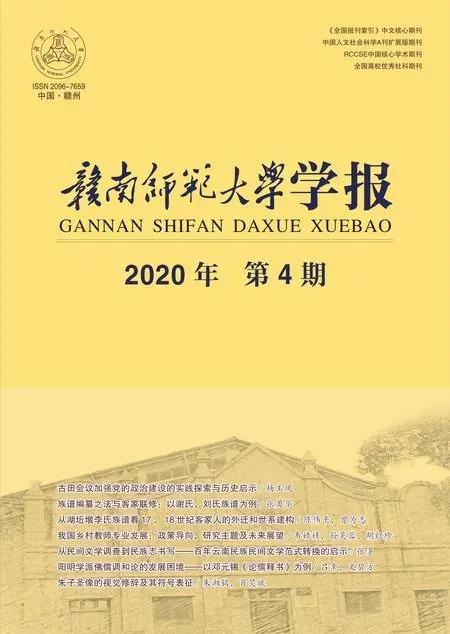朱子圣像的视觉修辞及其符号表征*
朱湘铭,肖炅斌
(1.赣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西 赣州 341000;2.中共珠海市香洲区委政策研究室,广东 珠海 519000)
朱熹画像伴随着朱子学说受到后世,尤其是元、明、清三代统治者的青睐和推崇,因而由普通人物画像被尊奉为圣像。当前,学界针对朱子图像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文献的搜集整理与考辨。高令印、方彦寿、朱杰人以及台湾学者陈荣捷诸先生均在该领域用力颇深,所取得的研究成果令人瞩目。其中,高令印专门探讨了福建各地新发现的朱熹画像石和塑像。[1]302-316陈荣捷梳理了海峡两岸及日本等地的朱子画像。[2]80-87方彦寿的著作后出转精,详尽考辨了中国历代以及韩、朝、日等国出现的各类朱熹图像和书帖。[3]3-113朱杰人则主要针对近年来社会上广为流传的朱子画像被张冠李戴现象进行了辨伪。[4]
上述研究,为全面了解和进一步研究朱子图像奠定了坚实基础。然而,流传了数百年的朱子圣像不仅仅是对其视觉形象的表象感知,其背后蕴含的诸多视觉修辞现象和文化内涵值得深入探讨。时至当下,朱子圣像为何会出现不同图式,并引起学界围绕朱子“真容”与“伪像”的论争?事实上,朱子圣像早已不是单一的图像文本事实,而是一例典型的图像符号传播案例,其“格式塔特质”值得我们深入探究。
一、“自戒”与“垂训”:朱熹画像钩沉及类型分析
朱子画像的缘起,一般认为肇自他人为朱子所作的画像以及年逾花甲之时的对镜写真像。从现今存世文献的梳理来看,最早的朱子画像据信诞生于宋孝宗乾道九年(1173)。朱熹《写照铭》对该画像作了记载:“乾道九年,岁在癸巳,予年四十有四,而容髮凋悴,遽已如此。然亦将修身以毕此生而已,无他念也。福堂□□元为予写照,因铭其上,以自戒云。”[5]3995该画像创作于乾道九年,时年朱熹年逾不惑,正值人生壮年,但已“容髮凋悴”。陈荣捷先生认为,“是年朱子居家著书。年尚壮,而照之容髮凋悴,未必写真也。”[2]80
朱熹画像的另一次创作,发生于南宋孝宗淳熙元年(1174)九月庚子,三山(今福州)郭拱辰为朱子图容写貌,事见朱熹《送郭拱辰序》:“(郭拱辰)乃能并与其精神意趣而尽得之,……而风神气韵,妙得其天致。有可笑者,为予作大小二象,宛然麋鹿之姿,林野之性。持以示人,计虽相闻而不相识者,亦有以知其为予也。”[5]3649可见,郭拱辰的画艺能达到“风神气韵,妙得其天致”的至高境界。朱熹对郭拱辰的创作颇为赞赏,尤其激赏郭氏所画之像以形写神,画出了他的精神气质——“宛然麋鹿之姿,林野之性”。后世也因该画像得到了朱子认可,遂将“麋鹿之姿”当作图写朱子形貌的重要依据。
朱子本人亦为丹青高手,[5]3758据说61岁时曾对镜写真,其《书画象自警》云:“从容乎礼法之场,沉潜乎仁义之府,是予盖将有意焉而力莫能与也。佩先师之格言,奉前烈之馀矩,惟闇然而日脩,或庶几乎斯语。”[5]4005此像赞未标明具体日期,亦不知所赞之像为何。陈荣捷先生认为,“此像可能朱子自画,亦可能为别人所画。既云自警,则以自画视之为宜。”[2]80该画像的创作年代因朱熹《南城吴氏社仓书楼为余写真如此因题其上,庆元庚申二月八日沧洲病叟朱熹仲晦父》诗有“苍颜已是十年前”句,故推测当作于绍熙元年(1190)。
朱子生前最后一幅画像诞生于宋宁宗庆元庚申(1200)二月八日,时南城吴伸、吴伦兄弟建社仓书楼,并为朱子绘制了一幅画像(是年三月九日朱子离世)。朱熹曾题诗云:“苍颜已是十年前,把镜回看一怅然。履薄临深谅无几,且将余日付残编。”[1]541这首七言绝句除提及“苍颜”外,并未过多述及自己的容貌,字里行间洋溢着朱子暮年时的惆怅与不甘。
南宋中晚期以降出现的朱子画像,已由生人画像变成了神像(逝者遗像)。后世摹写往圣先贤的神像并张挂于壁间以供瞻仰、膜拜和规鉴的传统自古就有。如宋人郭若虚指出:“盖古人必以圣贤形像、往昔事实,含毫命素,制为图画者,要在指鉴贤愚,教明治乱。故鲁殿纪兴废之事,麟阁会勋业之臣,迹旷代之幽潜,託无穷之炳焕。”(1)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卷一《叙自古规鉴》,见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续编》本。这种具有“垂训”功能的神像能激发观瞻者丰富联想,原因在于:图像创作者通过视觉修辞,强化绘画的情感表达,对观瞻者的情绪产生影响,激起观者的信仰使之实现道德的升华。
然而,因时空阻隔以及受图像创作者对朱子生平了解的多寡等拘限,他们创作出的朱子神像难免会出现差异,由此衍生出了诸多不同式样和容貌的版本。(2)朱熹逝世后,服膺朱子学说的亲朋故交、门生后学,纷纷摹写朱子神像,张挂于学堂、书院、文庙以及私人书斋的壁间,以示缅怀、瞻仰和膜拜。此外,晚宋及元代出现的朱子像赞数量众多,说明当时行世的朱子神像数量不少。参见方彦寿:《朱熹画像考略与伪帖揭秘》,第11-21页。明初宋濂《宋九贤遗像记》中载有一段针对朱子神像的描述:“晦庵朱子,貌长而丰,色红润,发白者半。目小而秀,末修类鱼尾。望之若英特,而温煦心气可掬,须少而疏,亦强半白。鼻与两颧微齄,齄微红。右列黑子七,如北斗状,五大二小,六在眉目傍,一在颧外,一在唇下须侧。耳微耸,毫生竅前,冠缁布冠,巾以纱,御上衣下裳,皆白,以皂縁之,裳则否。束缁带,蹑方履,履如温公,拱手立,舒而能恭。”[6]295-296这是迄今最为详细的针对朱子容貌的正面描述。
宋濂称该画像乃“世传家庙像影”,既然是“世传”,说明并非时人新作,从时间上大致可推断为明前人的作品。从宋濂的描述来看,画面中的朱子为站立像,所呈现的视觉形象是一位神态安详温煦的长者,儒者风范尽显。与前述郭拱辰刻画的朱子形象着眼于传神不同,“宋九贤遗像”中的朱子面容特征非常明显:一是鼻头和两颧间有红癍(俗称酒齄鼻),二是右脸颊(自眉梢至唇下)生有七颗黑痣,三是眼角末端有鱼尾纹。这一版本的容貌刻画,对后世诸多传世的神像、圣像都或多或少产生过影响。

图1 文公先生像
明代画家郭诩曾作《文公先生像》(见图1),这是现存最早的由知名画家绘制的朱子画像。该作品见录于《钦定石渠宝笈三编·延春阁藏》:“明郭诩画朱子像一轴。(本幅)纸本。纵二尺七寸五分。横一尺八寸一分。设色,画巾服小像。首题‘文公先生像’隶书。款‘后学泰和郭诩拜写’。钤印一,太和郭仁宏印。鉴藏宝玺:五玺全。宝笈三编。”[7]该画像构图简单,无背景陪衬,人物半身像呈略向左倾斜的金字塔形,既显得庄重又不嫌呆板。朱子面容慈祥和蔼,微向左侧身,拱手凝视前方,右脸上的七颗黑痣呈北斗七星状,眼角的鱼尾纹及额头的波浪纹,暗示着这是中晚年的朱子;须髮刻画纤毫毕现,衣褶纹路遒劲有力。从设色和运笔来看,整幅画多施以淡墨,尤其是面部线条的勾勒柔和淡雅,须髮的刻画似用撕毛法,墨色浅淡,线条遒劲如铁线;头巾因用墨清浅而呈透明状,唯有眼睛用浓墨,将炯炯如炬的目光和盘托出。淡着色减弱了黑线与白纸的对比,起到了和谐有致的效果。总体而言,该画像面部表情栩栩如生,通过独特的人物形象刻画,将老年朱子的儒雅气质和盘托出。
与郭诩《文公先生像》颇相似的另一幅画像,是收藏于台湾故宫博物院的《宋徽国朱文公遗像》。该画像从构图到人物形象乃至某些细节,譬如衣褶纹路等,均与郭氏作品十分相似。但也存在差异:《宋徽国朱文公遗像》塑造的朱子面容更显苍老,身躯也略显佝偻。二者的高相似度,似乎暗示了彼此间的某种联系。方彦寿先生认为,“来自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朱子像有脱胎于郭诩画的痕迹”。[3]10
此外,安徽省档案馆收藏有一幅据说是“目前保存最早的朱熹画像”,理由是该画像中有三段题跋,其中居首的一段文字较长,款署“时成化二十三年夏五月吉”。在这段题跋中,一位自称“达”的服膺朱子学说的丹青手,自述从他人处得到一本朱子年谱,并对其中朱子画像甚为景慕,故“切摹先生之真”,作此画像。方彦寿先生认为,此像所据底本即叶公回之《朱子年谱》中的插图。[3]52
除上述以丹青形式出现的朱子画像之外,还有一类是以插图(版画)形式出现的朱子图像。方彦寿先生爬梳了大量史料文献,以详尽可靠的内容、平实流畅的分析论证,完成了他关于古代书籍版刻中的朱子插图研究的系列文章。[3]在众多版本的朱子插图中,有以下诸版本值得关注和分析:

图2 《朱子实纪》 图3 《紫阳朱氏建安谱》

图4 泳古堂刻《朱子年谱》 图5 《朱子文集大全类编》
其一,《朱子实纪》本(见上图2)。《朱子实纪》由明代婺源人戴铣刊行于正德八年(1513)。该书“纪朱子之始末,与夫今昔尊崇之实”,卷首有《太师徽国文公像》,并称“右像乃朱氏家庙所藏文公六十一岁时所写真也,兹谨模寘卷端,使学者得以想见大贤道德之气象云”。[8]嘉靖三十一年(1552)刊行的《紫阳文公先生年谱》卷首朱子像与戴氏《朱子实纪》本几乎完全一样。《紫阳文公先生年谱》由宋人李方子原编,明李默、朱河订补。该本卷首的朱子像上方题“文公先生年六十一像”。
其二,《紫阳朱氏建安谱》本(见上图3)。该谱修于明万历四十八年(1620),由朱熹十五世孙朱莹主纂,其中朱熹像题为“九世祖文公真像赞”。画像上方为明景泰皇帝钦颁的像赞。该画像与其他传本画像颇不一样:朱子身着朝服,交领右衽,手执朝笏,头戴五旒冕冠,项上着方心曲领,显得威仪整肃。清康熙二年(1663),朱子后裔婺源朱烈订梓的《紫阳朱夫子年谱》卷首朱子像题“紫阳朱夫子遗真圣像”,沿袭了《紫阳朱氏建安谱》本旧制。此外,清康熙五十六年(1717),杨毓健《重修南溪书院志》中的朱子像,以及晚清戴凤仪编纂的《诗山书院志》中的朱子像均承续了该图式。
其三,清舒城黄氏泳古堂刻《朱子年谱》本(见上图4)。该年谱由清人黄中编订,曾于清康熙十七年(1678)刊行于江宁,又于康熙二十九年重刊。卷首有《太师徽国文公真像》,图左文字云:“右像乃家庙所藏文公六十一岁时所写真也。威仪俨肃,与尝泛观者大相径庭。因拜手谨依原像摹写锓梓于卷端,使观者亦可想见先生平生之气象云。”[9]
其四,《朱子文集大全类编》本(见上图5)。该书由朱熹裔孙朱玉于清雍正二年(1724)编纂并刊行,卷首有圆月形“朱文公遗像”,被学者们奉为最经典的朱子自画像。值得一提的是,该像与明人赵滂编纂的《程朱阙里志》卷二《崇祀志》中的“晦菴文公像”颇相似。
以上胪列的诸本朱子像属人物绣像,另一类朱子版刻像则为情节插图。这类图像往往刻画出多个人物或某个特定场景,其功能除叙事之外,还能凸显核心人物的形象及性格特征。譬如由武夷徐表然撰、孙世昌刻印于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的《武夷志略》,在其《寓贤志》中,精心绘制了卅一幅与武夷山相关的理学先贤版画。清乾隆十六年(1752)由董天工刊行的《武夷山志》,沿袭了《武夷志略》旧制,绘刻了多幅先贤版画。再如,明万历年间书林午山熊氏刊刻的《重刻丘阁老校正朱文公家礼宗》,该书每卷均配有与内容相关的礼仪示意图,卷首有专门介绍朱熹生平事迹的版画十一幅。
总而言之,从存世的朱子画像来看,可谓形式多样、丰富多彩。就画像的属性而言,既有生像又有神像;就画像的形式和媒介而言,既有丹青作品又有版画石刻。(3)有关传世的朱子石刻画像,参见陈荣捷《朱子新探索》、方彦寿《朱熹画像考略与伪帖揭秘》相关内容。然而,不管是哪种类型和形式的朱子画像,都一致宣称是“真像”,都力图“说服”后世观瞻者:这就是朱子真容!为达至该目的,图像创作者们运用了各种视觉修辞技巧,图像隐喻就是其中之一。
二、“麋鹿姿”与“七星痣”:朱子神像的图像隐喻分析
承上文所述,朱熹《写照铭》中有“容髮凋悴”句就可以看作图像隐喻。(4)隐喻作为一种认知现象,对人类思维方式、艺术创造和语言使用等影响极为深广。美国语言哲学家约翰·塞尔(John Searle)指出,“隐喻意义不是字面意义(literal meaning),而是说话者的表述意义(utterance meaning)”。对隐喻而言,“那种原初的字面意义被超越了,句子获得了一个新的字面意义。这种字面意义等同于之前的隐喻言说意义”。参见(英)戴维·E·库珀著,郭贵春、安军译:《隐喻》,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55页。“容髮凋悴”属人物视觉形象的描绘,即面容和须髮呈现衰老状态。“凋”原指草木经霜冻之后的半伤(衰败)状态。譬如,“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论语·子罕》)。这是借物(松、柏)喻人(君子),符合隐喻“用此言彼”的表达模式,意谓品德高尚之人能禁得起严峻考验。朱熹自称“容髮凋悴”,沿袭了中国古代借物(松、柏)喻人(君子)的隐喻思维,其意旨不仅仅只是为了表达容颜已经衰老,其真实意图可能在于表达理想或志向尚未实现。正是通过当下(“容髮凋悴”)与未来(实现理想、志向的路途依然遥远)的两相对比,才更能凸显言说者内心的焦虑、无奈与忧伤。朱熹毕生身体力行,力图将儒家先哲们的学说发扬光大,儒家“修齐治平”理念更是成了他毕生奋斗的目标。当他目睹写真像时,不禁感慨韶华易逝而宏愿却未实现,故将此画像当作自勉与鞭策的动力。
隐喻不仅仅是一种语言现象,更是人类的一种认知现象。通常,隐喻是在彼类事物的暗示之下感知、体验、想象、理解、谈论此类事物的心理、语言和文化行为。图像隐喻则借助图像语言,诸如线条、颜色、构图等,通过艺术构思创作出具体或抽象的意象,从而实现意义建构。就像宋代画坛自黄筌、黄居寀到徽宗画院再到南宋画院,画家多以具有吉祥富贵寓意的珍禽瑞鸟来寄托对政治升平、生活富足的向往。就朱熹神像而言,“麋鹿姿”与“七星痣”可谓其形象构成的两大视觉要素,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建构起了朱子圣像的丰富文化意义。
何谓“麋鹿姿”?麋鹿者,麋与鹿也。这是两种生活于山林沼泽间的哺乳动物。现代汉语中的“麋鹿”,一般专指原产于中国的鹿科哺乳动物,其形体比牛大,毛淡褐色,雄性有角,角像鹿,尾像驴,蹄像牛,颈像骆驼,整体上又不像哪种动物,故俗称“四不像”。作为野生动物,麋鹿何以与人类文化产生了联系?人们为何会以麋鹿自比?麋鹿与人之间必定存在某些“异质同构”关系。
先秦典籍中有关“麋鹿”的记载,大多与山野荒郊、蛮荒无序的生活状态有关。譬如《晏子春秋》以“麋鹿父子同麀”代指尊卑长幼无序的原始蛮荒状态,《孟子》以“鸿雁麋鹿”代指野外荒郊。后来,人们因麋鹿生活于荒野山泽,远离人世纷争,心生慕往之意。唐初陈子昂《喜马参军相遇醉歌》序云:“吾无用久矣,进不能以义补国,退不能以道隐身。天子哀矜,居于侍省。且欲以芝桂为伍,麋鹿同曹。轩裳钟鼎,如梦中也。南荣曝背,北林设罝。”[10]899表达了陈氏对自然和隐逸生活的向往。李白《山人劝酒》诗有“各守麋鹿志,耻随龙虎争”[10]1692句,赞誉“商山四晧”及上古高士巢父、许由等隐居山野,与世无争的处世态度,透出对隐逸山野之高士的敬慕。此“麋鹿志”指隐居山野的志向,正与李白“功成拂衣去,归入武陵源”的人生理想相符。权德舆《卧病喜惠上人李炼师茅处士见访因以赠》诗有“各言麋鹿性,不与簪组群”[10]3608句,“簪组”指冠簪和冠带,这是士大夫的装束和身份象征。该诗句表明了心迹:欲退隐山林,不与世间追求功名利禄的士夫为伍。唐崔道融《元日有题》诗有“自量麋鹿分,只合在山林”[10]8285句,以“麋鹿”自比,希望像麋鹿一样在山野间自由自在地生活。这可以说是一位避世在野者对自己的人生定位。
宋人苏轼《次韵孔文仲推官见赠》诗有“我本麋鹿性,谅非伏辕姿”[11]9163句。“伏辕”,本义指拉车的马,引申为因利禄功名而奔走的世俗之人。诗句既咏陶渊明不事权贵、不求利禄的遗世独立精神,又当是诗人自己的人格写照。苏轼《和陶饮酒》(之八)诗有“我坐华堂上,不改麋鹿姿”[11]9467句,意谓即便高居庙堂,也不会因功名利禄去攀附,逢迎,附庸,而做出有违本性之事。曾巩《初发襄阳携家夜登岘山置酒》诗有“颇适麋鹿性,顿惊清兴长”[11]5562句,意谓自己的本性与“麋鹿性”颇吻合,言外之意即表明欲立志隐居山林,与麋鹿为伍。
要而言之,无论是“麋鹿同曹”“麋鹿志”“麋鹿性”“麋鹿分”,还是“麋鹿姿”,都折射出了中国古代士大夫们的崇高人生追求。这当中既暗含儒家“穷则独善其身”的处世态度,又有道家“道法自然”“天人合一”思想的文化基因。可以说,麋鹿的林野之性,诸如不受羁约、融于自然等,成了身处世俗社会并深受各种利害关系束缚的人们挣脱“尘网”的精神象征。古人所谓的“麋鹿性”“麋鹿姿”并非附庸风雅的标榜,而是正统士大夫的一种自我(精神气质)的认同和身份定位。朱子赞誉郭拱辰为其所绘真像,认为画作“风神气韵,妙得其天致”,原因就在于画像完美展示了朱子自我认定的精神气质与身份定位。这种精神气质,一经郭拱辰妙手定格,就奠定了朱子在世人心目中的地位。
朱子画像在世间流传最广的核心特征要数“七星痣”了。从《宋史》本传及宋元人所作的年谱、行状及其他记载来看,朱子“颊生七痣”并没有可靠的事实依据。因而“七星痣”说很可能是后人的附会。(5)朱杰人先生认为,宋濂自述其所见画像来自“世传家庙像影”,可以推定朱子家庙所藏画像也是有七痣的。针对陈荣捷先生断定朱子之痣是“传说”的观点,朱先生认为如果陈氏观点成立则会否定朱子自画像的真实性,等于推翻了现存所有朱子像的可靠性。而据陈氏与高令印先生的考证,朱子的自画像应该是可靠的,所以朱子额头的痣也应该是可靠的。参见朱杰人:《朱子伪像考》,《中华读书报》,2017-09-27。据陈荣捷先生考证,朱熹“面有七黑子”之说起于明代。[2]88本文无意推定朱子“颊生七痣”的可靠性,而是试图探究“七星痣”本身包蕴的图像隐喻内涵。
从上文分析来看,目前传世的朱子神像绝大多数都刻意凸显了朱子“颊生七痣”的面部特征。当然也有少数情况例外,那就是画面中的朱子身体略向右侧身,以左脸示人,无法判断其右脸是否生有“七星痣”。譬如刊刻于明代建阳的《事林广记》后集卷三《先圣类》中的朱熹全身像即以左脸示人。
在古人看来,“颊生七痣”是一种天生“异相”,这种“异相”大多成了其人性格气质或人生道路及成就等方面的外在标签或征兆。史传中记载的有类似天生异相之人还有多位:刘邦“左股有七十二黑子”。南朝梁元帝萧绎“背生黑子,巫媪见曰:‘此大贵兆,当不可言。’”[12]南朝梁陶弘景“神仪明秀,朗目疏眉,细形长额耸耳,耳孔各有十余毛出外二寸许,右膝有数十黑子作七星文。”[13]北魏寇讚“尝从相者唐文相,文曰:‘君额上黑子入帻,位当至方伯封公。’”[14]北宋钱守俊“发后有七黑子如斗。在民间时,有乡人目为草中鹘,言其勇鸷也,积官至潘州防御使。”[15]上述例子虽有附会之嫌,但在古人看来,倘若体表生有呈特定形状的黑痣,往往是吉祥之兆——预示着其人将来必定富贵、骁勇、睿智或能力超群。朱子右脸颊有呈北斗状的七颗黑痣,当然也暗示着他并非等闲之辈。这似乎也为朱子的超凡脱俗增添了某些天命色彩。据朱子十六世孙朱玉所编《朱子文集大全类编》之年谱云:“明分巡李稠源(琬)丰城人,曾官婺源令,得之故老传闻云,文公四代祖妣程恭人官坑墓葬,时下有七石,故生文公面有七痣。”(6)朱玉辑:《朱子文集大全类编》册一《文公年谱》,清雍正刻本。值得注意的是,明儒陈献章右脸亦有呈北斗状的七黑子。《明史》载:“献章仪幹修伟,右颊有七黑子。”[16]明人邓元锡《皇明书》的记载更详尽,“(陈献章)身长八尺,目光如电,脸右有七黑子如北斗状。”[17]二者形象或许存在某种关联。
总而言之,无论是“麋鹿姿”还是“七星痣”都以图像隐喻的方式共同建构朱子在世人心目中地位。具体而言,通过麋鹿的某些人所共知的显著特征与人类精神追求的类比,用此言彼,假物言道、以象明理,正所谓“生于直告之不明,故假物之然否以彰之”(《潜夫论·释难》)。作为一代硕儒,朱子在宋、明、清三代士大夫心目中的地位不可谓不高,在儒学倡明时代,朱熹被尊称为朱子,其著作被广泛搜集、整理,大量刊刻,朱子学说被阐发倡扬,朱子的容像势必会引发世人的密切关注。“麋鹿姿”是经朱子明确认可的容像特质,可谓朱子精神追求的象征,而“七星痣”则因其本身包含浓郁的谶纬色彩和天命观,更能激发人们的无限想象,也更能引发普通民众超越理学范畴的信仰崇拜热潮。
三、“睹其貌”与“味其道”:朱熹圣像意义生成与建构
上文述及安徽省档案馆收藏的一幅据说是“目前保存最早的朱熹画像”,该画像中居首的一段文字道明了画像创作缘由:“庶几往来士夫,与夫凡有血气者莫不具尔瞻,肃尔容,端拜秋阳之皜皜,景仰泰山之岩岩,睹其貌而求其心,得其心而味其道,格物以致知,正心以诚意,不徒付之于诵说,向慕想象之间而已也。”[3]51-52这实际上也是历代朱子神像大量涌现的共同理由。
朱子及其神像受到后世膜拜和崇祀,是与朱子身后受到历代统治者的追封和赏赐,其学说受到后世王权操持者的推崇,以至于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这种至高无上的尊荣是分不开的。据《宋史》记载,宋理宗宝庆三年(1227),朝廷赠朱熹为“太师”,并追封为“信国公”。“三月庚戌朔,……工部侍郎朱在进对,奏人主学问之要。上曰:‘先卿《中庸序》言之甚详,朕读之不释手,恨不与同时。’”[18]789朱熹的《中庸章句》深得理宗赵昀青睐,甚至有“恨不与同时”的遗憾。其实这种遗憾对于服膺理学的后世儒生而言,都是普遍存在的。为弥补这种不能与朱子同时的遗憾,研读其遗书,瞻仰其遗像,欣赏其遗墨,就成为晚宋的文化风尚。绍定三年(1230),朝廷改封朱熹为“徽国公”。嘉熙元年(1237),宋理宗“诏以朱熹《通鉴纲目》下国子监,并进经筵。”[18]813至此,朱子理学成为南宋朝廷官方认可的学说。淳祐元年(1241),理宗诏曰:“我朝周敦颐、程颢、程颐,真见实践,深探圣域,千载绝学,始有指归。中兴以来,又得朱熹精思明辨,表里混融,使《大学》《论语》《孟子》《中庸》之书,本末洞彻,孔子之道,益以大明于世。朕每观五臣论著,启沃良多,今视学有日,宜令学宫列诸从祀,以示崇奖之意。”[18]813让朱熹入孔庙从祀,标志着朱熹道学正统地位的确立。只不过因当时宋金对峙,曲阜孔庙处在金人统治区域内,南宋朝廷的这一举措并未真正实现。直到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朱熹才真正进入曲阜孔庙从祀贤儒的行列。
明朝建立后,统治者极力推崇朱熹,不仅以朱子后代自居,而且将朱学当作维持明廷统治的坚强纽带。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清圣祖下诏:“宋儒朱子注释群经,阐发道理,凡所著作及编纂之书,皆明白精确,归于大中至正。经今五百馀年,学者无敢疵议。朕以为孔、孟之后,有裨斯文者,朱子之功最为弘巨。”谕大学士等“议覆宋儒朱子配享孔庙……升于大成殿十哲之次”。[19]雍正七年(1729)曲阜孔庙大成殿重建落成,重塑朱熹像,列“十二哲”第十二。[20]
自宋迄清,朱子屡受朝廷推尊,尤其是程朱理学被作为取士标准进入科场后,民众(尤其是士夫阶层)对朱子的崇祀之风日炽,各地纷纷建祠立庙,大兴书院,肆力传播朱学。由此,朱子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不仅仅是儒学先贤,甚至成了不亚于宗教信仰中的神祇,因而其画像也由神像变成了圣像。不同场合(基于创作初衷或作品用途的不同)的朱子圣像,因受特定环境的影响而呈现不同的风格特征和画面形象。譬如上文述及以《紫阳朱氏建安谱》为代表的“朝服版”朱子颇特殊。画面上的朱子头戴五旒冕冠,这在等级制森严的古代社会,绝不允许胡乱穿戴,更不允许僭越使用,因而成了区分身份地位尊卑的显著标志。除天子外,允许著冕服的有:公、候伯、子男、孤、三命之卿、再命大夫、一命大夫。朱熹爵位为男爵,故所著冕服为五旒冕冠。图像绘刻者通过这一独特的服饰意象——五旒冕明确标示出了像主的特定身份和社会地位。
颇值得玩味的是,“朝服版”朱子多出现于由朱子后裔编纂的家谱、年谱,另有清人杨毓健《重修南溪书院志》和戴凤仪《诗山书院志》中。其中《诗山书院志》卷首收录了两个版本的朱子像,后一幅即朱子朝服像,题记云:“后像则国朝升配十哲之次所塑,祀于正殿者也,敬依二像摹于简端,俾都人士展画瞻仰,恍然于先贤道范久而弥尊云。”[21]而《重修南溪书院志》中画像显然是翻刻了《紫阳朱氏建安谱》中的朱子及其父韦斋画像。可见,“朝服版”朱子像因其特殊的创作初衷——供族裔瞻仰或作为祭祀之用,突出其仪态威严整肃。相较而言,文集以及由他人编纂之年谱中的画像,则侧重展示朱子的个性气质,如上文分析的“麋鹿姿”,既揭示出朱子的贫寒出身,又暗示其因仕途不得意和精神追求而产生的隐逸情怀。朱子曾在主管华州云台观期间,自称云台隐吏朱熹仲晦父、云台真逸等。[2]36“隐吏”“真逸”等语虽有自嘲之嫌,但何尝不是他人生的理想追求。
当然,朱熹圣像的意义生成与建构,离不开图像观瞻者的内心体验和感受。明初宋濂指出,朱子圣像问世后,“时而观之,则夫道德冲和之容,俨然于心目之间,至欲执鞭从之,有不可得于戏九贤亦夫人哉”。[6]296宋濂从观瞻者的角度分析了朱子圣像的视觉效果:朱子的“道德冲和之容”能引起人们的情感波动,睹像思人,进而服膺其学说并努力践行之,即所谓“俨然于心目之间,至欲执鞭从之”。这是一种因情感感召而产生的“劝服”,朱子圣像“垂训”的功能,正是通过特定的图像文本,并借助欣赏者的观瞻,引发他们相应的兴奋、敬畏、钦佩,乃至沉醉,才最终得以实现的。美国当代学者尼古拉斯·米尔佐夫指出,人们的“观看创造了情感。正是那种激动和沉醉的情感把奇异非凡和单调乏味分隔开来,也正是这种丰盈的体验把视觉符号或符号学的循环的不同组成部分纳入一种彼此相连的关系之中。在这些时刻,视觉的力量是如此强大而令人惊异,用大卫·弗里德伯格的话来说,它们唤起了‘钦佩、敬畏、恐惧和渴望’。视觉文化的这个方面居于所有视觉活动的核心。”[22]故此,就不难理解历代朱子圣像所独具的“格式塔特质”,诸如感性特质(“麋鹿姿”“七星痣”等)与情感维度(圣像带来的感召力)了。这些“格式塔特质”经由人们的视觉经验,来进一步影响受众的情感态度、价值信念和实践行动,以实现劝说意图。正所谓“图像不仅造就了人们的思维,而且还使人们有了特别的感受并采取了行动”。[23]
四、结语
综上所述,针对人物画像的创作而言,图像隐喻手段主要是通过对像主的外部特征,包括衣着服饰和体态特征,诸如相貌、肢体动作、表情神态等来实现的。众所周知,人类的情感表达除了语言表达之外,还体现在各种身体态势上。体态是人类交流情感的重要方式之一,人们常将人类的特定肢体动作和表情神态称作体态语言,既然是“语言”,当然具有能表达的属性。就体态语言本身而言,“它既是一种社会习惯,又是一种意义系统”。[24]体态作为一种特殊的“语言”,它的表意更具有隐喻性。因为体态“语言”是通过人类的身体动作来言说(表达)的,因而天生具有“可看性”,又因其意义的表达和准确把握需要借助某种社会习惯和约定俗成的意义系统,故而体态“语言”又是“可读”的。
朱熹友人陈亮《朱晦庵画像赞》云:“体备阳刚之纯,气合喜怒心正。睟面盎背,吾不知其何乐;端居深念,吾不知其何病。”[25]这里的“睟面盎背”就揭示了人的内心世界、情感欲念是通过体态“语言”来表达的这一基本规律。所谓“睟面盎背”,《孟子·尽心上》云:“君子所性,仁义利智根于心,其生色也睟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26]朱子“体备阳刚之纯”“气合喜怒心正”,这些内心形象文本的“真相”仅仅存在于形象文本和形象接受之中。在朱子圣像的形象传播实践中,形象的操作者(图像创作者)往往有意识地选取具备其“特征的面相”来进行符号化传播,诸如上文所述及的“麋鹿姿”“七星痣”,也包括服饰方面的五旒冕冠、缁布儒巾和拱手而立这样的肢体动作。作为继孔子之后的硕儒,朱熹需要被表现得很神圣。人们常好奇于圣人的生活“真相”,并常常获得失望的结果。生活中的圣人常常不是形象学背后的“本人”,而是社会主体以像似符号为导向的传播效果聚合,是与人们所期待的形象有关的它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