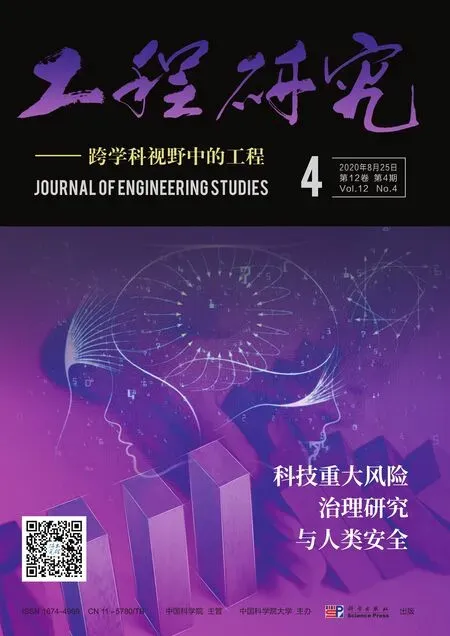试论工程建造的具身性知识运作
李 旭,邓 波
工程哲学
试论工程建造的具身性知识运作
李 旭,邓 波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工程技术与社会研究所,西安 710055)
工程建造(施工)本质上是把人工物本身结构、功能、形态的知识(know what),在怎么建造人工物的知识(know how)的指引下,建造主体在施工情境中手脑并用、身体力行地激活、调动、构造经验与技能,对工程涉及的物质性要素施展“上手”操作,从而实现人工物从知识、符号到物质实体转化的过程。其知识运作必然具有鲜明的“具身性”(embodiment)特征。传统知识论往往把工程知识作为科技知识的应用与附属,作为同科技知识本质上一样的表征性知识来理解,必然造成对工程知识具身性这一鲜明特征的严重遮蔽。在科学、技术、工程“三元论”的框架内,通过分析传统知识论对工程知识可能造成的遮蔽及问题,进而以当代具身性知识论为视域,把工程建造活动嵌入到工程全周期的具体环节与过程,对其知识运作的具身性问题展开初步的现象学研究。
工程建造;现象学;具身性;工程知识;具身性知识运作
工程建造(施工)是将人工物现实地建造出来的物质性实践过程,本质上是把工程设计构建的知识形态、符号形态的虚拟人工物转化为物质形态人工物的知识物化过程,其中交织着知识与物质的运作,即把人工物本身结构、功能、形态的知识(know what),在怎么建造人工物的知识(know how)的指引下,建造主体在施工情境中手脑并用、身体力行地激活、调动、构造经验与技能,对工程涉及的物质性要素施展“上手”操作,才能实现人工物从知识、符号到物质实体的转化。因此,工程建造(施工)中知识运作必然具有鲜明的“具身性”(embodiment)特征。这里所谓的具身性,主要是指工程建造(施工)过程中的管理者以及操劳者在长年累月的施工管理和施工操劳过程中,将其自我所掌握的技艺与身体相互交融,最终服务于工程人工物本身的一种“娴熟”过程。
工程建造(施工)中的具身性作为工程知识具身性最显著的表现,理应成为知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然而,由于人们深受逻辑实证主义思想的影响,认为:“技术知识是科学知识的应用,而工程知识则是技术知识的应用。工程知识、技术知识仅被视为科学知识的退化形式,尤其是工程知识,根本没有作为独立知识形态的合法地位。”[1]传统知识论往往把工程知识作为科技知识的应用与附属,作为同科技知识本质上一样的表征性知识来理解,必然造成对工程知识具身性这一鲜明特征的严重遮蔽。笔者将在李伯聪教授提出的科学、技术、工程“三元论”的框架内,通过分析传统知识论对工程知识可能造成的遮蔽及问题,进而以当代具身性知识论为视域,把工程建造活动嵌入到工程全周期的具体环节与过程,对其知识运作的具身性问题进行初步的现象学研究。
1 传统知识论的内核及其对工程知识的遮蔽
从近代笛卡尔主义到现代逻辑实证主义,再到当代第一代认知科学所形成的传统知识论,可以说都是与具身认知截然相反的离身的知识论。第一代认知科学的知识论作为传统知识论的当代形态,主要以符号主义为进路,“以认知可计算主义为纲要”[2],坚持心灵与肉身相分离,认为二者是相互独立的个体,绝对地认为二者不存在任何因果关系,完全忽略了身体在认知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而是简单得将其理解为,思维活动或者徒手的操劳活动只是在某种具体的规则下进行机械化的符号表征。这一进路始终坚持肉体与心灵之间是一条永恒的平行线,是一种完全对立的形而上学关系,使得肉体这个物质体在认知的具体过程中被排除在外,完全忽视了其在认知中的地位。这种认知思维充分反映了传统知识论的内核。
1.1 现成性存在预设
以逻辑实证主义为主要理论形态的语言学或语义学哲学成为传统认知科学的哲学之基。其一方面认为主客体之间的“对话”是通过语言这一中间环节来进行的。具体表现为,“主体将客体通过符号的认知进行表征与说明,而客体本身借助主体的符号表征又被主体重新认知。物质世界中作为认知主体的实践者对世界的认知就是一种符号表证的过程,而表证的传播途径就是语言本身。”[2]121另一方面认为,认知主体的心智活动或脑思维活动是一种没有任何物质体参与其中的无形活动,因此,这一类活动也就无法通过认知主体的视觉感知而被直观察觉。但是这种主体认知活动可以通过言说的方式存在于世界之中。在这一言说的过程中,分析与系统的综合判断被作为言说“成败”的关键之所在。并且这一理论刻板地坚持语义分析和言语逻辑分析,把对在世之物的分析仅仅依靠于言语逻辑的判断,完全忽视了肉体与心智结合而产生的具身认知理念。这一思想严重脱离了人类社会所处的历史与人文环境,忽视了心理对科学探究的影响。传统认知科学坚持认知理念是对信息的表征和操控。这一理念下的认知活动与计算机在运算中对符号的加工具有异曲同工之处。
在工程建造(施工)的具体实践活动中,如果以上述现成性存在预设思想作为工程建造(施工)活动的纲领性思想,工程建造(施工)根本就不需要技术交底,也不会出现监理行业。一方面,工程共同体各方只需要在工程人工物建造之前将工程建造(施工)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通过主客体之间的“对话”进行具体表征。这一思想严重将工程建造(施工)的“情境性”与“突发性”事件进行了“遮蔽”,与基本的思维逻辑相背离。另一方面,在工程建造(施工)活动中的“操劳者”是“活生生”的思维者,并不是像器械一样进行无思维的机械运动。在具体的操劳过程中,一味地按照规范或者其他标准进行机械的操劳,往往是“徒劳”的。很多情况只有推进到工程建造(施工)的具体情境过程中才会出现,这种过程性表现为时间的长度和空间的分布,这构成了工程场景,而工程场景往往具有特殊性,而且工程建造(施工)的“操劳”过程也存在价值判断,叠加了人的因素和人的心理因素。面对这种过程性问题,仅仅依靠具有普遍意义的规范与标准显然是行不通的,与之相反,关注特殊性在这一过程中显得更加重要。
1.2 心物二元论
传统认知科学一贯坚持身体与心智是两个永远平行的独立个体,构建了一个较为系统的离身认知构架。自柏拉图以来,对身体的“鄙视”成为西方思想坚持的一贯传统。柏拉图认为:“肉体和灵魂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二者之间保持着一种互不交融的平衡关系,各自独立于世界之中,相互分离。始终坚持认知主体获得知识只是灵魂与心智的自我活动,与肉体无关。”[2]117这种传统认知在笛卡尔那里得到了强化以及后续的发展,最为典型的就是笛卡尔的心物二元论以及康德的客观主义认识论。
笛卡尔认为:“知识是认知主体的心灵对客观世界进行表征的结果。”[3]第一代认知科学视笛卡尔的这种思维为其思想的精华之所在,并在之后的时代里将其不断发展与传承,形成了一个系统而又完整的认知世界观,尤其是将心灵的感知放在了最高的理论高度,使其成为符号表征主义的理论来源[4]。这一思想把“旁观者”置于了另一个高度,几乎把所有的认知都给予在“他者”身上。在对知识的认知过程中,绝对客观性被作为最高的理念,自我本身被置于自然之中。接着,康德客观主义认识论在认知中使得内部心灵与外部世界相分离。这一思想将表征主义作为其认知特征,提前预设了主客体和内外世界的分离,使得认知活动将身体置于活动之外,没有发挥实质性作用。
在工程建造(施工)活动中,站在施工管理者对施工技艺掌握的视角,如果一味坚持心物二元论,项目经理与生产经理的区别几乎很难被厘清。在当今教育普遍化的大背景下,工程建设行业的管理者往往都接受过长达四年的大学工科教育。当这些管理者进入工程建造(施工)现场从事具体管理活动时,往往表现出一种差异性。经过几年的发展,一部分管理者被分流为项目经理,而另一部分管理者被分流为生产经理。如果按照心物二元论的理念,在同样的工程教育背景与同样的施工现场从事同样工程管理工作的工程管理者应该具有同样的技艺,并且应该持续从事同样的工作。但是这一情况与现实是截然相反的。这就说明,正是由于个人面对同样的工作,个体身心统一的程度,造就了个体的自我,在工程建造(施工)管理活动中,表现为项目经理和生产经理的差异性。
1.3 表征主义
表征主义认为“经验的现象性特征可以由其表征内容得到说明”。[5]在认知的理念中具体表现为知觉世界的表征,并不是触觉世界的操作。而“知觉表征又是知觉意向的一种,知觉意向则是心智意向在知觉问题上的主张”。[6]这就说明,知觉表征同时具有知觉经验与知觉意向两个维度的表征理念,而且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特殊的现象逻辑关系。
在上述传统认知科学理念的影响下,工程知识被理解为科学知识、技术知识的应用会带来一些必不可少的现实问题,其中最为直接的就会出现两个反问,即:工程知识究竟在何种意义上运用科学知识、技术知识?身心二元论在工程建造(施工)中如何凸显及会引发什么问题?
首先,科学知识与技术知识在工程建造(施工)的实践活动中,必然会被运用,但并不等于这一实践活动的完全科技化。例如,工程项目的具体实施,仅仅通过将已有的科学知识、技术知识、工程知识进行简单的机械堆砌,是根本行不通的,人工物本身的建造活动需要运用大量的知识,并且这些知识必须在施工建造的具体场域环境中进行优化与排列组合。站在工程实施所用到的知识体态维度,工程建造(施工)用到包括工程哲学、技术哲学、工程伦理学以及工程社会学一类的基础性知识;同时,涉及工程数学、工程力学一类知识;也包括施工标准图集一类的技术知识和一些无法言说的符号性知识。但是,一个现代化的人工物仅仅依靠上述知识是完不成的,要想使得人工物落地建造与后续投入使用,必须在上述知识的基础上,加之其他经验性知识以及具身性的工程知识。
其次,身心二元论在工程项目中有他存在的可能性,但是这种思维会带来一系列问题。例如,在工程建造中进行技术交底时,由于操劳者自身掌握的知识有限或者理解不到位,使得技术交底无法按照预期目标进行落实,会造成施工工序错乱,产生施工安全及施工节点把控不到位等问题。具体表现为一种机械的、无思想的操劳活动,即“人是机器的论断。”[7]而这一论断正是传统认知科学得以存在与发展的基石。鉴于上述观点,认知主体的认知过程可以前置在计算机系统里。这显然是行不通的。例如,世界上任何一个工程项目的建设都不可能在动工之前将施工中可能遇到的事件前期处理好,一定会有现场突发事件的发生。
综上,传统知识论是把理论置于优越地位的“理论优位”知识论,科学理论当之无愧地成为现代知识论分析的唯一典型样板。按照这种知识论,工程不过是科学技术的应用,工程实施就是这种应用最显著的表现,它不过是把相关科技知识加以运用而已,不存在什么独特的知识形态及运作方式,因而也无需进行知识论的研究。显然,这样的知识论必然造成对工程知识尤其是工程实施知识的长期忽视与遮蔽。因此,站在传统认知科学的理论高度研究工程建造问题显然是不现实的,正是出于对上述认知的不满,一条不同于上述思维认知的具身认知诞生且不断发展。这种具身认知来源于对传统认知科学原理的理论突破。
2 具身性知识研究对传统知识论的突破
波兰尼“个人知识”和第二代认知科学为当代知识论的研究开辟了具身性知识论的路径,身体由此被引入知识论。这一理论认为不仅神经及生理引起了心智,而且认知能力也由人类的身体与环境的互动而产生。它一反表征主义认知观,否定了自笛卡尔以来表征操作在认知行为中的决定性地位,认为认知行为应该是丰富的、与主体的身体以及主体所处的社会环境和所接受的文化有关,这些因素合力造就了知识,科学知识也不例外。由此开启了从第三人称向第一人称具身性科学知识论转向的研究。
具身认知科学即第二代认知科学认为人类活动及其基本认知必须依附于身体本身[8]。不论在本质上还是在方法论层面,第二代认知科学与第一代认知科学相比,都存在着质的区别。一方面,第二代认知科学一反常态,将实践经验作为认知基础,而不是过分地强调普遍原理。另一方面,第二代认知科学将认知的重点转向对实践过程中所发生的事件或情形进行综合判断与经验总结和归纳,反对传统认知科学强调的唯科学化。具身认知科学突破了第一代认知科学的弊端,这一功效主要源于现象学。其中最典型的代表有胡塞尔、梅洛庞蒂以及海德格尔等。
2.1 胡塞尔对具身性的认知
尽管胡塞尔的现象学将其研究域偏重于主体性意识,但是他也刻意地强调了具身性在主体性认知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其特别强调在外部感知中身体也发挥着共同构造的功能。在胡塞尔看来:“意识主体本质上也是具身主体,并且由于这一具身性特征,主体性在超越论层次上已然与他者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并由此与他者构成了超越论的交互主体性。”[9]也就是说对一个具体事物的感知行为,身体是参与其中的而不是孤立存在的,也不可能在思维中已然勾勒出实际存在之物。而且,这种具身认知特别强调情境性与场域性。即必须“身临其境”,只有这样,认知主体才可能较为全面地认知相关客体。例如,在具体人工物建造过程中操作者的经验与其具身认知是密不可分的。当一个抹灰工对一面墙面进行抹灰的过程中,在其进行内墙面抹灰的同时,其脑海中已经能感知到外墙面的抹灰情境以及施工工艺,虽然此时此刻其并没有面对外墙面。正如胡塞尔所述:“这是一种充实意向与空洞意向的复合”[10]。正是在这种不断实践具身操作的活动中,自我的感知经验不断升华,最终应用于人工物建造(施工)的实践中。
2.2 梅洛庞蒂对具身性的认知
在具身性的认知发展进程中,梅洛庞蒂提出了“具身的主体性”[11]这一理论。这一主体性思维“通过身体与世界的物质性互动而实现”[12]。他认为身体本身是认知世界的开始,身体与外部世界直接接触产生认知,包括人的心智只有在身体的依附下才能产生。正如其所述:“认知主体对事物的认知常常表现为一种‘我可以’的意愿,而不是‘我觉得’的不确定回答,这种‘我可以’的自信正是源于‘我’本身,也就是身体本身,而这个身体是与世界融为一体的‘身心’合一的共同体。”[13]可以理解为认知主体的一切认知的心智都源于身体存在的本身。认知主体的心智只有通过具身性才能与世界互动,包括人的精神依附于身体。在工程建造中不论是项目管理者还是建筑工人,其在工程建造中所使用的知识,有很大一部分是通过实践操作与身心认知相互结合而产生的,这里包括面对相同的操劳不同的操作者获取的感知不同,以及在工程建造中只会干而无法言说的知识即“默会知识”等,都深刻地说明了这一论述。
2.3 海德格尔对具身性的认知
海德格尔“在世界之中存在”理论深刻显露着其对具身性认知的思想。在他看来:“对在世存在之物最好的认知不是一味的感知或简单的觉察,而是身临其境,在实践的操劳过程与情境中认知在世之物。因为操劳有它自我存在的意义,像工件的制作仅仅通过思维的感知是永远无法存在于世的,只有在‘上手’的操劳实践中不断被认知,不断被修正,最终独立存在于世界之中。”[14]而工程建造活动所使用的技术以及所遇到的问题,在工程建造的前期并不能完全被预估到,恰恰是在“干”的过程与情境中发生的,与海德格尔的思想一致。例如,在工程建造活动中,施工主体在对施工技术管理的基础上,运用携带施工技术本身的施工机具或施工设备,在施工工艺和施工操作的情境下,最终完成具体人工物的建造。在施工情境中对技术管理的重要性就如同黑格尔思想体系中所流露的:“人类徒手之外,借助生产工具或者某些手段达到自我目标实现目的的手段是一种‘理性的狡狯’”[15]一样重要。黑格尔的这一思想主要表达了“在世存在者”或实践主体在具体实践过程中,通过与“徒手”操劳相反的方式即通过利用或借助器械的手段理性地改造世界,最终达到自我目标的实现,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将这种自我意志转化为一种普遍的共识性知识,将知识普遍化或规律化。这种思维在工程建造的过程维度表现为操劳者以及参与工程建造的共同体在使用或者借助施工机械的基础上,理性地进行自我操作与团队协作。通过这一系列的理性活动,最终实现对人工物本身的建造。甚至,可以将这一个体知识进行系统凝练与推广,形成“工法”文件,在整个行业推广。
2.4 德雷福斯的技能获得模型
“新手–高级初学者–胜任–精通–专家–大师–实践智慧”,这七个阶段无一不在强调身体在认知过程中的必然作用。人们掌握了某项技能并不是心灵表征的结果,而是技术被内化为对相应情境有直接反应的能力。可以说,德雷福斯的技能获得模型为深入研究工程知识的具身性运作提供了范例。但是,在肯定具身性技能的基础性作用的同时,他又对概念性、符号性、表征性知识作了与具身性知识二元对立的理解,认为这些表征性知识的运用会打破肉身性的实践情境,它们的运作与具身性知识无涉,不可能渗透到具身性技能之中。可以说,德雷福斯仍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心物二元论。
新近的研究中,麦克道尔认为:“理性的概念、符号运作能力经反反复复的具身性运作、训练贯穿于具身性的技能之中,找到了真正突破心身二元对立的方式,为深入具体地研究工程建造将知识物化的具身性运作机制提供了新的视域。”[16]因此,在工程建造的具体实践中,工程思维对人工物本身的质量产生着间接影响。这种工程思维就是目的——工具性思维,这是一种具有操作性和运筹性双重属性的思维。
3 工程建造实践中的具身性知识运作
随着李伯聪教授“科学–技术–工程”三元论的问世,工程作为一支独立的研究域被人们所重视,工程哲学确定了其独立地位。李伯聪教授将三元论阐述为:“为了更简明地辨析与把握科学、技术与工程的不同特性,我们可以简要地把科学活动解释为以发现为核心的人类活动,把技术活动解释为以发明为核心的人类活动,把工程活动解释为以建造为核心的人类活动。”[17]这就进一步可以推断出,科学哲学的基本问题是“科学知识何以可能”的问题,技术哲学的基本问题是“发明何以可能”的问题,那么,工程哲学的基本问题则是“造物何以可能”的问题。工程哲学基本问题的明确,带来工程哲学近十几年的蓬勃发展。现阶段工程哲学的研究推进到了工程知识论的领域,工程的实践本性要求工程知识论的研究不能像传统知识论那样局限在理论的抽象层次,必须朝向工程实践本身,必须亲身经验地深入到工程活动的实际情境。工程实施的知识运作并非只是简单地应用现成的理论知识,而是在工程实践中主体具身性地不断集成应用已有知识并创生新知识服务于人工物建造的“干”的过程,而这种“干”的过程,包含着建造者“亲历亲为”的具身操劳活动。因此,关于工程建造的具身性问题研究,应当在“实践优位”工程知识论背景下展开。
工程建造就是施工主体把施工图纸上符号化的人工物知识(know what),按照怎么做的知识(know how),通过其身体力行的具身性有序操作,构造出具有一定功能、形态的物理结构的知识物化过程。所谓操作就是参与工程建造的主体徒手或者使用工具及施工机具对相应的对象所施加的动作。它既包括知识过程,也包括物质过程。正是其中的具身性知识运作把知识过程与物质过程联结起来,打破了心身的、心物的二元对立,实现了知识的物化。下文将深入到工程建造(施工)的真实情境,从施工图纸、施工主体、施工管理三方面探讨工程建造(施工)实践中的具身性问题。
3.1 施工图纸认知的具身性
施工标准图集作为“按图施工”的工具性文件与工程建造的质量和效用直接相关。对施工标准图集的解读,不是个体的“上手”而是群体的“上手”。在群体的“上手”过程中,一定会有一个领导力即群体的管理者。管理者与其发出的指令直接影响着施工群体对施工标准图集的解读力。这里的管理者如果只是照搬以往学习的相关知识或项目经验,那这样的解读将是具有缺陷的。管理者不仅要参考其所掌握的明言知识,更要在大脑意识中将其升华,最终以一种具身性的综合知识参与解读,发出指令。进行具体实操的操作者也是如此。在这一过程中,一些人往往只把重点放在了管理者和其指令上,而忽略了操作者以及操作本身在施工标准图集解读过程中的重要性。“在现代社会中,从政治和道德层面上看,管理者和操作者是平等的,不能厚此薄彼;从工程实施和行动实践的层面来看,管理者和操作者也是各有重要性而不是有‘重’有‘轻’可以畸轻畸重、厚此薄彼的。”[17]208因此,在施工标准图集的解读过程中,两者都要考虑到。
在荷兰学派的观念中,我们有了图纸,有了结构,功能是未来才能发生。三者的关系通过设计得以找到。施工图主要是围绕结构展开的。实物只有实际的存在,结构运行起来才能具有功能。施工图主要以符号的东西呈现了结构。结构包括了它的物理结构和它使用的各种材料,包括涉及的各个专业。只有读懂图纸才能对结构进行一番剖析。只有理解设计,才会在know what的基础上know how。因此,对施工标准图集的解读过程中,指令者与“上手”者的具身知识是工程建造前掌握know what的“不可变量”的效用。
3.2 施工操作者即工人操作的具身性
工程建造的具体“上手”操作最终是由建筑工人(在我国以农民工为主)完成的。工人层次的高低,决定着工程建造的成果——具体人工物的质量。我国目前社会发展的具体情况,对何为工人即对工人群体的具体划分并不明确。站在实践哲学的高度,从工人工作的客观情境出发,并结合工人自身的知识结构以及工人目前所处的社会福利待遇这些角度来看,李伯聪教授将我国的工人群体大致分为以下几类:“普通工人(主要包括从事熟练劳动的初级工和中级工)、高级技工(主要包括部分高级工、技师和高级技师)、灰领、工人和工头等类型。”[18]69这一划分,对我国工人群体的结构和构成做出了一个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透视。站在建设工程行业的角度,以及从工人在工程(项目)实施中的处境、工人素质培养、工人在工程(项目)实施中的作用以及如何维护工人权益等多视角出发,具体探讨工人即进行哲学高度的工人的具身性之思决定着人工物的质量。
在工程建造的“上手”活动中,建筑工人的素养即具身知识对人工物建造的质量不可或缺。在工程建造的具体操作中,所述的工人特指建筑小工(主要是进行简单操作的体力劳动者群体)、技术工或者技师(木工、支模工、水电工、砌筑工、抹灰工、架子工、安装暖通工等)以及作为上述主体的默认管理者即包工头。在多数情境下,工程建造的人工物的质量问题并不是出在工程设计阶段或者技术交底环节,而是归因于具体“上手”操作的工人这一层次。由于在“上手”的具体操作情境中,操劳者与被操劳者操劳的物质对象是同时存在于一个操作环境或者操作界面中的,二者是不能分离的,这与马克思思想中的物质对象相互影响、相互转化具有异曲同工之处,因此必须要进行操作界面的认知。
建筑工人在进行“上手”建造工程的时候,有的是“徒手”操作,有的是借助施工机具进行操作。这两方面有着操作意义或者说操作界面的区别。当建造人工物的建筑工人不借助施工机具,也就是其“徒手”操作的时候,他们的操作就直接指向了对象本身,这个指向操作对象本身的具身操作只会出现一个操作的界面。而当“上手”操作的建筑工人借助施工机具进行“上手”操作时,建筑工人是通过起“过桥”作用的施工机具与被操作的客体产生联系,这样的话仅仅依靠一个简单的操作界面就无法满足相关要求,也不可能叙述或者交代明白,这一情形下,必须通过两个操作界面来进行阐释。正如李伯聪教授所述:“当操作者使用工具或机器的时候,我们可以把操作者和机器之间的操作界面称为第一操作界面,把机器和劳动对象之间的操作界面称为第二操作界面。”[17]208在人和机器之间的这种操作界面也就是第一操作界面,对人和机器二者都提出了具体要求。一方面机器要做到为人服务,即具有良好的“人性化”;另一方面,人必须适应机器,即人应该经过专业的培训去操作机器本身,也就是有一个被动的学习与锻炼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不同的学习者,学习的结果参差不齐,达到非常熟练的程度的学习者,将这种操作的艺术与身体融合,表现出一种强有力的具身性。这就说明施工机具应该是为具体操作者量身定做的,因为一个不适合的“上手”机具直接影响到操作者具身知识的发挥。例如,在建筑施工的工程中,建筑脚手架和建筑脚手板的搭设高度和施工操作作业面的宽度直接影响操作者四肢的发挥,进而影响到其具身性,最终影响到建筑人工物的质量和工期。机器与被作用对象的物质性客体之间的关系就是第二操作界面。这是一种物与物之间的作用关系,操劳主体想要最终实现的人工物成果是通过这个界面来完成的,因此,制造者在对机械的制造中,要将造物的思维贯穿到所建人工物本身之中,也就是要符合“物的尺度”。正如在建筑施工中,钢筋进行冷拔或弯曲的时候,需要采用专业的操作机械,这一机械的设计型号要做到恰好符合建筑施工中国标(GB)和施工具体规范的要求,而且工人在具体的弯矩操作中,“上手”就显得十分的轻便(俗语中所述的干活十分节省力气),即建筑工人的四肢和大脑活动与其所使用的施工机具配合的地步达到“完美”。其本体的具身性或者具身知识运用到了极致。
3.3 施工管理的具身性
工程建造活动出现在特定的地理位置,这一特定的位置主要包括了自然环境与社会文化环境两个维度。即:“工程行动发生的特定地区的地理位置、地形地貌、气候环境、生态环境、自然资源等特殊的自然因素,以及该地区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基础设施、政治生态、社会组织结构、文化习俗、宗教关系等社会因素,构成了工程行动发生的自然与社会环境。”[19]站在这一视角,必须对工程建造的具体场所进行研究。要研究当地的地质地貌和土体,土木工程专业所学的必修课程《土力学》就深刻地诠释了这一情形。
在施工建造的具体情境过程中,生态观(绿色施工、文明施工的要求)越来越被重视,文化观越来越被施工建造和社会所关注。这两观也是施工企业参评“鲁班工程奖”的重要参考标准。随着经济社会的纵横发展,工程建造活动也开始从传统的粗放型发展转型到绿色发展,绿色建筑的热度被工程界广泛关注,正如李伯聪教授所述:“在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工程项目所耗用的资源越来越多,工程共同体以及社会相关者将自我的思维转向了生态环境角度,把工程放置在社会生态环境的场域,做到人工物、自然与社会的统一。”[20]在循环经济发展火热的当代社会,工程界(包括建筑工程、工业工程等)开始在工程本体的研究中加入生态观念。这一转型在具体施工技术措施上初见成效,具体表现为建筑的工业化与信息化。例如,在混凝土搅拌的方式上打破了传统的现场搅拌法,形成了在工厂进行集中搅拌集中供应的商品混凝土,以及采用工业残渣作为原料,制造建筑砌块,取代机制粘土砖等。这些都可以被施工情境环境管理所采纳,是环境具身问题之所在。
在对施工情境中环境管理的具身性问题的具体的研究管理活动中,要把各种自然和社会科学知识都融入其中。这是一个庞大的具身操作性问题,必须在后续进行深入研究。
4 结论
在工程建造的实践过程中,关注具身性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对人工物建造的质量与进度或者说施工功效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将以往传统知识论坚持的离身认知思维淡化甚至剥离工程实践认知视域,坚持具身的认知思维,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有利于人工物的建造活动。尤其,面对现代化的建设项目表现出的资金投入大、结构复杂度高、现场突发事件多等现实问题,在工程实施的情境过程或场域中,包括施工操劳者与管理者在内的工程建造共同体,只有将其所具备的知识与现场情形在具身认知的基础上深入结合,才能更好地服务于人工物本身。这一过程表明具身性知识在工程建造中的运作已经成为工程活动中的重要环节。由于工程建造的灵活性与知识更新的时效性,对工程建造活动中具身性知识运作的研究依然具有很长的道路。
[1] 邓 波, 贺 凯. 试论科学知识、技术知识与工程知识[J]. 自然辩证法研究, 2007(10): 41-46.
[2] 李炳全, 张旭东. 具身认知科学对传统认知科学的元理论突破[J]. 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6): 116-123.
[3] 孟 伟, 刘晓力. 认知科学哲学基础的转换——从笛卡尔到海德格尔[J]. 科学技术与辩证法, 2008, 25(6): 31-34.
[4] Davis R, Shrobe H, Szolovits P. What is a knowledge representation?[J]. AI Magazine, 1993, (14): 17-33.
[5] 刘 玲. 注意与表征主义[J]. 自然辩证法通讯, 2018, 40(11): 50-56.
[6] Fish W. Philosophy of Perception: A Contemporary Introduction[M]. New York: Routledge, 2010, 65-71.
[7] 刘晓力. 计算主义质疑[J]. 哲学研究, 2003(4): 88-94.
[8] 罗志达. 具身性与交互主体性[J].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57(3): 143-150.
[9] 胡塞尔. 交互主体性现象学(第2卷)[M]. 耿 宁编. 海牙: 马尔梯努斯奈伊霍夫出版社, 1973: 57.
[10] 胡塞尔. 事物与空间[M]. 克拉斯格斯编. 海牙: 马尔梯努斯·奈伊霍夫出版社, 1973: 57.
[11] 冉 聃. 赛博空间、离身性与具身性[J]. 哲学动态, 2013(6): 85-89.
[12] Fusar-Poli P, Stanghellini G. Merleau-Ponty and the “Embodied Subjectivity”[J]. Medical Anthropology Quarterly, 2009, 23(2): 9-93.
[13] 梅洛庞蒂. 知觉现象学[M]. 姜志辉译. 商务印书馆, 2001: 255.
[14] 海德格尔. 存在与时间[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9.
[15] 黑格尔. 逻辑学(下卷)[M]. 商务印书馆, 1976: 437.
[16] 郁 锋. 麦克道尔和德雷福斯论涉身性技能行动[J]. 哲学分析, 2019, 10(3): 3-11, 196.
[17] 李伯聪. 工程哲学引论[M]. 郑州: 大象出版社, 2002.
[18] 李伯聪, 等著. 工程社会学导论:工程共同体研究[M].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0.
[19] 邓 波, 贺 凯, 罗 丽. 工程行动的结构与过程[J]. 工程研究-跨学科视野中的工程, 2007, 3: 49-59.
[20] 李伯聪, 等著. 工程哲学[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
On Operation of Embodied Knowledge in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Li Xu, Deng Bo
(The Research Center of Engineering Technology & Society, Xi’an University of Architecture and Technology, Xi’an 710055, China)
The essence of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is in using the knowledge of the structure, function, and form of artificial objects (know what),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knowledge of how to build artificial objects (know how) to realize the process of transformation of artificial objects from knowledge and symbols to material entities. Engineering knowledge has distinct characteristics of embodiment. However, the traditional knowledge theory often regards engineering knowledge as the application and combin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knowledge and even to regard it as a kind of representational knowledge, which has inevitable resulted in the concealment of the distinctive features of engineering knowledge. In the ternary framework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engineering,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ossible problems resulting from the applic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knowledge theory to engineering knowledge. On the basis of the contemporary theory of embodied knowledge, the authors put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activities into different processes of the whole engineering cycle and carry out preliminary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 on the embodiment problems of knowledge operation.
construction; phenomenology; embodiment; engineering knowledge; embodied knowledge operation
2020–05–19;
2020–06–27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工程知识与工程思维的哲学研究”(13BZX027)
李 旭(1993–),男,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为工程技术管理哲学、工程知识论。E-mail:1073150909@qq.com
邓 波(1963–),男,教授,研究方向为技术哲学、建筑哲学、工程哲学。E-mail:xazm.5386@163.com(通讯作者)
N03
A
1674-4969(2020)04-0388-09
10.3724/SP.J.1224.2020.00388
——访陈嘉明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