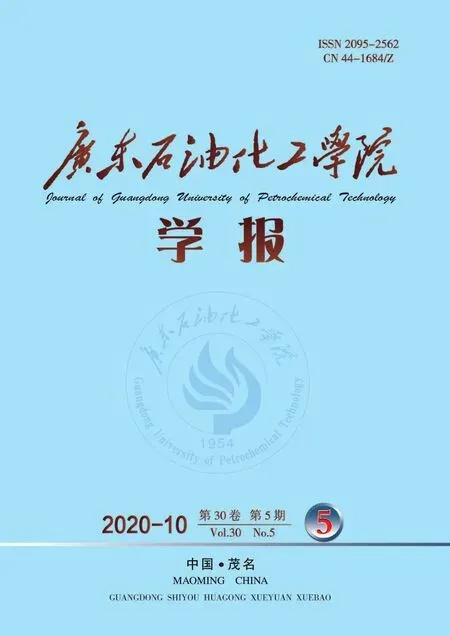孙中山对中西“融贯”文化的政治运用1
陈尧
(哈尔滨商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150001)
孙中山在辛亥革命之后总结道:“取欧美之民主以为模范,同时仍取数千年前旧有文化而融贯之。[1]”这是孙中山对待文化观的一贯方针。他还更明确地说过自身思想的来源:“余之谋中国革命,其所持主义,有因袭我国固有之思想者,有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者,有吾所独见而创获者。”[2]可以看出,他的思想有源于我国传统的,也有引进西方的。他对于中西文化观上的“融贯”,按照时间划分,主要可分为三个阶段,并体现出了不同的政治倾向。
1 援西入中,寻求救国真理
第一个阶段是在辛亥革命以前,此时的孙中山援引西学补充中学,将“融贯”表现为政治纲领的提出,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构成了三民主义。此时期的三民主义属于旧三民主义的范畴。旧三民主义是孙中山学习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产物,主要解决民主独立、民权行使与民生发展三大问题。孙中山对于探索中国的出路,不得不思考文化的取向。面对中国根深蒂固的封建专制主义,孙中山积极向先进的西方学习正规的民主主义。由于中国传统文化根深蒂固,孙中山对中国进行改造必须因袭一定的中国传统文化,防止外来文化引起排异反应。因此,孙中山在锻造自己的革命纲领的时候必须考虑本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契合,以此作为民主主义的启蒙前提。“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作为旧民族主义的内容具有积极的战斗意义,明显是近代民族国家观念与传统“华夷之辨”结合的产物,体现了国家要求独立的迫切愿望。虽然它没有明确的反帝纲领,但是将矛头指向了腐朽的清朝统治,最终推翻了反动政府。“创立民国”是旧民权主义的内容,构成了推翻封建君主的利器,这是共和思想进入中国的重要标识,但是存在历史局限性,缺乏明确的民众权力建设,也缺少彻底的反封建精神。“平均地权”是旧民生主义的重要内容,旨在预防资本主义的弊端,具体以核定地价、照价纳税、照价收买、涨价归公的方式实现土地国有,但是旧民生主义将地租转交给国家,没有解决农民要求获得土地的问题。
在旧三民主义这一纲领下,孙中山还提出了很多具体的政治方案。他还参照了中国传统政治管理思想中的监察制度与考试制度,以美国的立法、司法、行政三大制度为模板,形成了五权宪法,以弥补三权分立的缺陷。可以说,旧三民主义就是援引西学于中学,经过整合“融贯”之下的产物。旧三民主义的目标是要“建立民国”,采取符合世界潮流的共和政体,取代腐朽的君主专制。他认为民众理应拥有管理国家公共事务的权利,“人民自治为政治之极则,故于政治之精神,执共和主义”[3]。旧三民主义面向传统的解释较少一些,吸收西方的精华多一些,其政治上的诉求是为了加强中国的凝聚力,对中国本身建立新的意识形态,必然体现出“融贯”中西。究其实质,他主要是向西方学习,结合中国实际推陈出新,将有价值的传统文化注入世界潮流,并做出新的解释,使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绽放出洋为中用的奇花异朵。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西方进步思想的传入,西方政治理论、制度与落后的中国现实对接不上,中国内部南北地区思想也存在着差异等诸多矛盾,他试图用西方的文明来改造中国时就显得瞻前顾后、左右为难。所以,他在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选择中,选取的都与中国某种传统思想能够承接的东西,也就同时做出了一些西学中源的解释。
辛亥革命以前的孙中山就看到了中国处于落后挨打的弱势地位,必然会怀疑中国传统文化的时代性。他不仅对传统文化产生了认同危机,而且产生了文化自卑心理。近代中国的传统文化光环不但消失,还使知识分子产生了危机感和文化自卑感,特别是西方的侵略势力大规模进入中国之后,中国人更是产生了强烈的民族危机感,担心文化侵略会使中国丧失自身的文化、全盘接受西方文化、丧失固有的民族精神。孙中山将文化自卑感化作动力,利用西学中的精华来拯救中国人的思想。他有选择地吸收外来文明,并同时转向对传统文化的回归,在文化的冲突中寻找适合中国发展的文化理念,力图改变中国格局上的位置。
孙中山秉持清醒的态度,坚定地认为中国不能事事迷信西方,更不能全部照搬照抄西方文化。中国应该有所辨别,学习西方的文化技术并大力推广,然后“渐渐发明”,进而使中国在各个方面“转弱变强,易旧为新”,旧事物才能转换为新事物。孙中山主张根据中国实际现状,对西方文明进行学习和吸收,这是因为他已经看到了西方文明中的一些弊端。由此可知,孙中山是根据中国社会的需要而进行甄别吸收,按照中国社会的发展状况来吸收有价值的成分。
2 中西兼容,倡行建国方略
第二个阶段是在辛亥革命、“二次革命”以及讨袁、护法运动等革命活动陆续失败以后,孙中山的“融贯”表现为通过中西文化的兼容,并将其运用于建国方略上。为了改变国家的落后状态,孙中山用心理建设来提升民族士气,用物质建设改善国民生活环境,用社会建设满足人的政治权利。
孙中山的建国方略思想的第一部分就是心理建设。建国方略所包含的重要内容是行易知难思想。孙中山引用传统的知行观来论述国人需要加强心理建设的同时,也展现了他对于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创新。孙中山的知行观融入了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及自己的革命经验总结。“知”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所形成的知识、二是通过修身而获得的伦理道德方面的知识、三是自然科学知识、四是革命理论。孙中山所说的“行”也具有四种含义:一是指日常生活的各种活动、二是指道德行为与活动、三是指科学实验、四是指资产阶级革命实践。后两种知行内容的增加,融入了西学的内容。扩大了知行内容的孙中山,还大力宣传行易知难,以此鼓励革命党人无畏前行。此外,孙中山还在国民性改造和三民主义的宣传中加强国民的心理建设。在国民性改造方面,孙中山结合西方道德中的“利群”“利他”性来塑造“好人格”,使国人具有公德,能够“替众人来服务”[4]。他还主张用传统道德中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5]来加强国人自身的修养功夫,从内心上加强我们的心理状态。在三民主义的宣传方面,孙中山加强对国民党党员的宣传,努力使“四万万人的心理都归化本党”,促进国人都具有共和的心理意识。中西兼容的心理建设是孙中山在有选择性地继承中国传统知行观精髓的基础之上,积极学习西方先进文化成果而形成的以行易知难为中心的思想体系,对于民国的总体建设具有巨大的作用。
孙中山的建国方略思想的第二部分就是物质建设。他之所以主张建国方略,就是要加强中国的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试图用先进思想在解构儒家文化中建立起新的社会秩序。因为儒家文化是在农耕文明体系下建立起来的,在近代社会中表现出了落后,为了由弱转强,孙中山根据中国的自然状况和经济发展的需要,主张实施各项具体的发展政策。物质文明建设包含了孙中山建设资本主义国家的具体规划,“注重于铁路、道路之建筑,运河、水道之修治,商港、市街之建设。其次则注重于移民垦荒、冶铁炼钢”。这些建设方案是他考察了西方社会得出的理论成果,体现了系统建设的整体性思维,描绘了顺应时代潮流的具体蓝图。
孙中山的建国方略思想的第三部分就是社会建设。发展民权是社会建设的重点。由于中国长期受封建专制影响,“人心涣散、民力不凝结”,孙中山认为必须加强民权建设,激发民主意识,最终实现“民之所有,民之所治,民之所享”[6]的政治模式。他认为国人要学会“议事之学”[6],即学习开会,以此来商议国家大事行使民权。参考了西方议事规则的民权就是“民有选举官吏之权,民有罢免官吏之权,民有创制法案之权,民有复决法案之权”。具体而言,实现民权要通过议事、讨论、修正、计票、表决等具体的操作规则体现出来,以引导民主意识淡薄的中国民众。这不仅是对共和制的必要举措,而且批判了封建专制的独裁统治,只有赋予了国民正当的权利与义务,民权政治才能实现,进而促进社会的发展。
建国方略思想是以中国古代的认识论为理论依据,融入先进的进化论和生元说思想,主张通过发展实业计划而提高物质生产力,坚守传统文化中的公理良知,推广人道主义思想,扩展自由、平等、博爱的道德观念,落实民有、民治、民享的政治权利,国民以天下为公、自由博爱为共同抱负,努力实现世界大同的美好愿望的一种相对全面的理论。这一方案有其独到的建构方式:它以中西文化合璧为结合点,使民族主义、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三股进步思潮与中国固有的心性论哲学相融合,消解了大多数国民心中的奴性思想。从孙中山建国方略的思想脉络可以看出,对待传统文化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笼统判定孰优孰劣。“融贯”时应注意符合时代发展的需要,能够被时代所用。孙中山利用西方政治学说来改造传统文化,并用中国人的语言习惯和思维方式在中西文化的汇集处推陈出新,促进了中国文化从传统到近代的大规模转型,并在传统文化中增加了西方国家治世的内在根据,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他保留传统文化精髓,引进前沿西学,糅合中西,使两种来源不同的文化结合在一起,既促使中学的近代化,又促使了西学的中国化。同时孙中山对于文化观的努力表明,中西文化之间不是格格不入的,而是存在着巨大的互容性。
3 引进马列,完善政治秩序
第三个阶段是在孙中山的晚年。此时的中西文化观的“融贯”,还出现了一个更高层次的趋向,他不仅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理念,而且将中国的大同社会与列宁所宣传的苏维埃主义联系起来、将中国的王道主义与国际主义联系起来。他认为苏维埃主义能够为“受屈人民当联合受屈人民以排横暴者。[7]”他还将大同和苏维埃主义相提并论:“夫苏维埃主义者,即孔子之所谓大同也。……露国立国之主义不过如此而已,有何可畏![7]”他还提出“以俄为师”,使中国学习西方的内容有所发展,这就使中国学习到了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马克思主义是西方文化的最高成就。所以,孙中山对西方的学习带有了前瞻性,高于同时代人对西方的学习,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他在1905年5月访问国际社会党执行局期间,谈到了要用中国社会的特殊性,汲取欧美文明中的精华部分,避免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各种矛盾的产生,使中国国民幸福地“生活在最纯正的集体主义制度之中”[1]。可见,马克思主义和孙中山在以集体主义制度作为新社会精神支柱上存在着共识。孙中山还将马克思尊称为“专从科学方法去研究社会问题之解决”[5]的社会主义学派的“圣人”[5]。他虽然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以及阶级斗争的思想存在异议,但是,他坚信“一般讲社会主义的人多半是道德家,就是一般赞成的人,也是很有良心,很有道德的”[5]。
在彻底认清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意图后,孙中山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并达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联俄”是孙中山希望中国能够借助苏俄的力量形成独立的国家,并且联合世界无产阶级共同打倒帝国主义。“联共”是孙中山为了挽救国民党而吸收共产党作为新鲜血液的重要政策,两党建立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联合战线,将民主革命推向高潮。“扶助农工”是指国民党大力动员农民工人进行反帝反封建革命,并从民生主义入手制定提升工农政治经济等利益相关的决策,这极大地促进了阶级基础发生变化。“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是国民党学习苏俄后而得出的重要结论。在这一政策之下,中国人民在国共合作领导之下发动了大革命。超越了孙中山以往革命效果的大革命,提升了中国人民的思想觉悟和组织程度,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在华的势力。这三大政策融汇了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将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本思想、团结友爱与人民主权论结合起来,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奠定了基础。
在“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下,孙中山将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结合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吸收了西方多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的口号“自由、平等、博爱”对三民主义的影响极大。孙中山将自由对应于民族主义,将平等对应于民权主义,将博爱对应于民生主义。孙中山从马克思主义理论汲取营养,移植到中国传统文化之中,以服务于社会现实的需要。中国传统社会重视家族、宗族,形成了稳固的家国同构型社会,但是古代的国指的是诸侯国,近代的国指民族国家。在面对外敌入侵之际,中国需要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概念,家国同构必然会形成近代的民族国家意识。针对当时亡国灭种的危险,孙中山运用民族意识主张新民族主义,进一步要求中国在国际社会获得民族的自由,民众在国家内部获得民主的自由。如何建设民族主义,孙中山认为:“第一条件是要我们知道现在处于极危险的地位;第二个条件是我们既然知道了处于危险的地位,便要善用中国固有的团体,如家族团体和宗族团体,大家联合起来,成一个大国团体。结成了国族团体,有了四万万人的大力量,共同去奋斗,无论我们民族是处于什么地位,都可以恢复起来”[5]。新民族主义是维持中国生存与国家发达的有力武器,也具有了明确的反帝要求。中国传统社会重视民本的思想,强调保证人民群众生存生活的重要性。孙中山认为中国社会早就有民权的思想:“两千多年前的孔子、孟子便主张民权。孔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便是主张民权的大同世界。”[5]面对外敌入侵以及封建皇权的长期压迫,孙中山以民本传统主张新民权主义,即国家交往之间的权利平等、国民内部的政治、经济平等。在国内实施关于民权的具体方法,孙中山提出选举权、罢免权、创制权、复决权四种直接管理政府的“全民政治”[5]。他还进一步将民权与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斗争结合起来。中国传统社会重视仁爱的思想,并且历代统治者都主张用仁政来保障国计民生。面对国人难以保证的生存问题,孙中山认识到了仁爱的重要性,并且将仁爱与博爱等同起来。他以博爱贯通新民生主义,国家治理只有以博爱的方式解决人民的“求生计”问题,“人类才可以享很大的幸福”。他以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作为新民生主义发展的手段。平均地权的口号是孙中山效法亨利·乔治和约翰·穆勒的理论而得出的土地纲领,同时“融贯”了大同社会、均田与公仓等古法。新民生主义将“平均地权”发展为“‘耕者有其田’”[5],批判了地主阶级的利益,体现了反对封建剥削的精神。节制资本是从西方社会引进的思想,节制“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对于“工人之失业者,国家当为之谋救济之道,尤当为之制定劳工法,以改良工人生活”。新民生主义以博爱的方式关怀工人,并与扶助农工政策结合起来,构成了国共合作的重要基础。
孙中山虽然主张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但他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很多理论都持肯定的态度。马克思主义是具有国际性的学说,不是某一个民族的文化,而是对各个民族的文化都有包容性,所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能够很好地结合。同时,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具有很大的包容性和同化性。在孙中山思想中,大同思想、民本思想、朴素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和谐思想等,都与马克思主义相互契合。这就是孙中山高于同时代人的地方——已经模糊地认识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能够建立起相应的文化基础。
孙中山对待中西文化观的态度虽然经历了变化,但是内容客观、公允。他认为中国传统的文化在近代已经显得滞后,如果通过开放交流的态度进行有比较的鉴别吸收,才能持续稳固发展。这也是他进化论思想在文化观上的体现。这种“融贯”使中国的文化发生了变化,为中国社会的转型奠定了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