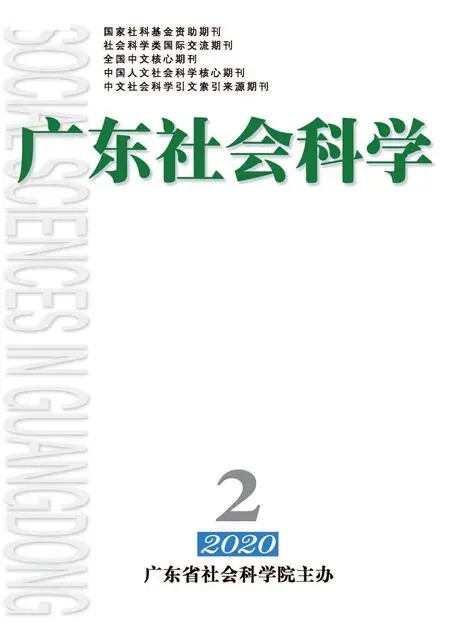布迪厄论“传记幻觉”:意义及其限度*
鲍 磊
20世纪80年代前后,伴随着社会科学的众多转向,社会学的传记取向同时从欧洲与北美的社会学传统中浮现出来。该取向呈现了当代社会学进展的一种新趋势,有人甚至以“传记社会学”(biographical sociology)名之①。“传记”(biography)概念亦加载了更丰富的意涵②,“成为一个重要的知识领域,具有认识论的和解释学的潜力”③。当然,该取向也引发不少争议,布迪厄1986年在一篇短文中所指斥的“传记幻觉”(biographical illusion),便是其中一个根本性的议题,因为它涉及该取向何以可能的问题。他指出,人类经验具有连续性的观点,在理论上和方法论上都内含危险,因为人类具有对经验进行重组并赋予其意义的能力,传记叙事的主体/题很大程度上系人为建构。该论一出,便成为该领域研究者不容回避的话题,他们经由论辩指出其合理或不合理之处,但布迪厄本人的立场、立论动机及其本人在相关著述中对该论的持守与权变,并没给予充分的观照。
总体上看,布迪厄秉持的是一种客观主义立场,反映了能否在传记叙事中找到客观性或传记叙事是否真实的问题。④这自有其合理性,但某种程度上却忽视了传记作为一种内在需要的合理性,也未虑及传记本身所具有的事实性特征和后果。本文旨在透过考察布迪厄生平境遇及其自我分析策略,尤其是其作品中隐晦的自传性反思,检讨布迪厄此论的意义及其限度,进而期待厘清传记社会学发展的重要前提性问题。
一、生活史与传记幻觉
在布迪厄看来,传记即生活史(life history)的书写。作为一个常识性的概念,生活史是被悄悄带入学术界之中的。他强调了生活史背后所暗含的一个重要的假设,即人生(life)便是一种历史。正如莫泊桑的《一生》(A Life)所显示,人的一生不可分割地成为个人存在事件的总和,此即其历史或历史叙事:“它包括开始(开启人生),不同的阶段,以及结束(意味着人生的终结和目的)。”⑤这种看待人生的方式默认了历史哲学是一系列历史事件,是一种历史性叙事或叙事理论。因此,人们难以分辨历史学家的叙事与小说家的叙事,尤其是以传记或自传叙事的形式出现时,便更是如此。布迪厄是要努力揭示该理论背后的预设:人生被看成了一个连贯的整体。
布迪厄批评了萨特对于福楼拜的传记研究。在他看来,萨特式分析依赖于无休止的、令人绝望的企图,把一个条件、一段历史和一件个人作品的全部客观真相整合到人为统一的“原初计划”之中。所谓“原初计划”(original project),是一种自由、自觉的自我创造行为,创造者藉此“可以自己承担起设计自己人生的使命”⑥。萨特“在作为个体的古斯塔夫那里,在他的幼年时期,在他的第一次家庭经历中,寻找福楼特作品的起源原则(the genetic principle)”⑦。这种生活被组织成为一种历史,它依据编年体的顺序(chronological order)、合逻辑的顺序(logical order)展开⑧。在布迪厄看来,没有人是服从原初计划的,也无哪个人的人生是符合必须以目的论方式实现的隐含计划。“在某种遗传的心理-社会学中,一位作家如何成为现在的他,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在某一特定类型作家中所处的地位或职位是如何形成的。”⑨
事实上,无论是传记性叙事还是自传性叙事,(由被访谈者)提供的事件并非总是以严格的编年体演替的方式展开,偏离主题线索的情形时常发生,他们不过出于可理解的需要,试图按照相互联系的序列加以编排。在某种意义上,主体与客体(访谈者与被访谈者)在接受叙事性存在所具有的意义方面具有相同的旨趣。“自传性叙事是受到为过去及未来赋予意义、进行合理化、展示其内在的逻辑所激发,经由创造合理的关联使之连贯一致,而连续性状态之间的原因与结果也因此成为其中必要的发展步骤。”⑩因此,在布迪厄看来,挑选若干重要事件来说明全部之目的,并建立因果联系或最终联系使人生变得一致,乃是一种将自己变成自己生活意识形态专家(making oneself the ideologist of one’s own life)的倾向。而那些天生倾向于接受此种人为意义创造的传记作者强化了这一点,为了使传记主体的存在具有解释上的连贯性,传记作者往往成为传记主体生活的理论家和同谋。
于是,当人们把生活视为一种展开的旅程受到质疑时,作为一种线性叙事的小说结构就会被放弃。福克纳的小说《喧哗与骚动》(The Sound and the Fury)便体现了这种“双重断裂”:生活被界定为一种对历史的抵制(anti-history)。莎士比亚在麦克白一剧末尾之处也表明:“这是白痴所讲的故事,大吵大闹,聊无意义”。布迪厄据此认为:“为了生产一种生活史,或者把生活视为一种历史,也就是说作为一种对重要的与有方向的事件序列的连贯叙事,或许符合了一种修辞学幻觉(rhetorical illusion),或者符合有关存在的一般表征,这是整个文学传统一直存在并且持续加强的。”而要避免这种修辞幻觉,最好的办法是到打破这些传统的人那里寻找启发。布迪厄引格里耶(Alain Robbe-Grillet)有关现代小说的评论指出,这种新文学表达模式的产生,是由于认识到小说话语的传统表征的武断性(内隐了连贯且统一的历史)以及事实的非连续性。
布迪厄接着提出了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即赞成或容许把日常生活经历视为统一体或整体的社会机制(social mechanisms)是什么?社会世界有各种各样对于自我进行整合和统一的制度,它倾向于以一种精心构建历史的方式,将常态与身份认同等同起来,而身份认同被理解为负责任的存在对自身一如既往的坚持。在这些制度中,最为明显的便是“专用名”(the proper name),它是“严格指称词”(rigid designator),“指的是所有可能世界中的同一对象”,“不断变化的世界上的某个固定点”,专用名的使用类似于“洗礼仪式”(baptismal rites)对于恒久不变的身份的指定。不同领域对于某个人表现所做评价,并不能改变他在人类社会中的定位。作为一种制度,专用名不受时空影响,超越所有生物的或社会的变化,为被指定的个人提供社会秩序所要求的名义上的连贯性,即自我认同意义上的身份认同。“专用名是其承受者跨越时间和社会空间可见的身份确证,是个人连续性声明的统一基础,也是整合官方记录、简历、任职履历、警方档案、讣告以及传记中各类声明的社会接受的可能性。它通过暂时的或最终的清算后给出裁决,把生活建构成一个有限的总和。”专用名只能证明人格的同一性,是在社会层面构成的个体性,它以巨大的抽象为代价。这就是为什么专用名不能描述它所命名的属性,也不能传递有关它的信息。
由此讨论,布迪厄认为生活史较接近官方模式,也接近于它所支撑的身份认同哲学。社会过程的批判分析在研究者无意或有意中发挥作用,建构了社会上无可指摘的“生活史”这种人工制品,尤其是对特权人物而言,其被授予了与其社会地位相一致的构成生命事件的历史序列。因此,那种“试图把生活理解为一系列独一无二又自足的事件序列,而不去了解‘主体’,仅察看与之相关的方面,其连续性便可能只是所谓的专名而已,这正如有人要理解地下铁而不考虑其网络结构一样荒谬”。因此,所谓的传记事件就是社会空间中的诸多投资与移动,或更确切地说,是“在审慎考察的场域中使用的不同类型资本的分配结构的不同连续状态”。我们对某人轨迹的理解,常是由于其轨迹在特定领域已预先连续性地建构起来了。
该文的最后部分,布迪厄强调了要重视个体所在的具体环境所带来的影响,重视个体在不同场域中的角色,重视个体与历史事件发生之关系,以破除所谓的社会表象(social surface),破除传记幻觉所建构的个体,回归实在的存在体(ens realissimum),这样也有助于摆脱作为直觉人(intuitus personae)的我们对于直觉的迷恋。
综上,布迪厄站在认识论的角度,认为传记存在着一个危险的主观主义问题,使传记作家陷入了一系列无法摆脱的幻觉之中。在回顾《学术人》时,他再次强调了自传的幻觉性,甚至认为写作自传,“经常既是一种为自己树碑立传的方式, 也是一种自掘坟墓的方式”,缺少真正的社会学洞见。那么,落实到布迪厄本人,他如何对待自己的生平?其(反思性)学术实践又将其置身何地呢?
二、布迪厄的生平境遇及其自我分析
华康德曾就布迪厄入职法兰西学院演讲中提到的“(社会科学)提出的每个命题都可以而且应该运用到社会学家身上”,问了一个尖锐的问题:“我们能否用布迪厄的社会学对布迪厄本人进行分析呢?您能解释自身吗?如果能,你为什么对谈论布迪厄的个人事务不置一词呢?”。
布迪厄的回应是,这一方面出于“职业上的警惕”,免于陷入学术体制尤其是法国学术界所推崇的极端唯我主义立场。对于知识分子卖弄逸闻趣事的做作行为,布迪厄不予苟同,甚至感到悲哀,直斥为“对怀旧情绪的自我放纵”(self-indulgence of nostalgic evocations)。更重要的是另一方面,他这样做,是要保证其学术话语和所发现事实的“自主性”,不为他人提供攻击自己的由头,因为对个人生活方式和喜好之类私人信息的披露,难免会落人口实。即人们会以简化的方式,用研究者的出身、品味之类的说辞来攻击其本人的观点,或者认为其研究对象不具有代表性。他甚至认为,提出个人问题的人是受到康德所谓的“病态动机”(pathological motives)力量所驱使:“人们想要了解他的背景或者品位,只不过是为了寻求反对他关于阶层与品位论述的武器”。布迪厄认为,其所从事的社会学实践区分了他的社会学话语和个人经验,而其社会学实践在某种程度上又是以其社会经验为对象的社会学产物。布迪厄提到将其自身作为研究对象来分析,并不是出于自恋,而是作为某群人的代表:“我在谈论自己时道出了他人的真相,这时常让他人愤怒”。
里德-丹阿哈伊(Deborah Reed-Danahay)指出了另一种隐含倾向,即包括布迪厄在内的男性人种志学者一直对自传体写作深感不安,在人类学作品中他多次批评这种“自恋”(自传体书写),并将自己的反思性形式与之划清界限。罗格尔斯(Susan Carol Rogers)也观察到,自传体反思一直受到法国人类学家的抵制,他们将其与“英美‘后现代’人类学”联系在一起。奥克利(Judith Okely)则指出,反思性自传之所以遭到强烈抵制,乃是因为它建立在非常西方的、以民族为中心的传统之上。
当然,布迪厄此举,与其个人出身和生平境遇有着更大的关系。他时常提及童年生活的比阿恩村庄和在巴黎高师接受教育经历对他的影响:它们“使我能够探索我作为客观主义观察者的主体性中那些最模糊的领域”。在与华康德的公开对话中,布迪厄称自己为“阶级叛逃者”(class defector),展示了出身所带给他的耻辱:“我大部分青春时光都是在法国西南部一个偏僻的小村庄里度过。我惟有放弃许多重要经验和所得,而不仅仅是某种口音,才能满足上学的要求。”求学经历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他本人的社会地位:作为一名农村寄宿生,他只能穿一件灰色的罩衫,而走读生则穿着最新式的服装,他的加斯康口音也常常受到取笑。当然,这些在学校里成为“他者”的经历,也使布迪厄意识到自己的不同,意识到自己独特的思维、穿着和说话方式。他明确承认,寄宿学校的经历和上层阶级的流动使他对社会生活有了独特的看法,能够“跨越”不同的社会环境。
由于农村出身,他将自己定位为阿尔及利亚的“准原住民”和在法国乡村田野工作中的“客观的知己”,以维护自己的民族志权威。理查德·尼斯(Richard Nice),曾如此评价:“我认为布迪厄本人的过去有两个版本。一个是神话般的故事,他在其中是一位面对城市文明的农村男孩,另一个是他更加认真地思考过的,是成为一个小资产阶级并获得成功的故事。”不过,布迪厄的反思性立场有时显得复杂或自相矛盾。其作品表明,教育制度再现了社会阶级,法国资产阶级的孩子(继承人)最容易获得精英高等教育机构的教育证书,出身工人阶级家庭的孩子因其惯习和性格,在法国的教育制度中取得成功的可能性较低。布迪厄本人却是个例外:来自外省,出身一般,却在法国教育体系中大获成功。他并没有透露更多取得成功的信息,也没有透露何种因素导致他最终成为法兰西学院社会学教授。
应当注意到,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法国人文科学领域,有两种强有力却相互对立的观点:强调全部现实背后正式结构的结构主义和强调人作为个体存在经验尤其是自主行动中固有意义的存在主义。这两种立场的各自的缺点是未能认识到对方的解释优势。当然,布迪厄多少还是偏向结构主义的,他“吸收了结构主义的很多真知灼见和有用方法,摒弃了结构主义用一种过于经验化和过于静态的方法把社会生活描述成一种遵循规则而不涉及策略行为的叙事”。
在进行民族志研究的过程中,布迪厄形成了自己关于客观结构和主观理解及行动之间的相互作用的观点,这种经历也帮助他形成了自己的思想定位。作为研究者,其任务既不是把自己的看法强加给研究对象,也不是简单地再现研究对象的概念,而是要像哲学家巴什拉那样,在研究中“赢得”事实。在《社会学的技艺》中,社会学研究就被视为一种赢得社会事实的持续努力。布迪厄逐渐认识到,这种研究最基本的困难之一就是对当地人关于他们的行为所进行的漫无边际的解释应给予何种程度的重视。对布迪厄来说,人们的生活并不是按照自由的选择或策略进行的,而是受到惯习和社会领域客观条件的制约。他在《再生产》中写道,“在教育或思想传记的每一个时刻”,惯习“倾向于复制客观条件系统,而这正是它的产物”。
之后,布迪厄把这种田野研究方法用来研究比阿恩地区的村庄,把实践活动中的个人知识与客观模式的抽象知识结合起来,运用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摒弃人们理解自己日常行动的常用方法。因为这些日常的叙事往往包含着歪曲和失察,许多思想观念行为便根源于此。“布迪厄的研究计划就是理解人们所采用的实际策略,这些策略与自己解释之间的关系,以及人们在追求自己目标的过程中,尽管自己不是有意识地选择甚或没有意识到,然而却再生产出客观模式的过程”。
布迪厄去世后出版的《自我分析纲要》(Esquisse pour une auto-analyse)(以下简称《纲要》)是其自我分析的一个极为重要文本。布迪厄特意在扉页强调:“此非自传”(This is not autobiography)。按照他自己的界定,该书既非文学亦非自传,但他又确确实实地为自己的社会学设定了一个文学的或传记的限制。他想象自己是在给受过高等教育的读者做最后的交代。布迪厄向自己的受众呈现了潜在自己方法背后的基本经验,他讲自己的人生故事不是出于其他的原因,而是为了展示有关自己研究工作的故事。他在《纲要》中试图运用惯习理论来探究自己的人生轨迹,但这毕竟是他最个性化的作品,他交代了自己更多的过往(如他的童年,他在寄宿学校的早期教育经历,以及他在阿尔及利亚服兵役的经历等等),他的写作风格,他个人内心的自我,同时也为他的公众形象及其矛盾表现进行辩护。
该书标题与精神分析具有某种程度上的共鸣。在弗洛伊德那里,自我分析是精神分析训练的必要补充。“我只能借助客观获得的知识来分析自己(就像个局外人一样)”。布迪厄最初把该书描述为“自我分析”(self-analysis),但很快就重新给贴上了“自我社会分析”(self-socioanalysis)的标签。他试图将文本呈现为一种非自我的精神分析、一种非自传:我将最客观的分析用来服务最主观的东西。
布迪厄如何根据他的社会阶级再生产理论解释自己的轨迹、自己的成功故事呢?他没有设定一个连贯的生活史叙事,也不是按照确切的时间顺序呈现,这符应了他有关传记幻觉的观点。布迪厄没有从他的童年出发,他的叙事直接从其在巴黎高师的学习时期开始。对布迪厄而言,教育场优先于家庭:“理解首先要理解你所形成的场和所反对的场。这就是为什么我的论述方式可能让读者惊诧,因为读者可能希望我从头开始,即作为一种方法要点,通过唤起我早年的岁月和童年时期的社会世界,我必须首先考察的是我在1950年代进入这个场时的状态。”布迪厄将他职业生涯中的大多数“选择”描述为机遇和惯习的混合体,他从人格特征和生命轨迹两方面来审视惯习。布迪厄就是其自身惯习的产物,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抓住某些机会,充分利用他继承的性格,以便在学术生活中取得成功。然而,在他的自传体作品中,布迪厄并没有提供太多关于他是如何抓住机遇的(如他只是提到在开启职业生涯时,阿隆给了他建立自己研究中心的机会)。
在《纲要》中,布迪厄的写作一反线性生活叙事的传统,尽管他也揭示了自己生活经历的诸多方面。对于精神分析叙事来说,从头开始并非必须,布迪厄自我分析中情节和故事的错位在这方面与精神分析是完全相一致的。布迪厄在回答一个有关他的知识分子自传的问题时,对其社会角色进行了自我呈现:“我不必告诉你,在我的‘智识之路’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许多事情都是偶然发生的。我自己的贡献,无疑与我的惯习有关,主要在于充分利用它们,发挥我的最大能力(举个例子,我认为我抓住了很多很多人都会错过的机会)。”布迪厄的家庭故事(特别是他与父亲的关系)在《纲要》快结束时才被提及。随着该书的展开,一个新人物从阴影中走了出来,这就是社会学家本人(布迪厄),他在向读者倾诉自己“所做、所思、所是”。
三、布迪厄隐晦的自传体反思
如要在布迪厄一生所写的40多本作品中挑选,那么对他自己生平着墨较多的,当推《学术人》《帕斯卡式沉思》以及他最后的遗作《自我分析纲要》。当然,在后期各类学术性采访中,也可窥见布迪厄对于自己人生历程的某些细节或多或少隐晦的交代。事实上,尽管布迪厄只是在最后著作署名“一次自我分析的尝试”(An Attempt at Self-Analysis),但实际上,他之前所写的每一部作品都应以之为副标题。
在早期著作《阿尔及利亚人》(the Algerians) “解体与痛苦”(Disintegration and Distress)一章临近结尾的描述,可视作布迪厄的生平写照之一,至少说是掺入了他个人的背景。此处内容所描述的是阿尔及利亚迅速变化过程中,年轻知识分子们“持续面对表现不同行为方式的新价值观的浸染,因此不得不有意识地去审查自己传统的隐性前提或无意识模式,这类人被抛在两个世界之间,被两个世界所排斥,过着一种双重的内心生活,成为挫折和内心冲突的牺牲品,其结果是不断地受到诱惑,要么采取一种不安于认同的态度,要么采取一种叛逆的消极态度”。
布迪厄也是介于两个世界之间的人:对他来说,这两个世界是他成长的法国农村的传统世界和他成长的知识分子、社会科学家的城市世界。这后来成为布迪厄作品中涉及反思性方法的一部分。在晚期著作中,布迪厄承认有“我的两个部分”,并试图通过继续在他的家乡比阿恩做研究来调和二者。在阿尔及利亚,他看到了传统社会与现代世界的对立,以及这种对立对相关个人所造成的影响。尽管文化背景不同,但在比阿恩也存在着类似的现象。对布迪厄来说,人生轨迹反映的是集体的历史,而不是单个人的历史,他一直试图淡化自己经历的独特之处,因为在他看来这些经历对于任何来自类似背景的人来说都是相同的。布迪厄认为个人生活发生在与文化和象征资本相连的社会和物理空间中,他就是在此框架下诠释个人故事。布迪厄在比阿恩和阿尔及利亚进行的研究,便开始了对于访谈方法的使用,包括扩展的个人叙事和生活史叙事。布迪厄将这些文本视为“自我民族志”(autoethnographies)——即知情者对其自身社会文化环境的评论和分析。
《学术人》被华康德认为是“抵制自恋式的反思性或自我理解的典范”之作。这项关于教授的社会阶层和教育轨迹的研究,展示了学者的社会阶级出身或惯习,如何影响到他们所接受的教育类型和之后在学术等级体系中的最终位置。可以说,该书某种程度上包含了布迪厄整个生平轨迹的缩影。在英文版序言行将结束时,布迪厄提到“借助对他人的分析包含了篇幅可观的自我分析”。这表明了他探索教育轨迹这一主题的动机,很大程度是出于他自身的经历。但这也是一本最让布迪厄焦虑的著作,那就是可能带来对于文本深层意义和作者本人的误读,甚至以一种背道而驰的方式被人加以解读:“作品发表以后,一种对所写东西失去控制的极大危险”。事实上,他在整个第一章都在试图避免这一点。
在后来的访谈中,布迪厄称该书为反传记(anti-biography):“这本书实际上既是检验社会科学中反思性之适用范围的尝试,也是一项寻求自我智识的事业”。“关于我们何所是的最密切的事实,最不可想象的未被思考的事实,都铭刻在我们过去和现在所处的社会地位的客观性和历史之中”。布迪厄自认为《学术人》代表了他自己“认识论试验”(epistemological experiment)的高潮。这项试验开始于1960年代早期,他将之前用来揭示陌生领域(阿尔及利亚农民和亚无产阶级)中亲属关系逻辑的研究方法,运用到了熟悉的领域。这项研究的“方法论”意图,“是要推翻观察者与他的研究领域之间的自然关系,让平凡变得特殊,让特殊变得平凡,为了清楚地说明在这两种情况下什么是理所当然的,提供一个非常具体且实用的证据来表明对客体进行全面的社会学客观化的可能性以及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我称之为参与者的客观化(participant objectivation)”。
如果把布迪厄的社会学研究生涯分成三个阶段,那么中间阶段的研究便更多地体现了他对于客观性的寻求,尤其是有关法国大学中的教育和法国中产阶级品味的“社会分析”,基本上都是依据先进的定量方法进行的。但即便这些研究中也明显具有隐晦的自传性质。以《国家精英》为例,布迪厄视其为“他自己学徒生涯的集体经历”。该书研究的是他母校巴黎高师的仪式性和象征性“制度仪式”。布迪厄虽然没有插入他自己对国家精英教育的个人叙事,但为了传达自己的经历,他转向了其他人的叙述。他利用普通人的集体历史,阐述了共同经历和群体的共同精神:“那些来自社会和地理空间主要区域的作家们,其自传体叙事构成了无与伦比的社会学文献,作为与这些社会轨迹相关的主观经验的第一手记录,这些社会轨迹实际上比我们想象的更为可靠也更为天真。”
几年后在《帕斯卡式沉思》“非个人的自白”附文中,布迪厄提供了一个更加个人化也明显更为主观性的视角。之所以将自己作为知识分子的自传如此命名,其意在以此种方式既将自己与卢梭所体现的法国自传体告解传统拉开距离,又通过唤起这种比喻将自己置身于该谱系之中。他并未以自传式的风格把自己塑造成“英雄般的学者”,而是展现了一位战胜逆境并设计自己人生的人。布迪厄写道,他“不打算提供那种所谓的‘个人’记忆,那种为学术自传提供阴郁背景的记忆——对杰出大师的敬畏之情、与职业选择交织在一起的知识选择”。布迪厄有时是以一种不经意的方式,讲述自己的职业生涯:“我从哲学中逐渐走出来的距离,无疑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所谓的存在之偶然事件,对此人们可以径直说,这是在我作为一位人种学者和社会学者的‘职业’的起源”。
布迪厄晚期的作品又重新回到他早期的访谈和叙事研究方法。在《世界的苦难》中,受访者的证词被作为论证社会苦难模式的依据。布迪厄不再认为定性研究访谈缺乏客观性,相反,他提到了采访的重要性及其在社会学研究中的方法论品质。哈梅尔(J.Hamel)认为,这种社会学方法是兼具“挑衅性的和伴随性的自我分析”(the provoked and accompanied self-analysis),因为它是在社会学家提出要求或“挑衅性”时进行的,而且访谈者必须跟随着受访者的叙述,参与者的对象化也正是经此过程才成为可能。事实上,访谈者很容易就能识别出自己与受访者共有的特征。该书每章都包含一个访谈,描述了苦难的某一特定维度,详细交代了访谈的背景和访谈进行时的若干细节,并且同时从方法上和理论上对受访者的证词进行了分析。
虽然在此前的研究中,布迪厄所秉持的客观立场,并不把访谈内容作为其研究的依据,但在《世界的苦难》中,这种立场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被访谈的普通男女的谈话成为重要的例证。社会行动者的实践意识不再被视为虚假意识,布迪厄认为这是一种知识惯例,它倾向于将社会行为转化为个人(或群体)的行为,而不是将其置于构成社会学理论目标的客观关系层面。哈梅尔认为布迪厄此时对常识的批判并不是因为它是一种虚假的意识,而是因为它建立在社会行动者自发意识基础之上。自发意识不能表达受访者的痛苦,因为它与受访者的行为直接相关。因此,人们不能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解释他们痛苦的原因,但是他们可以从实践的角度来加以解释。事实上,《世界的苦难》中受访的被压迫者以实用的语言表达了自身的处境:“某些访谈者,特别是处境最不利的人,认为这提供给他们一个特殊机会,使他们能够作证,使他们的意见得到听取,使他们的经验能从私人领域传播到公共领域。(他们)也能有机会充分解释自己所说的话,也就是说,能建构他们关于自己和这个世界的观点,并把他们在这个世界中看到的自己和对这个世界的观点公开化,变得可理解,并被证明是正确的。”
布迪厄对常识的评论表明了反思社会学家和不具有反思性的普通人(外行人)之间的对立。普通人无法根据自身所处环境的认知来改变自己的生活。日常生活是不受质询的,它是理所当然的,这一功能使人们能持续过自己的生活。然而,普通人有时也会以社会学家的身份思考和评价他人的行为。反思性并非学术界的专利,尤其是在当代社会,随着外行人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发展反思性知识,外行人的知识能力越来越多地反映出与社会科学家接近的特征。事实上,人们经常试图解释为什么会以特定的方式行事,即便有时觉得这种行为令其反感。
可以说,布迪厄将自己客观发现的全部武器装备(他所塑造的社会学工具)用来服务于对他而言最为主观的东西:他自己。“我对自己所做的工作与我对社会世界所做的工作是分不开的”。增加对一个方向(即“社会世界”)的了解以增加对另一个方向(我自己)的理解为条件。对布迪厄来说,这两项活动是同一项活动。“我不是在讲述我的生活史:我是在试图为科学社会学做出贡献。”尤其是到职业生涯的最后阶段,布迪厄似乎对自己的生活经历如何塑造他的作品的问题变得更加开放。在法兰西学院的最后一场演讲中,布迪厄谈到了自己的工作是一种“自我社会分析”,是一种理解塑造他人生轨迹的社会力量的方式。《纲要》一书中所提供的自我分析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基于他在学术领域的社会历史定位。根据他自己的理论,布迪厄不能写一本自传,但为了给自己和自己的作品增添权威,又需要把自己的经历和背景介绍给他人。这种张力遍及布迪厄的几乎所有作品。
四、结 论
由于布迪厄对科学客观性的捍卫及其采用的实证研究法,人们很容易认为其理论具备严格的科学性和客观性。但这其实忽略了布迪厄作品中颇富个人化的哲学维度,即通过自我批判来持续追求自我知识(self-knowledge),以达自我完善和解放之目的。在布迪厄看来,以自我意识为中心的传统哲学所进行的自我审查形式(如内省沉思、忏悔、现象学叙事、自传体记忆等),并没有真正理解更深层的、无意识的、社会结构性的自我层面,而后者恰恰塑造了个人的自我意识。客观的社会学分析在此可有所助益,因为它绕过了个人回思过往的选择性记忆和防御机制,也避开了肯定自我的保护性叙事虚构。他认为,只有超越自我反省、自我意识、自我分析的极限,才能意识到自己思想的极限,然后去努力超越之,即便这种努力不会完全成功。这是布迪厄对自己的社会世界进行批判性分析背后的动机逻辑,而这又可能会反思性地导向对其作品和其自身的分析。
可以说,布迪厄并未全然将传记斥为幻觉。当然,为了摆脱传记可能的陷阱,必须研究制约传记主体思想和行为的社会结构,即必须重建客观的社会关系网络:“这是为了打破传记作家与传主的合谋,当他们试图通过创造一种人造的存在感来赋予生活连贯性时,这种存在感除了出生证明上的名字之外,没有任何永久性的东西。”布迪厄坚称,关系系统定义了场域状态以及由于个体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而拥有的不同惯习。“场域”是围绕科学、艺术、政治、文化和其他事件的评价而形成的社会空间。在这些建立客观社会关系的权力场中,个体凭靠竞争获一席之地。在相互交织的社会关系网络中,个体所处的位置使他们能够在某些可能性的范围内采取行动,具备某种情感思维方式。后者便是所谓的“惯习”:品位、技能、语言以及表达意见和做决定的方式。“惯习,是所有生平经历的产物”。总的来说,惯习的作用是无意识的,因为它是历史的结果,是个体自身综合社会的方式。在布迪厄看来,“传记事件的意义和社会价值”并非基于主体而构成,而是基于行动者在社会空间中的“位置”(placements)与“位移”(displacements)而构成,后者首先赋予传记事件以意义。
古斯多夫(Georges Gusdorf)也认为,传记提供的只是针对鲜活人生幽灵般的、不完整的和被歪曲的图像,而一种好的生活史应当“为个人提供一种系统辩护(apologies)或道义支持(theodicies)”。鲜活人生从来就不是摘要式的,而只能基于由现在赋予的结构来认定。正是叙事者本人赋予事件以意义:“我们常常基于对我们的现在和未来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过去来行事,而忘记了现在所具有的决定性力量。”现在经由回忆过程形成了过去,回忆过程给过去注入了内容、意义和方向。在生活史中,过去的罪恶由参照更好的现在为藉口,而现在的罪恶则以寻找过去的困难为藉口。生活史就像一个飞去来器(boomerang):从现在抛向过去,又借势返回并进入未来,但方向与力量乃由现在决定。回顾过去是一个目的论的进程,它指向一个特定的目标,即当下。叙事者站在目标的位置,借助只有在当下才能看到的线索,展开其人生发展轨迹。
惯习的不同造成个体生平经历上的差异,后者反过来也影响前者。在成功者的叙事中,人类生活的各个阶段被联系在一起,形成令人信服的整体。叙事者当前的生活状况就像一个棱镜,早期的生活经历由其得以过滤。当受访者报告他们的经历时,他们从不同的社会立场出发,或多或少地认同公认的文化脚本。
“过去-转折点-现在的模型”(a past-turning point-present model),被认为西方自传的原型之一:“我们永远在讲述我们是如何经由抛弃过去而成为现在的自己”。我们有权讲述自己的生活,我们必须证明我们已经获得了对自己的控制。既然现在赋予过去以意义,既然叙事的自我是主体,而过去的自我是叙事的对象,那么今天的自我必须控制昨天的自我。昨天的自我不负责任,今天的自我却必须负责任地行事。过去的自我可以摆脱不愉快,而现在的自我必须面对它。伯陶(Daniel Bertaux)提出了一个类似的观念,即“传记的意识形态”(biographical ideology),意在强调生活之线的“片段化”特征,主体试图重觅与拼凑(bricoler)一种隐秘的连贯性,但这种意识形态拼凑并不是一种(心理的)幻觉,而是一种存在性需要,一种集体现象,它在后果上也具有真实性。
因此,传记叙事在讲述个人自己(或他人)的生平时掺入其他成分,对叙事者本人而言有时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作为研究者,关键事项之一并非要去弄明白这种连贯性是幻觉还是现实,而是要清楚个人在谈论或书写自己的生平时,如何给予这种连贯性。换言之,研究者应当去揭示的,乃是这种连贯性的根源,隐藏在其背后的动机与需要,以及建构它们的更大的意识形态。或许,正如默顿所提倡的,人们(社会学家)应当训练出细心的“社会学之眼”(an attentive sociological eye),看懂字里行间说了什么才是问题关键所在,并且要在理解过程中,设身处地将自己的理解增补进叙事者因考虑到社会限制而忽略或删除的空间。此外,人们也可以通过叙事者的其他作品,包括发表的相关言论和他人证词,来加以验证。世界上的生活条件和经历千差万别,每一种经验都必然是片面的,“我们惟有把从众多生活世界中获得的经验汇集起来并加以比较,个人经验的有限现实才会显露出来,依赖和相互联系的复杂网络也才会显露出来,对个人生平与广泛的社会进程之间的紧密联系也才会有新的发现”。
①鲍磊:《社会学的传记取向:当代社会学进展的一种维度》,上海:《社会》,2014年第5期。
②英文中的“biography”已成了一个“打包性”概念,涵盖了自传、传记、日记、回忆录、生活史、个人叙事等体裁,甚至成为“传记研究法”(biographical method)的缩写。中文有“传记”和“生平”两种表述,“传记”是以书面形式对“生平”的呈现。
⑥⑨Pierre Bourdieu,TheFieldofCulturalProduction:EssaysonArtandLiteratur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p.161,p. 1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