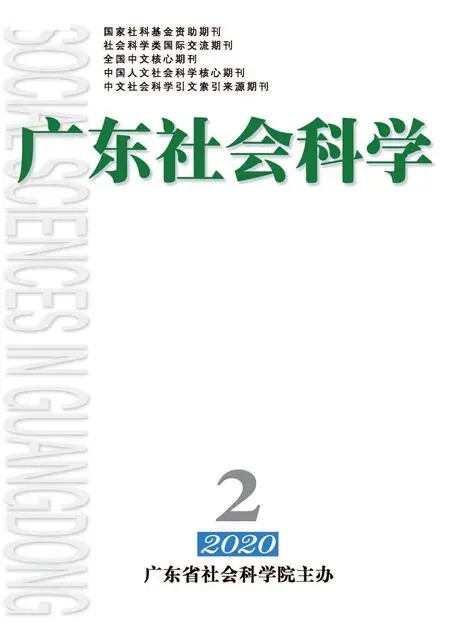新政与宗教:清季自治筹款中的庙产征用纠葛*
孟祥菊
明清以降,佛道各教与世俗政治之间,并未产生泰西各国政教合一体制下那种冲突剧烈的政教矛盾,相反,两教在国内尚有一定的发展趋势,各类神灵寺庙、道教宫观等连绵分布在各省境内,形成庞大的庙产财源。①光绪后期,国家财政日益窘困,而各项新政改革的需款却陡然上升,庙产财源遂成为朝野各方挖潜追逐的重要领域。这些财政挖潜行为令“新政”运动与宗教势力间的矛盾骤然凸显。清季庙产兴学研究早有学人涉及,②地方自治筹款亦大规模染及各类庙产财源,财源获益虽明显可观,但却引发剧烈的教俗冲突。官府因支持士绅此类“剥夺”寺庙财源的行为,亦被僧徒群体目为祸源,由此产生了僧、绅、官之间事关多方的复杂纠葛。“俗教矛盾”和“政教矛盾”夹杂在一起,折射出清季新政改革的别样面相,值得作深入剖论。
一、庙产丰裕与自治筹款介入
宋元以降,乡间小民终年衣食辛劳,在完成赋役、应付家庭日常开支后,收入所剩无几。他们收入虽然微薄,但对宗教神明的捐献却毫不吝惜。明清时期,释道二累的社会影响力在乡里社会根深蒂固,全国各地庙宇繁多,难计其数。庙宇大致分为四类:载在祀典的官庙、家族祠庙、佛教道教庙观、民间自发建设的神庙。其中,官庙所占比例很小,其他三类则占据绝大部分。
万历年间,冯从吾曾言:“余尝览海内郡邑志,即撮尔岩邑,其寺宇多则数十,少亦十数。”③据民国六年的《山东临沂县志》记载,全县官庙只有35个,佛教庙宇却多达254处,道教庙宇也有301处,民国初年,该县二教庙宇多达586处。④据萧公权对晚清国内寺庙的研究,“十九世纪的华北农村,人口在1000人以上的村庄平均有寺庙7.25座,100人到200人的村庄有寺庙2.73座,100人以下的村庄平均有寺庙2.13座。”⑤关于全国庙宇、庙房数量,庙地、庙财总数,很多学者试图用科学方法计算出精确数字,但这是个极其庞大的工程,碍于多种客观条件限制,很难对其作出全面统计。也有学人试图通过地方志文献计算地域性庙宇的数量,如张玉法根据清末《山东通志》统计山东各种庙宇数量;⑥苏云峰对湖北的祀典庙宇做过详细统计;⑦王笛也对嘉庆年间四川的祀典以内的庙宇做过统计;⑧王庆成对晚清直隶八州县的庙宇进行了研究。大致核计,平均每县811.4个。⑨实际上,各县寺观庙宇的数目应远超此数。晚近各省修志时,因地方志性质及篇幅所限,会只选择记录州县境内知名度高、规模大的少数寺院,而忽略大量的乡间小寺庙。并且国内不少中心城市的寺庙数量也未统计在内。习五一曾以北京为例,对大城市的寺庙进行过统计,数目惊人。⑩因此以地方志为基础的统计并不全面。许效正对庙产中的庙房、庙财、庙地等进行了详细统计,尽管其核算或有误差,但他所做的推论具有一定说服力。他认为,清季全国城乡各类庙宇大约有200-300万座,这些庙宇大约拥有1600多万间房屋,1900多万亩土地,财源入款几近亿元。
数量可观的庙产在晚清受到社会各界的垂涎觊觎。戊戌变法时期以庙产财源兴办学堂,大约是晚清庙产被征用的开始。1898年光绪帝颁下上谕:“至于民间祠庙,其有不在祀典者,即着由地方官晓谕民间,一律改为学堂,以节靡费而隆教育。”这表明清廷此时政策导向是只保护列入祀典之寺庙,而其他庙产可因地制宜,补充地方新政之需。光绪末期,清廷推行新的社会治理模式,鼎力实施地方自治改革。然而,支撑自治事业的财源经费在制度安排上却排在练兵、兴学等其他官方主导的改革事业之后,加之国家税、地方税的划分并未落实,中央经费和地方经费亦未厘然分界,清廷颁布的《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在自治经费获取途径方面可谓“搜肠刮肚”,将眼光瞄向了庙产财源这一领域,“自治公所可酌就本地公产房屋或庙宇为之”。清廷早先虽有针对外省侵占庙产颁下纠偏补漏的上谕,但问题是并未对庙产产权、征用范围、征用方式等方面做出明确规定,庙产财源征用政策存在着相当的模糊性。宪政编查馆颁布的上述《自治章程》自然成为各省奉行的准则,各地绅董基本上认定“不在祀典之庙产”即为地方公产这一论断,极少顾及僧界及民众的实际利益与诉求,这也暗示了寺庙财产在清末的命运走向。
北方省份中,直隶新政改革被视为各省楷模,总督袁世凯实施的“剥夺”政策具有典型性。袁氏态度明确,只保护列入祀典以内和僧徒自置的庙产,对其他范围的庙产毫不留情。袁离任直隶后,他的继任者杨士骧仍坚持这一政策,将庙产充公支持地方自治建设。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1909年1月),天津县议事会通过《天津县议事会定清理庙宇庙产办法六条》《天津县议事会移董事会议定养赡僧道办法十一条》两个文件,将全省不在祀典之庙产尽数收归董事会管理,一刀切地将庙产划为地方公产。《清理庙宇庙产办法六条》的核心就是认定全部庙产均为地方公产,交董事会管理,寺院、庵观、民间神祠均可无条件征用。虽然为减少政策实施的阻力,制定了养赡僧道办法十一条,但补偿比例非常低,且条件相当严苛,与被征用的庙产财源收益相比,这种补偿微不足道,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僧俗纠纷。从各种史料来看,直隶征用庙产财源的力度应该最大,绅董们的执行也最坚决。吉林省的做法紧随直隶,全省民间庙产全部划归自治会经营管理,理由相当充足,“俾无用之资财,充维新之要需。”
陕西省对提庙产兴办新政亦甚积极,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凤县境内的僧人宽来等人到巡抚衙门控告县令纵容属下抢占寺产,要求行省大员主持公道。提学使对众僧严行斥责,认为该县秉公酌提庙产,已给僧人留下焚修之赀,已属平允之至,而僧人呈词来控,尤属刁钻可恶。批词体现陕省大员坚决捍卫地方士绅权威的特点。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河南省和奉天省。河南对提取庙产办新政异常热衷,省谘议局的议案提议:凡先贤祠庙、社庙、庵观、寺院及附属财产,若由公建者皆视为公款公产;若由募化或部分人集资建设,但已拨充公益费用者,如拨充公益费用的义庄、祠堂、会馆及其附属财产等,亦得视为为公共财产。对于酌提数目,提议以该庙不动产与动产的30%为限,由自治绅董确查后呈请地方官核办。河南庙产征用力度不可谓不大。奉天省提拨庙产比例与河南相似,奉天南路建议将各乡寺庙中香火、庙房、土地等调查清楚,概提三分之一收入作为小学堂办学经费,剩余部分则拨作开办董事会之经费,奉天锦州自治机构亦请提庙产办理自治研究所,均被奉天巡抚允准。
南方省份情形与北方省份稍有差异,偶有顾及寺庙和僧侣利益的情况,但也普遍存在以庙产财源办理自治的趋向。江西省万寿宫由商务总会经理,每年租金七千余串,收入颇丰。后因筹办自治,经自治议员吴盛麟、梁际升等提议,将庙产提作自治经费。但兴国县议事会请求提拨庙产租税补充自治经费的建议,却受到赣抚批驳,认为议事会之前已禀请抽收茶馆、包席馆、酒馆、煤油等捐,在未说明利弊情形下擅自开征,现又欲提治平观的花生落地税、火神庙糯谷等项落地税、仙娘宫地租等多项庙产,这种贪婪行径令人异常反感。慎重提取庙产的事例也出现在湖北省。玉泉寺为该省著名名胜古迹,当阳县想以此作为财源办理新政,鄂督告诫提用此处寺产必须谨慎,不可仓促草率。这种告诫并无严禁之意,实际上鄂省征用庙产办理自治的现象较为普遍。类似案例,安徽也不少,安徽无为州绅士丁云骧等人,因筹办自治经费确无着落,公同议定将庙产作为举办自治经费,得到允准。
浙江抚臣支持倚重民间绅董的倾向也很明显,该省绍兴属县内清隐寺,为王氏远祖捐建,产业丰饶,年可收息数千金。后被该邑士绅以藉办公益之名强行接收管业,王氏后人纠合同族禀控到省,但浙抚认为清隐寺建自汉晋时代,事隔千余年,王氏宗族不能视为己产,而应划归公产。浙抚显然是选择站在士绅立场去处理庙产纠纷。江苏巡抚也支持该省自治公所的清查筹款行动,批令该所绅董“除家庵外,凡属寺院,均须一律清查。”“谓募建者不在清查之列,实属误会,亟应明白开导,以免疑阻。”这类批词,明显代表了苏省大员的政策倾向。其实在传统社会,大量民间寺庙的产权不仅仅按照佛教戒律设定,往往由施舍者与住持僧人之间私下契约确定,僧人一般负责日常经营,施主则分享监督权利。作为施主后代,在民间产权习惯中亦有监督所捐产业的权利。但在清末,当监督权成为地方新政阻碍时,便不被官方认可,巡抚用公的概念否定了施主的既有权利。后来苏、浙等省因征用庙产而发生了诸多不可调和的纠纷,引起严重社会动荡,在僧立教育会极力斡旋下,地方官审夺利弊,强硬态度有所缓和。
二、庙产征用之途径
地方自治在各省的推行处处需款,清政府应对此难题的“法宝”依旧是奉行此前咸同年间所施行的“就地筹饷”办法:各省“自可因时制宜,量为变通,并准就地设法另行筹措。”各省就地筹款达到了“苟能搜罗巨款,无不立见施行”程度。庙产财源一般包括实物与收益两个部分,各省征用的情况或许千差万别,但大类情况包括了实物征用、附捐征缴和无偿占用等三种形式。下面根据文献蒐集情况,略述如下:
(一) 征用寺庙场所举办自治
寺庙、道观、神庙等场所遍布南北,不需耗巨资整饬修缮,便可直接征用,拨做自治办公场所,或用于召开民间耆绅会董集会,或作自治培训场所等。这种征用庙产行动在各省普遍存在。江苏苏属境内,此类举动堪称典型,这在《江苏自治公报类编》中有详细记载。
江苏省共成立自治公所26个,其中有16处建在庙宇里,占总数的61.5%。地方自治机构及其活动是《申报》报道的重点之一,该报尤其关注自治研究所、宣讲所、选举所及地方自治临时会等选址利用庙宇作为场所的情况。报道不仅涉及江苏一省,其他行省举办自治,征用庙宇、道观、神庙、宗祠等情况,也为该报所关注。下表所列,以苏省为主,间有涉及其他省份部分地区占用庙产场所,举行集会等办公活动的大略情况。

《申报》所载地方自治机构占用庙产情况列表
庙地是庙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各地庙宇有数额不菲的土地资产,清末实施地方自治,官绅不会对僧人丰裕的寺产视而不见,这笔庞大的财富,成为各地官绅征用的重点。庙地拨充自治经费的案例在各省境内非常普遍。天津县议事会公布的一项议案清单中,有关庙产问题占四分之一。另外在刊出的一份已结案件清单中,议决案共有37件,而解决庙产问题的议案有21件,占议决数量的57%。这些数字表明,庙产对地方自治举足轻重,甚或是公款公产的主要部分。
(二)征缴庙捐补助自治经费
清季各省境内的庙宇、道观、神庙等皆积存一定数额资金,来源于信徒所捐、僧道外出做法事收入、庙房租息等。庙产清查完毕后,地方官绅制定征收规则,令寺庙住持每年一次性或分几次缴纳规定数额的捐资。各地收捐方法差别较大,“有以各庙之进款为标准,捐收十分之二者;有合某地方各庙,每年共捐钱若干者;有分别春秋两季,捐纳若干者。”庙捐始于宋代,清末财政史料中有庙捐的大量记载,其用途不一,大约不外乎创办学堂以及举办自治事业所用。《江西全省财政说明书》调查本省庙捐后,显示出本省以此挹注的大略:“本省祠庙产业由县署迳行管业者,有新建县之澹台祠租,泰和县之黄山谷祠租谷除租谷变价列充祭祀用费外,并未拨充本地各项公益之用。又查弋阳县劝学所入款内有庙田租谷,饶州府中学堂入款内有火神庙年息,广信府中学堂入款内有罗饶沈钟公祠租,鄱阳县高等学堂入款内有永福寺租谷及屈公祠祭品银息钱,南丰县敬业学堂入款内有汤祠租息。”此时江西士绅禀提庙租充当自治经费的报道亦频见报端,说明提取庙租的做法在江西普遍存在,已为地方一种经常性收入来源。陕西省和河南省在征收庙捐创办学堂和自治事业方面,亦有相应的记载。
奉天各州县征收庙捐的情况普遍存在,各州府庙捐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先后创办”,城厢议事会因开办自治经费短缺,于宣统二年征收庙捐,准备将城厢庙产彻底调查,然后派人劝导,按规定每年提取部分现金。从寺庙田产中抽取公益捐是湖南省的通行办法,湖南省谘议局规定:“以累进法征庵观寺院等之田房附捐”作为自治公益捐。在江苏,“经忏捐,每寺院僧人每家伙居道士,诵经一日应捐大洋五角办法,照董事会原案,由地方官札饬僧道两会司,逐月查明本城区僧道诵经若干日,按数纳捐,汇交自治公所。”这可以看作是自治机构征收庙捐补助自治的典型案例。天津知县决定从光绪二十七年(1901)“提天后宫庙房租及正殿香资,认充清丈局捐款,每年缴津钱三百吊。”从资料来看,该庙住持僧“届期交纳,并无贻误。”在此之后,地方自治机关对庙产的征捐缴费行为更是变本加厉。
在浙江,杭州府太守及仁、钱两知县于光绪三十三年三月(1907年5月),召集各庙宇僧道开会,勒提庙捐。庙捐划为六等:“一等五百元,二等三百元,三等一百五十元,四等七十元,五等三十元,六等十五元”。规定捐款分四季认缴,各寺僧均未提出异议。“各自认定签押者计有一百二十余寺,已占浙省寺院之多数,议定未到各寺将来亦不能抗捐。”在山东莱阳,光绪三十二年抽提庙捐,凡有住持庙宇,每年共缴纳制钱600贯,无住持各村,认缴制钱400余贯,宣统二年住持庙宇又加制钱420贯。山西省亦举办庙捐,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以前,收征常年庙捐的府县有乡宁、介休、灵邱等县。随着新政深入发展,征收范围与征收力度不断加大。
(三)以处罚形式占用庙产
清末自治筹款途径除了征用庙房庙地、征收庙捐外,以处罚形式占用庙产的情形亦屡见不鲜,往往一僧犯法违规,将会导致整个寺庙判罚充公。
直隶省天津县议事会了解到祇树园僧人慧海案发后,致函巡警总局,认为按自治章程,庙宇及其产业均归地方公款公产,应将祇树园庙产没收充公,由议事会接管。巡警总局复函认可此提议。议事会另函知县,请求援照河北大寺淫僧光大成案,将祇树庙产全数充公,办理地方公益。该庙产业最终交议事会变价充公,以五成归议事会兴办公益之事,以五成为警局修盖廵所之用,祇树园庙产最终被无偿瓜分。在保定,某寺方丈因贩卖烟土被押,该寺其他僧人在得到补贴生活费后被驱逐,寺产经议事会议决,归地方自治经费。南乡姚家村,西大药王庙僧人昌印因犯奸案,由巡警总局禀请,将庙产充公,得到直督杨士骧批准。庙地由自治董事会与四乡巡警南局公同办理出售,所得价银归作警、学两项经费。省城功德院、青莲寺两处庙产最多,被自治会先售掉若干,剩余之地尚有五六千亩,或招佃租种,或变卖生息以充自治经费。
这种以处罚形式征用庙产财源的方式在他省也普遍存在。位于河南商城县南的笔架山古剎寺,寺产富厚,学董周晋三与县令梁韶如、绅士张胜之等藉口事故,带人将寺产抄没,将田稞400余石全部充公,并捏罪请县令缉拿在逃寺僧。后该寺僧人了情和了凡提出禀控,周晋三的驳词显得蛮横无理:“现行立宪地方自治,观察何人,渠安得过问?”奉天锦州府筹设自治研究所时,官府邀众绅召开特别大会,郝姓会董认为,建立自治研究所筹款困难,东街财神庙按年可收锦钱万余吊,提出将东街财神庙之产,移作办理地方自治之用,这一意见得到巡抚批准。江苏某城自治公所董事毛子健认为,邑庙住持邱金生不守清规,举动乖谬,应将该羽士所管怀回楼公产基地拨归中区收租,充作自治经费。自治员绅借助官势随意征用庙产财源,态度蛮横,各寺庙禅院缺乏官方保护,其失助弱小境况可想而知。
三、佛道两界的抗争
倒卖和隐匿庙产是佛道两界常见的应对行为。面对自治机关的征用,寺院一般不会心甘情愿将寺产充作地方自治之资。寺僧和道士等通过设法隐匿和盗卖转移等方式尽可能减少损失。寺僧倒卖庙产之事频见报端。河北三太爷庙产,在地方公款公产章程出台后,该庙道士刻正极力运动各方势力,企图保住庙产。东直门北小街口袋胡同邻近尼姑庵之土山子地基,该庵尼姑声称,此地为该庵庙产,已经卖给位于后海的俄国教堂,试图以此来拒绝自治公所的染指。上海送子庵住持恩荣无视禁止出售庙地规定,将庙产出售。城厢议事会称,庵地归自治公所收管,令该僧将所收定洋赶紧退还,而该住持僧人辩称,所收定洋已买地迁葬慧月僧墓,钱已用罄,无法返还。
隐匿庙产在当时亦屡见不鲜。如意庵住持王明山将善庆庵地基占据,并盖房开店,此后又将善庆庵庙产捐助农林学堂,却伙同李义中隐匿如意庵庙地。此事被议董事会获悉,将庙宇及其产业查勘收管,以充公用。面对倒卖隐匿庙产的案件频发现象,天津议事会感叹“深恐迟延日久,庙产一空,于自治经费所失甚大。”
挟民武力抵抗是清季各省政教对立的极端形式。地方官绅热衷于利用庙产兴办自治,本意甚美,却低估了强行征用背后的巨大阻力。征用庙产不但涉及利益再分配,且触及大众精神信仰。清季民智未开,民间尊崇鬼祀、迷神信佛之活动广泛盛行,人们常常视神佛之寺庙比自家性命更重要,因此每遇有侵犯寺庙者,无不群情激奋,一旦再有匪徒乘机煽惑,极易激成极大风波。清末随着征用庙产力度的增大,地方社会变乱蜂起。广西阳朔修仁交界之民众,因阳朔县知县董毓梅勒提庙产,激起公愤,各村民携载米谷牲畜避聚猺山中,并派壮丁于隘口持械扼守,与官府对峙。幸而地方官及时抚慰,终未酿致不可收拾之巨患。
浙江仁和县属西塘镇议事会,预备在相定庙宇内开成立大会,但遭到该镇邱宝元等人寻衅滋事。他邀同50余人,将议场门口之栏杆及桌椅等打毁,会中各职员皆由后门奔逃。当乡村庙宇遭到士绅侵占时,僧道和乡民习惯于向地方官员控诉,而地方官员往往偏袒征用庙宇的士绅,寺僧和乡民有冤无处申,便会采取聚众砸毁学堂及自治机关的极端行为。
杭州府属钱塘县所辖之安吉、长寿、定南、定北四乡,俗称上四乡,因筹办自治经费短缺,分区摊派。各乡议员贴出通告,本省大员已批准将庙产房屋清查后一律提充自治经费。各乡闻此,痛斥自治“除勒派苛敛以外,别无何种政策”。各村社庙为乡民共同捐资建成,数百年一直承载春秋报赛等祭祀活动,现要强行归公,群情激愤可想而知。在全国影响极大的山东莱阳民变、川沙自治风潮、鄞县僧界大暴动,都与自治征提庙产财源有密切关系。
反复提充庙产是导致山东莱阳民变的原因之一。莱阳全县境内庙宇有两千多座,庙产所得向来由各庙宇自收自支。清季新政繁兴,不得不就地筹款,从光绪三十年始,以各种理由数次加收庙捐。后又因筹办自治,再提三成归官变价,僧道群情激愤,于是聚众千余人入城滋闹,自携免提庙产谕稿,逼官照钞用印。朱令阳奉阴违暂允寺僧请求,随后派兵四十名,严拿僧道数十人,分别责押监禁,并饬铁匠速制镣铐数百具备用。拿获赴署滋闹僧道尼姑多人,该令用杏花雨、连环计、火烧舰船、连生贵子等非常规刑罚方式挨次拷打,每堂刑讯,惨叫之声难以忍闻。僧尼纷纷会议,欲联合民众,杀官劫狱,以为报复。众僧尼与曲士文一起,煽动变乱,焚毁富绅数家房屋,并与官兵对抗,致事态不可收拾。
江苏省川沙自治风潮起因也与提用庙产办自治有密切关系。川沙事件导火索为“素党”首领丁费氏率领徒众攻击设在俞公庙的自治公所,直接起因是长人乡议事会决定,俞公庙是地方公款公产,将其部分房屋改为自治公所。但是对丁费氏及其信徒而言,俞公庙是他们公共活动场所,更是他们的私产,一旦被自治公所人员占据,其忿忿之情可以想见。1911年2月6日,长人乡议事会正在俞公庙开会,丁费氏率领百余名信徒聚集庙前,砸毁自治公所招牌及其他设施。自治绅董逃出,禀告本县同知后,丁费氏与丁阿希被捕,但随即逃脱,事态于是处于失控状态。仅仅一个星期,乡董、议员等自治职员住宅二十九家,小学校十二所,自治公所三处全部被打毁,一名乡董身受重伤,受损金额达三四万元。最后松江府太守出兵1100名,江苏巡抚程德全也责令6艘炮舰开赴川沙,风潮最终平息。时人评议川沙自治事件时,对地方自治议员大加批评,认为议员“专以勒捐苛罚,结交长官欺压乡闾,据民祠为办公,争庙宇为学塾,假公济私,害民肥己,自治局竟成怨薮!”在列举苛捐时,提到“不论何等庙产,一例罚充公用。”“苛罚勒捐款项正多,笔难磬述。”本应造福地方的地方自治却遭到民众激烈反对,川沙县发生大规模的“自治风潮”,使乡议会禁止“素党”的议决案,最终未付诸实施。
宁波鄞县僧众暴动也是这一时期的典型事件。甬郡境内寺院众多,很多已改为学堂,万寿寺又被指定为自治公所,该寺住持与僧教育会迭次反对,未获允准,而且各乡举办自治纷纷效尤,导致驱逐僧众、暴力抢夺寺产之事频发。僧众屡至僧教育会商议办法,后纠集二三百人,至知府衙门跪香,请求豁免,亦未解决问题。后僧人至万寿寺,与自治公所职员大起冲突,将公所什物捣毁一空,经鄞县郑大令调解而临时解散。地方自治议员与寺僧的冲突却自此拉开序幕。各处僧众1000余人陆续云集甬镇,鄞县郑令恐僧人入城滋事,不准其入城;僧教育会遍贴通告,约束僧徒,在万寿寺召开大会讨论办法;自治会也召集绅学各界,连日秘密会议。宁波府邓太守和鄞县郑令,见此情势,迅将实情上禀浙抚。在此期间,绅、僧两派函电纷纷,互相指责,僧俗摩擦不断,僧人与巡防队殴斗,致伤防勇4人,僧徒2人亦伤势严重,且1名僧人殒命。事态严峻,各方均筹议办法,力求平息事件。
宁波府僧教育分会控诉该县众多寺庙被作为地方公产拨归自治公所,导致僧界恐慌,力请政府收回成命。宁波知府审时度势应允了僧教育会请求:寺院庵观不在城镇乡自治章程第五条所列各款内,鄞县城区以万寿寺为自治公所,必须双方协商妥当,不能直接将城厢万寿寺等十余寺作为地方公产。鄞县自治机关却认为,从县志来看,该寺为唐周景运年间所建,为本地公产无疑。该寺五月间因藏秽窝赌,曾被巡警局拿获,按例理应将寺封禁。况在万寿寺设所,已得浙抚批准,各乡公所多恃寺观而建,若将咨部核定之案再做变更,寺僧定会援案反对,对自治前途大有危害。宁波知府反对这一主张,认为该寺本非地方公建,不应看作地方公产。住持不守清规,藏秽窝赌,应罚住持,与寺庙无涉。重申若借用万寿寺部分房屋,必须经过双方协商,不能单方面收为公产。这一意见得到浙抚认可,“仰即转饬遵照并饬该分会知照”。然而,自治会绅董认为,寺观早被列入公产清查范围之内,且清查章程亦经地方官绅公同认可并刊册印发,现官府却态度忽变,执意要求宁波府说明理由以释群疑。该绅董的要求遭到宁波知府严厉斥责。县令亦做自我检讨,希望自治议员顾全大局,和平解决争端。
浙江巡抚增韫秉持息事宁人态度,分别对鄞县城区自治会、鄞县郑令、以及僧教育会各打五十大板,以便能够速结此事。他首先告诫鄞县城区自治会,个别僧人聚众闹事,应通过正当途径解决,不能意气用事。借用庙产必须双方达成协议,严禁抑勒庙产行为;他告诫鄞县郑令,自治会借用寺院,必须遵照僧立教育总会禀准章程办理,若寺僧腐败则更换住持,不得擅提寺产,僧众逞蛮应督同僧立教育分会共同整顿约束;他告诫僧教育会,严格约束僧人滋事,不能任其逞蛮,借用寺产,须经绅僧双方协商办理。面对如此结果,鄞县自治机关无法接受,指责官方袒护僧众,恼怒至极,呈诉谘议局“开会表决,全体辞职并汇缴执照。”谘议局对僧教育会制定的租用寺院章程亦不认可,认为施行细则内所添条文不可行。但浙抚坚持前议,强调征用庙产须经双方协议,才不致因场所问题再起冲突。
当事人、参议者依据自身认知和利益诉求,各取所需地运用清廷征用庙产政策行事,因而呈现出前后矛盾的改制思路和多岐性分析方法。风潮爆发前,为完成清廷督催的宪政指标,地方政府希望通过征用庙产,能快速达成政绩,赢得声誉,因此征用庙产不遗余力。而后地方官府态度大变,则是事态恶化催生的结果,地方风潮大起,会危及地方官员仕途与政绩。莱阳民变爆发后,朱槐之、奎保、杨耀林、孙宝琦均受到不同处分;广西全州知县周岸登饬派绅士征提庙产,差点引起变乱风潮,清廷将其撤职查办便是显著案例;湖南长沙饥民抢米事件爆发后,时任湖南巡抚的岑春蓂被清廷革职,均折射出处事不当导致的官员个体损失之大。
从地域上说,清末僧俗庙产纠纷及寺僧暴动遍及全国,新政期间各地对民间庙产的征用掠夺,是国家依靠强迫手段促成,必然会激起宗教人士强烈抵制,庙产问题成为牵涉各方利益的敏感问题。对民间庙产的侵占和掠夺,确实能够减轻举办地方自治的财政压力,对推进国家政治近代化进程起到一定作用。但这种放任征用民间庙产的行为,激化了政教和教俗矛盾,无视僧道和信徒的经济利益及此类群体的精神信仰依赖,必然会引起这一团体的强烈反对。清季新政改革在财政困绌背景下冒进实施,连带孕生的诸类矛盾,确系朝野各方必须面对的难局。其得失损益,进止权衡,值得今人回到历史田野做深入的解读和探究,有裨于为当下治国理政提供智慧。
①近代以来,庙产是一个模糊笼统的说法,细究起来,寺庙的种类范围甚广,如称寺、庙、祠、庵、观、宫、洞、馆、殿、阁、道场、梵刹、宫观、祖庙、家庙等数以百计的称呼,围绕此类拜祀活动场所及其附属产业的财源十分巨大。(参见王鹤鸣等编:《中国寺庙通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1页)
②关于清末庙产兴学的研究主要有:许效正的《清末民初庙产问题研究(1895-1916)》(陕西师范大学2010年博士论文)、《试论清末民初(1901-1915)湖南的寺产冲突》,(北京:《法音》,2012年第12期)、《清末庙产纷争中的官、绅、僧、民—1905年广州长寿寺毁学事件透视》(北京:《世界宗教文化》,2017年第3期),陈显川的《清末新政时期巴县应对改革的态度与潜在目的—以巴县档案为中心的考察》(成都:《成都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鲍宁的《清末北京城庙产兴学与新式学堂建设》(开封:《史学月刊》,2016年第12期),张佩国的《从社区福利到国家事业—清末以来乡村学校的公产及经费来源》(上海:《学术月刊》,2015年第10期),徐跃的《清末四川庙产兴学及由此产生的僧俗纠纷》(北京:《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5期)等。
③冯从吾:《少墟集》,《文渊阁四库全书(别集类)》,集部232,第1293册,卷十三,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233页。
④沈兆祎等修,王景和等纂:《山东临沂县志》(一),民国六年铅本,第180页。
⑤Hsiao Kung-chuan,RuralChina:ImperialControlinthe19thCentury,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67,p.19.转引自许效正:《清末民初庙产问题研究(1895—1916)》,第30页。
⑥张玉法:《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山东省(1860一1916)》上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2年,第126~131页。
⑦苏云峰:《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湖北省1860一1916》,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41),1981年,第92页。
⑧王笛:《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648页。
⑨王庆成:《北方寺庙和社会文化》,北京:《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2期。
⑩习五一:《近代北京寺庙的类型结构解析》,北京:《世界宗教研究》,2006年第1期。
———姚春敏博士《清代华北乡村庙宇与社会组织》一书简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