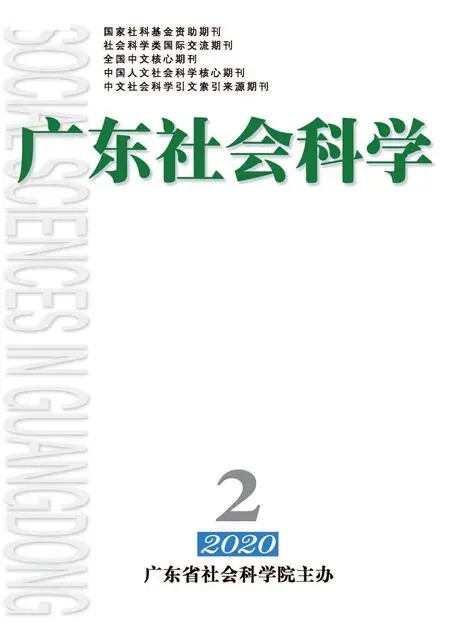论诗歌翻译与中国新诗创作的三重关系*
熊 辉
长期以来,我们借用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或美国学派的平行研究来处理中外诗歌关系,并普遍认为外国诗歌对中国新诗的发生发展产生了积极或负面影响。但实际上,中外文学关系视野下的“影响”并非虚妄的对接或没有事实依据的联系,故外国诗歌要对中国新诗创作产生实质性影响,缺少翻译中介环节便无法实现。而从译介学的角度出发,外国诗歌的翻译与中国新诗创作之间并非简单的影响和被影响的关系,二者还具有同质化倾向和交互促动的潜在关联。
一、诗歌翻译与创作的同质关系
鸦片战争的爆发逐渐浇灭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民族文化自信,在西潮涌动的语境中,摈弃传统诗歌的抒情方式而借鉴西方诗歌的艺术经验,成为新诗革命的方向。在讨论外国诗歌的翻译对中国新诗创作产生影响之前,不得不提及的是,二者具有同质的关系,即翻译诗歌参与了中国新诗创作,在经验积累及情思表达等方面,诗歌创作与诗歌翻译显示出诸多的相似性。
翻译活动必然会包含创作的素,因而诗歌翻译行为有时也是一种诗歌创作方式。创造性是诗歌翻译与叙事文学翻译的最大差异,翻译者常常会从民族诗歌艺术或个人审美偏好的角度出发,
创造性地对原诗的形式及内容进行修改,翻译的过程融入了能动性的创作,如此便会使译诗相对于原诗而言具备一定的创新性。因此,我们可以近乎绝对地认为,诗歌翻译过程中的创造性是不可避免的。诗歌的可译性问题成了长期以来中国翻译界争论的焦点,但一直没有统一的结论,原因还是因为人们没有认识到诗歌翻译过程中的创造性特点,没有从创作的角度去理解翻译。中外翻译学家根据文学翻译的历史经验曾对翻译进行了如下论述:“文艺翻译正是一种创作活动,因为文艺翻译的结果是用另外一种语言创作新的艺术价值,翻译是和这种语言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而最主要的一点则是从翻译中也可以看到译者的创作个性。所有这一切都为多少世纪以来的文艺翻译实践所证实。而且,各国的文艺翻译历史都表明,文艺翻译史总是追随着文化史,并且是总的文学过程的表现方面之一,因此,把文学准则用于文艺翻译是完全正确的。”①尽管中国的诗歌翻译从20世纪初才开始形成规模,但朱自清等有志于探讨中国诗歌翻译的学者也认识到了诗歌翻译过程中的创造性:“有人以为译诗既然不能保存原作的整个儿,便不如直接欣赏原作;他们甚至以为译诗是多余。这牵涉到全部翻译问题;现在姑就诗论诗。译诗对于原作是翻译;但对于译成的语言,它既然可以增富意境,就算得一种创作。况且不但意境,他还可以给我们新的语感,新的诗体,新的句式,新的隐喻。就具体的译诗本身而论,它确可以算是创作。”②对译诗活动中的创造性体会最深刻的诗人应该是郭沫若,他1923年翻译雪莱诗歌后的感受集中体现了译诗与中国新诗创作的相似性。同时,翻译外国诗歌可以练习中国新诗创作,使之更加完备。闻一多先生也正是在翻译霍斯曼等人作品的过程中不断地试验他的格律诗主张,才使他的现代格律诗创作逐渐趋于成熟;何其芳晚年采用格律形式去翻译维尔特及海涅的诗歌,为自己的现代格律诗理论寻找证据。这些事例表明,译诗的创造性在某种程度上是中国新诗创作的一种训练,这种创造性所积累的经验与中国新诗自身在创作活动中所获得的经验一样,在推动中国新诗创作的方向上具有相同的功用价值。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外国诗歌的翻译与中国新诗的创作具有同质性。
译者在新的语言文化环境中赋予原作生命的翻译行为,如同诗人赋予其作品生命的创作行为。在一个异质的文化语境中,译诗要获得生命就必须依靠译者根据民族诗歌的审美要素进行再次创作,才可能使原诗在异域获得长足的生命力,被广泛地传播和接受。从中外诗歌翻译史上的实际情况来看,大凡优秀的诗歌翻译文本都与译者的创作才能密不可分,比如英国诗人菲茨杰拉德在翻译古代波斯名诗《鲁拜集》时,将原作加以英国诗歌式的改造,译作反而被视为英国诗歌历史上的著名篇章;与此相似,美国意象派诗歌先驱庞德在翻译中国和日本古典诗歌时,也因为加入了太多的创作因素(实际上是一种误读),从而使《神州集》被视为创作作品而非译作,并冠冕堂皇地进入了美国诗歌的历史殿堂。1923年底,创造社主将成仿吾先生翻译了一篇名为《关于莪默伽亚谟的新认识》(New Light on Omar Khayyam)的论文,集中讨论菲茨杰拉德对《鲁拜集》的翻译。这篇文章认为,菲茨杰拉德的翻译就是一种创作,“当我们想起斐氏所恃仅用英国的服饰装点出了一个800年以前的波斯天文诗人的诗,他的盛名似有不可思议之处。真的,我们若不切实地知道斐氏不止于是一个译家而远远超过,他的盛名之由来是不可解的。Charles Eliot Norton教授很明白地说明了斐氏的真的地位。他说:‘我们称斐氏为译家,是因为我们欠少一个更好的名字来表示诗情由一国语言向另一国语言之诗的转换,与原诗的意景(境)用一种不完全相异而适合于另一时地习尚之新态的形式再现。这是受了一个诗人的作品之灵感而作的一个诗人的作品;这不是翻译而是一种诗的灵感之再现。’”③菲茨杰拉德翻译莪默伽亚谟的诗歌时,采用了如同成仿吾所说的“表现的翻译法”(Expressive method),④翻译过程中译者的创作激情毫不逊于他自身的写作行为。艾略特在《庞德诗选》(Selected Poems of Ezra Pound,1929)的序言中高度肯定了《神州集》的艺术成就,断言其因为对中国诗的“发明”而将被视为“伟大的杰作”。艾略特在此将庞德的译诗视为英语诗歌中的佳作,而非外来的某种异质性诗歌作品。由此看来,诗歌翻译过程因包含着情感和艺术的创新而体现出一定的创作特征,胡适当年用《关不住了》来宣告新诗成立的纪元,恐怕也是看到了这一点。
在某些情况下,翻译诗歌如同创作诗歌一样表达了诗人的情思,译诗与中国新诗创作的相似性即二者表达诗人感情的对等性;从文学接受的角度来讲,这种同质化还表现为二者为读者了解诗人或诗人所处的时代提供了对等的信息。译者常常根据自己情感表达的需要去选择诗歌翻译文本,如同读者由于某些文本所表达的情思切合了自己的心境而兴奋不已一样。众所周知,胡适翻译了大量的爱情诗,对于一心要打破诗歌形式并倡导文学革命的人来说,其译诗题材的重要性远远逊色于体裁的重要性,但胡适译诗在情感方面的类同性却暗示出其题材选择的有意性。胡适到底为什么会选择爱情诗来翻译呢?《关不住了》一诗明显反映出胡适意欲冲破压抑人性的传统爱情理念;《老洛伯》中锦妮陷入了爱情和道义的两难境地中:一边是深爱着她且“并不曾待差了我”的老洛伯,一边是她们互相爱恋的吉梅。这似乎表达了胡适自身的情路历程:锦妮无异于胡适自己,老洛伯无异于胡适的夫人江冬秀,他们共同经营着传统的、也是很符合道义的婚姻。有学者认为,胡适翻译的爱情诗是为了弥补自身感情的缺陷,借译诗来抒发自己的感情,⑤由此我们不难看出,胡适的这些译诗表达了他在创作中想表达却不便公开的情感,倒是翻译像创作一样表达了他内心浓厚的情感。1923年7月,郭沫若在翻译“鲁拜诗”时曾说:“本译稿不必是全部直译,诗中难解处多凭我一人的私见意译了。”⑥郭沫若所谓的“私见”就是他本人对外在世界的看法或独到的情感体悟,而其译作也因为有了这样的“私见”而洋溢着浓厚的诗性特质。另外,利用译本可以发现译语文化的许多内容:“从可能得到的文本中选择哪些文本进行翻译,是谁做的决定;谁创造的译本,在什么情况下,对象是谁,产生什么效果或影响;译本采取何种形式,比如对现有的期待和实践作了哪些选者;谁对翻译发表了意见,怎么说的以及有什么根据、理由。说的略微夸张些,翻译告诉我们更多的是译者的情况而不是译本的情况。”⑦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读者在面对诗人的译诗时犹如面对了诗人自己创作的诗歌文本,诗歌翻译与中国新诗创作对读者了解作者或作者所处的时代而言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
译诗与中国新诗创作在建构民族诗歌大厦的工程中做出了同样重要的贡献,这是二者同质化的又一体现。翻译文学在创造和丰富本民族文学方面起着与创作同样重要的作用,有学者甚至认为翻译文学本身就应该被划入到译语国文学大家庭中:“既然翻译文学是文学作品的一种独立的存在形式,既然它不是外国文学,那么它就该是民族文学或国别文学的一部分,对我们来说,翻译文学就是中国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完全是顺理成章的事。”⑧因此,翻译诗歌应该是民族诗歌的组成部分。在中国新诗刚刚诞生之初,其在形式艺术和内容思想上还显得比较单薄,不但不具备和传统诗歌对峙的实力,更不能真正独立地彰显其独立的文类品格,而正是大量的译诗作为新诗的一个组成部分直接建构并证明了新诗创作的实绩。作为中国新诗的组成部分,译诗理应划入中国新诗的行列,但长期以来,由于种种认识的偏差,翻译诗歌在中国的地位没有得到承认。在这一点上,美国人显然对翻译诗歌做出了更为开放的认同姿态,一位亲临美国的学者见证了美国人对待庞德译诗的“特别”态度:即在1998年出版的《美国名诗一〇一首》(101 Great American Poems)中,李白的《长干行》经庞德翻译为The River-Merchant’s Wife: A Letter 后,“一首中文译诗,居然荣膺‘美国名诗一〇一首’的殊誉”,并且“李白的《长干行》经过庞德的生花妙笔,已经被美国人毫无愧色地‘攘为己有’”。⑨
从民族诗歌创作历史和翻译诗歌历史来看,翻译与创作一样,均是民族诗歌的构成部分,为民族诗歌的建构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二者具有明显的同质化特征。总之,翻译诗歌活动固有的创造性因子、译诗表达情感的特点以及译诗在民族诗歌历史建构过程中的积极介入等诸多因素,表明诗歌翻译与中国新诗创作之间具有同质化关系。
二、诗歌翻译与创作的促进关系
诗歌翻译与新诗创作之间具有顺向的促进关系,具体而言,诗歌翻译刺激了中国新诗创作的发生和发展,为处于茫然和无序状态的中国新诗创作指引了方向,同时为贫瘠的新诗坛提供了创作资源,推动着现代新诗在艺术的轨道上不断探索和进步。
大家都纷然祝贺。老巴说:“过年我去归元寺烧了香。我什么都没求,只求阿东找个好工作,看来菩萨晓得我心诚呀。”
首先,诗歌翻译使中国新诗创作有了摆脱古代诗歌束缚的能量,促进了新诗创作的发生。“译诗,比诸外国诗原文,对一国的诗创作,影响更大,中外皆然”,⑩卞之琳先生在说此话时,已经充分体悟到了译诗对中国新诗创作具有无可替代的影响力。中国诗歌在晚清时期步入了僵化的发展境地,谭嗣同、梁启超等人提倡的“新学诗”以及后来黄遵宪提倡“我手写我口”的“新派诗”,均没能把中国诗歌引向复兴的道路,但他们的努力为中国诗歌的转折性发展作了充分的准备,因为他们以及后来的一大批人正是在接触并翻译外国诗歌的基础上,对中国诗歌未来的发展作了仔细的思考,并产生了美好的构想。也即是说,外国诗歌以及外国诗歌的翻译诱发了中国诗歌的新变,没有翻译诗歌,何来中国新诗?的确,诗歌翻译正是在改变中国诗歌观念的同时,赋予了新诗冲决传统罗网的力量,我们今天回望新诗的发展历程时不得不承认,如果没有译诗,中国新诗就会失去向中国传统诗歌发起冲击的力量。如果没有译诗的样本与模式,中国新诗就减少了改变传统诗歌观念与固有创作模式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对中国新诗的建设而言不可或缺,因为没有这种可能性的发生,新诗自身的创作就会因为文体特征的模糊而无法展开。
上世纪20年代,从世界文学发展趋势出发,朱湘在《说译诗》这篇文章中阐明了翻译诗歌对民族诗歌艺术复兴具有不可或缺的促动性,他从前意大利诗人裴特拉(Pet·Rach)介绍希腊诗到本国,酿成文艺复兴;英国诗人索雷伯爵(Earl of Surrey)翻译罗马诗人维基尔(Virgil),始创无韵体诗(Blank Verse)等事例出发,证明译诗对一国诗歌复兴所具有的积极意义。同理,诗歌翻译不仅诱发了新诗的产生,赋予了新诗发展的驱动力,而且在新诗诞生的初期为新诗创作提供经验教训,辅助幼稚的新诗创作走向成熟。“倘如我们能将西方的真诗介绍过来,使新诗人在感兴上节奏上得到鲜颖的刺激与暗示,并且可以拿来同祖国古代诗学昌明时代的佳作参照研究,因之悟出我国旧诗中那一部分是芜曼(蔓——引者)的,可以铲除避去,那一部分是菁华的,可以培植光大,西方的诗中又有些什么为我国的诗不曾走过的路,值得新诗的开辟。”中国现代新诗发展所需要的元素大都来自译诗,是译诗扶持中国诗歌走上了新路,并为其发展提供了营养,我们很难对“没有诗歌翻译就没有中国新诗创作的兴起”做出肯定或否定的判断,唯一可以肯定的是没有译诗,中国诗歌会像失血的动物一样衰老贫弱。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认为,自由诗、小诗、新格律诗、叙事诗以及十四行诗都受到了翻译诗歌的影响,否则新诗形式便不会如此丰富。
外国诗歌的翻译不仅刺激了中国诗歌的新变,而且为中国新诗创作提供了模式,使在翻译过程中模仿外国诗歌形式进行创作成为一种特殊而常见的现象。外国诗歌的示范作用对刚刚诞生不久的新诗来说尤为重要,作为一种观念而非创作实践的产物,白话新诗在初期必须有一个可资借鉴和模仿的对象,否则就会失去方向和目标,陷入茫然和混乱的创作状态。近代以来,我国知识分子致力于“为中国选择一种优秀的文化以做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从文学上讲,人们翻译外国文学的目的也就是为了给中国文学寻找合适的方向,并且在实际上,翻译文学也成了新文学创作时效法的对象。从胡适借一首译诗来宣布新诗成立的“新纪元”这一事例中,我们可以明确地推断译诗必将成为新诗创作的模仿对象。胡适在新文学运动之初指出:“西洋的文学方法,比我们的文学,实在完备的多,高明得多,不可不取例。……因为西洋文学真有许多可给我们做模范的好处,所以我说,如果我们真要研究文学的方法,不可不赶快翻译西洋的文学名著做我们的模范。”茅盾进一步认为翻译外国文学才可能创造我们自己的新文学:“现在中国研究文学的人,都先想从介绍入手,取夕阳写实自然的往规,做个榜样,然后自己着手创造。”但茅盾并非彻底的民族虚无主义者,他认为翻译文学和中国古代文学在建构新文学的过程中同等重要:“我们相信现在创造中国的新文学时,西洋文学和中国的旧文学都有几分的帮助……我们是想把旧的做研究材料,提出它的特质,和西洋文学的特质结合,另创一种自由的新文学出来。”施蛰存在谈它的做诗经历时说:“还有一个投稿记录是成功的。那是《现代评论》居然给我刊出了两首诗。《照灯照地》,《古翁仲之对话》。其时我刚从牛津大学出版部买到了英译本的《海涅诗选》,它对于我的诗格也起到了作用,这两首诗便是当时的代表作了。在短短的努力于诗的时期中,我也曾起了一点转移。海涅式的诗引起了我的兴趣并不长久,所以我只摹仿了十余首就转移到别的西洋诗方面去了。我吟诵西洋诗的第二阶段是斯宾塞的《催妆诗》及《小艳诗》,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我曾读了《催妆诗》的全部,又曾用Spencerian Stanza的脚韵法做过一首较长的诗,题名《古水》”。这种创作潮流在一定程度上养成了中国新诗对外国诗歌的依赖,当然这种依赖关系也说明了译诗对中国新诗创作的重要性。直到21世纪的今天,人们在谈论初期白话新诗的不足以及百年新诗创作成败时,仍将原因归结为忽视了中国新诗对外国诗歌艺术和精神的充分吸纳,没有考虑到二者的亲密关系。
诗歌翻译还为刚刚诞生的新诗提供了创作资源。很多新诗人正是在不断翻译或阅读外国诗歌(含外国诗歌的翻译文本)的过程中,产生了与外国诗歌精神的共鸣而有了创作冲动。现代诗人怀着强烈的民族情感,不断从国外输入新的诗歌精神和诗歌形式,有的甚至偏激地认为只有外来物才是中国诗歌和其他文学创新的宝贵资源。傅斯年曾在《文学革新申议》中说:“中国今日革君主而定共和,则昔日文学中与君主政体有关系之点,若颂扬铺陈之类,理宜废除。中国今日除闭关而取开放,欧洲文化输入东土,则欧洲文学中优点为中土所无者,理宜采纳。”几乎在整个现代时期,诗人普遍将翻译诗歌视为创作过程中必不可少的重要资源。首先,对于那些诗人兼译者而言,他们的创作风格无不打上自己所译诗歌的印记,胡适、郭沫若、闻一多和徐志摩等,他们的作品十分明显地证明了他们的创作资源更多来自国外;其次,对于那些直接阅读翻译诗歌的诗人来说,他们中的很多人也是因为有了阅读译诗的经验才走上了诗歌创作的道路。比如当年围着炉火读郑振铎所译《飞鸟集》的冰心,没有译诗在形式和精神上的刺激和启迪,她的创作就难以发生。其实,把翻译视为资源利用到具体的写作中不只局限于诗歌这类文体,它是中国现代文学创作的普遍做法,例如鲁迅在谈他是如何开始写小说的文章中,就明确阐明外国文学作品和翻译文学是他的创作资源:“回国以后,就办学校,再没有看小说的工夫了,这样的有五六年。为什么又开手了呢?——这也已经写在《呐喊》的序文里,不必说了。但我的来做小说,也并非自以为有做小说的才能,只因为那时是住在北京的会馆里的,要做论文罢,没有参考书,要翻译罢,没有底本,就只好作一点小说模样的东西塞责,这就是《狂人日记》。大约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此外的准备,一点也没有。”
根据以上论述我们不难发现,由于翻译诗歌的影响,中国新诗创作才获得了艺术和精神上的资源,并逐渐积淀起自身的诗学传统,建构起有别于传统和西方的民族性艺术经验,最后得以在其百年的历史中闪耀着无数动人的华章。
三、诗歌翻译与创作的互动关系
诗歌翻译在促进中国新诗创作的同时,自身也得到了发展和提高。中国新诗在翻译诗歌的声援下确立了文坛地位,在对译诗进行模仿的基础上实现了自身的进步和发展;初期的诗歌翻译无论在形式上还是精神上都显得有些蹩脚,但随着中国新诗的进步,译诗文体在艺术上也有了很大的改观。因此,译诗与中国新诗之间无形中构成了一种互动关系。
从翻译诗歌与中国新诗发展的历史过程来看,二者之间呈现出相互需求和促进的关系。从诗歌翻译的角度来讲,近代很多译者采用古体诗去翻译外国诗歌时,尤其是面对西方新词汇的时候,感到形式和语言对他们的翻译形成了巨大的障碍。因此,晚清时期很多诗人体认到要翻译好外国诗歌,既有的古典诗歌形式显然难以如愿,于是一种不同于古诗的诗体形式呼之欲出,这为新诗的发生迎来了长足的空间。近代文学家吴汝纶在给胡适的信中认为,翻译外国诗歌使得创造新的诗体更显必要:“欧美文字与我国绝殊;译之,似宜别创体制,如六朝人之译佛书,其体全是特创;今不单不宜袭中文,并不宜袭用佛书。窃谓以执事雄笔,必克自我作古。又妄意彼书固自有体制,或易其辞而扔其体,似亦可也。不通西文,不敢意定。独中国诸书无可效仿耳。”古诗体在翻译诗歌中的局限性日渐暴露,在中外交流日渐频繁的语境下,中国诗歌势必需要改变自己的形式,方能适应诗歌翻译形势的发展,让译者不再拘泥于形式和语言的困扰,尽可能充分地再现原作的情感和艺术。以严复翻译西书时流露出的语言差异为鉴,吴汝纶总结出在翻译外国书籍时应采用新的体裁:“指事若自为一书,则可纵意驰骋。若以译赫氏之书为名,则篇中所引古书古事,皆宜以元书所称西方者为当,似不必改用中国人语,以中事中人固非赫氏所及知。法宜如晋宋名流所译佛书,与中儒著述显分体裁,似为入式。”连桐城派古文家吴汝纶都主张在翻译外国文学时,不宜采用严谨刻板的古体,可见翻译外国诗歌时所孕育的有别于古诗形式的诗歌新体势必产生。然而,翻译外国诗歌不仅成为中国新诗的催生力量,而且还为中国新诗提供了丰富的形式资源,使自由诗、小诗、现代格律诗、长诗、叙事诗和十四行诗等等在新诗坛上竞相开放,生机勃勃。另一方面,中国近代诗歌革命的失败表明中国诗歌的发展也需要一种不同于传统的诗体,中国诗歌发展对文体的需求有利于促进诗歌翻译活动的开展,因为白话新诗在语言和形式上与古体诗相比,是翻译外国诗歌最适合的文体,中国新诗在发展的过程中改善了诸多不足,并拥有丰富的文体形式。自此以后,译者可以自由地选择合理的诗歌形式去翻译外国诗歌,减少了翻译过程中所受到的束缚,反过来又促进了诗歌翻译的发展。
从诗歌文体的角度来看,译诗与新诗依然具有相互促动的关系。新诗在中国文化土壤上诞生,但却吮吸着外国诗歌的营养成长,而作为外国诗歌与中国新诗发生联系的中介物,外国诗歌的翻译体会直接影响中国新诗的形式。翻译诗歌活动自身的诸多特点决定了译诗在形式上采用非格律化的白话自由体更容易达到翻译的效果,因此,很多人都采用自由体翻译外国诗歌。五四以后,自由体翻译成了诗歌翻译的一种风尚,这种风尚又影响了同期的诗歌创作,白话自由体逐渐成为中国新诗的主要形式。但这并非是一种单向度的影响,翻译诗歌在给中国新诗引入外国诗歌形式或提供“翻译体”的形式资源之际,其自身当然会受到中国现代新诗形式及相关理论倡导的束缚。比如五四时期,由于打破传统诗歌格律和对自由精神的诉求,中国新诗创作者采取了与传统形式彻底决绝的态度,热情地拥抱自由形式的诗歌。受此种时代风尚的影响,译者主要采用自由诗的形式去翻译外国各种体式的诗歌,甚至包括格律体诗歌。拿新诗倡导者胡适的诗歌翻译来讲,在“作诗如作文”的时代浪潮中,他在翻译外国诗歌的时候,一方面适当保留了原诗的形式艺术,另一方面在诗句排列和韵律上还是更加“自由化”,其所译《老洛伯》即是明例。以现代中国诗坛的实际情况来看,自由体形式的翻译与自由体形式的创作相辅相成,翻译外国诗歌时采用的自由形式和新诗自由诗创作几乎同时出现,二者相互影响制约而又相互支援促动:没有外国诗歌形式之“翻译体”的出现就没有现代新诗文体的创新;但同样不可忽视的是,翻译诗歌能够从马君武、苏曼殊等人的“古体”演变为五四以后的自由体或新格律体,没有新诗形式的变化和发展,同样就没有译诗形式的创新。
翻译诗歌与中国新诗创作发展之间的相生相伴关系持续了很长时间,直到今天我们的新诗创作依然无法摆脱翻译的影响,而在汉语文化语境下的翻译又不可能抛弃中国新诗形式而独立存在。有学者分析认为,到了20世纪3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新诗创作的逐渐成熟,“英诗汉译也逐渐摆脱了与中国文学伴生关系甚密的局面而更加相对独立地发展。”此中深意饶有趣味:首先,20世纪30年代以前的新诗,根本没有摆脱翻译诗歌的影响,也没有进入独立的创作轨道;其次, 20世纪30年代之前的翻译诗歌,很难获得独立的品格,它总是和中国新诗的创作需求糅合一团,无法离开新诗而独立存在。此时,我们脑海里会出现这样一些很有意思的问题:究竟是现代诗人偏爱新诗体而选用其来翻译外国诗歌呢?还是缘于在翻译外国诗歌时不得已采用了新诗体,进而带动了其在中国的兴起呢?这是一个值得严肃思考的问题,在五四时期,采用白话诗体翻译和采用白话诗体创作几乎是对孪生兄弟,他们在中国新诗诗坛上出现的时间也几乎是同时的,因此,应该辩证地回答以上问题,翻译诗歌和新诗之间其实存在着相互促进的关系。晚清以降各地兴起的白话报刊和梁启超等人提出的“诗界革命”拉开了中国诗歌变革的序幕,直至五四新文学取得胜利之后,白话文取代文言文确立了文坛的正宗地位,新诗人纷纷采用白话自由诗形式来创作诗歌;但另一方面,整个现代时期的诗人比如胡适、戴望舒、卞之琳、穆旦等纷纷采用自由诗形式去翻译外国诗歌,创造出自由诗创作的浓厚氛围,助推了中国新诗坛自由诗创作的潮流,维护了新诗革命的合法性,稳定了新诗的文体地位。所以,在中外诗歌交流的过程中,我们一则可以认为,现代时期的译者兼诗人所据有的形式观念或形式自觉意识促使其在翻译国外作品时,更愿意采用时下盛行的自由形式去替代原诗的格律体式;也可以认为,译者采用自由诗形式来翻译外国诗歌,容易给一般读者造成外国诗歌就是自由诗的错觉,故极力效仿翻译体进行创作,导致自由诗创作蓬勃发展并成为新诗的主要形式。对于翻译者,尤其本身是诗人的翻译者而言,他们在翻译外国诗歌的过程中逐渐习得了新的创作艺术和构思方式,对诗歌的审美诉求逐渐发生改变。因此,对这部分诗人来讲,翻译既是文化交流,也是学习模仿,更是一种创作训练,他们在翻译中逐渐完善了自我创作。不过需要提及的是,本文虽立意论述诗歌翻译与中国新诗创作之间的互动关系,但并不表明存在于二者之间的影响与被影响之关系是平衡的,中国新诗创作固然会左右诗歌翻译活动的开展,但比之后者对前者的影响而言,可谓过之而无不及。
① [苏]加切奇拉泽:《文艺翻译与文学交流》,蔡毅、虞杰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7年,第32页。
② 朱自清:《新诗杂话》,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第71~72页。
③ [美]Edward S· Holden:《莪默伽亚谟的新研究》(New Light on Omar Khayyam),成仿吾译,上海:《创造周报》(第34号),1923年12月30日。
④ 成仿吾:《论译诗》,上海:《创造周报》,第18号。成仿吾所说的翻译方法(即表现的翻译方法)主旨如下:“译者用灵敏的感受力与悟性将原诗的生命捉住,再把它用另一种文字表现出来的意思。这种方法几与诗人得着灵感,乘兴吐出新颖的诗,没有多大的差异。这种方法对于能力的要求更多,译者若不是与原诗的作者同样伟大的诗人,便不能得着良好的结果。所以译诗的时候,译者须没入诗人的对象中,使诗人成为自己,自己成为诗人,然后把在自己胸中沸腾着的情感,用全部的热力与纯真吐出。”
⑤ 廖七一:《译者意图与文本功能的转换——以胡适译诗为例》,洛阳:《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
⑥ 郭沫若:《波斯诗人莪默伽亚谟的100首诗·序》,上海:《创造季刊》(第1卷第3号),1923年7月1日。
⑦ [英]西奥·赫尔曼:《翻译的再现》,《翻译的理论建构与文化透视》,谢天振编,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3页。
⑧ 谢天振:《译介学》,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239页。
⑨ 谢谦:《庞德:中国诗的“发明者”》,北京:《读书》,2001年第10期。
⑩ 卞之琳:《人与诗》,上海:三联书店,1984年,第19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