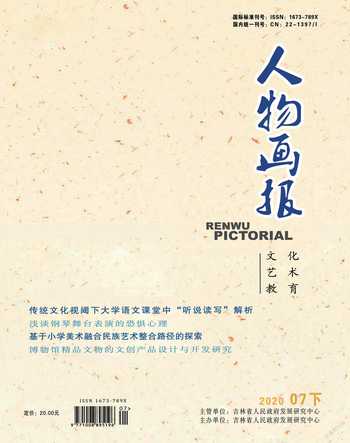孙多慈的《自画像》心理
王嘉慧
摘 要:孙多慈是我国20世纪初的女性艺术家。她的绘画大多表现人物肖像。本文试图从社会心理的角度出发,立足于女性视角,挖掘孙多慈《自画像》中画家的自我认识,并结合与他画像(徐悲鸿《孙多慈像》)之间的对比,分析孙多慈两个相互矛盾的“自我”。并结合人物的成长环境及社会局限,试图作出比传统图像学分析更为深入的阐释。
关键词:孙多慈;自画像;自我身份;心理反抗;封建局限
孙多慈(1912-1975年),原名孙韵君,安徽寿县人,自幼酷爱丹青,1930年9月成为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旁听生,师从徐悲鸿学习素描,1935年以高居榜首的成绩毕业,中华书局曾为其出版《孙多慈描集》。1937年起,随父母辗转长沙、桂林至浙江丽水,在浙江省立临时中学、美术专科学校任教。1949年前往台湾,于台湾省立师范学院任教。
封建时代,女性艺术家被禁止进入正规艺术界空间,因此,潘玉良、孙多慈、蔡威廉等“民国新女性”的画作得不到足够的重视。封建书香门第出身的孙多慈虽然接受了较为开放的教育,但不能不受根深蒂固的家庭影响。笔者认为:孙多慈作为当时女性创作的典型,始终无法摆脱家庭的封建性及自我的情感束缚,一生都在男性权威的震慑下。
一、自我身份的矛盾
在孙多慈的《自画像》(油画)中,其穿着打扮都还是学生模样,军绿色的棉袄和齐耳的短发显然是当时典型的装束,粉红色的围巾为画面做了点缀,引人注目的是孙多慈的双眼:坚定且智慧,画面呈现出典雅庄严的氛围。当时的民国女性以受教育为荣,认为知识是“新女性”的标志,孙多慈正是按照理想中的自我对艺术形象进行塑造——画中装束显然是其引以为傲的身份象征。画中的另一个身份信息标志是其手中的画笔和调色板,可是不难发现,整幅画面并不具绘画场景的真实性,其中不见画板画架,穿着干净的孙多慈用坚定的眼神望向观者,实则是有意的摆拍。笔者认为这是对早期受教育的女性及油画身份的强调——接受新式教育的孙多慈向往独立的知识女性,这种身份认知对应的自我形象在这幅绘画中被有意识的塑造了出来。
《孙多慈像》是徐悲鸿1934年为孙多慈所作油画的素描稿,其非常珍视此画。根据该画收藏者康寿山先生的撰文,当时两人情投意合。画中的孙多慈身着当时流行的学生装,手臂互相交叉,整体姿态放松,眼神温柔,帽上点缀的串珠显出其审美追求。显然,在绘者眼中,孙多慈美丽优雅,柔和顺从。
上文两幅画作描绘对象同为一人,但多有不同:自画像上庄严知性的面孔,在徐悲鸿画笔下则似笑非笑,温婉可亲,与此形成对应的是,拿着画笔的手势也表现出了坚定有力和柔软放松的明显区别。通过对孙多慈遗存照片的整理得知,徐悲鸿画作更加符合孙多慈的真实面貌,据此,笔者认为:孙多慈的自画像其实是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了美化,经这种美化,人物形象更加立体动人,“民国新女性”的身份得到了凸显。
相较徐悲鸿《孙多慈像》中将孙多慈置于普通女性之位进行观察、着意凸显其较传统女性之美的创作行为,孙多慈《自画像》显然强调了自己知识分子和画家身份的独特标签,种种细节透露出新时代民国女青年通过受教育体现自身价值的渴望。透过这两种视角,我们或许可以窥探孙多慈关于“自我”的部分矛盾。
二、对父权制隐含的心理反抗
孙多慈《自画像》中对自我身份的建构所反映出来矛盾的“自我”投射出一个现象:孙多慈对父权制隐含的心理反抗。从现有研究得知,孙多慈成长在一个封建制的家庭环境中,强势的传统“严父”和充分的家庭保护使其缺乏果敢之性,易于产生依赖。参照徐悲鸿和蒋碧薇与廖静文的情感经历,不难看出,徐悲鸿对于顺从宽和的传统女性特质抱有充分的期待,而与独立刚强的女性主义思想常生龃龉,实际上,在孙多慈与徐悲鸿长达十数年的情感纠缠中,处处都可以窥见孙多慈的被动和依从,这或许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归因于其对母亲的情感认同和下意识模仿,同为大家闺秀而长期处于从属地位的母亲角色,和自主选择的、与“严父”形象不无相似的恋爱对象,无疑支撑了孙多慈对于传统女性审美的进一步认可,并确实压抑了其对“新女性”角色的自由追逐。
女儿早期因父亲所形成的品性在社会化过程中往往会转移到其他的异性身上,孙多慈在与徐悲鸿的感情经历中所表现出的温柔顺从,正是一种权威转向另一种权威的标志,依据郭艾妹《女性主义心理学》,当这两种权威发生冲突并需要做出一个选择的时候,孙多慈必然会选择最初的权威放弃之后代替的对象,这也解释了孙多慈之后放弃徐悲鸿的心理态势——当权威需要权衡,为了再次得到最初权威的认同,女性会重新将温柔顺从返还,重新得到了父爱。
在儿童成长到一定程度、走向社会的时候,会发现父亲更具有权威,儿童会因此将父亲勇敢、坚毅、严肃的一面吸收进自己的心理态势中,隐秘地存在于“自我”当中,这种潜在的“自我”始终在压抑着真实的“自我”,随着权威的增加,自身的压抑也会随之增大。这直接作用于女性特质的形成——温柔顺从的品性在压抑之下逐渐被纳入“自我”,最终成为建立在父性权威上的“超我”。笔者认为,孙多慈的自画像体现出了这种自身的心理对抗。
压抑与反抗是相辅相成的。在民国早期,孙多慈属于较早接受新思想的女性,痕迹虽然隐微,却常有对父权文化的反抗表现。《自画像》中的女性形象,充分反映了当时的孙多慈对独立、进步颇有认同,并主动通过画笔对理想“自我”进行大胆的表达。
三、时代的局限性
事实上,从整个社会环境来看,孙多慈无疑是其所处时代的女性创作群体的命运的典型——虽然出生于名门,已经能够接受良好的教育,但由于社会和家庭封建性的客观存在,无论于内还是于外,孙多慈艺术事业的发展仍然受到不小的束缚。
论及这种现象背后的原因,首先,民国时期的女性仍然局限于家庭,且上下阶层分化明显:上流社会的女性局限在娱乐功能上,麻将是女性增强“友谊”的最佳途径,下层阶级的女性被束缚在家务劳动和照顾孩子上,“三从四德”和“男尊女卑”等传统文化观念仍然束缚着女性的思维;其次,除指定的活动外女性基本无法受到教育,没有钱买材料,也沒有类似画室的个人空间,更谈不上学习绘画的氛围。此外,许多禁忌和社会对谦卑、美德、服务的期待要对女性被排除在学院派绘画阶层、文艺俱乐部和知识分子圈之外负责。除了写日记、写信等主要私人性质的活动外,这些禁忌使女性丧失独立创造和知识发展的机会。而且女性在被允许从事工作的内容和形式上会受到严格的社会约束。
此外,画幅的大小及题材的选择也有所限制:女性艺术家从事的项目不能大过小幅的油画或水彩画,委托制作壁画、雕刻及教堂版画等较大的画作更不会让女性参与;那些不能够证明女性谦卑、勤劳和宁静美德的肖像创作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阻止。尽管一些女性已经开始能够以巧妙的方式躲避或者颠覆这类规范和污名,但是大多数女性艺术家还是会受到社会的束缚,画作的表现依然是按照男性能够接受的姿态和职业来描绘,比如孙多慈的《灯下缝补》、《抱婴图》等。
家庭在相当程度上造成了孙多慈的矛盾性,固有的封建性又限制了其发展,但家庭的矛盾性事实上透露了一种由时代造就的必然性。民国时期,不只有孙多慈呈现出这样的自我身份意识和对家庭及父权制的反抗,蔡威廉、潘玉良、关紫兰也有类似的经历。
四、结语
当今学术界,女性艺术家绘画的品评标准仍然在相当程度上受到男性话语的影响,男性艺术家对女性艺术作品的分析和品评,还停留在一个自认为公正权威的范畴。这种艺术史的书写不仅没有将女性艺术家绘画的成就完全呈现,甚至还巩固了男性艺术家在绘画事业的绝对地位。因此,本文主要立足于女性视角,挖掘孙多慈《自画像》中画家的自我认识,并结合与他画像(徐悲鸿《孙多慈像》)之间的对比,分析孙多慈两个相互矛盾的“自我”。在本文中,笔者适当结合其个人情感经历,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尝试分析孙多慈对父权制的反抗,以此为窗口,对整个社会所处的封建环境进行观察。本文未采用学术界图像学传统方式分析画作的艺术特征,而主要从社会心理的角度凝视孙多慈《自画像》,关注这一具有典型性经历的女性作者形象,以期为之后研究民国女性画作及心理态势的学者提供思路上的参考。
参考文献:
[1]张晨,艺为人生 1928-1949年国立中央大学美术学专业学生文献集 上[M],2016.
[2]陈正荣,金陵佳人,2018.
[3]编辑委员会编,安徽历史名人词典 下[M],2008.
[4]郭艾妹,女性主义心理学,[M],2011.
[5]奥斯汀·哈林顿,艺术与社会理論 美学中的社会学论争,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3.
[6]李素芬,民国女性自画像研究,2015.4.
[7]谭潇潇,1912-1937年中国油画中的女性肖像题材研究,20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