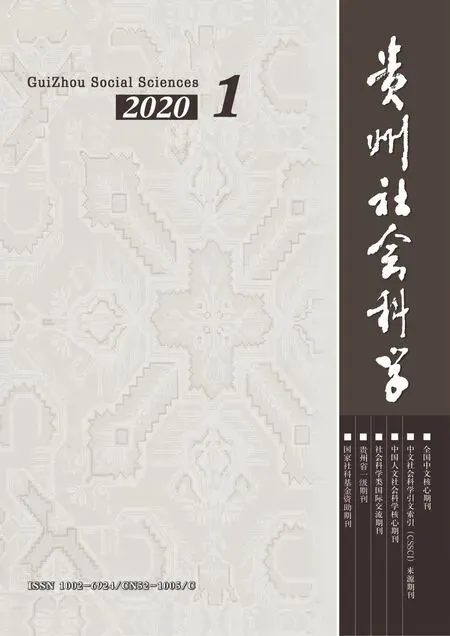政体学说与思想兴衰
程志敏 张祺乐
(1.海南大学,海南 海口 570228;2.西南政法大学,重庆 401120)
人类文明经过几千年的发展,一切都似乎进步得非常完善,很多问题好像都得到了完满的解决,于是,我们就很心满意足地把这些已经过时的问题束之高阁。但这种“心满意足”本质上不过是肤浅的自以为是,因为那些问题并没有真正得到解决,有些恒提恒新的问题也不可能得到一劳永逸的解决,更何况,今人奢谈的所谓“进步”,本身就值得怀疑——从卢梭的论文到施特劳斯的立场,无不表明我们在很多方面既然并没有什么进步,那就必须“回头”。[1]297这种回归未必能够让我们看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未必能够帮助我们找到自己的定位从而重新找到前进的方向,未必能够解决现实中急迫而困难的问题,如果我们仅带着“批判”、“怀疑”、“轻视”甚至“鄙薄”态度来看待古人,则更不可能有所斩获,但即便如此,“回头”也是必要的——正如柏拉图《王制》卷七的洞穴喻所示,“回头”乃是文明化的第一步(514b,515c),是走出洞穴、走向阳光的起点。“回头”未必有实质的意义,而不回头,则可能在盲目中快速奔向悬崖,并在不知不觉中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一
“政体”就是这样一个需要我们重新审视的被存入历史档案的重要卷宗。古人,尤其古希腊人,深入探讨过政体问题,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每一个重要的古希腊哲人(更不用说每一个伟大的古希腊政治哲学家)都对政体问题发表过自己的看法。毫无疑问,“政体”在古典政治哲学中占据着非常高的地位,但“政体”在今天却早已不是一个问题,当今最重要的政治哲学著作鲜有论及政体者。西方自《联邦党人文集》之后,“政体”问题在两百多年的思考中似乎完全消失了。究其原因,或可有三。
一、意识形态。在现代人看来,“自由”是生活最重要的目标,“民主制”才是最好的政体,其余皆不足论,无须再费力讨论,但殊不知民主制本身无疑存在不小的问题,古往今来反对民主制度的浪潮不绝如缕;此外,民主制与其他政体的区别主要在哪里,民主还有哪些亚种,各自的优劣如何等等,民主制的自由原则如何与寡头制的财富原则和君主制的德性原则相协调,都还需要研究,但“由于我们有了民主制是最好的政制这一理论预设,在描述历史的时候,就看不到这样一些问题”(刘小枫语)。民主、自由和平等等等思想虽是人类追求的珍宝,但如果被口号化、技术化和利益化,就变成飘摇无根的意识形态。现代思想种种灾难深重的危机警示我们:我们在空虚的现代意识形态中陷溺得太深了,无法体会到自己其实已经远离正道,远离真正的民主、自由和平等。这样一来,意识形态化的民主观念就变成了现代人尤其中国人的“骨刺”(张志扬语)。我们并不反对民主,恰恰相反,民主是我们赞成或反对它的基础,[2]27但我们不赞成民主的“主义化”,因为任何思想观念的意识形态化既妨碍我们真正领会其本质,更会由此把我们引入歧途。现代人自以为有更重要的问题要对付,殊不知却是“对越来越琐屑的鸡毛蒜皮知道得越来越多”(know more and more about less and less)。[1]78但当今在政治意识形态上的大一统以及政治实践上相对的稳定性,并不能掩盖我们在其中的迷惘、无知以及自我放任的不负责任——这恰恰就是现代精神萎弱的表现,也是现代各种危机的根源之一。
二、学理。在现代观念中,“政体”的内涵变得十分狭窄,因而往往不太受重视。但在古典思想里,“政体”是一个非常广泛而重要的概念,它远远不是如当今理论所谓“政府的组织结构和管理形式”,也不仅仅是“谁统治、怎么统治”的问题。与两千年(尤其是最近几个世纪)持续的技术化进程高度一致的是,“政体”内涵大幅度缩水,至今变成了一个“技术语汇”,被划入形而下的器物领域,其原有的那种对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并在各个方面直接指导社会生活的思想旨趣、理论关怀和宏远目标,被标准化、规范化和科学化了。这些看似进步的标准和规范实际上只保留了原来的外在形式,至多留下了一些理论化的方法和技术上的操作程序而已——由此不难理解为什么“政体”在现代政治哲学中不再受人青睐,也能够看出“政体”内涵不断缩小竟而变成技术操作的原因。
三、历史。现代人从完全不同的角度阐释政体观念的衰变原因,在他们看来,就算古代思想不乏真知灼见,但时过境迁,传统学术资源过时了;历史在进步,原有理论体系已不足以解释现在的经验。政治从业者高调宣布:“政治学和其他大多数学科一样,已经大有进步。各种原理的效果,现在可以了解得很清楚,但对古人(ancients)来说,不是完全不了解,就是一知半解”,[3]40这句判词前一半或许能够成立,但能否推出后半句,还有待讨论。专业学者亦明确判断:“用古老的亚里士多德的三分法——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不再可能把握现代的民主制度”。[4]12果如其然乎?古希腊城邦规模不大,人们生活在面对面的熟人社会中,但这种小国寡民的历史经验对我们毫无用处?[3]66现代民主制与古代民主制区别虽不小,难道这两种都冠以相同名号“民主”的政制制度之间没有相同、相似乃至相近之处吗?更何况,“我们没有资格说古典的观点已经被驳倒”,[2]28那么,尚未被驳倒的古典思想竟无可取材?
意识形态、学理和历史流变等因素相互交织并相互促进,互为因果:学理的萎缩既受意识形态的影响,也反过来为意识形态的膨胀添油加薪,在历史的演进中不断扭曲,层层叠加的多重遮蔽让后人再也见不到古典思想的真容。德性、幸福、理想、高贵等等之类的古典追求,连同“政体”或politeia一起,都被掩埋在思想地震后的历史废墟中。我们这项研究,试图唤起人们对那些重要思想维度的热情,至少要像一位年轻学者在其博士论文结尾处所写的那样认识到:“现代优越于古代,现代混合政体思想优越于古代混合政体思想,在某种程度上这是现代人的一个迷思。多数现代人陷入这种迷思而不可自拔,他们要么对古代不屑一顾,要么回顾一下以印证现代的优越。其实,古代的思想就像是远处存在的一个光源,它静静地观照着现代人的生活,并时刻等待着现代人去寻找失落了的光芒。”[5]267中国现在尤其需要这样的光源。
二
与西方自古以来大部分时间政体讨论都热闹无比而最近冷清寂寞的情形不同,中国数千年历史中绝少关于政体的探讨,但最近一个多世纪却比西方政体问题最风行的时代都更密集和广泛,而且“优良政制”目前仍然是急迫而棘手的问题。其紧迫性不言自明,其棘手的地方在于中国本土很少政体辩论的资源,即便数千年间时常挑起的“儒法之争”本身不过是君主制和贵族制内部关于治理方法的交锋,不是根本性的政体考量——汉宣帝所谓“霸王道杂之”与西方的混合制表面不似,实更不同。
我们必须借助西方的话语体系和政治实践来重新构建新的政治文明,以新法应对数千年未有之变,自保于世界列强之林,延续古老的命脉。康有为时代的国祚存亡问题在今天虽已不再那么尖锐,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家的生存问题就已得到彻底解决。剥开“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的意识形态外壳,我们会发现国际政治的基本内核:国家之间无公义。就算基本的生死存亡不是我们目前的首要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建国大业已经彻底完成,当前紧锣密鼓的深度改革,尤其政治文明的大力建设,足以表明“康有为问题”并未过时。
为什么中国历史上几乎没有政体问题?在梁启超看来,“中国自古及今,惟有一政体,故政体分类之说,中国人脑识中未尝有也”,[6]3-771这种独一无二的政体就是天下万国都不如本朝的“君主专制”,正是这种政体让中国濡滞不进,康有为在此几年前就已说过:“吾国行专制政体,一君与大臣数人共治其国,国安得不弱?”(1)康有为:《请定立宪开国会折》(1898年8月),见汤志均编:《康有为政论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338页。王绍光认为最早在中国引入“政体”概念的是梁启超1902年的《中国专制制度进化史论》,恐有不妥(《政体与政道——中西政治分析异同》,见《理想政治秩序》,北京:三联书店,2012年,第76页)。梁启超的“专制”说直接来自于孟德斯鸠,但孟德斯鸠对中国的大量讨论却以道听途说为基础,恐怕连一知半解都谈不上,故而显得“恶毒”。[7]135但我们如果换一个角度看,孟德斯鸠无意之中发现了中国政体如此成功的一些因素。被钱锺书讥讽为“老师巨子”的黑格尔对中国以及东方专制主义的看法亦复如是。(2)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19页;《法哲学原理》,范扬、张其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263,279页等。较为集中的讨论见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徐式谷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学术界近年来深入讨论了“专制”、“专政”和“独裁”等概念,逐渐形成共识:秦汉以来的制度不是“封建”,几千年的君主制也不是“专制”。
无论我们把中国漫长而又稳定的政治局面理解为“专制”,还是把它解释成君主制,甚至说它是君主与贵族(士大夫)的共和制或混合制,都不能否认这样的事实:上有天道隆命,下有人伦成范,前有祖法仪轨,后有千秋令名,内有圣贤教诲,外有清议谏诤,“六合”咸备,中国人的确没有必要为政体问题浪费心智。先圣俯仰取譬之时,早就体会到天道常理,我们唯一需要做的,无非“承天意以从事”而已,(3)见班固:《汉书》“董仲舒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502页。另参董仲舒:《春秋繁露·玉英》,见苏舆:《春秋繁露义证》,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70页。既然先圣已然“得道”,后人“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就不是懒惰无能、固步自封,而是依循正道。
柏拉图《法义》开篇也说礼法神授,西塞罗亦曰:“永生的天神把灵魂输入人的肉体,是为了让人能料理这块大地,并要人们凝神体察上天的秩序(caelestium ordinem),在生活中恒常模仿。”[8]101《新约圣经》载:“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罗马书》13:1),因而自基督教掌握政治以来,西方世界同样不存在政体问题——中世纪后期教权与皇权的争论不在此列,即便世俗一方高扬“君主制”,但它与基督教的政体没有任何实质区别,因为后者也是一种君主制。无论如何,中国人循天宗祖,没有“进步”,本来也不需要进步。
蒙森对古代腓尼基人的部分评价也许可以用来比附同属“东方”的中国,他说:腓尼基人“爱乡心切,总以其狭窄的本土为归宿”,他们的宗教概念粗糙而简陋,他们利用了古巴比伦的文明,“人类最初追寻星宿的轨道,大概就在这里;他们最初分别语言的声音而形之于文字,也是在这里;他们开始对时间、空间,以及在自然界发生作用的力量进行思考;天文学、纪年学、字库和度量衡的最古遗迹莫不指向此一地区”,他们“缺乏建国的本能,以及争取自治自由权的独创思想”,“争斗如果可以避免,他们总竭力妥协从事”,但这并不是懦弱的结果,也不是缺乏坚韧性和独特的民族性,实际上他们抵抗外族入侵所表现出来的顽强让人惊讶,“有时似超乎人性,有时似不如人性”,归根结底,“这是缺乏政治意识的结果;尽管他们有极深沉的种族观念,极笃实的依恋祖城的心肠,但这缺点却表示腓尼基人最独特的本性。他们不以自由为可爱,不以霸权为所愿:《士师记》中说,‘他们像西顿人那样安静地生活着,喜悦而无忧,拥有财货’”。[9]3-5但中国人从来不重商崇富,更不利欲熏心,更谈不上狡黠欺骗。[7]327-328其实,“自由”和“霸权”并不如现代人所想像的那样好,而安宁喜悦的生活即便没有自由平等,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好。也许,不需要政治法律意识的时代,才有真正的幸福(比较《道德经》57章与希罗多德《原史》1.31-33)。
三
如果不是因为海禁大开,“大地忽通”,事实证明曾经十分优秀的中国传统政治体制可能还会继续存在很多年,即如康南海所谓:“若使地球未辟,泰西不来,虽后此千年率由不变可也。”[10]151但这毕竟只是“若使”,历史不接受假设。自古一统的中国现在即便没有列强环伺,也再难闭门自娱,安享舒缓雅致的生活,中国被迫全面转轨。但被动接受,凌辱不堪,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何如主动改制更化,符采天人之策,以效汉武故事?
自1908年清帝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到1912年新政府通过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再到1946年较为成熟的《中华民国宪法》,中国人开始主动改变两千多年的祖宗成法,寻求富强之道,迈出了千里之行的跬步,收获的当然不仅仅是跬誉。究其原因,除了历史的教训、时势的引领和民心的向往之外,一大批饱读诗书、熟谙经义也了解国情的学子走出国门,放眼世界,博采众长,古今中西皆通,也是我们渐始摆脱中古走向成功的重要因素,起草《中华民国宪法》的张君劢(1887-1969)堪称个中翘楚——我们没有理由也没有必要盯着他们的所谓“历史局限性”不放,这种说法本身就殊为可笑。
竞今疏古和崇洋媚外不是“建国时代的新政治哲学”所需要的“新心理态度”,而厚古薄今和夜郎自大无疑也不是建设性的姿态。融贯中西,会通古今,回首百年,是为了现在。那么,现在究竟是什么样的状况,需要我们做什么以及怎么做?什么是优良政体?时贤纷纷撰文立说,拟从传统思想中开出现代政法局面,找到“升平世”所需的优良政体,其心志之高尚、精神之高洁、论说之高明,让人感佩。但反对者斥其为遗老遗少心态,囿于自家珍宝,掉入井底,虽有发明,难成正果。传统思想如何能够与西方现代文明接隼,这本身已经是一个大难题(百多年数代仁人志士的艰苦摸索以及数以亿万计的生命代价本身已足可说明全盘西化和全盘中化都不可取),至于说儒家学说能够生产出宪政文化来,则更似风马牛。
当前浸浸然已成显学的儒家宪政主义内部的学理冲突和“人格分裂”在康有为身上早已体现得淋漓尽致:他一方面承认“欧美之新法,固中国所未有,人士未习”,[10]352另一方面又认为西洋三权分立与共和制度“暗合经义之精,非能为创新之治也。”[10]151他一边呼吁引入泰西之法,一边又认为我国古代经义中本来就有这些东西,“其在吾国之义,则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故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是故黄帝清问下民,则有合宫;尧舜询于蒭荛,则有总章;盘庚命众至庭,《周礼》询国危疑,《洪范》称谋及卿士,谋及庶人;孟子称大夫皆曰,国人皆曰,盖皆为国会之前型,而分上下议院之意焉。春秋改制,即立宪法,后王奉之,以至于今。盖吾国君民,久皆在法治之中,惜无国会以维持之耳。今各国所行,实得吾先圣之经义,故以致强;吾有经义,存空文而不行,故以致弱。然此实治国之大经,为政之公理,不可易矣。”[10]338
康子树立孔教,绍述往圣绝学,延纳新世明牖,扞保门庭宗旨,他认为孔子之道“若其广张万法,不持乎一德,不限乎一国,不成乎一世,盖浃乎天人矣”,[10]468自是不难理解,但要说西洋政教无出于孔教普遍真理,甚至说外国之所以强大,正因“得吾先圣之经义”,实在牵强,且不说自以为是,但彼时的这种护教心理可能会妨碍今天的重新思考。包括康有为在内的整整几代人一直夹杂在救亡图存、开启民智、维护本土尊严、学习西方异质文明的种种困境之中,在完全不同的价值取向上摇摆犹豫,在不断涌入的西洋知识流派面前眼花缭乱人云亦云,在患得患失之间纠缠不清,不知所措,难以理出头绪来,至今依然。
四
儒学不乏精美的政治设计,但恐怕已不能照搬用于当世:即便“政治儒学”之说能够成立,也不能说明那就是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政治。儒家曾经十分管用的政治理念和具体措施,虽不无借鉴意义,却无论如何不再鲜活有力竟而可以简单“克隆”——康有为在现代文明危机开始时就已高瞻远瞩地指出:“夫治国之有法,犹治病之有方也,病变则方亦变。若病既变而仍用旧方,可以增疾。时既变而仍用旧法,可以危国”,[10]58又曰:“若引旧法以治近世,是执旧方以医变症,药既不对,病必加危”。[10]151
国学固有其妙,却主要不在政体上,否则,国事危矣。宪章文武与师法后王,本来就不矛盾,故孔子法后王而为圣师。康有为清醒地指出“不穷经义而酌古今,考势变而通中外,是刻舟求剑之愚,非阖辟乾坤之治也。”[10]149中西经义当然要穷,古今之变必须斟酌,然则何以穷究考辨?康子曰:“凡强敌之长技,必通晓而摹仿之,凡万国之美法,必采择而变行之”,[10]218师夷长技未必以制夷,却足可自强。
张君劢早年即已认识到,中国与西方的政法思想有着根本的区别,本土文明当然有极为重要的价值,但并不能成为未来国家建设的直接依据:
中国近来提出东方文化说者日盛,即吾辈亦以为东方文化自有其价值,不可忽视也。然但就政治就国家之理论言之,则古人之言,绝少可以为新国家建设之凭藉者,此国人所当确认者也,惟其然也,除以西方柏拉图以来之国家论,大昌明于国中外,无他法矣。[11]240
国人痛感时局,积极引入西学以求自强,渐而至于“全盘西化”之极端,为了抵抗这种买办文化,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一帮并不守旧的新派学人大力弘扬东方文化尤其中国传统思想,开启了“文化保守主义”的几代香火。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现代新儒家第一代宗师之一的张君劢却清醒地认识到,本土资源的价值自不待言,却不体现在国家政治方面。换言之,即便昌明西方自柏拉图以来的国家政体学说,也并不就是在否认传统文化的价值。
张君劢晚年在《中国现代化与儒家思想复兴》的演讲中提出了与上述洞见不同的看法,认为复兴儒学乃是中国现代化的途径,因为他发现欧洲现代思想建立在希腊哲学的基础上,中国同样可以利用自己旧有的基础。他的思考不是纯粹的学术探究或“思想的回忆”,而是要找出“中国思想复兴的方法”,最终得出了与早年不同的结论:“中国的土地是固厚而广阔的,足供建立新思想之用。……现代化的程序应从内在的思想着手,而不是从外在开始。”[11]500我们认为,从内在的思想方面着手现代化的建设,用儒家的学说为未来的哲学奠定基础,或者以复兴儒家思想而“让现代化在更稳固和更坚实的基础上生根”,(4)张君劢:《张君劢集》,第503页。张君劢这篇演讲一开始就说得很清楚,儒家思想与现代化之间本来就是矛盾和不相容的,参同一著作,第488页。均无不可,但这个层面的思考会给人错觉,以为思想(哲学)的复兴能够解决一切问题,仿佛重回正统儒家思想,宪政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思想义理和典章制度关系密切,却不能等同,更不能简单推导。
我们完全认同当前的儒学复兴,赞成“创造中国式的政治制度”,也有保留地同意蒋庆先生的如下看法:“中国的现代化必须建立在中国固有文化传统的基础上,不能背离自己的文化传统而丧失自己的民族特性,完全走西方式或者西方化的现代化道路”,(5)蒋庆:《政治儒学——当代儒学的转向、特质与发展》,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第359页,另参第39页。蒋庆的现代化问题意识实际上仍然是西方式的,根本上说,来自于西方政治神学和保守主义,因此,我们对于他的“现代化”理路有所保留。但“超越西方民主”这一正当而美好的愿望与“回归儒家本源”不是一个层面的问题。而且,“要留心的是,当代儒家的代表人物虽仍将‘现代的’一词以某种积极的方式纳入了自己的设计任务,但他们的具体论述事实上已经掏空了历史赋予‘现代政治’的任何实际内容。”[12]59这种“似古实今”的现代化方案与蒋庆自己所批评的以西学解儒学、以宋学压汉学的“儒学虚无主义”本质无二,都是各偏一隅。
蒋庆以“总别互摄”的天地人“三重合法性”,即“民意”、“神圣”和“传统”,来解释政治基础,颇有创意,但就此以为“西方政治由于其文化的偏执性格,在解决合法性问题上往往一重独大,从一个极端偏向另一个极端:即在近代以来是偏向民意合法性一重独大,在中世纪则是偏向神圣合法性一重独大”,[13]68未免失之简略。近代的民主诉求功过兼备,背后未必就没有基督教的神圣合法性为支撑,美国宪法即为明证。蒋庆的错误在于只从形式上看待三重合法性,而没有认识到它们的内在品质的重要性。也就是说,一重独大固然有问题,但即便现代西方的民主制同时具备了那三重合法性,也并不能说明它就没有问题:关键在于什么样的神圣、传统和人民。(6)苏格拉底恰恰因信奉神明而被城邦以“不信神”之罪判处死刑!“自由”、“民主”、“平等”、“传统”、“人民”的古今含义别若天壤,不是简单贴标签就能解决现实问题的。
康有为和张君劢等人在中西古今之间艰难纠结,终归走向“保守”,当代大儒们没能有所突破,甚至比他们走得更远。蒋庆看到了西方中古和近代政治所存在的问题,但没有看到西方中古之前,也就是古希腊罗马在政治问题上尚未“误入歧途”之时的有益探索,这对西方原初思想来说,乃是不公正的。西方古典思想不是解决现代问题的灵丹妙药,但它与中国的经义一样,都来自于遥远的古代,是极为漫长文明的结晶,其中必然有“道”,即如老子所谓:“孔德之容,惟道是从。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阅众甫。吾何以知众甫之状哉!以此”(《道德经》21章)。万物之所由,亦必是当今“另一开端”之始。(7)海德格尔:《哲学论稿(从本有而来)》,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18,20页,以及全书各处。从种种迹象来看,我们今天正处于一个全新文明的开端处,正如海德格尔所指出的,它来自于第一型文明,又与之争辩,并最终完成它。如果没有看到这一点,那么,“站在中国政治文化本为性的基础上吸取西方政治文化的优秀成果来解决当代中国政治文化重建问题”这一美好愿望,只能是自说自话,落不到实处。从这个意义上说,蒋庆违背了儒家“致广大而尽精微”的精神,少了一点“和而不同”的胸怀,陷入了自己所批判的“偏执”之中,总体上是从康有为、梁启超和张君劢那里倒退,回到了只讲大道理而忽略现实问题这一清谈误国的老传统中。
五
以天道性理为基础重建政治法律秩序,超越“心性儒学”或“生命儒学”,走向“政治儒学”,也许是一种进步,但我们不能狭隘地理解“政治”:传统儒学之根本首在心性教化(参《礼记·儒行》),却并非不重视礼法秩序;反过来说,政治儒学一时一刻也离不开心性儒学,而且必须以后者为基础,两者互相成就,不可分离:礼以节性、教以兴德,政以防淫,德以同俗,养以致孝(《礼记·王制》)。所以,不独“外王之学”堪称“政治”,“内圣之道”或礼乐教化本身也是“政治”——儒家经典《大学》“三纲八目”说得明明白白。“内圣”如何开出“外王”,儒门争论了几千年,与其说是理论的剖判,不如说是实践的探求,但无论如何,儒家生而具有的这个“旷世”难题不可断为两截。
“政治”含义本身十分宽泛,(8)施米特认为人们难以找到一种对政治的明晰定义(《政治的概念》,刘宗坤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29页),他提出以敌友的划分作为政治的标准(甚至定义),这个“合乎规范的定义”不是一个“包揽无遗的定义”,也不是一个“描述实质内容的定义”(第138页)。施特劳斯看得很清楚,施米特关于政治的看法不是一种普遍的界定,而是针对政治问题的司空见惯的答案,即自由主义,以去除自由主义为掩盖现实所制造的烟雾,也就是“对流行的文化概念进行彻底批判”(《〈政治的概念〉评注》,王贻译,见迈尔:《隐匿的对话——施米特与施特劳斯》,朱雁冰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年,第194页)。根本上是为了人的“安身立命”,即儒家所谓“藏身”,它不仅仅需要制度建设,还需要仁义教化(《礼记·礼运》)。西语politics[政治]亦同此理,也指人们在城邦(polis)中的存在方式:人们只能生活在“政治”或“城邦”中,因而是一种“政治的动物”,否则非神即兽。(9)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253a。但亚里士多德认为卓越之士作为“人中之神”(1284a),可以超越于政治和法律之外,似乎就接续了乃师柏拉图的“哲人王”观念,尽管对《王制》不乏猛烈批评。政治乃是人类无法逃避的命运,任何取消政治的行为本身就是政治性的。(10)施米特:《政治的概念》,第168,第203页(这里原文的Schicksal,“命运”,中文翻译成“谜”,似误;但第164页和第238页又正确地译成了“命运”,第193页注释18译作“不幸”。英译本作fateful和destiny,见Carl Schmitt. The Concept of the Political. Trans. G. Schwab.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p. 51, 78)。另参施特劳斯《〈政治的概念〉评注》,见迈尔:《隐匿的对话》,第200页。西方古典思想也把伦理教育视为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既是其“政治学”的基础,本身也是广义的“政治学”,《尼各马可伦理学》以“政治学”开始和结束,中间也不乏集中讨论政治学的章节。(11)分别见《尼各马可伦理学》第1卷第2到4章,第10卷第9章,第6卷第7、8章。另参《政治学》第3卷第4章。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除了前人学说的考辨、政体优劣的分梳之外,紧接着以大量论述教育的篇章结尾。考虑到《政治学》的残篇性质,亚里士多德接下来必定还有很大的篇幅专门谈教育问题,实际上《修辞术》和《论诗术》就是《政治学》这一关键主题的延伸讨论。
柏拉图的《王制》正标题讲制度(politeia),即让人在城邦中安身立命的组织形式,副标题则是“论正义”,即如何造就城邦的合格公民。这部经典著作即便在讲最为抽象的形而上学问题的地方,实际上都是在谈教育或天性塑造的问题(514a,540b等)。正如巴克所言,柏拉图并没有把教育设想为存在统治而产生的结果,或是统治的职责之一,而是反过来把统治设想为教育的结果。[14]253因此,政治问题就是教育问题,是产生这种精神的问题:视共同利益高于个人利益。毋庸置疑,柏拉图正是这样来看待政治问题的,因此,政治机制就转换成了教育机制。[15]254
施特劳斯指出,“人通过教育——自由教育——成为绅士。……实际上,绅士是‘热心人(the earnest ones)’,这是由于他们关心最重要的问题,关心那些本身值得严肃对待的事物,关心灵魂和城邦的良好秩序。”[16]10这样的绅士在我国古代叫做“君子”,在古希腊叫做kaloi kagathoi,他们当然不会“独善其身”,还要“兼善天下”(参《孟子·尽心上》),其修身、进德和学业,都是为了致用,即齐家、治国、平天下。
政制与教育关系密切,不可割裂两者并偏私一方,而且教育在政治哲学中地位崇高。如果社会共同体只有冷冰冰的制度,远不足以达成生活的幸福目标,还必须要有合格的公民在执行和完成,甚至设计规章制度的人首先需要的,也是教育。要知道,在《法义》“次优理想国”中,“教育部长”就是“首相”(765e1-2)。有了这些理论铺垫之后,我们再提出这样的观点,即,对于现代中国来说,儒家思想的首要功效在于人伦教化,包括统治者、辅助者和公民的教育,当不至于被人简单地误会。
但儒家的典章制度是否还能支撑起明天的中国,这恐怕已经成为问题,其实康圣人早就讲过:“尝考中国败弱之由,百弊丛积,皆由体制尊隔之故。”[10]219虚文体制,上下隔膜,政令不畅,运转失灵,说明体制本身就有问题,足可致命,康子变法之议,盖由此引出。墨守成规甚至抱残守缺,怎么可能“再立堂构”?康子猛喝“垂危之人,岂堪再误”,[10]152有如科吕班特的洪钟,至今仍隆隆作响,让我们听不进其他聒噪。
六
一个世纪以来,许多人不断追问:我们的问题究竟出在哪里?这个问题恐怕现在还没有答案,但我们已为此准备好了很多材料,一些局部的细节渐渐变得清晰起来,至少知道如何发问,还大体知道解决的方向。就政体而言,我们要探讨的是:时过境迁,风云流转,能否说明“政体冷漠症”(以及现代人普遍存在的“政治冷漠症”)就合理合法?反过来说,“国事蹙破,在危急存亡之间”,[10]53是否就可以病急乱投医而不预先冷静剖析、深入研究和远观取舍?具体而言,小国寡民或熟人社会的经验,能否有以教我?西方的政教文明并不具有普世性,是否就与我们无关,如是,又如何相关?
首先,东西方必然不同,任何简单的比附都不得要领,而以任何一方为参照系的评价,都必然变形失效。以古希腊最具代表性的雅典为例,这个范围极小却影响极大的文明样态有着自身的特殊性:“雅典不仅仅是个面对面的社会,还是一个地中海式的社会。”[17]104它以技术理性和形而上学为基础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不过是地中海区域的民族文化形态的世界性扩张而已(张志扬语)。西方现代性危机的根源可能就在雅典,尼采、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等人已经清楚地指出了这一点。我们在学习西方的时候,要充分认识到地中海不是整个世界,它所发展起来的辉煌文明并不具有普世性。东西方各有特色,崇洋媚外和数典忘祖会让我们的取经之道变得漫无目的。
其次,东西方的不同导致任何单向度的融汇努力终归都是一厢情愿的美梦,而囿于自身的民族主义或“本土视点”以抵抗“全球化”的企图,终究还是落入“全球化”的圈套,反而成了“恶的全球化”的帮凶。作为“全盘西化”对立一极的民粹主义,其本质是西方的精神和物质双重压榨的产物,看似守贞持节,实则投怀送抱:“所谓‘东方主义’,其实就是‘西方定位的东方观点’,它乃是‘古今之争’及其背后的‘诸神之争’的一种怨恨的表现。我们却当作‘时尚主义’跟着学了。”[18]278既然全球化的基础是“智力”、“强力”和“技术”,而西方在这些方面又掌握着绝对的话语权,我们的确需要好好想一想:“如果‘全球化’的今天和未来当真如此、只能如此,请问,‘本土视点’还有多大的能量翻天覆地?”[18]277我们必须站(而不是跪)在地上,但不能埋进土里。
最后,立足自我,兼收并蓄。“漂泊后的还乡之路依然漫长”(张志扬语),如果从检讨各自的长处而非短板开始,不失为一个堂堂正正的选择,用时下的术语来说,因为“返乡之路”终归不是解构性的,而是建设性的。解构的工作自尼采以来,已历一个半世纪,现在该让位于建构了。尽管解构的事情还必须向深处推进,更急迫的任务是要向广度扩展,并让人明白解构的现状、成就和目的,但我们不能等拆解和探析的工作完成之后,再来考虑重建家园的问题。在这个建构性的过程中,任何一方的清理工作都是必要的,都值得尊敬,没有必要厚此薄彼,尽管能够综合融汇两方(甚至多方)文明遗产的非凡大脑更让人期待。(12)大略言之,引入西学精髓和检点本土资源或可同时进行,各凭天资喜好,分头用功,一两个世纪的重新发掘、整理、解读、阐释、引申之后,才有可能谈得上创新,这时,双方才真正有可能会师碰面——目前任何形式的相互掐架都是鸡同鸭讲,根本是不成熟的瞎胡闹。而两个主攻方向内部的争斗,则不是不成熟,而是根本性的品质问题。病态的嫉妒心和门户之见甚至主动挑起窝里斗,实在可叹、可惜复可怜。
因此,归根结底,我们对政体问题的思考不是书斋冥想和学术作业,而是有着现实以及长远的考虑,它本质上是“社会病理学”、“传统毒理学”和“药物动力学”的实验。就目前而言,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
改善一个旧的政体的艰辛程度并不亚于建立一个新的政体,有如补习之艰难并不亚于从头学起一样。因此,一位政治家除了具备以上所说的素质外,还应该有能力帮助现存的政体改正其弊端。……然而,他如果对政体有多少类属茫然无知,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政治学》1289a3-8,颜一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