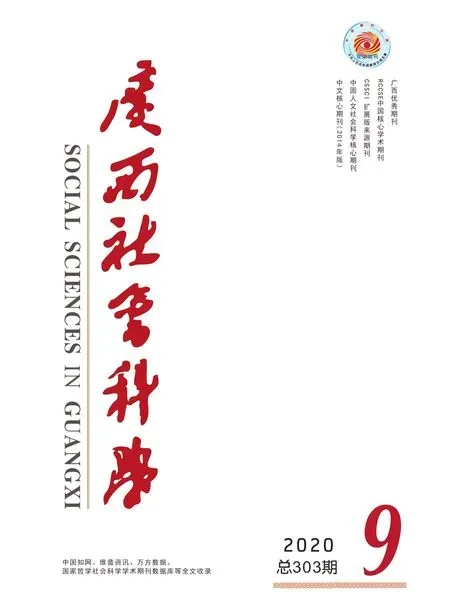媒介传播视野下的当代诗歌书写及其反思
(广西民族大学 文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6)
20世纪80年代以来,当代诗歌的传播方式实现了从手抄诗本、民间刊物等印刷时代产物,到电子公告牌系统、论坛等网络时代的写作,再到微博、微信等自媒体形式的转变。诗歌的传播离不开媒介,媒介作为意义输出与抵达的“中间项”决定了传播的范围、目标及可能。媒介在传播话语的同时,也形成话语。媒介本身呈现出一种价值立场与文化意识,构成了媒介话语的权力。表面上回归大众文化空间的诗歌,实际上却正在失去诗歌本身的思想性和批判性。新媒介技术的普及让诗歌从精英化走向大众化,但诗歌的神圣性与崇高性也在这一过程中被消解。
一、诗歌媒介变迁与大众化趋势
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文革”期间是“地下诗歌”的年代[1],诗人写作的诗歌以手抄本的形式小范围流传于地下。这一时段能够接触到现代诗的读者很少,许多诗歌只是部分诗人之间的交流,没有可以公开出版的条件。直到1978年中国的政治社会发生变化,此前一直处于“地下”的诗人们才崭露头角,如1978年4月复出的艾青写下诗歌《红旗》,同年12月北岛等人创办民间刊物《今天》,青年诗人的诗歌终于有了一个真正的传播平台,程光炜将其看作是新时期当代诗的开端[2]。也有人称《今天》与围绕着它的诗人们为“点燃数十年中国现代诗热浪的第一缕火光”[3],这些诗人创作的诗歌风格与当时诗坛的主流诗歌风格迥异,其语言朦胧、晦涩,引起老诗人臧克家、艾青等的批评,同时被诗坛命名为“朦胧诗”[4]。这些朦胧、晦涩的现代诗相较于“地下诗歌”而言已经广为人知了,但诗歌依然是精英文学的象征,晦涩、朦胧的诗歌传播也必定有限,读者大部分都是知识人。民间办刊这种形式在这一时间段内始终是诗歌发表的主要阵地,不断从民间涌现的诗歌新生力量对抗与重构着同时代的诗歌话语。
之后出现的“第三代诗”是在“朦胧诗”的影响下产生的,以各地(主要是大学生)自办的诗歌刊物为阵地,“和朦胧诗一样,这种先锋性的诗歌探索,也以组织社团、创办刊物的‘民间’活动方式进行”[5]。因此,荷兰汉学家柯雷指出,“当今中国算得上重要的那些诗人,最初几乎个个都是首先在民间诗坛发表诗作和发出自己的声音”[6]。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当代中国的文学历史和文学空间中,文学体制具有巨大的体系性与覆盖性,有它严密的科层制结构与运作方式,它也是当代中国文学生产的主体渠道”,而民间办刊所形成的“独特的亚体制文化”则具有更多的自主性和随意性[7],这种出版机制使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的诗歌呈现出一种多元的发展状况。
与此同时,国家级的诗歌刊物《诗刊》复刊之后,紧紧把握时代转型的气息,“对‘文革’的话语模式进行清理并促使了诗性话语模式的转型”[8]。“1979年3月号《诗刊》转载了北岛在《今天》第1期上发表的《回答》,作为第一次公开发表的作品,该诗用崭新的言说模式与诗艺法则创设了思想启蒙和政治诗学的新维度”[9]。从北岛开始,“一些诗人的作品开始被《诗刊》及其他公开出版的杂志刊登,尤其是舒婷、顾城等逐渐进入主流文学界的视野”[10]。而且,作为官方主流文学刊物,《诗刊》杂志社从1980年举办第一届“青春诗会”开始,此后每年举办一届,扩大了当代诗歌在20世纪80年代的影响与传播。
从“朦胧、晦涩”的批评到政治抒情话语的确立,这与官方诗刊对朦胧诗的推动有很大关系。朦胧诗在诗坛的地位也发生了变化,不再是民间诗歌话语的代表,而成为新的主流诗歌话语。因此,“第三代”诗人喊出“PASS北岛”的口号,他们一反“朦胧诗”的政治抒情话语,将诗歌写作深入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从个人角度“表达了对都市弱势群体(如农民工和妓女)超乎寻常的社会关怀”[11]。新形成的诗歌话语对个体生命与日常生活的关注使其为更多人所接受。尽管“第三代”诗也是从民间刊物逐渐走入官方诗刊的,但诗歌本身已经发生变化,“第三代”后来形成了以西川、王家新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写作”和以于坚、韩东等人为代表的“民间写作”。“知识分子写作”以知识分子的立场坚守着诗歌的精英文学道路,拒绝与大众媒介的合作而囿于一角。“民间写作”的平民立场以“口语诗”的方式表达了日常生活的琐碎,这种表达也迎合了大众媒介的需求。
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逐渐步入互联网时代,互联网的开放性、平等性、自由性将诗人的写作变成诗人与读者的对话,新形成的文化空间孕育了新的写作与传播形式,诗人写的一首诗发在网络上即刻会有读者评论,似乎大家都拥有了鉴赏诗歌的能力或评判诗歌的权利。这种大众化的传播空间不仅扩充了以大众文化为代表的公共文化的传播内容,也使得诗歌以更加便捷的方式传播。“口语诗”在网络时代的泛滥与其自身语言的质素相关,诗歌这种短小的文体非常适合网络对于短平快的需求。新媒介的大众化又正好与“口语诗”的流行倾向相暗合,“网络自身的优势与新诗的质素一拍即合,使诗歌找到默契的合作伙伴”[12]。换而言之,“口语诗”在有意无意中迎合了网络新媒介的特点,使诗歌走向大众化的传播,网络媒介的出现极大地扩大了诗歌文本的读者群。
二、大众传播与诗歌事件化
在对21世纪以来的当代诗歌发展进行考查之后,我们不难看到引起人们热议的诗歌事件又是怎样带动着诗歌传播的。“‘诗歌事件化’已成新媒体时代的诗歌常态,甚至已成为诗歌传播过程中一种至关重要的策略”[13]。从20世纪的纸媒到21世纪的网络、自媒体等多渠道的媒介传播促成了“新媒体时代”诗歌的多元化、丰富化,同时带来大众诗歌文化的繁荣,在诗歌传播的意义上而言,这一时期成为当代诗歌发展的最为重要的历史时期。新媒体不仅压缩了传播时间,也消除了诗歌传播在空间上的距离,新的交互形式塑造了21世纪诗歌繁荣的大众文化特征。
“‘下半身’是第一个与互联网密不可分的中国诗歌事件,这类诗歌文本及其作者,依托网络这个最佳媒介和环境,找到自己的读者并且持续发展。互联网更容易催生短平快、无关痛痒的文本生产。”[14]“下半身”的代表诗人沈浩波和伊丽川的诗歌曾引来许多争议,他们的诗歌“把身体推向了某种极端化、粗鄙化的写作境遇,使得诗歌具有了鲜明的对抗、消解审美意识的观念与反文化的政治学特征”[15],如果从这个层面上来说,“下半身”写作对身体的解构具有某种文化反抗的意味,但写作中对身体的消解与消费也使其诗歌走向一种消费化写作。这类诗歌的易读性与互联网这种新媒介的传播机制相吻合,形成了一种易于传播的文本,原本表达人类精微情感的诗歌被简单化为一种戏谑的文本,而诗人潜藏其中的一点批判也显得无关痛痒。
2006年出现的“梨花体”是大众参与的一次网络诗歌事件,“梨花体”因赵丽华而得名,诗歌具有明显的口语化特征,被称为“口水诗”,每个人都可以模仿,不少人质疑“梨花体”能否称为诗歌。这次大众参与的诗歌事件之所以能够形成在于网络提供的传播条件,网络的确增强了读者与诗人的互动,但大众的参与使诗歌的传播形成一次文化事件。
2010年出现的“羊羔体”是根据车延高名字的谐音而来,这是继“梨花体”之后又一次“口水诗”事件在大众媒体上引起喧嚣。车延高的《徐帆》获得当年的鲁迅文学奖诗歌奖,诗中过于直白的表达引起网友在微博上热议,许多人质疑这一诗歌奖并呼吁抵制该奖项。后来的“乌青体”“啸天体”,同样是在微博上传播并受到质疑的诗歌事件。这些事件产生的影响使“口水诗”的合法性开始被动摇,无论是诗人还是普通读者都对这些称之为诗的作品感到困惑不已。微博作为一种微文体适于诗歌这种短小的文体广泛传播,但这种公共空间同时也造成诗歌的娱乐化、消费化。新媒介形成的这种虚拟的公共空间一方面使诗歌与大众的距离重新缩短,但另一方面,媒介本身的特性决定了其能使诗歌扩大传播范围,同时也会对诗歌本身造成损耗。
2015年初,《诗刊》微信公众号推出了农村妇女余秀华的诗歌《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和一系列评论文章。一时间人人转发,形成一股余秀华诗歌热。在余秀华诗歌大热的背后,人们更多关注的是诗歌之外的东西,比如诗人的身体残疾,诗中大胆露骨的描写等,这是事件对诗歌的形成的遮蔽。
当代诗歌的发展从精英化不断走向大众化的过程中,大众化传播实际上同时选择了诗歌的类型。“第三代诗”之后的发展就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口语诗”成为当代诗歌中传播最广的诗歌类型,究其原因无非是“口语诗”写作的易模仿性。除去于坚、韩东和伊沙等人的一些诗作,大多数当代诗人的口语写作并无多少深意,甚至出现大量粗制滥造的“口水诗”。这是口语叙事诗写作的危险,它容易将诗歌推向过于口语化和浅层叙事的特征,这恰好暗合了媒介文化的大众传播,致使诗歌走向复制化、同一化和秩序化的误区,正是这种没有深度的叙事使诗歌缺失了对文化价值的关怀和人性复杂的深度挖掘。“再现叙事呈现了趋浅化、庸俗化、粗陋化、极端化的写作趋势,再现的叙事变成现实主题‘应景’的写作,延缓与忽略了当代诗歌语言的自然生长、自我繁殖、裂变、创造的可能。”[16]
当代诗歌之所以能以这样的面貌被读者接受,离不开21世纪以来媒介在诗歌的大众化传播上所塑造的审美价值。正如学者刘坚所指出:“媒介文化将大众审美精神注入精英文学和通俗文学的审美实践中,生成了文学世俗化审美的价值和观念体系。”[17]就当代诗歌而言,作为大众文化传播手段的媒介在进行一次次诗歌事件传播的同时也参与塑造着大众的诗歌审美体系。近十年来,“梨花体”“羊羔体”“啸天体”“乌青体”等“口水诗”的广泛传播成为一种娱乐狂欢,诗歌在新媒介的推动下以事件的方式回到大众视野之中,却缺失了诗歌本身的严肃与沉思,“新媒体语境下的诗歌已呈现出一种‘优伶化’的趋向”[18]。诗歌无力对当下的现实展开批判,也无力对人性的复杂表达关怀,而是陷入一种消费娱乐的趋势,从而失却了诗歌真正的声音。
三、反讽书写:虚无主义倾向的当代投射
当代诗歌中出现的“梨花体”“羊羔体”以及余秀华诗歌热等事件既是大众文化的表征,也是新媒体技术发展的结果。正如罗振亚所指出,“新媒体写作者和读者之间界限的消除,直接对话交流的互动功能,使读者能够自由介入甚至左右文本的修改、完善方向,对文本跟帖或评论自主到了不受任何限制的程度,真正达成了作品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一体化”[19]。特别是“为你读诗”等微信公众号的传播,使得诗歌与大众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传统的诗歌刊物也开始用微信公众号平台发表与传播诗歌。诗歌的媒介化使其成为大众文化的组成部分。
大众文化话语背后则渗透着与传统精英文学不同的书写策略,“反讽”构成其质地与精神。一方面,反叛表现为诗歌的反讽叙事。“反讽是语言策略,它把怀疑主义当作一种解释策略,把讽刺当作一种情节编排模式,把不可知论或犬儒主义当作一种道德姿态。”[20]另一方面,大众文化本身的娱乐化、消费化、流行化、商业化等特征决定了它的传播机制,诗歌本身并不是大众文化关注的对象。正如菲克斯所言:“大众文化的意义仅仅存在于它们的传播过程中,而不是存在于其文本中。”[21]
当代诗歌作为文化之一种,自然也不断显现出反讽和反讽性。反讽的诗歌形成了文化的刺点,在赵毅衡看来,这种诗歌的写作是一种“聪明主义”的写作,“‘聪明主义’不是网络时代的机会主义:哪怕在书面诗歌时代,聪明也是好诗的标准……为什么诗本来就遵循‘聪明主义’? 因为诗给我们的不是意义,而只是一种意义之可能。诗的意义悬搁而不落实,许诺而不兑现,一首诗让作者和读者乐不释手,就是靠从头到尾把话有趣地说错。”[22]从反讽作为策略对精英文化的去蔽、解构,到反讽融入媒介转型的“虚无主义”情结之中。反讽,从“聪明主义”的文本策略到激进的“虚无”倾向,在诗歌生产中俨然变成一种主流价值。
如果我们回顾当代诗歌口语写作的历史,就可以清晰地看到当下的口语写作所形成的两种形态。一是以于坚为代表的转喻式写作,表现为对语言“‘还原’的透支”和“对诗的本质的背离”[23];二是以伊沙为代表的反讽式写作,“体现出一种否定,甚至消极的力量,对文学的肯定和建构予以消解”[24]。从于坚到伊沙,是口语叙事逐渐走向反讽的体现。也就是说,“‘口语写作’发展到了伊沙的写作,反讽渐渐成熟,这时候的诗歌在诗学形式上是一种重大突破,‘反讽’也成为朦胧诗以来的当下诗歌书写较重要的话语策略,但是,‘反讽’成为中心化、主流化写作趋势也意味着某种潜在危险”[25]。这种写作形式在某种程度上体现着诗对主流文化、精英文化的反叛,他们在消解主流意识形态与文化价值的同时,不断解构着人性的崇高与庄严。无论是“梨花体”“羊羔体”还是余秀华事件,他们的诗在内容与形式上与伊沙所代表的反讽化写作有着内在的相似性,都通过反讽的书写策略凸显了当下的虚无主义倾向。
21世纪以来媒介技术的发展形成了一个虚拟的网络空间,诗歌在这个空间中的写作与传播呈现出与传统媒介完全不同的特质。吴思敬指出,新媒体诗歌“是诗歌史上一次深刻的变革,它改变了诗歌传播方式的同时,也在改变着诗人书写与思维的方式”[26],新形成的媒介空间带来了知识的分解、权力的离散,同时媒介的丰富性、变化性决定了话语秩序的变化与解放,媒介信息与媒介本身变成信息社会的主体与内容。而新媒介本身的及时性、便捷性、自由性,修正了符号发出者的专制、独一身份,意义发出者的身份也变成多个,意义的传达空间变成块茎式的传播,这也吻合了时代对不同的传播空间的强烈的文化诉求,以及不同群体对多元文化的认同。“‘口语写作’的话语实践与运动性,的确呈现了消费文化下的后现代景观,但是它在诗学建构上却显示出不尽如人意的一面,这吻合了后现代社会的消费文化的否定特征。”[27]“口语写作”陷入消费社会下的精神虚无与文化虚无,以反讽的写作消解价值与崇高,解构人性的庄严。
四、通感书写:超越“反讽”
反讽话语作为当下文化反叛的一种极端形式,它指向了诗歌写作的另一种极端:对艺术语言与诗性的偏离。如果我们承认诗在本质上是一种关于语言的艺术,那么诗歌的发展作为艺术的本体性则仍然关乎语言的生命力。在诗歌写作中,语言意识体现着诗人的认知思维,它为认知主体提供了反思与自我追寻的思想源泉与有效动力,它关联着诗歌的语言与思维、形式与内容,诗歌在此既是对现实的体认,同时也是对超验本体的回应。具体而言,诗歌表达需要借助特定的修辞与语言技巧,“修辞化的语言所描绘的世界既是时代敏锐的文化触角,同时也专注于幽暗的精神世界的勘探,修辞的语言强化了文本效果,抵达审美化、主观真实”[28]。
为此,首先,当代诗歌的书写需走出当下的反讽话语模式,回归隐喻、通感、陌生化与超验等诗学的方式,使诗歌写作回归语言的诗性创造。“诗性是一种语言状态,是思想和语言互为表象的特殊形态,是此诗知与不知,彼诗道与未道的事物之间的关系。”[29]语言作为诗歌书写的本体追求,诗歌的意蕴也在语言中完成。正如伊格尔顿所言:“一首诗的语言就是其思想的构形”[30]。
其次,当下诗歌的写作应该超越反讽的策略式写作,回归通感书写的诗性创造。“在现代诗歌书写当中,通感所揭示出的具象与抽象结构空间,指向人类复杂的感性的‘通感领域’,这个抽象的领域又对外在对象具有极强的感性创造力、生成力和建构力,从而处理自我个体的感性世界与外在对象的神秘关系。”[31]通感书写强化了诗歌的文学空间,支撑着诗人与现实世界的联结与感应。
最后,在媒介时代的诗歌发展中,通感书写是一种基于超验表达与通感修辞的写作形式,它借助隐喻、象征、超验、陌生化等修辞沟通诗歌与外界的联系,在生命与自然万物之间实现灵性的感应,它指向人的生命本体与艺术价值。在此意义上,它是对大众文化与媒介文化的反讽话语的反拨,同时在语言与情感层面上对反讽进行有效的补充,以对诗性价值的回归超越语言与现实的虚无性。
综上所述,在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当代诗歌传播媒介进行梳理后,可以看出从纸质媒介到网络媒介再到自媒体的传播,当代诗歌的面孔是不断被选择性地呈现的。这背后由文化因素与资本因素所左右的消费时代的文化需求,使当代诗歌正偏离语言本位的诉求。物质与消费营造的时代反讽,从文化上要求诗人面对这种景观化的社会现实,诗歌的反讽成为当代诗歌书写的一种策略。但这种书写策略在面对消费时代的文化时,所形成的批判与建构已经变得羸弱。而通感书写在回归诗歌语言本位的同时能够重新激活词语的生命力,使当代诗歌的书写回归语言的诗性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