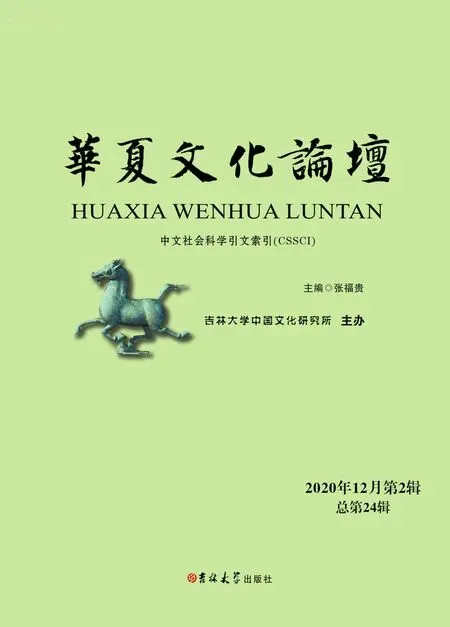王国维的“古文观”与古文研究
【内容提要】王国维先生学术生涯后半期致力于古文字研究,研究对象涉及到当时所能见到的各类古文字材料。其中对于古文的研究历经十年之久,打破了自汉代以来“古文”即从仓颉造字到周宣王之前的文字的传统观念,使“战国时六国用古文”成为不刊之论,初步建立了一套比较合理的古文研究理论体系。这一科学的“古文观”,开辟了新学术方向战国文字研究,促进了“二重证据法”的提出,推动了科学古文字学的建立,在古文字研究史和王国维个人学术生涯中都具有重要意义。
“古文”一词产生于汉代,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成为我国经学、文学、文字学中的重要概念,在不同学科具有不同涵义。经学中指古文经及古文经学派;文学领域的“古文”指与骈体文相对而言的有先秦和汉代传统、切于实用的散文,是唐宋古文运动所倡导的文体形式;文字学上的“古文”意义更为复杂,既可指与隶书、楷书等“今文字”相对应的“古文字”,可指五帝三王时代的文字,可指战国时期东方六国文字,又可指《说文》古文、石经古文、《汗简》古文、《古文四声韵》古文等汉以后历代辗转抄写的先秦文字。本文要讨论的是汉代以来所谓的文字学领域的“古文”。
王国维清楚地认识到“古文”这一概念的复杂性,也认识到汉代学者将“古文”看作五帝三王时代(从仓颉造字到周宣王之前)的文字的错误,①张富海:《汉人所谓古文之研究》,北京:线装书局,2007年,第2页。遂于“古文”研究用力颇巨。1916年作《史籀篇疏证》,首次提出“壁中古文者,周秦间东土之文字”的观点。1916年春开始作《魏石经考》,反复修改至8月完成。1916年11月作《汉代古文考》,辨析汉人所谓“古文”的所指。1923年作《魏石经续考》,对前作《魏石经考》多有修正和补充。1926年作《桐乡徐氏族印谱序》以大量出土战国文字材料为论据,重新阐发论证“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的观点。这一系列关于“古文”实际所指的专论和对石经古文、《说文》古文的集中研究,不仅更正了汉代以来对于“古文”的错误认识,建立了“古文”为战国时六国文字的科学系统的“古文”观,所提出的研究方法、研究成果为后世提供了创造性的示范和可资借鉴的结论,为科学古文字学的建立和战国文字研究奠定了基础。
1927年初夏王国维先生赴水而逝,可以说他在人生最后的十年,于古文研究方面,给学术史留下了宝贵的遗产,近百年来,古文字研究得到极大的发展,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随着出土文献的增多,王国维的“古文观”已基本被学界认同,成为不刊之论。但学界对王国维“古文”方面的研究成果,或直接引用或概述性评价,本文从王国维“古文观”的形成过程和古文研究的具体材料入手,重新认识这种思想的价值及影响。
一、“古文观”的发轫期
1916年,王国维结束四年多的旅日生活,回归祖国。这一年在他的学术生涯中也可谓重要的转折。文字学研究方面,对铜器的整理已经完成,《宋代金文著录表》和《国朝金文著录表》业已成书,西北简牍研究和甲骨文考释成绩斐然。古文字学四个分支中①李学勤:《我国三十年来的古文字与古代史》,《经济社会史评论》,2012年第00期。,他已涉猎三种,研究主要方向转向古文领域。在前期古文字研究中积累了丰富经验,对古文字材料的理解更加深入,学术眼光更加敏锐,这促使他在古文研究中取得了更大成就。
1916年2月作《史籀篇疏证》,3月作序一篇,该文为王国维古文研究的发端。文中首次提出:“壁中古文者,周秦间东土之文字也。”但主要内容还是针对《史籀篇》的作者、时代和《说文》籀文来源的考论。②关于“战国时秦用籀文”的观点,我们别文讨论,此文将不再赘述。对古文没有过多的论述。
11月作《汉代古文考》一文,该文最初刊入《学术丛编》第八、九、十三册,后收入《观堂集林》时分为《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说》、《〈史记〉所谓古文说》、《〈汉书〉所谓古文说》、《〈说文〉 所谓古文说》、《〈说文〉今叙篆文合以古籀说》、《汉时古文本诸经传考》、《汉时古文诸经有转写本说》、《两汉古文学家多小学家说》、《科斗文字说》等九篇。这一系列论述中对汉代“古文”进行了详细阐释,厘清了汉代“古文”的不同所指、《说文》古文的时代和性质、古文在《说文》中的分布等内容,“古文观”初步形成。
(一)汉代“古文”名同实异现象
王国维分析了《史记》《汉书》《说文》等文献中“古文”一词出现的不同语境,指出汉代学者所谓“古文”实际上有多种所指:
1.文字学范畴:指用以书写壁中书、张苍所献《春秋左氏传》的古文字。《说文解字·叙》介绍所收字体时云:“今叙篆文,合以古籀。”又云:“时有六书,一曰古文,孔子壁中书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异者也;三曰篆书,即小篆……”①(汉)许慎撰、(宋)徐铉校订:《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63年,第314页。“古文”即《说文》所收的古文经中的文字。王国维举司马迁、扬雄之说,认为“汉人以其用以书六艺,谓之古文”。
2.文献学范畴:指古文旧书。王国维说:“太史公所谓古文,皆先秦古文旧书。”如《五帝本纪》:“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余尝西至崆峒,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皇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索隐》云:“古文即《帝德》、《帝系》二书也。”司马迁作《史记》所参照的《五帝德》、《帝系姓》、《谍记》、《春秋历谱谍》、《国语》、《春秋左氏传》、《孔氏弟子籍》等书,“凡先秦六国遗书非当时写本者,皆谓之‘古文’”。②《观堂集林》卷七,中华书局,1959年,第307-308页。
3.经学范畴:指古文经和古文经学派。《汉书·艺文志》冠以“古”字的经籍,如《尚书古文经》、《礼古经》、《春秋古经》、《孝经古孔氏》,皆为古文经。后“古文”又从书体之名转为学派之名。《地理志》中多次出现的“古文”,是指古文《尚书》家和古文经学派。
王国维揭示了“古文”名同实异的现象。这一名称可指称古文字——古文旧本——古文经——古文经学派,而将这四个概念密切联系起来的,则是“古文”的文字学范畴的意义。汉代统治者积极提倡、民间自觉保护、学者爱好追求,今古文之争论、语言学和文献学的发展,都为古文研究带来了契机。唐兰在《中国文字学》里认为许慎即在这种良好的学术环境下,根据古文经,《史籀篇》、《仓颉篇》,其他古书里的材料和“六书”系统,写成了《说文解字》这部“中国文字学里的惟一经典”。③唐兰:《中国文字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21页。
古文与汉代通行的隶书区别很大,由此而产生的问题,就是汉代学者所认为的文字学范畴的“古文”,究竟从何而来?是什么时代的?汉代学者对这种古文的看法是否存在问题?这种古文观,对后世的文字研究产生了什么影响?
(二)关于古文的时代和地域
《说文·叙》云:“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蹏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以迄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体。……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至孔子书六经,左丘明述《春秋传》,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说。其后,诸侯力政,不统于王,……分为七国……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④(汉)许慎撰、(宋)徐铉校订:《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63年,第314页。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篆文,谓小篆也。古籀,谓古文、籀文也。”⑤(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763-764页。由上段话可知“古文”一词,主要指自仓颉至周宣王太史籀时期的古文字。“许慎认为,虽然古文经书的书写时代晚于《史籀篇》,它们所用的字体却早于籀文,因为孔子等有意用比较古的字体来写经书。”①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54页。自《说文》成书直至清代,人们对“古文”的理解均是这样。段玉裁甚至說:“凡言古文,皆仓颉所作古文”。②(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 1页。
最早对此提出质疑的当是吴大澂。吴大澂在《说文古籀补·自序》中写道:“窃谓许氏以壁中书为古文,疑皆周末七国时所作,言语异声,文字异形,非复孔子六经之旧简。虽存篆籀之迹,实为讹伪之形。”陈介祺:“疑孔壁古经亦周末人传写,故……古文则多不似今之古钟鼎。”③裘锡圭:《文史丛稿》,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171-173页。吴陈二人认为这些经书是周末人用当时通行的文字书写的。王国维继承并发扬了这种观点,在《史籀篇疏证序》中提出:
“许书所出古文,即孔子壁中书,其体与籀文、篆文颇不相近,六国遗器亦然。壁中古文者,周秦间东土之文字也。”④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七,中华书局,1959年,第254-255页。
在《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说》说:
“秦灭古文,史无明文。有之,惟有一文字与焚诗、书二事。六艺之书行于齐、鲁,爰及赵、魏,而罕流布于秦,(犹《史籀篇》之不行于东方诸国)其书皆以东方文字书之。汉人以其用以书六艺,谓之古文。而秦人所罢之文,与所焚之书,皆此种文字。是六国文字即古文也。观秦书八体中有大篆,无古文。而孔子壁中书与《春秋左氏传》,凡东土之书,用古文,不用大篆,是可识矣。故古文、籀文者,乃战国时东、西二土文字之异名,其源皆出于殷周古文。而秦居宗周故地,其文字犹有丰镐之遗。故籀文与自籀文出之篆文,其去殷周古文反较东方文字(即汉世所谓“古文”)为近。”“汉人以六艺之书皆用此种文字,又其文字为当日所已废,故谓之‘古文’。”⑤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七,中华书局,1959年,第305-306页。
在这段话中,王国维认为《说文》中的古文其实有殷周古文和六国古文两种意思。用来书写六艺之书的东方文字,汉人称其为“古文”,是秦统一文字时所废除的对象,六国文字即为古文。古文、籀文,是战国时期东、西二土文字之异名。都是从殷周古文发展而来的。秦居宗周故地,因此,秦国使用的文字与殷周古文更为接近。
在《〈说文〉所谓古文说》指出,许慎并沒有见过很多殷周古文,其原因主要是:记录彝器铭文的拓墨方法还没有出现,因此,许慎无法亲自观察出土鼎彝,也没有拓本可以参考。《说文》中的古文,并不是古老的殷周古文,而是出自壁中书及张苍所献《春秋左氏传》,是用战国时期的六国文字书写的。许慎所说“籀文与古文或异”并非《史籀》大篆与《史籀》以前古文的不同,而是“许君所见《史籀》九篇与其所见壁中书”的不同。
学界最初有很多反对的声音,出土材料的不断增加,给王国维的“六国用古文”的观点带来新的证据。现在学界已普遍认同他的观点,并认为在当时的六国文字材料很少的情况下,此观点“一语道破了壁中书来源,可谓发千载之覆,是古文研究的奠基之作。”①李春桃:《王国维与清末民初古文研究》,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编:《战国文字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中西书局,2017年,第38—45页。“先生从古今文字体势之演变,驳斥长期以来由古而籀,由籀而篆,由篆而隶的谬论……这对自北宋以来千余年间的古文字研究,乃至古史研究是一重大突破。”②袁英光,刘寅生编著:《王国维年谱长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 年,第148页。
王国维在1916年提出的“六国用古文”的说法,是处在“古文观”初步形成时期,从史书、保存鼎彝铭文的方法、古文字的发展来分析的,并没有用具体的古文字材料加以证明,因此还不够完善。
(三)古文在《说文》中的分布
《说文·叙》:“今敘篆文,合以古籀。”以往认为,篆文在字头,古、籀在重文中。而段玉裁认识到《说文》中的一部分字头是小篆与古文或籀文的迭合,“小篆因古籀而不变者多……其有小篆已改古籀、古籀异于小篆者,则以古籀附小篆之后,曰‘古文作某’、‘籀文作某’。此全书之通例也。其变例则先古籀、后小篆。”③(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763-764页。“小篆之于古、籀,或仍之,或省改之,仍者十之八九,省改者十之一二而已。仍则小篆皆古、籀也,故不更出古、籀。”④(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 1页。当小篆与古文或籀文一致时,古籀不再重出。
王国维致信于罗振玉,陈述自己对《说文》中字头的疑问:
“许君体例,篆文与古籀同者,不出古籀;其与古籀异而古籀相同者,则出古文,不复出籀文;惟篆文与籀文异(篆或同古文,或古文无此字,)始出籀文独少于古文。”⑤王国维著;刘寅生,袁英光编:《王国维全集·书信》,中华书局,1984年,第56页 。
并询问罗振玉意见。后在《〈说文〉今叙篆文合以古籀说》中区分《说文》正字,深入研究体例问题。王国维认为《说文》“今敘篆文,合以古籀”是指正字,而不是指重文。正字有篆文、古文、籀文三种来源。具体情况为:
1.小篆、古文、籀文不一致,则列出古文、籀文;
2.小篆、古文、籀文一致,则不列古文、籀文,只在正字出小篆;
我国在一段时期中的经济发展理念是先发展,之后再进行治理,这种模式虽然能够取得一定的经济效益,但是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对生态造成了破坏。而随着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恶化、水土流失和土地荒漠化的问题更加突出。因此,应该采取一定的措施进行营林护林工程的建设。在十八大的会议上,我国提出了“五位一体”建设规划,其中比较重要的内容是绿色发展的理念,这个理念的提出充分体现了我国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的决心和改善生态环境建设的目标。对林地进行管理的强化不仅能够提升林场的经济效益,同时还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林业规模的扩大,为实现生态文明和经济建设提供坚实的基础。
3.小篆有,无古文或籀文,亦在正字单列小篆。
4.有古籀、无小篆,古籀不能不列,又不知放在何处恰当,则古籀直接列于正字。
因此“正字中之古、籀,则有古、籀、篆文俱有此字者,亦有篆文所无而古、籀独有者。”“凡正字中,其引《诗》《书》《礼》《春秋》以说解者,可知其为古文。”“引《史篇》者,可知其为籀文。”“引杜林、司马相如、扬雄说者,当出《仓颉》、《凡将要》、《训纂》诸篇,可知其为篆文。”⑥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七,中华书局,1959年,第319-320页。
王说不但指出了古文在《说文》中的分布,还提出了判断标记。但他只针对《说文》一书来论证,并未列举具体实例。许多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过研究,张世超先生在《“今叙篆文,合以古籀”》一文中,用秦文字、六国文字和《说文》正篆进行对比分析,得出了《说文》中被称为“正篆”的字头篆文,其中的许多字来源于六国文字,“只不过是许慎将它们篆文化,构建了一个理想化的文字构形体系而已。”①张世超:《“今叙篆文,合以古籀”考》,《古代文明》第7卷第1期,2013年1月。有理有据的论述,就更科学也更有说服力。
二、“古文观”的沉淀期
汉代学者所谓古文,自汉代流传下来,主要保存在《说文》古文、三体石经古文,《汗简》和《古文四声韵》中,统称为传抄古文。魏正始年间用古文、小篆、隶书三种字体刊刻石经,所以被称作三体石经或三字石经。《说文》可以说是汉代古文研究的集大成者,三体石经则继《说文》之后代表了曹魏时期古文发展的情况,三体石经在唐代就已遭到严重破坏,连拓本也失传了,我们所能见到的只有《隶续》中的摹本。清末有残石陆续被发现,石经古文重新走入人们的研究视野。1916年春,王国维始作《魏石经考》,由汉石经之经数石数,以考魏石经之经数石数。1916年8月作成《魏石经考》,1923年作《魏石经续考》,石经古文的研究时间较长,且不断修正和补充,代表王国维“古文观”沉淀期的最主要的成就。
(一)经数、石数、字数、排列、字形来源、书手等
赵万里对王国维的石经古文研究做了概括:“初岁丁巳,先生据黄县丁氏所藏魏石经残石,以定魏石经每行字数及每碑行数,复以《太平御览》《洛阳记》所载碑数及诸经字数量参互求之,以定魏石经经数。又排比《隶释》所存残字为经文考、古文考,合之碑图,署曰《魏石经考》,刊入《广仓学宭丛刊》中。及癸亥春,洛阳城外汉魏太学遗址出土魏石经残石一,两面分刻《尚书》《无逸》……又次为古文、石经古文(即壁中遗文),与《说文解字》中之古文同出一源,故如五字、典字、禹字、后字、弼字、简字、革字、德字、鸟字、民字、韦字、杀字、远字、陟字、事字、侯字、襄字、卯字古文均与《说文》全同。壁中古文实即战国时东土通行文字,故石经古文颇有与传世古玺印、兵器文字相合者。此外石经古文见于宋人书,如《汗简》《古文四声韵》亦一并入,以供比勘之助力。末附《隶释》所录魏石经碑图,盖转从前考录入,此书出,则前考成陈迹矣。”②赵万里《静安先生遗著选跋》,吴泽主编、袁英光选编:《王国维学术论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432页。赵万里的说明,基本可以概括王国维三体石经观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情况。
魏石经所刊是当时立于官学之经中,最为重要且有古文本的经学要著。王国维认为其中的古文,主要有如下特点:
2.魏石经古文主要来源于壁中古文,汉除壁中古文及张苍所传《春秋左氏传》外,没有別的古文。传到魏时,即使不是壁中之本的原形,使用的也必为壁中古字。
3.魏石经的古文有的与殷周古文相合,这些字并非出自许书,因《说文》中并未收录鼎彝文字。
4.关于石经的书写者,史料记载不同,王国维则认为石经并非出自一人之手。
(二)古文的书体风格
《科斗文字说》一文,王国维根据古书中记载,推断“科斗文”其实是古文的别名。如:《后汉书·卢植传》:“古文科斗,近于为实。”郑玄《书赞》云:“《书》初出屋壁,皆周时象形文字,今所谓‘科斗书’。”称古文《尚书》为科斗书。卫恒的《四体书势》说:“汉武时鲁恭王坏孔子宅,得《尚书》、《春秋》、《论语》、《孝经》,时人己不复知有古文,谓之‘科斗书’。汉世秘藏,希得见之。”王隐《晋书·束皙传》云:“太康元年,汲郡民盗发魏安釐王冢,得竹书漆字科斗之文。科斗文者,周时古文也。其头粗、尾细,似科斗之虫,故俗名之焉。”①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七,中华书局,1959年,第337-338页。王国维认为西汉没有“科斗文字”的说法,从文字的记载来看,“科斗文字”的说法,首先由东汉末年的学者提出,并盛行于魏晋以后,是书体之名。“魏晋之间所谓科斗文,犹汉人所谓古文。”“古文”表明其来源,而“科斗”表明其书写风格。
在《魏石经考五》一文中,王国维追溯了历代古文书体的源头,对照魏石经古文、传世字书、出土器物文字、文献记载等,认为孔壁中书的写法不得而知,魏石经中古文才是科斗文,是历代古文书体的源头。并于1916年6月15日书信中说:
“近考古之书体,有一事堪奉告者,即两头纤纤之古文实自三字石经始。卫恒谓正始中立三字石经转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是邯郸淳之古文不如是也。许书古籀文字体本当与篆体不甚相远,今所传字形亦锐其末者,盖雍熙刊本篆书或出徐鼎臣,古籀当出句中正、王惟恭二人之手。二人夙以古文名,无怪其作汉简体也。”②王国维著;刘寅生,袁英光编:《王国维全集·书信》,中华书局 1984年,第86页 。
王国维据此认为三体石经中的古文,“丰中锐末或丰上锐下”的写法,是有意依据“科斗”这一名称而作,在此之前并么有这种写法。此后所谓古文,就专用这种书体了。
我们从今天的出土文字来看,“科斗”一名似乎并非凭空想象、为标新立异而起的名字,因为许多出土的楚文字恰恰符合科斗文描述的书体风格。王国维因没有亲见最初孔壁古书的真实写法,对待“科斗文”这一概念是非常谨慎的,这体现了他严谨的学术精神。同时他也认识到不同书手的作品是有差别的。书手的个人风格问题,是释读古文字时不得不考虑的因素,也是影响汉字形体演变不可忽略的因素,王国维已经发现了这个问题。关于壁中古文书体风格和书手对古文字体风格的影响的认识,也是其科学“古文观”的重要方面。
魏石经是继《说文》之后对古文的又一次良好的保存,石经古文也是古文研究的重要文献。王国维重视石经古文,较早对传抄古文展开研究。随着传抄古文对于新出土文字释读意义的重新发现,王国维的研究也重新为学界所重视。
三、“古文观”的建设期
1925年,王国维任教于清华国学研究院,1926年10月创作《桐乡徐氏印谱序》,这是王国维有关古史与古文字的最后作品之一。该文针对当时钱玄同等人对《说文》古文及壁中古文经的质疑,在距最早提出“六国用古文”的观点十年之后,以大量出土战国古文字材料为论据,进一步证明古文实为战国时期东土流行文字。如果说第一阶段,是古文观初步形成期,第二阶段对石经古文的具体研究是古文观的沉淀期,第三阶段就是古文观的建设期。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积累为第三阶段的研究直接提供了古文材料和理论依据,使得第三阶段的研究理论性更强,研究方法更进步。第三阶段主要研究如下:
(一)战国文字的种类、特点
王国维在《桐乡徐氏印谱序》中说:
“三代文字,殷商有甲骨及彝器,宗周及春秋诸国并有彝器传世,独战国以后,彝器传世者唯有田齐二敦、一簠及大梁上官诸鼎,寥寥不过数器。幸而任器之流传,乃比殷周为富。今世所出,如六国兵器,数几逾百。其余货币、若玺印、若陶器,其数乃以千计。”①王国维:《观堂集林》第一册卷六,中华书局,1959年,第299页。
战国传世彝器较少,而玺印、兵器、货币、陶器数量多,因此文字内容简单,如陶器、玺印、货币文字大多只记人名或地名,兵器文字有固定的铭文形式,因此不能完全和壁中书相印证,即便如此,仍可找到与汉人所传古文的相合之处。
(二)魏三体石经古文及《说文》古文的时代、国别
六国文字和壁中古文体现出相同的特点,即均为“讹别简率,上不合殷周古文,下不合小篆,不能以六书求之”,与同时代秦国文字差别较大。这是战国时东方文字的特点。并进一步指出魏石经及《说文解字》所出之壁中古文是战国齐、鲁间文字。
批评世人认为壁中古文为伪造的错误。强调壁中古文“上不合殷周古文,下不合秦篆者,时不同也;中不合秦文者,地不同也”,但绝非伪造。
(三)研究古文的方法:参照六国文字
研究魏石经古文、《说文》古文等壁中古文,应与六国兵器、陶器、玺印、货币对照,不应与殷周古文对照。虽关于它们的研究者少、材料少、谱录少,但仍能推断出此四种文字自为一系,又与壁中古文为一系。
王国维所见的战国文字材料不多,但清醒地认识到兵器、陶器、玺印、货币等器物上的文字是与甲骨、彝器同样重要的古文字资料,在研究古文时是最重要的参考。可以说,为了证明自己所主张的古文观的正确性,王国维反复求证,历经十年,使这一问题最终得以解决。
(四)传抄古文与出土六国文字的对比
《桐乡徐氏印谱序》认为壁中古文为战国文字,并比较了大量的字形来证明壁中古文与六国四类文字的相合之处。为了验证王国维的观点,也为了更加清晰地比较字形,我们一一核对文中所举字例,文中除了《说文》古文,石经古文、兵器、陶器、玺印、货币等铭文外,还有几种文字无法归到这六类之下,我们单列为“其他”。用括号标明所对照的战国文字的国别(齐、三晋、燕)等。因内容较多,我们在此举例加以说明。①我们的字形比较、国别的确定,主要参考了如下资料: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周金文集成》(修订增补本),中华书局,2007年。故宫博物院编、罗福颐主编:《古玺汇编》,文物出版社,1981年。高明编著:《古陶文汇编》,中华书局,1990年。汪庆正:《中国历代货币大系》(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徐在国编著:《传抄古文字编》,线装书局,2006年。冯胜君:《郭店简与上博简对比研究》,线装书局,2007年。陈光田:《战国玺印分域研究》,岳麓书社,2009年。何琳仪:《战国古文字典》,中华书局,1998年。若遇王国维未指明器名或器名与当前不同时,我们则使用当前常用名称。如,王国维所说的“罗氏所藏断剑”,即《殷周金文集成》(修订增补本)11184号器郾侯脮戈。
从下表我们可以看出,《说文》古文、石经古文和六国文字有很多相似之处。主要有四种情况:1.石经古文与各类文字字形完全相同。2.《说文》古文与各类文字字形完全相同。3.《说文》古文与六国文字大同小异,有细微差别。4.《说文》古文与石经古文字形不同,分别有形近的六国文字。
我们一一核对表中文字的出处和国别,四类文字大多为齐、三晋、燕、楚文字,王国维所说应该是符合事实的。当然,有许多学者进行过系统研究,将《说文》古文、石经古文等传抄古文与战国文字进行对比研究。关于壁中古文的具体国别,学界也多有讨论,我们这里只分析《桐乡徐氏印谱序》中的例字,不进行全面研究。


四、王国维“古文观”的学术意义
王国维“古文观”自1916年提出,到1926年的再次论证,历经十年,最终得以确立。基本内容为:
《说文》古文(汉代学者所说的古文)不是从仓颉造字到周宣王之前使用的文字,而是战国文字。2.《说文》古文实际上是战国时期与秦文字相区别的,来自于东方六国的文字。3.《说文》古文是流传了两千年的古文,六国古文是各个时代新发现的。4.传抄古文与出土的六国文字互证,是正确的古文研究方法。
我们纵观其整个古文观的发展过程,可以得知古文观不仅对于古文研究有重要的意义,对王国维的个人学术生涯和文字学史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王国维古文观在学术史上的意义
1.对于传抄古文研究的意义
《说文》古文、三体石经古文、《汗简》等传抄古文,是古代发现的战国文字。但经过漫长的岁月,“经传注疏的‘隶古定’及字书中的“古文”,并非战国文字的本来面貌,我们只能从传钞古文中得其仿佛。因此,对《说文》古文、籀文、三体石经、《汗简》、《古文四声韵》之类的传钞古文资料应倍加珍视。”①何琳仪:《战国文字通论》(订补),江苏教育出版社,2003年。但在王国维之前对它们的重视不够,王国维之后,这些传抄古文才逐渐得到学术界的重视。
王国维的古文观经历了三个发展时期,在不同时期,对古文的不同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
发轫期:研究《说文》古文的时代、地域、性质,在字书中的分布情况。形成了与汉代学者沿用了两千年的古文观不同的古文观。
沉淀期:研究石经古文所刊经籍的版本、石经的排列、字数、石数,主要将《说文》古文、三体石经古文两种传抄古文对照,同时引用《汗简》、《古文四声韵》中的古文,引用甲骨文、金文进行对比,深入研究字形。指出“古文”和“科斗文”是对古文从形体结构、书体风格两种角度的称名。
建设期:确立传抄古文研究与出土战国文字对比的方法、材料的来源、国别、种类,总结文字特点及与其他体系文字的不同。
通过对三个时期总结,我们不难发现,王国维看似零散的研究,实际上建立了一套古文研究理论体系、研究方法。这在所能见到的战国文字材料还不够丰富的百年前,是一种相对合理的理论体系。王国维以其古文研究实践和科学的研究理论体系为后学指明了研究方向,具有开创意义。
2.对于战国文字研究的意义
两千年前孔子壁中书的发现,是战国文字的首次大发现,一直被人们忽视,以至于没有认出它们的真正时代。唐兰先生说:“汉人把孔壁发见的战国末年人所写的经书,误认为孔子手迹,又断定孔子所写的一定是原始古文,所以把古文经推尊得太过分了,把文字发生的时代都紊乱了。①唐兰:《中国文字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21页。裘锡圭先生指出,“古文经学家看到这种古文字跟籀文不同,就把它当作比籀文更古老的一种字体了,古文经学家之所以会得出这样的错误结论,可能他们极力想抬高古文经地位的心理大概起了作用。”②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55页。文化、政治、学者们的文字意识都影响了汉代学者关于古文的认识。而王国维“六国用古文”的“古文观”,真正揭示了“古文”为战国文字的事实。纠正了汉人古文观的错误。将东周文字分为东土文字和西土文字,从文字学的观点出发,区分时代和地域,提出新的文字分类方法。同时将殷周古文和六国古文两个混淆的概念区分开来,这对于以“隐姓埋名”沉寂了两千年的战国文字焕发新生具有重要意义。何琳仪先生指出:“近代战国文字研究,是建立在出土文字数据和对传世‘古文’研究基础上而兴起的新学科,王国维则是这一学科的奠基人。”③何琳仪:《战国文字通论》(订补),江苏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9页。
3.对于《说文》研究的意义
随着“古文”这一模糊的概念得以澄清,《说文》研究也脱离了传统《说文》学的研究范畴和方法,开辟了更多研究方向。胡光炜先生的《说文古文考》(1927)舒连景《说文古文疏证》(1935)商承祚先生的《说文中之古文考》(1934-1940)都是较早的关于说文古文的研究。近百年来,关于《说文》古文的研究层出不穷,比如利用出土资料来考证“古文”来源,考察正字中的古文、籀文等情况。学者们一边研究《说文》本体,一方面验证王国维的古文观是否正确,大大促进了古文字学的发展。
4.对后学的启发
王国维在研究魏石经古文时,多次引用《汗简》和《古文四声韵》的内容,何琳仪先生在《战国文字通论》一文中,指出了两部书的重要性:“北宋初年,郭忠恕根据当时尚能见到的“古文”材料,辑成《汗简》。其后,夏竦又在该书基础上增补许多“古文”,辑成《古文四声韵》。这两部书虽然取材较为庞杂,且时有讹误,但从保存传钞古文材料而言,至今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以往学者对这两部书的评价甚低,考古新材料已经证明:《汗简》和《古文四声韵》乃是释读战国文字不可缺少的工具书。”④何琳仪:《战国文字通论》(订补),江苏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6页。虽然以往学者对两部书不够重视,但王国维对两部书的利用说明,他对材料的理解和利用是客观的,有很强的包容性。
同时,他在研究《说文》古文和魏石经古文时,不仅对比了战国出土文字,还对比了甲骨文、金文等殷周古文,即使他认为古文实为战国文字,但仍旧对殷周古文加以合理的利用。可以说他拓宽了古文研究的资料来源,值得我们反思和学习。王国维古文研究是较早的对汉字字形发展演变的历史面貌和进程进行的研究,但他的研究毕竟在百年前,没有丰富的新出土材料作为依据,难免有一定的局限性。
(二)王国维古文观对自身学术生涯的意义
1925年7月王国维在清华大学作题目为《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的学术演讲,提出“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汉之壁中书,晋之汲冢书,均其著者也。”面对甲骨文等新出土材料,强调新学问的产生离不开对新材料的发掘和研究。随后,1925年秋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开设的《古史新证》课上,正式提出“二重证据法”,强调用“地下之新材料”补正“纸上之材料”。我们认为,长达十年之久的古文研究和科学的“古文观”的确立和建设,对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提出有直接的促进作用。
另外,《说文》古文和魏石经古文都是传抄古文,属于传世文献,而兵器、陶器、玺印、货币等是出土文献,王国维利用二者进行互证,正是“二重证据法”的最好体现。可以说,古文研究促进了“二重证据法”的提出,而“二重证据法”反过来又指导古文研究。因此我们认为,科学的古文观与“二重证据法”在王国维自身的学术生涯中都居于重要地位,可谓其古文字研究思想的总结。
《汉语文字学史》将民国以来古文字学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从1911年辛亥革命后到三十年代,为科学古文字学的草创阶段。三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末为奠基阶段。1978年以后为古文字学的全面发展阶段。处在第一阶段早期的罗振玉、王国维对古文字学的建立有创始之功。①黄德宽,陈秉新:《汉语文字学史》,安徽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186页。我们认为王国维长达十年之久的古文研究和科学的“古文观”,是科学古文字学建立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一环,促进了二重证据法的提出,为战国文字研究奠定了基础,影响了近百年来的学术界,在古文字研究领域和王国维个人学术生涯中都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