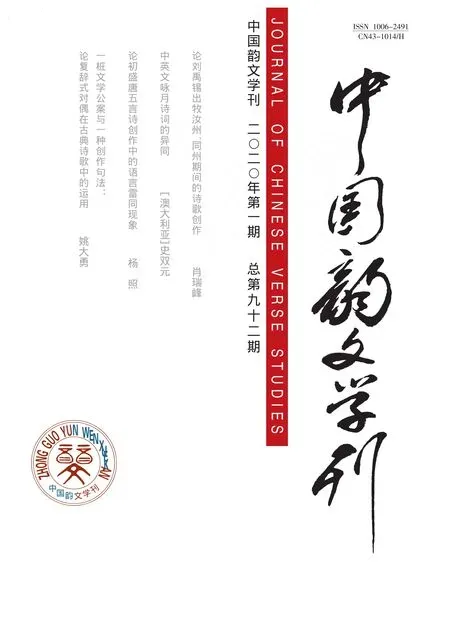邺下文学集团同题共作赋的兴盛及文学史意义
甘比海
(1.贵州师范大学 文学院,贵州 贵阳 550001;2.遵义医科大学 管理学院,贵州 遵义 563003)
辞赋的群体性创作自西汉前期的藩国赋家集团已肇其端,西汉中后期中央朝廷的御用赋家群扬其波,至汉灵帝时设鸿都门学以书画诗赋取士的风尚继其绪;到了汉末建安时期,在曹操为诸子选置“文学属官”以及此期文学风气的转变背景下,邺下文学集团以同题共作的方式再度兴起了赋的创作热潮。本文在概述建安邺下文学集团及同题共作赋基本情况的基础上,从创作方式的角度讨论同题共作对此期辞赋阶段性创作热潮兴起所起的作用,同时,进一步探讨这一创作方式在赋体文学发展演进史上的影响和意义。
一 彬彬之盛的邺下文学集团
邺下文学集团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自觉致力于文学创作和探索的团体性组织,也是汉末建安时期最为活跃、文学成就最高的作家群体。在曹操、曹丕、曹植父子的组织领导下,大批文人才士望路而争趋,形成了彬彬之盛的文学团体,成就了令后人倾心赞颂的文学盛事。所谓文学集团,胡大雷先生将其定义为:“为了从事文学创作、文学评论或其他文学活动而组成的、共同进行文学活动的团体。”[1](P1)根据胡大雷先生的论述,共同开展相关的文学活动是文学集团主要目的。它的形成需要多方面的因素和条件:首先,相对安定的社会政治环境和较为富庶的经济条件是文学集团得以形成的前提条件;其次,文学集团必须要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即文学盟主,以组织领导文学创作活动的开展。其三,需要较多的文学才士的积极参与;其四,相近的创作风格倾向,共同的文学理想,是文学团体得以形成的动力要素;最后,丰富多彩的团体活动,酬唱往来的文学风尚,逞才竞采的创作动机,是文学集团文学创作的重要形式。
东汉末年,由于长期的外戚专政和宦官弄权、政治腐败,导致民不聊生,终于在汉灵帝中平元年爆发了声势浩大的黄巾起义。在地主、军阀的联合打击下黄巾起义虽然最终失败,但是东汉王朝已是名存实亡,从此陷入了军阀混战割据的局面。曹操以超群的才略在军阀混战中迅速崛起。先是迎献帝而都许昌,挟天子以令诸侯,接着用武力荡平北方各股割据势力,称雄北中国。建安五年,曹操以少胜多在官渡大败袁绍,又于建安九年击败其子袁尚,进占邺城。古邺城,大致在今河北临漳县西南和河南安阳市北郊一带,地处兖、并、冀三州交界要冲,战略地位极为重要。邺城本为袁绍势力的根据地,曹操占有邺城后,把它作为自己的大本营。此举为曹操称雄北方奠定了雄厚的基础,《晋书·乐志》云:“曹公破邺,武功之定始乎此也。”[2](P701)曹操大力经营邺城,自建安十五年起,先后在邺城营建了铜雀台、金凤台、冰井台等。邺城逐渐成为当时北方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曹操又以“唯才是举”的用人标准,吸纳了大量择主而事的文人,他在为其诸子选置署官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团体——邺下文学集团。众多的文人才士环绕在曹氏父子周围,游息于铜雀台之间,或“洒笔以酣歌”,或“和墨以谈笑”,[3](P1694)或宴游而赋诗,或悯时而伤乱,在集体的努力下兴起了一场影响深远的文学创作热潮。
钟嵘《诗品序》云:“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笃好斯文,平原兄弟,郁为文栋,刘桢、王粲,为其羽翼。次有攀龙託凤者,自致于属车者,盖将百计,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矣。”[4](P58)钟嵘用“彬彬之盛,大备于时”概述此期的文坛盛况,足见他对当时文坛的推崇和赞赏。对于邺下文学集团的成员,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中亦作了列举:
自献帝播迁,文学蓬转,建安之末,区宇方辑。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仲宣委质于汉南,孔璋归命于河北,伟长从宦于青土,公干徇质于海隅,德琏综其裴然之思,元瑜展其翩翩之乐,文蔚、休伯之俦,于叔、德祖之侣,傲雅觞豆之前,雍客衽席之上,洒笔以成酣歌,和墨以藉谈笑。[3](P701)
刘勰列举出了邺下文学集团的主要的成员:曹操、曹丕、曹植父子,王粲、陈琳、徐幹、刘桢、应玚、阮瑀,路粹、繁钦、邯郸淳、杨修,共计13人。牛润珍先生通过考证,认为邺下作家群主要有22人,在刘勰所列举的基础上增加9人:甄皇后、应璩、吴质、丁仪、丁廙、荀纬、刘庾、苏林、蔡琰。[5](P100-109)然而邺下文学集团的成员或许还不止这个数目,钟嵘所谓“盖将百计”,或非虚言。
二 同题共作的含义及其范畴界定
邺下文学集团以作品的丰硕、创作活动的频繁和作家的气质风骨成就了这一时期文坛的盛事,而辞赋的同题共作是这一时期十分普遍的现象,这在整个文学史或是辞赋发展演进史上都是极为特别的。南京大学程章灿先生把这一时期辞赋的同题共作这一现象看作是“集体自觉努力的突出表现”,在界定其概念时他认为“同题共作只是规定一个大致的题材范围,作家有一定的自由发挥余地”。[6](P45-46)程章灿先生对同题共作的界定重点强调创作活动的集体参与,指出了同题共作的特点是作家群体在大致题材的范围内有自我发挥空间地进行创作。河南大学马予静先生则对同题共作的内涵做了进一步的阐释,她指出:“同题共作是一种集体性的创作活动,它应当包括两个方面的创作要素,其一是写作的共时性,其二是题目的一致性。”[7](P56)马予静先生对同题共作的界定实际上兼顾了三个方面的内容:创作活动的集体性;写作时间的共时性;作品题目的一致性。本文对同题共作的诠释和范畴的界定即在马予静先生所下定义的基础上稍作阐发:所谓同题共作是众多作家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围绕某一相同题材或事由,在相同或相似创作动机的触发下所进行的集体性创作活动。本文在界定同题共作赋的范畴时,首先放宽了对赋作题目完全一致的限定,而强调事由和题材的相同,因为完全可能存在同题不一定共作、共作也不完全同题的现象。例如,此期《沧海赋》有曹操、曹丕、王粲作三篇,经考论曹操、曹丕赋作为建安十二年北征乌桓后回邺城途中临观渤海所作,而王粲此时尚于荆州依附刘表,建安十三年方归于曹操帐下,故不可能同题共作。再如挚虞《文章流别论》云:“建安中,魏文帝从武帝出猎,赋,命陈琳、王粲、应玚、刘桢并作。琳为《武猎》,粲《羽猎》,瑒为《西狩》,刘桢为《大阅》。凡此各有所长,王粲其最也。”[8](P1905)则知曹丕、应玚、王粲、陈琳、刘桢五人之赋因同一事由而作,赋类一致,当列入同题共作范畴,但五赋题目并不完全相同。其次,侧重强调作品的关联性和创作的时空限定,这关涉到作者是否为文学集团成员和是否参与集体创作。
根据上文对同题共作的定义和范畴的界定,并对邺下文学集团作家作品进行了逐篇考论和统计,涉同题共作的作家有曹操、曹丕、曹植、王粲、陈琳、徐幹、刘桢、应玚、阮瑀、繁钦、邯郸淳、杨修、丁廙、丁廙妻、缪袭、傅巽、卞兰17人,赋作(包含辞、七体)135篇,约占邺下文学集团作家总数的74%,约占所涉作家赋作总数的73%。(1)程章灿先生在《魏晋南北朝赋史》中对建安作家涉同题共作赋的情况进行了统计,认为涉及同题共作赋者有18 人,作品126 篇,占作者总数的100%,赋作总数的68%。与本文统计结果存在差异的原因有二:其一,讨论的对象和范围有所不同,程先生是对整个建安时期同题共作赋状况的概述,本文则集中讨论邺下时期;其二对同题共作的定义及范畴的界定有所不同。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45~46页。如表1所示。可见同题共作是这一时期辞赋创作的主要形式,极大地刺激了此期辞赋创作的兴盛。

表1 邺下文学集团同题共作赋一览表①
邺下文学集团同题共作赋的产生,(2)注:“畋猎赋类”“离别赋类”等赋类诸篇虽赋题不完全一致,但创作的事由相同,作品内容相关,经考论属同题共作范畴,故列为一类,并列出赋题。或是游戏娱乐,应教进献;或是骋辞竞采,为文造情;或是触物兴感,为情造文;或是唱和往来等。南京大学巩本栋先生认为“诗词唱和的性质是同题共作”[9](P161),因而把诗词的联句、应酬、赠答、次韵、拟和皆列入唱和的范畴,认为这些唱和形式皆具有同题共作的属性,逞才使气是同题共作产生的重要动力。巩本栋先生说的是诗词的唱和,而赋也存在着唱和现象,只不过以赋唱和并不像诗词唱和在形式上有那么严格的要求,尤其是在律赋形成以前。王芑孙《读赋卮言·和赋》:“要是同作不和韵,前此邺下七子时相应答,已为导源,特不加‘奉和’字耳。”[10](P288)据王氏所言,则建安邺下时期以赋往来应答的活动已导和赋之源,当属同题共作范畴。例如,曹丕《玛瑙勒赋序》云:“玛瑙,玉属也。出自西域,文理交错,有似玛瑙。故其方人因以名之。或以系颈,或以饰勒。余有斯勒,美而赋之。命陈琳、王粲并作。”[8](P1074)又陈琳《马脑勒赋序》亦云:“五官将得马脑以为宝勒,美其英采之光艳也,使琳赋之。”[8](P968)则陈琳、王粲赋之于曹丕当为奉和而作。此期其他大量的同题作品,虽未明言为同题应命奉制之作,但亦可推知为这一类作品。因此,以赋唱和、应答是此期同题共作赋的重要的形式。
三 邺下文学集团同题共作赋概览
建安邺下时期的文坛是一个群星闪耀的舞台,曹氏父子身先垂范、文人才士望路争驱,他们或宴游集会、或登临怀古、或颂美功业、或感离伤逝、或行旅征伐、或赏鉴方物、或游戏娱乐等,在这些活动中产生了大量同题共作的抒情和咏物赋作。
(一)宴游畋猎,同享宾主之欢
宴游集会是邺下文学集团最主要的活动,众多的文人才士齐聚邺下,围绕在曹氏兄弟周围,曹丕、曹植则以文坛领袖的身份,热心创作,礼爱文士。在曹丕的领导和组织下,他们在邺下开展了很多形形色色的游宴集会活动,或高会于西园,或讲论于东阁,或驰骛于北场,或旅食于南馆。在这些驰骋游宴活动中,集体创作产生了大量的诗赋作品,他们“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体现出“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的“建安正格”。[3](P196)在徐幹、陈琳、应玚、刘桢等人相继亡殁后,曹丕在写给吴质的书信中对当时的情景表达了无限的追忆和感叹,他说:“昔年疾疫,亲故多罹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11](P591)邺下文人的这种风尚又被后世文人无限向往地称颂为“邺下风流”。
东阁命赋,共戒盈满。东阁讲堂,在铜雀园左近,是曹丕避暑之所,也是与诸贤文才讲论、述作的地方。《初学记》卷十《皇太子门》引《魏文帝集·叙诗》曰:“为太子时,北园及东阁、讲堂并赋诗,命王粲、刘桢、阮瑀、应玚等同作。”[12](P229)太子之谓当是后人所追书,曹丕建安二十二年被立为太子,其时阮瑀等多已辞世,无从同作。邺下文人宴集作乐并不是毫无节制地放情纵欲,而是怀着居安思危、虚怀纳谏的心态自戒。曹丕作有《戒盈赋》,其序云:“避暑东阁,延宾高会,酒酣乐作,怅然怀盈满之戒,乃作斯赋。”[8](P1073)赋文主要讲述登高增惧、处满怀愁的道理,要自己时刻铭记盈满之戒,广开言路,虚怀纳下。应曹丕之命,陈琳、阮瑀各有《止欲赋》一篇,应玚作《正情赋》,王粲作《闲邪赋》,曹植亦作《静思赋》,曹丕自己也作有《闲思赋》,这六赋皆先写自己对某一美女的梦寐思念和不懈追求,最后却又归于自律自戒。
田猎驰骛,众贤共赋。建安中,曹丕、陈琳、王粲、应玚、刘桢跟随曹操出猎,命各作赋。曹丕作《校猎赋》、陈琳作《武猎赋》、刘桢作《大阅赋》、应玚作《西狩赋》、王粲作《羽猎赋》,其中王粲《羽猎赋》最得曹操称许。则五赋皆可列入同题共作赋的范畴。此外,应玚还有《驰射赋》和《校猎赋》两篇,曹丕有《游猎诗》。在这些赋中,既描写围猎场面的盛大、骑射的精湛、军容的严整,又表达了对曹操德行和功业的颂赞。曹氏兄弟文武双全,多次随父出征;邺下诸文人大多久历乱世,亦有过军旅经历。因此,他们不仅乐于诗酒唱和的宴集,也有着效命疆场、建功立业的志向。
(二)感离伤逝,共诉人事之悲
悯孤怜寡,共诉悲情。汉末建安时期是一个“世积乱离,风衰俗怨”[3](P1694)的时代,割据战乱和社会动荡给每一个阶层的人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此期的文人以悲天悯人的情怀,感人至深的笔触,共同叙写了这个时代的悲情。他们或睹兵燹祸结,而叹生灵之荼毒;或遭亲故亡殁,而悲年寿之不永;或感出妇怨女,而悯妻孥之孤寡;或赠别送离,而伤独处之凄凉等。此期的作家对寡妇怨女这一特殊的群体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对她们的不幸遭遇也表现出了特有的同情。蔡邕之女蔡琰,因汉末天下大乱,为胡兵所掳,身陷南匈奴十二载,并生有二子。曹操与其父蔡邕生前交好,虑其无后,派使者持玉璧赎回。有感于蔡琰的不幸遭遇,曹丕和丁廙皆作有《蔡伯喈女赋》,蔡琰自己也作有《悲愤诗》叙述自己的苦难经历。阮瑀于建安十七年因病辞世,留下孤儿寡母,曹丕有感于其处境的悲苦而站在当事人的角度作《寡妇赋》以表哀怜。曹丕《寡妇赋序》云:“陈留阮元瑜与余有旧,薄命早亡,每感存其遗孤,未尝不怆然伤心,故作斯赋。以叙其妻子悲苦之情,命王粲并作之。”[8](P1073)丁廙妻亦有《寡妇赋》,从内容上看当为同一事而作。则曹丕、王粲、丁廙妻《寡妇赋》三篇皆作于阮瑀亡殁后不久,当为同题共作。建安中,平虏将军刘勋妻子王宋,嫁入二十余年无子,后刘勋另悦山阳司马氏女,而出王宋。对此,曹丕、曹植、王粲皆作有《出妇赋》,以当事人的口吻,控诉男女婚姻的不公,表达对美好爱情的恋慕和婚姻自由的渴求。
丧幼亡故,哀辞悼赋。汉末建安时期兵燹连年,自然灾害频繁,疫疾流行,人人朝不保夕,生命在时代的灾难面前变得极为脆弱。大致在建安十七年前后,曹植丧长女金瓠,作有《金瓠哀辞》。此后曹丕、曹植又各丧幼子,伤痛之余,曹植作有《行女哀辞》《仲雍哀辞》。挚虞《文章流别论》云:“建安中,文帝临淄侯各丧稚子,命徐幹为之哀辞。”[8](P1905)徐幹、刘桢皆有《仲雍哀辞》《行女哀辞》,辞文已亡佚,仅存目。据题目可知,当为伤悼曹丕、曹植幼子而作。此外,伤悼赋作有四篇,曹丕有《悼夭赋》,其序云:“族弟文仲亡时十一岁,母氏伤其夭逝,追悼不已,余以宗族之爱,乃作斯赋。”[8](P1073)应玚、王粲、杨修亦各作有《伤夭赋》一篇以表哀悼。置酒高会,宾主同欢;歧路惜别,内心伤悲。建安十六年,曹操率大军西征马超、韩遂,兄弟老母及诸文人皆从,曹丕留守邺城。曹丕为大军送行,望着行军队伍在蒙蒙阴雨中渐渐远去,内心倍感凄凉,曹丕写下了《感离赋》,情意深沉,思念不舍之情溢于言表。行军队伍中的曹植、徐幹亦分别作了《离思赋》《哀别赋》以表达离别的忧伤。
(三)登临游览,述迹以写志
除了置酒高会、宴集亭阁之外,登临游览也是邺下文人的重要活动,在这些登临游览活动中也产生了大量诗赋作品。他们或登高台而颂盛德,或临陂池而状物色,或游山川而抒逸志,或览古迹而缅先贤。登临赋类产生最早、艺术成就也最高的作品当为王粲的《登楼赋》。王粲的《登楼赋》大致作于其寓居荆州之时,开启了赋史上登高体物以抒怀写志的先例。此期的同类赋作有曹操、曹丕、曹植父子三人的同题《登台赋》各一篇,曹丕、曹植兄弟各有《临涡赋》一篇,曹丕王粲《浮淮赋》各一篇,杨修、曹植《节游赋》各一篇。这些作品皆同题共作。
建安十二年,曹操北征乌桓,曹丕、曹植兄弟或从。返邺途中,临碣石,观沧海,曹操、曹丕赋父子同作有《沧海赋》各一篇。曹操《沧海赋》仅存一句,无法观其全貌,曹丕《沧海赋》铺写了沧海恢宏的气象和诡谲的奇观。
建安十四年夏,曹操大兴水军,东征孙权,曹丕、王粲从征。大军泛舟万寿,列于淮水之上,刀枪林立,旌旗如云,军容严整,声势浩大。曹丕、王粲见状而作《浮淮赋》,对曹军的阵容进行铺写,盛赞了水军的威严,表达了曹军必胜的决心和愿望。
建安十七年,铜雀台建成,曹操率诸子登铜雀台,命各自作赋。《三国志·魏书·陈思王传》云:“时邺铜爵台新成,太祖悉将诸子登台,使各为赋。植援笔立成,可观,太祖甚异之。”[13](P557)曹丕《登台赋序》:“建安十七年春游西园,登铜雀台,命余兄弟并作。”[8](P1074)另曹操亦有《登台赋》一篇,赋文大都亡佚,今仅存两句。
建安十八年,曹丕、曹植兄弟随曹操还归于谯,拜祭祖坟,游经涡水时,同题共作有《临涡赋》各一篇。曹丕《临涡赋序》云:“上建安十八年至谯,余兄弟从上拜坟墓,遂乘马游观,经东国,遵涡水,相佯乎高树之下,驻马书鞭,作临涡之赋。”[8](P1072)曹植《临涡赋》今仅存题。
王粲、陈琳、应玚、刘桢相继亡殁之后,曹植怀着抑郁的心情与杨修于仲春时节同游北园,二人同作有《节游赋》。见满目春色,绿树芳葩,草长莺飞,因此杨修赋表达了无比欢快的心情。而曹植赋则伤感之情多而欢乐之意少,丧友之痛、失宠之悲,在字里行间显现无遗。
(四)同物共咏,竞采以逞才
愁霖喜霁,时令兴志。汉末建安时期,不仅社会动荡,战乱频繁,而且自然灾害不断,时而烈日暴晒、经久不雨,时而淫雨绵绵、逾月不息,这在此期大量的此类作品中可以得到印证。接连的自然灾害,使得原本就饱受战乱之苦的黎民百姓的生活变得更加艰难。邺下文人并不是只知道宴游高会的酒肉之徒,也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迂腐书蠧,这是一代有责任感、勇于担当的文人。他们时刻关注着外面世界的迁移变化,寒来暑往、阴晴变幻都牵动着他们的悲喜之情。曹植、陈琳、王粲、刘桢、繁钦、杨修皆有《大暑赋》,铺叙了三伏天气下,飞禽走兽、花果草木和人民劳作的千姿百态。此外,王粲、应玚、曹丕、曹植四人同有《愁霖赋》各一篇,叙写了军旅途中遭遇连连阴雨的天气,使得征途的艰难,表达了满怀的愁绪和对艳阳的期盼。又有《喜霁赋》五篇 ,同作者为王粲、应玚、曹丕、曹植、缪袭五人。
方物巧艺,宾主共赏。曹操对西北的军事征伐,重新打通了西域与中原的交通要道,恢复了西域与中原的联系,使得西域大量奇珍异物流入邺城。曹丕是一个对殊方异物、奇珍异宝极为感兴趣的人,而此期的文人亦把收藏、赏玩西域的珍宝作为一种雅趣。曹丕得西域玛瑙勒,作《玛瑙勒赋》以美其宝饰,并命王粲、陈琳同作。庭中种有大秦迷迭香草,曹丕、曹植、陈琳、应玚、王粲同作《迷迭赋》各一篇,以赞其芬芳。获车渠玉石碗,宾主赏玩,曹丕、曹植、陈琳、应玚、王粲、徐幹同题共作《车渠椀赋》各一篇。此类赋作共计14篇,或即情而赋,或宾主共咏,或应命而作,皆可列入同题共作的范畴。邺下文人集团作为一个由宫廷贵族主导的文学群体,除了诗酒为文之外,其他的娱乐活动也极为丰富,弹棊、博弈、投壶、斗鸡等都在当时宫廷里极为流行。此类作品有王粲、曹丕《弹棋赋》各一篇,王粲、邯郸淳《投壶赋》各一篇。器物方面,徐幹有《圆扇赋》,曹植有《九华扇赋》。
草木禽族,触物兴感。赋家感于外物,兴寄以情志,故有咏叹之文。此期以植物为题材的同题赋作共有12篇:见往昔所植径寸之柳已成合抱之材,而叹流光之逝、人事之非,故曹丕、王粲、陈琳、繁钦皆有《柳赋》;见炎夏之槐有葱郁之荣,而感恬淡之致、清润之怡,故曹操、曹丕、曹植、王粲、傅巽皆有《槐赋》;见南国之橘树不荣于铜雀之台,而感草木之难化、情志之不移,故曹植、徐幹皆有《橘赋》。以飞鸟禽族为题材的同题共作赋有14篇:有陈琳、应玚、王粲、阮瑀、曹植《鹦鹉赋》各一篇,皆共咏鹦鹉以自况;曹植、杨修《孔雀赋》各一篇,通过对比孔雀前后的处境,以叹世人待人处事之变;曹丕、王粲《莺赋》各一篇,怜笼鸟之哀鸣而作;曹植、王粲《白鹤赋》各一篇,咏白鹤之素雅以兴寄逸志;曹操、曹植、王粲《鹖鸡赋》各一篇,咏鹖鸡好斗之性以喻勇武之士。
(五)神女嘉梦,陈情以止欲
人神恋慕的书写传统由来已久,屈原《离骚》《九章》《九歌》等楚辞作品中讲述了大量的人神、人鬼之恋的故事,营造一种缥缈虚无、屡求未遂的感伤和哀怨的氛围,通过对性别界限的模糊处理,借以表达对君王的某种政治诉求。其后,宋玉的《高唐赋》《神女赋》,叙楚王与神女的遇合,同样是借神女这一意象以寄托某种策略性的政治论述。再有宋玉《登徒子好色赋》、司马相如《美人赋》,通过叙写楚王与登徒子、章华大夫、宋玉,梁王与邹阳、司马相如等人,对美与丑、情欲和道德的评判和选择,以表明君王对于美色绝对占有的权威,实际上也是臣僚士人在君王权威面前的自我阉割和去势。产生于邺下文学集团的《神女赋》共有4篇,同作者有陈琳、应玚、王粲、杨修。为建安十三年曹操南征荆州,于九月据有江陵后,大宴宾客时所作。陈琳、应玚、杨修从征,皆预此宴,王粲新附,亦与高会。临江陵之水,感巫山神女之事,同题竞采而作。此期神女诸赋,虽然在题材上和表达方式上对前作进行了因袭和摹拟,但不再有过多的政治性意图的书写和参与,而是以集体的力量书写一种情欲的美感,表现出的是一种娱乐性的取向,最后又归于自我的克制。此外,徐幹、缪袭有《嘉梦赋》各一篇,亦属于这一类作品。曹植的《洛神赋》代表了建安时期“神女赋”类的最高水平,其作年可确考为黄初三年,因此已经不属于邺下文学集团时期的范畴了。
(六)军旅纪行,慷慨以任气
由于战乱频繁,邺下文人大多有过军旅征伐的经历,他们跟随曹操或北征乌桓,或南征荆野,或东征孙权,或西征马超等。因此,在赋中,既有记叙行旅所见,又有描写军阵威容、战争场面的内容,或表达驰骋疆场、建功立业的英雄气概,或抒写征途劳苦、憎恨战争的哀怨情怀。可以说军旅征伐是邺下文学集团的集体性活动中仅次于宴游的活动,也是同题共作赋产生的重要的环境。曹操常常鞍马为文,横槊赋诗,很多诗篇都是在征战的间隙所作,曹氏兄弟及邺下其他文人亦多次随军出征,军旅经历的丰富,让他们在征伐的过程中写下了大量的军旅纪行的作品。
建安十二年,曹操北征乌桓,陈琳从征,作有《神武赋》,叙写了曹军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威严勇武。陈琳归附曹操之前,作有《武军赋》,叙写的是随袁绍征讨公孙瓒的经过和情景。应玚有《撰征赋》,或亦作于征乌桓之役。(3)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系应玚有《撰征赋》作年于建安十二年曹操北征乌桓之役。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第361页。俞绍初《建安七子集·建安七子年谱》则谓作年为建安十年,为曹操北征幽州赵犊、霍奴事。中华书局,2012年,第414页。
建安十三年七月至十一月,曹操率军南征,曹丕、王粲(4)王粲原在荆州附于刘表,建安十三年八月,刘表在惊恐中病逝,刘琮代立;九月,王粲等说服刘琮投降曹操,王粲亦归投曹营,因功封关内侯,此后跟随曹操南征。、陈琳、应玚、阮瑀、徐幹、杨修等皆从。在此次南征过程中产生的赋作,有曹丕《述征赋》、阮瑀《纪征赋》、徐幹《序征赋》、王粲《初征赋》可列入南征军旅纪行赋类同题共作的范畴。
建安十四年三月,曹操再征东吴,曹丕、王粲和刘桢随行,曹丕、王粲同题共作《浮淮赋》。从内容上看,曹、王《浮淮赋》二赋不仅有登临游览的色彩,更有军旅纪行的成分。
建安十六年七月,曹操西征马超、韩遂,曹植带病从征,阮瑀、王粲、徐幹、繁钦亦等随行。是役,徐幹、阮瑀作《西征赋》各一篇,王粲作《征思赋》,曹植赋有《述征赋》《离思赋》,繁钦作有《述征赋》。
建安十九年七月,曹操东征孙权,曹植留守邺城,作《东征赋》,铺写六军声威之壮。杨修应教亦作《出征赋》,繁钦亦作《撰征赋》。从内容看,三赋当作于同时。
建安二十年三月,曹操西征张鲁,曹植、陈琳、繁钦从行,曹植、繁钦同作有《述行赋》。
据上文,同题共作是邺下文学集团的辞赋创作的主要形式,而同题共作又生发于各种群体活动和事件中。因而,此期赋作在写作策略、艺术构思等方面都有着显著的集体倾向,但是集体性的风格倾向并没有淹没赋家的个性。就整体而言,邺下文学集团同题共作赋的特点是同中求异与异中有同的并举。具体表现为:题材、事由相同,但组织设计与写作策略上又有所不同;创作动机上,是“为文造情”与“为情造文”双重动机的并存;作品风格上,既表现出集体性风格倾向,又有自我个性的保持;艺术追求上,创作情境相同,但是各自营造的情景却不同。因此,同题共作不是纯粹文字娱乐游戏,也不是刻板的复制和机械的模仿,更不是为了追求千篇一律和整齐划一,而是在集体活动中把游戏娱乐与逞才使气创造性地结合起来,在创作动机、主题意旨、艺术手法、风格倾向等方面整体表现出同中有异与异中有同并峙的特点。这一方面促使赋家改变了写作策略,同时助推了辞赋体式的演变。
四 同题共作对赋体文学的影响和意义
邺下文学集团围绕辞赋开展的同题共作活动不仅成就了当时文坛的盛事,而且对后世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首先,拓展了辞赋创作的题材范围;其次,同题共作这种独特的集体性创作方式也助推了辞赋自身体式的不断演变,辞赋篇幅愈加精炼短小,诗与赋的界限愈加模糊,赋的小品化、律化趋势愈加明显;其三,在集体性的创作活动中辞赋的功能得以拓展,辞赋同题共作的开展形式变得多样化。
(一)拓展了辞赋的创作题材
同题共作作为一种集体性的创作形式,多产生于团体活动开展过程中,因而在创作动机的触发上具有即时性,在创作题材的选取上具有随机性、广泛性。这种创作形式一方面影响了辞赋体式,一方面极大地拓展了创作题材的范围。
汉赋发展到东汉中后期,开始转向小品化。在体制上,由“体国经野,义尚光大”的“鸿裁”转变为“触兴致情,因变取会”的“小制”;[3](P283)在表达方式上,抒情和咏物开始引导整个赋坛的走向。汉末建安时期是一个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时代,随着文学的自觉,此期的赋家不断进行创作的探索和尝试,他们努力地寻求新的自我表达方式,大胆尝试新的文学体式,丰富文学题材,拓展创作视野,在频繁的交流和集体的努力下,终于开辟出了一片广阔的文学新天地。而邺下文学集团则是这种新变的推动者和实践者。从表达方式和题材上看,抒情赋和咏物赋是邺下文学集团乃至整个魏晋赋坛的创作的两大主旋律,而咏物又几乎占据其中的大半壁江山。邺下文学集团成员的咏物赋作题材广泛,体式新颖,他们或状夏云暑雨以寄愁喜,或摹殊方异物以表意趣,或假花草果木以兴情致,或托飞鸟禽族以言逸志,或叙奇巧戏弄以赋闲情,无物不可入赋,无赋不体物色。
从总体上看,邺下文学集团的赋作在题材选择上既有前代的因承和摹拟,又有新题材的摄入和拓展,这是此期对文学史的一大贡献。其对传统题材的因承和摹拟,在抒情赋方面,神女佳人题材诸篇是对自宋玉、司马相如、张衡、蔡邕等以来相关赋作的摹写;游猎赋类诸篇是对汉代畋猎大赋的因承和革新;曹植、王粲、陈琳等《鹦鹉赋》诸篇是对是近代祢衡《鹦鹉赋》的因承;军事纪行赋是对东汉纪行赋的承接;曹植、王粲《酒赋》是对扬雄《酒赋》的因袭和超越;等等。而对题材的拓展,则有登临类,如登台、观海、涉水等;抒情类,伤逝、别离、哀怜等;禽鸟类,如孔雀、鹖鸡、白鹤等;殊方异物类,如玛瑙勒椀、车渠、迷迭香等;草木类如槐树、柳树等;鱼虫类,龙、蝉、龟等;等等。
(二)助推了辞赋体式和写作策略的变化
邺下文学集团关于辞赋的同题共作活动产生的影响还在于助推了赋家写作策略的变化和赋自身体式的演变。从东汉后期开始,汉大赋逐步向小品化趋势转型,而赋的同题共作现象的出现,又进一步推动了小品化的进程。大赋与小赋直观的区别在于篇幅上的长短,而同题共作最重要的规范也在于创作时间上的控制。因此,像汉代赋家那样积年累月、殚精竭虑的创作方式在同题共作的情境下变得不现实。由于同题共作在时间上的限制,整个创作过程需要赋家在较短时间内完成。因此,作赋速度的疾缓、创作时间的长短成了赋家能否参与同题共作的一个重要条件,从而到导致了赋家在作赋策略上的变化,篇幅精短的小赋成了他们必然的选择。通观邺下文学集团相关赋作,可以看出那些凡属于同题共作范畴的赋篇幅都极为精短,一般多则几百字,少则几十字,很少有上千字的,这样的结果是大量短赋、小赋的出现。此外,散体大赋与小赋的区别还在于结构上的调整、艺术思维的转变。赋家虽然放弃了铺陈空间的建构和名物的累叠,但是也因此有了较为充裕的时间和精力来进行艺术层面的润饰,如句子的对仗、音韵的调谐、辞采的精细、情景的处理成了他们着力的重点。由此,赋骈化、律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曾经“义尚光大”、鸿篇巨制的散体大赋,不断演变成骈俪精工的短章小赋,从某种程度上说同题共作也是这一演变过程的重要推动力量之一。
由此,赋家在参与同题共作活动的过程中进行了在写作策略上的调整,最明显的是篇幅上的浓缩,从而导致了小赋、短赋的大量出现。其对赋家艺术构思的转变之影响则更为深远,具体表现在:语言风格上,由巨丽繁复向清丽通脱转变;句式的组织上,对仗工整的句式所占的比重也越来越大,对仗的形式也越来越多;在音韵上,由汉大赋较为宽泛、散漫的押韵方式,开始转变为有意识地调谐音韵,这在曹植的赋作中表现得比较明显,到南朝“永明四声律”的出现和广泛运用,最终助推唐代律赋的形成;在铺叙结构上,赋家逐渐放弃对繁复名物的堆砌和宏大场面的建构,而转向诗化意境的嵌入;在体物的过程中,注重精工地描摹和雕琢,移情于景,力求情景交融,致力意境的营造。这样的转变,带来的是诗与赋文体界限的模糊,赋成为一种名副其实的“两栖”文体。此即所谓赋的诗化。以至于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很多赋只要稍做调整便成为一首诗,或者本身就是诗,在流传过程中难以辨认,而被误认为是诗或赋,这种现象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大量存在。赋在吸收诗歌的艺术手法的同时,诗歌也在借鉴赋的一些表达方式,如赋的铺叙结构、体物手法、对仗技巧等,这对律诗(特别是排律)的形成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此为诗的赋化。但从整个文学发展史来看,赋的诗化还是占主导的。诚然,这种演变的趋势也并不完全是由辞赋的同题共作促成的,但是这种创作方式促使了赋家写作策略和意图的转变,因此赋家把较多的注意力转移到了所谓的形式层面,从而在创作过程中有意或无意中助推了辞赋自身体式的演变。
(三)丰富了辞赋的表达功能
同题竞采、应命献制、即情兴作是邺下文学集团同题共作的主要形式,但是随着辞赋自身的不断发展和演变,同题共作的形式也越来越多样化,同题共作的表达功能得到不断拓展。自邺下文学集团之后,出现了以赋辩论、以赋酬答、诗赋互和等一些新的表现形式,并且对以赋量才提供了一定的参照。
反题作赋。赋家因对某一事物看法不同,而针锋相对地反驳并提出自己的不同见解而作的赋,称之为“反题赋”。反题赋由于在创作事由上一致、内容上直接相关、创作时间上相近,是唱和的一种形式,也可纳入同题共作赋的范畴,可以说这是同题共作的变体。东汉前期围绕都城问题而兴起的京都赋热潮已肇反题赋之端绪。在两晋南北朝时期这种现象开始大量存在。如张华作《鹪鹩赋》盛赞鹪鹩“不怀宝以贾害,不饰表以招累”[8](P1790)的品性,主张无为人生;傅咸针锋相对作《仪凤赋》以诘难,以才智为贵,主张有为人生;贾彪当仁不让,亦作《大鹏赋》反对张华鹪鹩式的人生观,主张以才智远祸避害的积极人生态度。再如陆云作《逸民赋》鄙弃功名富贵,赞美“逸民”隐居避世的高洁情怀;其友何道彦则作《反逸民赋》以反驳陆云的观点,就“仕”与“隐”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陆云又作《逸民箴》辩驳何道彦的看法,阐述自己的观点。
以赋酬答。王芑孙《读赋卮言·和赋》云:“要是同作不和韵,前此邺下七子时相应答,已为导源,特不加‘奉和’字耳。”[14](P288)据王氏所言,则建安邺下时期同题共作的活动已导以赋酬和之源。本文虽然把唱和酬答作为同题共作的重要形式,但是邺下时期只是出现了以赋唱和的端绪,并没有真正直接地以赋赠答的实例,建安邺下倒是出现了大量的赠答诗。命题作赋,应命而献、同题竞采仍然为同题同作赋的主要创作形式。魏晋以后,随着赋的体式不断演变,赋的功能也不断地拓展,赋家开始以赋进行赠答酬唱,是为“酬赋”的真正范畴。这样的一些赋作虽然不是在文学集团的组织下产生的,也没有明确的创作主题,由于唱和的本质是同题共作,因此“和赋”自然也为同题共作的表现形式。如《梁书·陆倕传》载陆倕作《感知己赋赠任昉》,任昉作《答陆倕感知己赋》。又如《梁书·谢征传》载:“裴子野为《寒夜直宿赋》以赠征,征为《感友赋》以酬之。”[15](P747)
诗赋互和。通常,酬唱赠答是以相同的文体为依托展开的,但是浦铣在《复小斋赋话》中辑录了一条特别有意思的以诗和赋的例子:“湘东王作《琵琶赋》,以和世子范旧《琵琶诗》。”[14](P376)以诗和赋,这种跨文体的唱和形式在文学史上已实为罕见,但这充分说明了赋在南朝时期一个值得注意的发展趋势——赋的诗化。无独有偶,同书又辑录了一条相映成趣的例子:“南唐徐常侍铉《木兰赋》,和其兄《拟古诗见寄》。”[14](P376)出现这种“逆反”现象仍是由于诗与赋的界限越来越模糊所致。由于赋的同题共作实践方式的演变和赋家关注重心的转移,进一步促使了赋的诗化与诗的赋化两种相向趋势的凸显。
试赋量才。试赋也是同题共作的一种重要形式。由于赋兼综才学,“会须作赋,始成大才士”[16](P492),一个人才学的高下是可以根据他所作赋的品次来衡量的,于是有了试赋之名。试赋又分为制度性试赋与非制度性试赋,通常所谓的试赋都是指制度性试赋。非制度性试赋在汉代就已经出现,大量命题创作、同题共咏的作赋形式本身就有以赋量才、以赋逞才的属性。汉灵帝设立鸿都门学,以诗赋书画选士,开启了制度性试赋的端绪。建安时期,曹操率诸子登铜雀台,并命曹丕、曹植作《登台赋》,曹操实际上有以此机会来判定诸子才学优次之意,曹植因才思敏捷,所作赋甚为可观,一度被曹操认为是诸子中最可定大事者。同题共作过程中的种种限制,以及参与创作的赋家逞才使气的创作心理,本身也就包含了“试”的成分。但真正的制度性试赋是在隋唐时期科举制度形成以后才产生的,特别是唐代以“诗赋取士”,律赋成了试子应考的重要文体。就创作机制来说,文学集团赋的同题共作活动实际上也为试赋量才提供了组织与运作上的启示和参照。只不过同题共作赋存在随意性、自发性,范畴上更为宽泛,个人发挥的空间更大,体式上无明确限制,更重要的是没有严格的时空限制;而制度性试赋以制度的形式规范了试赋的方方面面,如主题(事由)、时间、场地、赋体形式(韵部、韵数)以及评判的标准都以制度的形式确定下来。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试赋是一种制度化、规范化了的同题共作形式。
结语
作为建安邺下时期赋体文学重要的创作形式,这种创作形式以团体活动和赋家一致关注的物事为创作载体和书写对象,在曹氏父子的大力倡导和身体力行的垂范下,调动了众多赋家的积极参与,刺激了当时辞赋创作的兴盛,他们或应命而献,或唱和往来,或即兴而赋,或同题竞采,造就了一段段文坛佳话,充分体现了这一时期文学的集体自觉。同时,同题共作并非是仅仅是逞才竞采的文字娱乐游戏,赋家在集体创作的过程中,广采创作题材,不断拓展辞赋的书写范围,围绕咏物和抒情两条主线,相互借鉴和超越,巧构铺叙空间,精炼语词字句,追求音律整饬,营建艺术情景。抒情则慷慨悲凉,体物则细致入微,在整体趋同的风格中有自我个性的凸显,在个性的彰显中有着相似的表达诉求和审美倾向,从而同题共作又以集体的努力探讨和实践了辞赋的创作艺术。这种创作形式的开展不仅在当时取得了空前的文学成就,而且成为赋体文学的一种创作传统,为此后的文学团体所追慕和承继,从而不断拓展辞赋的表达功能,丰富了同题共作的表现形式。此外,赋的体式也在这种创作形式的推动下,进一步向骈化、律化演变,使得建安邺下时期成为辞赋发展演变的一个重要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