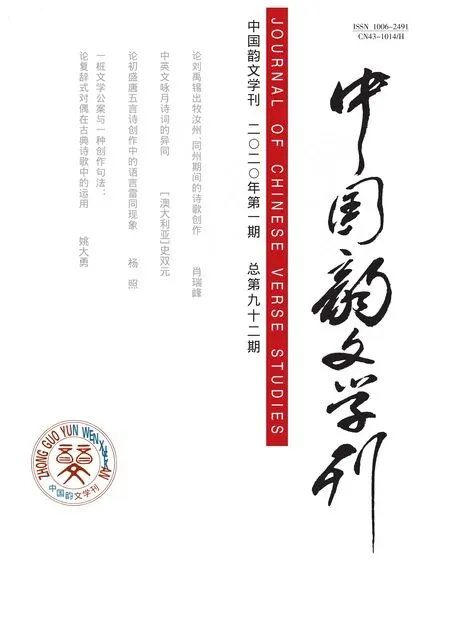杨万里“湖中隐者为陆游”说平议
关鹏飞
(南京晓庄学院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1171)
陆游四十二岁隐居镜湖,已有“渔隐”之志(王质《寄题陆务观渔隐序》)。虽早看穿“元知造物心肠别,老却英雄似等闲”(《鹧鸪天·家住苍烟落照间》),却基于心中仁义,又加养家所迫,不得不征蜀,一场空忙。晚年归居山阴,诗中常写隐士,出现“湖中隐者”形象(1)林岩指出,陆游诗中之“隐”,与其“归休”“退居”有很大差别,前者并非其自我认可[林岩:《晚年陆游的乡居身份与自我认识——兼及南宋“退居型士大夫”的提出》,《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第33页],这也从另一个角度佐证本文的观点。但本文在撰写时尚未拜读此文,故思路不同。。此人善笛避世,“莫知何许人”,可遇不可求(2)陆游开禧元年(1205)作《初夏闲步村落间》:“忽遇湖边隐君子,相携一笑慰余生。”(钱仲联:《剑南诗稿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7册,第3523页)此是“可遇”。同年秋《湖上》有句“欲觅高人竟安在,又闻长笛起沧州”(第3592页),自注云“湖中有隐士,月夜必吹笛,人莫有见者”,此是“不可求”。可遇处少,不可求处多,如“我欲从之何处求”(《道室杂题》其二)、“湖中有啸父,何计得相从”(《穷居》)等。。由于陆游高超的诗艺渲染,在当时即已引起杨万里注意,其《再答陆务观郎中书》认为,湖中隐者当为陆游。钱仲联认为杨说“非无因也”[1](第4册,P2136),于北山《陆游年谱》在湖中隐者的基础上,指出“独孤策”也是陆游虚构的形象(3)于北山先生云:“昔杨万里曾谓务观诗中长啸吹笛之湖中隐者即务观自况……则独孤策或亦务观所塑造之艺术形象而借以自喻者欤?”(《陆游年谱》,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171页)则于先生是比较倾向于认同杨万里之说的,并加以发挥。,李彦灵则借用西方理论,认为是指陆游之超我[2]。前辈时贤对杨说皆有承袭,而没意识到杨说提出之后,陆游以不置可否的态度继续创作“湖中隐者”诗歌,这里面是否存在值得推敲的深因?杨、陆二人以诗歌结交,既是“邢尹不可相见”,又有“韩柳”式的互相成全,“湖中隐者”成为二人交游的重要线索。本文探源溯流,寻究杨说与陆诗的源头,认为杨说源自苏轼对陶渊明诗歌的评论,而陆诗的创作则来自其修道与作诗绾合的家学。尽管杨说没有正确揭示陆诗内涵,却间接地对陆诗后续创作带来影响。这就不仅回答“湖中隐者”是谁,也努力揭示出杨、陆复杂交往对诗歌创作的隐蔽作用。
一 杨说溯源:从“东方有一士”到“湖山有一士”
杨万里与陆游之间,在政治上存在较大分歧,陆游倾向于恢复中原,杨万里倾向于守住现有国土(《千虑策·国势》),使二人在具体问题上差异很大。如评价岳飞,陆游说“剧盗曾从宗父命,遗民犹望岳家军……白首自知疏报国,尚凭精意祝炉熏”(《书愤》),对岳飞抗击金军的功绩极为赞赏,杨万里却批评,其《题曹仲本出示谯国公迎请太后图》说“君不见岳飞功成不抽身,却道秦家丞相嗔”[3](第3册,P995),倾向明显。在晚年进退上,一有机会,陆游不忘为国捐躯,直到死前仍留下“王师北定中原日”的千古绝唱,而杨万里绍熙三年(1192)八月退休之后,认为国事无可为,虽朱熹、赵汝愚等人希望他起来维持时局,都没答应,十四年间隐居不仕,直至离世。袁燮《题诚斋帖》云:“抽身早退,晚节益高。其平生之志欤?”[3](第1册,P3-4)颇得杨万里心曲。在《寄陆务观》诗中,杨万里甚至劝诫陆游也别出来做官(4)诗中有句“不应李杜翻鲸海,更羡夔龙集凤池”,于北山先生指出:“实际上杨万里此诗,系轻信传闻的误解,和陆游的生活、思想不相干。”(《杨万里诗文选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09页)虽有“传闻”之嫌,但正揭示出杨、陆二人在这方面的巨大差别。。由于政见上态度差异明显,二人的交往,纯以诗歌发。如唱和,陆游有《简杨廷秀》,杨万里有《和陆务观惠五言》。也互相评价诗集,陆游有《杨庭秀寄南海集》二首,杨万里亦有《跋陆务观剑南诗稿》二首。因此,杨万里评价陆游诗歌中的“湖中隐者”,便不足为奇。
在杨万里看来,陆游诗中所写的“湖中隐者”就是陆游自己。其《再答陆务观郎中书》云:“某老病余年,今七十有六矣。加我数年,亦可以齐执事矣;来教未得以八十康宁之福嫮我也……近尝于益公许,窥一二新作,邢尹不可相见,既见不自知其位也。独其间有使人怏怏无奈者,如‘湖山有一士,无人知姓名’,又如《寄湖中隐者》是也。斯人也,何人也?谓不可见,则有欲拜其床下者;谓不可闻,则有闻其长啸吹笛者。斯人也,何人也?非所谓不夷不惠者耶?非所谓出乎其类,游方之外者耶?非所谓逃名而名我随、避名而名我追耶?公欲知其姓名乎?请索琼茅,为公卦之,其繇曰:‘鸿渐之筮,实维我氏。不知其字,视元宾之名;不知其名,视言堰之字。’既得是占,颇欲自秘,又非闻善相告之义。公其毋谓龟策诚不能知此事……”[3](第6册,P2879-2880)“鸿渐”指陆羽,指出此人姓陆。“元宾”指李观(韩愈《李元宾墓铭》),指此人之字有“观”。“言堰之字”是“子游”,暗示此人之名。既是卜卦,不必精确符合每个字,故整合此卦内容,意在指出此人即陆游。
杨万里提出此说,从内容和思维上看,受苏轼解说陶渊明“东方有一士”启发。苏轼《书渊明东方有一士诗后》云:“‘东方有一士,被服常不完。三旬九遇食,十年著一冠。辛苦无此比,常有好容颜。’此东方一士,正渊明也。不知从之游者谁乎?若了得此一段,我即渊明,渊明即我也。”[4](第19册,P7567)“东方有一士”出陶渊明《拟古》其五:“东方有一士,被服常不完。三旬九遇食,十年著一冠。辛勤无此比,常有好容颜。我欲观其人,晨去越河关。青松夹路生,白云宿檐端。知我故来意,取琴为我弹。上弦惊别鹤,下弦操孤鸾。愿留就君住,从今至岁寒。”[5](P227-228)苏轼把陶诗中的“东方之士”看作陶渊明自己,与杨万里把诗中的“湖中隐者”看作陆游自己,如出一辙。这不是偶然的。
由前文可知,杨万里书信完成于“七十六”岁时,即嘉泰二年(1202)。此时陆游所写与“湖中隐者”有关的诗歌多达十首,按时间顺序依次为:《夜坐闻湖中渔歌》《题庵壁》《雨三日歌》《村舍杂书》《冬日读白集爱其贫坚志士节病长高人情之句作古风》《斋中杂兴》《寄赠湖中隐者》《闻笛》《长饥》和《道室杂题》。最早者《夜坐闻湖中渔歌》作于庆元元年(1195),但仅说“疑是湖中隐君子”,而最早点明湖中隐者的是庆元三年(1197)《题庵壁》诗后陆游自注:“每风月佳夕,辄有笛声起湖之西南,莫知何人,意其隐者也。”[1](第5册,P2332)杨万里不挑第一首,而以《村舍杂书》中的“湖山有一士”发论,明显与“东方有一士”合。如果说杨万里从周必大处所观如此,何不也像后面所举出的“《寄湖中隐者》”(即《寄赠湖中隐者》)那样列出诗题,而单单挑出跟“东方有一士”句式相同的“湖山有一士”之句?
其次,杨万里文中所云“益公”,指周必大。周必大与苏轼晚年文中所写“海上道人”有关。周必大《跋山谷书东坡圣散子传》云:“山谷作《庞安常伤寒论后序》云:‘前序海上道人诺为之,故虚右以待。’道人指东坡也。今又书《圣散子传》,若安常,所谓得二公而名彰者耶!淳熙庚子正月十五日。”[6](第230册,P298)据考,黄庭坚《庞安常伤寒论后序》云:“其前序,海上道人诺为之,故虚右以待。”[7](P415)因此“道人指东坡也”乃周必大之论。黄庭坚《题东坡书道术后》又云:“东坡平生好道术,闻辄行之,但不能久,又弃去。谈道之篇传世欲数百千字,皆能书其人所欲言。文章皆雄奇卓越,非人间语。尝有海上道人评东坡,真蓬莱、瀛洲、方丈谪仙人也。流俗方以造次颠沛秋毫得失,欲轩轾困顿之,亦疏矣哉。”[7](P646)既云“海上道人评东坡”,则黄庭坚之意,似乎海上道人非苏轼,与周必大异。考苏轼所涉“海上道人”,有《录所作海上道人传以神守气诀示吴子野并跋》:“‘但向起时作,还于作处收。蛟龙莫放睡,雷雨却须休。为有无穷火,长资不尽油。夜深人散后,惟有一灯留。’丁丑正月十九日,录示子野,向尝论其详矣。”[4](第20册,P8881)由此可见,苏、黄二人皆未指明苏轼与“海上道人”之关系(5)故后人常混淆,如张振谦《道教文化与宋代诗歌》第九章“道教对宋代诗人影响的个案研究”第一节“苏轼与道教”中,一方面指出苏轼曾号“海上道人”(《道教文化与宋代诗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第321页),另一方面又在“苏轼与道士交游考述”中把“海上道人”列为与苏轼交游者(第333页)。,周必大却极感兴趣,原因盖出于苏轼对陶渊明的评论。苏轼既这样评论别人,自不能不让后人如此评他。当有此共同爱好的周必大与杨万里一起欣赏陆游新诗的时候,不放过与“海上道人”类似的“湖中隐者”也就不足为奇了。周必大《跋山谷书东坡圣散子传》作年早于杨万里提出此说时间,则杨万里或间接受周必大影响。但二人皆有得于东坡,则无疑问。
苏轼之所以这样评价陶渊明,意在指明自身与陶渊明之紧密联系,即文中所言“我即渊明,渊明即我”(6)文中所说的“‘我’即渊明,渊明即‘我’”的“我”,可否指《拟古》诗中“我欲观其人”“知我故来意,取琴为我弹”的“我”?不是没有这种可能,然而,古典诗歌中的“我”多为抒情作者自己,此一点似不必专门在文中指出。故此处之理解,仍以“我”指写这篇文章的苏轼。,是一种欣赏乃至追慕的表现。这与杨万里对陆游的欣赏乃至追慕一致。诚然,杨万里与陆游的诗歌主张有差别,但无妨于欣赏彼此的诗歌。他们不仅积极评价对方,而且有强烈的“并肩战斗”意识。陆游在《喜杨廷秀秘监再入馆》中首倡此论:“公去蓬山轻,公归蓬山重,锦囊三千篇,字字律吕中。文章实公器,当与天下共。吾尝评其妙,如龙马受鞚。燕许亦有名,此事恐未梦。呜呼大厦倾,孰可任梁栋?愿公力起之,千载传正统;时时醉黄封,高咏追屈宋。我如老苍鹘,寂寞愁独弄。杖屦勤来游,雪霁梅欲动。”[1](第3册,P1591)诗中所言“龙马”“燕许”,皆暗示杨、陆。杨万里《和陆务观见贺归馆之韵》则云:“君诗如精金,入手知价重。铸作鼎及鼒,所向一一中。我如驽并骥,夷涂不应共。难追紫蛇电,徒掣青丝鞚。折胶偶投漆,异榻岂同梦。不知清庙茅,可望明堂栋。平生怜坡老,高眼薄萧统。渠若有猗那,心肯师晋宋。破琴聊再行,新笛正三弄。因君发狂言,湖山春已动。”[3](第3册,P1375)前皆谦不敢当之意,至“平生怜坡老”句下,始做正面回应。“坡老”即苏轼,他对萧统所编《文选》(尤其是选陶渊明之作较少)意见很大。对此,杨万里以“怜”字(意即“爱”)表示赞同,并补充论证说,如果萧统心中有《诗经·商颂·那》的盛美之德,自不会师法晋宋;言下之意,萧统在《文选》选篇中“厚今”(“今”即“晋宋齐”等萧梁所处时代不久前之作品),是心中没有盛德,苏轼批评有理。就全诗看,杨万里至此才点明,心有盛德的人,自会“千载传正统”“高咏追屈宋”,暗示对陆游之说的赞同。在《答陆务观郎中书》中,杨万里指出陆游对他的妒忌和推崇,其实不在于真妒忌或推崇,而是学韩柳,彼此抑扬,共传千古:“大抵文人之奸雄,例作此狡狯事,韩之推柳是已。韩推之,柳辞之者,伐之也。然相推以成其名,相伐以附其名。千载之下,韩至焉,柳次焉,言文者举归焉。仆何足以语此?然亦岂不解此?”(7)辛更儒:《杨万里集笺校》,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6册,第2865~2866页。个别断句、标点有误,参考韩立平《同岑异苔:陆游、杨万里诗坛地位考索》(《浙江学刊》2010年第3期)一文。此韩柳之说虽以玩笑发之,配以“燕许”“龙马”之说,深意自见。一方面,杨万里对陆游的钦佩与苏轼钦佩陶渊明类似,从而把苏轼之论移到陆游身上,无可厚非;另一方面,杨万里深刻意识到陆诗的价值所在,也深刻体味到文人之间互相倚重的传播之道,那么通过评价陆游诗歌而使彼此引起后人关注,可谓用心良苦。
尽管苏轼对陶渊明的评价对后世影响很大,但苏轼的评价一定正确吗?袁行霈认为:“此东方之士乃设为理想中人,非固定指某人,亦非自指。”[5](P228)较为中肯。杨万里对陆游“湖中隐者”的评价,是否也不一定确切呢?通过分析陆游此系列诗歌的来源,我们遗憾地发现,杨万里的评论颇有问题。
二 陆诗缘起:修道与作诗绾合的陆氏家学
跟杨万里一样,陆游也深受苏轼影响,如诗歌创作方法,陆游《跋〈东坡诗草〉》云:“ 东坡此诗云:‘ 清吟杂梦寐, 得句旋已忘。’固已奇矣。晚谪惠州,复出一联云:‘ 春江有佳句, 我醉堕渺莽。’则又加于少作一等。 近世诗人,老而益严,盖未有如东坡者也。”[8](第10册,P164)但陆游最欣赏苏轼处,在于其始终不衰的为国为民气节,《跋东坡〈祭陈令举文〉》云:“东坡前、后集祭文凡四十首,惟祭贤良陈公辞指最哀,读之使人感叹流涕。其言天人予夺之际(8)苏轼《祭陈令举文》:“呜呼哀哉,天之生令举,初若有意厚其学术,而多其才能,盖已兼百人之器。既发之以科举,又辅之以令名,使取重于天下者,若将畀之以位。而令举亦能因天之所予而日新之,慨然将以身任天下之事。夫岂独其自任,将世之士大夫,识与不识,莫不望其如是。是何一奋而不顾,以至于斥,一斥而不复,以至于死,呜呼哀哉。天之所付,为偶然而无意耶?将亦有意,而人之所以周旋委曲辅成其天者不至耶?将天既生之以畀斯人,而人不用,故天复夺之而自使耶?”(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苏轼全集校注》,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8册,第6994页)对比可见,陆游对苏轼之说有所发挥。,虽若出愤激,然士抱奇材绝识,沉压摈废,不得少出一二,其肝心凝为金石,精气去为神明,亦乌足怪!彼愦愦者固不知也。绍熙甲寅(1194)十二月二十九日,笠泽陆某谨书。”[8](第10册,P196)庆元三年(1197)陆游写《书志》,果用此意:“肝心独不化,凝结变金铁,铸为上方剑,衅以佞臣血。”[1](第5册,P2310)那么当陆游在写“湖山有一士”的时候,受“靖节先生”陶渊明的“东方有一士”之影响,受苏轼对它的全新评论之启发,当无疑义。
问题在于,可不可以把“湖山有一士”一诗的源头推广到所有涉及“湖中隐者”的诗篇中去?从各方面看,陆游是不赞成的。首先,在杨万里评论之后,陆游陆续创作出多篇有关“湖中隐者”的诗歌,包括《入局》《访隐者不遇》《初夏闲步村落间》《湖上》等,在这些诗歌中,多处出现与杨说抵牾者。比如,杨说“谓不可见,则有欲拜其床下者;谓不可闻,则有闻其长啸吹笛者”,这是就《寄赠湖中隐者》“无地得申床下拜,夜闻吹笛渡烟津”生发而来,此处尚且是“欲拜”,有意而已,并非实现;此后的《初夏闲步村落间》,陆游则“忽遇湖边隐君子,相携一笑慰平生”。如是陆游自身,如何“忽遇”“相携”?其次,陆游对注诗的要求极严,《跋柳书〈苏夫人墓志〉》云:“近世注杜诗者数十家,无一字一义可取。盖欲注杜诗,须去少陵地位不大远,乃可下语。不然,则勿注可也。今诸家徒欲以口耳之学,揣摩得之,可乎……然予为此言,非独触人,亦不善自为地矣。”[8](第10册,P281)如果把杨万里此说看作友朋间的玩笑,自不必严肃对待,一旦影响学界众人,定其是非之际,则应视作注陆游诗。然杨万里此说之提出,皆“揣摩得之”(9)如:“非所谓不夷不惠者耶?非所谓出乎其类,游方之外者耶?非所谓逃名而名我随、避名而名我追耶?公欲知其姓名乎?”等。,难怪陆游不置可否。
实际上,陆游创造“湖中隐者”形象与其家学密切相关。杨万里仅就陆游“湖中隐者”的几首诗得出结论,难免以偏概全;但没有熟究其诗背后的家学渊源,是杨说失误的根本原因。下面着重论述此类诗歌所涉陆游家学的两个方面:一是陆氏家学修习道家、道教的传统,二是道家道教神仙思想在诗歌中的呈现。阐明此论,则“湖中隐者”真实内涵亦迎刃而解。
陆游与道家、道教关系密切,张振谦论之已详[9](P365-374),这里着重分析与本论题有关之部分。我们发现,陆游家学与道家、道教关系密切的传统中,很多与仙人有关。且其祖上多有求仙之举,不乏绝类湖中隐者之事。如被陆游奉为始祖的陆通,字接舆。《庄子·逍遥游》记载云:“肩吾问于连叔曰:‘吾闻言于接舆,大而无当,往而不返。吾惊怖其言,犹河汉而无极也;大有径庭,不近人情焉。’连叔曰:‘其言谓何哉?’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疠而年谷熟。’吾以是狂而不信也。”[10](P26-28)《庄子·应帝王》亦有肩吾与陆通的对话,多是陆通开导肩吾者。此或与《岁晚幽兴》自注“先太傅亲受《三住铭》于施肩吾先生”[1](第6册,P3264)以及《老学庵笔记》卷五所记载施肩吾弟子方五授道要给陆轸有关:“先太傅自蜀归,道中遇异人,自称方五。见太傅曰:‘先生乃西山施先生肩吾也。’遂授道要。施公,睦州桐庐人,太傅晚乃自睦守挂冠,盖有缘契矣。”[11](P65)作为陆游高祖,陆轸七岁所作之诗,或对陆游有所影响(10)见陈鹄《西塘集耆旧续闻》卷一:“陆太傅轸,会稽人,神采秀异,好为方外游。七岁犹不能语,一日乳媪携往后园,俄而吟诗曰:‘昔时家住海三山,日月宫中屡往还。无事引他天女笑,谪来为吏在人间。’”(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295页)。无论是神人还是异人,都充满文学想象后的仙气,与“湖中隐者”类似。
由于深受道家、道教影响,陆游认为神仙是存在的,“神仙元可学,往矣不须疑”(《道室秋夜》)。但其所谓神仙,并非世人想象中的神仙,而是活在人间,如“地行仙”一般,这在其祖母所遇道人身上有体现:“祖母楚国夫人,大观庚寅在京师病累月,医药莫效,虽名医如石藏用辈皆谓难治。一日,有老道人状貌甚古,铜冠绯氅,一丫髻童子操长柄白纸扇从后。过门自言:‘疾无轻重,一炙立愈。’先君延入,问其术。道人探囊出少艾,取一砖灸之。祖母方卧,忽觉腹间痛甚,如火灼。道人遂径去,曰‘九十岁’。追之,疾驰不可及。祖母是时未六十,复二十余年,年八十三,乃终……世或疑神仙,以为渺茫,岂不谬哉。”[11](P61-62)在陆游看来,此“道士”无异于神仙。访仙也是陆游热衷之事,“饱知句曲罗浮路,不访初平即稚川”(《养气》)。初平指王子敬,稚川指葛洪。又说:“谿父园公殊未见,颓然谁与共忘形?”(《道室即事》)“谿父”指《列仙传》中的仙人,“园公”为商山四皓之一。有时也以仙人来访作为得道的标志之一:“青城山上官道人……忽自语养生曰:‘为国家致太平,与长生不死,皆非常人所能。然且当守国使不乱,以待奇才之出,卫生使不夭,以须异人之至。不乱不夭,皆不待异术,惟谨而已。’”[11](P12)
另一方面,对陆游影响极大的陆龟蒙(11)陆龟蒙自编《笠泽丛书》,陆游取以为号,更有多篇诗文使用与陆龟蒙有关的典故,如《村舍杂书》其一:“我本杞菊家。”引用陆龟蒙《杞菊赋》。正因为陆游对陆龟蒙推崇备至,因此,当杨万里提倡晚唐诗,而又不满于陆游批评晚唐诗的时候,便以陆龟蒙为例,如《读笠泽丛书三首》其一:“笠泽诗名千载香,一回一读断人肠。晚唐异味同谁赏,近日诗人轻晚唐。”尽管莫师砺锋在《论陆游对晚唐诗的态度》中指出,“陆游斥责晚唐的话并不是针对杨万里的”(莫砺锋:《唐宋诗歌论集》,凤凰出版社,2007年,第435页),但杨万里批评“近日诗人轻晚唐”是否针对陆游,俟考。目前来看,可能性较大。,正式把此类神人、异人写入诗歌,其《四明山诗》诗序云:“谢遗尘者,有道之士也。尝隐于四明之南雷。一旦访予来,语不及世务,且曰:‘吾得于玉泉生,知子性诞逸,乐神仙中书,探海岳遗事,以期方外之交。虽铜墙鬼炊,虎狱剑饵,无不窥也。(已上八言谢语,不知所谓者何。一云出《隐中书》。)今为子语吾山之奇者……凡此佳处,各为我赋诗。’予因作九题,题四十字。”[12](第18册,P7157)此为组诗,虽名为写“四明山”胜景,实则以“有道之士”谢遗尘发之,此类有道之士,亦乃陆游欲求者。陆游求访之心很重,此类诗句如“囊中幸有黄庭在,安得高人与细评?”(《春晚》)在“湖中隐者”系列诗歌中亦有内证,如“清宵定许敲门否,拟问黄庭两卷经”(《简湖中隐者》)。
当时陆游所居附近确有道士,如会稽舜山的老叶道人[11](P30)。绍熙三年(1192)所作《赠镜中隐者》亦云:“小筑林间避世纷,不妨野叟是知闻。来游喜有檝迎我,归卧岂无云赠君?得鹿梦回初了了,吠獒声恶尚狺狺。从今雪夜频相过,纸帐蒲团要策勲。”[1](第4册,P1811)此宜可证陆游“湖中隐者”形象并非完全虚构。
据陆游“湖中隐者”系列诗歌自注可知,湖中隐者住于镜湖西南[1](第4册,P2198)。为什么选择镜湖西南?盖与羽化登仙有关。其《镜湖西南有山曰外山,民某氏居之,其居少西小潭,受飞泉群山环合,真异境也。为作短歌》云:“汉东九十九重冈,武都九十九脉泉,岂如君家环翠阜,小潭佩玦声锵然。我欲从君乞庵地,开轩下看泉中天。金丹九转太多事,服水自可追飞仙。云孙相遇不相识,笑问尘世今何年。掬泉弄月清啸罢,却折玉井秋风莲。”[1](第4册,P2198)“玉井莲”,钱仲联引《华岳志》卷一云:“玉井,在上宫前五尺……玉井生千叶白莲,服之令人羽化。”[1](第2册,P874)玉井莲意象,在陆诗中不止一见,另如“行矣秋风高,去采玉井莲”(《书怀》)等。而陆游于镜湖西南发现神仙之地,为“湖中隐者”增加神仙气息。
这些现实所有的道人和胜景,与陆游家学中存在的虚无缥缈的神人、异人结合,催化出带有浓重神仙气息的“湖中隐者”形象。这在陆游此类作品中随处可见。仙人的特点在于超越时间,其寿命与人相比皆为长寿,故陆诗常写此点。如“似生结绳代,或是葛天民”(《冬日读白集爱其贫坚志士节病长高人情之句作古风》)、“何当五百岁,相与摩铜狄”(《斋中杂兴》)、“湖中有隐士,或谓千岁人”(《乙巳秋暮独酌》)等。又仙人常养药飞升,陆游亦写到此类之事,如 “甘泉胜牛乳,灵药似人形。处处筇枝健,年年鬓色青”(《简湖中隐者》)等。当然,在陆游的观念中,神仙与人的差异并非很大,在地上也可成仙,谓之“地行仙”,如“三百里湖随意住,人间真有地行仙”(《舟中戏书》)等。此类特征,皆可内证出“湖中隐者”的神仙特点。
由此可见,“湖中隐者”并非确有其人,也不能等同陆游自己(12)尽管陆游自己渴望修道成功,也曾自我幻化,如绍熙四年秋《有客》云:“有客隐华山,学道忘岁月。灵苗生绝壁,光景中夜发。属刂根食之尽,倏尔换金骨。通籍虎豹阍,日预通明谒。绿章奏封事,误字坐责罚。后身幸不忘,去日苦飘忽。白首三入朝,未省及黔突。方逃申公钳,已取卞和刖。福微不盈眦,罪众几擢发。上天岂怜之,寸步使屡蹶。拔其利欲根,还之山水窟。洗心谢宿愆,世事等闽粤。”但这都是艺术处理之后的形象,不能等同他自己。,而是各方因素综合起来之后,在陆游作品中虚构、塑造出来的富有仙道气息的诗歌形象。杨万里径指其为陆游自身,实则有吹嘘、玩笑之嫌。
三 不是回应的回应:陆游后续此类创作的转变
遍检现存陆游作品,杨说出现后,陆游并没直接回应。这或许跟杨万里、陆游对“隐士”态度不同有关。先看杨、陆二人隐士观念差别所在。杨说对隐士有大段定义:“非所谓不夷不惠者耶?非所谓出乎其类,游方之外者耶?非所谓逃名而名我随、避名而名我追耶?”认为隐士乃方外之士,与朝政无关。这与其早年的观点一致。杨万里曾写《读严子陵传》:“客星何补汉中兴,空有清风冷似冰。早遣阿瞒移汉鼎,人间何处有严陵。”周汝昌对此有精彩论述,认为杨万里讽刺隐士:“犹如说:若国都亡了,看你们这般‘高人’还往哪里隐居垂钓去。”[13](P73)此正可看出,在杨万里眼中,隐、仕泾渭分明,不容混淆,因此要隐居就不关心朝政,要关心朝政就不隐居。杨万里本人也身体力行,中年立朝,像苏轼一样奋不顾身,一旦晚年隐居,至死不出。中间虽不一定全忘国事,究竟不占主流。陆游的隐士观念与杨万里相反。他曾说:“客星犹不作,肯应少微星。”(《简湖中隐者》)“客星”典出《后汉书·严光传》,少微星又名处士星,钱仲联注引《晋书·谢敷传》,全句意谓还没有像严光那样成为帝王之友,怎肯以处士身份死去?“湖中隐者”虽是隐者,却关心国事。陆游本人确实晚年还出山,身体力行着他的隐、仕不截然区分的观念。如“士生蓬矢射四方,扫平河洛吾侪职。湖中隐士倘可逢,握手与君谈至夕”(《雨三日歌》),更把报效国家作为预设中的谈资,要与“湖中隐者”切磋。陆游直到去世还不能忘情祖国,真可谓“假隐士”。陆游隐居生活中常因关心朝政而破坏修道(13)体现在陆游诗中便是修道与“钓鱼”间的矛盾。《道室杂咏》说:“采药不辞千里去,钓鱼曾破十年功。”此类钓鱼,含有杀生破功之意,实则亦用姜太公钓鱼的典故。,这在一定程度上促使陆游塑造“湖中隐者”,因为“湖中隐者”能做到“有竿不钓鱼”的境界(《乙巳秋暮独酌》),而这正是陆游缺乏的。
尽管陆游没直接回应杨万里之说,却在杨说提出后,在“湖中隐者”系列诗歌的创作中做出相应调整,可视作“不是回应的回应”。这主要体现在陆游强调“湖中隐者”身份的侧重点发生变化。为便于分析,特将陆游“湖中隐者”诗歌按年代制表如下:

表1 陆游之“湖中隐者”诗歌
从表1可以发现,“湖中隐者”诗歌,以杨说提出之年为分界线,前后各有十首。杨说之前,多作于夏日,共六首;杨说之后,多作于秋日,共五首。从诗歌所写内容与体制上看,有如下变化。
首先,在强调“湖中隐者”的未知身份及不可接触基础上,出现相携谈心之举。应该说,在陆游此系列诗中,“湖中隐者”形象前后有一致性,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姓名难知,如“湖山有一士,无人知姓名”(《村舍杂书末首》)、“镜湖有隐者,莫知何许人”(《冬日读白集……作古风》其九)、“姓名莫能知,况可得疏亲”(《乙巳秋暮独酌》)等。二是不可触及,难以晤谈,如“湖边吹笛非凡士,倘肯相从寂寞中”(《题庵壁》其一)、“湖中隐士倘可逢,握手与君谈至夕”(《雨三日歌》)、“我欲往从之,烟波浩无津”(《冬日读白集……作古风其九》)、“何当五百岁,相与摩铜狄”(《斋中杂兴其七》)、“无地得申床下拜,夜闻吹笛渡烟津”(《寄赠湖中隐者》)、“一曲忽闻高士笛,临窗和以读书声”(《闻笛》)、“烟波一叶会当逝,吹笛高人有素期”(《长饥》)、“一声清啸去已远,我欲从之何处求”(《道室杂题》其二)、“怅望沧波友,弓旌岂易招”(《入局》)、“笛声尚近人已遁……何如小住共一尊”(《访隐者不遇》)、“欲觅高人竟安在,又闻长笛起沧州”(《湖上》)、“湖中有高士,折简恐难招”(《村游》)、“湖中有啸父,何计得相从”(《穷居》)、“清宵定许敲门否,拟问黄庭两卷经”(《简湖中隐者》)等。以上资料,有些从正面写难以面见,有些则以希冀之语表达相见之意,实则仍未谋面。这两个特点,贯穿此系列诗歌,且相辅相成,共同组成“湖中隐者”最重要的两个特征。
杨万里对这两个特征的把握极为准确(14)他在《再答陆务观郎中书》中说:“独其间有使人怏怏无奈者,如‘湖山有一士,无人知姓名’,又如《寄湖中隐者》是也。斯人也,何人也?谓不可见,则有欲拜其床下者;谓不可闻,则有闻其长啸吹笛者。”检出“无人知姓名”,又说“不可见”“不可闻”,都可看出杨万里对这两个特征的准确把握。,但杨万里把重心放在获知其名上,而对能否触及,则一笔带过。这当然是为论述其观点服务,因为一旦关注能否触及,则“湖中隐者”与陆游是否为一人的说法就无从论证。或者不如说,正因为杨万里如此误读陆游之诗,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而通过上面举例可以看到,陆游对姓名的关注只有三例,对能否相见相谈则报以浓厚兴趣,多达十四处。因此杨说出现之后,陆游一举打破与“湖中隐者”不可相见的预设,而在1205年写下《初夏闲步村落间》,其中描述陆游终得所愿,与其相会:“忽遇湖边隐君子,相携一笑慰余生。”[1](第7册,P3523)这无疑是以诗歌的方式回应杨说(15)但这样一来,会不会破坏“湖中隐者”形象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保持神秘性,只不过便于渲染,归根究底还是要看德行。从陆游诗中多次提到的“幽人岂知我,月夕闻吹笛”(《斋中杂兴》其七)等来看,陆游尽管与其久难谋面,但不代表“湖中隐者”不知晓陆游,二者之间所谓的相见,并非留意于是否相逢,而在心灵是否相通。在心灵相通的前提下,见与不见,实则不过是施于庸人的障眼法而已,别无深意。。
其次,在“湖中隐者”的基础上,创造新的“太湖隐者”形象。据钱仲联考订,《寄太湖隐者》一诗“嘉定元年夏作于山阴”,钱先生云:“太湖隐者,犹诗中常见之镜湖隐者,皆托言,非实有其人。”[1](第8册,P4195)所言甚是。太湖隐者形象的塑造,是在“湖中隐者”基础上进行的,他也有神仙气息,如“有时跨蛟鲸,指撝雷雨奔”。也有隐仕不分的观念,如“郦生吏高阳,马周客新丰,从来豪杰士,大指亦略同”。更有难以触及却与陆游心通的特点,如“具区古大泽(16)“大泽”或许是陆游由镜湖联想到太湖的重要原因,他曾自称“我居大泽中”(《村舍杂书》其九),此处大泽自然是指镜湖。而从太湖与镜湖在陆游诗中皆可称作大泽来看,这恰是二者可通之处。,烟水渺千里,可望不可到,中有隐君子……嗟我独何人,乃许望颜色;逝将从之游,变化那得测”。问题是,既然在山阴,陆游何以会联想到太湖?我们不能肯定地说,是因为杨万里将“湖中隐者”指实为陆游,而他又居于镜湖,所以有意跳开镜湖。但从所存太湖隐者诗歌本身来看,因为这首诗歌的创作,使此类隐者的身份遍布长江以南,他们虽隐居江湖,而心系天下。考虑到南宋特殊的政治因素,疆域又集中于多水之南方,陆游通过诗歌对隐士的身份进行重新定义,无疑有助于联合更多的江湖隐者。这既能消除杨万里把此类隐者指实为陆游所造成的狭隘性,也能敦促更多的江湖隐者承担起应有的社稷重任。这与孔子所云“礼失求诸野”有异曲同工之妙。
最后,从诗歌体制上看,“湖中隐者”从侧杂于组诗,转为多呈单篇题咏。在杨说提出之前,“湖中隐者”诗歌隐没于五组诗中;杨说提出之后,则仅剩一组诗,其余皆单篇独行。这也可以看出,经杨说提醒后,陆游对“湖中隐者”的形象塑造变得更自觉。考杨说前涉及“湖中隐者”的五组诗,分别为《题庵壁》其一、《村舍杂书》末首、《冬日读白集……作古风》其九、《斋中杂兴》其七、《道室杂题》其二。此五组诗,皆为一个整体,抒情主人公为“我”(即作者陆游),而“湖中隐者”侧杂其间,遂与“我”纠缠不清。尤其是《村舍杂书》,颇为模仿陶渊明诗体,如第一首:“今年夏雨足,不复忧螟虫。归耕殆有相,所愿天辄从。”[1](第5册,P2510)与陶渊明“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绝类。又如第九首“浮家亦可乐,何必爱吾庐”[1](第5册,P2513),更是翻案陶诗“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在这样的背景下,末首“湖山有一士”确实是学陶渊明“东方有一士”,杨万里所说不误。但在杨说出现之后,陆游有意识地规避此类,组诗中唯有《秋晚杂兴》其八颇有嫌疑。但《秋晚杂兴》中,有三首诗分别有自注,其中第八首自注“隐者”,第九首自注“禹庙”,第十首自注“项羽庙”,这三首虽归于组诗之下,实则自注宛如小标题,独立性较大[1](第7册,P3964),与杨说之前的五组诗差别明显。
从以上三个变化可以看出,在杨说提出后,作为同时代且互有交往的诗人陆游,不能不做出回应,哪怕某些回应并非直接的。他通过继续创作、创新此类诗歌,不仅有力回应杨说,而且促进此类诗歌的发展:第一,使主题更为明确。在杨说之前,陆游写“湖中隐者”一再重申不可触及,却又想晤面,杨说之后,为破除“陆游等于隐者”之论,陆游不得不使二者相携,却不必多说,“一笑”而已,便已明了彼此心迹,使交心、契心主题更显豁。第二,使隐者内涵更为丰富。在杨说之前,隐者局限于镜湖,杨说之后,为撇清自身、隐者、镜湖三者的有机关联,陆游别出心裁地创造出太湖隐者形象,使诗中隐者内涵不仅扩大涵盖面,更增加号召江湖隐者心系天下的感染力。第三,使隐者系列诗歌更为独立。在杨说之前,湖中隐者常包含在各类与抒情主人公“我”密切相关的组诗中,杨说之后,陆游基本斩断此类组诗,使用单篇题咏的方式,“湖中隐者”的身份也就更独立,更饱满,从而完成“湖中隐者”形象的塑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