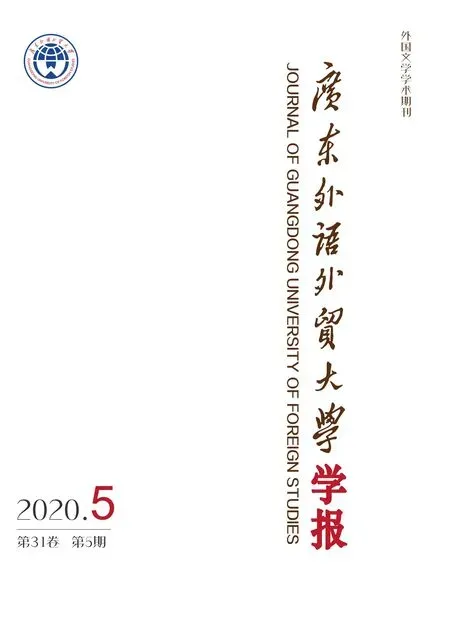数字技术与权力:《女巫的子孙》的现代复仇
罗靖
引 言
在加拿大女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1939-)的创作经历中,莎士比亚应该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譬如她对《李尔王》和《麦克白》部分情节的戏仿之作《猫眼》(Cat’sEye,1988);与《哈姆雷特》形成互文的《格特鲁德的反驳》(GertrudeTalksBack,1992);为纪念莎士比亚诞辰四百周年创作的歌剧剧本《夏日的喇叭》(TheTrumpetsofSummer,1964)(傅俊,2003:200-201);为纪念莎士比亚逝世四百周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女巫的子孙:威廉·莎士比亚〈暴风雨〉的改写》(Hag-Seed:WilliamShakespeare’sTheTempestRetold,简称《女巫的子孙》)①。事实上,当二○一六年《女巫的子孙》出版时,阿特伍德已值七十七岁高龄,在古稀之年挑选《暴风雨》作为改写文本显然绝非偶然:一方面,早在《与逝者对话:作家谈写作》中,阿特伍德(Atwood,2003:102-103)就援引《暴风雨》,直言“普洛斯彼罗扮演了上帝的角色……凯列班并非没有洞察力”;另一方面,她在一些著作中直接注入了《暴风雨》的细节信息,如布克奖获奖作品《盲刺客》(TheBlindAssassin,2000),作品《在其他的世界:科幻小说与人类想象》(InOtherWorlds:SFandtheHumanImagination,2011)。由此可见,阿特伍德对《暴风雨》的关注由来已久,这极可能是因为《暴风雨》内死里逃生的求存情景,与她对“加拿大的中心象征……是生存”(艾特伍德,1991:23)的思考内在契合。基于此,当《暴风雨》这个英式复仇故事改写并呈现于加拿大文化时,作者在预设的“复仇与宽恕”命题之下,不免将加拿大文学脉络中显著的“生存”特色投射其中,叙述了戏剧导演菲力克斯(Felix)在相继遭遇亲人离世和下属算计失业后,“逃往”乡村隐姓埋名十二年,最终绝处逢生复仇成功的故事(Atwood,2016)。《女巫的子孙》被表述为一个非暴力的复仇故事,并在情节设计上与《暴风雨》构成了明显的互文关系;不仅如此,文本结构还借用了创作《神谕女士》(LadyOracle,1976)的手法,通过对人物职业身份的巧妙设定来呈现“戏中戏”的合理性,将戏剧《暴风雨》嵌套进菲力克斯的复仇中,实现两个文本的彼此勾连。
相比于《暴风雨》,《女巫的子孙》的明显不同之处在于王权斗争被改写为日常生活叙事,复仇者身份从贵族回归至“平民”,正如雷蒙德·威廉斯(Williams,2006:33)所言:“这不是关于王子的死亡,而是更加个人化、普遍化”。文本中个人回忆性叙述鲜活地呈现为一部中产家庭溃败史,主人公中年失业的关键情节,既是对当下大量工作缺乏稳定性的真实写照,又难免不让深陷职场的读者产生代入感。作为阿特伍德为数不多的以男性为主角的小说之一,《女巫的子孙》通篇男性群体形象的形塑,超出了不少读者的预期,作品呈现出那些看似坚强的男性背后所承受的无助和愤怒,因为在现代社会,“并非所有男人都能成长为超人……小说中的男性人物的混乱、绝望、愤怒和矛盾并不仅仅存在小说之中,也存在于外面真实的世界里”(阿特伍德,2012:62)。尤其是文本中大量的心理描写和日记体形式的运用,使文本更加接近真实。《女巫的子孙》出版之后,迅速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有学者认为“为了书写难以预测的情景,阿特伍德放弃了她惯常的反面乌托邦书写”(Percec,2018:295);“这部作品并没有作家以往作品的那般犀利……似乎也并没有那么明显地让边缘/女性发声说话,表达她特有的人文关怀”(孔小溪,2017);另外有学者认为作品中囚犯的创造力、行动与解读表征了他们的政治诉求(Jayendran,2020:15,19);《女巫的子孙》“以一种讽刺式的幽默来鞭挞社会现象,体现了一名有良知的当代公共知识分子的人文思想”(袁霞,2017:65)。这些观点不一的评论无不提示着改写文本在保留源文本复义风格时,自身所具有的丰富性与复杂性。由于《女巫的子孙》是近些年的新作,所以目前只有少数学者对它展开了研究②,这意味着文本的文化政治内涵尚未得到充分挖掘。那么,在书写日常经验时,作者关注了哪些边缘群体和社会现实?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个现代复仇故事中,话语符号“女巫的子孙”背后的“女巫”指的又是什么?本文将以这些问题为出发点,进行深入探讨。
复仇之因:“公平”的投票机制与资本权力
《暴风雨》中,普洛斯彼罗公爵统治米兰城邦的合法性,来自以血缘为基础的世袭制和长幼有序的等级制,所以弟弟篡取王位就被指认为对规制的僭越。在现代文明社会,尤其在受社会达尔文主义影响之后,这种“顺位继承”“长者为尊”的伦理性思维就被“优胜劣汰”“能者居上”的竞争性思维所取代。主人公菲力克斯获得导演职位的合法性,来自他全心投入的工作态度和独特的戏剧创新,较之菲力克斯在戏剧艺术构想中的各种新奇创意,助手托尼(Tony Price)精熟的是钻营与奉承,奇怪之处在于才华横溢的知名导演却被助手所取代(Atwood,2016:11-23)。在文本对托尼导演能力充满质询的表象背后,需要追问的是:董事会为何对他有所倾向?或者说,什么力量打破了资本主义社会个人才能自由竞争的共识,有权对“能者居上”用人机制中的“能”进行操作和转换?
文本中托尼拉赞助的特殊技能或许可以揭开谜底,他“巴结赞助商和赞助人,与董事会攀谈,争取各级政府的资金支持,并撰写高效的报告”(Atwood,2016:13)。在意欲把戏剧节打造成盈利的文化产业思维中,上座率、拨款权、赞助人投资、经济效益等等,都不得不成为决策者需要多加考虑的要素。当资本的逻辑悄然褪去戏剧导演身份的光环时,创造力作为戏剧导演“质”的区别的重要程度便会降低。在竞争恶化的职场,当菲力克斯的创造力不具备可计算性,被抹去这个“质”的差异时,他已沦为资本的打工者,难以挣脱被安排的命运。正如齐格蒙特·鲍曼(2002:19)所言:“他们手无寸铁地暴露在神秘的‘投资者’和‘股东’的皮鞭之下,暴露在更令其莫名其妙的‘市场力量’、‘雇佣条款’和‘竞争要求’的皮鞭之下,承受那不知何时会落到身上的鞭笞。” 托尼成功“篡位”的原因恰好就在于他借助了资本的强大力量。在由资本架构的社会权力关系中,菲力克斯知名度再高,终究也只是可以随意替换的“物件”,既然可以替换,毫无预警地遭遇解雇也就顺理成章。
如果说福柯(Michel Foucault)的现代性批判主要从权力视角出发,那么鲍曼(Bauman,2000)则是从流动性角度上审视现代性。在职业流动性或不稳定性日益成为常态的当代社会,菲力克斯的中年失业并非个案,而是整个职场竞争的缩影。这不仅反映了人们对失业的普遍焦虑和为职场竞争担忧的“感觉结构 (structure of feeling)”(Williams,1977:132-134),而且引申出对资本权力的进一步探究。《暴风雨》中,普洛斯彼罗因独占魔法而拥有权力,魔法书成为权力的载体,魔杖化为权力符号,在土著凯列班辛苦地劳作里,权力关系清晰可见。在《女巫的子孙》里,“魔法”的控制权业已让位于资本,董事会作为资本的代言人,将资本的权力运作隐藏进形式公平的“董事会投票”(Atwood,2016:19)中。如果说文艺复兴时期,知识因否拒平民而被神秘化,那么在《女巫的子孙》里,资本的权力及其运作机制因为披上了形式公平的神秘外衣,变得令人难以察觉。从始至终,隐藏在公平投票环节表象之下的资本权力,都未能成为菲力克斯仇恨的对象。“权力关系体现在生活和社会的方方面面”(丁林棚,2016:136),在司空见惯的失业现象背后,看似公平的投票机制背后所隐藏的操控权力并未受到充分关注,在法律法规健全的现代社会,菲力克斯即使受到不公待遇也只能申诉无门。实际上,《女巫的子孙》的现实意义不仅在于它撕开了“优秀也会失业”的真相,更在于文本将潜藏于“公正”表象之下“非公正”的“恶”透露了出来,等待读者去发掘。
对于菲力克斯来说,中年失业仿佛整个人生都被倾覆,他寄希望于借助乡村的离群索居生活(Atwood,2016:30-32)来疗伤,仿佛自我流放到人烟稀少的乡村就可以逃避城市的苦难,即便这种隐居会彻底切断几十年来建立的所有社会关系。然而,资本的力量同样渗透进乡村,乡村的一切早已不是世外桃源,假房东莫德太太因为菲力克斯对废弃空屋的打探而瞬间变脸,因为对于这个并无所属权的房屋,收取房租还是交房屋税,这一进一出的“巨大”差异在她头脑中迅速切换,不仅如此,在利己动机驱使下,她家提供的任何“服务”都会被换算成金钱(Atwood,2016:34-35)。这种现象折射出窘迫的乡村生活背后那种对金钱的迫切渴望,当单纯依靠耕地无法维持生计时,颇多底层农民不是沦为农业工人,就是离开熟悉的土地,被迫过上颠沛流离的生活。虽然文本叙述并不意在表现城乡差异和中下层人士之间的阶层区隔,但也在无意中呈现出城乡在不稳定生活状态、冷漠的人际关系、被金钱主宰的思维方式这三者上的趋同性。很明显,冷漠的乡邻关系始终无法帮他摆脱痛苦和疏解仇恨,只会任由他在复仇的执念和对女儿的“幻觉”中越陷越深(Atwood,2016:41)。当乡村救赎之路崩塌时,菲力克斯需要依靠什么来完成复仇大计?如果魔法的力量无法被现代科学所解释,那么对于非科幻小说而言,如何才能让复仇过程显得更加真实?在乡村叙事中,不经意间出现的“可见物”——数字电缆(Atwood,2016:44-45)早已留下暗示,数字时代的到来恰好为复仇做好了铺垫。
复仇之力:被征用的数字技术与持续控制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信息资源的获取打破了地理空间限制,即使身处乡野,人们也能将获取信息的范围向外无限扩展,通过高速网络体验数字技术带来的世界快速变化。如果说,《羚羊与秧鸡》(OryxandCrake,2003)整体笼罩着对生物技术的负面情绪,那么,《女巫的子孙》则转向了对数字技术的正面肯定,文本中不仅提及了脸书(Facebook)、网络购物等数字媒介带来的社交方式的改变,还通过优酷、3D虚拟、手机地图等细节,呈现出数字时代对生活方式的多方面影响(Atwood,2016)。数字社会,复仇对象托尼与萨尔(Sal O’ Nally)为了获取更大的社会知名度不断增加媒体曝光率,希望借助网络的热度带来职位的进一步提升。正如齐格蒙特·鲍曼等(Bauman,et al,2013:26)所言,可见性与曝光率从威胁变成了诱惑,一个人的知名度和公众视野可见度,代表着他的社会认可程度和存在的价值意义。托尼和萨尔行动轨迹的主动暴露解决了菲力克斯复仇中的“寻找”难题,利用网络搜索技术进行的“追踪”与“监视”变得更加隐蔽便捷。菲力克斯“惊讶于通过网络所获取的个人信息”(Atwood,2016:45),这种惊讶可能来自作者本人,在网络社交媒体推特(Twitter)上的活跃,早就让阿特伍德对“互联网+”时代的便捷与互动方式有着切身感受。不仅如此,托尼等高层将利于犯人的文化资助项目撤销的决定,又为菲力克斯成功动员犯人们参与“行动”制造了契机,由此而言,犯人们对公平秩序的渴望与菲力克斯的复仇动机存在着高度吻合。从某种意义上说,《女巫的子孙》不全是菲力克斯的个人复仇故事,它还表达了在强调“个人”概念的西方社会,“共同体”在维护个体利益时的重要性。在这一点上,普洛斯彼罗式个人英雄主义对个人知识、能力、理性的崇拜,通过“自助-他助”转换,被改写为对共同体的强调,相应地,为个人利益的复仇行动被抹上了为集体权益斗争的色彩。
监控技术与网络技术的介入,在菲力克斯复仇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犯人八只爪(8Handz)利用黑客技术,在弗莱彻县惩教所的密闭空间,安装了自己的监视系统和摄录设备。一般说来,加拿大监狱普遍采用的是以摄像头为主的电子监视系统,除了保留福柯所论及的“全景敞视建筑”的核心监视原理,“在被囚禁者身上造成一种有意识的和持续的可见状态,从而确保权力自动地发挥作用”(福柯,2012:226);还具有可灵活调试监控图像、数据存储便捷、视频资料无限回放等功能。电子监控技术可以捕捉人眼视野的盲点,并将捕捉到的视频数据即时存储,作为佐证的材料随时提取。这也就是说,对数字技术和数据资源的占有,意味着对话语权的进一步掌控。一直以来,托尼陷害菲力克斯的那些邪念无法作为犯罪事实进行惩处,就是因为在明处越过法律底线的行为容易受到警觉,而暗处潜伏在法律边界之外的意念不会受到惩罚。但是有了摄录技术的助力,前来视察的司法部长萨尔的丑态被镜头所捕捉,时任遗产部长的托尼意欲“利用混乱除掉萨尔,然后嫁祸给这群暴徒们”(Atwood,2016) 的真面目也无法遁于无形。数字技术的发展,使得“证据”的难题迎刃而解,摄录技术撕开了权力者伪善的假面具。
如果说监狱通过限制犯人的行动空间彰显权力,那么,虚拟网络恰好因为能冲破物理空间的限制而具有力量。较之戏剧现场的一次性表演,录播技术可以不受时空限制,将录好的视频向更多受众传播。创作《暴风雨》的文艺复兴时期,真相通常来自亲眼所见或亲耳所听,依赖视或听的主体在场,所以《暴风雨》结局中不免留下隐患,因为一旦脱离特定场域的限制,复仇对象的瞬间性自省和忏悔就会缺乏监督和持续控制,加之时空限制,真相难以广泛传播,矢口否认不过就是一念之间的事。到了纸质媒介时代,虽然签字画押能使罪行留有痕迹,但纸媒同样具有不易储存和容易销毁的缺陷。故而在数字时代,菲力克斯用新媒介取代了上述两种传统方式,利用网络云端存储的永久保留性和数据提取的即时性特征有力钳制托尼,迫使他答应将“识字项目”改为扩大资助力度并延长资助期限等一系列条件(Atwood,2016:224-229)。很明显,在托尼看来,网络的迅速传播力是自己根本无法掌控的强大力量,网络上的公众舆论能形成巨大合力,让他瞬间身败名裂,加上视频图像的低成本(乃至无成本)快速无限复制,网络的威慑力能轻而易举地达到对他进行持续心理控制的目的。正如德勒兹(Gilles Deleuze,2012:191)所言,“我们正在进入控制社会,这样的社会已不再通过禁锢运作,而是通过持续的控制和即时的信息传播来运作”。文本中技术作为一种可被征用的手段,使权力倒置成为可能,文本内两股无形力量的对抗中,网络力量解构了当权者的权力,搜索技术、摄录技术和云存储技术,作为新的“权威”发挥着颠覆性的作用。
复仇之思:话语权力与无力感
相对于《使女的故事》(TheHandmaid’sTale,1985)这类具有一定政治性的作品而言,《女巫的子孙》似乎是“去政治化”的。尤其在后殖民主义批评理论研究氛围里,人们通常认为前殖民地作家的改写应从解构殖民话语开始,但是在《女巫的子孙》的字里行间,却难见明显的种族、女性、阶级等政治议题,即便是书写监狱意象,作者也在刻意回避那些用作拘禁的单间牢房场景,迅速将笔触转至针对犯人的文学教育,让集体性学习表演来取代隔离和惩罚。这无疑是违背常理的,因为淡出大众视线之外的牢狱生活,往往给人残酷单调的印象,况且,读者想看到的是文本中犯人的罪有应得,远非逍遥快活。那么,阿特伍德为什么要脱离常识和读者期待,如此设计文本?
这显然是有原因的,小说第二十二节里的批注或许可以提供线索。起初这份批注的作用主要有两个,一是用来提醒导演菲力克斯剧中各角色的分配,二是保护女主演,让她有充分的心理准备(Atwood,2016:137)。然而,恰恰是批注的细致程度让敏感者觉察到作者的意图并非如此简单,因为犯人的真实姓名和监狱编号已被刻意隐去,取而代之的是由族裔身份和入狱原因构成的意义丰富的症候群。在仅有十几人的角色名单中,可以清晰地辨认出东南亚裔、越南裔、非裔、华裔、爱尔兰裔和黑人混血、墨西哥裔、意大利裔的字眼(Atwood,2016:137-140),尤其可疑的是,在未对他们的家庭背景、婚姻状况、教育经历、工作经历逐一认真介绍的前提下,族裔身份在批注中显得十分醒目。另一方面,作者又尽量回避了全部设置族裔身份的写法,以免留下偏激的印象而失去说服力,那么作者为何要欲盖弥彰,隐晦地制造族裔罪犯人数比例高的假象,这些欲言又止的族裔信息透露出什么呢?
在第二十二节的批注中对他们有着这样的叙述:“迫于压力加入了零售店行窃组织”(Atwood,2016:139);“劫富济贫……因拒绝对慈善机构进行黑客攻击而遭其资深同伙举报”(Atwood,2016:137);“曾在阿富汗服役的老兵,美国退役事务部没有支付其应激障碍症的治疗费用”(Atwood,2016:138)。显然,潜伏在叙述话语中的是另一种声音,半调侃性的犯罪原因传达出现代版“女巫的子孙”们与凯列班相似的复杂性,既让读者认定他们犯罪的恶的事实,又让读者因了解他们所承受的生活压力和社会不公而触发同情和怜悯。文本用“女巫的子孙”为题,不仅旨在立体化重塑现代版“女巫的子孙”形象,突破大众对罪犯持有的刻板印象,还在深层次引导读者去探寻这些“女巫的子孙”的生产者为何。事实上,“迫于压力”“顶罪”“劫富济贫”(Atwood,2016)这些字眼透露出来的潜文本,反倒消解了读者对罪犯的厌恶情绪,而将批判的矛头直指那些弱肉强食、贫富悬殊、制度不公的社会现实,由此可见,“女巫”的话语内涵并非指向那些与生俱来的“族裔”身份,而是底层人容易遭遇的恶劣生存环境及对少数族裔来说容易遭遇的歧视与排斥。
话语“女巫的子孙”就出现在对土著凯列班的谩骂中,从话语权看,贬语“女巫的子孙”是个被定义的概念,它有着松动的所指,与其说谁是“女巫的子孙”,毋宁说在权力者眼中,谁会被视作女巫的子孙。很明显,阿特伍德对边缘群体的关注并没有消退,她意在凸显边缘群体倒置为主体的意义,为污名化的“女巫的子孙”们发声。她将《暴风雨》中普洛斯彼罗与凯列班的主奴关系,改写为菲力克斯与犯人们的“师生”(朋友)关系,并带着诸多困惑组织文本:譬如犯人是否也具有正当权益?教育替代惩戒能否具有一定功效?如何才能让罪犯获得“新生”?对监狱犯人实施莎士比亚戏剧教育的设想,一方面是基于自身作家与曾任教师的双重身份,另一方面还源自阿特伍德高中时期,莎士比亚戏剧作为必修课的求学经历(阿特伍德,2018:49)。利用莎士比亚的“粗话”特色训练语言自控能力,利用文本续写分析训练思考能力,利用团队模式培养合作意识(Atwood,2016),这三点明显透露出作者在罪犯改造问题上的态度明显是教育多于惩戒,并且她认为这种教育可以是文学教育。因此,弗莱彻县惩教所课堂对凯列班优点的讨论,不仅是为凯列班正名,更是为了帮助罪犯产生对自我的重新认知。《女巫的子孙》表层上虽是以菲力克斯的复仇为主线,但在深层次却是将监狱犯人的重塑作为叙事链的重要辅线,将这些底层人物作为当代版的“女巫的子孙”着力书写。
《女巫的子孙》中对秩序破坏者的复仇,是以回归“能者居上”的规则为目的,这一点与《暴风雨》中对秩序恢复的强调具有内在一致性,只是菲力克斯所生活的社会体系中存在的那些缺陷与漏洞,未必因为某个个体的复仇成功就能轻松纠正和填补。表面上借助数字技术,使得《暴风雨》中的后续报复问题在《女巫的子孙》里不见踪迹,实际上即便有便捷的网络和云存储技术,数据安全和网络安全也是不容回避的问题。更何况,假如复仇对象一直隐藏邪恶本心,不在监控设备下显露蛛丝马迹,恐怕有再缜密的安排和先进的设备也会无计可施。确切来说,技术发挥作用必须依赖复仇对象罪恶的主动敞露和复仇主体对时机的迅速抓取,缺乏巧合的光环,技术也会无能为力。况且,菲力克斯复仇使用的技术手段(如摄录、药物)的合法性和道德规范性还值得再三商榷。如果再次仔细阅读《暴风雨》,同样会发现这种似曾相识的无力感,虽然故事以大团圆结局,却能隐约体认出无力感为生命体验的内里。虽然伊丽莎白时代,英国航海技术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但是,海上风险仍让人心有余悸,尤其在一六○九年“海洋冒险号”船舰灾难事件(胡家峦,2007:4)以后,暴风雨仍是恐惧的代名词,显然技术的发展未能彻底清算认知上的盲点,面对自然,人仍旧是抱有敬畏之心的渺小他者。莎士比亚虽赋予了普洛斯彼罗以知识和智慧,但也安排了前后两场暴风雨,来表征潜意识中残留的对自然不可控的恐惧情绪。
《女巫的子孙》中无力感的转移策略,直接指向了两处值得思考的增补。第一处是对十二年蛰伏期的浓墨重彩地书写。在某种意义上,菲力克斯的幸福感获得不是单纯来自复仇目的达成,而是积极地心理调适帮他走出了执念与仇恨。《暴风雨》中“失去”的表达主要涉及“权位”这个所谓身外之物,而《女巫的子孙》中“失去”已然弥漫进情感领域,监狱的罪犯承受着囚禁身体的惩罚,菲力克斯面临的则是精神上的囚禁,二者较之,走出监狱对身体的禁锢有期限,但走出精神的禁锢却困难而漫长。复仇之于个体,无论结局如何,浪费在仇恨上的光阴都显得毫无意义。宽恕与化解的秘诀还在于第二处增补中大学女教授的出场,她的出现改写了《暴风雨》中普洛斯彼罗妻子的缺失状态,让整个复仇图景增添了一丝暖色调。显而易见的是,作者完全规避了以往作品中“性别政治”的典型性书写,而是用“男性间战争”中女性扮演的疗愈师角色来代替性别冲突。文本用“情感”来回应仇恨,用精神之爱引领男性走出心理牢笼,将基于爱的亲密关系作为医治精神创伤的良药。
结 语
阿特伍德始终以锐利的目光警惕着日常生活中潜藏的权力及其变体,展现了投票机制背后的资本权力、具有颠覆意义的数字技术权力以及日常生活中话语权力的博弈与缠绕。《女巫的子孙》的文本意义首先在于揭示了一个相对残忍的社会真相,就是如疾病、失业等种种变故所招致的中上阶层的滑落,竟会如此迅速与彻底;其次,在这样一个相信技术、相信理性的时代,文本流露出对技术局限的忧虑,譬如现代医学技术在救治某些病人上的无力感,复仇中数字技术所依赖的环环相扣的极度幸运,又难能可贵地打破了现代人可能存留的对技术的迷信。虽然数字技术的使用,可以引发话语权变化,并显露出对弱者的特殊意义,但在社会大环境无法彻底改变时,心理调适和情感力量才是文本所暗示的可行性个体修复策略,这种主要向内聚焦于个体层面的迂回方案,在大团圆结局中又略显悲观与无奈。
注释:
①本文对《女巫的子孙》原文的引用为作者自译。本文分析同时参考了沈希译《女巫的子孙》,北京联合出版公司二○一七年版和朱生豪译《莎士比亚喜剧全集Ⅲ》,作家出版社二○一六年版,不再另注。
②截止至二○二○年三月十八日,在中国知网(CNKI)以“女巫的子孙”为主题检索,检索出《女巫的子孙》相关论文七篇。截止至二○二○年四月十四日,在Web of Science 中以“Hag-Seed”为主题检索,检索出《女巫的子孙》书评四篇,学术论文六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