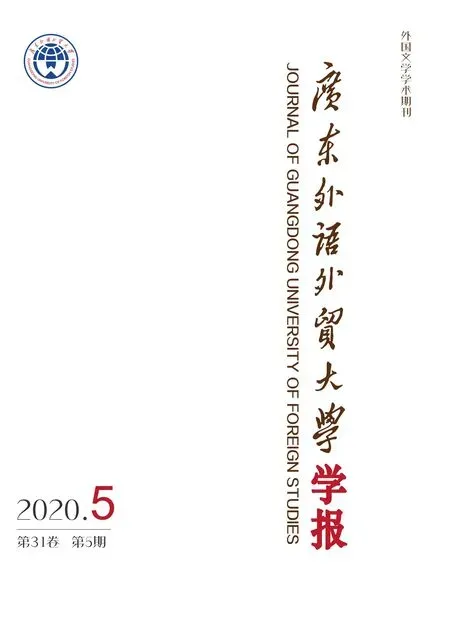中国百年翻译文学阅读史变迁:表征与反思
肖娴 陈元飞
引 言
如同呼吸、说话,阅读是人类生活的基本形态,古今中外关于文学阅读的轶事不胜枚举。林纾译作因其叙事新奇生动、译笔传神而大受欢迎,故时人有“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之感慨。阅读刺激也带来阅读狂热,歌德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中有读者因对书中情节过分着迷,模仿小说中主角的穿着,甚至学习书中主角自杀的故事,这就是有名的“维特狂热”(Werther Fever)。阅读体验因人而异,每个人都通过阅读内省自身,了解外部世界,西谚有云“You are what you read”,一个人的阅读史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知识构成、视野和价值观。一个民族的阅读史则塑造了这个民族的文学、文化传统。翻译文学在塑造中国现当代文学形态的过程中,发展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类型。从读者阅读史视角考察翻译文学的传播和接受,也是构建中国文学阅读史整体图景的一部分。
阅读史史话
阅读史研究通过探索人类阅读活动的历史变迁,探讨具有相似阅读行为习惯的“读者共同体” 的阅读对个人认知、思想或一定历史时期社会关系形成的影响。十八世纪西方的“阅读革命”始于教育领域改革和文化普及。书籍贸易的兴盛、公共图书馆的出现、室内照明的改进等因素都从客观上促进了阅读变革,阅读方式也从朗读转向默读,从精读转向快读,从公众场合阅读转向私密阅读。二十世纪中叶,欧美国家兴起了以传统目录学、社会文化史和读者反应论为理论基础,融合学科史、媒介研究等多个学科的“书籍史”(L’histoire du Livre)研究领域,新文化史学研究从日常语言、书籍阅读、服饰、食物、身体等诸多视角切入,以重构“物质史”。西方学者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从书籍史研究逐渐转向关注阅读史研究。一个时代的阅读史,体现了这一时期人们认知活动的脉络。阅读史研究对了解人类知识、思想、理论探索和发展过程非常重要,本质上属于史学研究,但与图书馆学、文献学、传播学、文化学、社会学等学科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具有较强的交叉学科性质。阅读史研究的是过去人们阅读实践和阅读体验的历史,涉及人与阅读活动及阅读对象——文本之间的关系,强调书写以及文本之于人的意义(张仲民,2007),追溯那些已经被遗忘或消失的阅读姿态和阅读习惯(Carvall, 2003),更关注阅读与生活、社会、权力的关系。
相较西方,中国有更悠久的书籍史传统。由于印刷出版技术的限制,古代书籍较为难得,且多以传抄为主。中国留存下来的艺文志、校勘、注疏、补遗、书话、诗话、词话、评点、眉批等不计其数。到十八世纪中期,汉语出版的书籍比其他所有语言出版的书籍总数还要多。历史上关于惜书、焚书、禁书的记载也很多。中国书籍史上有过两次大灾难,秦始皇焚书坑儒自不必说,梁元帝萧绎一生饱学多识,却终而亡国。城破之前,他焚尽了平生藏书十四万册,说:“读书破万卷,犹有今日,故焚之”。令人唏嘘。要知道,十四万册藏书量在当时算得上网罗天下书了。随着当代文化和媒介的发展,阅读的内涵比读书的对象更丰富,对阅读对象的范畴也有必要重新界定。阅读可以包括文字以外的图像、音乐、电影、唱片、碑铭等。中国对阅读史的译介始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大规模的人文社科学术翻译运动。李长声一九九二年和一九九三年在《读书》上发表了《从音读到默读》《书· 读书·读书史》两篇文章,阅读史研究逐渐受到中国史学界的关注,并被作为一种史学研究方法应用于其他学科。阅读史研究借鉴文学与文化批评理论,结合“读者反应论”等新文化史史学方法进行研究(许高勇,2013)。二○一八年初,由王余光主编的十卷本阅读史研究首部通史——《中国阅读通史》出版。虽则如此,中国阅读史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丰富的阅读史料尚待发掘。
阅读史理论奠基人达恩顿(Robert Darnton)在其代表作《迈向阅读史的第一步》中将阅读史研究分为“外部阅读史 (external history of reading)”和“内部阅读史(inner dimension of reading history)”(Darnton,1990:157)。概括来说,达恩顿的外部阅读史研究主要回答“谁阅读”(Who)、“阅读什么”(What)、“在哪里阅读”(Where)、“何时阅读”(When)的问题,而内部阅读史研究则需要回答“怎样阅读”(How)和“为什么阅读”(Why)的问题。从操作层面来看,阅读史研究的内容与方法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书籍流通史研究;(2)群体阅读史与个人阅读史研究;(3)阅读形态史;(4)断代阅读史整体研究。
书籍流通史研究可从宏观上对大量书籍的馆藏、借阅、流通、出版等信息进行宏观系统分析与数据统计。因阅读活动属于个人行为,具有即时性、主观性和不可控性,要对多人的阅读史进行追踪记录或对社会群体的阅读史进行统计,操作难度大。但随着电子阅读的普及和大数据时代的来临,一定范围内的阅读数据计量越来越成为可能,也为阅读史研究的数据提取、分析等实证研究路径提供了极大的便利。群体阅读史可以有多个研究维度,按年龄、性别、阶层等分类,可对不同群体的阅读特征、能力、习惯等进行研究。如研究儿童阅读史、青少年阅读史、女性阅读史。个人阅读史研究则既可以研究普通读者的阅读史,也可以研究名人阅读史。研究方法可以是调查、追踪记录、访谈等实证研究,也可以通过作品、日记、传记、书信等文献获取材料。阅读形态史关注阅读形态的变迁。例如,中国古代,普通民众在勾栏瓦舍间听说书人讲故事的底本称为“话本”,后来文人利用“话本”的故事题材进行书面创作,于是有了可供阅读的话本、拟话本小说,对“话本”的阅读形态也从听读发展到默读。对这些话本小说的文本研究也是了解一定历史时期阅读形态发展不错的视角。断代阅读史整体研究则可以通过宏观的横向、纵向比较,研究一定历史时期读者的阅读主体、阅读对象、阅读效果、阅读形态等特征,如本文对中国百年翻译文学阅读史特征的分析和总结,得出不同阶段读者翻译文学阅读的“共相”。
翻译文学阅读主体
(一)何为翻译文学
翻译文学有别于“文学翻译”,不同于本土文学,也不等于外国文学,它是中国文学的特殊组成部分(王向远,2004:10)。长期以来,即便是文学界也将“翻译文学”与“外国文学”等同起来,这两个概念有很大重合之处,但也有区别。“翻译文学”的主体是译者,译作是译者创造性地超越语言层面,追求文学审美层面的产物,译作源于原作,却又与原作分离。
翻译文学与文学翻译常被混为一谈。文学翻译是文本转换的行为过程,而翻译文学则是文学翻译这一过程的最终成果,是以作品形式呈现的一种文学存在方式,是一个本体概念。
简言之,不是所有的“文学翻译”活动所生产出来的作品都能成为翻译文学,正如每个文学爱好者都有权利写作,但并非每个人的作品都能称得上“创作”。优秀的译作通过出版、阅读、接受,以本国语言进入文学系统中,方能成为翻译文学。如《海燕》《欧也妮·葛朗台》《变色龙》等翻译文学作品,以中小学课本为载体,被一代又一代青少年读者阅读、熟知、消化、吸收,成为他们知识结构和文化素养的一部分。
大量国外文学作品通过翻译进入中国文化语境,一部分译作具有文学审美和社会现实双重价值,语言达到了文学语言的审美标准,为文学翻译活动树立了典范(Cavall,2003:4)。从原作到译作,经历了复杂多变的“文本旅行”,才形成了翻译文学。文本能否被接受并融入本土文化,取决于多重因素。其中,读者的阅读行为对翻译文学作品文本意义的现实化和具体化非常重要,翻译文学需要被阅读,需要通过“文学熟知化”的过程逐渐被接受。经时间淘洗,其中一部分优秀作品沉淀为译入语文学系统中的经典,其价值才能固定下来。
(二)谁是阅读主体
《阅读的历史》作者费希尔认为,“读译作的时候,异国情调和时代特色因似曾相识而变得寡淡无味,兴奋的感觉也就荡然无存。……有朝一日各国语言全都俯首称臣、销声匿迹,英语原著最终一统天下”(费希尔,2009:290)。然而,他说的并非事实,他的预言也不可能实现。纵观中国翻译文学阅读史可以发现,外国思想家和作家在中国的影响,主要通过译作。中国确有一部分能够阅读原作的读者,且随着教育的发展,这个群体在逐年扩容。但对大多数读者来说,主要还是借助阅读译本来了解外国文学。从人类学的角度来说,人类在全球化进程中将逐渐分化出两大族群,可以不甚准确地将其分为有高度移动能力的和无移动能力的两类。有高度移动能力的知识精英可以轻易穿梭于世界,从多个渠道去了解、鸟瞰整个世界;而移动能力较弱的阶层,无法用外语阅读的群体,在知识获取方面,则会更依赖于翻译。
(三)作为读者的译者
从阅读史的角度来看,不仅作者即读者,译者也是读者。罗斯玛丽·阿罗约(Rosemary Arrojo,2002:73)认为,翻译是“译者用另一种语言在另一个时间和文化环境中,阅读别人的文本”。翻译可以看作是译者对特定文本的阅读和阐释的结果,每一个译本,本质上都是不同译者的独特解读。译者最首要的身份是读者和阐释者,而且应该是理想的读者。斯皮瓦克(Spivak Gayatri Chakravorty)(1993/2000:398)说,“翻译是最亲密的阅读行为。”翻译阐释行为是阅读过程中固有的,译者也必须是一个好的阐释者。为翻译而阅读,可以说是阅读的最高层次,因为译者不仅要合理地解读文本,还必须努力用另一种语言重构与原文意义、结构、风格都贴近的译文。每一位译者都是阐释原文本以创造另一个新文本的读者。
阿尔维托·曼古埃尔(Alberto Manguel,2002:前言)曾这样发问:一个有天赋的译者,他的阅读会影响我们对原作的认识多深?经由译者的翻译和诠释,读者对一个作者权威的信赖会有什么变化?译作的影响不仅关注“影响者”,更需要关注“受影响者”。而阅读史要强调的就是阅读的主观能动性,读者对翻译作品进行创造性“阅读”“误读”乃至“误解”,阅读过程中,误读时有发生,并导致误解。误解的确存在,但并非不能理解。
翻译是细读文本的有效方式,这是每一个译者的具身体验。在阅读过程中,人类以语汇、观念、经验与直觉去阅读和感知作者所不曾唤起的东西。译者不仅阅读意义,还阅读感觉。理解是翻译的前提,翻译是理解的产物。为了翻译而阅读的读者,在原作与自己正在或即将产出的译作之间进行着一种探索式的“发问与答问”。籍此,原作中难以捉摸的概念和翻译难点被译者通过阅读搜集、整理、转换,一字字地铺展、陈列、表达出来。译者作为翻译作品的第一重读者,会基于自己的经验来阅读。译作既有原文本的字面意义、文学意义,也有译者的经验投射。
翻译文学中陌生化的人名、地名、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确能给读者带来了与本土文学不一样的距离感,偶有译者为了给读者制造似曾相识、身临其境的阅读体验,将原文中的外国人名、地名甚至物品名都归化成中国的,如傅东华译GonewiththeWind(《飘》),将人名译成中国旧式人名,地名也尽量归化,如Atlanta(亚特兰大)译为“饿狼陀”,黑人的口语改成中国式乡村土话,如“俺”“娃”等,这样的翻译策略,似乎并不能传达原作风格。发生在不同时代、异国他乡的故事之所以依然能打动读者,是因为人类对文学艺术美的共同体认,沉浸其中的阅读乐趣及其对世间万物的理解和共情,而非作者或译者的一味迁就。阅读的乐趣跨越语言的巴别塔,跨越文化的鸿沟,为人类文明的沟通搭起一座座桥梁。
“翻译或许是一个不可能性、一次背叛、一场欺骗、一个发明、一道希望的谎言——但在阅读的过程中,它使读者成为更有智慧、更好的听众”(曼古埃尔,2002:前言)。即便读者读到的翻译文学是经过删节、改编、变形,甚至是译者的再创作,翻译文学在译介、传播的过程中被读者接受并逐渐经典化,都能给读者带来异域的阅读感受,甚至影响其知识构成。
中国翻译文学阅读史流变
从阅读史视角来看,中国的文学翻译是如何通过阅读、传播和接受成为自成体系的翻译文学的呢?清末民初,文学翻译勃兴之时,精英群体如何开翻译文学阅读风气之先?今天的大众阅读、多媒介阅读背景下,翻译文学在中国如何接续传统,融入主流,甚至影响创作?从阅读史回溯中国的翻译文学传统,可以为我们了解翻译文学的发生、传播和接受提供全新的视角。
(一) 从发生到兴盛
中国古代最早的翻译活动始于佛经翻译。佛经翻译虽属宗教翻译,但佛经翻译传下来很多文学词汇,如“一尘不染” “三生有幸”“大千世界”“如是我闻”等,极大地丰富了汉语语汇,可视为文学翻译之雏形。由于印刷业、出版业和平民受教育程度的限制,阅读在当时还只是极少数精英阶层的特权,平民了解教义,接受佛学思想还只能靠口口相传的方式,而非自主阅读。佛经译场里通过讲经、问答方式,传播佛教教义。佛弟子的发问方式可以是不解故问、试验故问、疑惑故问、轻触故问或利乐众生故问,对于佛家弟子的发问,尊师回答的方式也多样,包括一向记(肯定地回答而不踌躇)、分别记(不同的问题,采取不同的回答)、反诘记(以反问方式回答)、舍置记(与修行无关的问题,置之不理)等。佛经译文虽有文学文本之特征,但因这种翻译完全是在宗教翻译的系统内运作,没有独立运行,因此即便所译佛经具有文学意味,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翻译文学,这种以口授传播佛经的方式还算不上翻译文学阅读,但它对后世的翻译文学产生了一定影响。
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翻译文学阅读史的发生则要晚近得多。文学翻译活动较之自然科学翻译要晚,受当时“经世致用”思潮的影响,也出于知识分子对中国文学的自我优越感和对西方文学的无知。从一八七○年左右第一部汉译小说《昕夕闲谈》至今,中国人接触到翻译文学也就是近一百五十年的历史。纵观中国一百五十年来文学汉译史,译介的外国文学作品可谓海量。据粗略统计,从一八七○至一九一九年间,有翻译小说二千五百六十九种、诗歌近一百篇,戏剧二十余部(郭延礼,1998:15)。翻译了大量诗歌、小说、戏剧、散文,“雅俗不分,华洋夹杂,读者不论有心无心,也乐得照单全收”(王德威,2005:2)。这一时期的翻译文学不仅承担着“经世致用”的社会功能,更满足了国人“遣情娱乐”的阅读需求。在中国悠久的阅读史上,四书五经、诸子百家才是文人阅读的正统。而一八七○年以后,从世界各民族语言译入的翻译作品,逐渐被阅读、传播、接受,成为翻译文学,渐次丰富了中国的文学传统。清末民初是中国文学翻译大盛的时期,二十世纪最初十年,中国的文学出版物中,文学翻译作品占五分之四(乐黛云,2005:2)。作为文化现象的阅读,在接续传统,承继文化的同时,亦深受时代变迁和文化政治的影响。翻译文学从诞生之初,就是国家理想凌驾于文学理想之上,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翻译文学阅读都不是“纯文学”阅读。清末民初的文学翻译活动从一开始就是“开眼看世界”的知识精英为救亡图存而发起的,梁启超将小说翻译与国家理想联系起来,认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梁启超,1902)。因为小说具有“不可思议之力”,能够支配人道。梁启超认为应该译印西方政治小说,主张“译书强国”。“五四”时期的译者则通过翻译改造文言文,提倡白话文,以翻译来塑造国民性。
(二)从阅读暗流到阅读的黄金岁月
抗战时期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翻译和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十七年”间的文学译者众多、译业兴盛。这一东西文化对峙的特殊时期,仍然有不少英美文学作品译入,但主流译介的外国文学作品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以俄苏文学为主。“文革”时期意识形态占据主流,大规模的俄苏文学翻译甚至亚非拉美国家文学文化作品翻译,翻译与民族、国家、社会、政治总有密不可分的关系。革命现代主义下,“大众”被升华成为“人民”,通俗文学失去了生长的土壤,甚至存在的合法性。
“文革”是文化的浩劫,也是民族阅读史上的饥荒岁月,靠背诵和援引语录获得“真理”,八个样板戏,八亿人民看了八年,成为人们全部文化生活的内容。在“十七年”和“文革”的阅读饥荒年代,翻译文学作品的题材受到比较严格的限制,整个文革期间,公开发行的译作只有二十部,其中苏联文学占六部,无书可读是当时的普遍困境。然而,对于阅读的限制并未能够完全锁住人们求知的渴望。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开始,其实已经有相当数量的读书小组在各地成立,上山下乡让知识青年在闭塞而又广阔的农村天地得以沉醉于被主流意识形态视为“洪水猛兽”的西方翻译作品中,暂时忘却了生活的艰辛与前途的未卜。这成为当时地下阅读涌动的暗流。
谢玺章在《一个人的阅读史》里谈及他获取并阅读“灰皮书”的细节:这是一本让他三十年来不能释怀的《布拉格之春——196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纪实》,译者署名“上海市 ‘五·七’干校六连翻译组”,内部发行。经辗转托人,他“穿过王府井新华书店北侧一个不挂牌的小门,经一条又窄又黑的过道,走到头,两间不大的房子,进门时,工作人员还要看证件或单位介绍信”(谢玺璋,2010:14)。“文革”期间很多翻译家都遭劫难,然而翻译活动却并未完全停止,国外出版的新书还是很快就被翻译进来,由于“文革”时期的“纸荒”,这些书印刷极其简陋,当时俗称“灰皮书”“白皮书”“黄皮书”。这些翻译作品只在“内部发行”,目的是为了解并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和国外敌对势力,“供内部批判参考之用”,也只在极小的圈子里流通、阅读。而恰恰是这些简陋小众的书,在那个知识饥荒的年代给年轻一代读者带来隐秘的阅读喜悦。这种阅读方式在当时像是在封闭的铁屋子顶上打开了一扇窗户,“不大,却也透进了一缕阳光,让生活在铁屋子里的人们有了一线希望”(谢玺璋,2010:16)。“文革”期间生产和经济建设放缓甚至停滞,一部分能获得这些翻译作品的年轻人在学校教育缺失、思想荒芜的遗憾中,却从另一个“无心插柳”的角度,提前获得了阅读和思考的自由,开始独立思考,用异于主流意识形态的眼光看待这个世界,这促成了后来八十年代年轻一代的精神觉醒。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出现了西方学术著作翻译的热潮。仅一九七八年到一九八七年的十年间,从西方引进的人文社科类翻译作品多达五千余种(陈久仁,1994)。近代以来,国人对西学的阅读态度并不是一直敞开怀抱欢迎的,而是在一种“封闭——开放——再封闭——再开放”的循环中踌躇前行。可这一次西学翻译热潮,则是“暴风骤雨式”的。八十年代是继清末民初“西学东渐”以来的又一次大规模的西学热潮,以不可抵挡之势,席卷了沉寂已久的中华大地。这期间,二十世纪西方主要的理论著作和学术思潮都被译介进来,很多新名词、新术语被大量移植,人人谈萨特,言必称“存在主义”。“弗洛伊德热”“韦伯热”“海德格尔热”悉数登场, 从全球范围来看,中国这一时期对理论的生吞活剥和全盘接受并不是一国之个案,对理论的痴迷在西方也有出现过。一些并不好懂的荒诞主义、象征主义、超现实主义、意识流等现代主义作品频繁出现在《外国文艺》《世界文学》《译林》等主流翻译文学期刊上。八十年代不论理解与否,人们都如饥似渴地阅读,八十年代成了中国阅读史上的黄金岁月。一个令人伤感但颇有说服力的例子就是,海子在山海关卧轨自杀时身上带着四本书:《新旧约全书》,海雅德尔的《孤筏重洋》,梭罗的《瓦尔登湖》和《康拉德小说选》,没有一本中国书——当年西风之盛由此可窥。然而,随着国外通俗文学的兴起和译介,翻译文学的阅读风向随着八十年代文化转型,在人们尚未觉察时,已悄然有了变化。
(三)走向类同的阅读理性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大规模的国外通俗文学译介给翻译文学阅读史带来了一大转变:阅读由雅趋俗,由阅读狂欢走向阅读理性。
这里的“雅”与“俗”可以分别理解成为严肃文学和通俗文学。一九七九年,外国文学期刊《译林》创刊,与《外国文艺》的精英阅读路线不同,《译林》从创刊之初就以译介国外通俗文学为己任。第一期刊载了侦探小说《尼罗河上的惨案》,读者争相购买,印数达十万册以上。由于“打开窗户”还处在观望阶段,尚有一定阻力,《尼罗河上的惨案》和《东方快车谋杀案》这类作品的译介曾引起一场不小的风波(李景端,2015)。尔后风波平息,《译林》杂志自创刊四十年以来,一直拥有为数众多且稳定的外国文学读者群。一九九二年,中国加入《世界版权公约》,出版商出于成本和市场的考虑,转而把目光投向已过版权保护时限的经典名著复译,这一时期大量的名著重译,出现了泥沙俱下、良莠不齐的乱象。
九十年代以后,市场经济高速发展,中国步入了消费社会的快车道,阅读日益成为无国界的文化消费。林纾的文言体翻译小说、俄苏革命翻译文学、现代主义、拉美文学等翻译和阅读热潮,都源于特定历史时期的需要和市场,在中国的文学传统中占据重要地位,但随着消费主义对社会结构和阅读习惯的改变,中国读者的阅读趣味开始具有无国界的类同性。如以《哈利·波特》为代表的“魔幻文学”,在中国和世界范围内的阅读,几乎没有本质区别,和本土原创小说一样,大众对翻译小说的阅读喜好逐渐回归了叙事传统和娱乐功能的本源。翻译文学阅读逐渐丧失了自己独特的历史,这也从侧面反映了阅读理性和文学的本质回归。
(四)困境与出路:后网络时代的翻译文学阅读
二○一三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曾从三千多条微博留言中统计出“死活读不下去的十本书”,其中翻译文学作品占了六本。依次是《百年孤独》《追忆似水年华》《瓦尔登湖》《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尤利西斯》,这些名著或陶冶过一代人的心灵,或激起过年轻人的斗志,或影响过一代作家的创作,但现在却成了“死活读不下去的书”,这是否表明,今人越来越不愿意静下心来读书了?而另一种情况是,二○一八年第十五次全民阅读调查报告中,覆盖三百多个城市的一万四千份问卷结果表明,近五成受访者人均年阅读量超过十本书,且八成受访者愿意为电子阅读付费。调查表明,在生活节奏倍速化的当下,国人的阅读量还不算少。看似矛盾的两种现象,实则有其深层原因。
后网络时代,阅读越来越“快”“泛”“短”“浅”“碎”,微文化正作为全新的信息方式海量、快速地改变着曾经流行的沉浸式阅读,转向浏览式阅读,人们的阅读行为和习性也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周宪,2016)。海尔斯(2014:4-5)将这种阅读认知方式的变化概括为深度注意力(deep attention)模式向超级注意力(hyper attention)模式的转化。比如,长时间平和、耐心地阅读一本维多利亚时期的小说,需要在聚焦时间上投入高度忍耐力,而看视频、打电子游戏、看动漫书或奇幻文学等则会追求强刺激,对单调沉闷的忍耐要求低,这时启动的是超级注意力模式。人类从印刷文明步入电子文明,沉浸式阅读势必逐渐被浏览式阅读取代,因此,需要沉浸式阅读的翻译文学也日趋式微,加上翻译文学本身的陌生化文化特质,相比本土经典文学作品阅读遇冷的境遇似乎更严峻。但我们同时也注意到,以上六本书都属于严肃文学,有的甚至还是颇为晦涩难懂的意识流小说、魔幻现实主义小说,需要高忍耐力的沉浸式阅读。而翻译文学中的通俗小说则在新世纪再度勃兴,如《哈利·波特》《达芬奇密码》等。《新史学:自白与对话》一书中收录了丹尼尔·罗什(Daniel Roche)与罗伯特·达恩顿的访谈对话,看似随意聊天中闪耀着不少真知灼见。前文也提到,达恩顿认为阅读史不仅关注“谁在读”“读什么”“在哪里读”“什么时间读”的问题,更要关注“为什么读”“如何读”的问题。他认为那些在人们看来不登大雅之堂的通俗读物、被禁的畅销书等可能拥有更多的读者,比名家名作和严肃文学更深远地影响了某个时代的心态(伯克,2006)。由此可见,后网络时代的翻译文学还有另一重特征:世俗化倾向。翻译文学阅读的由雅趋俗,体现了大众文化的兴盛。
中国翻译文学的“雅”“俗”更迭呈现轮动式特征。清末民初西学翻译运动中译入了大量西方严肃文学经典作品,后来也有不少通俗文学作品译入,如爱情小说、侦探小说、科学小说等。而“十七年”和“文革”期间,通俗翻译文学被挤压到了文学多元系统的边缘。改革开放后,以《译林》为代表的外国文学期刊以“打开窗户”为宗旨,开始译介当时在欧美流行的通俗小说,如《尼罗河上的惨案》《东方快车谋杀案》《教父》《吕蓓卡》(又译《蝴蝶梦》)等,这些通俗小说以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和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引起了封闭了几十年的中国读者极大的阅读兴趣。通俗小说的“文学熟知化”历程中,还有很重要的一环,就是电影改编。以多模态方式传播,其效果和影响更为可观。随着大众文化成为审美主流,曾经与正统文学格格不入的通俗作品在逐渐改变着人们的阅读趣味,也改变着批评家们对通俗文学的偏见。二○一七年,通俗类小说频频获得具有声誉的文学奖,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学的界限越来越模糊(芮小河,2018),甚至有学者从中国网络小说翻译文学的输出热看到了通俗文学先于严肃文学“走出去”,由“俗”到“雅”传播战略的可能性(陈彦旭,2018)。
电子文明时代翻译文学阅读“碎”“短”“泛”“浅”的危机或许正是翻译文学突围之契机,年轻一代的读者对知识阅读付费的接受度越来越高,翻译文学阅读走出困境之路,在于把握这个时代的阅读特征,以内容取胜仍是根本,翻译选材和译文质量是关键,传播方式是保障。翻译文学作品经由译者“理解——转换——表达”后,原文文本不仅实现了从一种文字到另一种文字的转换,更是从一种文化到另一种文化的旅行,文本经由翻译旅行的过程,也是文学在世界范围内经典化的必由之路。传统经典需要走下神坛,需要现代阐释。严肃文学需要放下身段,需要亲近读者,通俗文学也可能在读者的阅读、鉴赏中经典化。
结 语
从媒介文化史角度来看,人类文明的传播大致可分为四个时期:口传文化、手抄文化、印刷文化和电子文化四个阶段,翻译文学阅读史的变迁也基本遵循这样一个模式。翻译文学作品对人类文明的传播,其意义与价值并不亚于创作。正如当代著名作家莫言在《翻译家功德无量》一文中所说:“翻译家对文学的影响是巨大的,如果没有翻译家,世界文学这个概念就是一句空话……如果没有我们翻译家的创造性劳动,中国的当代文学就不是目前这个样子。”余华认可翻译文学对现当代文学创作的影响:“像我们这一代作家开始写作时,受影响最大的应该是翻译小说,古典文学影响不大,现代文学则更小”(王宁,2018:120)。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翻译文学阅读史,无论是清末民初风靡一时的侦探小说、英雄传记,还是建国后堪称青年人生教科书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牛虻》、《青年近卫军》,抑或是八十年代及以后影响一代作家创作和全社会人文思潮的西方现代主义创作手法和文学作品,都从翻译文学的阅读中汲取养分、获得灵感,进而使自己的作品也具有世界文学的特征,成为世界文学的一部分。
总的来说,中国翻译文学阅读史经历了由雅趋俗、由精英阅读走向大众阅读的流变;从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地下阅读走向八十年代的阅读狂欢,再到九十年代以后的阅读理性,翻译文学始终与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有过想摆脱的努力,但又总是被操控、掣肘,翻译文学影响了一代代读者的知识构成和价值观。翻译文学的阅读史是一面可以照见文化和社会变迁的镜子,也是中西交流史上与作为个体的读者最近距离的接触。考察翻译文学的阅读史,对了解文学史整体有极其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