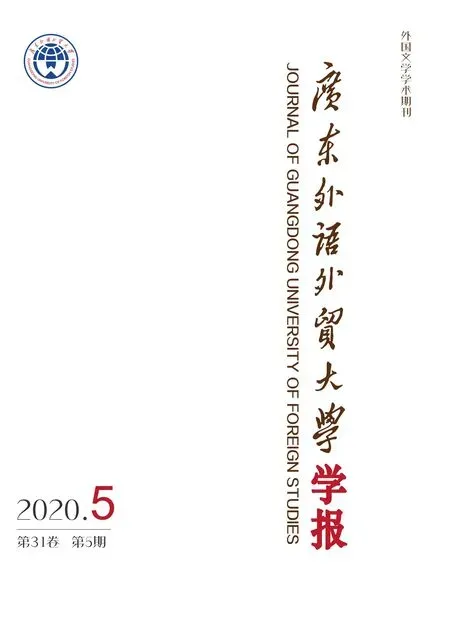里斯作品国外研究的发展与趋势
张雪峰
引 言
威尔士白人与西印度地区克里奥尔人的混杂血统造就了女性作家简·里斯(Jean Rhys)的诸多社会身份:她是加勒比地区黑人眼中的克里奥尔白人殖民者,却又是英国正统白人眼中的“野蛮”黑人;她在欧洲现代主义浪潮中密集创作,却因为一部《藻海无边》(WideSargassoSea, 1966)成为反帝反殖民的后殖民作家典范;她满腔热血地追寻永恒的爱情,却一次次沦为父权体系的牺牲品,背负“情人”的社会苛责①。 因此,当白人/黑人、英国/加勒比、父权体系/女性作家、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这些极具矛盾张力的关键词,同时汇聚到里斯的作品中时,她的作品就引发了英国与加勒比文学评论界的诸多关注,经历了从争议、热议再至跨文化研究的三个研究时期。
《藻海无边》问世之前的争议时期
在《藻海无边》问世之前,二十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是里斯的密集创作期,其早期作品《左岸》(LeftBank,1927)、《四重奏》(Quartet, 1929)、《离开麦肯齐先生之后》(AfterLeavingMr.Mackenzie, 1931)、《黑暗中航行》(VoyageintheDark, 1934)、《早安,午夜》(GoodMorning,Midnight, 1939)都在这一阶段诞生。《左岸》这部短篇作品集得到《跨大西洋评论》(TheTransatlanticReview)主编福特(Ford Madox Ford)的力荐与指导。在序言中,福特指出里斯“把控形式的能力没有几个作家能够与之媲美”(Rhys, 1927:24),肯定了里斯的现代主义叙述方式,使里斯挤入现代主义作家的行列。紧随其后,英国的主流媒体杂志《新政治家》(NewStatesman)、《旁观者》(Spectator)也纷纷聚焦其现代主义文体风格,将里斯与曼斯菲尔德(Katherine Mansfield)置入平齐地位。虽然里斯的现代主义文风受到肯定,但她的作品内容却受到英国文学评论界的一度质疑,其作品中浓烈的个人叙述色彩与近乎一致的女性人物的悲苦命运叙述,常被视为一种狭隘的女性视野,欠缺文化深度。因此,虽然创作于现代主义高峰时期,但里斯的作品却在二十世纪早期遭遇欧洲文学市场的冷遇。究其根源,主要源于两个方面的因素:
一是里斯的克里奥尔白人作家身份。作为加勒比地区欧洲白人移民者的后裔,克里奥尔白人既是英国白人眼中的黑人,又是西印度黑人眼中的白人殖民者,作为双重的局外人,他们不归属与任何一个民族群体。因此,里斯将自己文化身份的困惑贯穿其作品中,以早期作品中含混不清的地域辨识度,隐匿其英国身份与西印度身份的文化困境,这既引发了英国评论界对其作家身份定位的争论,“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是一个了不起的旅行者,但永远是美国人;乔伊斯(James Joyce)永远被公认为爱尔兰人,可是生于加勒比海地区的里斯女士呢?她是威尔士人?西印度人?还是英国人?”(Wolfe, 1980:15),又成为导致其早期作品在英国关注度较低的直接原因。
二是里斯早期的写作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英国文学写作的大环境背道而驰这一因素密切相关。当时的英国正值两次世界大战中间的动荡时期:战争、经济大萧条、西班牙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抬头、反闪族主义情绪、女权运动的日益崛起都使得英国陷于内忧外患的局势。因此,对于英国民族身份与帝国性的焦虑、质疑的同时,又要竭力维护英帝国民族身份的自豪感与优越性,就成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至六十年代英国晚期现代主义叙述的社会大背景。虽然里斯与伍尔夫(Virginia Woolf)、乔伊斯、海明威等人属于同一时代的作家,但是里斯的克里奥尔白人作家身份与其作品中始终如一的令人窒息的忧怨情绪,致使其早期作品被淹没在欧洲现代主义文学的浪潮中,“里斯的艺术源于一种敏锐的甚至是病态的情感与感知……其作品中的女性人物都不具备承受苦难的能力……这就引发了现代评论家的不安与敌意”(Wolfe, 1980:15)。里斯作品中贫穷、慵懒、懦弱、消极甚至是自甘堕落的里斯式女性人物,不仅与二十世纪初欧洲现代主义文学中隐含的帝国骄傲情感背道而驰,亦与欧洲女性主义运动的迅猛发展势头格格不入,这就是为何里斯早期的现代主义作品未被纳入《书写她们的生活:1910-1940的现代主义女性》(WritingforTheirLives:TheModernistWomen, 1910-1940)的原因。
与此同时,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加勒比地区正经历反对英殖民统治的民族主义运动,一些具有政治先见与导向的报刊以及团体的创建,有力地推动了这一阶段西印度民族文学的发展②,诸多如玛森(Una Marson)、麦凯(Claude Mckay)等本土或移民作家涌现出来,致力于构建纯正的西印度民族文学。由于里斯在一九〇七年已经离开多米尼加远赴英国,而且在离开加勒比地区后,疏离于其他加勒比移民作家群体,因此,里斯并未参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加勒比民族运动或民族文学的构建,这也是早期加勒比文学史及文学评论中鲜见里斯及其作品的原因所在。
《藻海无边》后的热议时期
一九六六年,《藻海无边》的出版不仅改写了《简·爱》中“阁楼里的疯女人”伯莎的命运,也使里斯名声大噪。英国作家兼评论家艾尔瓦雷斯(A. Alvarez)将其视为“在世的最优秀的英国小说家”(Wolfe, 1980:19);同样来自加勒比世界的奈保尔(V.S. Naipaul,1990:58)则称赞里斯“早在三四十年前就已经涉足我们当今所关注的主题:孤独、在社会与集体中的失感、心里破碎感、依赖、失落”。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开始,里斯作品的研究急剧增多,其作品研究基本上集中于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以及现代主义研究三个方面。
(一)里斯作品的后殖民研究
《藻海无边》的出版直接引发了加勒比评论界对里斯是否是西印度作家、如何界定西印度作家与西印度小说等关乎加勒比民族性的争论与探讨。一九六八年加勒比评论家莱(Wally Look Lai,1968)将《藻海无边》视为西印度小说中的杰作,将里斯视为优秀的西印度作家,认为《藻海无边》中典型的西印度风景与西印度文化“对西印度社会做出了艺术性的阐释”,而里斯也成为早期加勒比评论史上唯一的一位加勒比女性作家。与此相反,加勒比最具影响力之一的诗人兼评论家布莱斯维特(Edward Kamau Brathwaite,1974:38)却对里斯的加勒比作家身份书提出质疑:“《藻海无边》纯属虚构叙述,它忽视了加勒比社会与历史形成的广阔领域……”。布莱斯维特认为里斯作为克里奥尔白人的殖民身份与殖民视角,既不可能客观地反映加勒比地区真实的社会状况,也不可能反映加勒比非裔的殖民心理。作为加勒比非裔的代表,布莱斯维特实际上竭力维护的是加勒比庞大的非裔群体的文化话语权力,而《藻海无边》中的克里奥尔白人安托瓦内特(Antoinette)对黑人克里斯蒂芬(Christophine)以及蒂亚(Tia)的含混态度难逃种族优越感之嫌,这也是引发布莱斯维特质疑里斯西印度作家身份的原因。面对这样的争议,评论家拉姆昌特(Kenneth Ramchand,1976:93)索性对西印度作家与作品的问题给出明确的界定:“西印度文学作品是指出生或成长于西印度地区,并且能够在西印度语境下描述出一个可辨识的西印度社会”,这样就将里斯这一移居于英国的克里奥尔白人作家纳入西印度文学作家的行列。此外,拉姆昌特认为里斯作品中的克里奥尔方言是西印度文学的典型特征, 并将里斯置于与塞尔文(Samuel Selvon)、沃尔科特(Derek Walcott)等加勒比作家同等重要的地位,考查其作品中西印度的地域特色。至此,里斯西印度作家的地位才得以确立。
对里斯西印度作家身份的认可进一步推动了其作品的后殖民研究。里斯作品的后殖民研究相对集中于《黑暗中航行》与《藻海无边》这两部作品,主要是因为这两部作品中的女性人物安娜(Anna)与安托瓦内特都具有明确的克里奥尔白人身份。以斯皮瓦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为代表的学者,将里斯视为充满殖民反抗意识的后殖民作家,围绕其作品中的反殖民话语叙述,控诉欧洲殖民历史带给加勒比地区民族、种族、性别以及社会文化的创伤。但同时,里斯在《藻海无边》中有关克里奥尔白人与加勒比非裔黑人间民族矛盾的叙述,又不乏殖民主义与种族主义话语之嫌,亦引起了汉德利(George Handley, 2000:150)等评论者的质疑,将其视为“对于受废奴运动残害的庄园主阶层的深层同情”。对此,里斯作品的早期评论者斯坦利(Thomas F. Staley,1979:5)持不同意见,他认为“里斯对于加勒比非裔有着复杂的情感态度……她童年时与加勒比非裔的亲密关系以及在英国的经历都使得她能够理解、认同生活在英国白人世界里的黑人移民”;另一评论者奥康纳(Teresa F. O’Connor, 1986:35)则以里斯的采访与自传内容为佐证反驳斯坦利的观点,认为“无论是对多米尼加的黑人还是英国的黑人,里斯都没有流露出任何同情”;甚至连肯定里斯作品中后殖民反叛精神的斯皮瓦克(Spivak, 1985)也不满里斯在作品中对于加勒比非裔女性“属下”话语的压制,认为《藻海无边》中非裔女性克里斯蒂芬话语叙述的消失,使里斯难逃殖民与种族主义之嫌。
虽然上述评论者对里斯以及其作品中的殖民态度做出与殖民思想或同谋、或背离或含混等三方面代表性的解读,但却存在几个共性问题:一是上述评论都仅仅以作家本人或作品中人物的种族或民族身份为评判基点,视欧洲白人或加勒比克里奥尔白人为殖民者,加勒比非裔为被殖民者,是以现当代的后殖民思想审视里斯作品描述的十九世纪初加勒比地区的社会以及文化状况,这就势必造成时代错位解读,以后殖民思想的普适性特征遮盖里斯作品中具体的文化语境,忽略了里斯作品中的具体加勒比历史以及文化地貌;二是评论者们都是以殖民文化的主导性影响来评判里斯的作品,忽略了里斯作品中折射出的西印度非裔文化自身的能动性与反作用力;三是上述评论将里斯的后殖民身份与女性身份分而视之,由被殖民者反抗殖民者的叙述,进而拓展至女性反抗男权压制的叙述策略,这就将里斯作品中加勒比女性元素在加勒比殖民历史文化中的重要性做了模糊化的处理。
(二)里斯作品的女性研究
里斯作品的女性主义批评首先是针对里斯作品中女性人物的懦弱。里斯式的女性人物大都依赖男性,自愿受虐,甚至甘心臣服于男性权力,“与柔弱的女性气质而非女性主义的期望相一致”(Emery, 1990:11)。这样的文学叙事与女性主义寻求平等与女性自我身份的完整性似乎背道而驰,因此,里斯的作品首先遭遇到女性主义批评者的批判,“她作品中反复出现的主题是:女性永远是男性社会的受害者……一旦成为女性,就注定没有逃脱的希望,注定成为男性至上社会中的最底层”(Miles, 1974:99)。对此,以奥康纳为代表的评论家将里斯式女性人物的懦弱归因于里斯童年及在英国流亡的经历,虽然这一阐释是以里斯本人可信的自传与采访为依据,为后来的评论提供了最有力的支撑,但奥康纳将里斯作品中的隐含作者等同于真实作者,并未进一步挖掘里斯作品中自传性虚构这一特征,也未充分挖掘里斯式女性存在的深层社会原因。
与此相反,凯西(Nancy J. Casey, 1974)则聚焦于里斯短篇作品中以出卖肉体为生的边缘女性,赋予她们“被解放的女性”这一政治寓意,将其视为挑战传统社会价值体系的女权运动的代表。哈里森(Nancy R. Harrison, 1988:63)与克洛普弗(Deborah K. Kloepfer)都将里斯的女性人物视为言说主体,“里斯的‘史无前例’的世界是女性言语的世界,她们表达出她们想要表达的言语……她的女性人物或是叙述者想说的内容是否与当下自由女性的心声吻合已经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记录女性在男性话语框架里未曾言说的反应”。但略有差异的是,哈里森认为里斯的作品是对男性声音的反驳,而克洛普弗倾向于剖析女性文本中的母女关系,认为里斯不仅仅反驳男性话语,也反驳了女性文本中潜藏的女性文学这一母系语言影响的焦虑。哈里森与克洛普弗对里斯作品中柔弱的女性诗学特征做出了充分的解读。的确,里斯以文学叙事的方式诚实地感知、记录的不仅仅是西印度女性,也在记录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英国女性、欧洲女性以及所有不分民族、种族的女性的伤痛,展示所有边缘女性脆弱无助的真实面。里斯笔下的女性并不是以倔强与反叛表现其强烈的女性意识,而是以脆弱展现女性主义建构背后不曾言说的痛苦,这才是里斯与“里斯式女性人物”女性研究的意义所在。
(三)里斯作品的现代主义研究
《藻海无边》的成功,带动了里斯早期现代主义作品的研究。评论者将里斯与伍尔夫、乔伊斯等现代主义主流作家并置,聚焦于里斯前四部作品《黑暗中航行》《早安,午夜》《四重奏》以及《离开麦肯齐先生之后》中的现代性与现代主义特征,在关注其跨时空的意识流叙事美学特征的同时,探究资本经济市场对女性的物化影响,展现其早期作品对欧洲现代主义文化以及对欧洲现代性的批判与抨击(Karl, 2009:12-15)。本德尔(Todd Bender, 1997:110)则侧重于里斯早期作品中的印象主义风格,通过追溯里斯作品中的印象主义风格,突显里斯作品中的“含混”技巧,以此形成与读者的互动,“里斯刻意用这样的含混技巧,是为了让读者补充文本的空隙”。这些评论在前置里斯作品中欧洲现代性与现代主义写作风格的同时,却弱化了里斯作品中的加勒比后殖民性。
里斯的双重身份的确使其处于加勒比文学与欧洲现代主义文学的不同传统,因此必然会产生以后殖民话语与英国现代性为主要视角的不同评判准则。然而依据作家身份定性其作品,显然缺乏足够的信度,也不能全面考察里斯的所有作品。将里斯作品中的后殖民、女性以及现代主义叙事并置且分而视之是导致里斯作品评论出现分化的根本原因。
首先,后殖民批评是以殖民/被殖民的二分法为基准,女性主义批评是以男性/女性的对立模式为基准,而现代主义阐释是以现实主义叙事/现代主义叙事的对立为基准。因此,倘若单纯以后殖民、女性以及现代文学的标签定位里斯及其作品,难免会使其作品落入二元对立本质论的窠臼。里斯作品研究中的二元对立体系论是以现代主义文学与后殖民文学的对立与矛盾为基本预设立场,过度强调现代主义文学与后殖民文学之间的差异,而模糊或抹擦这两种文学传统间的交叉与重合,因此对里斯及其作品研究产生差异与分化视角就在所难免。
其次,里斯作品中的后殖民与女性主义视角,最终都是落脚于对殖民话语与父系霸权或反抗或同谋或含混的意识形态层面的内容批判,而其作品中的现代主义视角则注重其现代主义叙事形式的层面,将后殖民、女性主义以及现代主义分而视之的批评视角,不仅割裂了里斯早期作品与最后一部作品《藻海无边》之间的统一关联,亦造成里斯作品内容与形式的分离,最终形成里斯作品批评的极端分化趋向。
最后,以后殖民、女性以及现代文学这样旗帜分明的标签定位里斯及其作品,实际上是过度强调其后殖民性、女性主义以及现代性批评话语特征,这就容易忽略里斯作品中关于普适性的人类情感的伦理特征。事实上,里斯并不完全是一个政治性或社会性作家,甚至里斯本人也曾坦言自己“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女性主义者”(Nebeker, 1981:vii), 她只是借助文学叙事的方式诚实地感知、记录自己生活的那个时代的真实,她的作品试图诠释的只是女性,一个渴望快乐但却无法快乐的性别存在,诉说作家本人对女性作为社会边缘人的理解。但她的作品又绝非纯粹的自传性叙述,而是以人物自我的认知为圆心,辐射二十世纪初生活在欧洲现代主义与殖民主义语境下的所有底层女性,叙述的是所有底层女性的生存状态与心理状态,从而一方面揭露欧洲现代主义蕴含的帝国与殖民性,另一方面展现人这一拥有自然属性的个体在现代性社会逐步被社会、种族、性别、文化符码所奴化、僵化甚至商品化的历史现实,并藉此与读者进行交流,引发读者的情感共鸣。
二十世纪末的跨文化研究时期
二十世纪末,随着后殖民理论、女性主义批评与现代主义研究视野的不断扩大,评论界不再将里斯的后殖民叙述、女性叙述与现代主义叙述分而视之,而是将其后殖民、现代主义以及女性作家身份同时结合,显示出明显的跨民族、跨文化批评趋势。相对应于那些指责里斯具有含混文化身份的负面评论,埃默莉(Mary Lou Emery, 1990:7-8)与豪威尔斯(Coral Ann Howells)等人的评论更为中肯,她们都较全面地指出了里斯作品中的跨民族、跨文化书写特征。埃默莉指出里斯作品含混性的根源是由于其作品中多重文化书写传统的交织,“仅仅将里斯视为一位女性作家或是西印度作家或是欧洲现代主义作家无一例外地都限制了我们对于其作品的理解。在每一种语境中,由于其他两种语境的加入,使其作品总是在主流之外”。豪威尔斯(Howells, 1991:5)则强调里斯作品中的多重文化语境与女性书写特征的关联,“里斯通过她的小说建构的是欧洲现代主义语境下女性化的殖民情感意识,所有的殖民剥夺与文化错位都被聚焦、转嫁于性别之上,使得所有条件都凝练为独特的女性伤痛”。换言之,豪威尔斯亦认为不能简单地将里斯的作品归属于后殖民、女性主义或是现代主义传统,其作品中的后殖民性、女性主义书写特征与现代主义的叙事技巧错综交杂。
在这种大趋势下,评论者纷纷开始关注里斯作品中的跨文化性。与前述研究将里斯作品中的现代主义风格与后殖民叙事相分离不同,塞莎基里(Urmila Seshagiri)、康泽特(Delia Caparoso Konzett) 等评论者则是将里斯作品中的后殖民性与现代性合二为一。在《现代主义灰烬与后殖民涅槃重生:简.里斯与20世纪英语文学进化》(ModernistAshes,PostcolonialPhoenix:JeanRhysandtheevolutionoftheEnglishintheTwentiethCentury)一文中, 塞莎基里(Seshagiri, 2006)指出跨越英国与西印度社会的地域性赋予了《黑暗中航行》跨文学文化的叙述特征,里斯的这部现代主义作品具有明显的“后殖民转向”,“里斯开创了一种新的地缘政治,既挑战了现代主义形式成果的延续性,同时也开创了后殖民文学的中心目标”。
康泽特(Konzett, 2002:127)将里斯作品中合二为一的现代性与后殖民性称之为“后人文主义美学”(the aesthetics of post-humanism),认为在《藻海无边》与《早安,午夜》中,里斯以现代主义叙述方式,撼动了白人种族的神话论,“揭示出白人主导的西方文明标准不仅仅受到了被殖民者的挑战,也给白人文明自身带来了巨大的负担”;另一评论者约翰逊(Kerry Johnson)则是从空间角度,揭示出 《黑暗中航行》中现代主义与后殖民元素的交织,挖掘里斯作品中的后殖民现代主义美学特征;布朗(J. Dillon Brown, 2011:295) 在加勒比现代主义与现代性的研究中,也指出里斯作为早期加勒比女性作家,对加勒比现代主义与现代性的构建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二〇一三年,威尔逊与约翰逊(Mary Wilson,Kerry L. Johnson, 2013:4-5)在提及里斯作品研究的重要性时,明确指出里斯作品研究的重要性就在于其作品中不断交织的文化属性,“里斯研究关乎我们对于现代主义研究、加勒比研究、后殖民研究、女性研究的理解,最重要的是,关乎我们对于这些不同研究领域共性与差异的理解”,这种现代主义研究、加勒比研究、后殖民研究、女性研究错综交织的文化属性,恰恰能够为不同文学领域的跨文化研究提供无限可能。
与此同时,里斯的早期作品蕴藏的现代主义文化寓意也得到全新的阐释。齐姆林(Rishona Zimring,2000)聚焦于《早安,午夜》《黑暗中航行》与《四重奏》等早期作品中出现的女性人物化妆这一现象,揭示二十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的女性消费文化,暴露这一时期女性隐藏于化妆面具之后的艰难生存境遇;克鲁吉(Amy Clukey, 2010)则关注里斯作品中现代主义与世界主义的融合,认为里斯在《四重奏》中跨越国籍、民族、地域等局限,以现代主义都市漫游女性的视角,重新认知殖民扩张的辐射效应,因此,《四重奏》也被克鲁吉视为“现代主义化世界主义的典型代表”;约翰逊与莫兰(Erica L. Johnson,Patricia Moran, 2015:4)将里斯作品折射出的现代性视为“全球性现代主义”的典型,因为里斯作品中的现代主义已经远远超越了现代主义时间与地缘标记,是一种现代主义美学能指而非现代主义时间能指。
无论是对里斯作品中的后殖民现代主义,或是后人文主义、世界主义或是全球现代主义的认知,首先是对里斯加勒比克里奥尔白人身份的重新认知,当早期评论者纠结里斯的作品既无法代表欧洲白人也无法代表加勒比黑人的立场时,恰恰忽略了里斯书写的多重性可能,加勒比克里奥尔白人女性身份的书写视角,使其既可以洞察欧洲社会的历史变迁,亦可以折射加勒比社会的历史文化,这就自然而然地消解了出身、血统、肤色、民族、种族、地域等定势判断准则,使她与作品中的她们以多维度、差异化的眼光与视角审视后殖民女性的多元世界。
其次,对于里斯作品跨文化性的认知也同样折射出文学文类跨民族、跨文化的研究趋势。文学与文化的跨民族发展方向就是要跨越时空、地域与意识形态的局限,探索不同时代、不同社会文化语境中文学内容与表现形式上的重合与差异,关注不同文化之间的交融与对话,在解构潮流中寻找各种可能文学与文化的交叉点。后殖民性、女性主义以及现代主义叙事的多重交织,使里斯的作品研究跳出欧洲殖民/加勒比后殖民、男权/女权世界以及现代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的分界线,不仅拓展了里斯作品研究的广度与深度, 也重新审视了文学文类与不同文化间的交融。
结 语
历经沉寂与争议的里斯与其作品,终于在《藻海无边》之后迎来了热度与关注度。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开始,涌现出大量研究里斯作品的学术成果,形成了二十世纪末蓬勃发展的“里斯产业(Rhys industry)”(Savory, 1998:xiv),分别于二〇〇四年在多米尼克与二〇一〇年在伦敦召开的关于里斯研究的国际性学术会议,无疑都在证明里斯已然步入经典化作家研究的行列。里斯与其作品步入经典化研究行列并非偶然,而是一种必然,这种必然源于里斯与里斯作品中鲜明的矛盾聚集点,穿越于欧洲与加勒比世界的里斯与里斯笔下脆弱、敏感、近乎精神疯狂的里斯式女性人物,以她与她们的视角,讲述着历经战争、现代危机、资本经济、殖民主义的边缘群体的苦痛与挣扎,掀开西方现代性构建的那些理性、自由、独立、进步的虚幻光环,展示出现代人无奈与叹息之后的真实,这就自然而然地拓宽了后殖民文学、现代主义文学、女性文学与加勒比文学研究的范畴,为丰富后殖民文学、现代主义文学、女性文学与加勒比文学研究的内涵与寓意开拓出新的可能,为不同文学文类的跨民族、跨文化研究提供新的契机。
注释:
① 在早期创作中,里斯曾经接受了二十世纪初《跨大西洋评论》的主编福特的指导与帮助。后来,里斯介入了福特与其妻(澳大利亚艺术家)鲍文(Stella Bowen)的婚姻,饱受社会争议。
② 西印度(West Indies/West Indian)群岛通常指加勒比地区前英属殖民地,如牙买加、特立尼达、巴巴多斯以及安提瓜、圭亚那等。而“加勒比”(Caribbean)一词则指涉该地区所有的岛国。为便于论述,文内所提及的加勒比文学或西印度文学均指涉加勒比英语文学。
——评《后殖民女性主义视阈中的马琳·诺比斯·菲利普诗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