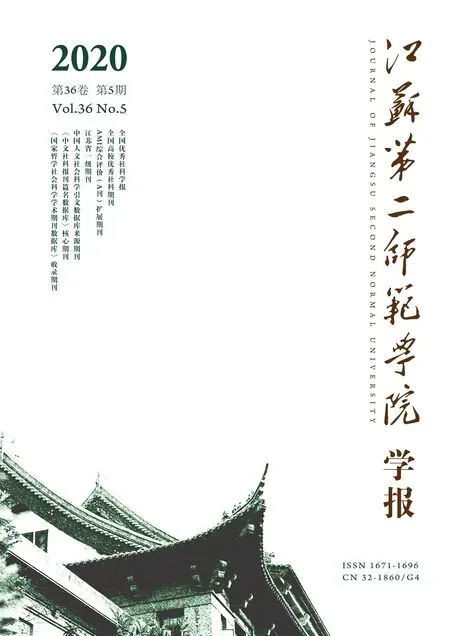“生命化语文”教学的生命补养与释放
曹明海 白花丽
(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 山东济南 250014)
人是教育的起点,也是教育的终点。真正的教育是心灵的沟通、生命的对话,其本质是对生命的呵护和终极关怀。我们的汉语文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为个体生命的成长和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它的教学指向就是生命成长的培育价值和个体生命的独特性、丰富性、完整性建构,力图用语文来补养生命,用语文来释放生命,让学生“享受语言文字的生命阳光”[1]351,即在语言文字运用的过程中张扬语文灵气,释放生命活力,建构生命丰赡的个性和人格,达成生命个体的总体生成。江苏省新海高中的李震老师和他的团队以“言语生命”为依据,重新理解和把握语文课程的“根”和“本”,标举以汉语言文字为根基的“生命化语文”,实施语文核心素养的教学策略,逐步实现了“立德树人”目标的深度推进。
一、“生命”的重构:生命化语文的教学新场域
如何开拓“生命化语文”的教学新场域?李震和他的团队注重对“人”的生命特性的关注和思考,用语言本体论把握教与学主体和生命的特征,站在人的生命成长与发展的高度重新审视汉语文的文化特质,深入发掘语文课程的文化内涵和蕴藏着的生命活性因素,使其成为学生在语言文字运用中领悟生命本真、激发生命潜能、实现生命价值的过程,让语文课堂呈现勃勃生机,开启了“生命化语文”的教学新场域。李震在专著《语文教学智慧与策略》和《李震讲语文》中通过理论探究和教学案例说明,从“人的建设”的高度来定位语文教学,深究语文教学的“元问题”,即“我们要建设什么样的人的问题”[2]。应该说,“生命化语文”抓住了“元问题”的教学本质。
1.人的符号性维度:生命化语文对“生命”的认知
何为“生命化语文”?即怎样理解和把握“生命化语文”的教学意涵及其目标取向,这是必须要明确的一个根本性问题。人论家曾经指出,人是一种符号性的存在,符号当属语言。符号性维度是人的存在所固有的,人总是离不开语言,我们总是在言说,总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不断地言说。因为言说是人的本性,人是靠本性拥有语言,言说是人的生命存在。因此,李震和他的团队确认“言语生命”就是坚实的理论依据,因为唯有言语才能发生人与人的生命沟通和思想交流。正如李震在《语文教学智慧与策略:迈向生命化课堂》中所说,“生命化语文”即以“言语生命”为一切教学思想和行为的原点,力图提升生命的质量,顺应并引导每一个个体言语生命的融通、健康、和谐而又富有个性地完整性发展[1]276-277。
对此,李震又做了具体化描述,明确“生命化语文”就是这样一种教学:转变多年来漠视汉语言文字的文化特性,摒弃了汉语言文字重心灵感受的基本精神,而盲目照搬西方语言统摄下所建构起来的教学理念、教学模式,我们必须重建以汉语言文字为核心的“生命化语文”教学主旋律,直面人的生命,遵循生命成长和发展的特点,以生命的言语品质发展为目标。“通过学生亲历和历练的语文实践活动,让学生在品味言语中舒展自己的生命,体验自己的生存状态,获得言语感知和情感丰盈的惬意,以汉语文的生命精神和生命意识促进言语生命的言语和精神同构共生,最大限度地使言语生命发展的潜在可能性变为言语创造和自我实现的现实存在性,从而达成言语生命在更高层次上的和谐。”[1]277在这个描述说明基础上,李震老师特别做了两个明确阐释。
第一,“生命化语文”的教学指向。具体点说,就是重建“语文课回归汉语文本体”的教学。一方面“生命化语文”要重新植根于汉语文本土文化,把握汉语文教学的文化特质;另一方面也昭示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与交融中,要大力标举“生命化语文”教学,勇于走向“言语生命”的新拓之路。因为西方科学理性教学观否定语言是人的生命形式,是活泼泼的人性舒展与跃动,过度追求语言表达的外显化、机械模型化,而忽视了语言表达的情意化,往往要靠直觉感受体验来内化,需要在一种内在情感的激发驱动下,在特定语境的感染陶冶过程中激活、点燃。因此,李震和他的团队着力开拓“生命化语文”的新场域,注重引导学生用自己的感官去触摸语言文字构成的字、词、语句,以抵达汉语言文字组合的情感世界深处,“感悟……我们汉语文的内蕴和真义”[3],感受主体生命所焕发出的光彩与神韵。如李震强调的,语言文字是有力度、有温度、有厚度、有美度的,要加强对汉语言文字的触摸与感悟,加强对语义世界深层文化内涵的品味与涵泳,打破机械式的技术操作——把原本气韵灵动的言语作品肢解成支离破碎的语码,从而彰显“生命化语文”教学的活鲜特色[1]351-356。
第二,“生命化语文”的教学功能。从“言语生命”的理论来说,言语可直接铺展为人得以栖居大地的家园,人就居留于言语的家中,言语就是存在本身。李震教授和他的团队发现,言语表达了人与世界的一切关系,人以言语的方式拥有世界,同时也完成了自身作为存在的生命建构。这是因为,言语作为符号,不是单纯的传递、交往载体,还蕴蓄了文化的因素、精神的内容。换言之,言语生成的语言符号是文化的底座,文化又是语言的存在。由此,李震和他的团队,从理论上把握了“生命化语文”的根底。在教学实践中凸显“生命化语文”的生命意识和主体精神,在语言文字的构成中发现并强调汉语文蕴蓄的文化精神,汉语文自此不再是外在于人的单纯手段和方式,不再是一种用时拿起来,不用时放在一边的语码,而是人和世界的交接点,“生命化语文”能把人和世界不可分割地联系并同构在一起。就人和语言的关系来说,人通过语言表达昭示自身的存在情态,语言就是人的有机构成部分。李震强调:汉字具有鲜活的生命力,理解和运用的过程中能感受到汉字藏着的诗意和生命的滋润[1]371-374。在这个意义上,“生命化语文”使语言成为血脉贯注、生机勃勃的生命主体,成为文化特质鲜明、精神底蕴丰厚的开放结构,召唤着他人的现身情态以及参与对话和交往行为。这显然是透彻摸清了“言语生命”的真义,从而建构了“生命化语文”的教学思想。
2.回归生命:一种生命化语文的教学视角
叶澜曾经指出:“教育具有鲜明的生命性,在一定意义上,教育是直面人的生命、通过人的生命,为了人的生命质量的提高而进行的社会活动,是以人为本的社会中最体现生命关怀的一种事业。”[4]139在一定意义上,教育即生命。李震和他的团队建构的“生命化语文”,其实就是“在起点上,直面人的生命;在过程中,通过人的生命,遵循生命的本性;在结果上,促进生命的成长,追寻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提高生命的质量。直面生命是前提,循于生命是保证,达于生命是目的”[1]282。人的生命成为教育的立足点和价值追求,“生命化语文”自然也不例外,它在语言文字运用中始终关注人的生命存在并致力于人的生命建构。
回归生命,作为一种生命化语文的教学视角,就是把我们的母语教育作为一种“民族文化的教化”。李震和他的团队标举并实施的“生命化语文”教学,对青少年学生的生命成长和完整性全面发展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实质上,“生命化语文”是为人的一生奠基精神底色的教学,是以其饱含的文化情感、民族的智慧和精神对人的生命进行潜移默化的诗意润泽和点染提升,全面开展人的精神建构。为此,李震老师以“生命化语文”的课例做分析,如他的《梅岭三章》示范课[5]134-139、宋凯老师的《周亚夫军细柳》问诊课[6],都不单单是语文知识、交际能力的语用活动,而是文化融入语用本体,形成心灵与文化的同构。这种教学都凝聚着生命个体独特的激情、思考、梦想等情感体验,浓缩着汉语文的民族精神财富。学生阅读课文的过程,会与其内在的生命因素和精神内涵产生感应,进而化为自身文化素养的有机构成。具体些说,“生命化语文”的教学视角,指出一个重要的“打破”、一个明确的“强化”。
其一,回归生命,打破传统的语文教学一直存在的生命缺失现象,关注的是人在语言文字运用中的现实存在,注重语用个体生命存在状态的真实。用一句话来说,就是摒弃习惯于教学以“共性”为前提,而不习惯于以“生命个性”为依据的教学常规,即所谓的“人”只是群体符号象征,而不是有个性、有生命的活生生的个体存在,在教学中就体现为培养接受知识的“容器”而忽略生命本有的主体性和创造力的发展。实施“生命化语文”的教学,学生不会再沦为被动的承纳者而遮蔽了个体生命的光华。如李震在《语文教学要善于唤醒》一文中强调要唤醒文字形象,唤醒生活经验,唤醒文化积累,唤醒审美关照,让学生重新享受汉语文生命的阳光雨露[1]358-366。
其二,回归生命,强化生命本有的主体性和创造力的发展,培养学生完善生命个性。在教学实践中,强调汉语文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意义以及对人的精神世界的建构,强调汉语文的文化情致和生命特质,倡导并推进汉语文的鲜活的语用感应和体悟活动。让“生命化语文”消解单一的理性认知,呈现活生生的生命存在,打开汉语文生气勃勃的生命成长通道。语文之于人,不容置疑,具有语用的功能和价值,但语用活动也是一种生命的存在,一种文化的存在,语用的过程就是生命活动的过程。从人的生命成长和发展的过程看,语用过程就是一个文化润泽、精神培植的过程,是人之成人的过程,它必然要求生命的全面出席和始终在场,吁求生命的激情投入和积极建构。因此,李震强调“滋润生命”,即“生命化语文”的教学要为个体生命提供适宜的条件,如生动形象的情境、如坐春风的氛围、宽容温情的态度等[1]335。这作为“言语生命”的活动形式,必然使语文课充满生命活力。
二、“生命”的凸显:生命化语文开掘的个性化
站在人的生命哲学和生命发展的高度,我们就可看到“生命化语文”教学在指向语用知识的积累和语用能力训练的过程中,也有力促进生命意义的开掘和生命精神的发展。所以,“生命化语文”教学的语用过程实质上是生命主体的参与和建构,是生命与生命交流的过程。它体现的是“言语生命”的特质,遵循生命发展的个性化法则,引导生命得到完整性建构。
1.爱与关怀:生命化语文教学价值与方法
“生命化语文”的教学,是在语用活动中生命对生命、灵魂对灵魂的主体性教学。这样的教学并非是一种“心灵隔离的活动”,而是“人与人精神相契合”,“人对人的主体间灵肉交流活动”[7]2-3。因此,“生命化语文”的教学就是让学生享受“言语生命”的阳光补养,在“语文与生命”的语用活动中诉诸人与人的生命交往和沟通,真诚深切的爱与关怀是生命交往和对话顺利开展的前提和保证。在李震和他的团队看来,在教学中如果你要得到语用的享受,那你就必须是一个有语用素养的人。如果你要用语文感化他人,那你就必须是一个能激励他人爱语文的人。“生命化语文”教学作为师生间的一种交流活动,应遵循主体间性的要求,彼此关爱、尊重、理解、开放并相互承领对待,充分体现语文化育精神、滋润情感的价值诉求。如张团思老师执教的《声声慢》[8]217-222,其教学之境,即语境、情境、意境、心境,让学生用心灵触摸到悲苦,从而得到心灵的洗礼。教学过程不是主体与对象的关系,而是生命对生命、主体与主体的平等相待,注重的是对人的生命的呵护和关怀。于是,“生命化语文”教学成为与人的生命、情感、心灵同构相融的活动,富有爱的抚慰、情感的激荡,整个语用过程充溢着生命活性和价值关怀,通贯着语文对人的自觉的理解和沟通。
首先,“生命化语文”教学是对生命个性的尊重,这也是一种生命化教学精神内涵的基底。尊重个体生命意味着教学是把学生视为活生生的人,有独特个性、独立的意识和行为能力的生命存在,教学要致力于唤醒、激发学生潜藏的无限的创造性和发展可能。因此,李震指出,要善于“激发生命活力”,强调生命个体之间的交流和碰撞,以促使生命的流动[1]336。这种流动包括思想、情感、知识、兴趣、爱好。生命因流动而鲜活,生命因鲜活而富有创造。人有基本的情感、尊重的需要,当学生感受到情感和心灵的温存和爱的挚诚关怀、鼓励和尊重,他的生命本性和内在活力就会被激发出前所未有的生命力量,自觉自愿地投入语言建构与运用活动过程中去,积极主动地去阅读体验、去沉潜涵泳,充满自信地与他人展开交往并表达自己的思想与情感。这是一种活生生的教学过程。这样一来,“生命化语文”教学在个体生命的主动参与下迸发出勃勃的生机和生疑求鲜的个性魅力。
其次,“生命化语文”教学相信学生具有无限创造性和发展潜力,对个体生命的成长怀有热切期待。人的生命是一个生生不息的发展的过程,每一个体都是具有自我激发、自我创造、自我规定的自为性的生命存在。因此,李震和他的团队在教学中从不因为学生一时的不足而对其进行否定性的评价。他们在教学过程中始终怀着一种真诚的期待和信任,并在日常的教学生活中将这种信任和期待传达给学生,让学生时时感觉到爱与关怀,从而化为自身行动和发展的内在动力,以主体的姿态参与语用意义与人生意义的建构。需要强调的是李震和他的团队,对学生的期待和爱的关怀最终指向学生语用教学活动中天真本性的舒展、张扬和生命的超越,而不是以自己的爱和信任作为让学生顺应而实施控制、训练的手段。因此,“生命化语文”教学对生命特性的关爱,绝不是对内在生命情怀的简单的干预,而是一种陶冶、一种自主之境中的默化,个体生命在信任、期待的目光抚慰和鼓励下,在积极、活泼、明朗的语用情境中得到滋润、丰富、延展、充实。如张团思老师的《声声慢》教学[8]218,让学生把意象化为情感,把诗人身世化作同情,这显然是学生个体心境的精彩展示。这就是说,“生命化语文”教学总是充满生气,对个体生命的期待、肯定、激励,对生命的呵护,热情洋溢的韵致,自主舒展的空间,都成为生命创造、发展的基础和保证。
从这个意义上说,“生命化语文”教学,是丰富多彩的生命活动的过程,本质上是一个阔大的生命精神空间的开拓,师生都是自我生命情感的主体投入,语用教学过程最终指向生命的成长与发展,以平和宽广的心境、诚挚接纳的态度来尊重生命的多样性,赏识学生的独特个性和完整生命,聆听学生灵魂深处质朴纯澈的心语,激发、捕捉学生稍纵即逝的创造灵光,对学生的点滴进步和发展予以肯定性评价。李震和他的团队践行的“生命化语文”教学提供了生动的教学智慧和思想启示。
2.生命完形:“生命化语文”教学审美策略
从某种意义上说,“生命化语文”,也可说是一个特定的生命“完形”。所谓“完形”,即指一种由主体的感受知觉活动组成的整体。自然世界与艺术世界里的语言、符号,或是一个抽象的点或线,也都包含着复杂的情感结构和生命特质。因此,艺术作品莫不与人相感应,与人的心灵相契合。这种“感应与契合”,既意味着与勃勃生机的自然力融为一体,也意味着与人的生命交流对话。因此,李震和他的团队注重把握“生命化语文”教学审美策略。
第一,“生命化语文”的言语作品,实质上是特定的审美完形。无论是一个文本,还是一篇课文,都是一个审美的“生命完形”,体现着作者全部的生命体验和人生感悟,是凝结了主体的情感、想象、理思、认知等诸多因素的生命形式。每一个作家都能在一个优秀的作品中看到“生命”,每一个画家首要的任务便是赋予他的绘画以“生命”。作品的生命力就是作者贯注其中的情感和生命,它以其特有的生命情感和思想光芒穿透和照亮每一个存在的对象,使整个艺术性作品呈现出鲜活而灵动的神韵和闪亮光彩。李震在《中学语文教学的美育途径》中对这类作品表现形态的解读,就是把握把它作为作家的生命之源和精神之气,强调一个语言形式就是一个生命形式[1]127-138。对这样的作品观照并不采用实证、分解的方式,而是采取感知美、发现美、创造美的策略,即整体的、情感的、体验的方法,用自己全部的生命去同构、去感应,以重现作品的生命样态,彰显出“生命化语文”审美教学特色。
在教学中精确把握文本的生命完形,课堂上能整体呈现文本一个个情感样态丰富变化的生命形式,与学生内在的情感结构契合无间,这种教学情景能使人得到审美享受。语文教材中选取的课文,大都体现着鲜活多姿的生活样态,都活跃着七情六欲的人,每一篇课文都记录着一个生命深刻的情感体验,贯注着一个生命不懈的情感追求,是生命个体自己的一种情感和意义世界的敞亮。如《背影》中的父子亲情,《藤野先生》中的师生情谊,一篇篇的课文汇集在一起,折射着人间万象的情感世界。李震和他的团队在“生命化语文”教学中充分挖掘、利用课文中的情感因素,通过合理的教学手段和方法引导、激发学生深入审美情感体验,唤醒他们的审美情感,促进个体生命的生成和发展。
第二,“生命化语文”教学文本,教学主体要化入审美的体验。审美并不排斥理性认知的因素。因此,李震和他的团队“带领学生从课文中走个来回”,让学生“能入善出”,即努力为学生的语用学习营造适宜的审美情境和氛围,促使学生全身心投入课文的审美体验,调动起自身的感知、理解、领悟等心理要素去触摸、体认生命化语文世界。在彼此相通、震颤共鸣的过程中,获得如品其味、如聆其理的真切感受和审美体验。
需要强调的是,“生命化语文”教学特别着意引导学生获得鲜活生气的情感同构体验后及时转入理智深悟和对文本意义世界的形而上思考,促使学生联系自己的语用经验,对文本进行新的意义诠释,赋予它回旋喷涌的生命活力,这“对学生欣赏与创作能力的培养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9],实质上是审美的最佳境界。可以说,学生对文本生命的整体观照和把握,是拆解、是移情、是体验,是主体进入文本世界,以自己的明敏灵性去体认文本世界,是物我同化;形而上的理性审视则是回味、是赏鉴、是审思、是重构,是主体出乎其外,凭自己的智慧理思去审视、探奥文本世界,这就形成了共同完成“生命化语文”教学的完整心理流程,正如王国维《人间词话》中所言:“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10]335。其实,李震和他的团队成员对教学文本的解读莫不如此,能入善出方能更好把握文本的情感结构和艺术营构,参悟其情理意蕴。
三、“生命”的建构:生命化课堂的教学语用性
随着“生命化课堂”的教学实践,李震和他的团队教学观发生了变革,他们认识到生命化课堂就是基于核心素养培养学生的语用能力,以人为本,注重以文化人,强调生命化课堂的建构根本上就是生命建构,通过语用促进生命的完整性发展。具体到课堂的语用教学实践,就是要把落实语用能力作为核心。因此,他们的“生命化课堂”教学变革和实验,摒弃了以往课堂形式上的操作模式,取得了明显的课堂教学成效,即注重语用教学的文化渗透,把“生命化课堂”作为语用的文化渗透活动,力图在语用中提升生命的质量。
1.重建“生命化课堂”的语用教学认识
长期以来,我们将课堂的语用教学仅看成是一个传递知识、培养技能的过程。李震和他的团队把“生命化课堂”作为语用的文化渗透过程,有意识地在语用的文化渗透中注重课堂教学内容的选择和接受。如李震在《行走在语言世界中》用不少课例来说明语用感受能丰富学生心灵,在生命化课堂教学中如何精心设计并切实开展语用的文化渗透活动[1]180-186。所以,学生获得了有价值的语用文化知识,丰富了自身的文化情感体验,培养了语用的文化创造能力,学生逐渐成为健全人格的语用“文化人”。这一“生命化课堂”的语用文化渗透过程,与学生的生命活动实现了同构。过去,我们有一个权威观点,即“教育是一个特殊的认识过程”。实际上,李震和他的团队将认识活动从生命活动中剥离出来,大力实行“生命化课堂”文化渗透的语用教学,从而发掘了学生的语用文化需要和潜力。显然,他们对“生命化课堂”的语用教学是从生命活动的高度进行观照的。
需要指出的是,李震和他的团队重视“生命化课堂”,转变了教与学的主体认识,强调“生命化课堂”作为文化渗透的语用主体,是向着学生自身的完整性生成所进行的一种语用文化自觉、主动的自我发展行为。李震从不同的层面强调,“生命化课堂”文化渗透的语用教学,要改变“唯师”的思维定式和行为习惯,要“尊重学生的诗意栖居”[1]345,“尊重课堂的学生角色”[1]346,鼓励学生在课堂上发挥语用积极性和主动性。对教师而言,要认识到“生命化课堂”文化渗透的语用教学不只是一种教学手段,更是以自己的语用知识经验与学生互动进行的一种创造性的语用交流和对话;对学生而言,“生命化课堂”的语用活动不只是为了获得语用知识、经验和技能,更重要的是要认识到语用的文化渗透是自己生命活动的一部分,是课堂文化渗透的语用活动主体,是对语用所呈现的文化内容进行选择、判断、吸收和创造的过程,是语用文化渗透中自主性、创造性的发挥,直接关系着语用的质量和水平。实际上,在李震和他的团队看来,“生命化课堂”是搭建“师生交往的平台”,文化渗透过程是平等的语用对话交流[1]347。教师和学生的活动虽然在语用活动中不尽相同,但在文化渗透的生命价值上是等量齐观的,教师和学生都是以生命主体的角色进行语用的文化渗透,以促进“生命化课堂”达成文化渗透的新场域。
2.注重“生命化课堂”设计的文化渗透
“生命化课堂”是由一定的语用目标、语用内容及语用活动方式组成的。从教学场域考察的角度看,实际上是一种语用中文化渗透与发展的人的生命对话活动。其目的在于唤醒生命个体的情感智慧,使每个生命个体具有成长和发展的勇气和信念。李震和他的团队实施的“生命化课堂”就是一种语用教学的文化渗透培育。
第一,“生命化课堂”设计的目标和原则坚持文化本位,立足于生命的建构,主张课堂语用教学旨在通过文化渗透活动来促进学生的完整性建构。所以,课堂设计目标既考虑实现文化渗透的传递和发展,又重视个体生存发展的价值,能满足学生的各种文化需要。如王旭彤执教的《“诺曼底”号遇难记》示范课[8]59-60,通过对话策略引导学生感受语言运用的形式之美、品悟语言运用的文化之美、体验语言运用的生命之美,就体现了这种“文化渗透与语用教学”同构的课堂设计特色。因此,李震和他的团队对“生命化课堂”设计遵循了以下两个原则:一是立足现实、面向未来,着眼于人的语用能力和文化素养长远发展;二是课堂设计的语用文化知识内容合理有序,使学生在课堂上不仅掌握语用文化知识技能,而且能感悟和体验到语用文化渗透中接受的情感和价值观念。
第二,“生命化课堂”在教学内容的选择上主要选择对学生最有价值的语用文化内容,即最有利于学生发展的语用文化内容,在一定的课堂上主要以语用知识经验的形态来呈现。
结合语用的文化渗透特性,李震和他的团队对“生命化课堂”语用内容的具体选择,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第一,语言文化,即语言所蕴含的本体文化,包括汉字、汉语、修辞、文体、文学等方面所构成和体现的语用文化。第二,与学生生活密切相关的语用文化。学生所处的是一个文化开放的信息时代,课堂教学作为联系传统和现代的纽带必须与社会时代文化同步,不可脱离时代文化生活,应及时吸取传统文化的精华来满足学生敏锐的文化需要。如王晓青老师执教的《我爱汉字》活动课[8]303-306,转变课堂教学模式,让学生做文化卡片,触摸先民与书法家的生命脉搏,从“家”“安”等汉字中透视先民对安定祥和与生命的追寻。同时,思姓名字源、讲文化故事,引导学生关注自我,又敬畏生命,从而在汉字文化场域中获得特有的感受和体验。显然,这种“生命化课堂”能培养学生的语用文化判断力、鉴赏力和思维水平,促进学生“文化渗透与语用能力”的完整性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