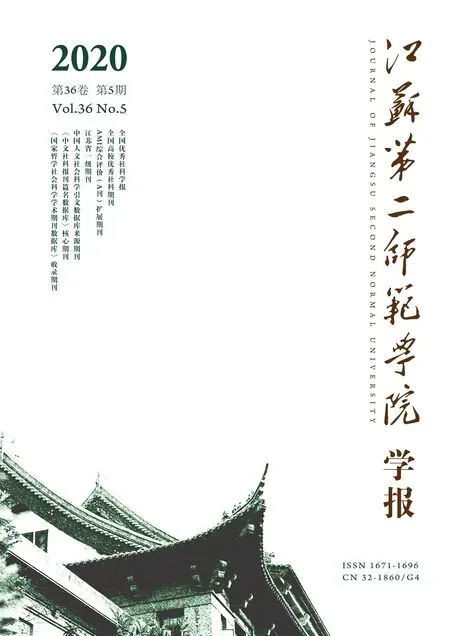从“穿插”到“互文”*
——《聊斋志异》对“以诗词入小说”叙事传统的开拓
方 弘 毅
(东南大学艺术学院, 江苏南京 211189)
就文体而言,小说长于叙事,以无韵的散文为主;诗词侧重抒情,强调韵律。而中国古典短篇小说从发端就形成了“以诗词入小说”的传统,如陈寅恪所言:“诗笔即谓诗之笔法,指韵文而言”[1]5。因此,要准确理解古典短篇小说与诗歌的关系,首先必须从诗歌在小说叙事结构中的功能以及韵散结合方式的差异入手进行梳理,进而分析作品的诗性内涵与艺术价值。本文认为,从古典短篇小说与诗词的关系而言,可分为四种历史形态: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唐传奇、宋元话本和以《聊斋》为代表的清代文人小说。前三种历史形态中,韵散结合的方式以“穿插”为主,模式较为机械,而作为清代文人短篇小说扛鼎之作的《聊斋》将诗词与小说两种文体相互融合,具有鲜明的“互文性”。不仅灵活而娴熟的运用“诗笔”,显示出高超的艺术才能,而且彰显出独特的人性价值和丰富的诗性气质,造就了中国古典短篇小说创作的崭新高峰。
一、《聊斋》以前古典短篇小说“以诗词入小说”主要历史形态
从现存的作品看,古典短篇小说在先秦两汉时期已经出现并具备一定规模,但其作为独立文体成熟的标志当是汉魏六朝笔记小说的出现。《文心雕龙》有言:“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2]655,可见所谓“笔记小说”主要是以散文笔法进行叙事,但又多以“曰”“其诗曰”“作诗曰”“《诗》云”等引出诗词韵语辅助行文。其来源及功能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以诗词抒发主要人物情感,推进情节发展,丰富人物形象。笔记小说的主要内容是以“粗陈梗概”的语言记述人物逸事,情节结构比较简单,人物形象亦较为单薄,于文中穿插诗词可看作是对叙事的补充。例如《搜神记》中描写韩重悼亡之时,巧妙穿插了紫玉公主的自诉诗:“故见鄙姿,逢君辉光,身远心近,何当誓忘”[3]190,寥寥数语,微言大义之中突出了紫玉公主对爱情的忠贞不渝的形象,烘托出强烈的感伤氛围,使得主要人物更加生动鲜活,成为整篇作品中的一个亮点。其次,直接引用《诗经》或俗语对情节加以佐证,揭示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说明人物的某种特征。从文体上看,这种引用一方面是受当时文风的影响,另一方面也起到了抒发人物情感,突出作品内涵的作用。应当指出的是,汉魏六朝小说中不论是引用古诗俗语抒情叙事还是穿插原创诗词韵语表现人物情感都十分契合人物形象,符合情节发展的需要且多是以小说人物的口吻脱出,显得十分自然得体,可以断定是作者深思熟虑之后的艺术创造。
总体而言,汉魏六朝笔记小说中穿插诗词韵语数量不多,也远未形成固定的模式,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唐传奇兴起之前。从古典短篇小说发展的脉络考察汉魏六朝笔记小说与唐传奇源出一脉,但与汉魏六朝小说搜集整理与集体创作杂陈的状况迥异,唐传奇不仅在文体上更加成熟而且多出自文人的个体创作,因此唐代的短篇小说创作实现了作品数量和质量上的飞跃。其中,质量上的飞跃主要体现在唐传奇在结构安排上更加精巧,情节描写有了较强的虚构性、故事性,人物塑造也更加个性化。较之汉魏六朝小说,唐传奇穿插诗词的数量大为增加,结构上也开始形成固定的程式:首先,几乎绝大部分唐传奇作品都插入、引用或截取了诗词,有些传奇作品则是直接取材于诗歌而写成的。例如《飞烟传》中共出现了七首完整的诗词作品,《长恨传》等作品多取材于文人诗歌或乐府。其次,在结构布置上传奇中的诗词多出现在情节发展的高潮部分,多为主要人物表明心志、烘托情感之用;也有出于作品和情节完整需要的诗词穿插,如描写送别、宴饮酬答等特定场景时通常会安排诗词作品;或以诗词承接下文,为后续情节埋下伏笔。这些安排一方面体现了唐代文人以作诗词炫才明志的文化风尚,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唐传奇融“史才、诗笔、议论”一体的文类特征。最后,唐传奇的诗词穿插较之汉魏六朝笔记小说更加灵活,不再是笔记式的可有可无的元素,而是融于整篇作品叙事之中推进故事发展的有意为之的设计。
宋元时期话本小说的出现标志着短篇小说中诗词韵语的穿插有了可遵循的成法。“话本”是以说书底本为基础加工而成的,因而在诗词穿插的文本模式上与前两种短篇小说类型有较大区别。按照说书人叙述故事的顺序,话本当中的诗词有了固定的位置和相应的功能:“篇首诗”一般篇首出现,多数引用古诗起到引出作品主题的作用,也有概括作品主题和价值取向的自作诗。“篇首诗”作为整篇作品的引子,在结构上引领全文,称之为“入话”。“分回诗”出现在故事情节转折之处,具有总结前文,承接后续情节的功能,从而为故事的发展留下悬念,引发观者兴趣。在整篇话本的末尾通常会出现“收场诗”,总结全文,抒发作者感受。除此三种固定模式之外,宋元话本中还存在根据说书节奏或情节发展的需要于文中其他位置插入诗词的情况。以“三言”“二拍”和《清平山堂话本》中保存的话本作品来看,这类情况通常出现在对客观情况的描绘、对故事背景或主要人物特征的必要交代或以旁观者的视角对情节发表议论之时,自作诗词、引用俗语旧作皆有,带有一定程式化色彩,如介绍女子外貌时通常以含有“桃红”“香肌”“玉肌”等词汇的诗句形容或以“嫦娥”“织女”等形象比喻,并没有太多个性化的描绘。总体而言,宋元话本中的诗词插入继承和发展了汉魏六朝笔记小说与唐传奇的功能模式,又有适合自身需要的发展。一方面,宋元话本发扬了以诗词写人、议论、抒情、状景的传统,以彰显话本艺术“讲得字真不俗,记问渊源甚广耳”[4]199的追求;另一方面,话本的诗词穿插较之前两种形态更加随意和自由,与笔记小说简略的叙述和传奇小说中立的叙事不同,“说话”过程中艺人必须以“全知者”的身份把握、操控故事情节的发展,于是穿插诗词便成为驾驭上下文关系,在叙述过程中灵活随机抒发说书人议论,揭示人物心理活动的主要方式。
总之,通过对上述三种古典短篇小说发展的主要历史形态中诗词穿插的运用经历了数量上的由少及多,方式上由简到繁,功能结构上的由机械单一到灵活多样的漫长过程。汉魏六朝笔记小说与唐传奇以文言为主,作者或整理者都是文人,诗歌的文辞典雅,不论叙事、议论、抒情都达到了较高的艺术水准;宋元话本为白话文偏多,是说书人的集体创作或改变,虽然其中大多能与故事情节交融映衬,其中不乏构思精巧的作品,但在文辞上不免陈词滥调,水平参差。不论如何,前人的这些丰厚探索为《聊斋》进一步开拓“以诗词入小说”的崭新艺术境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提供了极富价值的借鉴。
二、《聊斋》“诗稗互文”艺术境界的开拓与创造
在清代之前的小说和诗词创作中,就历来存在同一文本中共时性前后文互相渗用、互为依托、互相补充或不同文本中历时性的同题异作对某一相同题材进行演绎的情况。这种手法可称之为“互文性”,如将诗词韵语插入小说。《聊斋》在创作上的一大贡献就是丰富和发展了小说与诗词的“互文性”[5],其中诸多作品都能够技巧娴熟地交融众法,真正实现了跨越诗词、小说两种文体间多维度的功能互用与互化。
《聊斋》对古诗词的运用之所以能达到如此之高的艺术境界,与作者蒲松龄对前人诗词广泛、深厚的积累、勤奋的学习和较高的诗词创作才能有着莫大的关系。对于明清时期的读书人来说,不专心于八股时文而钟情于诗词不仅是不务正业的旁门左道,而且其自身也将时刻处于科举应试与专心兴趣的矛盾与纠结之中。蒲松龄也是如此,一方面举业功名于四书五经之外的“不令旁及”,八股制艺也强调“尤不可带词赋气”这些陈规无不时刻束缚着明清读书人之“诗笔”;另一方面,自幼喜好诗歌且“观书如月,运笔成风”的郢中诗社盟主少年科场得意的蒲松龄却纵情于“嘉宾宴会,把盏吟思,胜地互逢”的“朝夕吟咏”[6]27。尽管也曾有过“憎命文章真是孽,耽情词赋亦成魔”[5]的矛盾,但蒲松龄一生始终没有放弃对诗词的研习,即使在科场失意之后仍旧“肆力于诗歌古文辞”,对此他曾写诗表露心迹:“客久浮名心易冷,愁中诗酒戒难持”[6]1602,甚至在内心深处将对诗词学习与创作置于小说创作之上:“狐鬼事业属他辈,屈宋文章自我曹”[6]1687。综合蒲松龄的诗词创作来看,当时出于三个方面的动机:首先,是出于自身的狂热爱好,将诗词研习视为科举的“补业”;其次,借诗词曲赋以炫才,这一点从《聊斋志异》中大量的诗词曲赋以及《聊斋诗集》的大量创作上可以得到证实。蒲松龄少有文名,诗词曲赋颇为时人称道,所谓:“少年与邑李希梅及余从伯父历友、视旋诸先生结为郢中诗社,以风雅道义相劘切,始终一节无少间”[6]3446。清代除科举之外,亦开“博学鸿儒”,举荐“文词卓绝之人”,由此分析蒲松龄以诗词曲赋炫才有可能是想借诗词技艺功名;最后,在科场屡屡失意之后借诗词抒发胸中愤懑,并将诗词曲赋通通介入《聊斋志异》的创作,达到“借稗传文”的目的。总之,蒲松龄在诗词上的勤奋研习和横溢才华并没有给他带来功名,却为《聊斋》增添了无限光彩。
1.“以故为新”脱化前人诗词入小说
《聊斋》“以诗词入小说”方面最大的特色在于其中作品不仅有大量的诗词穿插,更擅于将前人诗词的内容及意趣巧妙地脱化入小说叙事之中。所谓“脱化”[7]其方式应当包括:前文论述过的对前人诗词的引用和穿插,用于新的情境;借鉴与暗示性的衍用前人诗词的情境、本事;隐喻、暗喻、暗示性的点化前人意境,进行再创作。对《聊斋》中的脱化笔法已经有了非常详尽的研究,本文重点论述的是《聊斋》以前人诗词之“意”融入小说创作,并彰显出崭新意境的艺术手法。“脱化”最早起于诗法,显见于宋诗“夺胎换骨”“点化”“脱换”之法,蒲松龄将其广泛运用于《聊斋》创作通汇百家而不留痕迹。
《聊斋》擅长将前人诗词意象化入小说,以创造更为丰厚的新意象。其中以恣肆浪漫者为最多。正如王渔洋所说:“料应厌作人间语,爱听秋坟鬼唱歌”[8]285,《聊斋》擅长写鬼,营造秋天的萧索氛围,因此多化入李贺、屈原、杜甫等人诗歌中秋天的意象,如“白杨”“枫林”“萧萧”等。此类意象不仅在《公孙九娘》《连锁》《林四娘》有巧妙地运用,而且亦多见于蒲松龄自己的诗歌作品。《聊斋》最杰出的艺术创造在于衍用前人诗意,作为叙事的开端或故事的场景。如小说《宦娘》就是对《关雎》《棠棣》相关诗意的衍用。小说以“琴瑟友之”“如鼓琴瑟”之诗意展开情节叙述,描写精通琴艺的温如春得遇知音良工,并在女鬼宦娘的努力下终成眷属的故事。满纸浸润着宦娘、良工与温如春三人琴瑟和谐的互相爱慕,女鬼宦娘虽为温如春的知音却奈何为鬼不得与之结缘,她转而成功撮合良工与温如春结合。小说结尾写宦娘“出门遂没”,可谓意味无穷,既有宦娘思心上人而不得的遗憾,又有其对有情人的美好祝愿,此篇的情节设置当是作者创作时心境的写照,又与原诗意境高度契合,堪称绝妙。又如《荷花三娘子》一篇写三娘子由花化人,由人为石,又因与宗湘若的至情所感,再次夺胎为人。此篇的情节直接化用于陆游诗句“花若解语应多事,石不能言最可人”的意境写照。此外,《婴宁》《小翠》《瞳人语》等篇目中皆有化用诗词意境,作为小说情节场景的情况。
2.诗稗意象的关联与互用
蒲松龄不仅有深厚的诗词积累,自己创作的诗词也颇具水准。《聊斋》当中不仅保留了大量蒲松龄的诗词创作,还大量存在小说情节叙事与诗词内容互相化用、互用的情况。对此,有研究成果已经从题材、意象的关联性维度将蒲松龄的诗词创作与小说创作进行了比较,并认为二者间存在互文的情况。本文认为,机械地将蒲松龄诗词与小说中的某几个意象提取出来对比研究,强制阐释其间的互文关系显然太过局限,但是蒲松龄创作的诗词与小说的确有诸多意象互用、文辞相似之处。总的来说,不论诗词小说其笔下女子多妩媚绮丽、空灵多姿,其诗词《梦幻八十韵》《西施三叠》等作品可谓:“缠绵艳丽,如登临春、结绮,非复人间闺闼”[9]468;在《绛妃》《公孙九娘》《小翠》《胡四姐》《青凤》《巧娘》等诸多小说作品中也有大量相同或类似意象频频呈现。如“拈带”“俯首”“嫣笑”“哀曼”等描摹女性情态的意象,又如“垂鬓”“倾鬓”“罗裙”“绣鞋”等描绘女性穿着打扮的意象,在蒲松龄的诗词和小说创作中便时常共用,相得益彰。还有一些小说中直接描绘与诗词相关的情节且栩栩如生,当时取自作者鲜活的生活体验。如《白秋练》中数次详细的叙说了主人公吟诗派遣心郁的经历,在《聊斋诗集》中也多见类似诗作,如《为青霞选唐人绝句百首》《听顾青霞吟诗》《伤顾青霞》等作品。
当然,也会出现诗词与小说呈现直接互文关系的情况,如《林四娘》中详尽描写林四娘与陈宝钥度曲吟唱,先极言其乐,转而又“亡国之音哀以思”“意绪苦痛”哀乐对比,跌宕起伏间写尽离别的感伤,在《连锁》《书痴》等小说作品中也有大量笔墨描写女子的才情与离别的感伤。该题材在蒲松龄诗词中也颇为多见,《赠妓》《树百宴歌妓善琵琶戏赠》之类写歌妓音乐才华的诗词,从情感方式到所用意象都与上述小说中的情节相一致;诗歌《试后示篪、笏、筠》中说阅卷之人“心盲”“目瞽”与小说《司文郎》中和尚的叹语高度一致;蒲松龄还擅长将诗歌意象与小说意象相融、相契:如《丐仙》中:“中有花树摇曳,开落不一;又有白禽似雪,往来句舸于其上”[8]1707充满了诗情、诗意,《聊斋志异》中多数作品均有这种以诗化韵语直接入小说的情况。因此可以认为,这些小说中相关情节的描写是诗词所表达情绪、主旨的延展、演绎与整合。
3.诗词与小说文体功能的转换与整合
蒲松龄是一位情感丰富、长于诗词的小说家,这几种身份在其创作实践中时常互相跨越、互相转换。他不仅实现了诗词、小说之意象互用、文辞相通、题材共用、语言相融,而且还将二者的文体功能互相转换与整合,从而达到抒情叙事交相辉映,亦真亦幻的艺术至境。对此,陈寅恪曾做如下评价:“清初淄川蒲留仙松龄聊斋志异所纪诸狐女,大都妍质清言,风流放诞,盖留仙以齐鲁之文士,不满其社会环境之限制,遂发遐思,聊托灵怪以写其理想中之女性耳。实则自明季吴越胜流观之,此辈狐女,乃真实之人,且为篱壁间物,不待寓意游戏之文,于梦寐中以求之也。”[10]75这段话精辟地指出了小说与现实的关系说明《聊斋》中之狐鬼塑造不仅直接取材于现实中的人和事,而且还寄托着作者自己的生活经验与情感。蒲松龄以跨越多个角色的“易性”视角写“闺情”,将自我的情感状态融入小说叙事。《连城》的男主人公“乔生”向女主人公连城求爱时的赠诗即是蒲松龄的诗作《闺情呈孙给谏》的前四句。显然,“乔生”就是蒲松龄的化身;《宦娘》中写到良工在听琴过程中对温如春心生倾慕,宦娘对此亦悲亦喜,凝成一阙《惜余春词》吐尽求爱不得的闺怨,这首词是推进故事发展的重要因素,起到承接叙事结构的重要作用,写尽思慕,凄婉柔美,经查证此词是作者由《惜余春慢·春怨》原文移入,记录的是蒲松龄“男子作闺音”的真实情愫。作者将自身精神诉求、情感取向化入笔下人物,于婉转曲折间借助丰富多彩、性格生动的不同人物类型抒发自己不同阶段的喜怒哀乐,在真幻跨越间穿插自如,得心应手,自然流露。
一般而言,诗词抒发的是创作主体的真情实感,而小说需要创作主体以“他者”视角完成叙事。《聊斋》的高明之处恰在于通过“易性”创作、移入己作等方式将自己的真知灼见、款款深情化入小说中的角色,于叙事过程中自然吐露;在小说叙事之中根据角色特点、情节场景融注入对应风格诗词,传情达意,能够使人物塑造更加鲜活,故事结构更加紧凑,场景转换更加自然,便于读者“参与”到故事当中,获得切身的情感体验。蒲松龄根据对小说中人物和故事的期待在诗词、小说文体功能间自如跨越,目的是将自身感受融入小说,所谓:“幻境之妙,十倍天真”,“千幻并作,皆人心所自动耳。”[11]100围绕这个中心,《聊斋》中的短篇小说从情节到人物都充满了至情与匠心,蒲松龄不拘一格地将古今不同类型的小说人物类型熔于一炉,重新整合,抒发自我。例如,《嫦娥》围绕“极我之乐,消我之灾,长我之生,而不我之死”[8]1609写尽人间感悟、悲欢离合。小说在人物设置上别具一格,以仙女嫦娥,凡夫宗子美和狐妖颠当三位主人公的爱情、际遇展开叙事,充满奇幻又感人至深。《聊斋》以真情寓奇幻,以实感托于小说人物、叙事,将自己置于小说之外,又不时地介于故事之中,转换自如,技巧纯熟精湛,是明清之前几种短篇小说形态所不能企及的。
三、《聊斋》的诗性张力及其“诗笔”文化增殖
前文所述之“诗笔”,大多指涉诗词与小说相融合、相互文的形式结构与艺术技巧层面,而诗性则主要指作者创作作品时的意境创造与主体情感投射,也就是作者借助作品自我性情抒发的方式,诗性内涵的丰厚与否决定了作品的精神含量,与“诗笔”指向的艺术表现特征互为表里。通常,一部成功的小说除了娴熟而新意迭出的艺术技巧而外,还需要以核心价值内涵与独特的生活体验注入作品,如此,“诗笔”才会产生文化增殖。反之,如果失去了独特、丰厚的诗性内涵支撑,即使艺术技巧再纯熟,作品也必将流于空洞,迷失价值。
就核心价值而言,《聊斋》有着与大多数明清时期文人戏曲、小说相一致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非科举出生的文人借戏曲小说的创作“传文”“传诗”,以获得认同与精神上的满足;另一方面,宣泄自我价值的独特性与宿命间的悲剧性冲突。于是乎,蒲松龄的情感好恶、思想意识便成为《聊斋》贯穿始终的控制人物命运、故事走向、情节结构的主宰。对于符合自我价值的形象,多寓之以美好的情感、加以积极的褒扬;而对于厌恶憎恨的事物则予以戏谑、讽刺、甚至以“异史氏”的名义直接鞭笞。首先,以情感好恶为区分标准,《聊斋》当中的人物有着鲜明的两个阵营:反面人物多是生活中让作者感到义愤的贪官墨吏、教官学官、见利忘义的小人等;美好的温情往往寄托于一切有灵性的生命,不论是天仙地骨、花妖狐媚、花草动物在蒲松龄笔下都有情有义。总的说来,蒲松龄对小说中与自己遭际相似的贫苦百姓与落魄之人总是无限同情,把一切善意的期许寄于其身,如《邢子仪》《瑞云》《乐仲》《仇大娘》《蕙芳》等作品无不如此,其中的小人物总是被各种机缘巧合、神仙眷属所青睐。《蕙芳》中落魄的小商贩马生意外邂逅了仙女蕙芳的爱恋,得以“顿更旧业,门户一新”,作者借此褒扬“木讷笃诚”的价值取向,也可以看作是对美好命运降临的期待。其次,作品当中的神仙妖媚多充满包容博爱的情怀,凡人则总是充满贪婪,但最终却多被作者宽恕和温煦。《小翠》《神女》《红玉》《霍女》无不如此,劫富济贫的狐妖霍女与生计无着的穷书生黄生相爱,在霍女得到巨富公子侧目之后,与黄生同谋千金卖生后二人得金而去,霍女虽对黄生颇深,为了黄生能生儿育女,甘愿牺牲自己,为黄生促成新姻缘。
《聊斋》诸多作品中对落魄书生、小贩无原则的宽宥;对人性贪婪的暴露、对世间种种不公的鞭笞,都源于作者在现实生活中的情感体悟,这些经验体悟融入作品之后,便构成了《聊斋》诗性精神的内涵“著我”与“发愤”。现实中饱尝失意的蒲松龄,为“著我”转而“沉冥抑塞,托志幽遐”[6]6:《叶生》《王子安》《考弊司》等作品中久试不第的穷书生形象是蒲松龄五十余年科举生涯的真实写照;蒲松龄常年担任私塾先生、幕僚糊口,阅尽了世态炎凉,经历了种种酸甜苦辣,他始终狂放不羁,耽于幻想,胸无城府,至诚而有性情。凡此种种,皆入《聊斋志异》。因此,在小说里我们能看到如其大嫂般的悍妇,如顾青霞般擅于吟咏的妍女,如其妻子刘氏那样“默若痴”的平凡女子;也能看到疏狂寂寞的私塾先生,如王子服、冯生、耿去病这样天真烂漫的“痴子”,如《酒友》《酒虫》《王六郎》中的酒痴。这些人物、情节都鲜活反映了“病骨支离”、穷困颠沛中蒲松龄本人的真实经历、思考与期许。“著我”是为了“发愤”:《席方平》《梦狼》《三生》《潍水狐》等篇目以“死而复死,生而复生”的虚幻世界中循环往复宣泄义愤,对昏聩的教官、学官盘剥书生的怨愤;对妻子、岳父等刻薄势利亲戚的咒骂都跃然纸上。在循环往复的泄愤之后,作者通常将其对现实生活的美好愿景寄托于小说的虚幻之中:《贾奉雉》中主人公因为厌恶科举而求仙,又因为眷恋人间被逐返,在物是人非的境遇中将科举的黄粱重演一遍,而后登仙而去。在叙事结构上与之类似的篇目还有《考城隍》《马介甫》《续黄粱》,这类小说多有所本,再加以夸张的藻饰,以主观宣泄为目的安排情节发展,通篇充溢“著我”与“发愤”意识,跌宕起伏。
作品的“诗笔”与诗性内涵互为表里,因此诗性的张力所带来的是诗笔的文化增值。蒲松龄认为:“磊落之气,寓之于诗”[9]686,诗歌与小说的融合互渗就是“发愤”与“磊落”的呼应。“聊斋少负艳才,牢落名场无所遇,胸填气结,不得已为是书。余观其寓意之言,十固八九,何其悲以深也”[8]31。历史上屈原、李白都将这种感愤之情写入诗中,蒲松龄大多作品也以此为中心。《聊斋志异》就是典型的以故事吐诗情,在其诗词中如《感愤》《怀张历友》《大江东去.寄王如水》等所抒发的怀才不遇之愤懑,与小说《叶生》中“文章冠绝当世”抑郁而死在幻境中终于“为文章吐气”的叶生异曲同工,从意境使用到情感表达都相互关联。再者,《聊斋》继承了古典诗词多以美人设喻明志抒情的传统,将诗词中芳草美人转换为小说中的花妖狐媚,诉尽哀婉曲折。怀才不遇的蒲松龄随之以痴狂自恃,但内心深处又何其渴望着怜才之人的出现。于是乎,便有了《聊斋志异》中许多的痴生狂客与诗歌中“自笑癫狂与世违”的感伤;也便有了《胭脂》《青梅》《王桂庵》等作品中对“怜才恤士之德”[9]517的反复书写与其诗中“世人原不解怜才”“念我不才皆欲杀”[9]486“世上何人解怜才”[9]462的无奈悲叹。由此可见,蒲松龄的诗歌创作与小说创作多能跨越文本、文体而意旨相通、境界相融。不论诗词、小说中聊斋先生对诗笔、诗性的把握都深深植根于历代文人失意后著述“发愤”的文化传统之上,充分汲取前人“发愤之作”的意象素材与艺术手法叠加使用,巧妙加工。创造全新艺术境界的同时,形成了作品独特的诗性张力,也构成了“发愤”“磊落”之诗笔传统新的文化增殖。
从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到以《聊斋志异》为代表的清代文人短篇小说,构成了“以诗词入小说”的文学传统完整源流线索。该线索演进过程中总体上呈现出从“穿插”到“互文”的方式变化;由简单机械到繁复多姿的艺术技巧推进;更为重要的是在形式之外的精神价值递增,从单纯的以诗词辅助叙事、填补结构到将身世之感、孤愤之意融入虚幻的故事加以充分彰显,再到跨越文体、文本与人物类型的诗性交融,较之前人诸作,《聊斋志异》各方面的价值与成就都可称之为我国古典短篇小说创作的第一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