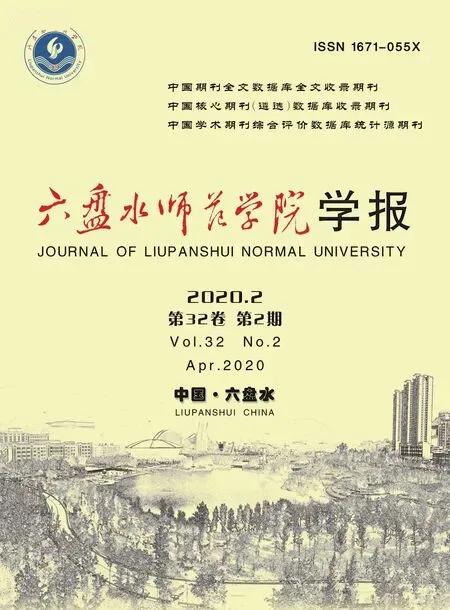《娇红记》之婢女形象探微
任小芳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陕西西安710119)
在群星璀璨的明代曲坛上,孟称舜享有很高声誉。其据元人宋梅洞小说《娇红记》改编的传奇《节义鸳鸯冢娇红记》(简称《娇红记》)流传至今。近年来,学者们对孟称舜及这部作品产生了浓厚的研究兴趣并取得可喜成绩。如黄春雨于2018年发表的《孟称舜<娇红记>之戏剧结构解析》[1]一文,以作品结构为切入点,对《娇红记》加以剖析;2016 年,杨婧在其文章《孟称舜<娇红记>的三重悲剧》[2]中,对《娇红记》的思想内容加以阐释;同年,李欣鑫在《戏曲<娇红记>的继承与发展——与小说版之比较》[3]一文中,通过将两种文体的《娇红记》进行比较,突出了戏曲《娇红记》的鲜明特色;周礼丹于2015 年发表的论文《<西厢记>中红娘与<娇红记>中飞红形象比较》[4]与郭佳慧在2016年发表的文章《简析<娇红记>中的丁怜怜形象》[5]都对作品中人物形象进行了剖析。但在人物形象分析中,对婢女形象的解读则稍嫌不足。事实上,小人物形象的塑造也蕴藏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对其进行分析,既有助于认识作品本身,也有助于认识晚明思想与文化。基于此,本文拟对孟称舜《娇红记》中以飞红为代表的婢女形象进行专门研究分析。不足之处,祈请指正。
一、婢女形象塑造的“承”与“变”
何谓“婢女”?婢女大致可以分为“侍女类和女仆类”。侍女多指随时陪同主人、主母或公子、小姐身旁的人,称“贴身婢女”。女仆多指以做脏、累、差的粗活为主的婢女,又称“粗使丫头”[6]95-98。《娇红记》小说与《娇红记》传奇中出现的婢女皆为侍女。
(一)《娇红记》小说之婢女形象塑造
孟称舜的《娇红记》系改编宋梅洞小说《娇红记》而来。《娇红记》小说中的侍女有五位,分别是湘娥、小慧、兰兰、绿英、飞红。作者对湘娥、小慧、兰兰、绿英形象的塑造,笔墨极为有限。对于兰兰,只是提了一句“红房下小侍女兰兰”。湘娥也只是出现了名字“俄舅之侍女湘娥突至娇前”[7]312。绿英则略具特征,作者写道:“娇病少瘳,因他事怒小鬟绿英,绿英怀恨,乘间以娇平日所为之事,以实告舅。”[7]334可见,绿英是个“睚眦必报”的侍女。小慧在得知小姐为了和申纯无障碍相处竟屈事飞红时,对小姐说:“娘子通判之女,贵人也;飞红,通判之妾,贱者也。奈何以贵事贱,此小慧日久所不能平者,”“娘子芳年秀丽,禀性聪明,立身郑重……今既委千金之身于申生,若弃敝屣,而又下事飞红,丧尽名节,此妾之所大不晓者……”[7]326-327在此叙述中可看出,小慧是一个有尊卑观念、重名节而又忠心为小姐着想的侍女形象。
与此书其他婢女形象创设的简略相比,飞红的形象创造则略为饱满。其一出场,作品概述道:“舅之侍女飞红者,颜色虽美,而远出娇下,惟双弯与娇无大小之别,常互鞋而行,其写染诗词与娇相埒。娇不在侧,亦佳丽也。以妗性妒,未尝获宠于舅。常时出入左右,生间与之语……红尤喜谑浪,善应对,快谈论,生虽不与语,亦必求事以与生言……及生再至,红亦与之亲狎。”[7]318由此,可看出,飞红除了侍女这层身份外,还是王老爷的侍妾。她虽貌美,但远逊于娇娘。她精通于诗词写作,“尤喜谑浪,善应对,快谈论”,并寻找机会接近才子申纯,并“与之亲狎”。总括起来,她是一个有才有貌、活泼、机敏、爱才但有时会流于轻浮的婢女形象。她与小姐原本和谐相处,但当小姐见飞红与申生戏于窗外,捉蝴蝶,因大怒诟红时,飞红采取了反抗。作品写道:“红颇撼之,欲以拾鞋事闻妗,未有间也。后遇望日,众出贺舅妗。飞红因语娇所履之鞋,扬言谓生曰:‘此即子前日所遗之鞋也。’”[7]318-319当然,此次报复,因“会舅妗应接他语不闻”[7]319而没有达到目的。后来,申纯怕娇娘误会,所以不愿理飞红。对此,飞红又心怀怨恨,在恰好发现二人私游后花园时,便因促步返舍,语妗曰:“天气晴朗,可入后园,牡丹盛开,能一观否?……妗因大疑。”在此前两情节展现中,可看出,飞红是一个有自尊,又有些睚眦必报的婢女形象。再后来,飞红着手打理家事。作品写道:“飞红方用事,跬步动容,无所求其便。”[7]324在此叙述中,作者展现的飞红是一个勤于职守、强于理家的婢女形象。为了能与申纯接触,娇娘不得已“投之以桃”,“屈己以事飞红,平日玩好珍奇之物,红一开口,则举而赠之”[7]326。对此,飞红亦“报之以李”,“见娇之待己厚者,渐释旧撼,与娇稔密”[7]326,且对娇娘说:“红受娘子之恩厚矣,苟有效力,当以死报。”[7]327从此以后,飞红便做起了申、娇二人忠实的红娘。她不但为二人传信,“潜书促生来,使与为诀”[7]335,还隐瞒娇娘之父带着病体羸弱的娇娘去舟中与申纯幽会。她的命运,也随着娇娘母亲的去世逐渐好转,作者于此写道:“自妗之死,飞红专宠与舅,”[7]331“人皆呼之为红娘子。”[7]326因为这样的原因,当她向王父隐瞒申、娇二人私情时,“舅方宠任飞红,信其言不复再问”[7]334。娇娘死后,王父得知事情原委,飞红遂伏地请罪,但并未被王父惩罚。王父与飞红讨论将二人合葬事,并“遣红来吊唁,营办丧事”[7]338。娇娘去世后,亡魂告诉飞红:“惟是亲恩未报,弟年尚幼,一家之事,赖汝支吾,善事家君,无以我为念。”[7]338综前此种种,可看出,《娇红记》小说中的飞红是一个才貌俱全、活泼诙谐、机敏爱才、善于理家、又恩怨分明,有恨报恨,有恩报恩的婢女形象。由此及从后来的命运书写及王父、娇娘对其的态度来看,作者显然对其是给以肯定的。
(二)《娇红记》婢女形象塑造之“承”“变”
相比于宋梅洞《娇红记》,孟称舜《娇红记》中的婢女数量则大为减少,只有湘娥、小慧、飞红三人。对于湘娥和小慧,作者给予的描写笔墨并不多,这点与《娇红记》小说相似。但在同样少的笔墨中,作者对人物性格特征的刻画尤为突出。《和诗》一出中,湘娥与飞红、小慧调笑。湘娥唱道:“三春好景最无过,花面丫鬟十八多,常来花下觅情哥,不见情哥奈若何,”“小梅香离绣房,走到花园儿里,撞著一个爱风流识趣人儿,那人儿将衫儿袖儿扯住了相调戏。”[8]122小慧唱道:“我在花园儿里,被那小奴才硬梆梆扯住在华阴底。若是汤著了身儿,打呵也该得的,若是合著了口儿,骂呵骂也应得的。”[8]122由这些曲词描写可看出,这两个婢女对“情”都极为渴望。就这点来说,与宋梅洞《娇红记》小说有了明显区别。
较之于《娇红记》小说,飞红同样是孟称舜《娇红记》中塑造的重要婢女人物。作者对这一人物的塑造,相比于《娇红记》小说来说,也是有继承有创新。《和诗》中,飞红自云:“俺飞红颇饶姿色,兼通文翰。”[8]121可看出,在才貌俱全、精通翰墨上与《娇红记》小说是一致的。在自尊和恩怨分明、有恩报恩、有怨报怨上,飞红也与《娇红记》小说中的飞红如出一辙。孟称舜《娇红记》曾两次写到飞红的“报怨”。第一次是当娇娘在飞红处看到自己的鞋时,笃定飞红与申生有染,便大骂飞红云:“你丫鬟们呵,止不过房中刺绣添针黹……妆台拂镜除香腻。谁许你游月下,笑星前,看花底,春情一片闲挑起,将渔郎赚入在桃源里。则怕奶奶知道呵,把粗棍儿,敲杀你丫鬟辈。”[8]188并威胁飞红说:“还亏你说,我去告知奶奶打你下半截来……我今权且记着,下次如此,定不干休。”[8]188对此,飞红怀有怨恨,内心表达说:“小姐,你做的事瞒谁?倒几次寻嗔我,我拼的乘便告知奶奶,看怎生解说?小姐呵,你没人处,没人处,狂乱行为。蓦地里,将人笑耻。果然是,果然是言清行亏。则怕你假清清,怎生般遮瞒得到底。投至那西厢月下闻消息,御沟叶上传名字。那时节呵,敢则漏泄春光你悔自迟。”[8]188-189《诘词》一出中,娇娘云:“飞红怀恨在心,在我爹娘面前,说起鞋儿……”[8]190由娇娘这一话语,可清楚看出飞红将自己的报复是付诸行动了。第二次报复起因于申生为了避免娇娘误会,便不再搭理飞红。飞红怀恨说:“申生明见我在此,佯然不采去了。我想申生奚落与我,皆只为着小姐。小姐呵,你前日失鞋事被你瞒过了,今后再有甚事,我径说与奶奶知道,倒替你愁哩。”[8]200于是,当她看到申生与娇娘在花园幽会,便故意请夫人游春,窥破二人隐情。
对于飞红的报恩,孟称舜《娇红记》也交代得很清楚。就飞红内心来说,对申纯是真心爱慕的,也是乐于交往的。但在受到娇娘厚遇、看到二人真心爱慕后,飞红便尽力成全二人。《会娇》一出,飞红称赞娇娘说:“姐姐,你今日朱粉未施,双鬟绾绿,愈觉可人也;”[8]109“我觑申家哥哥和小姐呵,两下低鬟相向,我心中猛然暗想。多管他佳人才子,都一般儿风流情况。一个待眉传雁字过潇湘,一个待眼送鱼书到洛阳。”[8]110“姻缘分定,也拣不得许多。眼前倒有个人儿在此,似那申家哥哥呵,他俊样儿,天生绝,和你一般情意惬。”[8]114可见,飞红认为申、娇二人郎才女貌,二人彼此有情,所以真心希望二人结合。娇娘屈事飞红后,飞红更是竭力为二人之事奔波。娇娘病重之时,她写信唤来申生,并偷偷搀扶着娇娘去舟中与申生见最后一面。
但较之于《娇红记》小说,《娇红记》传奇中的飞红又有所不同。这一不同是突出了她对“情”渴慕的一面。如《和诗》一出中,飞红表露心声云:“二八花容侍女身,随他无事度芳春。也知一种伤情思,秋波暗里去撩人。”[8]121《合冢》一出中,飞红唱道:“我飞红自顾才貌,不下于人,寄身侍妾,不得配个少年郎,长自闷怀。”[8]258当申生来王家被她看到后,她自思云:“俺看申家哥哥,果然性格聪明,仪容俊雅,休道小姐爱他,便我见了,也自留情。今日老爷不在家,奶奶又睡着,且到堂中厅瞧他去;”[8]121“俊书生,我为你逗春情,几次花前陪笑迎;”[8]200“俺自昔申生去后,心下好生念他。他今因养病,重到我家。我每与他中庭相遇,语言调笑,两下更是关情。今趁此昼闲,则东轩上偷觑他去。”[8]183由这些曲词自述可看出,飞红虽然身为下贱,但正当青春,对“情”不仅是渴慕的,并且付诸行动。这较之于《娇红记》小说表达的隐晦来讲,显得直接而热烈。
但尽管如此,孟称舜《娇红记》中飞红的“情”又不同于《牡丹亭》中杜丽娘的“至情”,她表现出理性的精神。此精神一是表现于她尽管爱慕申纯,但看到申纯与娇娘真心相爱、郎才女貌自是般配后而乐于成全二人。二是在亲身经历了小姐被“聪慧多情”四字所误后,她不再怨怼“不得配个年少才郎”,而是“放下了许多”[8]258。对《娇红记》小说中“飞红专宠于舅”这一说,孟称舜也未予以表现,而是代之以“俺自小姐亡后,独居无伴,好是凄凉”[8]263的话语阐述。《泣舟》一出中,她劝慰娇娘说:“姻缘成悔,展转无常,安知此后,不可复合?只要俺姐姐善自将觑,保全身子罢了。”[8]244由这些描述不难看出,飞红对“情”尽管是渴慕的,但却“止乎”于她所认识的“才子佳人合配”、知恩图报之“理”。她对“情”的认识又是客观准确的,看到了“情”辗转无常、翻转成悔的发展特征,所以其行动中少了杜丽娘“为情而死,又为情而生”的“至情”特征。
综上,孟称舜《娇红记》的婢女形象对《娇红记》小说既有继承,又有创新。继承表现于婢女描写都以飞红为重心,突出了她才貌俱全、精通翰墨、有恩报恩、有怨报怨、恩怨分明等性格特征。创新主要体现于刻画了婢女对“情”的渴慕,并且赋予其“情”以理性规范的约束,同时表现出对“情”认识的客观冷静。
二、婢女形象书写体现的价值内涵
由上可知,孟称舜对《娇红记》中的婢女形象塑造较之于小说《娇红记》在继承的同时,又有新变,其身后体现出一定的价值内涵。
(一)符合戏曲这一文体的传“奇”特征
孟称舜的《娇红记》在文体上属于“传奇”。“传奇”作为一个概念,其最早使用者是中唐元稹,他创作崔、张爱情故事就题名为“传奇”。至晚唐,裴铏将他的小说集子命名为《传奇》。由此可知,在唐代,“传奇”多指小说作品。两宋时,一些说唱文学也被称为“传奇”,如“诸宫调传奇”。后来,宋元杂剧与南戏也被称为“传奇”。到明中叶,篇幅较大的南曲戏曲剧本亦称为“传奇”。据上可知,“传奇”既包括小说,又可指戏剧作品。但无论是哪种体裁,记述“奇异诡怪”之事是共性。尤其在戏剧领域,传“奇”更是作品被广泛接受的必备条件。孔尚任在《桃花扇小识》中云:“传奇者,传其事之奇焉者也,事不奇则不传。”[9]2李渔《闲情偶记》谓:“古人呼剧本为‘传奇’者,因其事甚奇特,未经人见传之,是以得名。可见非奇不传。”[10]334诸如此类,都说明是否传“奇”已成为衡量一部作品艺术成就高低的关键。
作为孟称舜代表作的《娇红记》显然属于“传奇”之列,它对以飞红为代表的婢女形象塑造中亦体现出传“奇”的特征。飞红虽然“身为下贱”,但作品中并没有表现出她的奴性。她不再像《锦笺记》中的婢女芳春、《凤头鞋记》中的巧妇、《梦磊记》中的秋红、《花莛赚》中的芳姿,为了小姐甘愿牺牲自己的一切,也不再像《怀香记》中的春英那样胆小、逆来顺受。她也不只是一个简单的穿针引线的人物,亦不再扮演插科打诨、逗观众一笑的角色。飞红的“奇”之一表现于她不同于一般丫鬟的文化修养,她颇有“诗才”。剧中说她“今年二八,与小姐同庚同月而生”,并多次出现“颇饶姿色,兼通文翰”的概述。此展示了飞红虽处在婢女丛中却与众不同。飞红见到申生后,流露出仰慕之情,并采取行动。此处笔墨,使飞红形象更加光辉,也为后文写娇娘多疑而“诟红”埋下伏笔。遗鞋事件发生后,娇娘怀疑申、红二人有私情,便大骂飞红。飞红怒指小姐云:“小姐,你做的事瞒谁?”[8]188之后,便有了两次报复行为,致使申纯被逐,申、娇二人难以相见。关于飞红这些情节的插入,使演绎申娇二人爱情故事的情节跌宕起伏,这自然也契合戏曲传“奇”的文体需要。
(二)展示了晚明婢女的生存现状
孟称舜《娇红记》对婢女形象的塑造,也体现出晚明时婢女的社会地位境况。晚明时代,婢女地位有所提高,统治者也以法律形式纠正以往滥杀奴婢的行为。如明吴履震《五茸志逸》中记载:“常西瑛与家人饮酒,其妻用头上所插金篦揭肉而食。时有客人来访,其妻去厨房准备茶水,后发现金篦不见,疑为婢女所偷,将婢女杖罚致死。常西瑛夫妇怕见官司,私下贿赂其婢父母才免于诉讼。”[11]183然而,这种地位的提高只是相对而言,婢女仍然是被压迫的对象,其被虐待和致死之事屡见不鲜。如一个叫刘司辰的人在南京光禄少卿邹观光家,见“其妻内捶一婢,声彻客座。邹已失色。刘逡巡辞归,邹又固留,捶久不止,声愈厉,其婢气垂尽”;正德八年(1513),“刑部主事陈良翰妻程氏,杖杀婢女,解尸置木柜中”[12]504。此诚如王雪萍女士在《16-18世纪婢女生存状态研究》中指出的那样:“在国家公私和私人家规的预设规范下,婢女的日常生活给人的印象是:绝对地服从主人,随时听从主人的吩咐,按照主人的意图办事;如果办事不力,出现偏差,就会遭到主人的惩罚,轻则被骂,重则被打。有时会挨饿受冻,遭受男主人的性侵犯以及女主人在嫉妒心理支配下的报复行为。”[6]116《娇红记》传奇中,无论是普通侍女湘娥,小慧还是侍妾飞红,他们生活的重心只可能是为主人服务。因此孟称舜并没有赋予他们“终成眷属”的美好结局。所以,尽管飞红对申纯有爱慕欣赏之情,但其低下的婢女身份加之严格的社会等级秩序注定已成为王文瑞妾的飞红绝无与申生结合的可能。
(三)体现了晚明重“情”的文化特征
《娇红记》传奇对婢女形象书写体现出晚明重“情”的文化特征。孟称舜《娇红记》成书于晚明,这一时期,意识形态领域掀起一股张扬个性、反对禁欲主义的思潮,反映到文学作品中,则体现出重情的思想。汤显祖临川四梦“因情成梦,因梦成戏”。冯梦龙编撰的《情史》处处洋溢着情的光辉。身处晚明文化思潮中的孟称舜,写“情”也是其创作的重心。他早期杂剧《花前一笑》写江南名士唐寅春游金阊时,巧遇沈素香。为了跟素香再次相见,唐寅跟访到吴兴,不惜易服自荐,为沈家公子拥书。后历经坎坷,终得谐姻眷。《泣赋眼儿媚》写陈诜因与歌姬江柳热恋,被杖责并发配至八百里外的辰州,二人挥泪而别,后陈友陆云为江柳除去乐籍,配于陈诜为妻。对这两部作品,朱颖辉先生申论道:“无论是唐寅和沈素香的一见钟情,也无论是陈诜与江柳的两年热恋,作家都持赞赏的态度。唐寅为了追求沈素香,竟辱没了江南第一才子的身份,甘为人下拥书,借以接近意中人;江柳虽被杖责发配,但对陈诜坚贞不二。这种为追求美满爱情而不惜做出牺牲的心态和行动,都在作家笔下,得到了酣畅淋漓的表现。”[8]17孟称舜《娇红记》被王养浩盛赞为“情史第一佳案”,其在婢女形象刻画中对婢女追求爱情心声及某些行动的表述,从此角度来说,正体现出晚明重情的时代特征。
(四)展现了孟称舜“发乎情,止乎礼”的价值观
《娇红记》传奇对婢女形象书写还体现出作者发乎情,止乎礼的价值观。晚明社会,是一个纵情声色的时代,也是一个社会矛盾剧烈的,颠倒的、混乱的时代。罗宗强先生说道:“这是一个天崩地裂,必将改朝换代的时期。皇帝昏庸,宦寺专权;党争不断,无官不贪;连年灾荒、四处民变;加以边境战事不断,国库空虚。民无可食之粮,国无可用之兵。整个一幅末世景象。”[13]806在这样的社会中,文人士大夫虽放浪形骸,但终究是儒士,他们的作品依然带有浓厚的道德色彩。如汤显祖塑造的杜丽娘在虚幻的世界里尽情表达自己的深情,但一回到现实世界,就讲“鬼可虚情,人须实礼”[14]206。李贽的思想核心是重视情之真,但在评论文学作品时,仍把道德放在很重要的地位,盛赞《水浒传》中的宋江为“忠义之烈”。冯梦龙编《情史》,是为了立“情教”。孟称舜婢女形象的书写也体现出对道德的关怀,对“礼”的重视。孟称舜父亲孟应麟“为人刚正不阿,为部所憾,抗辞奉母归里,年八十有二而卒”[8]4,是封建时代比较典型的忠臣孝子和耿介儒士。孟称舜挚友马权奇、陈洪绶、祁彪佳、卓人月等人也都是耿介之士。在学业上,孟称舜遵孔孟之道,“自幼受家学影响,好读《离骚》《九歌》,工诗文词曲”[8]4。在各方面影响下,孟称舜的作品必然带有浓厚的正统观念。如其传奇《贞文记》女主人公张玉娘在父母唤其游春时,她以“做女孩儿们的道理,畏行多露”[8]28来婉拒。在沈佺专程来见她时,她以“未饮合卺之杯,恐无相见之理”[8]28断然拒绝,并随之把无心仕进的未婚夫逼上求取功名之路。在她殉夫之后,作者也让他的两个婢女紫娥、双娥及张所养的一只鹦鹉主动陪葬。其历史剧《二胥记》借剧中人物之口,历数昏君佞臣贻害社稷,残害忠良的罪恶,树立起明君、忠臣、孝子、节妇等道德化的典型形象。《娇红记》全名为《节义鸳鸯冢娇红记》,其中,“节义”二字即明确体现出作家的正统观。依此来说,《娇红记》传奇中对婢女“发乎情,止乎礼”的形象书写,也正与此相类,体现出孟称舜对“情”的理性思考和对人伦秩序建设的看重。
综上,孟称舜《娇红记》传奇较之于宋梅洞《娇红记》小说,其创新主要体现于刻画了以飞红为代表的婢女对“情”的渴慕,并且赋予她们的“情”以理性规范的约束。作者对婢女形象的这种塑造,既是出于作品传“奇”的文体需要,也反映了晚明重“情”的时代特征,同时对人们认识晚明婢女生存境况提供了借鉴,亦体现出作者“发乎情,止乎礼”的价值观念。
三、结语
作为晚明时期重要传奇作品,《娇红记》以其独特的魅力征服了许多文人学士。孟称舜踩着前人的肩膀用仁者的情怀塑造了一批身为下贱的“婢女”形象,为我们呈现出了一幅鲜活的晚明婢女图画,亦有助于我们了解这一时代的文化特征。通过将《娇红记》传奇与《娇红记》小说进行对比,发现其继承和创新,联系文体特征、婢女生活现状、时代潮流、作者思想挖掘新变后的价值内涵,拟在提供一种相对完整的研究古代作品中人物的方法,基于此,更多的文学作品可以得到进一步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