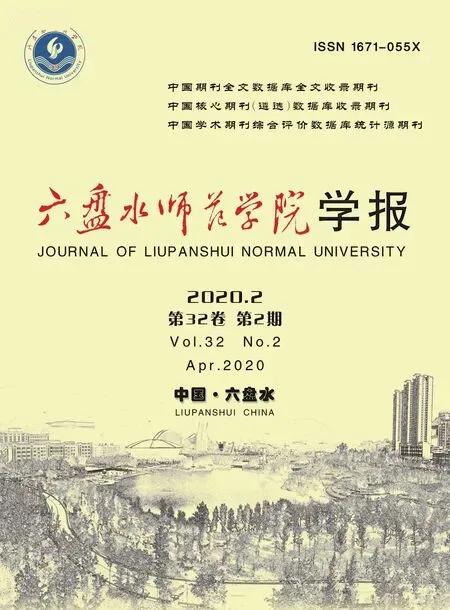从检察机关运作看民国反腐实况
——以郭云观、查良鉴案为例
陈一
(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上海200042)
各级官员的腐败问题是贯彻民国始终的一大难题。无论是北京政府还是南京国民政府,中央政府高层均意识到了腐败问题的严重性,并在各领域多管齐下制定了详尽的反腐制度。单就国民政府时期的刑事立法层面而言,1928年和1935年的新旧刑法均设有“渎职罪”专章,明确贪腐行为及其刑罚措施。此外,还有为数不少的反贪腐单行立法,如1931 年颁布《惩治贪官污吏暂行条例》,对贪污、受贿等罪行进行严厉处罚;1938年公布的《惩治贪污暂行条例》是为抗战时期专门制定的反贪腐法规,加大了对贪污犯罪的惩罚力度;1940年国民政府公布自国民政府成立以来第一个“惩治贪污”方面的正式单行刑事法规《惩治贪污条例》,将惩治贪污人员的范围扩大到公务员以外的人,处罚更细更严,增加了死刑,并在战后的1946年重新修订颁布。
多管齐下的反腐制度建设也使得国民政府时期在贪腐问题上的管辖主体较多。例如,监察院作为五权之一监察权的行使者,在各地方派遣监察使,如传统中国之监察部门一样监督各级官员,对于违法乱纪者予以行政惩戒。对于触及刑事犯罪的官员,一般会交由司法机关处理。抗战胜利后,贪腐案件凡触犯刑事法律者,一般均划归司法机关管辖,以刑事司法程序处理各种相关案件,法院检察处在其中有着重要作用。
学者对民国的反贪腐制度问题虽有相当一部分的关注,但其关注点多在整体反腐制度及其借鉴启示,或在于立法层面规制的变革①;而在以民国检察权为主题的研究中,又多只是将其作为观察检察权的辅助手段②,缺乏从司法机关特别是从检察机关的侦查起诉工作角度的观察。上海是国民政府时期的要津与经济中心,从反腐角度来说,“大老虎”不少,“小虾米”更甚,而该时期上海检察机关对于贪腐案件的查办情况,也可窥见整个国民政府时期反贪反腐在实际运行中的情况。
一、“打虎”无力亦无心:郭云观与查良鉴案始末
民国时期特别是国民政府时期,政府高层官员的贪腐问题是长期普遍存在的现象,即便是司法领域也不例外。通常而言,尽管在国民政府的五权体系中设置了监察院来监察各级军政官员的行为查处贪腐,但涉及刑事犯罪的依然会交由司法机关处理。检察机关在此时理当代表国家公权力对此提起公诉,但在实际运行过程中,检察机关却往往在“打虎”的大案要案中起到相反的作用,以各种理由纵虎归山。特别是在面对自身司法系统内部官员贪腐问题时,或如烫手山芋般推诿,或以法律上的理由不予实质处理。本文谨以郭云观和查良鉴的贪腐案件为例,探析上海地方检察机关在处理这些重大贪腐案件中的做法。
郭云观与查良鉴是国民政府时期上海法律界两位非常重要的人物。郭云观是浙江玉环人,早年曾考取外交官并驻美多年,驻美期间在哥伦比亚大学修习国际法,抗战前即长期担任上海第一特区地方法院院长,租界沦陷后逃亡宁波等地,抗战胜利后出任上海高等法院院长。查良鉴,浙江海宁人,美国密歇根大学法理学博士(S.J.D.),抗战前曾于华东多地高校任教并在上海执律师业,后被聘为上海特区地方法院编纂、后补推事,旋升任第一特区法院推事兼书记官长,租界沦陷后迁往西南大后方并在四川、重庆等地任职,抗战胜利后任上海地方法院院长。可以看到,郭、查二人的组合是国民政府时期上海司法界最主要的负责人。而这二人分别在抗战前后因贪腐问题被人举报,但最后都成功脱身,丝毫没有受到任何负面影响。
(一)郭云观“贪赃渎职”案始末(下文简称“郭案”)
郭云观在1932 年11 月调任上海第一特区法院院长并一直担任至租界沦陷。然而,郭云观刚担任院长不过两年多,即在1935年初被人举报至司法行政部,称其“恃宠贪赃”,希望司法行政部将其“撤职查办,以肃官箴而正法理”[1]74。在自称“上海公共租界受屈人民代表”李大中呈具司法行政部的举报信中,李氏指控了郭云观的三大罪状。
第一,郭云观就任后任人唯亲,勾结律师包揽诉讼案件。李氏称郭云观对外行整饬风纪之名,对内则清退原法院工作人员,“收罗戚友党羽,为敛财之工具”。其所任用的三名书记官魏振寰、邹光和王能泽入院前分别在李时蕊、施霖律师事务所担任过书记,入院后勾结律师掮客,“包揽词讼,招摇撞骗”。
第二,郭云观包庇和纵容魏振寰等人非法敛财。魏振寰担任上海第一特区法院刑事记录科主任书记官,利用拘票、搜索票作为敛财工具。“每出拘票”和搜索票时,“有钱则先期通风报信”,据此非法收受他人财物。
第三,魏振寰先前在民事执行处担任书记官时,与该处候补书记官邓武共同收受执行人与被执行人之贿赂。债权人如请求速办执行,则“视其请求之标的而定其应贿之数额,最低限度则抽十分之一”;相反,债务人若想暂缓执行,则交债权人双倍的贿赂即可。而且,邓武是郭云观的亲戚,在充任庶务时,与律师休息室的茶役徐鼎兴合伙收受贿赂。而律师休息室向来是肥缺,邓武和徐鼎兴利用律师送礼以及售卖委任状、诉状的差价大力敛财。公共租界百姓虽多有不满,但碍于邓武与郭云观的关系,都不敢举报。
司法行政部据此举报信命令上海第一特区法院的上级法院——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的院长沈家彝及首席检察官郑铖调查此事。调查工作主要由检察处检察官负责秘密侦查。经过将近一个月的“秘密访查”[1]80,分别就李大中所提到的三项问题做出回应。
首先,关于郭云观收罗党羽,勾结律师掮客的问题。检察处的调查结论认为,魏振寰、邹光和王能泽三人都是复旦大学法律系的优等毕业生,大学毕业后即被上海第一特区法院调取录用,担任学习书记官,其毕业日期与就职日期非常接近,不具备前往律所担任律师书记的时间条件,且经与复旦大学校方的沟通调查,三人亦没有在校期间律所实习的记录。此外,魏振寰与李时蕊律师的儿子是同学,但并不认识李时蕊本人;而施霖律师在复旦大学法学院兼任教授,邹光、王能泽都是其学生,仅是有师生情谊,且施霖律师曾经担任法官多年,行为谨慎,在律师公会的调查亦没有证据显示二人曾在其律所担任书记。
其次,关于魏振寰通过拘票和搜索票敛财一事。调查显示,魏振寰虽为刑事记录科主任,但并无开具拘票与搜索票的决定权。上海第一特区法院的刑事拘票和搜索票,都是根据租界捕房的声请,由轮值的庭长或主任推事及其配置书记官办理,“非魏振寰所能过问”。且根据检察官的访查讯问,该院的推事也均表示“尚无可疑之处”,没有发现疑点。
最后,关于邓武伙同魏振寰在民事执行处收受双方贿赂,以及伙同徐鼎兴利用律师休息室收受律师送礼和回扣的举报。检察处的经访查该民事执行处,得知魏振寰确实曾充任书记官,但其职责仅是“专办文稿”,并不负责出外勤,该处推事亦未发现其有异常。而邓武在民事执行处任候补书记官时,魏振寰已调离,二人未曾共事一处。至于邓武之身份,其与郭云观是同县老乡,传闻有师生关系,但不是亲戚。所谓的律师休息室茶役徐鼎兴,本是公共租界工部局捕房律师休息室的茶役,上海第一特区法院律师休息室茶役另有其人。不过,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检察处的调查报告承认,律师购买状纸时给予茶役小费的确曾是上海各地法院的“旧日恶习”,不过“本院及该地院曾会同示禁”,已经制定相应将呈规则来杜绝类似事件。
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对此事的调查结论认为,李大中的呈控“或故与牵涉,或泛陈无据”。究其原因,魏振寰、邹光、王能泽三人皆为大学优等毕业生,年少有为而平步青云,邓武与郭云观同乡且有师生关系,都难免遭人嫉妒攻讦。而且,郭云观“办事颇负责任”,“用人重视学历”,扶植戚党、徇私舞弊之事,“尚无所闻”。并将此调查结论上报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司法行政部得知后也表示,既然“查明所控不实”,那么郭云观也“应予免议”[1]86,不再纠察此事。
(二)有头无尾的查良鉴贪腐案(下文简称“查案”)
查良鉴在抗战胜利后就任上海地方法院院长直至1949年败退台湾。在任三年后的1948年中,查良鉴被署名方季良之人举报,称查良鉴在任期间存在严重贪污渎职行为。举报信以“七宗罪”的形式列举指控了七点查良鉴的贪腐罪行,归纳起来主要在三处。一是生活腐化,查良鉴有巨额不明财产,且其现在所居住之房屋——静安寺路静安新村的公寓原为汉奸张某所有,抗战胜利后理应没收;二是查良鉴徇私舞弊,与前上海地方法院检察处首席检察官黄亮“疏通保释”,违法释放不符合保释条件的在押犯罪嫌疑人;三是查良鉴在院带头行奢靡之风,致使整个上海地方法院风纪败坏。举报信还声称,前监察院委员俞奋处有相关的证据材料,致使囿于查良鉴的后台和人脉尚不敢擅自告发查处。
最高法院检察署在接到举报后于8月初指令上海地方法院检察处首席检察官张毓泉负责此案,并“密函国防部保密局协查”[2]2,可谓是十分重视了。1948年7月方才就任上海地方法院检察处首席检察官的张毓泉接到指令后十分为难。在当时国民政府的司法体制下,除最高法院检察署外,其余各高等、地方法院内设检察处,由首席检察官为首长,首席检察官理论上与法院院长平级,在法院内部形成“一山二虎”的吊诡局面。张毓泉虽刚就任首席检察官,但毕竟与查良鉴同一屋檐下办公,于理自不应违背最高检察署指令,于情又难以真正对查良鉴展开实质性调查。
张毓泉思虑再三,只得选择推脱,致函最高法院检察署,声明自己就任伊始,“案牍山积”且“本处人事尚未调整完善,暂无可托付之人,万一办理不慎,不特贻误要事,有负重寄,且恐审检发生误会摩擦,丛生事端,诸多不便”[2]5。然而最高法院检察署得函后再次指令张毓泉调查此案,称“本案情节重大、虚实湏明”,张毓泉是最合适的人选。张毓泉亦不含糊,始终以检察事务繁重、无人可托付等为由拒绝了最高法院检察署。
最高法院检察署知张毓泉再三推脱的难处,遂重新指令新上任的上海高等法院检察处首席检察官刘少荣调查查良鉴的贪腐问题,特别是查良鉴在静安新村的寓所是否系应查封之汉奸财产。刘少荣在得令后经调取案卷,确认该房屋确是汉奸张秉衡房产,在1946年3月被上海高等法院“查封在案”,7月张秉衡案判决后,该处房屋被“宣告没收”并在随后被执行拍卖[3],查良鉴拍得此屋形式上亦无法律问题。但是,由于之前张毓泉的一再推脱,当该案辗转来到上海高等法院检察处时,时间已是1949年5月,上海战役随即打响,该案件也随着国民政府在上海的败退而不了了之。
值得注意的是,查良鉴在此同时受到了不止一人的举报。除了方季良的举报外,又有自称朱殿元之人在1948年下半年上书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控告查良鉴“自串舞弊”。司法行政部亦指令上海高等法院院长郭云观会同时任检察处首席检察官杜保祺调查此案。郭云观、杜保祺调查此案后,报称“朱殿元地址既无此门牌号数,又无所谓朱殿元其人”,且举报信“所控各节更属任意捏造”,有“挟私污蔑”之嫌[4]。司法行政部亦不再追究。而查良鉴在1949年跟随国民党逃往台湾后,参与要案、担任高官,丝毫没有受到此次事件的影响。
二、“郭案”与“查案”之分析
贪腐问题一直是整个国民政府时期的顽疾,甚至可以说是国民党败退台湾的元凶之一。而国民政府的建立与当时的军阀、门阀、财阀等寡头势力密不可分,致使统治阶层内部派系错综复杂、盘根错节,对于政府高层或者有相关背景之官员,其查处难度相当之大。郭云观是玉环当地巨贾郭国芳之子,清末科秀才,早年曾在北京政府法律修订馆、外交部、大理院等中央机关任职,国民政府建立后长期执掌上海司法界,在上海以及国民政府中央皆有复杂的人脉关系,试图依靠上海地方检察机关的力量扳倒郭云观难免力不从心。查良鉴出身名门望族,海宁查氏家族是当地的显族,查良鉴本人亦在上海及周边地区深耕多年,与法学教育界、律师界多有交集,更非一般司法官吏可以挑战,且其跟随国民党败退台湾后又历任“最高法院”院长和“司法行政部”部长,参与查办多起要案,一直深得蒋介石信任。
在“郭案”中,郭云观被人举报的重要一点便是庭外与他人徇私舞弊、枉法裁判以及纵容下属勾结律师包揽词讼。虽然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在调查报告中一再澄清此事,但其实在当时的司法界,这些现象屡见不鲜。例如,曾在上海第一特区法院担任过推事的吴经熊在辞职后于1930 年开始执律师业,经常通过自己在法院的人脉关系,通过庭外活动解决案件。“刘海粟与裸体模特纠纷案”中,吴经熊作为刘海粟的辩护人,考虑到原告一方较强的官方背景,有针对性地进行了一系列的活动:在开庭的前几天,吴经熊安排刘海粟与承审该案的推事郑雯——据刘海粟回忆该推事还是吴经熊旅欧期间的同学——一起吃饭,就诉讼结果安排进行了事先约定。案件审理也朝着预期的方向进行,即罚刘海粟五十元,刘海粟也按照事先的约定,没有上诉,此案终于告一段落[5]。吴经熊的事迹显然不是个例,且其执律师业的时间亦与郭云观就任上海第一特区法院院长的时间有所重合,而吴经熊回忆当时律师“每晚都要出去应酬”的情况十分普遍[6],显然这大多与当事人及法院推事有关。至于所提到施霖律师曾与院内多位书记官存在师生关系,学生帮助老师介绍案子的情况,在当时就已有印证。时人在介绍施霖律师时,指出他在沪上多所高校兼职教授,经常邀请一些毕业生到他家里吃饭,这些与他较熟的学生也会给他介绍一些案子的当事人给他[7]。显然李大中的举报信内容并非空穴来风。
“查案”同时出现两人相类似的举报内容,本身即有一定的可信度。但查良鉴深得蒋介石等高层信任,且在上海一带宗族势力强大、人脉关系盘根交错,故调查任务中张毓泉一再推脱,郭云观、杜保祺、刘少荣等人则含糊其词避重就轻,都不愿意在这一问题上深入追究。一是忌惮查良鉴的人脉关系深知其不可动摇,二是对查良鉴的贪腐问题多少有所耳闻或目睹,甚至自身参与其中,两者矛盾,只能选择推脱或模糊化处理。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在“查案”中最高法院检察署致上海地方法院检察处的指令中,两次均提到本份密电附有“原副状一件”以及“报纸四件”,但在整份往来电函的档案中,并未见到任何相关的副状与报纸材料,亦不可知方季良所谓的“七宗罪”具体为何。显然,两处的附件均不翼而飞,很难认为是档案整理与数理中的无意疏漏,不难排除这些对于查良鉴不利的证据在密电到达之时便已被刻意销毁或隐藏的可能。
此外,“郭案”与“查案”的举报行为本身亦颇值玩味。在李大中对郭云观的举报信中,李大中自称为“上海公共租界受屈人民代表”,李大中具体为何人史料无迹可查,甚至可能只是化名,但一普通民众的举报信为何可以直通中央司法行政部并引起注意,使得司法行政部下令调查租界地方法院院长。况且,当时的上海公共租界,本身即是达官贵人与富商巨贾之聚居地,真正居住其中的“普通人民”甚少,且李大中的举报信字迹工整、言辞行文考究,其本身可能即是与郭云观有过节之显贵,或至少是其雇佣之墨客。而查良鉴几乎在同时被两人分别向最高法院检察署与司法行政部举报,似乎太过于巧合,且普通民众举报信通达高层同样困难重重。朱殿元已被证实为化名,方季良同样可能不是真名,查良鉴作为国民政府高层乃至蒋介石倚重之人难免遭嫉,其背后难说没有相关利益人士指使。可见,国民政府费尽心思设计的反贪腐制度,在遇到真正“大老虎”之时,往往不能起到真正的“打虎”作用,甚至沦为高层争斗的工具。
三、检察处“反贪”之主要内容
虽然国民政府时期的检察机关对于真正有贪腐嫌疑的政府高层人员并无力打击,但其依然在打击贪污犯罪中有所业绩。在抗战胜利、《惩治贪污条例》颁布之后,上海地方法院检察处和上海高等法院检察处自1945—1949 年记录在案的贪污案件数量分别是322 件与99 件,单从数量上而言并不算少。但在这些所查处的案件中,真正受到刑事处分的涉案人员铨叙级别和所涉事项、金额等,皆不可与“郭案”及“查案”相提并论。
在上海地方法院检察处和上海高等法院检察处侦办的这些贪污案件中,军政各机关部门的科员、办事员以及各警局派出所的警长警士③占了绝大多数的比重,这些在日常工作中偶然机会私吞少量公产或者收受当事人贿赂者,甚至仅仅用刑事简易程序就予以定罪量刑。而在为数不多的“打虎”案件中,诉讼档案的呈现往往如“查案”一般有头无尾,在上海高等法院检察处和地方法院检察处互相公文往来之后便没了下文。在其为数不多案情详细的诉讼档案中,则如同“郭案”那般清一色出现了不起诉的情况。例如,在最高法院检察署指令上海地方法院检察处管辖的浙江省松阳县前县长徐雄飞涉嫌贪腐案中,尽管有松阳县多名群众联名的举报信与起诉状详尽描绘徐雄飞的斑斑劣迹,以及福建浙江监察区监察使的弹劾状指出已有证据表明其有“贪污之罪嫌”。但是,上海地方法院检察处依然以相关证据不足和缺乏互相印证为由,做出了不起诉的决定。在相关群众上诉至上海高等法院检察处后,高等法院检察处依然以相同理由不起诉,并列举十条理由说明“被告犯罪嫌疑均属不足”,最终驳回了上诉[8]。可见,上海高地二级法院检察处侦办的所谓贪污案件,所查处的几乎均为基层公务人员,面对真正大案要案时,往往畏首畏尾,选择冷处理或以证据不充分为由做出不起诉决定。
诚如上文所言,国民政府时期高层势力的盘根交错以及世家大族对于军政机要职务的垄断,使得各级政府要员和主要负责人背后都有着复杂的利益关系,而乱世的社会环境又为各级政府官员的贪腐创造了条件,使得贪腐问题普遍存在。而检察机关在民国时期相对弱势,国民政府时期常年挂靠在法院内部,甚至一度有很高的废除呼声,也注定其在真正的反贪领域只能流于形式,面对真正的“大老虎”畏首畏尾,无法发挥司法对于惩治腐败的真正作用。
四、结语
从以上的内容不难看出,国民政府时期检察机关的反腐工作整体而言难谓成功。虽然案件体量以及最后的定罪率并不低,但其实质是有量无质之行为,大量案件均是基层公务人员的轻微贪污受贿案件,真正进入司法程序的各军政要员贪腐案件极少,被最终起诉定罪者更是屈指可数,绝大多数是冷处理或者以证据不足为由径行不起诉。对于司法系统内部主要负责人的贪腐调查更是互相推诿,最终不了了之。
究其缘由,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这与国民政府所处的时代背景有关。整个民国时期作为中国近代转型期,新老势力交叠,加之内战外患不断,社会稳定性差,除了暴力征伐的手段,金钱成为社会关系稳定的重要润滑剂。当一个国家处于变革时期、介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由于转型过程中权力监督制衡等种种的缺位,致使其中的腐化现象比该国在其他时期的腐化现象更为普遍,腐化的程度则与社会和经济的迅速现代化有关。通常,腐化现象在现代化进程的最激烈阶段,往往会蔓延于整个官场[9]。国民政府时期,贪污在各级政府中的普遍程度,已经超过了北洋军阀政府时期。它在30 年代即已十分突出,后来愈演愈烈,到40 年代中后期达到高峰[10],已然成为严重的体制性腐败。
其次,国民政府的政制建设使得其难以真正展开司法反腐工作。孙中山先生在建立民国之时,就将西方近代的三权分立模式与中国传统的考试和监察制度相结合,形成“五权宪法”之理念,即立法、行政、司法、考试和监察五权。孙中山先生本人对中国特有的考试和监察权有殷切期盼,认为可以“集合中外的精华,防止一切的流弊”[11]。显然,监察权是孙中山法律思想中反贪腐工作的重要权源。国民政府向以孙中山继承者自居,在制度建设上亦与之契合,设置监察院作为中央反腐机关,并在地方以特定的监察区为单位设监察使。监察使在发现地方官员贪腐时,可以向监察院呈报相关情况请求弹劾,监察院的监察委员根据呈报情况行使弹劾权,并将触犯刑法的案件交由司法机关侦审处理[12]。但是,正是由于监察院只有行政上的处罚权,与司法机关的侦审脱节,检察官对于监察使所查获的证据材料需再次进行司法层面的调查。这一来对于同一份证据材料需经监察和司法两次查证,使得反腐的成本增加、效率降低;二来导致反腐过程中出现监察院与检察官无法互相配合,甚至出现双方结论截然相反的情形,例如上文提到的徐雄飞案中,监察使已将收集的证据提请监察委员行使弹劾权,而检察机关却一再选择不起诉。
最后,国民政府的政权性质也使得其对各级官员的贪腐无能为力。国民政府是国民党内部亦即蒋介石为首军派势力以自己的军事优势,对外通过征伐其他割据的地方军阀,对内通过对抗国民党内其他势力集团而确立的新的党、政、军中心[13]。其本质上只是一个旧式的军阀总领。一方面,这导致各地军阀或官员各自为政,中央政府难以实际掌控全国、凝聚力量,导致虽然中央法律法规的制定在文字层面较为完善和现代化,但在实际司法运作过程中存在很大差距,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是家常便饭。另一方面,也使得各军政要职负责人往往被世家大族或与之相关的旧军阀所垄断或掌控,他们背后的利益相关方错综复杂,各机关之间的政治和金钱利益盘根交错。国民政府出于维护自身统治以及所谓的政府声誉的需要等原因,对贪污腐败行为,从制度上和实际操作中,都采取否定和打击的态度。但是,出于权力平衡和有裙带关系的利益团体之相互利益维护等因素,造成统治集团对贪污腐败行为客观上的纵容,乃至最终造成积重难返的体制性腐败[14]。这一系列的原因也导致了国民政府后期的快速崩溃瓦解。
当下,随着监察委的成立以及《监察法》的通过,中国的反贪腐工作进一步完善和加强。诚然,一套科学的反腐败制度出台绝非易事,需要经过长期艰苦的探索实践,我国的监察体制也仍在不断完善当中。因此,从监察机关到司法机关的反贪体制要向着更加科学化和精细化的方向发展,处理好监察机关与司法机关特别是检察机关之间证据材料、强制措施的衔接工作,节约司法资源、提升司法效率,对于涉及“大老虎”的重案要案,可以引入异地的指定管辖等机制,这些都是国民政府反腐工作中留给我们的思考和借鉴。
注释:
①前者如谢冬慧:《民国后期反贪制度论略》,载《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庞静:《透视民国反腐》,载《人民公仆》2015年3月号。后者如张琳:《民国时期职务犯罪法律规制考》,载《兰台世界》2013年第9期。
②如杜旅军:《中国近代检察权的创设与演变》,西南政法大学2012 年博士学位论文;刘清生:《中国近代检察权制度研究》,湘潭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③在国民政府中后期,警长、警士皆为低级别基层警务人员,中高级别警务人员为警官。参见韩延龙、苏亦工等:《中国近代警察史》(下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