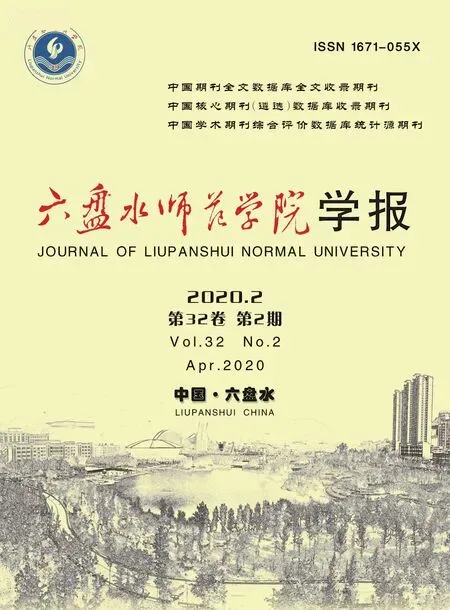羸弱与固执:周邦彦情爱词中抒情主人公性格的矛盾体现
周伟
(兰州大学文学院,甘肃兰州730000)
情爱词占据清真词的很大一个比例,是讨论清真词时应该着重加以观照的一个研究视点。值得留意的是,周邦彦能够在宋讫清这一段历史时间里被尊为“词中之圣”(蒋兆兰《词说》)[1]500,多半是由于其词“语意精新,用心良苦”(王灼《碧鸡漫志》)[2]182、“最为知音,且无一点市井气”(沈义父《乐府指迷》)[3]1438的艺术技巧而获得的。至于其情爱词的题材内容,不仅没有为其词作的接受带来益处,反而多致讥评,如刘熙载《词概》就这样评价道:“美成词信富艳精工,只是当不得个‘贞’字。”[1]492滥情弥眼的特点本是词体产生之初由于场合为歌筵酒畔而带来的一种类似于遗传因子的特性,但在道学家眼中就多有龃龉了。
迄今为止,关于清真词的研究已相当充分。学术界从艺术成就、叙事技巧、艺术渊源、接受传播、文学史定位等方面进行了探讨,已对清真词的大部分基本问题进行了阐释。这里,本文将选定周邦彦情爱词中的抒情主人公作为研究视角,探讨隐藏于其背后的双重性格:羸弱与固执。以期能够为解读这类词提供一些帮助。
一、羸弱性格:伤感与孤独中的无助
周邦彦情爱词中抒情主人公形象给人的第一个直接印象便是在人世无常、世路坎坷的折磨下流露出来的羸弱性格。所谓“羸弱性格”,也就是我们个体性格构成中那类易于感伤、趋于消极的人格品质。情爱的体验是周邦彦生命经验中的一大组成要素,也是他形之于词的一大题材内容。俞平伯《唐宋词选释·前言》说:“周词实为《花间》之后劲。”[4]14正是看到了这一点。
在周邦彦的情爱词中,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位抒情主人公,他感性而幽独,似乎生活中的一点点草木之惊也能触动他敏感的神经,勾起他对远方恋人深深的回忆,从而带给他巨大的打击。自然风物常常引发他对于感伤的联想,如“若遣郎身为蝶羽,芳时怎肯抛人去”(《蝶恋花·叶底寻春春欲暮》)[5]173,有含恨不尽之意;“人如风后入江云,情似雨余粘地絮”(《玉楼春·桃溪不作从容住》)[5]133,包含多少无奈之感;“红糁铺地,门外荆桃如菽。夜游共谁秉烛”(《大酺·春雨》)[5]108,万物皆竞作生长,而唯“我”心如死灰。我们看到,词人总能被自然界中的风吹草动唤起生命中的无常人事,从而在内心深处惹起忧郁的心事。
分散在主人公周遭的景物也多是那类比较阴郁压抑、破碎残缺的,如“烟锁漠漠,藻池苔井”(《侧犯·暮霞霁雨》)[5]63,一片混茫;“杜宇思归声苦。和春催去”(《一落索·杜宇思归声苦》)[5]355,竟联想到这声声皆苦的杜鹃声把春天也从“我”的身边驱赶开了,可想其内心的惨痛之状;“海棠开后,燕子来时,黄昏庭院”(《烛影摇红·芳脸轻匀》)[5]408-409,何其的索寞无聊;甚至连丽日明景也无法消释抒情主人公的内心愁苦:“而今丽日明金屋,春色在桃枝。不似当时,小桥冲雨,幽恨两人知。”(《少年游·朝云漠漠散轻丝》)[5]183
在离别的痛苦面前,天各一方的抒情主人公只有借助凝眺远方来寻求虚无的慰藉了:“回顾,始觉惊鸿去云远”(《荔枝香近·夜来寒侵酒席》)[5]74,“去难留,话未了。……谩回头,更堪归路杳”(《早梅芳近》)“花竹深”[5]53,“谁信无憀,为伊才减江淹,情伤荀倩。但明河影下,还看稀星数点”(《过秦楼·水浴清蟾》)[5]249。尽管天边尽头处没有令“我”满意的答案,但眼前虚空里无尽的空间还是能够捎带去一部分相思愁苦的吧。
周邦彦展现的正是人世间不可避免的聚散无常造成了抒情人物陷入如此痛苦不堪的境地之中。我们看到,词人常常在词中直接表达对离别的埋怨和无奈:“大都世间,最苦为聚散”(《荔枝香近·夜来寒侵酒席》)[5]74,“嗟万事难忘,唯是轻别”(《浪淘沙慢·晓阴重》)[5]301。所道出的不啻为一种立世箴言。别离之际,抒情主人公常常只能陷入“去意徊徨,别语愁难听”(《蝶恋花·早行》)[5]166的尴尬情景之中,无法挣脱,在其漫长的别离生涯中,抒情主人公备受相思之斫伤。所谓相思令人瘦、相思令人老,远方的恋人在抒情主人公的心中何尝不是处在同样的煎熬地位:“斜倚曲阑凝睇、数归鸿”(《虞美人·金闺平贴春云暖》)[5]367,忧郁而寂寞;“玉骨为多感,瘦来无一把”(《塞垣春·暮色分平野》)[5]87,羸弱而消瘦。这些描写与其说是在想象远方恋人的生活场景,不如说是词人自身生活场景和情感状态的真实记录。等到再次聚首的时候,抒情主人公也只能徒叹“别来人事如秋草,应有吴霜侵翠葆”(《玉楼春·当时携手城东道》)[5]127的人事变化而已了。
别离给爱情带来了新鲜血液和浓浓生机,却也给持有这份爱情的人带来生命中难以承受的残缺与无奈。短暂的别离或许只会引发几缕情感的涟漪,而漫长的别离就常常会引起深切的痛苦了。周邦彦一生羁旅在外,常常是居无定所,与那些产生爱恋之情的歌妓舞伎一经别离,见面的机会便微乎其微了。正是这样的生命现实在他敏感的内心世界里产生了巨大的天摇地动,把他多感多愁的内心世界拆散得四分五裂。周邦彦用词表现出来的自身的羸弱性格,正向我们展现了他的这一心理现实。陈廷焯在《词坛丛话》中说:“昔人谓东坡词胜于情,耆卿情胜于词,秦少游兼而有之。然较之方回、美成,恐亦瞠乎其后。”[1]497陈氏看到的周词中的“情”,很大一部分即是由我们这里所讨论的周邦彦情爱词中抒情主人公的羸弱性格所提供给我们的心理直觉。
二、固执性格:矢志不渝的遥思与凝望
作为人,会天生地具备这样一种天性:极端地爱恋或憎恶着某样事物。心理学上所谓的“偏执狂”就指的是这个特性在日常生活和社会交往中明显表现出来的那一类人。但我们这里所讨论的“固执”与心理学上的“偏执”有所差异,前者较之后者在概念范围上更广泛、更内隐得多,同时在对外伤害方面也小得多。生活经验告诉我们,对于情感而言,一旦深刻化了,就常常在精神结构中凝固为一种敏感性的启发装置,一旦获得了这种装置,我们的某种情感就会在精神活动中获得极大的自由度,就会变得易于触发、易于渗透。我们常常说“不由自主”,就正与这种现象有关。
在周邦彦的情爱词中,我们看到其中的抒情主人公对恋人怀有一种固执的爱情。对暂在身边却将要别离的恋人他始终难以割舍,而且每次割舍都不免心如刀绞。《早梅芳近》便是这样一首书写离别场景的词作:
花竹深,房栊好。夜阒无人到。隔窗寒雨,向壁孤灯弄余照。泪多罗袖重,意密莺声小。正魂惊梦怯,门外已知晓。 去难留,话未了。早促登长道。风披宿雾,露洗初阳射林表。乱愁迷远览,苦语萦怀抱。谩回头,更堪归路杳。[5]53
开头的“花竹深”三句描绘出了一个幽深封闭的庭院景象,这是两人幽会时所专有的一个二人世界;此时这个世界安全而姣好。至“隔窗”两句,色调便有所趋暗了。原来美好的二人世界被外界的不安渐渐侵入。至“泪多”四句,原先的美好尽皆为痛苦所代替。晓光侵入房栊,正标志和暗喻着分离也侵入了两人之间的这次相聚。于是下阕便转入到具体的分别情景了。“去难留”三句是具体的话别场景。在这次话别中,彼此内心里面涌动着的万千情绪、万千话语还来不及表达万一,征途已不得不踏上。“风披”两句状路上的清晨景物,可以联想到,当时初日将升、林表华然、风吹雾散、露落草轻,四近稀疏的人家犹在梦中,而唯独词人独骑深林,甚至当时还尚因昨夜的幽会而瞌睡未醒。如此遭际,那位孤身上路的词人恐怕是喟叹不已吧,“乱愁”两句正表现出了他那种耿耿于怀、怨天尤人的精神状态。最后,既不能奈何,便只有空望来路了,而那无穷的凝望,换来的也只能有无穷的伤怀与无穷的愁苦。余韵溢出言外、回荡在苍茫云天间。
当然,清真词中把抒情主人公的固执性格展现得更加深刻的还是在别后相思的情景下,此时加上词人自身宦游在外的形役之苦、索寞之苦、志气不得屈伸之苦,对远方恋人的依恋便大大加深了。劳累的旅途之中抒情主人公常常怀念起可以给予自己慰藉的恋人来:“下马先寻题壁字,出门闲记榜村名。早收灯火梦倾城。”(《浣溪沙·日薄尘飞官路平》)[5]333清闲的逸游亦赶不尽内心的相思;“到而今,鱼雁沉沉信息,天涯常是泪滴。”(《瑞鹤仙·暖烟笼细柳》)[5]300何其神思黯然。
值得留意的是,清真词中充斥着大量描写抒情主人公遥望远方以寄相思的画面:
立多时,看黄昏,灯火市。(《夜游宫·叶下斜阳照水》)[5]347
凝眸处,黄昏画角,天远路歧长。(《锁阳台·花扑鞭梢》)[5]245
但徘徊班草,欷歔酹酒,极望天西。(《夜飞鹊·别情》)[5]96
有时候甚至连方向也无法判断:“落霞隐隐日平西,料想是、分携处。”(《一落索·杜宇思归声苦》)[5]355读来令人不忍。可以说,抒情主人公所凝望的虚空的无极,正是其固执情感的外象化。
周邦彦甚至将这份对现实中恋人的固执爱情寄托到自己所爱惜的事物身上去,从而形成了其独特风格的咏物词。如其《三部乐·梅雪》:
浮玉飞琼,向邃馆静轩,倍增清绝。夜窗垂练,何用交光明月。近闻道、官阁多梅,趁暗香未远,冻蕊初发。倩谁摘取,寄赠情人桃叶。 回文近传锦字,道为君瘦损,是人都说。祅知染红著手,胶梳黏发。转思量、镇长堕睫。都只为、情深意切。欲报消息,无一句、堪愈愁结。[5]284-285
将所咏之物梅雪升格为人,使其变成自己的所恋对象,这本身就营造了一种虚无缥缈的抒情境界。我们仿佛看到有一位客子陶醉于梅花雪片之中,将纷飞的梅雪想象成自己的所思恋人。这种于幻中求真的行为难道不正是痴情的流露?可以想见,那位远方的恋人已化身在这片圣洁坚贞的梅雪之中,尽管是凛冽的寒冬也掩藏不住她内心的情爱。梅雪因相思而瘦损,这样奇绝的想象更是将词人内心的伤感表现得淋漓尽致。作者还在其中掺入了“红叶题诗”和“回文锦”等典故,更为词作的抒情增添浪漫和悲凄的气氛。以上这些艺术处理,一方面使得所咏之物获得了更深厚的寄托内涵,一方面也使得抒情主人公的爱情获得了更加形象地展现。
自然界中目睹到双宿双飞的禽类也会激发起词人源源不断的深情来:“菇蒲睡鸭占陂塘。纵被行人惊散、又成双。”(《虞美人·疏篱曲径田家小》)[5]363这里岂止是在说眼前的物,更是主人公与远方恋人之间爱情的写照;“黄昏客枕无憀,细响当窗雨。□看两两相依燕新乳。”(《荔枝香近·照水残红零乱》)[5]72有无限深情便有无限怨抑,对眼前成双成对的飞禽也不禁嫉妒起来了。
总之,我们可以看出,抒情主人公对远方恋人的这份爱情已经凝固为其本身的一种感发装置了,它能够在各种情景下被抒情主人公表现出来,而且总是表现得如此的固执、如此的无畏,其情感之深刻之热烈,其性格之固执之无畏正可用其笔下一句词句来形容:“但连环不解,流水长东,难负深盟。”(《长相思慢·夜色澄明》)[5]394沈谦在《填词杂说》中说:“‘天便教人,霎时厮见何妨’‘花前月下,见了不教归去’,卞急迂妄,各极其妙。美成真深于情者。”[1]478确实,周邦彦对于词这种艺术的“深”不仅仅体现在其写作技巧方面,也在于其注入词中的这份从现实中获得的感情的深刻上。
三、双重性格:斩不断的藕丝
藕本是脆弱易断之物,但折断后的藕之间却仍然连接着无数细小的藕丝,这是个自然界里奇妙的设计,正如人的生命虽然脆如芦苇,但却存在着完成不可思议之事业的潜能一样巧妙而神奇。用“藕丝”作为一种喻象,恰可用来象征着羸弱与固执的这样一种复合性格。周邦彦情爱词中的抒情主人公,呈现给我们的常常不是一种单一的性格类型,他是丰满而实在的,是很难用抽象的语言以一两个词概括出来的。笔者在这里所揭示的其身上的这种复合性格,就正反映了其复杂性格的一端。
我们看到,抒情主人公面临着同藕丝一样的命运:被外界所摧折,而又在被折断后难以割舍下另一半。现实的难堪反衬出主人公羸弱的一面,而内心的念念不忘又反衬出其固执于情的一面。这两者不是单一存在的,而是复合存在的,难以分清谁是谁。我们从词作中对羸弱与固执分别寻求证据时,也顶多只能看到哪一方面更明显一些而已。
周邦彦常常在久别之后于羁旅之地回想当日的惜别场景,这被学者李俊概括为周词中“沉思前事”的重叠性结构。抒情主人公在沉思前事之际,就常常表现出这种既羸弱又固执的复合性格出来。如《风流子》一词:
枫林凋晚叶,关河迥,楚客惨将归。望一川暝霭,雁声哀怨,半规凉月,人影参差。酒醒后,泪花销凤蜡,风幕卷金泥。砧杵韵高,唤回残梦,绮罗香减,牵起余悲。 亭皋分襟地,难拼处、偏是掩面牵衣。何况怨怀长结,重见无期。想寄恨书中,银钩空满,断肠声里,玉筋还垂。多少暗愁密意,唯有天知。[5]7-8
上阕是对羁旅之地环境的刻画描写。秋天的景物萧索而空旷,令人不禁心从底寒,更何况川原里尽是入夜的沉霭,耳边萦绕的尽是哀婉的雁鸣,月色又是那么清冷寒冽,而人影的络绎不绝又恰恰反衬得词人自身更加的孤独起来。酒醒后,词人百无聊赖,起视远近,一切已归深夜了,不知何处捣衣的声音铿锵入耳,唤起词人思念的悲情。思之而不得见固然将致使词人倍添羸弱之状,但也正因为现实的这份不满足,使得词人内心越发燃起了怀念的激情,于是又从羸弱之态中转化出固执之态了。紧接着,下阕转入了词人对昔日分别场景的追忆、对远方恋人生活场景的幻想,并在其中穿插着词人的喟叹,写来悲不胜悲、令人牵情。纵观之,词中塑造出来的这位抒情主人公形象,面对沉思前事、怀念深情的生命痛苦,既在这份痛苦中展现出了自身生命的羸弱状态,也将其固执的生命状态表现了出来。这两种状态没有一前一后,不是泾渭分明,而是水乳交融、互为依存。正是这种复合性的性格展现方式让我们感受到了抒情人物生命存在的复杂与痛苦、艰难与无奈。诚然,如果词人只在词中表现出来羸弱的一面,则由之透露出来的爱情痛苦将会远远弱于这种采用复合性格来展现的方式。
李俊认为周词中除“沉思前事”外,还有一种叫“故地重来”的重叠性结构①。在“故地重来”结构下的词作中,抒情主人公因目睹同一地点的沧桑变化,而深深感受到命运的无情与时间的虚无,从而形成一种无常生命的幻灭之感。幻灭感的形成正体现了抒情主人公性格上的羸弱。但周词不止于此,在其幻灭的背后,我们又能读出其对爱情的坚守与珍重,这也就是其羸弱背面的固执。我们来看其词作《垂丝钓》:
缕金翠羽。妆成才见眉妩。倦倚绣帘,看舞风絮。愁几许。寄凤丝雁柱。 春将暮。向层城苑路。钿车似水,时时花径相遇。旧游伴侣。还到曾来处。门掩风和雨。梁间燕语。问那人在否。[5]373
上阕追忆昔日与恋人幽会的生活场景。对方因预感到离别的将至,已显露出百无聊赖的愁苦之状,令人心生不忍。下阕述自己故地重游,然芳春将去、众花将谢,季节的沦没与人事的蹉跎恰恰若合符契,一种对人生的幻灭感不觉间侵入到词人内心深处。一路上流连旧迹,奈何所睹皆非旧识。及至来到故人屋前,只见一堵苔藓遍布的门墙将抒情主人公与风雨云烟一齐隔绝于外。不光人已非,连物也难葆其旧。眼前的一切不禁使得这位抒情主人公变得神思衰谢,那横梁上的燕语声也被他听成了自己的心语:那个人还在不在?无疑,这首词的幻灭感是十分强烈的。对于一般人而言,人事上的衰谢不过是一种平常的人生现象,所引起的也不过是平常的喟叹而已。但在这位抒情主人公身上,我们看到了其不同凡响的感伤与哀怨,可以想见,这位抒情主人公该是具备一副如何羸弱的性格!但作深一层思考,他何以产生这样的感伤与哀怨,不言而喻,正是由于他对爱情怀有一副固执、坚定、不屈不挠、无畏无惧的心肠;越固执于爱情也就越备受现实的斫害与欺凌。陈廷焯《云韶集》卷四评论此词说:“重寻旧迹,却写得如此凄凉,唐人‘桃花依旧笑东风’不及此也。”[6]305诚然,周邦彦的这首词比起崔护的那首绝句《题都城南庄》来是要更深厚沉郁得多。
周邦彦用各种情景来塑造一个悲痛羸弱又心地执着的抒情主人公形象:“奈向灯前堕泪,肠断萧娘,旧日书辞,犹在纸。雁信绝,清宵梦又稀。”(《四园竹·浮云护月》)[5]57看着旧日往来间的书信,痴情的女主人公已经很难再次入梦了;“金屋无人风竹乱,衣篝尽日水沉微。一春须有忆人时。”(《浣沙溪·雨过残红湿未飞》)[5]332春日慵倦,奈何忆人!“书信也无凭,万事由他别后情”(《南乡子·寒夜梦初醒》)[5]317,维持至今的书信往来已经不能慰藉“我”的热烈情感了,须知造成“我”如此煎熬、如此烦躁的罪魁祸首正是这分别之后燃烧不尽的痴情呵!在这些例子中,我们看到这些抒情人物的灵魂正在被现实的生离所斫伤,而让我们倍觉震撼的是他们又能将此残破的灵魂屹立于苦难面前,坚持着守护爱的真谛。惨淡的人生面前,拥有一颗赤子之心的人们谁不是这样一个既羸弱又固执的人呢?
周邦彦还常常让自己笔下的抒情主人公从对面设想,以增加其情感的深度。如:“叹将愁度日,病伤幽素。恨入金徽,见说文君更苦。”(《扫花游·晓阴翳日》)[5]90“金徽”即琴,以喻才男才女间的爱情。俞平伯《清真词释》评“恨入”二句谓:“渡到彼方,一语便透。”[7]再如:“想而今、应恨墨盈笺,愁妆照水。”(《还京乐·禁烟近》)正如俞陛云《宋词选释》所云:“言情处则遥想妆楼中恨墨愁妆,相思无极,安知独客伤离,亦为伊憔悴,倘归飞有翼,方知两心相忆同深也。”[8]从对面设想的这种体例有这样一个明显的效用:揭示我们人类在不能将“心”互换的局限性面前的人生悲剧。文学理论上“真”的问题的不可解决性正是这个人生悲剧的一种“人生—文学”的投影。
古人由于时代局限的原因,他们的爱情多留给了社交场合相识相知的歌妓舞伎,而对于妻子,他们常常直到悼亡之际才会流露出相濡以沫以来的夫妇之情。有不少学者将这一现象的原因归结为:二者之间的婚姻是建立在封建礼教关系上而多无深厚感情。这自然是不可缺少的可能性,但笔者认为更大的可能性应该是:古代作家们由于深受封建礼教的束缚,不方便直接在作品中表现对妻子的眷恋与依赖。夫妇关系作为人伦之首,是异常尊贵的;如果一个丈夫在作品中书写对妻子的思念与不舍,恐怕会被社会认为是不务正业、溺于情爱的。连皇帝在后宫中稍有专宠之举都会被满朝文武讽谏曰淫乱后宫、荒于朝政,更何况是一般人呢,谁敢承担此亵渎人伦的大罪?且看周邦彦的《玉楼春》:
玉琴虚下伤心泪。只有文君知曲意。帘烘楼迥月宜人,酒暖香融春有味。 萋萋芳草迷千里。惆怅王孙行未已。天涯回首一销魂,二十四桥歌舞地。[5]128
开头即以旧日回忆入手,展现昔日夫妇之间的缠绵深情。词人回想起当初琴瑟和鸣的场景,既有夫妇团圆的喜悦,也不缺离别时候的伤心;不拘于一端,适得圆满,倍增实感。下阕回归现实,是自己远隔家乡、羁旅千里的场面。在这惆怅的时刻,思念起亡故的妻子,词人不禁心痛欲绝,而回首之际,正是离开不久的热闹都市扬州。扬州距离美成的老家杭州不远,可见他方离家不久;当此之际,其悼亡之情可想而知。
要之,周邦彦情爱词中抒情主人公的性格在羸弱与固执的交织之中显示出了其深刻的复杂化。其笔下的情爱不是一种团圆式的人间爱情,而是一种多磨多难式的才子佳人爱情。正是这样的设定造成了其笔下的抒情主人公总呈现出来羸弱感伤的精神状态,但在其深处,我们又总能看到抒情主人公背后的固执与坚持,即便现实如何多灾多难、别离不断,但那根牵拉在彼此之间的爱情之线,总如藕丝那样似细而牢、似脆而坚。抒情主人公总是呈现出这样的面貌:“无限柔情,分付西流水。忽被惊风吹别泪。只应天也知人意。”(《蝶恋花·酒熟微红生眼尾》)[5]174柔情似水,虽柔弱却从未截断;此情何比,无情之天亦为感动。
四、结语
生活上的无奈分别以及人生中的种种苦闷给周邦彦的情爱体验带来了不可避免的悲愁绵邈,为其情爱词的书写注入了一股沉重浓厚的悲剧元素,正是这份悲剧元素使得其情爱词中的抒情主人公带上了羸弱感伤的性格特点。但经过深入的细读与分析,我们发现,在抒情主人公羸弱感伤性格的背后,还有着更为直通人心的坚执一面。可以说,正是由于有这份隐在的固执坚定性格作为“骨”,其羸弱感伤的性格“外表”才能焕发出感染读者的风力来。也正因此,周邦彦情爱词中的抒情人物获得了一份活生生的丰满性格;他不是一个经由作者给带上精心策划的脸谱的硬生生形象,而是一个与我们一样有着复杂的矛盾体验的活生生人物。这正是周邦彦情爱词能够打动人心的一个重要原因。
注释:
①参见李俊:《“故地重来”和“沉思前事”——周邦彦词的重叠性结构》,《文学评论》2019年第2期,145-152页。作者在文中提出了周词具有“故地重游”和“沉思前事”的两种时空重叠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