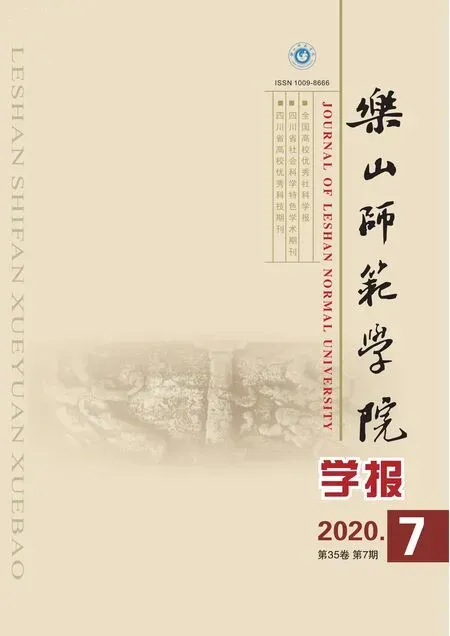南京国民政府“汽油节约”运动述论(1947—1949年)
林增煜,周石峰
(贵州师范大学 a.历史与政治学院;b.马克思主义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汽油作为一种液体燃料,无论在平时抑或战时,都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物资。“汽油节约”也是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消费节约运动的一环。学界对于国民政府倡导之消费节约运动多有讨论,但个案研究尚显薄弱①。而对于民国时期的汽油问题,相关论著虽有所涉及,但或侧重于梳理国民政府在全面抗战时期解决汽油问题的相关政策,或侧重于探究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汽油进口,尚未有对战后国民党政府的汽油政策和汽油管控进行专门的考察②。本文将以上海为中心,对1947至1949年南京国民政府开展的“汽油节约”运动进行初步探讨。首先分析上海开展“汽油节约”运动的背景,进而爬梳运动的主要举措,最后则审视其历史限度。
一、汽油限额进口与厉行消费节约
全面抗战时期,汽油作为一项重要战略物资,曾有“一滴汽油一滴血”的比喻。抗战胜利后,社会对汽油的需求并未有丝毫下降。尽管战后国产汽油的产量具有显著的提高③,但远远满足不了社会的需要,仍需从外国大量进口,由此所消耗的外汇数额巨大。1946年3月,行政院院长宋子文基于各种现实的考量,实行“开放外汇市场”④,导致“无限制的供给外汇,汽车汽油十分便宜”[1]。尔后国民政府意识到外汇流失严重,于1946年11月份修订《进出口贸易暂行办法》,对进口物资实行输入许可制度。汽油此一项物资,虽作为许可进口之物,但同时也受到限额规制,“其限额由输入临时管理委员会订定,交由分配处分配之”[2]。自此“全国油料分配之机构,不得不限制使用”[3]。汽油这一项物资开始从不限量的自由进口转变为限额进口⑤。1947年2月上海爆发“黄金风潮”,物价上涨,抢购成风。汽油恐慌频发,“路边列队等候加油之汽车长蛇阵到处可见”[4]。南京、广州等地之汽油更是有货无市,油价飞涨[5]。尽管该风潮最终得以暂时平息,但由于汽油进口的限制性规定,加上诸多经济政策和战后社会环境对油价的影响,国民政府意识到对汽油使用进行管控日益显现出其重要性和紧迫性。
汽油作为燃料,其最重要的用途在于为汽车等交通工具提供动力能源,此外部分工业亦以此作为燃料或辅助用料。上海作为民国时期著名的“销金之窟”,汽车数量庞大。“开放外汇市场”后,上海无疑首当其冲。进口汽车大量涌入,“真有‘车满为患’之势”[1]。1946年12月底,上海全市拥有汽车为19 000余辆,1947年2月增至20 836辆。[6]至9月底,已登记的各类汽车达到26 000余辆。据《和平日报》记者张乃敏估算,假定每辆汽车平均每月需消耗汽油量为150加仑,则全市汽车每月需耗油量将达到390余万加仑,不禁感叹“这数字确已是惊人”[7]。
1947年秋,为适应“总动员”之需要,国民政府酝酿推出若干节约消费办法。1948年9月,蒋介石又以“国民一分子”的资格发起“勤俭建国”运动。无论是“厉行消费节约”还是“勤俭建国”,提倡和实行“汽油节约”都是计划中的重要内容。上海汽车数量如此之庞大,所消耗之汽油量如此巨大,通过若干政治手段对上海的汽油使用进行管控,已成为必然。“实行节约应从上海做起”[8]。“汽油节约”运动之目的,当在“于少数之限额中,须供给本市工厂汽车,公用事业等之消耗”,且“不消耗外汇起见”[9]。
二、“汽油节约”运动的开展
(一)限制私人使用汽车
汽车是汽油最主要的使用载体。就上海而言,据从欧美游历回来的人描述,上海汽车数量之多甚至可以比肩于当时的伦敦和巴黎。[10]汽车一物,“一般下层老百姓与之无缘,故不必说,即连中人以下也都无法享受”。[11]汽车成了上层社会炫耀性消费的象征,消费汽车是“一种拥有财富的证据”,然而不适当的汽车消费也是“下贱与罪过的标志”[12]。因此,在南京国民政府及上海当局看来,限制私人使用汽车是节约汽油消耗的有效手段,也正如时人所说,“实施汽车节约,第一步先要取缔私人的过量汽车”,上海富人一人拥有数辆汽车已相当常见,所以“应该先将这些过剩的汽车取缔后再设法淘汰其他汽车”[13]。
1947年9月行政院出台的《私人使用汽车限制办法》规定除医师、工厂矿场、新闻报社等行业得使用私人汽车之外,私人自用或营运车辆将被限制,即实行“分期抽签核减”。随后上海市政府依据此法制定《限制私人汽车及公务用车各项规定》。相对于行政院之汽车限制方法,上海当局的规定更为严格。该规定共分为两部分:一是在限制私人汽车方面,一年之内新车“不得加发牌照”,私人汽车在未经行政院批准前“一律暂停过户”,但救火车及救护车等公用事业用车经核实后可发照。非特殊情形,私人不得自国外携带汽车进口。“凡有闲阶级之汽车,当在取缔之列”[14]。二是在公务用车方面,该法对市政府各部门添置小客车作若干限制性规定。[15]12月,上海当局拟实行汽车分级配油,厉行节约,出台《公私汽车登记领照暂行办法》,对公私汽车之申请登记程序进行具体规范。“合乎行政院颁布的节约办法内准许备用的私人和私法人的车辆,明年1月起可继续申请登记,并可发出牌照。”[16]也就是说,医师、工厂、矿场、新闻报社等使用之小汽车或大汽车将重新准予登记。
1948年9月行政院颁布《减少汽车节约汽油办法》,规定上海汽车按照8月19日登记数量减少三分之一。[17]10月份,根据上海市府制定的汽车汽油节约办法,决定除公共汽车、市政用车、受外交优待及领有正式执照之营运货车外,其余汽车采用“四去一”或“二去一”的方式进行核减。[18]即凡机关使用的汽车满四辆抽去一辆,私人汽车两辆去掉一辆[19],除医生及新闻记者外,“逢星期日及非办公日,市民一概不得使用自备汽车”,而医生出诊,以是否随身携带诊具为标志。[20]至1948年,对汽车使用的种种限制规定愈加严格。
(二)从汽车凭证购油到分级配油
1947年8月底,上海市政府公布《本市汽车凭证购买汽油办法》,并定于9月5日起实行凭证购油。该法案共6条,具体规定凭证购油的适用对象、流程甚至于军车用油的办法。该法强调“如未领购油证者,加油站拒绝供应”。纵观全文,该法仅强调要将汽油直接灌入汽车油箱内,由加油站人员将购油量及日期填入购油证,[21]却并没有对每辆汽车的购油量作出限制性规定。正如公用局方面所宣称,该法施行之目的在于“防止汽油私运‘匪区’及便于统计汽车实际用油数量”[22]。
凭证购油实行之初,各加油站“加油情形,良好如旧”[22]。然于9月5日,行政院亦颁布《私人使用汽车限制办法》,规定工厂矿场、民营企业、新闻报社等不予限制之车辆的加油限额。“小型车每月加油以60加仑为限,大型车每月以100加仑为限”,[23]此举一出,各车主深恐汽油一经限制,便难以获得,“争相至加油站购贮大量汽油”,由此造成各加油站缺油及拥挤现象。面对如此严峻态势,上海当局又出台规制汽车加油相关条例,规定各种机动车辆每次加油,必须加入油箱,最多每三天加油一次,机器脚踏车每次加油不得超过1加仑,小汽车每次加油不得超过10加仑,货车则为20加仑。[24]亦即小汽车每月加油限额100加仑,货车限额200加仑。此限额加油办法的出台既在于响应厉行国民政府“消费节约”的号召,也是为缓和当时上海的市场态势,故上海设定的限额标准相对于行政院的规定而言较为宽松。自10月份开始实行后,汽车加油站情形“已逐渐恢复常态”[22]。
为更好厉行国民政府规定的汽车汽油节约,上海当局在节约委员会下设立汽车汽油检查小组。该小组由公用局召集,警察局、汽车商、出租汽车业、运输汽油业及各汽油公司等共同参与,旨在取缔囤积及非法黑市买卖,以及检查私人汽车使用情况等。“如查得囤积及黑市买卖情形,将按取缔日用品紧急措施办法处罚”[25]。1947年12月,为统筹汽油分配工作,上海当局组建“汽油分配委员会”,下设车辆汽油分配组及轮船工商业汽油分配组,分别负责汽车及轮船工商业汽油使用额度的分配事宜。[26]上海市的汽油节约及汽油分配工作日益组织化和专门化。
设立汽油分配委员会是实行分级配油的先声。1948年1月1日,上海汽油分配委员会实施《本市机动车辆分级配油办法》,标志着上海正式实行汽车分级配油。依照该办法,自用汽车依据空车重量被分为四个等级,分别对应四级不同的配油量,最低30加仑,最高75加仑;营业汽车不分等级,每月限额100加仑。而自用货车亦分为三级,同样对应三个档次的加油量。同时,该办法重申“至多每三天加油一次,且须直接灌入汽车油箱内”及各种车辆每次加油之限额[27]。1948年7月,国民政府重定各地汽油配额,上海全市配油总额核减为150万加仑,汽车分级配油标准随之修改。以小汽车为例,最高60加仑,最低24加仑,营业汽车则为80加仑,[28]且外埠车辆此后“概不给油”[29]。10月,“勤俭建国”运动期间,国民政府推行“减少汽车节约汽油”,上海市配油额“按8月19日前一个月汽车实际用油量减少三分之一”[17]。市政府即出台核减车辆节约汽油之措施。按照“四去一”与“二去一”相关规定,应予核减之车辆按“大型车20加仑,小型车10加仑”的基本油量暂予继续配油,应予保留之车辆,仍然按每月分级配油方法配油。而根据10月份配油标准,自用汽车最高配油量为42加仑,最低则为17加仑。[30]
(三)试验节油新技术
上海当局还试图通过技术手段节约汽油。技术的改进主要体现于两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在于研发和推广节油器。公用局公共交通公司筹备委员会曾奉命会同中央化工筹备处等机构,联合研讨制造节省汽油所需之“炭清氧晶体”,然后交通公司运用其自制节油器,并于公共汽车上实验。若成功,则将其推广至其他繁忙线路。该节油器主要功效体现在,“对经过闹区之公共汽车,有特殊成绩”,然而对于经过红绿灯不多的区域,“其节省效力,并不显著”[31]。
第二种方法,即汽油中掺酒精。酒精同样也为一种燃料,相对于汽油,国内酒精产量颇为可观。不仅“台湾各糖厂酒精生产量极多”,而且“粤,闽,渝,赣等省制造糖蜜时亦均能生产大量酒精”。[32]若“汽车用汽油加十分之二无水酒精,及百分之一到四的丁醇,则上海每年可节省360万加仑汽油”,不仅节省下之汽油可以供应工业生产需要,而且可以“刺激台湾糖业增产”。此外,使用掺用酒精的汽油不但汽车耗油量不增加,且引擎发动更为平滑,价格也较为低廉,“有立即促其实现的必要”,因此上海工商辅导处建议全国经济委员会召集有关机关会商实施办法。[33]
三、“汽油节约”运动的历史限度
根据各汽油公司报告,上海全市工业和汽车汽油消耗量,1948年1月份为1 959 253加仑,2月份为1 843 219加仑,相比而言减少11万余加仑。从以上的数据或可看出,在上海当局的强力推动下,“汽油节约”运动不失为“已收节约用油之实效”。[34]然而,仅从零星的数字出发并不能一窥运动之全貌。如同战后初期国民政府将“节食”运动之“节食”责任转嫁于群众一样⑥,“汽油节约”运动的对象亦是以群众为主。而从群众的角度自下而上地考察运动的过程可知,限制私人使用汽车收效欠佳,限额配油制度弊病明显,“汽油节约”运动极具历史限度。
(一)限制汽车效果不彰
“沪上汽车数量并不因节约方案而减少”[35]。上海作为一座“挥金如土的不夜城”,每当夜晚11点钟,舞厅影戏院散场以后,络绎不绝的小汽车依旧在街上“风驰电掣”。[36]1948年8月后,南京国民政府要求上海汽车数量核减三分之一,然而每月经市长特准发给汽车牌照之车辆,“竟有百余辆之多”,而汽车发照审核委员会每月严格审核也仅是批准10余辆。[37]1948年10月上海的汽车汽油节约办法规定了具体的核减汽车方案,但该方案对应核减之汽车亦仅限制汽油的配给,并不吊销车照。因而领取汽油配售证者,连日来在市府门口“排成数条蜿蜒长蛇阵,长达200米”,可见上海汽车之众多。虽然汽油配量减少,但“固有办法之四轮阶级,仍可于黑市中求得汽油,照样使用汽车”[35]。虽然新汽车无法领得新照,但富户们“买进了新汽车,换上执照,再把旧汽车卖去”,仿佛“摩登小姐们一年年更换新式时装”。这样,“当可更显出他们的豪华富贵”。[38]有车阶级的“花前蜜约”不仅依旧,而且还可得到基本量10加仑的汽油配给“外快”。[39]可见,即使在高喊“限制汽车”的环境中,私人汽车的使用并未受到影响。所谓“节约也者,不过表面文章而已”[38]。
此外,限制汽车的措施虽对汽车商行造成一定影响,但并不妨碍汽车的进口和消费。汽车限制过户与停发新照,毕竟于汽车买卖有所冲击,因而最先站出来反对的,当然是汽车商行和汽车经售公司。该两行业要求市府“放宽尺度,使他们得以维生”[13]。虽然看似行业生存艰难,但社会上的汽车消费似乎也大有人在。早在1946年11月,小汽车已被列为禁止进口商品⑦,然而虽然私人进口自用受到限制,但是车行进口依旧,此类车行“可以说是豪富大户们的唯一买办”[38]。1948年9月,上海美通汽车公司进口一批一九四九式新型福特和谋克利汽车,《大公报》记者前去采访,问及“买了汽车如何领得新照会”,只听旁边一位西装革履的客人说道“买了,不一定在上海用”。[40]普通车行尚且如此,又何况孔家的扬子公司这样与政府高层有诸多联系的利益集团。1948年10月蒋经国在上海“打老虎”的无果而终,或许也早已预示着限制私人使用汽车无果而终的结局。
(二)限额配油诸多弊病
首先,战后上海汽油恐慌的氛围一直存在。汽车汽油节约办法甫一出台,无疑加剧了这种氛围。各种各样的囤积行为和加油方式层出不穷。若干车辆往返油站多次加油,或者在加完油后另以高价收购者,“遂得囤积,需要以外之油量,不虞匮乏”[41]。在每个加油站,市民争相抢购,“买得多的过剩,少的不够用,因而影响淳厚守法的市民”[42]。尽管上海当局采取相关措施暂时平息事态。但在此后,由于汽油不断涨价,加以汽油限量使用,汽油恐慌一直持续,与“汽油节约”运动相伴而存。
汽油涨价除了因本国货币膨胀和贬值外,也有外汇波动及加征关税等因素的影响。1947年10月,国民政府为“力谋平衡预算,节约靡费”,对汽油从价加征关税50%,[43]当月油价即飙升至每加仑25 500元,相较于之前涨幅超过一倍。[44]此后,汽油涨价不断。1948年1月,每加仑48 000元[45];1948年6月10日,每加仑40万[46],6月19日涨为每加仑58万。6月29日国民政府输出入管理委员会又调整为每加仑82万,一月三涨。社会各界对该会屡次调整售价,而未致力于疏导来源以解决恐慌“颇表反感”。[47]尽管汽油公司一直表示“本市汽油存底颇丰”,但恐慌的氛围未能由此减少,“若干车辆在黎明前即开至加油站预先等候”。[46]购油行列中占最大多数的营业性车辆购油气氛更加紧张,出差汽车及大卡车司机甚至直接“卧宿车上”,通宵排队。晨早时分,加油站前早已“停成长龙一条”,油量“瞬息告罄”[48]。如此般供不应求的市场状况亦催生出一批倒买倒卖者,“轧汽油”的黄牛们买到了汽油,便以黑市价格出售,“一天可轧汽油10加仑到20加仑”,“可以赚1000万元以上。”[49]此等囤积居奇的行为,真乃“不但需求者不足应用反而挑了一批人发财”[50]。更有甚者,“若干车辆由身穿制服之军人驾车,或由军人乘坐车上冒充军车,持强迫令加油”。[51]油价的不断上涨导致购油氛围的日趋紧张。在此情境下,用油者对汽油需求的投机心理与“汽油节约”的限额配给互相矛盾,“如不宽放供油数量,拥塞纷扰情形将永远无法改善”[48],如若宽放油量,“汽油节约”不啻于一纸空文。这一矛盾贯穿“汽油节约”运动始终,无法调和。
其次,从相关行业对汽油限额分配的态度中也可一窥该制度的流弊所在。配油制度出台后,汽油公司因感到该制度“不完备,很影响配油”,因而采用消极不合作办法,“多数汽车不但可配油,且可直接购油”,这无疑助长了黑市流行之风。[42]汽油分配量过少而未能满足实际需要,也导致与汽车相关的行业面临生存危机。1947年10月,小汽车每月最多配油100加仑,其实该配油量“比实际量相差很多”,不仅汽车销售颇受影响,纷纷要求政府按目前油量加配一倍,“如果不准,只好被迫停业”[13],而且对出租车行业而言,亦是“实感不敷应用,影响营业殊巨”,同样要求政府增加配售量,“若用油限量再不宽放,不但营业既受限制,公司势将濒于绝境”。[52]1947年10月的汽油限额尚且如此,往后限额不断缩减,其情形便可想而知了。1948年10月,随着上海全市配油额进一步缩减,私人小汽车的限制更为严格,汽油价高且配量不足,使广大出租车司机入不敷出,“大小车行均告亏蚀”,最后不得不“每日应召出差,以用完一日平均配给油量为限”,免得一月之汽油配量“在两三日即全部用罄”。[53]不仅给需要远行之人带来诸多不便,而且三轮车夫“趁机漫天讨价”。正如时人余一所说的,“自备汽车的数量不妨减少,节省下来的汽油,供应给出差的汽车,这才是个合理的办法,也是无人不盼望的。”[54]
再者,不止本国国民对汽油限额配售多有怨言,甚至连外侨是一片质疑之声。住在虹口一带的美侨,他们经常用自备汽车接送子女上学,若汽油供给受限,而又无直达公共交通车辆,将对其接送子女造成了影响。因此对当局节约汽油限制汽车的规定,“提出警告”。[55]限额分配虽然减少了汽油供给,但也使得人民生产与生活大受影响,恐怕也未必能称为“已收实效”。诚如时人所言,借紧缩配额的举措以达到限制用油之目的“已完全失去”[48]。
概而言之,作为战后国民政府所倡导的消费节约运动的一环,“汽油节约”运动是“国民政府尝试解决国家危机的一项办法,也是进行现代国家构建的重要基础和准备”[56]。战后,上海作为“车满为患”的大城市,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汽油节约”运动肇始之地,为节省外汇、厉行节约、撙节汽油而实行之“汽油节约”运动,其效果显然并不尽如人意。通过颁布限制私人使用汽车办法、实施汽油限额配给制度及试验相关节约汽油技术,表面上看,上海的汽油似乎有所“节约”。然而,深入考察“汽油节约”运动整个过程,却可看到,限制使用私人汽车的效果并不明显,限额配油制度自身具有诸多无法回避的局限性,“汽油节约”运动似乎并非“已收实效”。诚如运动初始时人所言,“抑专为节省外汇,以限制用油,从而使若干车辆,弃置不用,坐减其运输力量,则不免限于因噎废食的错误。”[57]战后国民党政府为其“最大限度集中全国人力物力”之目标,试图继续沿用战时做法,通过法规条令和社会运动等方式,对人民群众消费行为及社会生活进行规制。由此观之,其可谓并不成功。
注 释:
①孙钦梅从国家构建的视角梳理国民政府时期的节约运动,认为节约运动于国家构建而言并未达到应有成效。(孙钦梅《国民政府时期的节约运动与国家构建》,《江西社会科学》2016年第10期);专题研究中,李丹丹的硕士论文《纸张的进口、统制与配给(1945—1949)——以上海为例》(上海社会科学院,2015年)论述了战后上海的“纸张节约”运动。
②参见吴志华《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汽油问题及其解决》(《甘肃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及孔庆泰《国民党政府时期的石油进口初探》(《历史档案》1983年第1期)。
③战后初期国内的汽油产量,计1946年为5 057 000加仑,较1945年增加34%,1947年为8 744 000加仑,较1945年增加130%。见《我国汽油产量渐增》(《交通部公路总局第六区公路工程管理局月刊》1948年第1卷第10期)。
④关于战后“开放外汇市场”,可参阅宋佩玉、张向东《宋子文与战后“开放外汇市场”政策》(《史学月刊》2009年第7期)。
⑤孔庆泰指出,油类限额进口管理制度仅针对民用油品,对于军事所需用油,可以“专案订购”,不受此限。见孔庆泰《国民党政府时期的石油进口初探》(《历史档案》1983年第1期)。
⑥此种观点,见宋可伟,郑雪健《荒政与民心——1946年国统区的节食救灾运动评析》(《广东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18年第6期)。
⑦1946年11月颁布的《修正进出口贸易暂行办法》将“容七座以下之载客汽车其出厂价格超过美金一千二百元或相等币值者及其车台”列入附表四“禁止进口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