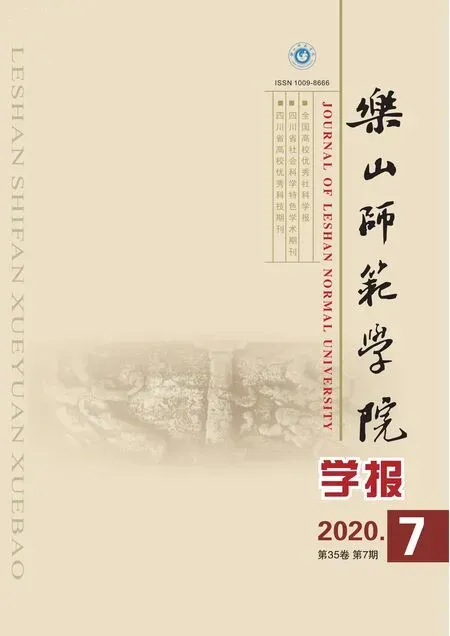苏轼倅杭词与守杭词的差异表现
陈泽宇,芮文浩
(安庆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安徽 安庆 246011)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1]2641(《自题金山画像》),苏轼一生宦海沉浮,几遭贬谪,大半个中国都留下他的足迹。在苏轼的词作各时期的研究这一问题上,言苏轼必言黄州,它已成为苏轼身上不可抹去的一道色彩,也成为人们了解及研究苏轼的热点。除黄州外,苏轼与杭州的渊源也颇深,东坡先后两次出仕杭州,此间不乏诸多精彩的词作。就苏轼黄州词和杭州词的研究现状而言,以笔者目力所及,学界对其杭州词作的研究力度和深度,远不及前者。《一位天才词人的试笔——苏轼前期杭州词平议》[2]14-19、《论苏轼的两次仕杭词》[3]135-137、《苏轼判杭词研究》[4]239-240、《苏轼倅杭心态浅析》[5]46-52、《苏词“应社”说——兼论东坡倅杭之心境与词境》[6]41-47及《苏轼判杭词创作的文化机制》[7]47-51等文较集中论及苏轼通判杭州这一时期词作的创作情况。这些文章着重于论述倅杭词是其“应社”还是“应歌”的性质抑或说明倅杭词始终秉承苏轼的“自是一家”“自出新意”,而不是“稚嫩无待多言”。对于知杭州的词作研究更是少之又少,张志烈教授的《苏轼元祐杭州词的情感意向》[8]55-60是仅此一篇注意到守杭的创作情况。《论苏轼的两次仕杭词》一文是仅此一篇注意并概述两个时期词作创作情况的文章,但对其两个时期词作的差异之处并无过多的论述。
倅杭词可算是苏轼早期的词作,初登仕途的苏轼从别情词到写景记游,多呈现婉约风格,试图在风光迤逦的杭州中排遣心中的苦闷,对其窥探苏轼前期词作的思想情感及艺术特色等可谓意义重大。守杭时期,苏轼经历“乌台诗案”之后再次的政治失意,处世更加圆融,各词作虽也有嗟叹人生或仕途之坎坷,但多一份清旷的意味。探究这一时期词的创作,有利于我们去认识已是“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苏轼在经历了元祐党争之后情感表达及意境等方面的变化。值得注意的一点,守杭时期可算是对东坡黄州时期所习得的旷达性格的检验,甚至是定型化。
一、倅杭词与守杭词差异的具体表现
从倅杭到守杭的跨越,东坡在宦海中完成了仕隐两难到承认人生多悲哀中寻求超越悲哀的旷达情怀的转变。杭州词作为苏词有机整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使我们可以一窥苏轼这一人生转变中不曾被人发现的别样魅力。
(一)倅杭与守杭:两次赴任,丰富词作
熙宁四年(1071)十一月,苏轼因与王安石为首的新党政见多有分歧,遭谏官谢景温诬奏,苏轼“未尝以一言自辩,乞外任避之”[9]1412通判杭州,熙宁七年(1074)九月离杭赴密,苏轼在杭州停留了近三年时间,此为倅杭时期。这一时期,苏轼带着“君岂久闲者,蓄极而通,必将大发于政”[10]358(《墨宝堂记》)的期望与“眼看时事力难任,贪恋君恩退未能”[1]314(《初到杭州寄子由》)的矛盾心情,开始了长达近三年的因政治上失意而第一次外任地方之职,以求“必进人事,然后理足而无憾”[10]355(《墨妙亭记》)报答朝廷。在词作中,渴望功名下引发的复杂情感与内心矛盾正是这个时期词创作的主题。
在倅杭近三年中,苏轼作词46首。写景记游和别情词是其主体,分别为8首与15首,已占词作的一半。咏怀与羁旅行役合计有6首,咏史怀古、哲理等其他题材的词作共计17首。
元祐四年(1089)三月,苏轼因策题之谤及疲于蜀洛之争,遂请外任避之,以龙图阁学士充浙西路兵马钤辖知杭州军州事(简称为“知州”),主政一方,并于元祐六年(1091)三月奉召还朝,此为守杭时期。苏轼此时已经历了九死一生的“乌台诗案”,人生阅历颇丰,借助道释两家思想来排遣仕途之苦累,一个旷达的形象已初现。在“更有鲈鱼堪切脍,儿辈莫教知”[11]819(《乌夜啼》莫怪归心甚速)中“谁似东坡老,白首忘机”[11]668(《八声甘州》送参廖子)成为创作的主流。
守杭时期,苏轼在杭州近两年的时间,共作词31首。别情词5首,写景记游也有8首,咏怀词有所增多,计7首,歌妓、羁旅行役等其他题材的词作共计11首。
(二)内容之不同:从“贪恋君恩退未能”到“禅心已断人间爱”
倅杭时期,正值杭州人事变动频繁之际,故苏轼多面临送别友人,其别情词创作自然是最多。这些词作除了表达苏轼与友人之间的真挚友情及离别时的千般不舍外,也流露出建功立业与避世幽怀的欲仕不能欲隐不忍交织在一起的矛盾心情。试看《南乡子》(东武望余杭):
东武望余杭。云海天涯两茫茫。何日功成名遂了,还乡。醉笑陪公三万场。
不用诉离觞,痛饮从来别有肠。今夜送归灯火冷,河塘。堕泪羊公却姓杨。[11]90
此词作于熙宁七年(1074年),词中“何日功成名遂了”表明了苏轼“致君尧舜”的迫切心情,另一面,“何日”一词却表明这种“功成名遂”多少是一种期盼,一种未知的惆怅,令人读来不难感受东坡万般滋味在心头的心酸。“还乡。醉笑陪公三万场”的前提条件是“功成名遂”,而欲“功成名遂”足见苏轼有锐意进取的淑世精神,其最终“还乡”是功成身退,此又源于道家的避世思想。应该说,苏轼在这里是用功成身退的美好愿望对因蹉跎岁月而壮志未酬的自我慰藉。诸如此类的词作还有“一舸姑苏,便逐鸱夷去得无”[11]74(《减字木兰花》云髻倾倒)、“爱君才器两俱全”[11]93(《浣溪沙》白雪清词出坐间)、“旌旆满江湖,诏发楼船舳舻。投笔将军因笑我,迂儒。帕首腰刀是丈夫”[11]99(《南乡子》旌旆满江湖)及“虚老严陵,君臣一梦,今古空名”[11]24(《行香子》过七里滩)等都曲折地表达了苏轼对建功立业的渴望,又想避世的复杂心态。
守杭时期,送别友人也是苏轼常面对的事情,但较之倅杭时期的送别词,最大的不同在于别情中侧重写友人与自己相同的志趣——淡泊名利,超然旷达。最典型的当属《临江仙》(送钱穆父):
一别都门三改火,天涯踏尽红尘。依然一笑作春温。无波真古井,有节是秋筠。
惆怅孤帆连夜发,送行淡月微云。尊前不用翠眉颦。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11]665
此词是苏轼于元祐六年(1091年)离杭前送好友钱勰赴瀛洲所作。开头写友人“天涯踏尽红尘”之仕途劳苦,但钱勰对此却是“依然一笑作春温”面对人生之逆境,可谓乐观至极。接着,一句“无波真古井,有节是秋筠”写出钱勰超然物外、淡泊尘世的高尚品格,深化其“依然一笑作春温”面对人生逆境的态度。在此,友人面对人生逆境的态度也正是苏轼面对逆旅的态度。下片一句“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使得词的苦涩之情稀释殆尽,既是对友人离别的安慰,更是揭示了一种人生的普遍哲理——由眼前及人生,以其看似平淡之词写出深沉的人生之感——你走我也走,大家都一样,以“无波真古井”不必“尊前不用翠眉颦”的人生态度待之,才是你我笑对人生失意该有的态度。一种泰然自若的豁达胸怀由此显现,这也是东坡旷达的性格使然。诸如此类的还有“笑看潮来潮去,了生涯”[11]624(《南歌子》冉冉中秋过)、“独棹小舟归去,任烟波飘兀”[11]633(《好事近》湖上雨晴时)等。
而写景记游的词作,倅杭时期,除了已被前人所关注到的东坡醉情于山水之间,抒写杭州景色秀丽,我们还应关注到词作流露出虚无的避世情怀,最典型的当属《行香子》[11]24(过七里滩)与《瑞鹧鸪》[11]28(城头月落尚啼乌)。守杭时期,在风光旖旎之中不仅有壮志未酬的悲叹,如《临江仙》(多病休文都瘦损)[11]611等,还有在浪漫主义格调中写出钱塘江涨潮之壮观,在开阔意境中显示出东坡洒脱达观形象的《南歌子》(海上乘槎侣)[11]620、在夜游西湖时叹老来无成的郁闷心境中以旷达的心态寄寓人生乐观的《好事近》(湖上雨晴时)等。
其咏怀与羁旅行役之作,倅杭时期,既有借思妇之口叹赈灾羁旅在外而回杭不得的《少年游》[11]59(去年相送);也有《醉落魂》(轻云微月)的“此生飘荡何时歇,家在西南,常做东南”[11]58的游宦在外而思乡甚切的词作。守杭时期,其咏怀羁旅行役词作,大都是写仕途之苦闷中,东坡总以旷达的情怀对待这些人生已是常事的身外苦累,如《鹊桥仙》[11]618(乘槎归去)等。
总体而言,倅杭时期,不论是别情词,还是咏怀、羁旅抑或写景记游的词作,内容总体特色可用“苦涩”两字来概括。守杭时期,阅尽人世沧桑后,以佛老排遣苦累,旷达成为词作中的主调,东坡总能于苦中作乐,成为一个“乐天派”。
(三)意境之不同:从清丽淡雅蕴苦闷到开阔沉稳见放达
胡寅在《酒边词·序》写道:“及眉山苏氏,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而逸怀浩气超乎尘垢之外。”[12]524但是,苏轼倅杭时期的词作,应该说,婉约之作多之。如《江城子》(孤山竹阁送述古):
翠蛾羞黛怯人看。掩霜纨,泪偷弹。且尽一尊,收泪唱阳关。漫道帝城天样远,天易见,见君难。
画堂新搆近孤山。曲栏干,为谁安?飞絮落花,春色属明年。欲棹小舟寻旧事,无处问,水连天。[11]78
词的开篇用“怯”“掩”“偷”三个词写出一个歌妓面对离别之时难以掩饰的伤心之状,在一曲《阳关》中诉说前往之地是那么遥远,以后见君恐怕是难上加难了,以此表达歌妓对陈襄的依依不舍之情。词人借歌妓的柔情百转衬托自己对于友人离去的不舍。下片力求委婉含蓄,先写出送别之时的景物,在“飞絮落花”这透出无限感伤的时节,“欲棹小舟寻旧事”,为眼前的愁情添上一笔难以言说的悲伤情绪,最终还是“无处问,水连天”,眼前只有水天连成一线,却无人能回答往昔之事在何处可以寻觅。在融情于景中,词人对于友人离去的黯然神伤的情状及对友人的恋恋不舍让读者感同身受。诸如此类柔婉蕴藉的词作还有《少年游》(去年相送)、《菩萨蛮》[11]81(秋雨湖上萧萧雨)等。
这不等于苏轼此时期的词作就仅仅在传统婉约词的写法里游弋,在“清丽舒徐,高出人表”中营造一个淡雅清新的意境以传递人生之苦涩是他倅杭词作的一大特色。试看《行香子》(过七里滩):
一叶舟轻,双桨鸿惊。水天清、影湛波平。鱼翻藻鉴,鹭点烟汀。过沙溪急,霜溪冷,月溪明。
重重似画,曲曲如屏。算当年、虚老严陵。君臣一梦,今古空名。但远山长,云山乱,晓山青。
词中以“鸿惊”“水清”“鱼翻”等意象在动静结合中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清淡澄明的风景,让人不禁惊叹七里滩风景之秀丽,为之流连忘返。词的下片续写山峰重叠曲折之秀美,让人感到东坡必是陶醉其中,可“虚老严陵。君臣一梦,今古空名”却给我们当头一棒。在如此美不胜收的风景中,词人发出这样的空叹的背后是“奋厉有当世志”[9]1411迟迟不能实现的无奈,以此虚无来劝慰自己。此外,《祝英台近》[11]26(挂轻帆)在“重重烟树”与“簇簇云山”中一轻舟在“急桨”中飞快地穿过钓鱼台,一人在醉眼弥松中“欹枕听鸣舻”中也一样,用词力求于清新中构造出一种水墨画般的淡雅意境,以其乐景写哀情,写出词人哀民生之多艰。词人只能在“谁念萦损襄王,何曾梦云雨”这样虚无的神话中寻找心灵的暂且宽慰。诸如此类还有《临江仙》[11]40(四大从来都遍满)、《昭君怨》[10]49(谁作桓伊三弄)及《虞美人》[11]67(湖山信是东南美)等。苏轼在这些词作中力求于以清丽的语言营造一个淡雅的意境,塑造出一个陷于人生悲哀的形象。
守杭时期,公已“参之孔、老,博辩无碍,浩然不见其涯也”[9]1422,“记取他年扶病,入西州”[11]616(《南歌子》古岸开青葑)的哀叹虽仍在心头,却以“独棹小舟归去,归去任烟波飘兀”的态度待之。此时期词作在取景上更加开阔,融情于景,浩然之气扑面而来。试看《八声甘州》(寄参廖子):
有情风、万里卷潮来,无情送潮归。问钱塘江上,西兴浦口,几度斜晖。不用思量今古,俯仰昔人非。谁似东坡老,白首忘机。
记取西湖西畔,正暮山好处,空翠烟霏。算诗人相得,如我与君稀。约他年、东还海道,愿谢公、雅志莫相违。西州路,不应回首,为我沾衣。
开篇钱塘江的潮起潮落以“万里”写出场面之壮阔,潮来潮去又以“有情”“无情”形容,实在写人世聚离无常,衬托出词人不忍与友人参廖子分别之情。一个“问”字引出在钱塘江口,斜阳照在渡口之上,此情此景不免让人悲从中来,将愁情更推上一层楼。其历史今古,多少往昔的人都在刹那间逝去,在这样浓得化不开的离别之情中,一句“谁似东坡老,白首忘机”以淡泊和旷达的心境暂且获得自我的宽慰和解脱。下片在万里烟波笼罩的青山的夕阳西下开阔美景中忆当年两人的情谊,以此为铺垫,写出两人亲密无间,要“愿谢公、雅志莫相违”而归隐。此外还有《南歌子》(古岸开青葑)的“更有明月千倾,一时留”以及《点绛唇》(莫唱阳关)的“北望平原,落日山衔半,孤帆远。我歌君乱。一送西飞雁”[11]628等词作于开阔的意境或写出别情,或写其旷达心境。
此外,守杭时期,“笑看潮来潮去,了生涯”的东坡在词中的情感较为沉稳内敛。例如,“禅心已断人间爱,只有平交在。笑论瓜葛一秤同”[11]663(《虞美人》归心正似三春草)的东坡将佛家的通透清明渗入其心灵深处,炽热情感已逝,剩下只有平常心对待世间的各种“瓜葛”。《点绛唇》(闲倚胡床)中寂静心态下的“闲倚胡床,庾公楼外峰千朵,与谁同坐。明月清风与我”[11]630;《好事近》(湖上雨晴时)于“照衰颜华发,醉中吹坠白纶巾”忧伤中“独棹小舟归去,任烟波飘兀”。这些阅尽人世沧桑后冲淡平和的词句可见东坡情感在经历仕途跌宕起伏后已趋于内敛沉稳,超然旷达的意境已成为东坡词的主旋律。
二、倅杭词与守杭词差异的成因
东坡杭州时期的前后差异,一方面有他的性格使然,王水照先生在《苏轼的人生思考和文化性格》一文中将苏轼的性格概括为“狂”“旷”“谐”“适”[13]93-96。另一方面,也有他宦海沉浮中思想嬗变的因素在其中。东坡在“孔、老异门,儒、释分宫。又于其间,禅律交攻。我见大海,有北南东。江河虽殊,其至则同”[10]1961(《祭龙井辩才文》)中完成了思想上的蜕变,成就了儒道释三家思想汇聚一身。应该说,在他的性格跟思想上,前人的研究颇丰,不需再赘述。王夫之《宋论》有云:“朋党之争,始于君子,而终不胜小人。害及宗社生民,不亡而不息,宋之有此也。”[14]86苏轼生于北宋中叶,庆历新政、熙宁变法、元祐更化等变法与党争贯穿生命的始终。因此,察其时代的因素是我们研究他杭州前后两个时期词风差异不容忽视的因素。
(一)变法与党争下的两难
庆历新政后,励精图治的意识成为统治阶级的共识。由此,大规模的变法运动——熙宁变法也拉开帷幕。这场由神宗支持,王安石为首的新党变法遭到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和苏轼等人的反对。苏轼从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到变科举兴学校再到利用进士考试反对王安石鼓励神宗的独断专任,同变法派的矛盾越来越大,遂遭到谏官谢景温诬奏苏轼于扶丧返川时于舟中贩卖其私盐,并追捕其艄公篙手等搜罗其“罪证”,然“穷治无所得”[9]1412,“公未尝一言自辩,乞外任而避之”。
元祐年间,高太后垂帘听政,启用司马光为首的旧党与苏轼等人。司马光为党人之私,尽废新法,苏轼为其新法益民之处而力辨之(如免役法),遂被“当轴者恨之”[9]1416。其次,苏轼草拟贬吕惠卿的诏书,反对以王安石配享神宗,倡以富弼配享神宗,遭其新党攻讦不断。在新旧党争互相倾轧之时,以苏轼为首的蜀党与程颐为首的洛党也是相攻不止。程颐门人谏官朱光庭首开其端,于元祐元年弹劾苏轼《师仁祖之忠厚,法神考之励精》有诽谤仁宗、神宗之嫌,此乃策题之谤。由此开元祐党人依文字党同伐异,大兴文字狱之端绪。此外,蜀洛之争还在司马光的丧礼上因“礼”之不同引起争辩而失欢。再者,台谏王觌等人针对策题《两汉之政治》的二次策题之谤。苏轼最终以龙图阁学士知杭州而告终。
坡公缘何在熙、丰之争与元祐党争中会屡屡遭其排挤,最终以通判杭州与知杭州告终,其因在于政治主张与当政者的不同,这也是党争之根源所在,最终导致党争从政见之争到意气之争的演变。苏轼主张“法相因则事易成,事有渐则民不惊”[11]1010(《宋史·苏轼传》),即主渐变非骤变。同时,在处世上主人情论,也即礼本人情。“王安石服膺孟子,追求尧舜之治,主张‘法先王之政者,以谓当法其意而已’……但求‘知为之于此,不知求之于彼,而彼固已化矣’的理想境界。”[15]66程颐也主张“法先王,行尧舜之治”,但在处世上主“敬诚格物,以致天理”。[15]66司马光主张执政者要有超乎常人的道德责任心,做到“仁”“明”“武”,才能政通人和。[16]119应该说,苏轼与新党及旧党是政见之争多之,蜀党与洛党之争从政治到学术之争兼之。在此背景下,士人多有其分歧,不左袒即右袒之,势同水火。最终,士人为其政治理想,为其学术之见,势必结党分派,互相攻讦也在所难免。东坡政治之失意,实乃党争之下的必然结果。
(二)“论议争煌煌”下的畏祸心理
王夫之在《薑斋诗话》上曾说:“宋人欲骑两头马,欲搏忠直之名,又畏祸及,多作影子语,巧相弹射,然以此受祸者不少,既示人以可疑,则虽无谤,亦可加以罗织,观苏子瞻‘乌台诗案’,其远谪穷荒,诚自取之矣。”[17]130观宋一代,北宋中叶是一个亟待改革的时代,遂有庆丰新政、熙宁变法等改革运动。其时,恰逢儒学复兴之际,文人士大夫以其前所未有之热情参与时政,以解“三冗”之病,“欲搏忠直之名”。改革中逐渐形成的党争造成参与者不得不选边站队,以行扣权门之实,望能“搏忠直之名”,使得一党执政,另一党势必失势,尽遭贬谪。政策亦朝令夕改,其刚正不阿者,更是遭受两党夹击,一贬再贬,如东坡是也。而文学创作之价值取向势必打上党争之烙印,其不得意者哀人生之多艰,仕途之无望,遂成为文学创造一大主题。
自北宋初以来,文人士大夫的“开口揽时政,论议争煌煌”[18]35(欧阳修《镇阳读书》)的社会风气在熙、丰党争中得到进一步的强化。由此,士大夫“缘诗人之义,托事以讽”而“言必中当世之过”望能“庶几有补于国”[9]1414成为士大夫参政的重要手段。然士大夫如此“多作影子语,巧相弹射”势必造成殃及自身。其台谏在此其中起着推波助澜之作用,每每“既示人以可疑,则虽无谤,亦可加以罗织”,大兴文字狱,成为执政一党打击异己的中坚力量。“‘进奏院案’开了北宋以‘文字’排击政敌异党之先声,在熙宁以后的新旧党争中遂成定制。”[19]125元祐党争中,旧党之于新党,莫不是台谏首发其难,罗织其文字,大兴文字狱为执政者扫除异己便是例证。士大夫惧党祸如畏狼虎中多少有畏台谏如狼虎之意味。联想“《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二十,光之章曰:‘臣之不才,最出君臣下,先见不如吕诲,公直不如范纯仁、程颐,敢言不如苏轼、孔文仲,勇决不如范镇”[20]5339之言,而被司马光赞誉为“敢言”的苏轼却“未尝以一言自辩,乞外任避之”,细究其原因,多少与惧怕台谏罗织文字大兴文字狱有关。可见,台谏所兴的文字狱所造成“诗祸”灾难,在当时士大夫心中所存在的阴影而造成的畏祸心理势必日益加深。苏轼在元祐六年(1091)还朝时,与新太守林希告别之际,曾在《西江月》(昨夜扁舟口)中写到“只有湖山案……使君才气卷波澜,与把新诗判断”[11]675,就可见诗祸给苏轼心中造成的阴影可见一斑。
基于此,倅杭时期,东坡在党争中虽也畏祸,但此时的东坡处于仕途的上升期且涉世未深,遂想以退为进,通判杭州后望能“庶几有补于国”,却遭遇“平生所渐今不耻,坐看疲民更鞭箠”[1]325(《戏子由》)的境况。在此情况下,公虽“有不便于民者不敢言”,但“亦不敢漠视也”,“缘诗人之义,托事以讽”便成常事。心中的烦闷日积月累,以醉情山水或饮酒唱和排遣苦闷也就自然而然成为生活的主调。遂有《行香子》(一叶舟轻)、《点绛唇》(四大从来都遍满)等词作在抒发迷人风景中看似东坡已忘却仕途所带来的苦闷,却也无法掩盖仕途中理想与现实巨大落差之下仕隐两难的苦涩。守杭时期,东坡已过知天命的岁数,在经历“乌台诗案”后,体会到“托事以讽”而遭“风闻言事”的谏官为其政见而意气用事,肆意搜罗诗文诬奏下狱,差点断送自己性命的切身之痛。在谪居中“读释氏书,深悟实相,参之孔、老,博辩无碍”,望能摆脱仕途之低潮时的种种苦闷,最终在“小舟从此逝,江海寄馀生”[11]467(《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中力求达到“也无风雨也无晴”[11]356(《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的旷达之境。对此,东坡在元祐朝看到自己不容于各党(主要有新党、洛党、朔党)后既畏党祸又疲于党争,遂自请知杭州,这才有我们看到守杭时期虽有“不用悲秋,今年身健。还高宴,江村海甸,总作空花观”[11]625(《点绛唇》不用悲秋)的壮志未酬慨叹,但“明月清风我”《点绛唇》(闲倚胡床)及“谁似东坡老,白首忘机”却已然成为词创作的主调。
三、余论
苏轼在倅杭与守杭两个时期的词作为我们探讨苏轼的风格差异、心态转变等方面留下了宝贵的内容。但是,我们不能否认的是两个时期词作在某些方面有相同之处也自有其独特的价值所在。就其题材的多样性上来讲,两个时期不相上下,从咏史怀古、哲理到戏谑、咏怀再到友情、羁旅行役等,可谓两个时期都兼而有之。这足以说明苏轼自始至终在践行他“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的词学理论。从其别情词来看,既有我们上述所讲的不同,也有某些相同点。例如,从倅杭中《江城子》[11]78(翠娥羞黛却人看)中借歌妓的不舍反衬自己对友人的依依不舍道出自己与友人(陈述古)的深厚友情,到《南乡子》[11]85(回首乱山橫)中追送友人陈襄中反复渲染自己对友人离去的离愁别恨与真挚友情。元祐时期,从《渔家傲》[11]602(送客归来灯尽)中别去亲密友人的悲哀心绪与对友人的挂念到《点绛唇》[11]628(莫唱阳关)于杭州开阔秀丽的自然风光中对友人离去的难分难舍,所有的这些足以说明苏轼具有待人真诚的可贵品质。从词的风格看,苏轼虽被大多数人认为是有开豪放之功,但他的词作中也不乏有婉约词的佳作。倅杭时期,《江城子》[11]31(凤凰山下雨初晴)、《菩萨蛮》[11]76(娟娟缺月西南落)等;元祐时期,有《西江月》[11]657(小院朱阑几曲)、《木兰花令》[11]660(知君仙骨无寒暑)等。这些婉约词作既有对五代及柳永等人词的创作的借鉴,并具有超越前人之势。再有,苏词中人生如梦,唯有宇宙永存的意识可谓贯穿其始终。倅杭时期的《清平调》(陌上花开蝴蝶飞)从“江山犹是昔人非”[11]973到“但远山长,云山乱,晓山青”;守杭时期的“一送西飞雁”(《点绛唇》(莫唱阳关)、“不用思量今古,俯仰昔人非”等便是例证。
从苏轼的倅杭与守杭的异与同可以看出苏轼的“变”与“不变”。其异为我们刻画苏轼从词的风格、意境到思想等方面的变化历程;其同为我们发掘哪些是苏轼一生从未舍弃伴随左右,及其词中哪些思想贯穿其始终。